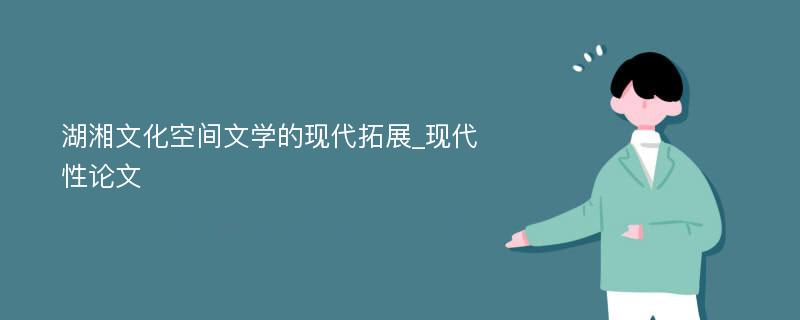
湖湘文化空间文学的现代性扩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文化论文,空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发生的语境不可能是“均质”的,由于被接受的文化空间不同,现代性与各个文化群落相互作用的方式迥然有别,从而带来了各个文化空间文学现代性体验和思考的不同向度。于世界之中国如此,于中国之湖湘亦如此。20世纪湖南文学的现代性想象是在湖湘地域文化、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想象和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它所呈现的启蒙叙事下的“自在民间”、祛魅时代的“巫楚世界”和现代文明之外的“世外桃源”等湖湘文化空间独有的文学现代性体验和思考,是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和扩拓。
一、启蒙叙事下的“自在民间”
在20世纪,湘楚区域文化始终处在国家主体文化的侵蚀和同化过程中,湖南乡土文学产生于中国社会现代化总体诉求的背景之下,再加上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之精神在湖南作家身上打下烙印,启蒙主义立场是其必然选择;在文化心态上,则存在着一种鲜明的政治情结,表现出对政治事件、国家决策的积极回应。但另者,湖南作家强烈的乡土情结和地域意识,使他们在面临城乡矛盾、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主流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冲突时,往往选择一种“乡下人”立场,自觉不自觉地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逃逸出来,表现出独异于时代主流话语的“边缘精神”,采用民间视角,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的显形文本结构下,往往还拓展出一个隐性民间文化结构,使湖南乡土文学启蒙现代性的主流叙事当中独有一种审美现代性体验: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了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①
周立波是一个典型个案。可以说,周立波的创作始终在自觉追随主流意识形态,按照政治的规范和要求展开对乡村世界的民间想象,在作品中构建乡村现实秩序,如《禾场上》、《山那面人家》、《山乡巨变》等作品。然而在其中,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作品一方面呼应着主流意识形态对私有制的批判,潜在层面又包含着对乡土民间的认同。如《山乡巨变》写农村中推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应该是充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但周立波却把一场政治运动放在民间生活舞台上演出,回避了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表达,有意无意把它们还原成充满人情的自然、醇美与和谐的民间仪式、民间习俗和信仰。如写副社长谢庆元自杀事件,本可渲染成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大家却在热烈讨论是否遇见水莽藤鬼,作者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充满民间文化的趣味。作品中“算八字”、“捉怪”、“寻短见”与“奔丧”等湖南益阳地区至今都随处可见的民俗文化,以其强大的娱乐性、趣味性和传统惯性,潜在地对严峻急切的政治和阶级斗争空间构成消解。因不时被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和作家特有的的审美趣味所干扰,使作品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的叙述视点发生游移,这种游移影响主题的完整一致,但却使小说有了鲜明的个性,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和“茶籽花”般芬芳秀美的民间气质。
在对韩少功乡土小说创作的线性追踪中我们也不难看到,韩少功这位早年站在政治启蒙立场上的知识分子,一度试图以小说创作来实现其启蒙农民、改造农民的现实主义作家,在经历了历史文化的寻根之后,却从启蒙农民逐渐走向了与乡村中的农民的某种认同。如在《马桥词典》中,一方面我们还是能看到韩少功的启蒙情怀,如对国民集体无意识的揭示与批判,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如“汉奸”一条中,作者用盐早一家的遭遇控诉了极左政治对基本人性的压抑与扼杀;“宝气”一条则揭露了农村基层干部欺软怕硬的德性,等等。不过,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图景虽然大主题未脱离时代合唱,但在乡村叙事的层面上却夹杂着丰富的信息:如“话份”对乡间秩序的规范,“乱伦”显示出的民间原始生命力,迷信观念对民间道德的维护,(宗族)械斗显示的为宗族利益而不惜牺牲自我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的气节,等等。马桥的民间生活藏污纳垢,但由于作者站在民间文化的视角,使他透过这些表面的封闭、愚昧和残忍,看到了丰富、复杂的民间生活形态,以及其中一种民间自在的精神。
在《暗示》这部作品作者对自在乡间的认同表现得更为突出。《暗示》中的太平墟和马桥一样是一个悠然自足的独立世界,如同沈从文的湘西,是一个保留着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保留着朴野的乡村情愫的精神归宿地。在太平墟生活的乡民们有着质朴的情愫和美好的人性,如武妹子忠诚、仗义,汉寅爹机智、善良,赣三爹热情、聪慧等等;即使是到城里去当具有特殊涵义的“小姐”雨香,作者也是站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上去肯定人物身上的种种美质。韩少功显然是认同乡民们对雨香的道德评价的;不仅如此,他还把雨香摆在城市和乡村道德的天平上,以乡村道德的自然、率真性来反衬城市道德的虚伪性。
乡土民间“是在国家权利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发生的,保持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②。在启蒙话语受到一定的挫折和都市文化的挤压时,在面对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异化时,在湖南乡土作家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感性状态下的浑然乡村世界,一个审美的世界,一个与主流文化立场不同的自在民间;而这一文化空间的存在,为中国现代性增添了异彩。
二、祛魅时代的“巫楚世界”
20世纪的时代主流精神是祛魅,湖南乡土文学作家的现代教育背景及近代湖湘文化赋予他们的经世致用精神,理应使他们成为科学主义的追寻者。但事实上,湖南乡土文学在“神的解体时代”却屡屡呈现出一种与20世纪中心主题反向运动的含魅趋势,在其作品中始终存在一个神秘而诱人的“巫楚世界”,这一点尤以30年代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80年代中期以来的湖南寻根作品为盛。湖南乡土文学对自然的迷魅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楚文化的那种“生命一体化、万物有灵”的观念,借助各类遗存至今的祭祀活动和日常生活习俗,以及近巫文学的潜移默化,绵延至今,巫楚文化对自然的敬畏、对人自身能力极限的谦卑的自知,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它深深根植在湖南乡土作家的血脉之中,影响其世界观、生命观和文学观,成为他们表达生命、感悟乡土、认识世界的一种特色表述。
在这个“巫楚世界”中随处可见对神巫作法、显灵的事迹,以及民众的虔诚迷信的描写。如沈从文的《哨兵》写凤凰军人信巫好鬼的执迷,他们不怕死,不怕血,唯独敬畏鬼神,写边城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听命于神巫;蔡测海的《船的殒落》写善贞娘娘的刺绣手艺之神,写善贞娘娘由一个枯朽的老太婆突然变成青春美丽的少女,写善贞娘娘越是吃毒药毒物越是通体透亮,越是诱人;《楚傩巴猜想》写酋长向王大力借头,王大力的头滚出一码多远还在说,请大王笑纳,其无头之躯还要走到家里把用头换地的契纸送给亲娘;韩少功的《老梦》写农场里请人“照油碗”,可道出窃犯所在方向和大致模样;等等。
在上述作品中作家们对日常生活中某些无从解释的自然或生命现象是在做原生态式的叙述,叙述人对世界本身的含魅性处于一种默认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湖南乡土的含魅意向的形成的另一种来源是将已知现象或事物迷魅化。如孙健忠的《猖鬼》写了一个年青美貌女子甜儿被猖鬼纠缠之事,其实是年轻女子因性压抑过度导致的精神病态,病理学上称为“花痴”。蔡测海的《鼓里——古里》中写的灵魂被洞里的妖精拿去的“落洞女人”既是此类,沈从文也有过此类描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亦对现实世界有意进行含魅处理。如“枫鬼”的传说,马桥的两棵枫树山火后居然枝叶都不损分毫;马鸣画过这两棵树以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取树木雕成木鱼以祈神消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枫树最终被公社砍走打排椅,结果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枫癣”症,这是马桥的枫鬼闹的——报复砍伐它的凶手。这类传说是可以做出科学解释的,如皮肤过敏症之类;但作者并未对此做出理性的辨别、质疑和科学的提示,而是表现出一种不仅仅是审美意义上的默认:自然界的植物也具有神性,而一切有神性的东西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否则侵犯者就会受到报复。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看到人们对尊重一切生命的呼吁。
现代性主流推崇和强调理性、去除宗教和神魅;然而现代性是把双刃剑,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扩张在创造丰富物质文明和取得巨大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而巫楚文化对于自然的原始而淳朴的态度,和现代生态理论的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自然本身不可忽视的生命主体性。巫楚文化中弥足珍贵的生态智慧惠泽湘人,使湖南作家在反观现代文明的暴力及人性的异化时,能借助对“神巫之事”“神秘”的描述,以展示世界的含魅性,营造出神奇的、独特的、有意义的生命世界,在以科学主义为主潮的中国现代性叙事之外生发出独具魅力的风景。
三、现代文明之外的“世外桃源”
20世纪湖南乡土作家差不多都可以称得上是风俗画作家。不管是沈从文类的抒情派,还是周立波类的写实派,虽艺术风格各有不同,但都得山水自然之灵,表现出对湖湘大地的热切关注,对自然风光的尽情描绘,在他们笔下常常可以看见一个清澈明丽、不受任何污染、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外桃源”。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纯美的潇水,彭见明《那山、那人、那狗》中的秀美山村,古华的《爬满青膝的木屋》中的偏僻而美丽的雾界山林……即算是写实派作家周立波也表现出风俗画描写的热情:在建国之初文学作品的风景描写多被“社会化”、“政治化”,成了一种社会景观的时候,周立波笔下的太阳的光彩、迷离的月色、阳雀子(喜雀)、温暖的茶子花、淅沥的春雨、嫩绿的秧苗,资水上下、洞庭湖畔随处可见的南国春景仍给我们带来似乎远离政治风雨的自然美。新时期初当伤痕、反思小说在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很多乡土小说家因而更加注重思想深度,但往往忽略了风景画和风俗画描写时,古华的《芙蓉镇》却能“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画面”,“芙蓉镇”“湖塘中水芙蓉竞开,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美景和风俗民情令人神往。
在湖南乡土作家的“桃花源”世界里,他们在对田园自然尽情讴歌的同时,还塑造了一系列与自然相融相契、浑然合一的“自然之子”。如沈从文《边城》中“在风日里长养着”、“自然既长养她也教育她”的翠翠,《雨后》中山野采蕨之余情欲之花自由绽放的四狗和阿姐,叶蔚林《山里的女人》中毫无礼防伦常概念的莫妮,孙健忠的《舍巴日》中在情爱的追求上主动出击的“岩耳”,还有古华小说中一系列美丽性感、朴质果断的女性如《“九十九堆”礼俗》中的杨梅姐、《相思树女子客店》中的观音姐,《蒲叶溪磨坊》里的赵玉枝等,都是湖南乡土作家所向往的优美、健康、自然、合理的自然人性和生命形态的体现。
湖南乡土作家有一种自发而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血脉中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朴原始、神奇浪漫的湘楚文化的眷恋山水、崇情尚性的基因。但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文化精神赋予20世纪湖南文学的政治性品格,使得20世纪的湖南乡土作家对自然的关注一度局限于从启蒙的角度来透视国人精神的痼疾,影响他们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入开掘,表现出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在乡土中的冲突、纠结。
直至90年代以来,湖南作家得益于远古巫楚生态智慧的朴素生态意识逐步通过现代转换、得到升华,表现出自觉的生态情怀。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即是典型。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作为一个乡居者,不再局限于政治的对峙、文化的对撞、城乡的对立等格局中进行乡土叙事,而是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思索人生存的模式与状态。在融入“山南水北”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中,他表现出对自然、生命的普遍尊重和对人类精神生态的关注。人与自然自在的本真生存与和谐相处,是现代社会几乎已经完全失落了的东西,因此也成为生态美学试图使之失而复得的理想,但韩少功发现它却是八溪峒山南水北之间的原生生态:清晨唧喳不停的鸟声,从寂静中升浮起来的虫鸣和蝉噪,禾苗上溪流上飘摇跳动的月光;山里人买板栗“论摇”的商品交易,农妇之间的瓜菜外交,山民们月下的狂欢和乱相迭出的笑……各种原生态的细节构成了“山南水北”间人和自然的和谐家园。
在全球化进程中,湖南作家基于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种种困惑,越来越多地把深情的目光投向未被现代文明所浸染的自由而充满活性的生态世界,及其中自在生存的自然、健全的生命本性,这个“世外桃源”在现代城市文明之外有其自身的自我协调机制,它让我们看到了自由舒展的现代人生境界得以发展的另一种空间之拓展。而正因为如此,湖南乡土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获得了全新的现代性品格。
注释:
①陈思和: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37页。
②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2页。
标签:现代性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湖湘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乡土论文; 韩少功论文; 沈从文论文; 周立波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