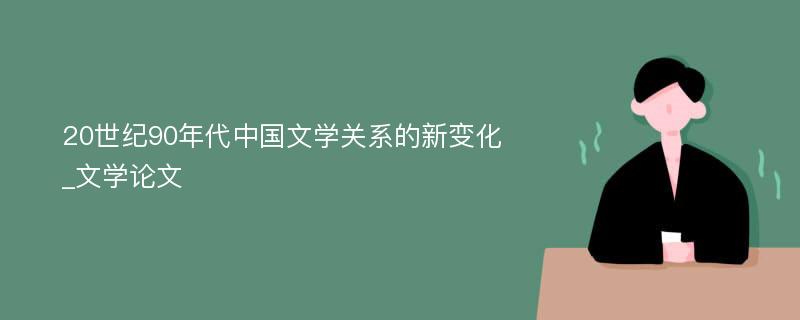
90年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新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年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的中国文学关系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90年代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既是批评家们所关心的,同时也是困扰今天文学批评的主要问题之一。我注意到批评家们在评价80年代中国文学时,很少有大的意见分歧,而一旦涉及到对90年代中国文学的评价,批评家之间的分歧明显增大,甚至是在那些对90年代文学持肯定态度的批评家之间,因肯定对象的不同,评价差异也非常大。一些人认为,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标志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回潮。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最能代表90年代中国文学进展的,是一批新作家新作品的产生。而一些批评家对90年代新出现的所谓“新生代”作家、“60年代”作家及“70年代”作家的作品根本不屑,他们所肯定的主要是那些老三届出身的知青作家以及更年轻的先锋派作家在90年代的创作。撇开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不谈,在我看来,90年代的中国文学就其所体现的文学关系而言,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以作家—作品为主而展开的文学关系;另一种是以作家—读者关系为主所展开的文学关系。尤其是后一种文学关系,反映出90年代中国文学关系的新变化。
一
所谓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关系,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为普遍的文学写作关系。这种文学关系表现为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进行创作,进而形成文学作品。在这种文学关系中,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主要是呈现个性,可以说,越是有个性的作品,越是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而所谓以作家—读者为主体的文学关系,主要体现为作家是根据读者的阅读需要来选择自己的创作。作家在写作时,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独特发现,而是考虑阅读市场的需求关系,如,读者关心什么,什么类型的作品容易获得社会的响应等等。即便是具有很强创造力的作家,在创作时也不仅仅是沉浸在自己的独创之中,而是要考虑如何使自己能够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并为他们所接受。对于前一种文学关系,即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关系,可以说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写作关系,同样也构成了一种读者阅读关系。作家在这种文学关系之下进行写作,几乎很少顾及包括读者在内的影响因素,对于作家来说,在这样的写作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对生活和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发掘和传递出来,用最富有独创性的声音向外界宣布自己的发现。读者作为一个文学因素,在这样的文学关系中,似乎是自明的,只要作家有独创性,只要作品本身具有感人的力量,读者不用说自动就会接受作家作品。这样的写作状况和文学接受状况,在8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是表现得相当充分的。那时的作家表面上看似乎非常重视外界对文学的要求,甚至不惜提出文学要“干预生活”的口号,让作家根据民众的意愿,在写作中扮演社会道德的代言人角色,但实际上对于80年代的作家而言,在进入具体的文学写作状态时,所面临的文学关系是相当纯粹的,或者说是非常单纯的,在文学和非文学的关系上,作家在写作时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区分,那就是只要是听命于自己的内心要求,只要是来自于作家自己深切的生命感受,这样的东西总是属于文学的,而那些作为任务被接受的写作,特别是在当时被当作政治任务交代下来的写作,很轻易地就被视为非文学的写作。至于读者的影响,对于作家具体创作活动而言,几乎很少有直接的制约作用。所谓很少有直接的制约作用,是指作家在进入到一种创造活动状态时,都是力求尽可能地排除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包括读者的影响在内,而力求将自己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80年代那些被称得上是文学关系的东西,差不多都围绕作家这一活动主体展开,是由作家决定并由作家召唤而来的。作家—作品是所有文学关系中的主体,至于那些在创作中起一定作用的因素,譬如读者因素,一般都被视为文学的外在因素。而事实上在80年代的文学关系中,读者因素在整个文学关系中的确还没有像90年代这样产生强大的影响。那些受到读者阅读期待支配的作家创作,在80年代虽然也有,但读者的影响对这些作家创作而言,并不是作为一种必然的约束关系支配着作家的创作,而是完全取决于作家个人的态度。作家可以在自己的创作中考虑读者的要求,但也可以不考虑读者的要求。换句话说,读者因素还没有成为一种作家创作必须考虑的因素。譬如,柯云路的《新星》在80年代被很多批评家视为是一种政治畅销小说,因为它是根据读者的某种期待要求而构造出来的乌托邦,作家在构造这一乌托邦的过程中,关注的是如何将读者的情绪煽动起来,至于小说是不是独创并不重要,所以,在《新星》这样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作家用以煽情的东西,主要都是那些支配现实生活的宏大政治事件,作家在创作作品时就像是在发表施政演说似的,尽可能对那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一一给予解答,以满足那些长期生活在权慑体制下的读者对政治问题的兴趣。但即便是这样的一种受制于读者影响关系的文学创作,与90年代的文学关系相比,前一种文学关系所体现的读者阅读期待对文学的影响关系,依然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因为在80年代,作家在创作时即便考虑到用煽情的手法来扩大文学的影响力,但这种考虑还仅仅是属于文学表现技巧,或者说,还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整个文学关系中唱主角的,依然是作家—作品关系。是作家在调动读者及相关的文学关系,而不是读者以及代表读者阅读需求的文学市场在调动文学关系。尽管80年代在理论上已经介绍国外的接受美学理论,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而已,作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实关系,读者对文学的影响关系并没有进入到一种全面的辐射状态。
90年代的中国文学尽管还延续着80年代的诸多文学关系,但读者进入文学关系这一事实,实际上正极大地改变着中国文学的现实关系。甚至可以说,整个90年代的文学关系的变化,都是围绕读者进入文学关系这一关系而展开的。不错,90年代中国现实生活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特别是经济生活走向开放型市场经济,使得原来意义上的社会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对于文学而言,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进入到文学领域,换句话说,那些在题材上反映经济改革,以为写一些现实正在发生的事件的作品,就是代表90年代中国文学的方式。其实,这种文学反映方式不足以构成新的文学关系,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学基础,其实还是80年代那种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关系。这种文学关系说到底,还是依托于一种较为封闭,因而也显得较为单一和稳定的社会关系。所以,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上,80年代的文学还是较容易把握。90年代文学关系相比之下,显然就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首先就是文学关系的复杂。我们几乎很难在现实的文学关系中轻易辨别出哪些是属于文学的,而哪些又是非文学的。譬如,像苏童这样在80年代后期被视为很文学的先锋作家,在90年代的文学关系中,就很难简单地说他的创作是一种纯文学的写作。再譬如,像金庸这样的创作方式,从一开始就有很浓烈的商业色彩,但到了90年代后期,批评界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方式。另外,像贾平凹、莫言、张炜这些80年代出道的作家,尽管在今天许多批评家眼中他们还是80年代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但从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丰乳肥臀》、《红树林》和张炜的家族史的写作来看,其中题材的选择和表达方式的变化,都带有90年代文学关系的影响痕迹。如,性和暴力的主题成为这些作家创作题材的一部分。这种变化,说明90年代的文学关系有着80年代文学关系中所没有的东西,或者说,90年代社会生活的变革,对文学关系的影响已经形成,这种变化我认为不是通过90年代生活题材的直接进入文本来实现的,而主要是通过以读者为核心的文化市场的影响关系来实现的。
二
那么,为什么说,90年代文学关系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读者进入到文学活动领域来实现的呢?在我看来,读者因素进入文学写作关系中,使得作家的写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以往那种不考虑读者因素,或者读者因素很少对作家创作发生影响的文学关系中,文学创作纯粹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存在着的。作家写作和读者阅读都是希望从文学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对作家而言,文学活动与他个人的生存关系是分离的,作家有自己的一份职业,他不靠写作维持生计,哪怕是那些专业作家,也主要不是靠稿费来维持生计,而是从作家协会等机构领取工资来维持生活。当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时,他们习惯地以一种精神创造的使命来要求自己。因此,他们不惜一切地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之中。像一个作家花数年乃至一生心血创作一部作品这样的事例,在以往的文学写作中并不是罕见的。而90年代随着读者因素全面进入到文学关系之后,文学活动由原来的作家决定一切,改变为读者决定一切。再好的作品,再有独创性的作家,一旦失去了读者市场,或者缺乏读者市场的竞争力,都有可能失去生存的基础。形成这种影响关系的原因之一,是90年代作家的生存条件直接与他作品的市场竞争力结合在一起。不管人们称90年代作家的写作是商业写作也好,或是其他写作也好,总之,90年代作家的写作必须面临市场的考验,即必须根据读者的阅读需求来选择自己的写作方式。所谓读者对文学活动的调节,当然并不是仅仅表现在作家创作时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要求,而是有更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我以为,主要是作家的整个写作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即90年代的作家一旦要进入到写作世界中去,他就必须面临着读者影响这一选择。作家在写作时会问自己,我是写给谁看的。80年代意义上的普通读者这一概念已经不复存在,90年代的读者被非常具体地划分出来:娱乐消遣型的读者、注重社会问题的读者、倾向于文体实验的读者,等等。当作家只有在明确自己的读者对象时,他的写作才有方向,许多题材、故事、人物、叙述、表现技巧等等,才有组合的可能。否则,即便有非常充实的艺术感受,作家也难于找到一种具体的把握形式,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知道自己该讲述给谁听。我注意到那些从80年代过来的作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90年代都面临着创作上的困惑,这种困惑并不是表现在作家个人对生活的感受缺乏,而是感受太饱满,感触太多,多到作家自己都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些内容,讲给谁听。我记得王安忆在90年代后期曾感叹过:10年前,自己“可真能写啊!信心那么充足和饱满。而如今却不同了,一切都变得很难起来。”“不是因为枯竭,更不是因为谨慎,倒是因为相反的情形。”(见王安忆《接近世纪初·序》)这的确道出了80年代过来的作家在面对90年代文学关系时的一种矛盾心情。该讲的故事在80年代,甚至更早些时候都已经讲过,再来讲这些东西谁听?当那些过去事件的经历者动情地讲述血泪斑斑的故事时,出乎意料的竟会遭到90年代新生代们的反感。历史的亲历者们呼唤着,让当年那些因冤屈而长眠在山林中的伐木者醒来时,新生代们说,让那些伐木者去死吧。而新生代们讲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人自己的成长故事时,同样遭来50年代和老三届前辈们的不理解。很难想象,这些读者可以统一在一种精神维度中。并且,也很难想象可以用一种价值判断的方式来否决任何一种读者类型的现实存在。我想,90年代作家在面对这样分裂的读者群体时,选择写作方式的参照,就是明确自己的读者。
如果说,90年代作家创作方式的选择受到读者市场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制约的话,那么,就90年代中国作家的实际生存状况而言,读者市场的潜在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几乎可以说,90年代维系作家生活的物质资源,已从原来的体制内的保障,逐步过渡到靠作家自己的写作来维持,稿费正成为维持作家生存和写作的必要条件,随之而起的自由撰稿人和个体书商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读者的需要,通过市场需求的形式反馈给作家。在这一反馈过程中,作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所谓自己的选择,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是作家可以放弃对读者市场的沟通,而采取一种封闭的写作方式。譬如, 在90年代仍然有不少作家维持原有的写作方式, 不管自己的作品能不能发表,也不管读者会不会接受自己的作品,反正这些作家不靠写作为生,有体制内的薪水保障。第二,是作家选择与读者市场配合的方式。与读者市场的沟通,当然不是作家与读者直接发生关系,而是通过出版商这一中间渠道,将作家的作品推向读者市场。出版商根据读者市场行情来物色作家作品,作家则根据出版商的需要来写作。这样的文学写作方式,可能对不少80年代过来的作家来说,不太适应,但这样的文学关系在90年代中国文学活动中的确是建立起来了。撇开对这种文学关系的价值评价,就这种文学关系的具体特征而言,我以为至少使得90年代的中国文学结构,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面向读者市场的作家写作,效率和写作速度成为一种必要的制约力。对于90年代的作家而言,遥遥无期的创作积累和构思,正在成为过去。对速度和写作效率的讲究,不是说一定会带来写作上的粗制滥造,事实上,80年代有些作家的写作速度也是相当惊人的。但只有在90年代,对差不多所有作家的写作来说,速度才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不仅出版和发行有时效的限制,就是读者的阅读也有时间性。对于日益发达的文化出版产业和以高科技为依托的传媒而言,不讲效率,不受时间限制的文学写作,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同样,对90年代的各类读者来说,阅读的兴趣居然可以不受时间的规范,而一劳永逸地倘佯在那种所谓审美世界的想法,在90年代大概也已成为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在这种背景下,作家的写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你的写作要进入读者市场,并且连续在这种市场竞争中获得自己的空间,那么,你就必须不断将自己的感受转化为文字,成为出版。作家在这种状态下写作,犹如演员的即兴表演,看你在转瞬之间能不能迅速释放出最大的艺术能量。这种现象在90年代的文学写作中其实是并不少见的。譬如,一些贴着后现代标签出台的作品,在理论上提出平面化和各种艺术拼贴的主张。这些理论实际上倒是反映出了90年代文学写作的真实状况。在一个快速旋转的时代,沉思和深度的探索的确变得非常艰难。为了适应这种不断增长的快节奏生活,印象式的平面俯掠和利用现有的资源快速拼接,不能不说是效率原则下的产物。
90年代作家写作的空间面临着全方位的开放。所谓全方位的开放,是指作家的写作不只是限定在完成书稿这样一个文字维度中,而且还面临着多重维度展开作品的可能。可以说,仅仅满足于将自己的作品变成文字出版的作家,在90年代已经不多了,尤其是90年代后期以来,差不多所有当代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在把自己的作品改写成电视剧和电影底本,或者说,在他们构思文学作品时,已经同时考虑在影视领域展示作品的可能性。文学与影视的结合已经成为90年代文学关系中的突出现象。虽然,在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写作中,影视剧的改编几乎很少有成功的先例,但在世界范围中来考察,很难说,这种展示作品的方式就一定没有出路。假如中国的文化市场能够进一步研究,传媒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弱化,那么,影视剧作为展示作家文学世界的一个通道不是没有可能的。
90年代面向读者市场的写作,改变着文学的现实秩序。出生策划成为改变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要手段。诸如“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作家、“70年代”作家,等等文学概括方式,让许多研究者感到名称大于实际内容,或者说,是这些概念本身对所指的作家作品缺乏严格的约束力。这种靠制造名词概念来推出作品的方式,在90年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并不新鲜的现象。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面向读者市场的90年代文学关系的运动方式。可以这样说,这些名词概念并不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的。制造这些名词概念的人,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出某一些作家作品。如果不制造这些富有刺激性的名词概念,就无法在既存的文学秩序中获得他们的生存空间。事实上,90年代一些所谓新作家在文坛的露脸,大都经过了杂志和出版商的策划。我们对90年代新出现的一批作家作品,经常是先知道有一个什么名称,然后再去寻找他们的作品。反过来讲,这正反映出策划正越来越深地影响着90年代的文学发展。
三
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80年代的文学关系虽然还在发挥自己的影响,但90年代逐渐兴起的面向读者市场的文学写作,正在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力。作为一种正在形成之中的文学关系,我以为现在要对它作出价值判断,还为时过早。主要还是看这种文学关系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能否产生出成熟的作家作品。
199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