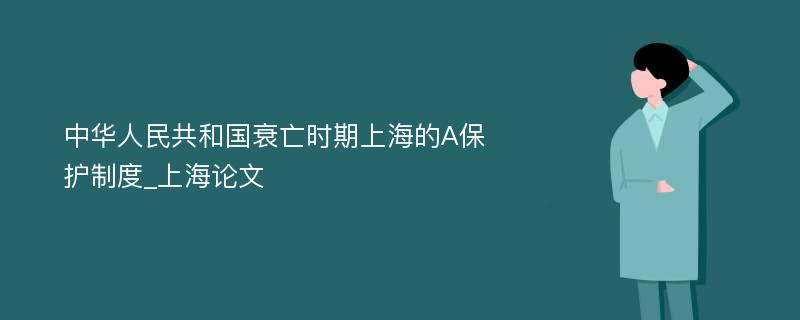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甲论文,上海论文,时期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甲制度在中国曾是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方式,上海开埠前实行过保甲制度,不过到清末已经名存实亡。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时期的上海,保甲制度在这座充满近代气息的都市社会里复活。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去探讨这样一些问题:40年代上海保甲制度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它在战时上海的有效性如何?它只能是战时的非常措施,还是可以作为常规的控制机制?它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抑或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的政治空间?
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保甲的基本功能为户籍管理。上海地区实行保甲法始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其法以10户立一牌头,10牌立一甲头,10甲设一保长,每户给予印牌,上写姓名丁口,入户出户均须注明所来所往,寺观客店概无例外[①a]。
在管理户籍的基本功能之上,保甲内实行联保连坐,一般以5户为单位,相互担保不为非法,或互相举报违法行为。保甲长按此催纳赋税,差遣徭役,掌管保甲内兵器,非丁不能动用。保丁除依法服役外,还发挥着乡里自卫的作用。可以说,传统的保甲组织是由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它具有行政、役法、保安三位一体的功能。
上海沦陷时期的保甲制度也执行着传统保甲组织的职能,组成方式亦颇似传统。日伪时期先后存在的三个上海地方伪政权[①b],都在其建立初始就着手制订保甲实施办法,推行保甲制度,规定清查户口、编组保甲为实施保甲制度的第一要旨[②b]。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10户为甲,甲设甲长;10甲为保,保设保长。寺庙、船户及公共处所等以保为单位。保甲编组完成以后,户口的登记、更动、清查均由户开始逐级上报,直至区长,保甲便成为遍布社会基层的户籍控制网络。
战时上海的保甲与传统保甲组织相似的另几项职能是:其一,必须负责基层社会的治安,组织男丁服役。汪伪行政院1943年4月2日颁布的《编查保甲户口暂行条例》中规定,保甲内必须办理联保连坐;保甲长须率领壮丁队,协助军警警戒,追捕违法者,紧急的并有先为逮捕之紧急处分权;保甲长还须教诫居民毋为非法事项,可对其中之屡教不改者施以罚款等处分。市府依此颁布《各区自警团组织暂行办法及团员服务暂行规则》,指令各区从速组织自警团,确定该组织负有协助军警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其各级首领均由坊镇长、联保长、乡长、保长、甲长依次兼任[③b]。其二,按户征收各类捐税。日伪统治时期,上海地区征收的赋税达60余项[④b],其中经过保甲按户征收的就有田赋、保安税、军警米、献机捐等大宗赋税。此外,保甲长还要挨户征收保甲费[⑤b]。其三,办理计口授粮和其他属于统制经济范围内的日常所需物品的配给管理事宜。
在因袭传统方面,战时上海的保甲组织与同时期在乡村中实行的保甲制度也有相似之处。作为乡村基层控制的唯一机构,民国时期的保甲制“仍沿以往以户为单位之政策”,“十家一束、十家一束地把各户编制起来。为的是以五家联保连坐的办法,肃清奸匪,平靖地方”[⑥b]。到了战时,乡村保甲的主要责任也在执行政府“战时功令”,其中最为艰巨者“为征兵与募集救国公债”[⑦b],与传统保甲抽丁催赋的功能异曲同工。
从外在的组织形式和功能结构看,40年代的上海保甲制度与传统的和乡村的保甲确乎没有什么区别。那么,能不能因此而断言,传统的保甲制度具有超越时空的功效,可以适用于上海这样的现代大城市呢?
上海编组保甲过程中遇到的阻碍首先提供了否定的答案。1938年9月,督办上海市政公署已着手编组保甲,将是项工作交由各区政务署第二科主管[①c]。尽管政府三令五申,编制工作推进缓慢。1942年2月18日,市府基于编制保甲工作“爰经两年多策动,未能全境完竣者尚属多数”,发出“催促各区公署迅速办理保甲的训令”[②c]。次年3月,市府再次为推进保甲制度特设保甲委员会。而上海全市编制保甲的大致完成,延宕到了1943年下半年。编组保甲的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上海城市政治空间的割裂性。“孤岛”时期,上海的政治格局是“三家”(日伪市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两方”(中方、外方),日伪市府不可能在其辖区以外编制保甲。“孤岛”沦陷以后一年多时间,两租界的原有社会控制系统仍有惯性。保甲的编制还不断遇到所谓“以前英美人统治时遗下之不良习惯的阻挠”,原租界辖区依然“各自为政”。市保甲委员会不得不每半月或一月召集原租界辖区会议,以便“保持全市保甲行政采取一致步骤”,实现“保甲一元化”[③c]。
第二,战时上海异常频繁的人口流动加剧了邻里空间结构的不稳定性,邻里间难以形成公共利益和认同,从而妨碍了保甲组织的进展。整个抗战时期,上海人口流动始终处于巅峰状态,既有大批上海人随企业、学校、机关等内迁后方,更有大量四方外乡人涌入上海避难。入大于出的人口压力加剧了本已严重的房荒问题,左邻右舍非但经常变换面孔,而且饱和的空间还要不断地再分割。时人记叙:“二房东别出心裁,迭床架屋,当小客栈一样方式租借给人,有了二层阁、三层阁的房客不算,阁楼上还要借铺场给人,早出晚归。甚至露台上盖几张马口铁,搭一个棚,也可召租。”[④c]如此的社会情境与严密的靠户籍控制的保甲制度显然产生抵触,市府也不得不承认:“办理保甲,尤其是办理联保切结一项,因城市地区居民复杂,且流动频繁,而实际上发生困难。”因此,市府只能采取牵制房东的办法,“责令房东督促新旧租户一律取具保妥,否则惟租主是问”[⑤c]。
第三,下层社会势力的对抗以及上海社会阶层的杂错,阻滞了保甲组织在上海全市协调一致地推展,而呈现出明显的地段差异。在租界与华界交界的地段和下层民众聚居的棚户区,编制保甲尤为困难。1942至1943年期间,市府和市警察局保甲处不断收到沪西棚户区、闸北棚户区以及贫民聚居的南市新市街地区、蓬莱、邑庙等地区的报告,反映这些地区或因“地瘠民贫,颇少人才”,有许多无正当职业者充任保长,以至保甲编组极为混乱[①d];或因“棚户林立,良莠不齐,倘不严厉彻查,难免宵小混迹”,故不能按期完成保甲[②d]。如果说,租界编制保甲的阻力主要来自行政权力的抵御及原有控制机制的惯性,那么下层地段的主要困难则在于那里的居民素质及游民习性的自然抗衡。
如上三种社会空间情境在世代家族聚居的闭塞的乡村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建筑于村落家族邻里基础上的保甲组织当然不能与此适应。然而,矛盾也在于此: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日伪地方政权必须仿照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使基层社会完全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非此便不能有效地控制这座大都市。传统的保甲制度最适合日伪政权的需求之处,主要就是依靠最接近的社会空间——邻里之间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因此,40年代上海保甲户籍管理中最受重视的一项便是联保连坐,即邻里互相担保不发生“越轨”行为,一旦发现,立即举报,如有隐匿,株连联保各户。上海市警察局于1938年7月印发2万张“人民连坐保结”,通令各分局从速办理,首先在华界辖区内实施联保连坐[③d]。1943年4月2日,汪伪行政院颁发的《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中,更规定了联保连坐的具体办法,市府于同月26日饬令市警察局、沪西警察局、各区公署、保甲委会员遵照办理,将此覆盖到上海全市[④d]。但如前所述,战时的上海社会是流动的而非稳定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分割的而非统一的,是多层的而非一体的,邻里间并不能遵循某种约定来保证政府需要的秩序。
那么,沦陷时期的上海又是依赖哪些因素来消除时空错位的矛盾,恢复传统的保甲制度呢?
二、在非常与常规之间
40年代传统保甲制度在上海的复活,其支撑因素是战争环境。在战时,无论统治的一方是战争的发动者还是抵抗者,也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总要采取非常措施,实行战时体制。汪伪国民政府则借助于这一时机,在华中沦陷区实行了带有掠夺性质的统制经济,运用政权的力量,依靠军队、警察乃至各级行政机构,通过各种行政命令,对社会经济实行干预。上海市社会局1942年1月呈报各区的物资统制情形中列出涉及民生的统制物品计31种,其中包括粮食、棉花、火柴、肥皂、禽蛋等人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①e]。在统制经济之外,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要受到政府干预。例如,市府明令严格限制饭馆、酒肆、舞场的营业时间,甚至连弄堂小贩的营业也要受到限制。市府还对市民婚丧宴会限定规格,具体到了哪种菜肴不可以上席[②e]。这样,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被纳入了统制经济的轨道。
但是,仅仅依靠国家机器和政府机构是不可能使社会基层的芸芸众生就范的,传统的保甲提示了控制基层的可能,因为建筑在户籍管理基础上的基层控制可以渗透到人们生活最基本的方面。这里最为关键的一环是户口米的供应方式的改变。1942年7月以前,日伪市府下属的上海市粮食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在各自辖区内设立公粜处,各户直接到所属公粜处购米[③e],按户授粮。此时,保甲的作用仅限于提供户口调查表副本作为各户登记授粮的依据,实际授粮之多寡掌握在公粜处手中,且“市民列队购米,秩序殊难维持,稽查亦属不便”[④e]。有鉴于此,市府从7月起逐步在全市实行计口授粮并划分大口小口不同的配给标准[⑤e]。这一方式大大强化了保甲组织的作用,因为需要运用保甲组织先行清查户口,以联保为单位印发户口调查表,由甲长挨户清查,确定人数及大口小口,填入户口清册,然后将清册转送保长汇制全保户口统计表,送由联保长报至粮食管理局,以此作为购粮之基本依据[⑥e]。这样,一方面转移了公粜处的一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则增强了居民对保甲的依赖感。这就给予保甲制度以立足的基础,因为普通的上海百姓不可能逾越保甲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证。
战时的统制经济为传统保甲制度的再现提供了一个机遇,但它并不具备经久不衰的支持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甲组织的基层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仍以民食问题为例:计口授粮刚开始推行,就有“坊保长所报人口多数不正确”的问题,其后又不断发生保甲长藉一切配给假手转辗之机从中渔利的“流弊”[⑦e],以至统制经济的基础日益动摇。如前所述,统制经济之下的上海经济生活已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而汪伪政府仍要依赖统制经济掠夺战略物资以支持日伪军的华中作战,这就使得种类广泛的配给物资出现严重的短缺,以致上海市面由紧张到恐慌。下列图表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形:
从表1可以看出,上海的户口大米供应每况愈下,三年的配米总量犹不足每人一年的消费量,即使再加上三年人均共配面粉111.5斤。亦只抵每人一年的消费量[①f]。而表2却显示配给粮食价格的狂涨。如此的统制经济,迫使百姓不得不投向黑市,所谓户口米虽说不可放弃,但已远不足以维持生计。由是,可以操纵原始配给指标的保甲组织日见疲软。
表1.上海市户口米配给情况表[②f] (1942年7月6日至1945年6月底)
日期配给期数 人均配给数量
1942.7.6-12.30 21 3斗3升5合
1943.1.4-12.30 33 5斗3升5合
1944.1.4-12.15 19 3斗6升5合
1945.1.4-6.30
1 1升5合
合计 74 1石2斗5升
表2.配给粮食价格表[③f]
日期1942年7月1945年 涨幅
大米价格(石)
250元 6500元(年初) 27倍
面粉价格(百斤) 247元1120000元(6月) 486倍
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基层控制的要求而论,建筑于户籍管理基础上的传统保甲制度就更难以适应战时的大都市社会了,沦陷时期上海的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非传统的保甲功能所能顾及,特别是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情绪,就连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都不能遏制。因此,保甲功能的扩充被日伪统治者提上日程,市府希望利用保甲控制社会意识形态,并把保甲本身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
其一,赋予联保连坐法以邻里间监督舆论和政治态度的职责,尤其是用以反共和防范抗日[④f],这就突破了联保连坐法原来的一般社会治安范围,扩展了保甲组织的这一主要功能。
其二,把保甲系统纳入官方政治活动的轨道。政府通过保甲去组织群众参加官方的集会、游行甚至是官办的文艺演出。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市警察局保甲处数次以摊派名额形式,指令各区保甲组织群众参加所谓“国府参战一周年纪念大会”及“日本使节大川演讲会”等[①g]。每逢与中日战争或民族情绪相关的政治敏感日,如八一三、九一八纪念日以及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缔结一周年,政府就动用保甲和自警团严加防范。这就是通过保甲的有形系统向社会基层灌输官方的意识形态。
其三,将保甲制度本身意识形态化。市府规定学校教育中要将“新国民运动”与保甲制度的宣传结合起来,年级班级应采用保甲编制,甚至要求小学算术补充教材采用有关保甲编组、户口异动等数学问题。在训练以保甲为基础的防共自卫团时,市清乡委员会制定了有关“思想教育”和“测验思想”的条文[②g]。警察局保甲处还组织保甲自警团乐队,特令各区总联保长为之筹款并募捐音乐会的入场券[③g]。
在传统中国,国家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注集中在士的阶层,保甲的基层控制并不担负此类使命。而40年代的上海保甲在传统的基层控制机制内注入了意识形态控制的功能,这是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所需要的功能扩展,还是一个傀儡政权在战时特定环境中的特殊需求?换言之,这是常规的社会历史变迁的要求,还是应急的非常手段?
如果把保甲制度放在战前战后的上海社会中去考察,可以发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地方政府也进行过类似的努力。
1930年,上海市政府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市组织法》拟将华界里弄划为邻、闾、坊三级组织,隶属于区公所之下,5户为邻,5邻为闾,20闾为坊,并为此开办地方自治人员训练所,按政府要求培训基层工作人员。就制度本身而言,这一构想与战时日伪市府的保甲并无原则的区别,只是突出地打上了“基层自治”的印记。而战争对于这两者的作用则完全相反,抗战前“自治计划”的流产正是由于“一二八战事和华北事变的纷扰”[④g],沦陷时期上海保甲组织的再现则借助了战争这一时机。
战后的上海市政府继续日伪时期的基层控制方式,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并于1947至1948年间开办了五期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班,其组织之严密,政治审查之严格,意识形态之浓烈,较战前及战时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受训人员分为户政、兵役教育两类,每人的自传、调查表及个别谈话记录均详细存档[⑤g]。训练班开办的宗旨虽称为地方自治的保甲组织培训基层人员,但应付内战和反共的意图通贯其中[①h]。因此,战后上海的保甲组织虽然张着“自治”旗号,但仍与战时保甲一脉相承。此举因内战局势的急剧变化而被纳入战时轨道。但是,当时上海市面经济生活的混乱与恐慌,已经导致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严重失控,保甲组织形同虚设。此时,战争因素之于保甲的基层控制只是促其瓦解而不是支撑其存在了。
如果把上海与重庆作一横向比较,则更难以断言保甲制度在近代都市的生存与战争环境的必然联系了。
民国时期,重庆市建立保甲制度是始于战前的1935年,而且,一以贯之地经营了14年,至南京政权覆亡时才废止[②h]。此间,重庆处于“大后方”相对安定的环境和同一政权的统治之下。虽然抗战时期重庆的保甲组织也具备同时期上海保甲组织的战时功能,但战争环境显然不是它的推动力,它的建立与相对完备是与国民党的“训政”部署相同步的。
可见,保甲组织并不是非常条件下傀儡政权的特殊需要,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何一个合法的和非法的地方政权的主观意愿而言,都需要有一个集社会秩序管理和意识形态监控于一体的社会基层控制组织,作为常规的统治形式和手段。战时上海保甲制度的复活,不过是日伪政权借助于非常时期具体的社会局势,在非常与常规之间找到了契合点罢了。但又一个问题是,包括日伪上海市政府在内的所有地方政府并非都能如愿以偿地推行保甲制度,也不是战争状态能够支撑这一切或持之以恒的。关键的因素是保甲制度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被现代城市社会所接纳,它的属性究竟是国家的,还是社会的,抑或是两者的共同空间?
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即使政府利用保甲组织操纵民生大计并试图控制社会意识形态,上海基层社会依旧对它有冷漠、无奈甚至是抵触的反应。这种社会反应除表现为保甲编组过程中的阻碍,还体现在其运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抵制。
首先是难以开展户口复查和掌握变异更动情况。1943年8月上海全市保甲组织大致编组完成时,南市、沪北、市中心等6区的户口复查和异动却未办理,为此,市府急令“统限8月底以前办理完竣”[①i]。然而,直至1945年上半年,市保甲委员会仍然不能按时收到各县区的户口异动统计呈报表,因此不得不在工作报告中承认“各县区保甲工作鲜有成绩”[②i]。
再者是自警团的涣散与低效。在号称有10万青壮年的自警团中,有许多人消极抵制,“躲在岗亭内,打瞌睡或是看小说,还有许多人花钱雇人代替,甚至有妇女、小孩代替”[③i]。申请免役者也大大超出规定范围,市警察局保甲处原估计免役者仅1千名左右,实际则有数倍之多,仅1943年12月至1944年12月,就有1466人申请自警团免役,因而保甲处饬令各警察分局在自警团本部成立后即进行团员调查,期望“届时可添出许多服务者”[④i]。
其三是征收保甲经费和催纳各类捐税的问题层出不穷。沪北、沪西、邑庙等区的保甲委员会不断向上司反映征收保甲经费之困难情形,“收支持感不敷”,每保办公经费,“只够拨发书记费”[⑤i]。日伪多次开会研究对策,决议“保甲费除赤贫可免除外,公务员、军警一切人等皆须缴纳”,并制定了全市统一征收的办法[⑥i]。运用保甲征收的军警米、献机捐等也颇为吃劲。市财政局长向市长报告:军警米征收工作“收效甚微”,“人民对于军警米,无不力竭声嘶”,故“应行停征军警米,以免扰民”[⑦i]。市府鉴于献机捐无以达标,印发购棉布证340万张,购买时按名附收献机捐10元,如拒绝缴纳,则不能购买配给布[⑧i]。
最严重的问题是保甲组织自身的腐败以及保甲人员与居民的矛盾。从编组保甲开始,就不断有保甲长利用职权虚报户籍以自肥,以不予申报户口勒索、刁难居民,还与二房东勾结敲诈房客以分赃。扣发居民购货证、购粮证以及挪用保甲经费入私囊者不在少数,乱摊派、乱收费的现象比比皆是。就连市警察局保甲处也滥用职权营私舞弊,以致日军特高处情报科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查[⑨i]。一般上海市民对保甲的腐败深恶痛绝,关于各级保甲人员的投诉、指控连续不断,直接冲突也时有发生。从1943年5月底到1944年底,由市警察局保甲处直接受理并处理的居民诉讼保甲人员要案共87起,其中南市区居民吴以扬等人联名控告区保甲办事处副主任萧刚一案直接由市长周佛海批示查处[①j]。
战时上海保甲组织如上的基础性功能障碍和致命的自身危机所表现的反社会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它自然会引出对其属性的讨论。习惯的思路是把保甲视同政府行为,由政权的性质来决定其属性。这样,认定日伪政权之下保甲制度的封建法西斯性质当顺理成章。这个结论在沦陷时期上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无可怀疑,但这仅仅是基于政权性质的一种评价取向。倘若注意与40年代上海保甲制度相关的另一些侧面,则可以对上海保甲的属性作出其他层面的思考。
首先,保甲的腐败问题是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的通病。抗战时期,大后方乡村中的保甲组织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因“地方人才之缺乏”,“土豪劣绅遂栖身于其间”[②j],凭藉保甲大发国难财。城市中保甲人员的素质并未高于乡村,陪都重庆保甲长的人选是该市行政中“最严重最困难之问题”,“一般保甲人员素质甚低,难为社会重视”,虽数经遴选和培训,但无明显好转[③j]。可见,保甲的腐败可以同时产生在合法政权和傀儡政权之下,可以同时产生在抗日的和沦陷的政治环境中,因此,由政权性质出发的判断不能囊括保甲的其他属性。
其次,战时上海的保甲组织并非一律遭到社会的排斥。一些保甲组织在查禁毒品和防治社会治安险情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效,得到居民的肯定。有些保甲长因负其治安之责而受伤甚至被杀[④j]。许多居民在上诉保甲人员的同时,都希望有一些清廉者来掌握保甲,有的还例举某保甲人员如何之廉洁为民,吁请以他们来取代那些贪赃枉法之徒[⑤j]。如是观之,上海基层社会需要能够保护其利益的社会控制,寄希望于政府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反对政府利用保甲对基层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由此提示我们对保甲的“国家”与“社会”属性进行双重层面的观察。
毫无疑问,组织保甲是一种政府行为,尤其是在战时的条件下。保甲非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而且一直处于警方的严密控制之下。即使在行政系统设立了保甲委员会以后,保甲依然未同警察系统脱钩,其主任即由市警察局长卢英担任。该会《暂行组织规程》并规定,区公署或区保甲办事处得延聘该区有关的军警长官为咨询委员”[①k]。
但是,政府又给保甲组织披上了“自治”的外衣。汪伪行政院设计了一套保甲长的“民选”程序及保甲的“民治”方式:甲长由本甲各户长公推,保长由保内甲长公推;保甲职员均不发给工薪,甲长办公处都须设在甲长的住宅[②k]。与此同时,保甲长的最后任命及更换都直接受制于政府。甲长由区长加给委任,呈报县政府备案;保长由区长呈报县政府加给委任,并由县政府呈报省政府备案。保甲长若不能胜任,也须县政府查明并令公推人改推[③k]。上海根据自己的行政建制相应执行。政府称这样产生和运作的保甲组织是“完成官治机能,确立自治基础”[④k],企图在自治的形式之下,使保甲摆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
上海保甲在国家与社会双重政治空间的徘徊,在基层社会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响,从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其一,保甲组织的社会属性常常导致基层社会对政府的离心倾向,表现为国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对立。按保甲条例规定,区保甲办事处和警察分局应为基层保甲的行政领导和督查机关,市府对基层保甲的控制正是经由这两个机构。然而,他们往往发现指挥不灵,所辖的保甲往往自行其事。市警察局保甲处经常得到各区保甲办事处的报告,反映其下属与之“毫不联系,隔膜音息”,日军特高处长和保甲处长专门就此进行商讨,但无有效措施[⑤k]。更有甚者,保甲长将保甲变成了自己的独立小王国,专与警察分局或上级办事处指派的保甲人员作对。闸北、南市等区发生多起上级圈定的新保长受到原保长的抵制、对抗事件,而原保长几乎都是“地头蛇”[⑥k]。
其二,消极接受来自政府的基层控制,对保甲的国家属性基本认同,从而使保甲成为国家和社会共同的政治空间。在一部分上海保甲中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张,政府指令保甲贯彻的各项意图未受到强力的阻抗。如发放居民证一项,两租界虽然在编组保甲的过程中步伐迟缓,但一经编就,开始运转,便比其他地段有序。因此,原公共租界因保甲长工作合乎上级要求而在全市先行发放居民证,原法租界除少数联保长有问题外也随后发放[⑦k]。又如,市府组织的各种政治集会和活动,几乎都动用市中心区的保甲去网罗群众参与,尽管到会或出场者十分涣散,但人数还是能凑够的[①l]。一般保甲人员与居民的关系也较为缓和,他们言行谨慎,以至于在众多的居民指控保甲长的案件中,极少涉及他们。在战后,他们中的大部分或被政府留用,或继续被推选[②l]。可以说,他们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到了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基层社会对保甲属性的两种不同反应同上海社会的地段差异有密切联系。第一类反应表现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尤其是下层贫民集中的苏北人棚户区。闸北、南市、浦东等区的保甲办事处多次向市警察局保甲处报告棚户地段的保甲长“不肯听命,极难统领”,经常策动“贫困”、“智识幼稚”、“天性好讼”的“江北同胞”与区公署、警察分局相对抗[③l]。1943年5月底至1944年底,市警察局所涉的有关保甲闹独立的要案,全部出自下层居民的聚居地[④l]。第二类反应则体现在市中心区,特别是原租界地区的中心区域。那里居住的大多数为中上层市民,其保甲长亦多数是有职业、有知识者。
从上可知,上海基层社会对保甲是国家的或是社会的属性并无一致的和确定的认同。这恰好证实了保甲本身属性的不确定性及上海城市政治社会的隔裂性。即使在非常的战时状态,在租界已从行政上被取消的条件下,上海社会的基层控制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割裂性的影响。
四、结语
如果要对中国传统的基层控制方式跨越时空的价值作一个总体的测评,那么,只能说沦陷时期上海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空间容纳了保甲,并在一些特定的层次上(如战时上海社会经济生活的统制)接受了它,使之活跃于一时。然而,作为常规的社会基层控制,保甲制度在整个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并未生根。这并不取决于战争因素,而在于这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处在严重的政治割裂状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若即若离,既未出现统一的强有力的公众领域来控制基层社会,又有一些社会利益群体或地域文化认同处在这个领域的边缘。
注释:
①a 《同治上海县志》卷七;《建设新上海与组织保甲刍议》,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上档资料”),全宗号R33,卷号287,第102页。
①b 1937年上海华界沦陷至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地区先后存在过日伪统治下的大道市政府(1937年12月)、督办上海市政公署(1938年4月)、上海特别市政府(1940年3月至1945年8月,其间,一度改称为上海市政府)。考虑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统称为“市府”。
②b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区政务署组织暂行章程》、《上海特别市区公署条例》、《行政院关于抄发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训令》,上海市档案馆编《日伪上海市政府》(以下简称《日伪》),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1、255页。
③b 《日伪》,第254—265、274—275页。
④b 根据“市政府统治期间各类捐税表”(1938年1月—1945年5月)和日伪市府其他征收赋税令统计所得。见《日伪》第435—437、496、528、537、612、668、680、695、751页。
⑤b 上档资料,R33,卷287,第129页。
⑥b 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商务印书馆1946年上海版,第83页。
⑦b 阮毅成:《战时县政工作》,《民意周刊》第8—9期。
①c 《日伪》,第35页。
②c 《日伪》,第229页。
③c 上档资料,R33,卷73,第12—13页;卷75,第100页;卷115,第29页。
④c 苏子:《上海人》,《上海生活》1939年第1期。
⑤c 《催促各区公署迅速办理保甲的训令》,《日伪》,第229页。
①d 上档资料,R33,卷77,第15页;卷221,第6—7页;卷225,第27页。
②d 《市府关于限期完成沪西办事处附近棚户保甲训令》(1942年3月19日),《日伪》,第248页。
③d 《市警察局关于拟具人民连坐保结变通办法呈及督办公署指令》(1938年7月),《日伪》,第161页。
④d 《行政院关于抄发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训令》(1943年4月2日),《日伪》,第254—265页。
①e 《日伪》,第555页。
②e 《市府关于限制酒肆舞场营业时间布告》(1943年8月30日);《市府公布上海特别市战时市民节约宴会施行细则》(1944年6月30日),《日伪》,第667、709页;徐大风:《弄堂特写》,《上海生活》1939年第4期。
③e 《市府等关于办理公粜处文件》(1942年4月—10月),《日伪》,第578—580页。
④e 《市粮食管理局关于降低食米配给标准及办理封锁线内外各区食米配给呈》(1942年8—9月),《日伪》,第606页。
⑤e 同上。
⑥e 同上文件,《日伪》,第611页。
⑦e 《市粮食管理局关于降低食米配给标准及办理封锁线内外各区食米配给呈》(1942年8—9月),《日伪》,第609页;上档资料,R33,卷225,第19—20页。
①f②f 潘吟阁等《战时上海经济》第一辑,上海经济研究所1945年版,第147页。
③f 同上。
④f 《行政院关于抄发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训令》(1943年4月2日),《日伪》,第265页。
①g 上档资料,R33,卷75,第7、9—11、17—18页。
②g 《市清乡事务局关于拟订清乡教育实施纲要呈及市府指令》(1943年9月);《绥靖部为限期推行乡区防共自卫团致市府函》(1938年12月9日),《日伪》,第293—296、182页。
③g 《为保甲自警团本部举办之音乐唱歌大会协力推销训令》,上档资料,R33,卷75,第71—73页。
④g 《上海市年鉴》(1936年),上F,第110页。
⑤g 上档资料,全宗号Q107,“地方自治人员训练班”档案。
①h 《训练大纲及组织规程》(1945—1949年)、《小组讨论记录》(1947—1948年),上档资料,Q107,卷3、卷8。
②h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3—586页。
①i 《市保甲委员会关于陈报实施编查保甲户口区域呈及市府指令》(1943年8月),《日伪》,第286页。
②i 上档资料,R33,卷65,第26页。
③i 屠诗聘:《上海市大观》上,中国图书杂志公司1946年版,第86—87页。
④i 《自警团免役申请报告及批文》,上档资料,R33,卷130—142;《各分局长保甲股主任协议会记录》(1944年8月11日),上档资料,R33,卷75,第97—98页。
⑤i 上档资料,R33,卷74,第8页;卷287,第89页。
⑥i 上档资料,R33,卷75,第96—97页。
⑦i 《市府推行随田赋带征军警米有关文件》(1943年9月—1945年1月),《日伪》,第674页。
⑧i 《市府等关于配给棉布附收献机捐文件》(1944年5月),《日伪》,第696页。
⑨i 上档资料,R33,卷226。
①j 《市民控保甲人员案》,上档资料,R33,卷225—230;《控萧刚案》,上档资料,R33,卷225,第26—36页。
②j 孙义慈:《战时物价管制》,中华书局1943年版,第37页。
③j 《近代重庆城市史》,第579—581页。
④j 《保甲长受伤及被杀等案》,上档资料,R33,卷222—224。
⑤j 《邑庙区第5联保第5保民众恳请速予撤惩该保保长另选贤能以谋地方福利案》,上档资料,R33,卷229,第154—157页。
①k 《日伪》,第252页。
②k 《行政院关于抄发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训令》,《日伪》,第257、260页。
③k 同上。
④k 《市清乡事务局关于补送第一、二期第三次清乡计划等签呈》,《日伪》,第322页。
⑤k 《为商讨保甲人员与警察分局联络问题案》,上档资料,R33,卷75,第92—95页。
⑥k 上档资料,R33,卷221,第6—7页;卷225,第19—21、60—62页。
⑦k 《保甲股主任辅佐官会议记事》(1944年3月17日),上档资料,R33,卷75,第22—25页。
①l 上档资料,R33,卷75,第4—18页。
②l 《整编保甲委员会人选名单》,上档资料,R33,卷287,第145—146页。
③l 上档资料,R33,卷221,第6—7页;卷225,第19—21、60—62页。
④l 上档资料,R33,卷225—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