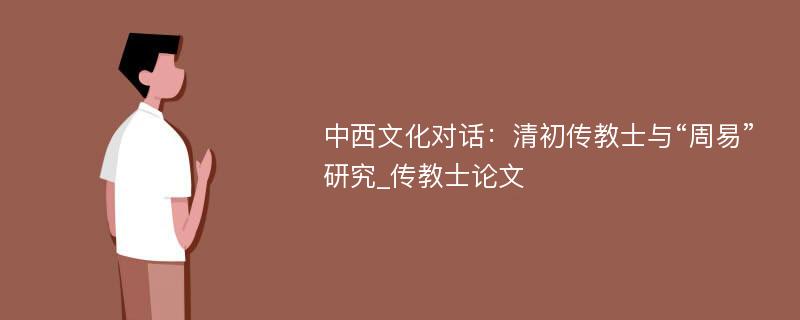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经论文,中西文化论文,清初论文,传教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明耶稣会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在清初期,中西文化交流达到很高的程度。在康熙的直接安排下,法国入华传教士白晋等人对中国的经典《易经》进行长达五年多的研究,这是清前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部分研究,并取得一些进展。① 但由于白晋研究《易经》的中文原始文献尚未公布,绝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还不能使用这批文献,相关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还未解决。本文依据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白晋读《易》的原始文献,并吸取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通过《易经》研究在康熙和白晋之间所展开的文化对话做一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一 康熙安排白晋等人研究《易经》的基本情况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是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到北京后和张诚(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一起在宫中为康熙服务,深得康熙宠爱。白晋很早就开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1697年返回法国,在巴黎做讲演时就说:“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易经》这本书“蕴含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② 这说明,此时白晋已经研读《易经》,并认识到《易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六年后,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白晋就已经写出研究中国典籍的著作《天学本义》。③ 在自序中提到《易经》说:“秦始皇焚书,大《易》失传,天学尽失。”表明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恢复天学,上卷是《择其解益明经书系天学之本》,下卷是《择集士民论上天公俗之语》,④ 如韩琰在给白晋《天学本义》所写序中所说:“此书荟萃经传,下及方言俗语,其旨一本于敬天。”⑤ 此时,白晋研究的内容虽然涉及《易经》,但尚未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易经》的研究上。
目前发现康熙安排白晋读《易》最早的文献是这样记载的:
四月初九日,李玉传旨与张常住:据白晋奏说,“江西有一个西洋人,曾读过中国的书,可以帮得我。”尔传于众西洋人,着带信去将此人叫来。再白晋画图用汉字的地方,着王道化帮着他略理。遂得几张,连图着和素报上,带去。如白晋或要钦天监的人,或要那里的人,着王道化传给。钦此。⑥据学者考证,这份文献的时间应是在康熙五十年。⑦ 傅圣泽(Jean- Fransois Foucquet,1665—1741)进京后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康熙对他的研究情况也十分关心。傅圣泽奏:
臣傅圣泽在江西聆听圣旨,命臣进京相助臣白晋同草《易经》稿。臣自愧浅陋,感激无尽。因前病甚弱,不能陆路起程,抚院钦旨即备船只,诸凡供应,如陆路速行于六月二十三日抵京。臣心即欲趋赴行宫,恭请皇上万安,奈受暑气不能如愿,惟仰赖皇上洪福,望不日臣躯复旧,同臣白晋竭尽微力,草《易经》稿数篇,候圣驾回京,恭呈御览。⑧
在白晋研究《易经》的过程中,康熙十分关注,多次问及此事:
七月初五日,上问:“白晋所释《易经》如何了?钦此。”王道化回奏:“今现在解《算法统宗》之攒九图,聚六图等因具奏。”上谕:“朕这几个月不曾讲《易经》,无有闲着;因查律吕根原,今将黄钟等阴阳十二律之尺寸积数,整音、半音,三分损益之理,俱已了然全明。即如箫笛、琵琶、弦子等类,虽是玩戏之小乐器,即损益之理也,查其根源,亦无不本于黄钟所出。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俱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出己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有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若不即其数之精微以考查,则无所倚,何以为凭据?尔可对白晋说:必将古书细心校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所释之书,何时能完?必当完了才是。钦此”。⑨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康熙不仅自己认真研究中国传统的数学、律吕和《易经》的象数之学,而且对白晋提出批评,“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也不要敷衍了事。这说明康熙十分清楚白晋的想法,知道他作为一个传教士在理解《易经》上会遇到许多问题。
《易经》为六经之首,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读懂并非易事。白晋在给康熙的奏书中也道出其苦衷:“初六日,奉旨问白晋‘尔所学《易经》如何了?钦此。’‘臣蒙旨问及,但臣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义。凡中国文章,理微深奥,难以洞澈,况《易经》又系中国书内更为深奥者。臣等来中国,因不通中国言语,学习汉字文义,欲知中国言语之意,今蒙皇上问及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倘圣恩不弃鄙陋,假年月,容臣白晋同傅圣泽细加考究,倘有所得,再呈御览,求圣恩教导,谨此奏闻。”⑩ 由此可见,康熙对白晋等人研究《易经》活动督促很紧,他们似乎跟不上康熙的要求和期望。
傅圣泽进京后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二人随时将学习的情况向康熙汇报,(11) 梵蒂冈图书馆藏的一份文献说明了这一点:
有旨问,臣白晋你的《易经》如何?臣叩首谨奏。臣先所备《易稿》粗疏浅陋,冒渎皇上御览,蒙圣心宏仁宽容,臣感激无极。臣固日久专于《易经》之数管见,若得其头绪尽列之于数图,若止臣一人愚见,如此未敢轻信。傅圣泽虽与臣所见同,然非我皇上天纵聪明,唯一实握大易正学之权,亲加考证,臣所得易数之头绪不敢当,以为皇上若不弃鄙陋,教训引导,宽假日期,则臣二人同专心预备,敬呈御览。(12)白晋向康熙奏报二人在《易经》研究上遇到的困难,希望康熙“教训引导,宽假日期”,亦说明康熙对白晋等人研究《易经》的细节非常注意。
傅圣泽于康熙五十年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和白晋产生分歧后,(13) 康熙就安排他研究数学和天文。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他在给康熙的奏书中说:
臣傅圣泽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义,蒙我皇上洪恩,命臣纂修历法之根。去岁带至热河,躬亲教导,实开茅塞。《日躔》已完,今岁若再随驾,必大获益,奈自去口外之后,病体愈弱,前病复发。其头晕头痛,迷若不知,即无精力。去岁犹有止时,今春更甚,几无宁息,不可以见风日。若再至口外,恐病体难堪,抑且误事。惟仰赖我皇上洪恩,留臣在京,静养病躯。臣尝试过,在京病发之时少,而且轻,离京则病发之时多,而且重,今求在京,望渐得愈,再尽微力,即速作历法之书,可以速完。草成《月离》,候驾回京,恭呈御览,再求皇上教导。谨此奏闻。(14)说明傅圣泽协助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不过两年。当然,傅圣泽主要做数学和天文学研究后,对《易经》的研究并未停止,在这一段时间仍然写了不少研究《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论文。(15)
白晋作为“索隐派”的主要成员,在“礼仪之争”中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反对阎当代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派别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另一方面,由于想推进和坚守利玛窦的思想和规矩,从而和耶稣会的原有思想和路线也产生矛盾,因此白晋向康熙奏报:
臣白晋前进呈御览《易学总旨》。即《易经》之内意与天教大有相同,故臣前奉旨初作《易经稿》,内有与天教相关之语。后臣传傅圣泽一至,即与臣同修前稿,又增几端。臣等会长得(16) 知,五月内有旨意,令在京众西洋人同敬谨商议《易稿》所引之经书。因(17) 寄字与臣二人云:‘尔等所备御览书内,凡有关天教处,未进呈之先,当请旨求皇上谕允其先查详悉。’臣二人日久专究《易》等书奥意,与西土秘学古传相考,故将己所见,以作《易稿》,无不合与天教,然不得不遵会长命,俯伏祈请圣旨。(18)这件事实际上涉及耶稣会内部在“礼仪之争”中的矛盾,白晋为证明利玛窦路线的正确性,采取索隐派的做法,认为中国的《易经》等古籍中就有神迹。其他耶稣会士认为白晋走得太远了,如果照白晋的理解,中国倒成了天学之源。所以,在京的其他耶稣会士要求白晋所有上交给康熙的文稿都要审查。耶稣会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教权对皇权的一种挑战,无疑会使康熙很反感。有学者认为,耶稣会的这种做法可能是导致康熙逐渐对白晋研究《易经》失去兴趣的原因之一。(19)
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梵蒂冈和康熙的矛盾日益加深,入华传教士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康熙逐渐失去了对白晋研究《易经》的兴趣:
五十五年闰三月初二日,为纪理安,苏霖,巴多明,杜德美,杨秉义,孔禄食,麦大成,穆敬远,汤尚贤面奏折,上将原奏折亲交与纪理安等。谕赵昌,王大化,张常住,李国屏,佟毓秀,伊都立尔公同传于白晋,纪理安等所奏甚是。白晋他做的《易经》,作亦可,不作亦可。他若要作,着他自己作,不必用一个别人,亦不必忙,俟他作全完时,再奏闻。钦此。(20)尽管如此,康熙仍很宽容,让白晋继续进行《易经》的研究。
这样我们看到,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五年,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康熙亲自组织了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并随时解决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在当时应是件大事。康熙为什么要让白晋等人读《易经》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 康熙让白晋研究《易经》的目的及其影响
康熙让一个外国传教士研究《易经》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首先,康熙对科学的兴趣很大,这是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汤若望和杨光先的历法之争开始,康熙就对西方科学产生兴趣,正如他事后所说:“朕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相互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21) 在中国历史上像康熙这样用心学习西方科学的皇帝可能仅此一人。(22) 康熙即位不久,就请南怀仁(Ferdnand Verbiest,1622 —1688)讲授天文数学,后又将张诚、白晋等留在身边讲授几何学。康熙对数学的这种热情一直保持着,康熙五十二年下令开蒙养斋:
谕和硕诚亲王允祉等,修辑律吕算法诸书,著于蒙养斋立馆,并考定坛庙宫廷乐器。
举人赵海等四十五人,系学算法之人。尔等再加考试,其学习优者,令其修书处行走。(23)同年六月十七日,和素给康熙的奏报称:
西洋人吉利安,富生哲,杨秉义,杜德海将对数表翻译后,起名数表问答,缮于前面,送来一本。据吉利安等曰:我等将此书尽力计算后,翻译完竣,亦不知对错。圣上指教夺定后,我等再陆续计算,翻译具奏,大约能编六七本。(24)这说明康熙当时在研究数学问题,对数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到热河避暑山庄,将陈厚耀等人都带到承德,同他们讨论《律历渊源》的编写,(25) 第二年命诚亲王允祉等人“修律吕,算法诸书”。(26)
很清楚,康熙安排白晋等人研究《易经》,正是他热衷于西方数学之时。《易经》研究在中国的经学解释史上历来就有“义理派”和“象数派”两种路向,因为《易经》本身是有符号系统和概念系统的结合体,所以这两种解释方法都有其内在的根据,且皆有著作传世。在象数派的著作中就包含了许多数学的内容,如郑玄所做的“九宫数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矩阵图”。(27) 康熙对邵雍等象数派的《易经》研究也十分清楚。康熙五十年二月在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康熙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28) 这说明康熙把对数学的兴趣和中国典籍《易经》结合了起来,两个月后就传旨江西巡抚郎廷极,让傅圣泽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
梵蒂冈图书馆也有康熙研读阿尔热巴拉法的文献,说明康熙当时对数学的兴趣。“谕王道化。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热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错处亦甚多,鹘突处也不少。前者朕偶尔传与在京西洋人开数表之根,写得极明白。尔将此上谕抄出并此书发到京里,去着西洋人共同细察,将不通的文章一概删去,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看起来此人算法平平尔,太少二字即可笑也。特谕。”(29) 从中可以看到,康熙对数学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这份文献也说明,在康熙学习数学的过程中,白晋等传教士起着重要的作用。白晋之所以能参与此事,是因为他入宫后曾和张诚一起用满文给康熙讲授几何学,做过康熙的数学老师,康熙对他教授数学的能力是充分信任的。另外,在当时的传教士中,白晋的中国文化基础最好,康熙曾说:“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人通中国文理,惟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亦尚未通。”(30) 康熙认为能完成此事者非白晋莫属。(31)
白晋对康熙的想法应该是清楚的,所以从象数的角度研究《易经》是他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他在《易数象图总说》中说:“内易之秘,奥蕴至神,难测而难达,幸有外易数象图之妙,究其内易之精微,则无不可知矣。”(32) 在《易学外篇》首节中说:“易之理数象图,相关不离,诚哉!斯言也。盖言理莫如数,明数莫如象,象数所不及者,莫如图以示之。”(33)
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文献中,有一件白晋研究《易经》的日程表及康熙读白晋研究论文后的御批,主要内容就是在交流《易经》所包含的数学问题。
二十四日。进新改了的释先天未变之原义一节,又释河洛合一,天尊地卑图,为先天未变易数象图之原一本,并《历法问答》定岁实法一本,交李三湖呈奏。奉旨:朕俱细细看过了,明日伺候。钦此。
二十五日呈览。上谕:尔等所译之书甚好了,朕览的书合于一处,朕所改已上所谓地形者之处,可另抄过送上。
七月初四日。呈御笔改过的《易经》,并新得第四节释天尊地卑图,为诸地形立方诸方象,类于洛书方图之原,及大衍图一张,进讲未完。上谕:将四节合定一处,明日伺候。钦此。
初六日,呈前书并新作的释天尊地卑图,得先天未变始终之全数法图二张,进讲。上谕王道化,白晋作的数甚是明白,难为他,将新作的天尊地卑图,得先天未变始终之全数法并图留下,《易经》明日伺候。钦此。
初七日,进大衍图。上谕:将大衍图留下,朕览,尔等另画一张,安于书内,钦此。谕尔等俱领去收看,钦此。
十二日,进讲类洛书耦数方图之法一节,图一张,呈览。上谕:将耦数方图之法与前日奇数之法合定一处,尔等用心收看,钦此。本日御前太监叶文忠奉旨取去原有御笔写类书方图奇数格一张,并耦数方图一张。传旨,照此样多画几张。钦此。本日画的奇数方图格二张,教太监李三湖呈上,留下。
王道化谨奏:初九日,恭接得上发下大学士李光地奏折一件,并原图一幅,说册一节与白晋看。据白晋看,捧读之下,称深服大学士李光地精通易理,洞晓历法。(34)这里所讲的《天尊地卑图》、《释先天未变之原义》、《洛书方图》、《大衍图》等,均为白晋从象数角度研究《易经》的图和著作。康熙出于对数学研究的兴趣,希望白晋研究《易经》,发现其中的数学奥秘。白晋在研究过程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康熙这方面的兴趣。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正是白晋《易经》研究中的数学和象数的内容“使得康熙领会了其中的数学的奥秘,并使康熙对《易经》的兴趣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康熙让一个外国人研究《易经》的原因或在于此。”(35) 目前,这个问题仍待进一步研究,上述白晋所绘制的各种《易经》象数的图式仍有待发现和系统整理。
其次,通过白晋的《易经》研究来证实“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是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对清初的思想和学术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谁最早提出这一思想,学术界尚有争论。(36)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康熙四十三年,康熙在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个想法:“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37)
康熙五十年,康熙在和直隶巡抚赵宏燮论数时说:“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38) 这段话是康熙首次把“西学中源说”和《易经》联系起来,其依据就是“阿尔朱巴尔”。根据这个谈话的内容和时间,可以做出两个判断:其一,康熙在此前已经了解并学习了西洋算法阿尔朱巴尔法;其二,开始给康熙讲授这一算法的不是傅圣泽,因为傅圣泽接旨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应是康熙五十年四月以后,即在康熙和赵宏燮谈话之后,魏若望认为傅圣泽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在热河时向康熙献《阿尔热巴拉新法》事,显然值得商榷。(39)
康熙四十二年,张诚、白晋、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在给康熙讲授西方数学时已经包括阿尔热巴拉法。这期间翻译的西洋数学书就有《借根方算法节要》,《借根方算法》有多种译法,(40) 《东华录》译为“阿尔朱巴尔法”,梅文鼎在《赤水遗珍》中作“阿尔热八拉”。阿尔热巴拉法在数学上指的是代数,出自825年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拉子模(Mohammed ibn Musaaikhowarizmi)所做的AI-jabr w'al muqabala一书,是代数学之祖。“这本书在12世纪译成拉丁文时,书名为‘Ludus algebrae et almucgrabalaeque’,后来简称algebra,今译为‘代数学’”。(41)
代数学源于东方,后传到西方,康熙说是“东来之法”并不错。但“东来”实际上应是源于阿拉伯,而康熙很可能把它理解为源于中国。有学者怀疑,这是否为“传教士为讨好康熙而故意编造的谎话呢”?(42) 史无凭证。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康熙在安排白晋研究《易经》以前,已有以《易经》为西洋算法之源的想法。说明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时有明确政治意图。因为“西学中源说”实际上是康熙对待西学的一种基本策略,是他在当时的中西文化冲突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文化政策。(43)
当傅圣泽再次向康熙传授阿尔热巴拉新法时,“用天干开首的甲,乙,丙,丁等字表示已知数,用地支末后的申,酉,戌,亥等字表示未知数(和笛卡尔用a,b,c,d等字母表示已知数,用x,y,z等字母表示未知数相仿),又用八卦的阳爻——作加号,用阴爻——作减号,以+为等号。”(44) 康熙在安排傅圣泽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以后,再次对阿尔热巴拉法表示出兴趣。
梵蒂冈图书馆的文献也证实这一点:
启杜、巴、傅先生知:二月二十五日三王爷传旨,去年哨鹿报上发回来的阿尔热巴拉书,在西洋人们处,所有的西洋字的阿尔热巴拉书查明,一并速送三阿哥处,勿误。钦此。帖到可将报上,发回来的阿尔热巴拉书并三堂众位先生们,所有的西洋字的阿尔热巴拉书查明,即送到武英殿来,莫误。二月二十三日 李国屏 和素。(45)
字与杨、杜、纪、傅四位先生知:明日是发报的日子,有数表问答,无数表问答书,四位先生一早进来,有商议事,为此特字。六月二十五日 李国屏 和素。
字启傅先生知:尔等所作的阿尔热巴拉,闻得已经完了,乞立刻送来以便平定明日封报,莫误。二月初四 李国屏 和素。
十月十八日奉上谕新阿尔热巴拉,朕在热河发来上谕,原着众西洋人公同改正,为何只着傅圣泽一人自作,可传众西洋人,着他们众人公同算了,不过傅圣泽一人自作,不过傅圣泽说中国话罢了。务要速完。钦此。王道化。(46)康熙前后两次热衷于学习阿尔热巴拉法,一方面和他的数学兴趣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的“西学中源”思想有直接联系。在指导白晋研究过程中,康熙提醒白晋注意中国古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告诫白晋“必将古书细心校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这实际在引导白晋向他的思想方向发展,正如在此期间康熙对李光地所说:“尔曾以《易》数与众讲论乎?算法与《易》数吻合。”(47)
三 康熙让白晋研究《易经》是他在“礼仪之争”中所采取的重要步骤
“礼仪之争”是康熙年间中国和西方关系中最重大的事件,这场争论对康熙的天主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康熙三十九年在清宫中的耶稣会士精心策划了一份给康熙的奏书:(48)
治理历法远臣闵明我、徐日昇、安多、张诚等谨奏,为恭请鉴,以求训诲事。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也而拜也。祭礼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位,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过抒于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郊天之礼奠,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原主宰,即孔子所云,“社郊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如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亲书“敬天”之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鉴训诲。远臣等不胜惶悚待命之至。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奏。(49)康熙当天就批下这份奏书:“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50)
康熙四十三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公布谕旨,正式判定“中国礼仪”为异端,应予禁止。(51) 四十四年,多罗特使来华。四十五年,康熙在畅春园接待多罗特使,传谕:“西洋人自今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同时让在华的传教士“领票”,告诫传教士“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52) 四十六年,多罗特使在南京正式公布教宗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敬孔的禁令,康熙在最后一次南巡中接见传教士,并有“永在中国各省传教,不必再回西洋”等语。(53) 派传教士龙安国(Antoine de Barros,1664—1708)、薄贤士(Antoinede Beanvollier,1656—1708)、艾若瑟(Giuseppe Antonio Provana)、 陆若瑟(Raimundo Josē de Arxo)先后返回罗马,向教廷解释其政策。四十九年,马国贤(Matteo Ripa)、德理格(Teodorico Perlrin)来华,康熙命傅圣泽进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五十一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发备忘录,确认多罗在中国所发的教令。五十四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颁布《从登极之日》。(54) 五十五年,康熙当着众传教士的面痛斥德理格有意错译康熙致教宗的信。[55] 五十六年,嘉乐特使来华。
从以上列出的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时间,正是“礼仪之争”激烈之时,是在多罗特使和嘉乐特使来华之间,此时也是康熙和罗马教廷关系紧张之时。这时康熙开始考虑对在华传教士应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要求。康熙四十五年传谕:“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者,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一定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教化王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先明白晓喻,命后来之人谨守法度,不能少违方好。”(56) 康熙对传教士反复讲的就是要遵守利玛窦的规矩。康熙第二次接见多罗时,向他说明了对待传教士的基本政策:“中国两千年来,奉行孔学之道。西洋人来中国者,自利玛窦以来,常受皇帝保护,彼等也奉公守法。将来若是有人主张反对敬孔敬祖,西洋人就很难再留在中国。”(57) 接着他传谕全体在京的传教士:
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因此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遵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教你们回西洋去,朕不教你们回去。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教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要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教化王若说你们有罪,必定教你们回去。朕带信与他,说徐日升等在中国,服朕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教他们回去,朕断不肯将他们活打发回去……朕就将中国所有西洋人都查出来,尽行将头带于西洋去。设是如此,你们的教化王也就成了教化王了。(58)“礼仪之争”中一些传教士的表现也令康熙恼火。先是阎当,不懂中国文理,却信口雌黄,康熙说他“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论中国经书之道,象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一点根据。”(59) 后是德理格擅自改动康熙给教宗的信,使康熙大怒,认为“德理格之罪,朕亦必声明,以彰国典”。康熙将他称为“奸人”,“无知光棍之类小人”。(60)
白晋是康熙最信任的传教士之一,多罗来华后,康熙让他直接参与一些重要活动,表示对他的信赖。(61) 在这种背景下,康熙让白晋研究《易经》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这个决定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兴趣问题。康熙想通过白晋的《易经》研究给传教士树立个榜样,让他们遵守利玛窦的规矩,知道“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62) 这是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同教廷政策展开斗争,争取入华传教士按其规定的路线在中国生活、传教的重要政治举措。这点康熙在几次谕批中说得也很清楚。康熙五十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读了白晋的手稿后说:“览博津(白晋——引者注)引文,甚为繁冗。其中日后如严党(阎当——引者注)、刘英(刘应——引者注)等人出必致逐件无言以对。从此若不谨慎,则朕亦将无法解脱,西洋人应共商议,不可轻视。”和素在向传教士传达后给康熙的奏报中说:“即召苏琳、吉利安、闵明鄂、保忠义、鲁伯佳、林吉格等至,传宣谕旨。苏琳、吉利安、闵明鄂等共议后报称:凡事皇上教诲我西洋人,笔不能尽。以博津文内引言,甚为繁冗,故谕日后严当、刘英等人出,恐伤我,不可轻视,著尔共议。钦此。洪恩浩荡,实难仰承。是以我等同心。嗣后博津注释《易经》时,务令裁其繁芜,惟写真事情。奏报皇上。所写得法,随写随奏,所写复失真,不便奏皇上阅览,即令停修。”康熙高兴地批复:“这好。”(63)
由此可以看出,康熙让白晋研究《易经》是和“礼仪之争”紧紧相关的。康熙想通过白晋的研究在这场争论中找到一些应对手段,因为需要说服的不仅有阎当、刘应这样的传教士,甚至还有罗马教廷。这个工作由传教士来做当然要比中国文人做更好。白晋既得康熙信任,又通中国文理,自然是为合适人选。
四 康熙对白晋的影响
白晋的《易经》研究是在康熙直接指导下展开的,因此康熙的思想对白晋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易经》研究,白晋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所变化。
白晋在《古今敬天鉴天学本义自序》中写道:“天学者何乃有皇上帝至尊无对、全能至神至灵,赏罚善恶至公无私,万有真主所开之道,人心所共由之理也。盖上主初陶人心,赋以善良,自然明乎斯理。天理在人心,人易尽其性而合于天。磋乎!未几人心流于私欲,获罪于天,离于天理而天理昧。至仁上主不忍人之终迷也……乃以天道之精微明录于经,以启世之愚象。”(64) 这是白晋在康熙四十六年的文字和思想,从中可以看到,文字是中国的,但思路和逻辑完全是西方的,是《圣经》的伊甸园原著、先祖原罪、天主救赎思路的中国式表述。在对中国典籍的了解上,《天学本义》基本上是对中国典籍的择录和对民间俗语的收集,全书的逻辑结构完全是西方的,是天主教神学的构架,和中国本土思想没有太大关系。因此,在康熙安排白晋研究《易经》的初期,白晋仍停留在原有的思想上,其研究结果使康熙很不满意。康熙在和素、王道化的奏书上批注说:“览博津书,渐渐杂乱,彼只是自以为是,零星援引群书而已,竟无鸿儒早定之大义。”(65) 这里的“自以为是”,是说白晋完全按西方那一套来写,逻辑是西方的,只是引些中国古书,但对儒家本义并不理解。康熙把这个想法也告诉了在京的其他传教士,因为此事事关重大,传教士决定把远在江西的傅圣泽调到北京,协助白晋研究《易经》。康熙五十年六月十日和素奏报:“远臣苏琳、吉利安等跪读皇上谕旨:至博津所著《易经》内引言,恐日后必为本教人议论。钦此。将书退回。臣等同样议:皇上洞察细微,深爱臣等,为我等深谋,臣等感激天地。惟臣等均不谙《易经》,故先颁旨。俟江西富生哲(傅圣泽——引者注),再与博津详定,俟皇上入京城,进呈御览。为此谨奏。请皇上指教。”(66) 这说明傅圣泽进京不仅仅是白晋的意见,更是在京传教士的集体决定。不久,和素也向康熙谈了对白晋研究成果的看法:“奴才等留存博津所著《易经》数段,原以为其写得尚可以。奴才等读之,意不明白,甚为惊讶。皇上颁是旨,始知皇上度量宏大。奴才等虽无学习《易经》,虽遇一二难句,则对卦查注,仍可译其大概。再看博津所著《易经》及其图,竟不明白,且视其图,有仿鬼神者,亦有似花者。虽我不知其奥秘,视之甚可笑。再者,先后来文援引皆中国书。反称系西洋教。皇上洞鉴其可笑胡编,而奴才等尚不知。是以将博津所著《易经》暂停隔报具奏,俟皇上入京,由博津亲奏。”康熙同意和素的这个看法,批示:“是。”(67) 和素的看法反映了康熙的思想,也说明白晋此时的《易经》研究还未进入角色,尚不能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把握《易经》。前引梵蒂冈所藏文献“七月初五日”条也说明这一点。因此康熙告诫白晋要“细心校阅”中国书,不能“因其不同道则不看”。
以上材料说明,白晋在康熙指定他研究《易经》初期仍未找到中西思想的结合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十分有限。康熙的批评对白晋产生影响,此后白晋的《易经》研究出现新的变化,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认识有所加深,索隐派的思想也更为成熟和圆润。他在《易纶·自序》中讲到《易经》在中国文化的地位时说:
大哉!易乎,其诸经之本,万学之原乎。《传》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前儒赞之云,其道至广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诚哉!易理至矣,尽矣,无以加矣。十三经《书经》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三代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实之为大训。《正义》曰夏商周三代之书,有深奥之文,其所归趣与坟典一揆。《图书编》五经序云:六经皆心学也,说天莫辩乎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孰非心乎,孰非圣人之心学乎?是知诸经典籍之道,既全具于易,皆实惟言天学心学而已。(6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此时白晋对中国传统文献,如孔颖达《五经正义》等较为熟悉,这同他写《天学本义》时已有所不同。他在1715年的一封信中说道:“我的研究就是要向中国人证明,孔子的学说和他们的古代典籍中实际包含着几乎所有的、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我有幸得以向中国的皇帝说明这一点,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学说和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相同的。”(69) 从中可以看到,白晋终于在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找到了一条通道,将二者完全合一。显然,此时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过去加深了,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这恐怕是康熙所始料未及的。
注释:
① Claudia von Collani.,P.Joachim bouvet S.J.sei Lieben undSein Werk,Steyler Verlag,1985; John 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F.Foucquet,S.J.(1665—1741),Roma,1982.国内学者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已故的阎宗临先生,1941年他在《扫荡报》副刊《文史地》上发表了他从梵蒂冈图书馆带回的一系列重要文献,这些文献以后绝大多数被方豪先生采用。参见阎守诚编:《阎宗临史学文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计翔翔:《博综史料兼通中西:〈阎宗临史学文集〉读后》,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2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47—368页;罗丽达:《白晋研究〈易经〉史事稽考》, 《汉学研究》(台湾)1997年第15卷第1期;韩琦:《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汉学研究》(台湾)1998年第16卷第1期; 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北京:宗教出版社,2002年;张西平:《梵蒂冈图书馆藏白晋读〈易经〉文献初探》,韩琦:《再论白晋的〈易经〉研究——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响》,以上两文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05—314、315—323页。
② 转引自林金水:《〈易经〉传入西方考略》,载《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67页。
③ 白晋的《天学本义》分别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Maurice Courant所编的Bibliothéque national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areens,japonais,etc的第7160号,7163号为《天学本义》;《天学本义》的另一版本为《古今敬天鉴》(两卷)编号为7161号;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分别有两个目录,一个是余东所编的Catalogo Delle Opere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XVⅠ- XVⅡ《天学本义》的编号为:25—1;由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编,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所整理的Inventaire sommmaire des manuscripts et impremeés chinois de LaBibliothéque Vaticane《天学本义》的编号为:Borg.Cinese.3。
④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316(14)《天学本义》白晋自序。
⑤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316(14)《天学本义》韩琰序。
⑥ 此原始文献有两份抄件,个别字略有不同,如其中一份将句中“料理”写成“畧理”,将“或用那里的人”写成“或要那里的人”。阎宗临选了其中没有涂改字的文献。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b),参见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169页;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81页。
⑦ 江西巡抚郎廷极在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五的奏折中,提到将送江西的传教士傅圣泽进京。罗丽达对方豪所讲到的有关白晋读《易》的十份文献做了很好的研究,见氏著:《白晋研究〈易经〉史事稽考》。
⑧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第281页。
⑨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原文献有两个抄本,文献中有“亦无不本于黄钟所出”句,阎本和方本均改为“亦无不本于黄钟而出”。参见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170页;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第282页。
⑩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原文献中有“假年月”句,阎本和方本均改为“假半月”。参见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170页;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第281—282页。
(11) 参见John W.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 Francois,Foucquet,S.J.(1665—1741),p.202.
(12)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此文献阎宗临未抄录。
(13) 参见John W.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 Francois,Foucquet,S.J.(1665—1741),p.202.
(14)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在这份文献的“恐病体难堪,抑且误事”一句中,阎宗临和方豪少抄了“抑”,但在“恐病体难堪”后加了一个“折”字,方豪在使用这个文献时也有疑虑,认为“折字下疑有磨字”,这是误判。“臣尝试过,在京病发之时少,而且轻”一句,阎和方本漏“且”字。见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170页;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第285页。
(15) Joan T.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 Francois,Foucquet,S.J.(1665—1741),pp.164—207.
(16) 阎宗临和方豪写为“通”,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第282—283页。
(17) 原稿有“会长”二字,后删去。
(18)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h),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第282—283页。
(19) 白晋在这里讲的会长是谁?罗丽达认为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骆保禄(Jean- Paul Gozani,1647—1732),韩琦正确地指出不是骆保禄,而认为是殷弘绪(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2—1741)仍不正确。因为此时殷弘绪是来华耶稣会的法国总会长,让白晋和傅圣泽将所有送给康熙的研究《易经》的文稿,也要送给会长看的指令是他下的,但具体去落实这一指令的是法国在华耶稣会北京教区的会长龚当信 (Cyr Contuncin,1670—1733)。也就是说,给白晋写信并具体审查他给康熙书稿的人是龚当信,而不是殷弘绪。而且殷弘绪1711年在江西,他是1722年才到北京。参见Joan T.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 Francois,Foucquet,S.J.(1665—1741),pp. 176 —179;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50页;罗丽达:《白晋研究〈易经〉史事稽考》。
(20)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第285页。
(21) 《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第86页。
(22) 参见白晋:《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冯作民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66年;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23) 《清圣祖实录》卷256,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甲子。
(24)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78页。
(25) 李迪:《中国数学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页。
(26) 《清史稿》卷45《时宪志》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69页。
(27) 董光璧:《易图的数学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页。
(28) 王先谦:《东华录》卷21。
(29)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
(30) 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参见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附录《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书》,李天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1) 参见Claudia von Collani.,P.Joachim bouvet S.J.sei Liebenund Sein Werk,Steyler Verlag,1985,pp.124—133。韩琦在《再论白晋的〈易经〉研究——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手稿分析其研究背景、目的及反响》中提出这个论点:“由此可看出白晋进讲《易经》的经过及其康熙的意见,从另一侧面也可反映出康熙对《易经》所含数学的浓厚兴趣。”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317页。
(32)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317(8),p.3.
(33)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317(10),p.1.
(34) 梵蒂冈图书馆Borgia Cinese 317—4,第22—24页。这份文献并未注明日期。
(35) 韩琦:《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
(36) 徐海松在《清初士人与西学》一书中认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梅文鼎。(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王杨宗则认为应是康熙,参见氏著:《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载《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四十年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37) 《康熙御制文集》卷19“三角形推算论”。
(38) 王先谦:《东华录》卷21;参见江晓源:《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7卷第2期,1988年。
(39) 梵蒂冈图书馆Borgia Cinese 319—4,其法文稿题为《代数纲要》(Abregé d' algèbre)。
(40) “九《借根方算法节要》上下二卷,共一册,有上述印记(即‘孔继涵印’,‘荭谷’及‘安乐堂藏书记’诸印)。按孔继涵藏本,尚有:十一《借根方算法》原书为三卷矣。其中十二《借根方算法》,八卷一种,又《节要》二卷,不著撰稿人姓氏,藏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算史论丛》第七卷,第69页)“《数理精蕴》编修前曾有《借根算法节要》一书问世,此书可能是西洋人译后给康熙讲课用的。”参见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第7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6页。
(41) 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1册,第218—219页,转引自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42) 参见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
(43) 参见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431—435页;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352—365页。
(44) 梅荣照:《明清数学概论》,《明清数学史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45)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杜、巴、傅分别指杜德美、巴多明和傅圣泽。
(46) 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439(a).杨、杜、纪、傅指杨秉义、杜德美、纪理安、傅圣泽。
(47) 《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丙辰。
(48) 这份奏书是耶稣会士李明在欧洲策划的。参见李天刚:《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9页;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217页。
(49) 黄伯禄:《正教奉褒》,参见李天刚:《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第49—50页。
(50) 黄伯禄:《正教奉褒》,参见罗丽达:《一篇有关康熙朝耶稣会士礼仪之争的满文文献》,《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
(51) 苏尔、诺尔编:《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沈保义、顾卫民、朱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2)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四件。
(53) 黄伯禄:《正教奉褒》,参见李天刚:《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第49—50页。
(54) 苏尔、诺尔编:《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1645—1941)。
(55)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7件。
(56)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2件。
(57)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61年,第124页。
(58)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4件。
(59)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1件。
(60)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2件。
(61)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19—132页。
(62)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3件。
(63)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25—726页。
(64) 白晋:《天学本义》,梵蒂冈图书馆Borg.Cinese.316—14.
(65)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22页。
(66)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32页。
(67)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735页。
(68) Claudia von Collani.,P.Joachim bouvet S.J.sei Lieben undSein Werk,Steyler Verlag,1985,p.209.
(69)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S176,f.340:白晋写于1715年8月18日的信(Collani所作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