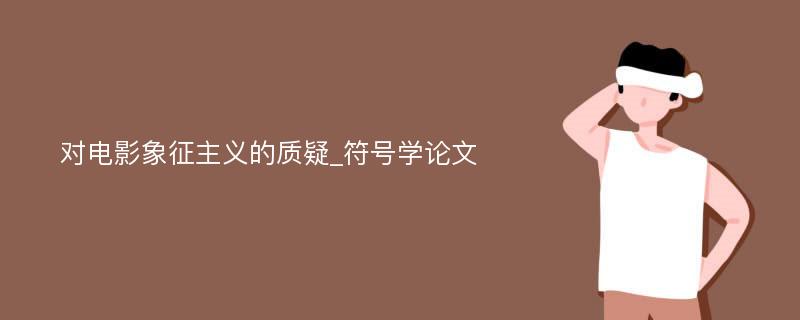
电影符号学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符号之本义及其基本功能
尽管符号学复杂得令人头疼,但是符号这玩意儿却出奇的简单。《现代汉语词典》说得就非常简单:“记号;标记”;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也不复杂:“常用的一种传达信息的基元,用以表示或象征人、物、集团或概念等复杂事物。”① 在这个定义中,“基元”一词至关重要。所谓基元,就是最基本最简洁最单纯,也就是最不复杂的东西,人类用这种东西来“传达”“复杂事物”的“信息”。换言之,它是人与人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信息运载工具,而这种工具最重要的特征是可以把大千世界的纷繁复杂化为简单。举例来说,“人”这个符号,在汉语书写时只有两笔,读出来也就ren这一个音节;同一个概念在英语书写中也不过people这6个字母,读出来也就两个音节,非常简单,但它却是全球60亿同类生物的总称,代表的是此前几百万年和此后不知多少千载地球文明的创造者群体。
在从猿向人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产生了交流信息的需要,可是,信息如何才能进行交流呢?当符号未曾产生之前的原始时期,每一个个体的感觉和意识都是单一的、特殊的,树是特殊的树,石是特殊的石,狼是特殊的狼,水是特殊的水,等等。在那样的情况下,交流的成本大得无法计算,甚至根本不可能。他们如果要表示黄河,就必须把对方拉到黄河边上去,如果他们当时离黄河有100公里的距离,那么,他们交流的前提就是首先得克服这100公里的距离。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成本。这跟我们今天使用货币是同一个道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货币就是一种价值符号,某一数量的货币代表某种量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一位农民揣一叠钞票上街,就可以把一辆汽车开回家,而如果他用同等价值的粮食去换一辆汽车,他得动用多少汽车来运载他的粮食?而汽车制造商又要动用多少交通工具才能把这些粮食运回去?那样的交易成本该有多高?
正是基于这一点,聪明的人类祖先发明了概念。所谓概念,就是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然后给它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符号。有了符号,才有了语言;有了语言,才有了信息的成几何级数增长;人类文明才得以长上翅膀飞跃式地发展到今天。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符号其实是概念的物质形式,没有概念,就没有符号。也就是说,符号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又是对感觉和知觉进行进一步深加工的思维工具。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符号产生的缘由,是为了将信息“打包”,从而节约信息交流的成本,而符号之成为符号,就在于它使本来纷繁复杂的东西变得简单。用符号学的话来说,就是用简单的能指,去指称复杂的所指。反过来说,如果能指跟所指一样复杂,甚或能指比所指还要复杂,那么,这个符号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比如说我们后面要讨论的“电影”。
符号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它的约定俗成性。既然符号是用来给信息“打包”的,那么,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之间必须事先有一个约定。举例来说,马路上有红灯和绿灯这两种符号,驾驶人员必须先学习“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这种学习就是驾驶人员和交通警察之间、驾驶人员和驾驶人员之间、驾驶人员和所有行人之间的约定过程。而幼儿从喊第一声“妈妈”开始,到进学校学习所有语言课程,都可以看做是他同社会之间的符号约定过程。只有当信息交流双方都承认了某种约定,符号才可能发挥作用。反之,则符号就没有意义。
此外,任何符号都存在于一个边界清楚的系统之中,也就是说,任何符号都是一定符号系统内的符号,离开了它所依存的那个系统,符号就将失去符号的功能。同样的书写方式(符号)在不同的符号系统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所指之物)。举例来说,“书”这个书写符号,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指“装订成册的著作”;同样的书写符号,在古汉语中既可以指“装订成册的著作”,也可以意指为“书写”这个动作;而到了日语中,则只能是指“书写”;在日语中,“装订成册的著作”则用“本”这个书写符号来表示。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一书中,大量引用早期人类学家们在非洲和南美原始部落中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原始民族所存有的大量装饰习惯在文明人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将120磅重的铜环挂在妻子的脖子上表示自己的富有和对妻子的爱心。我们之所以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我们和原始部落的人们不处在同一个符号系统之中。一件原本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一旦离开了特定的符号系统,就变得不可理喻了。
符号的另一个属性就是它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成熟的标志,是它的语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相对固化,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看它的字典词典编撰的成熟度如何。而当具有权威性的字词典面世以后,其符号系统的功能也就被固定下来了。一个书写符号,它的语音形式是什么,它的意义范围是什么,它的组合功能是什么,它的聚合特征是什么,字词典上标得清清楚楚,绝对不容更改和随意解释。而现代社会的一切交流,尤其是经济交换和司法运作,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种稳定性一旦松动,则现代社会将随之崩溃。
以上所列的这些符号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符号学的本质特征及其适用范围。这也是符号学的创始者瑞士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本人是一名语言学家的原因之所在。
符号学方法诉诸电影如何不可能
“电影语言”一词最初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一种惟电影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硬把它说成是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则势必牵强附会。这就是为什么马尔丹的《电影语言》一书尽管差不多普及到了中国电影工作者人手一册,但却没有人把它当做语法规范或语法手册来使用的原因。这是因为,在传统电影学范畴中,作为表达方式的规范只能停留于“文章章法”的层面,即作品的段式结构层面,再往下就不起作用了;具体到镜头内部的构成,以及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组接,则显然是不能用某种“语法”去加以规范的,镜头以及镜头之间的组接是完全个人化的,这是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留给艺术家的创造空间,电影艺术的创新正是在这一空间实现的。否则,电影作为艺术就失去了存在的权利。
仔细研究后我们发现,电影的表达方式和技巧之所以不能和人类自然语言等同视之,不能硬套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电影,首先在于电影没有自己固定的词汇系统。我们知道,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字典或词典,那是对字形、字音、词义、词性以及词与词组合规则的强制性规定,语法规则是建立在上述规则之上的,而基本意义固定的字或词是通过合乎规则的组合变化来实现其新意的。电影则完全不同,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可以任意阐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的意义与其载体同一。正如法国电影符号学鼻祖麦茨最终发现的那样,电影“符号”原本是一种“短路符号”。所谓“短路符号”,就是说其能指与所指在外部形态上完全同一,能指就是所指,所指就是能指,于是,本应作为替代原物的、轻便的意义携带物的能指符号,也就变得跟所指原物的本身同样沉重,无法不通过概念在语义的交换过程中随意携带。既然不能迈过概念这道关口,那么,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还有什么存在的权利呢?
索绪尔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发现了存在于一切人类语言中的音位,而音位在言语运行中的关键作用在于“区别性特征”。所谓区别性特征,是指甲符号与乙符号之间不容混淆的那个特征,举例来说,汉语中“今”和“京”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就在于前者的韵母是前鼻音,后者的韵母是后鼻音;汉字中“王”和“玉”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就在于“玉”字右下方的那一点。区别性特征必须是绝对清楚的,否则甲符号和乙符号就没法区分,没法区分就没法使用。索绪尔音位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有效地将语音符号划分到最小单位,观察信息传达过程中发出者与接收者如何有效地进行交流。
麦茨的电影符号学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当他企图把电影预设为一个符号系统的时候,他就必须首先解决一个问题,即电影这种“符号”系统中每一单个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换言之,既然他说电影是符号的集合,那么,那些所有集合的符号是什么?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麦茨的电影符号学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假说阶段,而不能像索绪尔那样自成体系。事实是,当麦茨把电影信息的最小单位划分到镜头时,就无法被继续划分了。由于镜头内部的信息与现实的物质空间在人类的视觉上同一,而又仅仅是在视觉上的同一,这使得我们不可能像对待现实物质世界那样,对其进行物理和化学方式的细分;即使细分是可能的,那也只能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愚蠢之举,因为,由此而获得的信息可能和作为一个叙事整体的电影本身风马牛不相及。
从信息学的角度看,电影镜头在本质上是一种无限不可分的,其在空间维度上是无限放射的,其在时间维度上是连续进行的。从大的方面说,电影镜头是没有边界的;从小的方面说,电影镜头内部的信息在物质上是无限可分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我们至少可以分解到像素或格的层面;但在意义上,它却是绝对不可分的。各种因素(不是元素)组合成一定量的信息团块,形成电影所需的基本信息单位。如果硬要拿语言学的工具去套的话,那么,它既可以被视为语素,也可以被视为音位。举例来说,一个长度是60秒的从空中航拍的现代战争场面的镜头,被拍摄的人物可能难以数计,各种火炮和战车成百数千,炸点不断在镜头前点燃,浓烟滚滚,炮声震天,而且各种物体都处于运动之中,每一秒钟或每一格都有无数生命在悲惨地死亡……请问,这是一个符号呢,还是若干符号的集合?如果说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符号,那么,难道就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关于残酷的符号吗?如果说这是一个关于残酷的符号,那么,难道就不能说这是一个关于壮美的符号吗?如果说这只是一个符号,那么,为什么就不可以说这是由军队、火炮、战车、爆炸、死亡、生存、正义与非正义、运动、冲锋、逃亡,甚至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无数符号的集合呢?如果说这是一个符号的集合,那么,用于集合的符号的数目究竟有多少?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边界何在?进而,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是什么?其所依据的组合规则又是什么?上述问题我们还可以无休止地问下去,只不过意义就不大了。
如果我们回溯一下人类符号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那是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是一个概念越来越精确化的过程。越到后来,就越倚重于概念的精确。电影发明的价值恰恰相反,它的价值在于使人得以回到复杂和多义,回到感性与知觉。著名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早在电影发明之初就指出:“一种新发现、或者说一种新机器,正在努力使人们恢复对视觉文化的注意,并且设法给予人民新的面部表情方法。”② 巴拉兹的这段话引自其著作《可见的人类》,该书中,作者痛感人类受抽象符号制约之苦太久,电影的发明使他看到了人类可以恢复通过视觉来传递丰富而多义的情感的希望,从而由衷欢呼。应该说,巴拉兹的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电影的出现,正是对人类符号文化日益精细、日益抽象的发展方向的一种互补性反动,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更趋丰富和立体。既然电影的发明是对符号文化的反动,那么,将电影视为符号,并用符号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电影,自然就会南辕北辙,驴唇马嘴。
有人之所以将符号学方法引入电影的研究中,是因为电影也是一种信息的载体,通过电影,我们可以获得信息。这本不错。然而,电影传递信息的基本原理和符号是完全不一样的。索绪尔明确指出:“曾有人用象征一词来指语言符号,或者更确切地说,来指我们叫做能指的东西。我们不便接受这个词,恰恰就是由于我们的第一个原则。象征的特点是:它永远不完全是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点自然联系的根基。”③ 索绪尔接着指出,天平可以象征法律,而车辆就不可以。按照索绪尔的定义,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④ 例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同一个概念,汉语读做ren,英语读做people,有道理可讲吗?没有,约定俗成罢了。电影则完全不一样,电影中的任何内容都是具体的,电影中的这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人,这一辆车就是这一辆车。电影的单格画面也好,单个镜头也好,都是现实的影像,而不是现实的抽象替代物。总之,你在现实中看到的是什么,在电影中看到的就是什么。不错,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要大量采用象征等手法的,然而,即使是象征手法的运用,也和现实中是一样的。举例来说,在西方,现实生活中天平象征法律,因而,西方电影中天平的出现就可以让观众产生法律的联想;而在中国,象征法律的不是天平,而是石头雕刻的狮子,那么,如果在中国电影中用天平来象征法律,观众往往就不会联想到法律,甚或可能联想到商品交换。这就印证了索绪尔所说,符号中能指和所指的连接是任意的,而象征与被象征之间的连接不是任意的。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语言学的革命性贡献,是他发现了语言以及一切符号系统的共时性特征:“一般共时语言学的目的是要确立任何特异共时系统的基本原则,……例如符号的一般特性就可以看作共时态的组成部分”。⑤ 而符号学正是建立在一切符号系统都必定处于相对静止的所谓共时状态这一点上的。与此相反,在电影影像和电影技法中,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共时性元素。几乎每一部影片都在寻求突破和创新,故事是新的,人物性格是新的,镜头处理是新的,剪辑方法是新的,声音效果是新的,因为创新是一切艺术生存的基础,电影概莫能外。推、拉、摇、移、全、中、近、特或许可以算是电影中的共时性元素吧,但这些又仅仅是技法而已,既不是能指,又没有所指,也没有任何语法意义,因此,我们在电影中实在看不到符号学施展的空间。
既然电影和符号不是同一类型的对象,那么,将符号学方法运用到电影的研究中就是值得怀疑的。而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电影符号学充其量可算做人类探索电影研究方法论更新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要说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有益的启示的话,笔者以为倒是证明了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的某种谨慎的正确:“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⑥ 因为,“电影语言”只是一种比喻,而不是语言本身,至少就今天人类的智慧水平来衡量,“电影语言”仍是我们“不能谈的事情”,所以,我们对它应该保持充分的敬畏,不要轻举妄动,说三道四,否则就会谬论迭出,闹出许多笑话来。
电影符号学荒谬之根源
我们指出电影符号学的荒谬,却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对电影作为特殊媒介的传达信息的机制进行探讨,我们所要指出的是,电影符号学对电影这一特殊媒介本质的把握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导致它最终南辕北辙,不知所终。就好比它只看到电脑和人脑有某些相似的功能,就把人脑当成了电脑,操起修理电脑的工具就来修理人脑。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要研究电影,首先就得弄清电影之为电影的本质,尤其是它的物质特性,这是我们进入电影研究的第一道门槛。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电影是人类的镜像,这本是不错的,只是其后来的发展错误地踏上了电影符号学的平台。
回望历史,人们常常会对古人的直觉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是因为今人所面对的一切都被遮蔽了太多文明的尘垢,从而不如古人的世界清亮澄澈,从而其对事物的观察和把握更为直截了当。回顾巴拉兹的著作,这样的感觉尤其强烈。“可见的人类”这一把握,可以说是对电影文明最直观,也最本质的把握。巴拉兹的研究完成于80年前,当时电影还处在襁褓期,今天看来难免粗糙和不系统,因而,我们不必过分认真对待他的每一个具体的结论。但必须指出的是,巴拉兹的研究思路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正如巴拉兹所指出的那样,电影发明之前,人脑的信息只能通过“印刷”技术复制的抽象的符号系统来进行远距离的表达和接收,电影发明之后,能进行远距离的表达和接收的就不仅限于抽象的符号系统了。这无疑使人类的文明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它是人类在已有的抽象文明的基础上,获得了一次“文艺复兴”,复兴了原本就属于人类的、只是被抽象文明排挤到记忆深处的具象文明,从而使人类的生活空间更加宽广,情感空间更加丰富。
人为什么能理解电影?就现实的层面来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如麦茨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因为,人在现实中所获得的信息并不都是来自语言——符号系统,甚至主要的也不是;除了睡觉时间,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随时都在接收着信息,这些信息传至大脑,受到大脑的处理、加工,于是人就理解了这些信息的意义。必须强调,在人获得的信息总量中,这些信息所占的比例,远比通过各种符号系统获得的要大得多。只是在电影发明之前,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被牢牢地限制在了“上帝”所规定的时空范围之内而已。电影的发明是人对“上帝”的一次造反,是人解放自身、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延伸自己感觉器官的一次革命。有了电影,人看得更远,听得更远了。正因为人在电影中所感知的信息与人在现实世界中所感知的信息同一,那么,人感知电影的心理机制与感知现实世界的心理机制也就同一,因此,研究人理解电影的机制的学理思路,就应该到心理学中去寻找。不错,人脑在处理和加工任何信息的时候,都离不开概念符号这个思维运行的载体,包括抽象信息和具象信息。但是,概念符号是在从感觉跃升到知觉的阶段才出场工作的。即使是抽象符号,也是首先以感觉的形态被人所摄取,到了知觉阶段才发挥其概念功能的。基于这个道理,我们也就没有理由相信电影符号学的假设,把电影中的信息强行规定为抽象符号的集合,然后再去解读那些“符号”所携带的信息了。
生命有限,时日无多。舍近求远,何苦来哉?
电影符号学之所以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行其道,几乎无人敢于置喙,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一登场就披着一件“科学”的外衣。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多斯在讲述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流变过程的时候,提到法国结构主义开山鼻祖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与丹麦语言学家雅各布森相遇,立即被索绪尔的学说征服,于是独创了他的“结构人类学”研究方法。⑦ 他说:“我们应该向语言学家学习,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在自己的领域使用同样严密的方法。”⑧ 不错,从20世纪初叶开始,普通语言学在索绪尔的领导下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且大获成功。而语言学似乎又横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可以通过语言学津梁,打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运用于社会科学,而这种雄心勃勃的计划,至少在20世纪的道义上又是不容置疑的。本文不打算置疑结构人类学等其他在现代语言学方法论平台上建立起来的法国学派,但是在笔者看来,至少连同列维·斯特劳斯在内的大师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索绪尔语言学派成功的前提,是他选择的方法来自于他面临的对象,即对象为先,方法为后。与此向反,现代语言学家以外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家们,则往往是方法优先,对象服从于方法。麦茨对这位祖师爷的教诲显然是言听计从,甚至如获至宝。从他初入电影研究领域的著作看,仿佛当时的他已经从上帝手中领到了开启电影密码箱的金钥匙,踌躇满志,前程远大。直到真正进入这个领域,才晓得牛皮不是吹的,硬着头皮朝里钻,把原本简单的事情越说越复杂,直到陷入自己布下的走不出来的迷魂阵。
吊诡的是,电影符号学戴着“科学”的面具粉墨登场,唱的却是一出彻头彻尾的反科学大戏,其中的意味无疑是悠长而深远的。毫无疑问,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壁垒鸿沟,二者互为表里,互相借鉴,互相促进,本是一切学术的题中之义。但是,人文社会科学者必须晓得,科学不等于技术,也不能等同于方法。这就好比算命先生在他的业务中使用了电脑,我们就不能因此而认定算命成为了科学,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人文社会科学者对自然科学的借鉴,首先是要借鉴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是什么?说来简单,实事求是而已。而虚妄之“事”,是不可能“求”出“是”来的。另一方面,一切科学研究的目的,都在于对纷繁复杂的现象界用简单的道理去给予说明,这既是一切科学家研究的理路,也是一切科学存在的价值。电影符号学把电影中的事情说得比电影本身还要复杂,把电影中原本凭着直觉和常识都能理解的问题拉进谁也无法理解的概念迷宫之中,使人们花在理解概念问题上的时间,比花在理解电影本身上的时间还要多若干倍。如此一来,就使目的和达至目的的工具交换了位次,工具异化为了目的,而目的反倒成为证明工具合法性的工具了。这无疑在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因而也是不足取的。
在笔者看来,符号是迄今人类进化史上最伟大的发明,是人类从猿到人最关键的一步,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其对人类的意义远远超过冶炼术、印刷术、蒸汽机、电脑等技术类发明不知若干万倍。与之相接近的伟大发明只有文字一项,而文字本质上不过是语音符号从听觉向视觉的延伸,获得进一步的物态化而已,其功能在于使之超越语音所受到的时空限制,从而得以传输于万里之远,留存于千年之后,由此而文明远播、积累、发酵、光大。因此,笔者当然绝对不反对符号,也没理由反对符号学。笔者置疑电影符号学的初衷,是反对对符号学的滥用。笔者期许的是,让符号学回归符号系统,莫让它孤魂野鬼一般四处游荡,指手画脚,招惹是非。
维特根斯坦说:“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当然不会有其他问题留下来,而这恰好就是解答……人们知道生命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灭。”⑨ 是的,既然电影的呈现方式与现实世界对于人类的呈现方式同一,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电影的呈现方式看做是与生命问题同样难以解答的问题,看做是上帝对人类的某种规定。
笔者的理解是,符号是人的创造物,所以,人能够认识符号;而人是上帝的创造物,所以,至少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人是不能认识人感知世界的机制的。而人通过电影感知世界的方式与人在现实中感知世界的方式大体相似,所以,人认识电影意义生成机制的难度,绝不亚于人认识自己感知世界的生理、心理机制的难度,哪里可能如麦茨想象的那样简单?
注释:
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58.198.
②[匈]贝拉·巴拉兹著.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25.
③④⑤[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4,102,144.
⑥⑨[奥]维特根斯坦著.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97.
⑦⑧[法]弗朗索瓦·多斯著.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