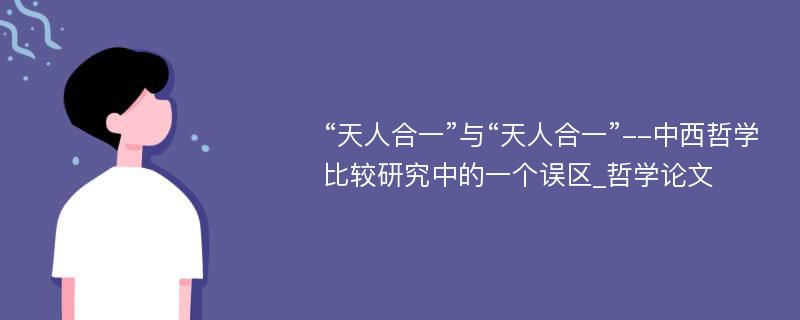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中西论文,误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领域,有的学者将中西哲学的基本精神分别概括为“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并以此来表征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已成定论,并且经常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尤其是看到西方某些思想家针对科技社会的诸多异化现象而表现出对东方文明所谓“天人合一”境界的浓厚兴趣,并以之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立即感到欢欣鼓舞,似乎不仅为这种中西哲学差异论找到了最好的旁证,而且证明东方文明实优于西方文明,甚至认为东方文明才是世界文明的唯一出路和归宿,这种由妄自菲薄一变而为妄自尊大的偏狭心态无疑与对中西哲学之差异的误解有关。因此,对于“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说进行一番考查和清算,已成为比较研究的紧迫工作。
2我们应该看到,中西比较研究并非只是站在一方的立场看待另一方。“比较”应该是某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视界交融”的“对话”。
由此看来,假如我们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分别概括为“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那么这一概括至少需要满足下述条件:1、天人关系构成了中西哲学共同的主要问题;2、它所涉及的概念在哲学上是相对确定一致的,并且在两种不同语言中可以找到相通互换的对应概念;3、“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天人相分”观念在西方哲学中亦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可以分别代表中西哲学的基本特征。然而我们发现,“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说并没有满足这些基本条件。
首先,“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所关涉的天人关系问题的确可以看作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但却不是或不完全是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一般说来,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说天人关系问题与思存关系问题无关,然而它们无论在形式、内容、意义还是在问题的层面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关系问题主要是内化为人生道德的问题来探讨的,而思存关系所关涉的则是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如此说来,我们的“对话”就有可能不是针对同一“话题”而进行的。
其次,当我们以“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概括中西哲学的基本特征时,它们所关涉的概念应该是相对确定一致的,否则就有可能陷入对所谈所论者究竟意指什么并不清楚尴尬境地。事实的确如此。就中国哲学而言,无论“天”还是“人”,它们的主要含义不下10余种,例如“天”,就有“上神”、“天象”、“法则”、“自然”等不同的含义①。由于“天”或“人”在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因而“天”与“人”之“合一”的方式亦势必有所区别。如此说来,当人们以“天人合一”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时,在理解上不一致是难免的。
同样,我们也很难在西方哲学中“天”“人”概念找到合适的对应概念。例如中国哲学之“天”可以译作heaven (天体、天国、上帝)、nuture(自然)、law(法则)甚至substance(实体),但是正如耶稣会传教士当年以中国哲学之“天”比附基督教之“上帝”而不得要领一样,上述概念亦都无法体现出中国哲学中“天”的恰当意义。更何况在西方哲学中这些概念所关涉的问题向来分属不同的部门(如神学、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所以即使我们能够找到合适的对应概念,那还要看它所关涉的问题对于中西哲学而言是否确属同一层次而且同样由类似的核心部门所研究的问题。
最后,即使上述条件不是不能满足的,也就是说,假设我们可以经过审慎的解释将天人关系调整为中西哲学共同的问题,并且能够将“天”“人”等概念梳理清晰,而且在西方哲学中为之找到合适的对应概念,我们仍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有没有充分的根据将中西哲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这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将“天人合一”看作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与此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而且除了少数人各持极端而外,大多数思想家在论及天人关系时其实是兼讲“合”与“分”的。②原因很简单,若天人从来无别就没有必要言“合”,既然讲“合”一定是针对“分”的。
如果说将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天人合一”无论如何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天人相分”则是极成问题的。假如我们可以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待西方哲学,那么在西方哲学中显然鲜有哲学家只讲“相分”而不讲“合一”,它讲“分”的目的无非也是为了“合”。古希腊人视自然为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大宇宙,城邦乃中宇宙,而人是小宇宙。因而人存在于宇宙之中并与之同质同构,亦即是同一的,哲学的目的就是去认识这同一的根据。中世纪人们认为人原本与上帝同在,由于原罪与上帝疏离,人生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信仰等方式使灵魂得到拯救,以克服这一分离而重返伊甸园。即使近代哲学发展了一种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看作改造与利用的对象,但它同样主张人之本性与一切自然存在的本性是一致的,知识当然要符合对象,科学的目标无非是去发现支配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之统一的自然法则。由此可见,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西方哲学“固执”于主客对立或人与自然分离的“局限”,都不能否认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一样是兼讲“分”与“合”的。它的一元论立场就是明证。
当我们讨论无人关系时,无论“合一”还是“相分”,都是就无人关系的存在状态而言的,或指原初状态,或指现实状态,或指理想状态。就原初状态论,应该说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同样承认“天人合一”。而就现实状态论,显然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一样试图克服“相分”,而将“合一”作为谋求和最高目的和理想境界。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论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的区别。对中国哲学而言,它以其理想的“合”掩盖了现实的“相分”,而对西方哲学来说,它则以现实的“相分”掩盖了理想的“合一”。换言之,这种观点其实是将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同西方哲学对现实的观念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无疑是毫无意义的。既然中西哲学同样既讲“相分”亦讲“合一”,而且都要求克服“相分”实现“合一”,那么以“天人相分”来概括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显然没有充分的根据。
其实,当人们以“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概括中西哲学之差异时,并未深究或以为没有必要深究它所关涉的概念是否严格确定。因为他们只是一般地就人与宇宙的关系而言。主张中国哲学主要将天或宇宙看作包罗万象之整体与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自然过程,人生存于其中并与之是统一和谐的;而西方哲学则以人为认识主体,以宇宙自然为认识对象,强调人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区别,突出了人在宇宙中的独立性和特殊地位。因而中国哲学以和为贵,西方哲学则以矛盾和对立为重。甚至于有人简单地把“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看作是一讲“和合”,一讲“分离”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然而,中国哲学重“和合”的思维方式并非与“分离”无关,而是基于“分离”包含“分离”的。且不说中国哲学中有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仅就“和合”而论,绝不能说中国哲学只是从“和合”来看待天人关系的。例如程朱理学确有“天人本无二”、“天人一物”之论,但这不过是为克服“天人相分”而确立的可能性和前提。若人性中并无理与欲的分别,人乃无欲而始终与天理相合,也就没有必要讲“存天理,灭人欲”了。纵观中国历史,它也绝非一团和合气氛,更多的是社会动荡与战乱灾难,大至国小到家,经常受到“分离”的威胁。正是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哲学更崇尚“和合”。
另一方面,西方哲学并不是只讲“分离”而不论“和合”的,实际上“和合”或统一同样是它的基本观念和理想目的。不错,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的确更强调人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区别,更强高人的独立性,更重视判别、对立和矛盾,但是它也从统一的角度看待分离,并且统一看作分离的根据与归宿。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大致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某种方式与他们心目中的宇宙根本实在(自然、存在、实体或上帝)达到统一,所以大多数哲学家持一元论的立场,没有人或很少有人真的将“分离”视作终极性的结果。西方哲学不仅从区别的角度考查自然,同样也从整体的高度寻求将自然万物统一起来的最高根据。
3 当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确是两种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的哲学形态,这是事实。不过这一差异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也不能笼统地看作一重“和合”一重“分离”的两种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中西哲学的差异呢?虽然上述差异论缺少充分的根据,但是经过我们的分析考查,它把我们引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上:既然中西哲学皆兼“分”“合”,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有可能表现在究竟如何克服“分”而达到“合”,亦即克服“分”的不同方式上。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力求通过理性认识去克服“分离”达到“合一”,主张知天才能识人;而中国哲学则力求通过内省直觉超越“分离”,感悟“合一”,认识人便是知天。这两种克服“分离”谋求“合一”的不同方式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形态。我们认为,哲学不可能只是一种形态,但是只要是哲学就必有其共同之处。换言之,中西哲学应该是“殊途同归”,源自同样的问题且指向同一个目标的。现在,西方哲学已经自觉列其“科学思维方式”的局限,中国哲学也应该反省其直沉觉感悟内省的方式的局限,去经受理论思维的洗礼。当然,我们对中西哲学之差异的解释只是探索性的,而且更深刻的文化、历史、经济等原因尚有待研讨。不过无论这一解释是否准确,它的思路应该是合理的。
以上分析或许并不准确恰当,也可能失之偏颇。我们的“质疑”更重要的目的是使人们自觉到在这个领域中许多基本的东西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以便引起人们对比较研究的基础工作的重视,将精力投入到诸如比较哲学的概念、方法和目的等基础工作上,更多一些具体详细的分析研究,那么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注释:
①参见冯禹:《天与人——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②参见冯禹:《天与人——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