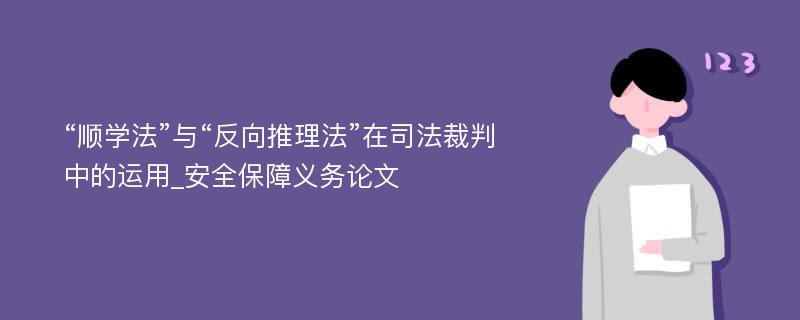
司法裁决中的“顺推法”与“逆推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论文,顺推法论文,逆推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14)01-0073-16 一、导论:材料、问题与思路 在司法裁决中,为维护法律的自治性与安定性,法官负有依法裁判的义务,须严格遵守法律进行逻辑推理,对是非曲直做出合乎法律的判断。但法律不可能是一套完全逻辑自洽的系统,其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法官在判决过程中必须对判决后果进行科学、合理地预测和评价,使之合乎社会的需求。由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已经成为我国当下主流的司法政策,此政策的提出具有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意味着法官要通过精湛的裁判技艺灵活应对当下的社会转型以及因之产生的各种利益诉求。就简单案件而言,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均无争议,对于裁判的前提与裁判的结论往往容易形成社会共识,在此情况下,法官可以根据逻辑规则自上而下地进行推理,裁判过程符合法律思维的要求,裁判结论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简单案件的裁决很容易达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但对疑难案件的裁判,法官经常面临法律的安定性与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之间的矛盾,法官严格或僵化地适用法律往往会出现不合理的结果,因此,在疑难案件的审判中,法官往往采取从后果出发选择判决理由的裁判思路。以下两则案例体现了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审判思路。 [案例1:乔某诉建设银行洋桥支行案]2009年4月30日下午,在北京市丰台区一家银行发生一起歹徒劫持客户进行抢劫的案件。乔某为银行保洁员但并不当班,正在办理银行业务时,歹徒商某用仿真手枪和尖刀劫持了她,威胁银行营业员交出银行钱款。营业员并未直接将钱交出,而是将成捆的钱拆散拖延歹徒,以等待警察救援。商某通过用尖刀划伤乔某的方式逼迫银行营业员交出钱款14万元,拿到钱后未离开银行多远就被警察擒获。事后乔某不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而且诊断患上反应性精神障碍,乔某因而状告银行要求赔付损失8万元。但是,法院认为,银行已经采取合理的安全保障措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于乔某受到的伤害银行并不存在过错,故驳回了乔某的诉讼请求。① [案例2:布德诉拉辛银行案]1970年4月27日,约翰·布德在拉辛银行办理业务时,一名歹徒持枪劫持了约翰,并用枪顶住约翰头部,要求银行职员莫菲交出钱或者打开门,此时莫菲位于与歹徒隔开的防弹橱窗后,她没有听从劫匪的命令,而是趴在了地上。随后,劫匪枪杀了约翰。约翰妻子作为原告将拉辛银行告上法庭,认为银行及其职员对其丈夫的死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伊利诺斯州高等法院认为该案属于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和先例遵循的疑难案件,然后根据后果的预测和评价创设了判决理由。在法院看来,如果判决银行因未服从歹徒命令而承担赔偿责任,将会激励歹徒犯罪,更不利于保护顾客生命安全与银行资产,最终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② 这两则案例案情极为相似,判决结论基本相同,但是判决思路却大相径庭。案例1的主审法官通过对法律的解释和事实的认定来完成法律推理,我们将这种审判思路称为“顺推法”;而案例2的主审法官,通过预测判决将要引起的后果,根据判决后果的可欲性来选择判决理由,从而得出判决结论,我们将这种审判思路称为“逆推法”。对这两种类型的法律推理可以做出大致区分:“一种是向后看的、原则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教义学的推理;另外一种是向前看的、政策论的、工具主义的后果论的推理。”[1]4法律方法的分歧事实上隐含着深层的观念差异,因为,法官对裁判方法的选择总是受到某种司法哲学的指导,司法哲学作为法官系统的裁判理念总是如影随形地融会于法律适用的过程之中,成为法律适用的灵魂与主导。正如卡多佐所说:“每个判决提出的问题其实都涉及一种有关法律起源和目的的哲学,这一哲学尽管非常隐蔽,实际却是最终的裁决者。”[2]17所以,对两则案例审判思路的比较,必然会追溯到其背后的司法哲学,一般而言,“顺推法”体现了法条主义的司法哲学,而“逆推法”则体现了后果主义的裁判理念。因此,本文的任务不仅是要展现两种法律思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将裁判方法放在更为宏大的司法哲学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为此,本文将通过案例解析对两种裁判方法的逻辑结构和思维规程进行微观论证,也在宏观的层面上对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这两种司法哲学进行反思检讨,通过批判性的论证揭示这两种司法哲学的适用场域和适用限度,并通过严谨的学术论证反观中国问题,为正确理解当下中国的司法政策提供智识上的贡献。 二、“顺推法”:法条主义的审判 (一)法条主义的审判思路 对于案例1,原告认为,银行对在银行办理业务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该事件,银行保卫人员及相关负责人反应迟缓,措施不力,造成了原告身心伤害,故要求银行赔付8万元。而被告认为,银行对现场的处置行为符合应急预案的要求,已经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其自身行为并无过错,不应承担对原告的补充赔偿责任。另外,原告已经与劫犯商某之间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已履行,这一调解内容应视为原告认可的可接受的实际损失,银行不应再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院判决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乔某所受伤害由劫犯商某造成,应由商某赔付;第二,根据现场的监控录像显示,银行已经实施了合理的安保措施、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第三,银行对歹徒的行为无法预见,对于歹徒造成人质的伤害,银行并无过错。③ 该案涉及经营场所经营人对客户的安全保障义务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侵权责任法》均做出了明确规定。④就该案的判决理由来看,主审法官在该案中的推理过程如下:(1)在银行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Tx),银行对于第三人给客户造成的伤害不应当承担责任(ORx);(2)在本案中银行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Ta);(3)故银行对劫犯给客户造成的伤害不承担责任(ORa)。该案判决推理的逻辑图式可以表达为:[3]275 (1)(x)Tx→ORx (2)Ta (3)ORa 这就是法学三段论的逻辑结构,也可以表达为:[4]150 (1)对于所有的x而言,若x满足构成要件T,则法律效果R适用于x (2)a满足构成要件T (3)法律效果R适用于a 从该案的审判思路来看,主审法官实际上采取了一种“解释+演绎”的审判思路,在裁判理念上,这体现了法官对法律解释正确性的坚信不疑和演绎推理有效性的坚决维护,即认为通过法律解释能够在法律体系内部确定“安全保障义务”的界限,通过演绎推理能够建立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之间的“逻辑涵摄”关系。这种审判思路体现了波斯纳对法条主义者的刻画:“理想的法条主义决定是三段论的产品,法律规则提供大前提,案件事实提供小前提,而司法决定就是结论。这条规则也许必须从某个制定法或宪法规定中抽象出来,但与这个法条主义模型完全相伴的是一套解释规则,因此解释也是一种受规则约束的活动,而清除了司法裁量。”[5]38 在法条主义的审判理论中,演绎逻辑处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具有逻辑有效性的法律论证才具有形式上的有效性,才能实现法律规则的效力。“一个演绎性判断,亦即一个结论性命题隐含于另一个或者若干个命题当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无论前提和结论的内容是什么,只要从形式上前提中包含着(或者等同于)结论,一个演绎性判断就是成立的。”[6]20因此,演绎证明通过逻辑充分保证结论隐含于前提之中,从而保障判决结论来自于法律规范。为捍卫形式推理的有效性和法律的自治性,法条主义者坚信对于任何疑难问题,法官总有足够的智慧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解决。法条主义因此具有这样的特征:第一,坚信法律的自足性。将法律作为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排除法律之外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第二,维护法律方法的自治性。在法条主义者看来,法律方法是一种科学的司法智识,通过运用科学的审判技术,司法裁判将产生唯一正确的答案。作为法律思维的法条主义强调规则的至上性、司法裁判的逻辑中立性,并坚信借助司法三段论从作为大前提的法条中逻辑地推导出判决结论。第三,法条主义是一种守成的法律思维,法条主义者要求裁判者严格忠诚于法律,坚决拒绝法官造法,法条主义的“司法决策具有向后看的性质,只反映规则或判例发布之际的知识状况,而不对新知识开放”。[5]64法条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说明法官“如何依法裁判”的法律思维,也是论证法官为何“应当依法裁判”的司法哲学。为限制国家权力的可能滥用和无限扩张,为维护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功能,罪刑法定、三权分立、法律至上成为建构西方法治国家的根本原则,但是,这些根本性的法治原则也极大限制了法学家的司法想象。根据这些原则所隐含的逻辑,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以致法官长期被法学家设定为“自动售货机”的形象,司法三段论被西方法学家扩展成了普遍化的司法理论原型。因此,法条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西方自由主义法律历史传统长期积淀形成的政治美德,代表了法律至上的法治传统、通过法律限制权力的宪政传统、通过法律保障权利的人权传统,是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等现代法治原则的司法衍生品。 (二)法条主义审判的困境 法条主义将演绎逻辑作为“依法裁判”的核心逻辑,但是,这种以为仅凭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就能解决复杂个案的心态只不过体现了法律人的致命自负,通过演绎推理维护法律的自治性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理论梦想,在晚近的英美法律推理理论中法条主义因而遭到普遍诟病,因为,在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决中,以法律三段论为核心的法条主义面临着诸多困境。 1.法律解释的难题 法官要顺畅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推理,必须通过解释来熨平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褶皱”,即通过解释建立规范与事实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法条主义者为捍卫自己的立场,假定了一种认识论:认为通过解释能够发现清晰、客观的文本意图或者立法意图,从而解释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就案例1而言,主审法官若要运用司法三段论进行逻辑推理,首先须对法条中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通过要件分析的方法对该不确定概念进行解释,如根据以下要件来判定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是否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防范设施有效、警示明确醒目、管理谨慎周到、制止侵害果敢、实施救助及时、保全证据妥善等。⑤要件分析意味着对事物特征的类型化处理,通过去粗取精的方式挖掘事物特征的构成要素,从而方便人们把握事物的特征,但是,法官还需要对各个构成要件进行再解释,如“有效”、“醒目”、“周到”、“果敢”、“及时”、“妥善”等概念,对这些概念进行再解释将使法律解释陷入一种无限递归的窘境。比如,在案例1中,假如在合理时间内及时交出银行钱财以挽救人质生命属于“及时地实施救助”的话,那么多长时间才算“及时”,这仅仅通过法律解释难以确定,因为通过解释来确定模糊的语词可能会陷入一种连锁推理的悖论。⑥“如果对一个标识所作的解释本身需要解释,就面临着无限回归的威胁,并且作为可以用来使我们的行为与它相符的规则观念,将消失于一个解释的深渊。”[7]67 为消除规则的不确定性,法律解释学为法官裁判提供一系列解释方法,这被当作一套程序性指令来填补因规则不确定而出现的约束力真空。迄今为止,法律解释学已经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份包含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清单,但是,法律解释学从来没有清晰地界定各种解释方法的边界,系统地说明各种解释方法的运用规则,这本质上缘于“解释”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解释是对既有规则的遵守与适用,还是为消除模糊情形而另行创造规则;解释是客观含义的发现与揭示,还是主观意义的阐发与创生,无论是在语言哲学还是在解释学上实际上都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理论家们往往根据不同的研究立场来定义“解释”这个概念,并以此建构各自的解释理论。解释概念的不确定必然导致解释方法的不确定,文义解释方法要求裁判者恪守法律的文义界限,但是文义的界限往往模糊难以确定;目的解释方法要求法官根据法律的目的进行灵活解释,但是目的的主观性使法律的目的和解释者的目的缠绕在一起,因此,在模糊标准适用的边际情形中,可能不会有任何解释技术有助于案件判决,法意模糊的消除实际上有赖于解释主体对解释方法的选择。事实上,对于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无论是立法历史还是法律文本只是给出大概的标准,从未给出精确的可以度量的规则,甚至可以认为立法者已经将此交给司法者进行决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对《人身损害赔偿条例》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应当根据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所从事的营业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⑦所以,仅仅依靠这些解释方法不但无法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反而加剧了人们的“解释性分歧”,因为人们凭借不同的解释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且法律解释学无法为解释方法的排序和消解解释方法的冲突提供明确的答案。⑧因此,法律解释学无法为法官提供一套关于在何种情况下选择何种解释方法的元规则,这将导致规则的每次适用都产生新的含义,法律解释只能是法官进行隐蔽式价值判断的幌子,法官事实上以解释的外衣进行独断的价值判断,以逻辑的形式掩盖造法的事实。 所以,法律解释的方法论从来都无法避免法官独断的价值评价。比如,“安全保障义务”是一个中心意思和边缘结构都不确定的概念,从语言学上来讲,这些概念本身都属于评价性概念,都带有语言使用者的价值判断,从本质上来讲是无法做到精确的。“法学界努力地要把价值概念中所包含的价值陈述,普遍地预先处理,所运用的方法便是通过描述的要素来定义评价性概念,但是,用来描述要素的概念仍然是评价性的。”[8]15在案例1中,法官在进行事实认定时,不仅要对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条的事实构成要件进行判断,还必须对案件事实进行价值判断,判断该案件事实是否与法律规范中预设的价值判断相符合。本案法官之所以能进行自上而下的逻辑推理,关键在于他对“安全保障义务”的独断性解释,这并不是对文本意图或者立法原意的忠诚探索,而是凭借法官个人经验或直觉进行的价值判断,从而将服从歹徒命令交出银行财产以保护人质生命的做法排除在“安全保障义务”的范畴之外。“逻辑形式背后是一种对立法依据之相关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这种判断经常未形诸于文或潜藏在意识里,但却是整个诉讼程序的根基和精髓。”[9]465“解释+演绎”式的法条主义审判并未保证司法裁判的逻辑中立性,更不能杜绝法官在裁判中的价值判断。因为虽然解释是进行演绎推理的前提,但是解释却不是通过演绎的方式做出的。 2.价值衡量的困境 一个法律判断能够完成形式推理并不能确保是完全理性的结果,原因在于推论的前提往往是存在争议的。演绎推理并非完全自足和自我支持的法律论证模式,而时常求助于外部推理。因此,法律论证的结构可以区分为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前者的目的是保证大小前提到判决结果的推理合乎逻辑,后者——作为法律论证理论的主题——的目的是为前提本身提供正当性依据。[3]273尽管法律论证理论要求,在法律论证的内部证成上,要尽可能地展开逻辑推导,以使某些表达达到无人再争论的程度,[3]82最大限度的逻辑推导能使法律判决尽可能地符合“可普遍化”的要求,但是,逻辑推导永远无法代替价值判断,因为逻辑推导的展开往往是以“价值共识”作为前提的,法律论辩势必从内部证成延伸到外部证成。通过外部证成形成价值共识,这就必然会突破实在法约束的范围而进入到道德论辩(普遍实践论辩)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论辩是法律论辩的基础。 在这两则案例中,人们从对“何为安全保障义务”的争论均延伸到银行财产与个人生命的道德选择问题,有人立足于保护个体生命权的立场,产生对“银行顾钱不顾命”的质疑,甚至认为法律规定本身是通过模糊不清的条款为银行开脱责任,法律的道德品性遭到考验,也有人认为保护银行财产是银行职员无法推脱的职责。⑨当法律论辩从内部证成延伸到外部证成时,人们的争议必然从根据法律的论辩发展为关于法律的论辩,法律论辩从一个解释的场域(法律是什么)走向一个衡量的场域(法律应当是什么)。因此对于疑难案件而言,伦理立场的普遍实践论辩往往是法律论辩的价值基点,疑难案件之所以疑难最终是由于达成确定的普遍实践论辩的结论之困难,在个案中对有效的法律规范的认识,最终的工作不在于逻辑意义上的“合法性”判断,对有效的法规范的认识本身包含着该法规范“正当性”的考量,而这一正当性考量正是来自于道德论辩。 当人们对法律存在争议时,往往诉诸更为抽象的道德原则或者“法理依据”,通过一个更高的价值标准中断人们的争论,这表现为“义务论”的论证模式。根据“义务论”的论证模式,一种行为在本质上是“善”或“正当”的,这是以某个法律共同体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基础进行证成的,不需要对某个法律规范的个案适用后果进行合理性的证成,因为在这种论证模式下,法律所关涉的道德价值是绝对正确的,不需要从其他的道德判断中推演出来。然而,在疑难案件的裁决中,道德原则或者“法理依据”往往是不确定的,并且往往相互冲突。在日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抽象的道德话语并无助于形成道德共识,反而加剧了人们的道德分歧。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当代道德言词最突出的特征是如此多地用来表达分歧,而表达分歧的争论的最显著特征是其无终止性。我在这里不仅是说这些争论没完没了,而且是说它们显然无法找到终点,似乎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任何确保道德一致的合理方法”。[10]9比如,在案例2中,人们从关于“银行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争论延伸到个人生命与银行财产哪个更为重要的道德争议,但是,在这样的道德判断上并不存在共识。如对于银行财产与人质生命的价值权衡,先例基纳威诉福克斯案(Genovay v.Fox)中存在这样的判决理由:虽然银行的行为能够阻挠抢劫犯严重犯罪行为的成功实施,而且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损失,但是受害人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价值更为重要。然而,案例2的主审法官并不这样认为。⑩ 现代社会的人们在基本价值问题上之所以存在“共识危机”,是因为社会成员往往借助于个体的直觉和情感做出价值上的独断,这体现了两种伦理学立场:直觉主义和情感主义。直觉主义认为对于某一行动是否正当或者某一行动的目的是否是“善”的,都是无法通过理性来认识和证明的,而只能通过人们心灵中的直觉来把握。但是,作为“常识道德”的直觉“无法用清晰而准确的语词陈述,缺乏真正自明,不与其他真理相悖的特征,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公理来指导实践”。[11]118所以,笼统地认为受害人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价值与银行的财产价值哪个更重要,只是一种朴素的“法感觉”。尽管很多法学家直言不讳地认为,法官的裁判是通过“法感觉”来进行的,但是作为直觉的“法感觉”与理性并不矛盾。因为作为直觉的“法感觉”只是论证的起点,只有经过理性的方法论说明之后,法官的裁判才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道德判断如何进行理性地证成。情感主义是对直觉主义的某种追随,这种伦理学立场最终将道德判断归诸人的主观态度,将道德分歧归诸“态度分歧”。在没有共同德性和统一权威约束的前提下,现代社会的人们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做出道德判断,因此,情感主义的根基扎根于原子式个体主义的现代社会。比如,在案例1的争论中,很多论据建立在个人朴素的道德情感和主观意志上,有人从银行职员捍卫国家财产的职责出发,有人立足于受害人的弱者身份或者受伤程度甚至其家庭状况,但这些论据只说明人们在案件讨论中的激烈情感色彩,并不是对一个道德判断的理性证成。个人的道德直觉和情感偏好导致人们在道德判断上的分歧,这根本上在于直觉主义和情感主义属于不可知论的伦理学方法论。为此,阿列克西致力于构建理性主义的法律论辩理论,认为在人们能够遵守理性论辩程序的前提下,人们对具有道德争议的法律判决就会达成共识,从而通过交流消除道德分歧,让裁判者走出价值衡量的困境。直觉主义或者情感主义的伦理学进路实际上通过某种决断的方式,为规范性命题在直觉或者主观态度处找到个体性的“基础理由”,阿列克西的论证理论则试图发展出一套约束主体言语行为的理性规则与形式,以对规范性命题进行理性地证立。然而,阿列克西为我们所提供的理性的论证规则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为“理想言谈情境”的论证情境的存在以及无法确保实现的对言谈主体内心的要求,(11)虚幻的理论前提使主张“通过交流达成共识”的法律论证理论成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在人质受到歹徒威胁的情况下,银行职员是应当交出钱财还是选择保护银行的财产,这似乎是一个道德两难问题。尽管道德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抽象的道德原则,但是,“疑难问题都不发生在原则上而是在适用上”,[12]178抽象的道德原则从来不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道德话语在司法判决中往往通过修辞的方式在起作用,或者通过独断地方式去解决分歧,而绝不是通过交流地方式去达成共识。这是因为,持有不同道德立场的人们不仅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还具有针锋相对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交往理性”可能只澄清一些误解,但无法最终消除偏见,更无法借此达成共识。道德分歧的存在是因为道德理论缺乏科学理论处理经验事实的技术,也就无法对道德探讨的前提以及对推理和检验具体道德命题的手段达成共识,即使在选择手段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如果分歧发生在目的的确定上,就根本无法达成共识了,因为不同目的在道德理论中被认为是不可通约的。以赛亚·柏林曾以价值多元难题的形式,指出人类无法逃避在善与善之间做出选择,但善与善之间并不存在可相容性和可通约性,因而如何选择,是一个无解的难题。[13]47所以,在抽象的意义上,无论是银行的财产还是人质的生命都是正当的。 人们借助于道德理论很难在道德争议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通过科学论辩能够解决事实上的争议问题。这是因为科学论辩能够通过可验证的手段解释和预测一些经验事实,所以“科学话语趋于合流,但是,道德话语总是趋于分流”。[14]60如在美国著名的布朗案的审理中,对于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否违背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中的平等原则,最高法院内部存在严重的道德分歧,因为不同的法官具有不同的平等观念。但是,大法官马歇尔的一个社会科学实验却产生强大的说服力,即由黑人学童从四个圆点(两个白色,两个棕色)中选择他们最喜欢的,几乎所有黑人学童选择白色,这充分证明了黑人学童的自卑心理,而这正是由种族隔离造成的,马歇尔大法官正是通过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所提供的社会调查成果推翻了在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政策。(12)同样,在案例2中,法官预测判决银行败诉会产生歹徒劫持人质抢劫银行,以及银行配合歹徒的行为激励,从而造成更大的社会损失,这种对判决后果的预测更符合一般人的经验或常识,而经验往往具有可验证性,因此能够摆脱道德分歧而产生强大的说服力。正如博登海默所说:“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就正义问题发生分歧时,这种争议的解决往往是以能够正确确定和评价经验性理由为转移的。”[15]273 在疑难案件中,道德或者价值判断上的分歧使具有统一理解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难以形成,基于不同的道德理由,人们将会选择不同的法律规则,自上而下的司法三段论难以真正完成。这样,法条主义者往往是根据某种价值判断限缩或扩张对法律规则的解释,从而使案件事实落在规则含义范围之内,用表面上的形式推理掩盖了事实上的价值判断,并有可能产生法官依靠个体的直觉和情感而进行的价值独断,从而造成司法审判的主观恣意。在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决中,通过法律解释难以发现明确的文本意图或立法意图,通过价值衡量难以达成共识性的价值排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明确的大前提而无法进行司法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而需要根据判决后果的预测与评价证立或创设裁判规则,这就为后果主义审判的出场提供了契机。对此,霍姆斯认为:“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制定法律,参考司法决定的可能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法官对这些后果的直觉,而不是常规司法意见中展现的抽象道德原则和正式法律分析,推动了法律变化。”[9]457 三、“逆推法”:后果主义的审判 (一)后果主义的审判思路 在案例2中,原告主张经营者对顾客的安全具有合理注意的义务,银行职员未服从劫匪的命令而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银行的过错还在于银行内部没有通过一项政策,并向其雇员做出这样的明确指示,要不惜代价的保护客户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并且认为在抢劫发生后银行未配备相应的应急策略,因此,原告要求银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认为,根据美国侵权法的规定,土地所有者或承租人对于被邀请者的安全具有一般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银行并没有绝对义务去阻止罪犯对顾客的侵害。本案中两造同样是就经营者对客户在经营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界限存在争议,对此,法院首先将该案认定为无明确法律规定和无先例可以遵循的疑难案件,然后再通过后果的预测与评价创设了判决理由。在法院看来,美国侵权法重述只阐明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应该对为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给侵害人之外的第三人带来的不合理伤害承担责任,然而本案中造成的人身损害不是由银行直接造成的,而是由罪犯造成。法院通过对先例的分析认为,合理的安保措施和防护装置未必能完全杜绝持枪抢劫案的发生,完全听从劫犯的命令也未必能避免人质所遭受的伤害,因此,不能强加给银行完全听从歹徒命令的义务。法院又通过区分先例说明了先例与待决案件的区别,根据相关判例,如果犯罪行为能够合理预见,银行具有消除危险的义务,这属于银行对客户在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在辛恩诉农业银行案(Sinn v.Farmers Deposit Savings Bank)中,对于歹徒已经点燃的炸弹导火索,银行具有及时警告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对于罪犯行为的结果可以合理预测。然而,本案的情况区别于先例,因为本案的关键是,对于罪犯行为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下,对于突如其来的罪犯命令,如果拒绝是否会产生赔偿责任的问题,而不是对于未来可能预见的犯罪疏于采取预防措施是否产生赔偿责任的问题。因此,在本案的上诉审中,主审法官没有从先例中寻找到可以适用于当下案件的判决理由,而是进行了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该案主审法官认为,假如强加给银行服从歹徒命令的义务,只会对歹徒有利,并且服从歹徒的命令并不会降低顾客遭受侵害的风险。事实上,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将会激励银行服从歹徒命令,无法保护银行资产安全,也将会激励歹徒利用人质来抢劫,因此会增加顾客在经营场所受到侵害的风险。(13) 不同于法条主义的审判,该案法官并没有通过对“合理注意”、“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或者通过对先例的类比来为当下案件的解决寻找判决依据,而是基于对后果的预测与评价进行判决,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和政策导向的判决思路,即不是裁断由谁来承担已经发生的不幸,而是向前看,做出的裁决要使今后发生同样不幸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因为司法裁判属于对损害责任或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行为,人们作为趋利避害的个体,判决结果必然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产生影响。所以,在这起银行抢劫案中,法官要弄清该案裁判后人们将来的行为动机是什么。法官若判原告胜诉,则自此以后遇到劫犯劫持人质时,为免于再次被起诉和支付赔偿,银行会产生把钱交给歹徒的动因,同时,这也意味着歹徒会产生劫持人质的动因。基于裁判后果的考量,法院应当避免更多不利后果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银行必须胜诉。这种裁判方法即为根据裁判后果选择裁判理由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需要向前看,考虑这个案子的裁决对将来会产生哪些效应——对类似情形中所涉及的各方,他们尚未决定将来做些什么,他们将来的选择可能会受到该案裁决的影响。”[16]5 (二)何为后果主义的审判 在德国,后果主义的审判被称为“结果导向的法律适用”,即“在证成法律裁判时,考量裁判的后果并在给定情况下,根据解释的后果来修正解释。简单地说,古典法教义学通过处理过去的事实并借助给定的规则来控制裁判,而后果取向则通过对裁判所导致之效果的期待来调控裁判”。[17]264这种裁判方法是基于德国法学对传统法律教义学解释规则的质疑而产生的,由于解释规则及其适用顺序不具有明确的操作性,解释规则在个案裁判结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限。因此,法官究竟是应当适用解释规则来获得解释结论,还是应根据解释结论选择解释规则的问题,成为德国法学界争论的问题。后一种做法更容易为实践所验证。在德国宪法学界,这种根据解释结论选择解释规则的做法,被称为宪法解释的结果取向,亦称结果考量、政治后果考察、政治后果取向、结果评判论证、价值判断等,此过程就是一个“价值”透过结果取向“进入”并决定“规范”解释的过程。[18]在英美法理学界,后果主义的审判理论是基于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反思而产生的,基于对形式主义法学机械司法的批判,又基于对现实主义法学价值司法的反思,英美法理学家试图在严格司法和自由裁量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麦考密克据此认为,法官在进行演绎推理之后应当进行“二次论证”,根据判决结果的预测和评价来进一步证立裁判规则,即“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Consequentialist Argumentation),法官对摆在其面前的各种可供选择的裁判规则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予以审慎考量,以权衡利弊。[6]125 在普通法系,后果主义既是一种结果导向的裁判思维,又是一种被称为法律实用主义(legal pragmatism)的司法哲学。根据麦考密克对英国判例的随机考察,这种结果导向的判决理论普遍存在于普通法系的司法过程中,“在某些案件中它甚至因为这种法官的判决模式而成为控辩双方的一种论证手段和辩论规范,并以此构成了以往对依法或依规则裁判的理解的颠覆”。[6]137后果主义审判之所以在普通法系普遍存在,与普通法系的法律文化、制度结构和法官素质不无关联,普通法系的法官因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而被赋予“社会工程师”的制度角色,从而法官较为关注判例对后案的影响。尽管由于法律文化和制度结构的差异,后果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大致而言,作为司法哲学的后果主义具有这样的特征:第一,后果主义将法律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否定法律的自足性而主张法律需要在变革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第二,后果主义是一种个案情境式思维,坚持法律意义的语境论,认为法律的效力是有条件的,在个案情境中,法律条文的含义会发生变化;第三,在法律解释上,后果主义否定法律条文所表达的语义或逻辑对个案裁判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认为法律所体现的目标和精神对司法裁判起决定性作用;第四,后果主义否定法律价值的一般化和抽象性,而主张法律价值的多元性。作为法律思维的后果主义是一种以后果为基础的论证模式(Consequence-based argument),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是根据某个判决结论所引起后果的预测和评价来选择判决理由的论证模式,将某种行为正当性的证立建立在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考量上。后果主义法律论证的逻辑图式可以表达为:[19]459 结论:行为X应当被实施 因为:行为X导致后果Y(经验性命题) 并且:根据目标Z后果Y是可欲的(规范性命题) 从逻辑图式来看,后果的可欲性往往被特定目标所检验,这些目标又往往蕴含着特定的价值或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后果论的论证和目的论的论证往往是相互支持的,这也是后果论证与目的论论证容易混淆的原因。但是,目标的可欲性并不能单独决定后果主义法律论证的成立,后果论证的成立必须符合论证的充分性、后果的可欲性、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三个关键特征。为回答“论证是否充分”、“结果是否可欲”、“行为是否导向结果”等三个批判性问题,将构成新的论证以支持既定论证。因为这些支持性论证与随后的批判性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依赖于这些支持,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才真正成立。因此,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论证形式,必然被其他论证形式所支持,往往是复合论证的一部分。就该逻辑图式来看,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既包含通过观察和预测进行判断的经验性命题,又包括根据目标对后果可欲性进行判断的规范性命题。所以,后果主义审判是在个案的具体的事实情境中进行价值判断,而非在价值冲突中做出终极性决断以决定哪种竞争性利益更有价值。 (三)后果论证与价值司法、目的论论证 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是一个价值透过结果进入并决定规范解释的过程,但是,价值判断如何通过后果影响法律解释,学术界对此并不存在统一认识,这导致学术界对后果论证的方法论属性存在理解混乱。德国法学家普珀将后果论证作为目的论意义上的价值评价,但是,他又主张“为了让法律适用者留意到这些进一步的实践后果,有必要在目的论的解释方法之外,另设一个对于解释后果的特别审查,也就是所谓的‘后果考察’”。受德国法学影响的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则将结果考量视为社会学解释,将后果论证作为对社会效果进行预测和考察的解释方法:“所谓结果取向的解释方法,简单说,即解释者把因其解释所作决定的社会影响列入解释的一项考量,在有数种解释可能性时,选择其社会影响较为有利者。”[20]253学界关于后果论证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往往将后果论证等同于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或利益衡量,同时,基于对法律实务的观察,学界又普遍认为后果考量的法律思维隐藏在法官的司法判决之中。(14)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后果论证是一种规范性的法律方法,不如说后果论证是对司法判决实践的描述性说明。 由于学界对后果论证的构成要素及其操作规程无清晰说明,关于后果论证实践功能的看法也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解释是一种结果。通常是在结果早已确定之后,才选择解释的方法。所谓解释方法只不过是对文本补充的事后注脚而已”。[21]306根据这种观点,法官先凭借其直觉的法权感发现裁判结论,再根据结论寻找解释规则。这种观点将法律解释方法作为法官进行实质价值判断或法律续造的修辞策略,已经沦为十足的现实主义法学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解释规则决定解释结论的形成,但是,后果论证对裁判结论起修正作用。(15)基于对法律安定性的考虑和维护宪政体制下权力界限的划分,这种观点试图维护解释规则在裁判中的有效性,但是,对于后果论证如何修正裁判理由及其操作规程又语焉不详。这样,裁判者的价值判断、现行法秩序的理性要求、社会公众的期待等都可以作为需要加以考量的后果,后果论证的界定不清从而为“价值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甚至会沦为极端的法律现实主义或庸俗的实用主义,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产生解构法治的危险。 学界对后果论证的理解混乱,缘于学界混淆了法律论证中发现与正当化的逻辑,这导致学界将后果论证混同于现实主义法学的“价值司法”。在笔者看来,后果论证并非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因为法律解释是以法律规则或法律文本为核心而展开的法律方法,而后果论证是在面对解释的疑难时而适用的法律方法,是基于裁判后果的预测与评价对裁判理由进行正当化的裁判过程。后果论证作为一种裁判方法,关键在于对裁判规则的正当化“解释需要基于论据而在众多解释性方案间进行选择。通过论据来证成或证立所选的解释,要与获得结果的实际过程区分开来。前者涉及的是证成的过程,后者涉及的是发现的过程。”[22]70在法律论证理论看来,法律发现和法律证立的过程是两分的,前者关涉到发现正确判决的心理过程,后者则关涉判断的证立以及在评价判断中所使用的评价标准。后果论证属于法律发现之后的证立过程,是对判决评价标准的确证,属于证立的逻辑而非发现的逻辑。因此,立足于法律论证的理论框架,司法裁决中的后果论证实际上是通过对裁判后果的预测和评价来正当化判决理由的证成模式,而非凭借裁判者主观的法感觉发现裁判结果的心理过程。 后果主义的法律论证也不同于评价法学的目的论论证。在哲学上,目的论思维是根据正义理念进行推理的思维方式,手段始终服务于待实现的目的,后果论思维则是依照因果律进行推理的思维方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需要凭借经验判断来完成。“实现一个目的的可能性问题必须与该目的内容的正义性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前者依照经验法则——因果律位于其中——考虑实际事件,后者旨在对意志意识的内容形成系统认识。”[23]107手段与目的关系不同于原因—结果关系,目的意味着人们向往或追求的某种事物,对手段与目的关系判断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而结果是被看作由某种原因导致即将形成的东西,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属于经验判断的范畴。尽管手段服务于目的,但手段与目的之间未必存在因果关系。手段可能完全外在于目标,如为消除贫困所进行的税收调节;手段也可能包含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如法律程序价值的实现是伴随着法律程序的部署来实现的;在这两种情形下,手段和目的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可能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如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返还,法律的手段只是根据一定道德标准所进行的指示,这和法律的目的并无任何因果关系。“在道德规范的背景下,当事人之间的交往事实产生正当理由,在不考虑将来预期和后果的情况下,这些理由在具体案件中即具有证明正当性的论辩力量,其力量并不来源于服务于目标后果的判决。”[24]41 在法学方法论中,根据法律规则的目的或者立法者的目的所进行的论证为目的论论证。在司法实践中,目的论论证往往发生在为某种结果、价值进行辩驳的复杂论证中,而后果论证则是建立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关系的科学预测基础之上,通过对判决结论与后果之间关系的经验判断,再根据一定的价值准则对后果的可欲性进行论证,从而实现判决的证成。这两种法律方法具有不同的逻辑图式: (1)解释X是可欲的,解释X导致后果Y;根据目标T,Y是可欲的(后果主义论证) (2)解释Y是可欲的,Y符合价值(目标或原则)Z,Z是可欲的(目的论论证)[25] (四)后果主义审判的限度 后果主义的判决因法官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为法律之外的因素进入司法过程开通渠道,使法官产生摆脱一般规则束缚的冲动,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司法审判的不确定性,后果主义的判决理论因此引起了法治主义者的警惕与担忧。因此,后果主义审判须经受批判性思维的检验,防止造成“价值司法”的危险,以避免对法治的解构与颠覆,这同时也说明了后果主义审判的前提和限度。 1.后果主义法律论证须满足“可预测性”的要求 追求形式正义,实现“同案同判”,是传统法治主义者所坚守的基本立场,唯有如此,法律才具有可预测性,因此,一个判决理由若在个案中证立,那么它同样能够适用于类似的案件,也就是说,判决理由的证立须满足“可普遍化”的基本要求。法条主义的拥趸据此认为,后果主义为司法行动只能提供地方性的而非普世化的指导,这使法律命题无法满足“可普遍化”的证立要求,法官在后果的掩护下会变得任意裁量而不受拘束,从而使法律判决没有任何的可预期性。但是,问题并非如此,后果主义审判所考量的后果是“系统后果”而非“个案后果”。所谓系统后果,指判决对类似案件所产生的一般后果,如同立法者在立法时所考量的事实,其目标在于通过考察判决的系统性影响建构普遍有效的规则;所谓个案后果,是指个别的、非典型的后果,即在具体个案情状中的特殊后果。[26]因此,后果主义实际上是着眼于判决的系统后果,根据判决结论对类似案件的系统性影响创制一般性的规则,而非根据个别裁决中特定当事人的特定后果创造个别化的裁判规则。 事实上,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理论对立被夸大了。法条主义所推崇的依法裁判(实际上是依据规则裁判)已经包含了依据后果裁判的内容,很难想象法条主义的裁判不考虑立法机关创设规则时所考量的后果(系统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纳认为,“如果把足够的强调放在审判的系统性后果上,那么法律实用主义就同法律形式主义合二为一了”。[27]79后果主义审判实际上是在疑难案件的裁决中基于判决的系统后果创设裁判规则,同时,又使个案裁判的正当性与可预测性保持着适当张力。在后果主义审判中,“法官在裁决一个非常规案件时要做的就是尽力得出一个在当时情形下最合理的结果,同时适当地考虑到诸如维持与先例判决的连贯性,并且尊重语言和宪法及制定法文本中可辨别出的目的为解释者划定的界限之类的有关‘理性’的自由运用的系统性限制”。[28]正如案例2的判决,法官既保持了待决案件与先例的连贯性,根据先例认定银行并不具有无条件服从劫犯命令的义务,又通过分析该案判决对类似案件的系统性影响,使判例规则具有可预测性。这样,既促进了判例规则的进化,又维护了判例制度的稳定性。 2.后果主义法律论证须满足“可行性”的要求 在裁判方法的建构中,后果主义将法官的视角从对语义客观性的探索或者价值客观性的追求扩展到各种经验性的社会科学,通过对后果的经验性统计及预测确保案件的可靠解决,通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来保证司法判决的客观性,以化解不可通约的道德分歧,预防因道德直觉和主观情感所造成的价值妄断。正如波斯纳所说:“法律实用主义的一个关键信条是,不存在把法律推理同其他实践推理分开的一般性分析程序,法律推理要摆脱法律语词的限制,从论证——贬义的‘修辞’,即没有事实支撑的语词较量——走向数据:统计学、精细测度、照片、图表。”[5]225可见,后果主义法律论证的证立,意味着司法裁决所依据的可欲后果是“外部后果”而非“内部后果”。所谓内部后果,指法律体系内部的后果,是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或法教义学理论能够确定的逻辑蕴涵性的法律后果;所谓外部后果,指法律体系之外的后果,是通过经验方法论的工具得以观察的对经济或社会产生影响的行为后果。[29]81后果主义法律论证所依据的后果并非通过语词的相互指称或逻辑关系的判断就能够确定,而必须满足“可行性”的要求,即该后果必须是能够通过经验加以证明的事实上的可能后果。 对后果“可行性”的预测意味着对判决效果的确定,包括判决的直接效果和判决的远程效应,对效果的确定依赖于社会科学与法学的科际合作,因为“传统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律方法论在现代快速变迁的社会已经明显不足,法学的自主性只是一种迷思,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合作,才是提高司法决定透明度并加以控制的唯一途径”。[20]256法官的司法裁决尤其是终审法院的判决不仅对个案中的当事人产生影响,还往往影响到类似案件的判决而产生事实拘束力。在通过法律解释无法产生确定结论的情况下,需要借助社会科学来控制法官的评价过程。利用社会科学进行结果论证的经典案例是美国“布兰代斯摘要”(Brandeis brief),在1908年马勒诉俄勒冈案(Muler v.Oregon)中,布兰代斯为捍卫女工的权利,规制最低工资和最长工作时间,他凭借自己丰富的社会科学素养,大篇幅援引统计数据和医学文献,说明劳动时间过长对妇女健康所产生的危险。(16)这说明后果主义论证要满足“可行性”的要求,需要法官提供充分的经验性证据以科学预测判决后果。这需要法官掌握一定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使法官的司法决策从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转化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在此情形下,“决策者知道各种结果的收益以及这些结果发生的概率,决策者可以根据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对各种结果进行权衡选择,这样就可以直接将期望效用最大化”。[30]185 法官毕竟不是社会科学的专家。很多人据此展开对后果主义审判的批判。(17)在他们看来,在审理期限的限制下,司法机关掌握的信息往往不完备,司法机构不具有立法机构的信息优势,无法在充足的时间内集思广益地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协调各种竞争性利益。鉴于司法机构既不具有信息优势,也不具有更具优势的信息处理能力,法官在有限时间内很难凭借其有限理性对判决结论的系统性影响进行确定和测度。必须承认,法官对判决后果的预测确实无法达到社会科学专家的水准,但即便如此,司法判决往往也是结果导向的。即使有些法官在表面上严格依法办事,遵循先例,表面做出完全不考量后果的司法判决,但事实上,法条主义的判决正是因为法官通过后果主义的考量做出了“理性选择”。尤其对于一审或初审判决,提高工作效率,避免能动司法的批评,避免错案追究,这些考量都可以成为法官做出法条主义判决的内在驱动力。比如,轰动一时的许霆案,一审与二审的差距如此之大的很大原因在于一审法院为了避免“错判”风险,而做出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判决,法官的判决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后果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考量,而非基于法官对法律文本的“正确理解”。可见,法官基于对后果的考量而做出司法判决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基于对法官能力的怀疑而彻底否定后果主义的审判思维大可不必。因为,司法判决的真相本来就是法官凭借有限信息做出的理性的解释选择,是一种经验不确定和有限理性状态下的司法决策。事实上,经验性的研究已经证明,在信息不完备和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即使法官不掌握社会科学的专业技能,法官往往可以凭借经验法则(Rule of Thumb)对判决后果做出合理预测。[31]经济学已经证实了经验法则在人类决策过程中的可靠性,经验法则在经济学中是基于重要信息进行决策的试探法(heuristic)。在司法决策过程中,经验法则同样有助于法官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使法官凭有限的重要信息做出合乎理性的司法判决。(18) 3.后果主义法律论证须满足“可欲性”的要求 后果论证是根据特定目标对判决后果进行评价,这一方面需要对判决的后果进行确认;另一方面需要说明价值衡量的具体尺度。在对后果做出预测时,法官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各种可能的后果中做出评价性选择,因此,后果权衡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价值评价问题。价值评价总让人们警惕价值恣意的危险,从而后果主义在具体语境中对价值判断的考量容易让人误解为价值相对主义。因为按照态度学派的观点,受法官前理解的影响,不同法官对后果的评价与权衡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是,这只是对后果主义的一种误解。后果主义审判所考量的后果不是“决定后果”而是“适应后果”,所谓决定后果是指一条法律规范的效力与适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间接后果,而所谓适应后果则指权利主体为了能够在一条规则的适用中获得利益或避免损害而改变其行为的作用,这涉及法律规则对权利主体行为的影响或激励。[26]决定后果与适应后果未必一致,因为人们在法律规则的影响下会做出某种适应性的策略行为,这未必是法律规则的决定后果。比如,为保障孕妇的劳动权益,可以通过一项法规来保障孕妇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孕妇劳动权利得以保障或改善的“决定后果”,反而会产生雇主不愿雇佣妇女从而造成妇女就业机会减少的“适应后果”。后果主义对后果的评价并不是仅仅关注立法者在法律规则中所预设的价值,而是根据判决所产生的适应后果来判断法律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需求的满足程度或具体利益的保护程度。因此,后果主义对后果“可欲性”的价值评价并不同于法条主义式的价值判断,法条主义只看判决结论与过去的法律价值是否和谐一致,而不去衡量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理想后果。而后果主义是通过一种经验性的方法,将价值问题转化为事实问题,来确定价值衡量的具体尺度。具体的经验性的方法是这样展开的:“法律工作者遇到实际问题后,会先明确问题所涉及的需求和利益,然后把它们转化为可行的目标,对目标的追求可以解决或缓解现实问题。与具体问题有关的事实和可适用的法律手段也必须加以确认和鉴别,对可选手段的效果进行事实的评估,继而对可能出现的后果和副作用做出预测。”[24]42因此,后果主义对后果“可欲性”的价值判断并非法条主义者通过先验原则所进行的道德判断,而是将自然科学的“探效逻辑”运用到价值理论中,根据实际需求和利益的最大化满足程度来确定价值。我们应当认识到,后果主义反对基础主义的价值理论,但又不同于价值相对主义,更不能将之归为主观主义的“态度学派”。后果主义反对一般的、先验的价值或原则,也反对将法官的价值判断完全归之于法官的意识形态、生活经验、个体性情等主观性因素,而主张价值应当寄托在每个事实性的后果之中,手段的有效性也通过经验性的方法进行评估,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通过对手段和目标的评估来影响司法裁决。看来,后果主义的“评价”难题或许是一个伪问题,后果主义通过对具体事实情境的强调,避免了价值判断的一般性和绝对化,也避免了价值判断的主观性。符合法治观念的后果主义审判是受到约束的“规则后果主义”而非“行为后果主义”。 四、两种审判思维的结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无论是法条主义还是后果主义,都有法官任意司法的危险。对形式正义的过分依赖导致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承受着巨大压力,使法官处于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紧张关系中,法官不得已用法律逻辑掩盖其实质的价值判断,从而出现判决理由表达与实践之间的悖反;若对后果主义审判所依据的“后果”界定不清,对其适用场域和适用限度界定不明,法官就会有滑向任意司法的危险,可能导致司法权的过度扩张。因此,我们要消除司法过度能动的危险,同时要避免司法的过度僵化,就不能偏执一端,把两种审判思维绝对对立起来,事实上,只有实现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首先,无论是法条主义还是后果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司法哲学或法律方法的成立,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场域。在社会稳定时期,社会权利在既定规则之下得到合理配置,法官的任务就是要像自然科学家一样,运用一般规律解释自然事实,运用稳定的规则处理常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法条主义的审判理论和法律方法,常规案件在既有的法律系统内能够得到圆满解决;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不断涌现新型的权利或利益诉求,法官必须处理法律的安定性与社会变动性的矛盾,以解决反常规的疑难案件,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若希望通过对法律的整体性解释和体系化整合,来维护形式逻辑在判决推理中的核心地位,无异于在囚笼里跳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借助于新的经验去修正形式逻辑的大前提,进行“超越法律的续造”,但是,后果主义的法律续造并非盲目的“法官造法”,而是基于经验的合理预测使法律的发展与变化建立在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基础之上。 其次,在复合的法律论证结构中,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的论证同时存在,并且相互支持。我们知道,法律解释在法律体系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在法律存在疑义时,法官要将法律作为一个融贯的体系来对待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需要进行法条主义的法律论证,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解释方法,运用类比论证、反对论证、当然论证等论证手段,确认包含在法律体系内的深层价值,在法律体系内部得出法律解释的结论,以维护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和一致性;但是,法官在适用法律规则时必须关注法律规则在个案情境中的适用效果,而法律目的和预期效果可能是不一致的,这就需要法官借助于目的论证、归谬论证、后果论证等论证形式,通过对法律后果的科学预测,重构隐含在法律体系中的价值或目标,进一步证成判决。因此,在疑难案件中,法官要证立对某一规则的解释,既要根据潜在的价值或原则进行融贯性和一致性的形式论证,也要根据法律的潜在目标或目的进行后果论证,这两种论证形式相互依赖。这主要体现为:第一,后果论证为法官在疑难案件中创制裁判规则提供正当化的论证方式,为演绎性证明大前提所需要的裁判规则进行证成。比如案例2的审理,法官并没有从先例中抽取判例规则,而是根据后果的预测和评价创设新的规则,这实际上是先通过后果论证来创制司法裁判的大前提,然后再通过演绎性证明产生判决结论,只不过后者为法官所省略而已。因此,后果论证是形式论证的支持而非替代。第二,后果论证能够弥补形式推理的局限,在法律论证的层级上属于外部证成或二次证明所运用的论证形式。基于法律解释的难题和价值衡量的困境,内部证成所需要的大前提要么模糊不清,要么存在规范冲突,而后果论证为法律规则的解释和对备选的裁判规则的权衡,起着关键作用,能够进一步证成内部证成所需要的大前提。第三,对后果主义论证限度的剖析说明,后果论证并非终局性的论证,需要经受其他论证形式的检验才能成立,尤其是,“通过后果论证所追求价值的过程必须标明一种合理的一致性,亦即一个判决的后果应当与相关的法律原则的目的相协调一致”。[6]146 再次,在司法裁决中,对于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哪一种法律论证形式对一项判决的证立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取决于判决证立的语境。任何法律论证形式都必须接受批判性思维的检验,即一个合理论证的成立,必须能够接受另一种论证的怀疑与质问。在法律解释具有争议的案件中,法官要在相互对立的解释结论中进行选择,需要判断哪种解释结论的后果更具有可欲性,如果法律后果可欲性是根据法律体系内所蕴含的价值判断的融贯性论证来证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原则的融贯性或一致性的法律论证对判决的证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法内价值的体系化整合能够形成价值共识,法律推理的大前提仍然在法律系统内部得以证立,形式逻辑对于判决的证立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假如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结论都能够根据法律原则进行融贯性证立的情况下,意味着法官从不同的法律原则或道德信念出发,会形成多种融贯的不同方案,好比“对一首诗恰好有两种解读方式,每一种都能够在文本中找到充分的支持表明它是系统的、融贯的,两个原则中每一个都能够充分支持一个不同的决定,满足一些似是而非的符合关系(lausible theory of fit)”。[32]161在这种情况下,要根据法律目标对判决的实际后果进行科学预测,根据社会科学的效用标准对后果的可欲性进行判断,此时,后果论证对于判决的证立起根本性作用。 最后,两种审判思维结合,本质是由法学性质决定的。法条主义将法学视为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律科学,旨在将法学打造成逻辑自足的学科体系,通过法学通说不断凝聚价值共识,通过打造具有示范性的知识范式,使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更具同质性,从而维护形式逻辑在判决中的核心地位。后果主义将法学视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法学,旨在打破法律的自足性,将法律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工具,使法律服务于社会目标,借助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使法律的运行与发展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法学既是一种追寻何为正义的理论理性,更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所以,法学是兼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性质的学问。只有综合运用法条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理论来认识法学,才能在审判思维和法律方法上,形成更为全面正确的认识。 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决中,既要“向后看”,使司法判决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立法者的要求,又要“向前看”,使裁判结论符合社会的要求。对于司法裁判而言,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同样既应掌握的推理技术,又需掌握裁判艺术。然而,司法裁判不能仅仅依据法官的直觉和经验或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裁判智慧做出,而必须将司法裁判技艺纳入到“法律科学”的框架内进行探讨,从而通过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提高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因此,对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必须从宏大的政治话语转移到微观的技术论证上来,防止其沦为某种肤浅的政治口号,为司法权的扩张赋予某种政治意义上的合法性,使后果取向的司法判决沦为现实主义的“价值司法”或者完全以民意为导向的民粹主义司法。因此,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需要我们从法律思维的内部视角研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技艺,为法官的裁判活动提供规范的方法论指导,使司法裁决受到法律教义和法律方法的内在约束,同时,也需要借助于社会科学的专业技术为法官对后果的评价和预测提供科学的外在保障,唯有如此,才能在我国的转型期实现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内在统一。 ①参见该案判决书:(2010)丰民初字第10943号;该案网络直播庭审实录参见http://www.chinacourt.org/index.php/chat/chat/id/5696.shtml,2013年9月5日;主审法官文章参见邢丽华、乔学慧:《我主审的全国首例人质状告银行案》,《法律与生活》2010年第18期。 ②See Boyd v.Racine Currency Exchange,Inc.NO.45557.56 Ⅲ.2d 95(1973)306 N.E.2d 39 PINEY BOYD,Appellee. ③参见该案判决书:(2010)丰民初字第10943号;该案网络直播庭审实录参见http://www.chinacourt.org/index.php/chat/chat/id/5696.shtml,2013年9月5日:主审法官文章参见邢丽华、乔学慧:《我主审的全国首例人质状告银行案》,《法律与生活》2010年第18期。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之后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也明确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案发生于《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主审法官事实上以《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作为判决依据。 ⑤关于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分析,参见汤啸天:《经营者场所安全责任的合理边界》,《法律科学》2004年第3期。 ⑥连锁推理悖论说明任何概念都是一种模糊的“类”,最典型的是谷堆悖论,既要回答多少粒谷子才能成堆,一粒谷子不能成堆,再加一粒也不成堆,以此类推,加到多少粒谷子才是谷堆,无法界定清晰的界限。参见[英]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126页。 ⑦参见黄松有主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⑧如拉德布鲁赫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耍熊的人看到公园布告上写着“不得带狗入内”,那么他是否可以把熊带入公园呢?根据类推法,他不能,因为对狗适用的规定必然适用于熊;但根据相反的推论(或者严格的语义解释),他就可以把熊带入,因为熊毕竟不是狗。参见[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⑨相关评论参见裴晓兰:《庭审现场播放案发时监控录像人质当庭质疑银行顾钱不顾命》,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0-06/19/content_560052.htm,2013年6月25日;《掏钱不慢,银行被判无责》,http://www.morningpost.com.cn/xwzx/bjxw/2010-07-01/59914.shtml,2013年6月25日;奥一网:《女子银行办业务遭劫持,诉银行索精神赔偿被驳》,http://news.163.com/10/0701/17/6AHATF1I00014AEE.html,2013年6月25日。 ⑩See.Bovd v.Racine Currencv Exchange,Inc.NO.45557.56 Ⅲ.2d 95(1973)306 N.E.2d 39 PINEY BOYD,Appellee. (11)关于法律论证理论为司法裁判所提供的论证规则,参见[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58页。 (12)See Brown v.Broad of Education of Topeka,347 U.S 483(1954). (13)See Bovd v.Racine Currency Exchange,Inc.NO.45557.56 Ⅲ.2d 95(1973)306 N.E.2d 39 PINEY BOYD,Appellee. (14)由阿图尔·考夫曼教授、乌尔弗里德·诺依曼教授和约亨·施奈德博士主持的慕尼黑研究计划“最高法官改判的论证理论视角”,确认了结果评判论证最经常地出现在德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中。参见施罗特:《哲学诠释学与法律诠释学》,载[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John E.Simonett教授则通过对28个典型性案例的考察说明结果导向的判决模式普遍存在,并通过考证说明,在25个州的上诉法院的判决意见中,可以发现“结果导向”这样的词汇。See John E.Simonett.'The Use of the Term "Result-Oriented" to Characterize Appellate Decisions,' William Mitchell Law Review 187(1984). (15)关于后果论证在判决中功能的德国法学观点综述,参见刘飞:《宪法解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中心的宪法解释方法考察》,《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16)See Muller v.Oregon,208 U.S.412(1907). (17)陈金钊将后果论归为“主体选择论”,他认为,由于法官社会科学素养和能力的欠缺,往往凭借主体的直觉和价值判断代替对后果的预测,基于对法官能力的怀疑,后果导向的判决思维具有破坏法治的危险。参见陈金钊:《法律人思维中的规范隐退》,《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 (18)关于试探法在司法判决中的功能,See Gerd Gigerenzer and Christoph Engel(eds.),Heuristics and the Law,MIT Press,2006.标签:安全保障义务论文; 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逆推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法律案例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法论文; 法律解释论文; 银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