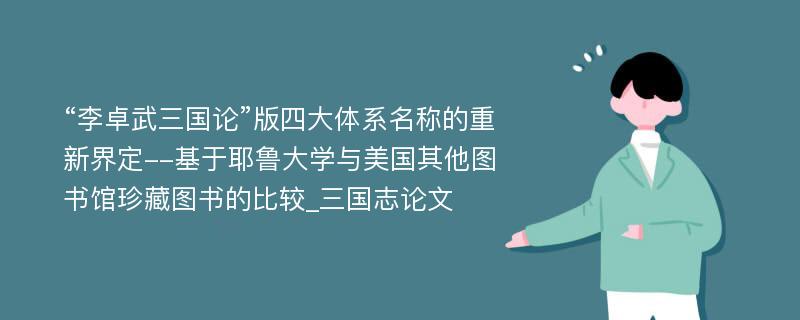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版本四大系统名称的再定义——以美国耶鲁大学等图书馆藏珍本比较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鲁大学论文,珍本论文,美国论文,批评论文,定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1-0077-14 笔者于2012年3月和2014年8月两次访问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看到了该馆藏《三国志演义》版本,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诸多李卓吾本资料,重新梳理李卓吾本诸本之间的关系。 首先介绍笔者看到的李卓吾本诸本。以下诸本都是一百二十回二百四十则,不分卷,版款是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括号内是本文使用的简称和笔者看到的资料形式)。 1.蓬左文库藏本(蓬左本。原本和复印资料);2.静嘉堂文库藏本(静嘉堂本。原本和复印资料);3.市立米泽图书馆藏本(米泽本。原本和数码图像资料);4.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九大本。原本和扫描图像资料);5.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早大本。数码图像资料);6.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都立中央本。原本和笔者拍摄数码图片);7.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京大本。原本和复印资料);8.上海图书馆藏本(上海本。原本和笔者拍摄数码图片、复印资料);9.南京图书馆藏本(南京本。影印本);10.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本(台湾本。复印资料);11.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本A(三槐堂本)(耶鲁本。原本和笔者拍摄数码图片);12.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本B(三国志真本)(耶鲁真本。原本和笔者拍摄数码图片);13.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本(法国本。数码图像资料) 根据这些版本的序文、本文、批评形式及各回回头书名等分为如下几种: 甲 有序文《序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蓬左本、静嘉堂本、米泽本、台湾本。 乙 有一篇《书富春东观山汉前将军壮缪关侯祠壁》文章:九大本、京大本、法国本。 丙 本文中的批评不是眉批,在本文行间:早大本、都立中央本、上海本、耶鲁本。 丁 书名叫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耶鲁真本。 ○不明:南京本。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后,学术界、出版界、古籍界普遍认为,甲是“吴观明本”,乙是“绿荫堂本”,丙是“藜光楼本”,丁是“宝翰楼本”。但以上分类是否妥当,同一分类是否同版等问题,均有必要弄清楚。如分类丙诸本本文批评形式与其他分类差异很大,好像形成了一个系统。但如分类甲和分类乙那样,只是由于序文等内文的差异或有无就轻作判断,似乎不妥。因为文章较短的序文容易加上或删掉,这些版本出版后传到现在,佚失序文等内文的可能性也很大,这就有必要根据版本版面状态(印刷状态)和本文文章、文字重新验证这些版本是否同版,并据此进一步确定“南京本”类属哪个系统。 首先来验证这四个分类是否妥当。为了比较四个分类的差别,我们以分类甲的蓬左本、分类乙的法国本、分类丙的上海本、分类丁的耶鲁真本为例。我们以各本第十回第七叶a面为例。蓬左本第一行“論”字到第二行“此”字,第一行“使”字到第二行“薦”字,有两条裂隙。法国本第一行“使”字到第二行“荐”字也有裂隙,与蓬左本同一文字,但裂隙处有所不同。蓬左本的裂隙在“使”“薦”两字正中,法国本在文字下面。据此可知,蓬左本和法国本是不同版本。再看上海本,从第一行“事”字到第二行“也”字、第三行“足”字,也有一条裂隙,蓬左本和法国本看到的“論”“此”“使”“薦”字无裂隙,因此,上海本与蓬左本、法国本不同版。再看耶鲁真本,蓬左本、法国本、上海本看到的裂隙,在耶鲁真本却一条也看不见。耶鲁真本本文第六行“一個”、第七行“两個”,蓬左本、法国本、上海本都作“一箇”“两箇”,只是正字和异体字的差异,但文字不同。蓬左本、法国本、上海本本文文章旁边有圈点“?”,耶鲁真本第二行“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和第八行“共薦一人”两处只有圈点,而圈点也是“?”,与蓬左本等形式不同。这样,耶鲁真本与蓬左本、法国本、上海本明显是不同版本。综上可知,属于以上四个分类的各本,分类既然不同,那么版木也是不同的异版。从版木相同还是不同的角度来看,上述四个分类应该是妥当的。 再来考察南京本属于哪个分类。南京本第十回第七叶a面第一行“使”到第二行“薦”、第三行“三”、第四行“間”字可以看到一条裂隙,与法国本一样,只有大小差异而已。由此,南京本与法国本系同版,南京本可以归于分类乙。 下面考察上述四个分类内诸本是否同版。首先看分类甲诸本第一回第二叶b面。蓬左本、静嘉堂本、米泽本第十行“曹”字到第五行“四”字有一条裂隙,静嘉堂本和米泽本第四行“禧”字也有裂隙。蓬左本、静嘉堂本、米泽本的同一个地方有条裂隙,特别是蓬左本的裂隙比静嘉堂本、米泽本还小。因此,蓬左本、静嘉堂本、米泽本这三本中,蓬左本印刷年限最早。再仔细比较静嘉堂本和米泽本第四行的裂隙,前者比后者更大,而且静嘉堂本的裂隙到“禧”字右边“喜”第三画,米泽本只到“禧”字左边“示”处,比静嘉堂本更短,因此,米泽本比静嘉堂本印刷年限更早。 再看台湾本。在蓬左本等诸本能看见裂隙的地方,在台湾本却看不到。此外,蓬左本中在很多地方能看见的裂隙,在台湾本中也看不见,我们由此不得不考虑,台湾本和蓬左本为不同版本。但是,蓬左本等所谓“吴观明本”才有的序文《序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台湾本中也有,因此也不能说台湾本与蓬左本毫无关系,这就需要再作细致比对。 再来比较蓬左本与台湾本《序批评三国志通俗演义》末尾部分。先看蓬左本,署名“秃子撰”下右边有“長洲文葆光书”,左边有“建陽吴觀明刻”。这也就是该版本叫作“吴观明本”的理由。台湾本署名“秃子撰”下左边也有“长洲文葆光书”,但署名位置与蓬左本不同,其右边是空格,无“建阳吴观明刻”文字。这表明,蓬左本与台湾本并非同版,同时也表明其中一方为另一方复刻本。以《三国志演义》为主的明清通俗小说版本,常有复刻之际加上或者删掉校订者、刻工、画工署名或出版书肆名等情况。 那么,哪一方是底本,哪一方是复刻本呢?我们来看看蓬左本和台湾本的第十八回第四叶a面。先看台湾本,框廓右上边三分之一附近有断绝,可知版木裂开了,第一行“留”字、第二行“戰”字上一半有缺损,第三行“爲”字和“唇”字、第四行“來”字和“正”字附近,字间有些变宽了。再看蓬左本同一地方,从框廓右上边三分之一附近开始,经过第一行“留”字、第三行“齒”字到第八行“的”字有一条裂隙,但与台湾本裂开的地方不同。特别要注意的是蓬左本第二行是“載”字(法国本和耶鲁真本为“戰”字,与蓬左本同版的静嘉堂本和米泽本为“載”字)。这部分内容是说,贾诩对张绣说自家军队战斗力要强于曹军,“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可见,“戰”字应该是正确的,“載”字乃蓬左本之误。产生错误的原因当是台湾本的“战”字上部破损后看不清楚,所以吴观明本翻刻底本时将“战”字误为“载”字。据此可知,蓬左本可能是根据台湾本而刻。也就是说,台湾本是底本,蓬左本是其复刻本。 再看上述两本第二十回第八叶a面。台湾本框廓右上边三分之一附近有一条裂隙,第一行“老”字和“朕”字、第二行“烈”字和“士”字、第三行“破”字和“指”字、第五行“交”字和“流”字、第六行“獨”字和“步”字,各行上字与下字的位置发生偏差,这很有可能是版木破坏未及时矫正所致。蓬左本虽然框廓右边没有断绝,但第一行“老”“朕”字离开了,两字位置好像与台湾本差不多,第二行“烈”字和“士”字,也与台湾本一样能够看到上下文字的偏差。台湾本廓既然没有断绝,蓬左本的版木也就可能未被破坏,但印刷结果却有了文字偏差,这有可能是以台湾本“那样状态”的版本为直接底本做成蓬左本版木的结果。这样,台湾本和蓬左本就非同版,而是底本和直接的复刻本关系,因此,台湾本和蓬左本是同一系统之内的两个小系统。 下面继续讨论分类乙诸本。各本第二十五回第五叶a面都在第一行“悔”字和第二行“問”字有裂隙,可见这三本是同版。再仔细辨析这条裂隙,法国本的裂隙较京大本、九大本小,没有达到第三行“接”字。京大本的裂隙到达第三行“接”字,手字旁“才”第二画能看见裂隙,但没有达到第四行“答”字。九大本这条裂隙是从第一行“悔”字到第四行“答”字。京大本和九大本差异不大,有时会看到上文所举第二十五回第五叶那种情况。由此可知,属于分类乙的三种版本,法国本印刷年限最早,京大本次之,九大本印刷年限最晚。 在比较这三本时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看各本第八回第十叶a面。通过比较发现,京大本和九大本一定是同版,但与法国本相比似乎有些不同,好像是异版。从文字上再作比对:法国本第一行有“非世之英雄也”文字,京大本和九大本的同一地方是“非世之英亦也”。此处文字场景是,吕布以为貂蝉被董卓夺取,向貂蝉说,“不能勾以汝为妻,非世之英雄也”,可见法国本文字是正确的,京大本和九大本“英亦也”三字显然意思不通。而且,第二行“内”字下面,法国本自然地连续下一字“庭”,京大本和九大本的“内”字和“庭”字中间有不自然的空格。由此可知,就京大本和九大本这一叶来说,法国本与京大本、九大本确实是异版,京大本和九大本有些部分做了补刻。这表明,这两本印刷年限比法国本晚很多,同时也说明这两本的关系密切。虽然京大本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绿荫堂本”,但这本是否真的为绿荫堂出版呢?九大本有封面,上面题“九思堂藏板”,而京大本没有封面,也未显示出版书肆名的相关记载,考虑这两本的密切关系,京大本与九大本一样,可能为“九思堂”刊行版本。 下面探讨分类丙诸本。耶鲁本和早大本都是完本,但上海本佚失了序文、图像、本文第一回到第九回,都立中央本只存第六十四回到第一百二十回图像和本文第一回到第二回第六叶。也就是说,上海本和都立中央本不能同时比较同一个地方,属于分类丙的四本,以下分两个阶段来考察这四本的关系。 以各本第一回第九叶a面为例。该面第一行“藏”字、第二行“賊”字、第三行“次”字有一条裂隙。同一个地方都有裂隙,可以判断这三本为同版。但这三本的裂隙大小有差异,耶鲁本的裂隙极小,只到“次”字的两点水“冫”细细地裂开,都立中央本的裂隙比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本大很多,从“次”字到第四行“川”字第一画也有条裂隙。早大本的裂隙比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更大,竟然到第五行“官”字第四画。由此可知,耶鲁本印刷年限最早,都立中央本次之,早大本印刷年限最晚。 再以各本第十回第九叶b面为例。该面都在第十行“請”字、第九行“報”字、第八行“以”字有条裂隙,因为在同一个地方有条裂隙,由此可判定这三本为同版。不过,耶鲁本的裂隙极小,“請”“報”“以”字上只看到很细的裂隙。上海本第七行“起”字、第六行“東”字、第五行“不”到第四行“極”字木子旁有条裂隙,早大本还到第三行“陶”字有裂隙,早大本的裂隙比上海本的更大,而且上海本和早大本也在第十行“不”字到第九行“百”字、第八行“陳”字有裂隙,早大本的更大,耶鲁本的同一个地方却无裂隙。由此可知,耶鲁本印刷年限最早,上海本次之,早大本印刷年限最晚。 这样,耶鲁本、上海本、都立中央本和早大本确实是同版,特别是耶鲁本印刷状态(版木状态)非常好,即使不是初印本,也是在很早阶段印刷出来的版本,上海本和都立中央本次之,早大本印刷年限最晚。那么,上海本和都立中央本哪本印刷为时更早呢?上海本序文、图像、目录均佚失,第一回到第九回本文也佚失(后由《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补抄);都立中央本则只有第六十四回到第一百二十回的图像和第一回到第二回第六叶的本文而已。也就是说,这两本确实是同版,但共同的地方没有剩下来,因此不能正确判定这两本的印刷时间之先后。仅就笔者观察印象而言,好像上海本比都立中央本为时要早一些。 综上所述,《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可分为四个大系统,分类甲中的台湾本虽然不一定与蓬左本同版,但两本关系密切;包括台湾本在内再仔细分类,《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诸本还可分为五个小系统。 可分为四个系统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中,分类丁所谓“三国志真本”与其他系统不同,书名加上了“真本”二字,内文与其他李卓吾本差不多,但也有些文字不同。下面再仔细探讨关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以下简称“真本”)的成立及其性质。 首先比较真本文章、文字与其他李卓吾本不同的几个例子。笔者在《〈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中文版)第二章第三节中考察“吴观明本”“绿荫堂本”“藜光楼本”的先后关系时,侧重这三本的文字异同。现在使用同一方法与例子,考察真本与其他李卓吾本的关系。以下①至⑩对应拙著《〈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第二章第二节表示李卓吾本各本的文字差异表格,使用以前的名称,“吴”是“吴观明本”,即分类甲;“绿”是“绿荫堂本”,即分类乙;“藜”是“藜光楼本”,即分类丙;“台”表示著中未提到的台湾本。 ①64.6.b 台:可令張翼呉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撻為等處所屬州郡;吴:可令張翼呉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撻為等處所屬州郡;绿:可令張翼呉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撻為等處所屬州郡;藜:可令張翼呉懿引趙雲撫涪水定江健為等處所屬州郡;真:可令張翼呉懿引趙雲撫涪水定江撻為等處所屬州郡 这个例子原来应该是“永水”(周曰校乙本、夏振宇本都作“外水”)“定江”“犍爲”三个地名并列,吴观明本、绿荫堂本、藜光楼本均有误,台湾本也有错,与吴观明本一样。真本文字与藜光楼本一样,作“涪水”,好像真本与藜光楼本关系密切。 ②66.5.a 台: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破敵;吴: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破敵;绿: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藜: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真: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 台湾本和吴观明本衍一“破”字,绿荫堂本和藜光楼本把那个衍字改为一个空格,真本无衍字,也无空格,或是把这个衍字删掉了,或是挤紧了空格,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因此很难判断真本的底本。 ③68.12.a 台:操取觀之一字不差;吴:操取觀之一字不差;绿:操又讀之一字不差;藜:操又讀之一字不差;真:操取觀之一字不差 台湾本和吴观明本作“取觀之”,绿荫堂本和藜光楼本作“又讀之”,意思都通。此句是左慈将《孟德新书》拿出来给曹操的场面,“取觀之”比“又讀之”更合适。真本作“取觀之”,同台湾本和吴观明本。 ④69.8.b 台:截住城内救軍;吴:截住城内救軍;绿:截住城内救軍;藜:截住城向救軍;真:截住城内救軍 显然藜光楼本有误,真本作“内”,同吴观明本、绿荫堂本,是正确的。 ⑤69.8.b 台:勿似董承自取其禍;吴:勿似董承自取其禍;绿:勿似董承自収其禍;藜:勿似董承自収其禍;真:勿似董承自取其禍 “取其禍”和“収其禍”,意思都通。周曰校乙本、夏振宇本都作“取其禍”,“取”很可能是“原形”。真本与吴观明本一样,作“取其禍”。 ⑥80.10.a 台:欠;吴:幸主公有兩川之地;绿:今主公有兩川之地;藜:今主公有兩川之地;真:幸主公有兩川之地 “幸”和“今”,语感有些差异,但文意都通。周曰校乙本和夏振宇本都作“幸”,那么“幸”字很可能为原字。真本与吴观明本一样,作“幸”。 ⑦90.13.b 台:見火必着;吴:見火必着;绿:見火必着;藜:見火必燃;真:見火必燃 “着”与“燃”意通。周曰校乙本和夏振宇本都作“着”,那么“着”字很可能为原字。真本与藜光楼本一样,作“燃”。 ⑧99.6.b 台:自有解危之策;吴:自有解危之策;绿:自有解危之策;藜:目有解危之策;真:自有解危之策 藜光楼本文字有误,真本正确,作“自”,藜光楼本错字好像是容易修正的;但真本究竟是继承底本的正确文字,还是将底本的错字改为正确的,很难作出判断。 ⑨100.6.b 台:願去者百餘人;吴:願去者百餘人;绿:願去者千餘人;藜:願去者千餘人;真:願去者千餘人 台湾本和吴观明本都作“百餘人”,绿荫堂本和藜光楼本都作“千餘人”,文意都通,但周曰校乙本和夏振宇本都作“千餘人”,“千餘人”是原来的文字。真本与绿荫堂本、藜光楼本一样,作“千餘人”。 ⑩100.7.b 台:文官秉筆而记録;吴:文官秉筆而记録;绿:史官秉筆而记録;藜:史官秉肇而记録;真:史官秉筆而记録 真本与绿荫堂本、藜光楼本一样,作“史官”。不管是“文官”还是“史官”,文意都通,周曰校乙本和夏振宇本都作“史官”。“秉筆而记録”自然是“史官”,“史官”更合适,因此,“史官”是原文,真本与绿荫堂本、藜光楼本好像都继承了原文。 以上,通过比较真本和李卓吾本各本的文字差异可知,真本文字与吴观明本一致的例子较多,但不一定都一致,有些例子与绿荫堂本和藜光楼本一致。特别是像例①那样,真本中也有与藜光楼本一样的错误。那么,真本的底本好像是吴观明本、绿荫堂本以后藜光楼本以前的李卓吾本,而且批评形式与吴观明本、绿荫堂本一样,是眉批。真本就是以这样的一本“李卓吾本”为底本,然后在修正有些本文和批评文章基础上自然而成,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中独立的一本。 如上所述,现存《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可分为四个系统,这四个系统简称为什么好呢?自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来,学术界曾使用过“吴观明本”“绿荫堂本”“藜光楼本”“宝翰楼本”等名称,但这些名称好像不一定是合适的。 从来叫作“绿荫堂本”的版本就是法国本和京大本,而且九大本、南京本也与法国本、京大本同版。南京本已佚失封面,九大本有封面,封面上题“嘉興九思堂藏板”。如前所述,早大本封面上虽然题“呉郡録蔭堂藏版”,但与法国本是异版,而与从来叫作“藜光楼本”的上海本、都立中央本同版。另外,耶鲁本封面上虽然题“古呉三槐堂/三樂齋/三才堂藏板”,却与所谓的“藜光楼本”同版。以上笔者整理如下: ○从来叫作“绿荫堂本”的版本和同版版本 ·法国本—无封面 ·京大本—无封面 ·南京本—无封面 ·九大本—封面上题“嘉興九思堂藏板” ○从来叫作“藜光楼本”的版本和同版版本 ·上海本—无有封面 ·都立中央本—无封面 ·早大本—封面上题“呉郡録蔭堂藏版” ·耶鲁本—封面上题“古吴三槐堂/三樂齋/三才堂藏板” 这样,从来使用的简称和封面上记载的书肆名不一定一致,特别是叫作“藜光楼本”的版本中,早大本和耶鲁本虽然是同版,但是封面上的书肆名不一样,而且,早大本封面上虽然题着“绿荫堂”,但与所谓的“録蔭堂本”不是同版。 确实,现在佚失封面的版本,也可能原来有封面,题刻与从来简称一样的书肆名;但也不能否定,封面部分在古籍版本中是容易更换的。从现存资料来看,从来的简称和封面上的书肆名不一致的版本确实存在着,从来的简称不一定能正确地表示李卓吾本诸本的情况。笔者认为,需要重新考虑李卓吾本诸本的简称。 那么,怎样的简称才是合适的呢?如上述,《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诸本可以各本冒头的序文等文章或各回冒头书名为指标而分类系统,这样的指标很难成为合适的简称。各本的藏书机关名称也不能明示各本的分类。笔者建议,仿照周曰校本等《三国志演义》其他版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等其他小说版本,暂时使用“甲、乙、丙、丁”文字,《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通称姑且这样指称: 李卓吾甲本A—台湾本 李卓吾甲本B—从来之“吴观明本”(A和B是直接的底本与复刻本的关系) 李卓吾乙本—从来之“绿荫堂本” 李卓吾丙本—从来之“藜光楼本” 李卓吾丁本—从来之“宝翰楼本”(即《三国志真本》) 以上,详细讨论了叫作《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三国志演义》同版异版的分类和简称及同版版本的印刷先后等问题。现存李卓吾本确实可以分为四个系统,但从来使用的简称不一定表示李卓吾本各个系统的正确情况,如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绿荫堂本”,有些版本封面上的书肆名和从来的简称就不一致。即使有些版本是同版,但由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这个版本很多书肆反复出版的缘故,封面上的书肆名也就不一定一样了。 那么,为什么很多书肆重复出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这个版本呢?大塚秀高说:“明末清初时期书肆常常继承着版木,一个书肆入手其他书肆刊刻的版木,只刊刻记载自己书肆名的封面,假装自家的新刊而出版,这样的情况是毫不稀奇的(原文为日文,引者译)。”[1]这个看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就《三国志演义》来说,很多书肆不但重新复刻或翻刻“李卓吾本”诸本,而且还用其他书肆刊刻的版木,加上重新制作的封面记载自己书肆名称,然后“假装”新刊出版。这种情况除了所谓“李卓吾本”以外几乎没有。 书肆用种种方式反复出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定有相应的理由。最让人想到的是,李卓吾这个人当时很受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商业出版,“李卓吾本”就会很畅销并获得很大利益。但这也仅为一种理由,因为,只为“李卓吾的人气”,很多书肆就没有必要反复出版同版的书了,那为何坊间书肆还将可以获得很大利益的畅销书的版木让给其他书肆呢?笔者估计,这里存在“禁书”问题。 对明清当局而言,李卓吾的思想是很危险的,书名中题着李卓吾人名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屡次受到禁书处分[2],书肆这才接二连三地改变出版书肆名称继续出版。这里好像存在着明清时期出版文化问题,为了全面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系统研究冠以“李卓吾”名字的明清小说版本出版情况及其假托问题,这就需要笔者另撰文而述之。标签:三国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