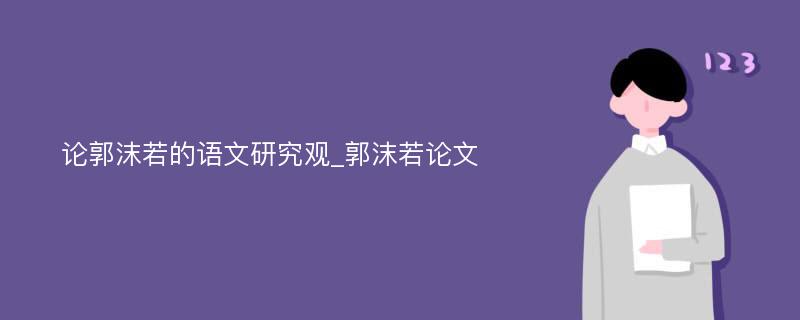
论郭沫若的国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国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也是一代国学大师。在国学研究方面,他不仅有一系列博大精深的国学研究成果传世,而且提出许多新颖独到的国学思想,形成了完整深刻的国学观。学习、宣传他的国学观,不仅有助于认清五四以来关于国学问题的纷争,而且对于今天以唯物史观正确地了解“国故”、认知“旧学”、评估“国粹”,进而正确认识国学与西学的关系、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国学与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
国学,亦称中学、旧学、国故等等,凡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皆在其范围。由衷地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是郭沫若国学思想的鲜明特色。
中华古国拥有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一部文化进化史”早在30年代,当西化论调甚嚣尘上之时,有些人就沉醉西风,蔑弃故我,认为中国固有文化“本无光荣之可言”。对此郭氏针锋相对地指出:总体而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决不是不光荣的,因为:“我们五千年来的生生不息的一部文化进化史,便是充分的证明。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各种民族的文化,尽管有兴有替,有盛有衰,或则曾光荣一时而永远销声匿迹,或则突经外患而一蹶不振。但我们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五千年中永远保持着了它的一贯的进化体系。”[①a]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它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传统,可以同古代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比肩而立,成为独具特色的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②a]。50年代初期他又指出:“几千年前以来,我们的祖先定居在亚细亚大陆东部的温带地区,发展了创造性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绵延不绝地不曾中断,文物和史籍之多,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这些都是勤劳而有智慧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替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不仅应该加以尽心的爱护,而且应该加以很好的整理。”[③a]
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与培养爱国主义情怀有密切的关系。早在郭氏之先,旧民主主义革命家秋瑾就曾经深刻指出:“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若不知本国文字、历史,即不能生爱国心也。”[④a]章太炎亦有言:“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不之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⑤a]从青年时期便萌“唤醒睡狮”之志的郭沫若,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无比热爱,他认同先贤的这些见解,更明确地指出:“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中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①b]不难看出郭沫若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深深依恋的情结,这是他毕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国学、阐发国学的强大的精神动力。
“对于中国的书不读,是最要不得的”在一切文化现象中,只有语言和文字这两种遗传代码是人类代代相传的基本信息,而图书典籍就是它们的物质载体。排斥先人的文化典籍就无异拒绝文化传递。五四时期有人否定中国古代典籍,提出“不读中国书”;这种提法虽有一定的针对性,终归是一种偏颇之见、非理性之说。郭沫若诚恳地忠告学人:“我们是用中国字、中国语言学东西的人,对于中国的书不读,是最要不得的。五四以后有些人过于偏激,斥一切线装书为无用,为有毒,这种观点是应该改变的。”[②b]结合他本人的经验,他自几岁开始就诵读“四书”“五经”,十几岁以后就接触先秦诸子,青年时期以后又深研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他自称:“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我都作了尽可能的准备和耕耘。”[③b]郭氏读了那么多古书,不但“只有好处”,并未“中毒”,而且使他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学贯中西,成果超人。
郭沫若对“中国书”很有感情,极其珍重,颇多好评。在经书方面,他说:“儒家的经书,一提起来大家都感觉不时髦,落后,甚至反动,其实‘六经皆史’,前人早就说过。我们把来作为史料看,正是绝好的史料。”[④b]在史书方面,“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家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二十五史》中的“前四史”,“中国学者都应该读”;《国语》、《战国策》也值得“选读”。在哲学著作方面,《论语》的“简练和精粹”,无论如何也是必读的书;《老子》那样“精粹而韵致深醇”的作品,在别的民族的古代是很少有的;《论语》和《道德经》在先秦哲学典籍中“可称双璧”。在文学作品方面,《诗经》的价值是“永不磨灭”的;《楚辞》中的某些作品简直可以“惊为神工”;《庄子》与《文选》对于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依然值得一读”;至于“唐人的诗,宋元以来的词曲,明清的小说”,应该多读[⑤b]。郭氏的这些论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表现出他对祖国文化典籍的热爱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期望。“抛尽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这是明代王守仁的两句诗,郭氏很喜欢,并赋予它更深刻的含义,多次加以引用,以便提醒人们,不要数典忘祖。
二
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世者无虑数十人,所谓“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⑥b],成为国学的重要内容。
研治国学若不借鉴考据学成果“是舍路而不由” 郭沫若称:“戴东原、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几位学者,他们的成功可以说是很有光辉的,现在的学者还没有谁可以赶得上。”当然,“戴、王、段的成功,只是对旧的文化加以解释、整理”,还需在此基础上“把中国文化推进得一步”[⑦b]。郭氏明确指出:凡欲在国学研讨方面有所成就,必须汲取考据学的研究成果,借鉴考据学的研究方法。例如“鲁迅是受过近代自然科学训练的人,而又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他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他具有着充分的条件能够阐发出民族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再如闻一多,他也是“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⑧b]。可见欲治国学,除近代科学方法外,清代考据学是非学习借鉴不可的;凡成大家者,均取此途,概莫能外。
建国以后学界曾有贬低清代考据学的倾向,认为它脱离政治,脱离实际,是一种繁琐哲学、无用之学。郭氏及时指出:“解放以后,对资料收集和考证工作有一个时期曾加以轻视,把乾嘉学派说得一钱不值,这是有些矫枉过正的。”[⑨b]他借研究《随园诗话》的机会对乾嘉学派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没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故考据无罪,徒考据而无批判,时代使然。姚姬传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而为之,实……为得其正鹄。”[①c]由是即把考据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缘由、学术短长以及这门学问对于国学研究的价值说得极为精辟、透彻。
“欲论中国的古学”,“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 清代考据学发展到清末民初,又出现罗振玉、王国维二位大师。尤其是王国维,能集清代三百年学术之大成,达到所谓汉学的尖端。其金石、甲骨、汉简、唐卷之学,戛戛独造,不仅为前修所不及,即使同时代学者,亦很少能与之颉颃。
郭沫若对罗、王的学术业绩有极为中肯的评价,他指出:罗氏之功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王氏的国学研究成果更“好象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综此二家,郭氏认为:“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②c]
“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这是一个深刻的命题。它有双重含义,其一是说国学研究绝对不应忽视罗王二家已取得的业绩,必须学习、消化、吸摄他们的成果,这样才能取法乎上。其二是说国学研究不应囿于罗王二家的水准,而要在他们业绩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即以甲骨卜辞研究而论,郭沫若指出: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从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某些讹传。但是卜辞研究是一种新兴的学问,我们对前人的成果只能“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把它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出发”,庶几超越前贤,更上层楼[③c]。事实也是如此,正如现今学者指出的那样:“夫甲骨之学,前有罗(振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董(作宾)。”甲骨学研究的初创时期是由“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而在甲骨学研究的发展时期,则是由“鼎堂发其辞例,彦堂区其时代”[④c]。正是后学以前修业绩为出发点的实证。
三
乾嘉考据之学在训诂名物方面,确有突出的成就,可是当涉及较为宏观的社会历史问题时,便显得力不从心,更不必说期待由它来阐明社会历史的规律了。因为乾嘉考据学所使用的方法毕竟是形式逻辑的方法,总体属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鉴于此,郭沫若又给国学研究提出新的任务。
“跳出国学的范围,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 五四以后胡适曾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在此前后,学者们对传统学术也做了不少整理的工作。郭沫若认为:对于他们所“整理”过的一些内容,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因为:“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⑤c]即以罗王二大师而论,他们确实对古代的材料“做了一番整理工夫”,但在清理中国社会、阐明中国历史方面仍有很多的不足。正如郭氏在1936年写的《我与考古学》一文中所说:“我们中国古代的详情,至今还是在墓里。民族的来源怎样,文化的分布步骤是怎样,和外来文化的交涉是怎样,以及古代社会的构成,各个构成阶段的递嬗……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所要的是材料,不是别人已经穿旧的衣裳;我们所要的是飞机,再不仰仗别人所依据的城垒。我们要跳出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⑥c]对于甲骨卜辞研究,郭氏从20年代末期就已进行,但他的研究与罗王二氏相较显然已有质的飞跃,他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于社会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⑦c]郭氏在甲骨文字研究中,不仅于文字考释颇多独得之见,更重要者是为我们揭示商代社会许多史实,尤其是商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他“商代奴隶社会论”的科学结论。两周金文研究也是如此。郭氏“从周代金文研究中”所得“西周及春秋时代颇有关于奴隶制的资料,为旧有文献所缺佚,足以定历史阶段”[①d]。所有这些,都与他深入国学而又跳出国学是分不开的。
“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 郭沫若在《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一文中赞赏他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的研究眼光犀利,考证赅博,立说新颖翔实。闻氏曾自称自己的研究重在三项课题:(一)说明背境;(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郭沫若指出:“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同的课题。”尤其是第一种,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汉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阶段上盘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阶段,只是在第二阶段的影子上跳跃。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阶段上来,然而也只在这里踯躅,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郭氏认为汉、宋诸儒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要想知道‘时代背境’和‘意识形态’,须要超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才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那便无从客观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不用说你更不能够批判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郭沫若赞扬闻一多:“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一“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道理讲得实在警策之至!
研究国学、切磋国故,终日和古董打交道,会不会象以往的某些汉学家那样沉溺不返、玩物丧志呢?郭氏指出,关键在于把握自我,“我辈勿忧玩物而丧志,幸于玩物中以见志焉。”[②d]尤应注意的是,在研究中不“陷入枝节性的问题,而脱离着预定的目标”[③d]。总之,“从糟粕中吸取精华,从砂碛中淘取金屑,亦正我辈今日所应有事。如徒效蠹鱼白蚁,于故纸堆中讨生活,则不仅不能生活,而使自己随之腐化而已。”[④d]陈词剀切,足资黾勉。
认清“过往的来程”,决定“未来的去向” 郭沫若认识到:“我辈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研究古代,在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破除迷信。其优秀遗产则挹之以益今,否则将沉溺而不知返矣。”[⑤d]他给自己的研究工作规定了这样的目标:“我主要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应度。”[⑥d]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特别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为范式,对祖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研究,终于在1929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该书《自序》中,他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这里所谓“过往的来程”,即是中国社会由原始公社制度到奴隶制度,再到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所谓“未来的去向”,则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郭氏以精湛的研究成果向世人宣布:“中国也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⑦d]“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厉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⑧d]在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他断言:中国历史上已经“经过了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是殷周之际的“奴隶制的革命”,第二次是周秦之际的“封建制的革命”,第三次是清代末年的“资产制的革命”。此外他更明确地宣布:社会进展的阶段,依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叠进,是不能有例外的。他向世人昭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只有沿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才是唯一可行的历史必由之路,才是中国人民民族振兴、国家昌盛的胜利之路。这一结论,是郭沫若从事国学研究成果的结晶。
四
“用科学的方法回治旧学”,这是郭沫若的一贯主张。这些科学方法主要包括人民本位的标准、历史主义的眼光、全面辩证的观点,等等。而归宗起来,亦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郭氏语重心长地指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①e]
对于旧有文化应以人民本位之标准而作权衡 郭沫若在国学研究中,始终贯穿一个重要的观念:人民本位。他以此为标准,衡量中国传统文化,区分精华与糟粕,体现出鲜明的民主精神。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提出对于历史人物评判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并称自己“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②e]。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又说:批评古人如同法官断狱,法官断狱是依凭法规律条,我们批评古人是依人民本位的准则;合乎这一准则的就是善,违背这一准则的就是恶。在《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中他更进而认定:“对于旧有文化自应以人民本位之思想而别作权衡,更不能沿既定体系以为准则。”“我们并不蔑视文化遗产,全要以人民本位为依归,本此绝对的是非,不作盲目之墨守。”[③e]标准既立,郭氏恪守不渝,遵照执行。
首先,郭氏在国学研究中以人民本位的标准来品评人物。他精心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象行吟泽畔、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屈原,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明清之际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他都有专门的论列。在诸多的历史人物中,他之所以以全副热情讴歌屈原,就因为他是一个“民本主义者”,是“注重民生”的,“他太息掩涕念念不忘民生的思想”是感天动地的,“他的诗意识是人民意识,他的诗形式是民间形式,他是彻内彻外的一个人民诗人”[④e]。他高度评价王安石,也是由于“他是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人”,他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意在抑制豪强、救济百姓,“他的政见,主要是由人民的立场出发,和秦汉以来主要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大臣们两样”[⑤e]。
其次,郭氏在国学研究中以人民本位的标准来衡量学术。比如在先秦诸子研究中,他说:“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⑥e]他援引《吕氏春秋》中“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等命题,认为吕不韦“尊重民意”、“反对家天下制”,“可以说是一位民主的政治家”[⑦e]。相反,郭氏对韩非颇多贬词,称他是一个“极端的王权论者”,“韩非子所需要的人只有三种:一种是牛马,一种是豺狼,还有一种是猎犬,牛马以耕稼,豺狼以战阵,猎犬以告奸,如此而已。”[⑧e]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其高下轩轾是极其明显的。到了50年代,他仍认为:“我们评价一位历史人物及其学术思想,应该从他的大节上来权其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⑨e]这一结论是他的人民本位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任何学说必有其“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 郭氏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及把学术文化“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唯物史观基本立场及历史主义的基本方法,认为任何学术思想“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⑩e]。他考察《周易》(主要是《易经》)这座“神秘的殿堂”,从中发掘出中国上古社会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生产活动,家族关系、社会组织、行政事务、阶级分野等政治活动,以及艺术、宗教、哲学等精神活动,使远古的“化石”得以重光[(11)e]。他以上述方法分析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更是析理精当,入木三分:“到春秋时代差不多一切都变了质,上帝坍台,人王倒楣,众人翻身,井田破坏,工商自主,龟卜失灵,旧的名物尽管不甘废弃,新的名物却是不断涌现,新旧交腾,有如鼎沸。这是社会制度变革时期所必有而且特有的现象。”[(12)e]他论述法家思想的问世也是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社会有了变革,然后才有新的法制产生,有了新的法制产生,然后才有运用这种新法制的法家思想出现。故尔法家倾向之滥觞于春秋末年,这件事的本身也就足以证明春秋中叶以后,在中国社会史上实有一个划时代的变革。”[(13)e]他论及名家的产生,也认为这是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各种事物起了质变。一切的关系都动摇了起来,甚至天翻地覆了,于是旧有的称谓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而新起的称谓还在纷纷尝试,没有得到一定的公认,在这儿便必然卷起新旧之争”,即所谓“名实之相怨”。反过来说,名家的产生亦足证“在周、秦之交,中国的社会史上有过一个划时代的变革。”[①f]总之,郭氏认为:任何学术思想都是适应一定社会的需要而产生,都有其生成的现实土壤,那种所谓纯而又纯、远离现实的思想学说,其实并不存在,至于有人“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逻辑”[②f],只能说明其对于唯物史观的治学方法尚缺乏深刻的理解。
郭氏把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贯彻到具体的国学研究中,创见迭出:他研究《周易》之制作时代,提出:“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因此它决非成于传说人物伏羲氏之手或成于有文字之先;又发现爻词中有晋国故事,故论断其亦非周公所作;还发现《论语》中“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句话,《鲁论》“易”字作“亦”,故孔子与《周易》之制作也无关系[③f]。《管子》一书,经郭氏考订,“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多汇集于此”。例如《明法篇》乃韩非后学所为,《水地篇》成于西楚霸王时,《轻重》诸篇成于汉文、景之世,《侈靡篇》中含有汉初政治、文化主张,当是吕后称制时的作品[④f]。郭氏的这些见解后来不断被学界所印证,有的虽有存疑但卓然可成一家言。
唯物辩证法是“参破”国学种种“门关”的一把“钥匙” 郭氏自称是“过渡时代的人”,旧学的根底、新学的培植,都使他获益非浅,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给了他精神上的启蒙,他“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⑤f]。他克服五四以后某些学者的形式主义、片面性、绝对化的偏颇,认识到:“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那种非辩证的态度是我在整个研究中所企图尽力摒弃的”。针对有些学者认为他“有点袒护儒家”的说法,郭氏回答:“话不能那样笼统地说”,其实不仅秦汉以前和秦汉以后的儒家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是先秦的儒家也各有派别,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加分析而笼统地反对或赞扬,那就是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假如说我有点袒护孔子,我倒有点承认。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的前驱者,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袒护’他。”同理,对秦汉以后的儒家就不应该一味“抬举”,因为“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肯定是不合时宜[⑥f]。运思辩证,使人折服。
辩证思维也使他在品评、裁量历史人物方面力求全面公正,提出许多发前人所未发的卓见。譬如人皆咒骂“暴虐无道”的殷纣王,却有使“中国东南部早得开发”之功[⑦f];秦始皇极端专制残暴,然而“统一中国是他对于历史有贡献的地方”[⑧f];韩非的学说固然是“充满法西斯味道”,使人“很不愉快”,然而他思想的“犀利”、文章的“峭拔”以及“公子囚秦,说难孤愤”的奋斗精神仍可垂鉴后人;至于顾炎武、王船山等清初鸿儒,虽有非凡建树,然而也只是“富于民族气节而贫于人民思想”[⑨f]。如此等等。由于郭氏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使他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国学研究的科学性、深刻性。
五
当国粹派与西化派各执一端、纷争不已的时候,郭氏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有人主张‘中国本位’的,这是半封建的意识。有人主张‘全盘接受’的,这是买办意识。”他主张:立足于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同时博采西方文化,“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⑩f]。总的说来是用辩证综合的方法,处理好古今关系和中西关系。他深刻指出:我们应取的“方针”便是:“对于古代的东西,不怕就是本国的,应该批判地扬弃;对于现代的东西,不怕就是外国的,应该批判地摄取”[(11)f]。
“吸收古人的遗产,以期继往而开来” 如前所论,郭氏深知:在中国大地上从事文化建设,是不能不以自己的先人的文化业绩为“出发点”的,民族文化遗产“直到现在乃至永远的将来,总是应该接受的”[①g]。他巧设譬喻:“植物吸收动物的死骸以为营养,动物也摄取植物的死骸以维持生存;大冶造器,熔化许多古铜烂铁而成新钟;造物生人,只把陈死的原素辗转抟拟……。”[②g]用以说明古代文化虽然已成陈迹,但仍可古为今用。当然,也须看到:历史的发展已经进入20世纪,人类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求知于祖先的事情越来越少,而求知于全世界的事情却日益增多,因此不应沉醉于既往,而要放眼于未来。他说:“我们要把固有的创造精神恢复,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精神,吸收古人的遗产,以期继往而开来。”[③g]
“继往”旨在“开来”,旧物皆需改造。6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了袁枚的《随园诗话》,郭沫若重读此书,写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其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兹主要揭出其糟粕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串。贯串者何?今之意识。”以现代意识反观传统文化、统贯旧有文化素材,使之服务于现实,正是郭沫若的精深见解。
“东西文化可以开出一条通路” 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会通。在这一交流会通的大潮中,中国文化必将迅速走向世界。郭氏以现代学人的深邃目光,把握了这一时代走向,他指出:“欧西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代了,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④g]他还说:“文化的成品应该是无国界种界的。举凡先觉者的精神生产应该是全人类所共同的遗产。……凡是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都应当赶快设法接受。”[⑤g]他不相信中西文化“路向”不同、分道扬镳、不可会通的文化观念,断言:“东西文化可以开出一条通路”[⑥g]。应该说,这是完全符合世界潮流的现代文化意识。以这种现代文化意识进行观照,便会发现有些人的文化心态不免有些失衡:有的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以为自己很低下,遇见外国人便叩头百拜”[⑦g];有的人则盲目自大,“只知道本国本族有‘粹’,而不知道他国他族也有‘粹’”,更不承认“他国他族的‘粹’,有时比本国本族的‘粹’还要‘粹’”[⑧g]。民族自卑感与民族自大狂,其实是病态文化心理的两种表征。为了建立健全的文化心态,郭氏提出以下救治之道:其一,以史为鉴,培养信心。要使国人知道,“以前的中国文化,并不全部由中国民族自己创造的,有许多部分是由外来”。即以音乐而论,“其实所谓‘国乐’是什么?现存胡琴、琵琶、二弦、月琴、横笛、洞箫,以及工尺的字谱,隋唐燕乐的残调,那一项是真正的‘国乐’?”[⑨g]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国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很有弹性”,此种特质今日不应当失之。其二,克服自大,医治“洁癖”。他屡告国人:“我们中国人是自诩为大国民的”,其实关门主义倾向极重,“洁癖到了排外,在今天是极危险的理论”。“文化上的义和团”,特别值得警惕[⑩g]。其三,借石他山,以攻美玉。外国的东西并非一切都好,要加以分析:“我们要宏加研究、介绍、收集、宣传,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11)g]其四,礼尚往来,全面交流。他认为近代文化交流“差不多是片面的”,传播进来的象“洪流”,介绍出去的似“溪涧”。他“期望中国文化像洪水一样奔流”到国外,他期待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都能够与英、美、苏并驾齐驱”,以使古老的中华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①a 《青年化,永远青年化》,《沫若文集》第11卷,第373页,以下简称《文集》。
②a 参见《中日文化的交流》,《文集》第11卷,第65页;《论中德文化书》,《文集》第10卷,第6页。
③a 《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439页,以下简称《全集》。
④a 《秋瑾集》第46页。
⑤a 《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63页。
①b 《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
②b 《怎样运用文学的语言》,《文集》第13卷,第25页。
③b 《十批判书·后记》。
④b 《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文集》第12卷第254页。
⑤b 同上书,第250—255页。
⑥b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3。
⑦b 《中日文化的交流》,《文集》第11卷,第71页。
⑧b 《历史人物·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
⑨b 龚济民等《郭沫若年谱》下册,第331页。
①c 《〈随园诗话〉札记》。
②c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③c 《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④c 唐兰:《关于尾右甲刻辞》,《考古社刊》第6期,1936年。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现代学术界有一谚语:“堂、堂、堂、堂,郭、董、罗、王。”
⑤c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⑥c 同上。
⑦c 《甲骨文字研究·序》。
①d 《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②d 《甲骨文研究·自跋》。
③d 《金文丛考·重印弁言》。
④d 《〈考古学报〉题词》,《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⑤d 同上。
⑥d 《跨着东海》,《文集》第8卷,第312页。
⑦d 《驳〈实庵字说〉》,《文集》第11卷,第430页。
⑧d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①e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②e 《历史人物·序》。
③e 《文集》第13卷,第162页。
④e 《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文集》第13卷,第305页。
⑤e 《历史人物·序》、《历史人物·王安石》。
⑥e 《十批判书·后记》。
⑦e 《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⑧e 《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十批判书·后记》。
⑨e 《史学论集·替曹操翻案》。
⑩e 《十批判书·后记》。
(11)e 参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12)e 《奴隶制时代》。
(13)e 《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
①f 《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
②f 《十批判书·后记》。
③f 《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
④f 《管子集校·序录》。
⑤f 《十批判书·后记》。
⑥f 《十批判书·后记》;《奴隶制时代·蜥蜴的残梦》。
⑦f 《论古代社会》,《文集》第12卷,第286页。
⑧f 《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文集》第17卷,第163页。
⑨f 《历史人物·序》。
⑩f 《水与结晶的溶洽》,《文集》第11卷,第80页。
(11)f 《沸羹集·新陈代谢》。
①g 《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文集》第12卷,第250页。
②g 《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创造季刊》1卷4号。
③g 《一个宣言》,《文集》第10卷,第100页。
④g 同上书,第101页。
⑤g 《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文集》第12卷,第259页。
⑥g 《王阳明礼赞》附论:《新旧文白之争》,《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299页。
⑦g 《中日文化的交流》,《文集》第11卷,第73页。
⑧g 《关于艺术的不朽性》,《文集》第10卷,第380页。
⑨g 《历史人物·隋唐大音乐家万宝常》。
⑩g 《天地玄黄·文艺工作展望》。
(11)g 《一个宣言》,《文集》第10卷,第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