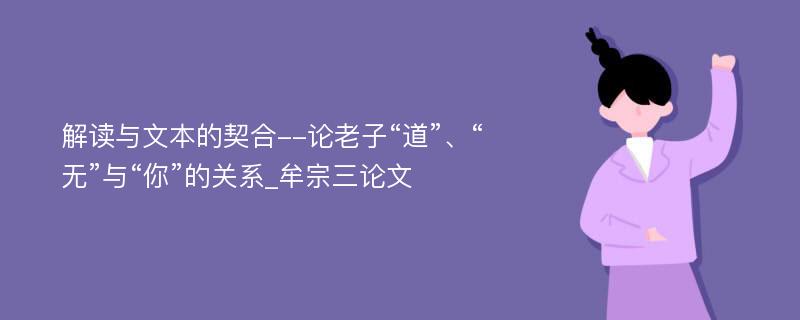
诠释与文本的契合——论老子之“道”“无”“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文本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1)03-0019-05
一、断句之争的实质
对于老子《道德经》第1章,不同时代注解者在“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断句问题上争执不休。对于第一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种断句认为应该以“无名”“有名”断句,持这种看法的自王弼、河上公、范应元始,现代学者如马叙伦、冯友兰、蒋锡昌、朱谦之、任继愈、刘笑敢等;一种断句认为应该以“无”“有”断句,持这种看法的自司马光、王安石始,近现代学者如叶梦得、白玉蟾、俞樾、梁启超、高亨、侯外庐、关锋、陈鼓应、卢育三等。主张以“无名”“有名”断句的注解者和学者认为,此句自古以来都以“无名”“有名”断句,并时常引用文子所说“有名产于无名,无名者,有名之母也。”(《文子·道原篇》)《史记·日者列传》所说“此老子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作为例证。
主张以“无”“有”断句的注解者和学者认为,上述断句并不符合道家老子的原义,并引用庄子的两句话为证:“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庄子·庚桑楚》)在论述老子思想时说“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庄子·天下》)这些学者进一步论证说,以“无名”连读问题不大,而且老子《道德经》有“道常无名”“无名之朴”的说法,无名可以是指称道体的一种方式,但“有名”连读就说不通,老子《道德经》虽然有“始制有名”之说,但这是指称的具体的有形的具体事物,按照老子哲学的思想逻辑,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不可能成为“万物之母”。现代学者陈鼓应所说亦可作为例证:
“无”“有”乃是哲学上的一个常用的词句。四十章上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说,这里应以“无”“有”为读。主张“无名”“有名”为读的人,也可在《老子》本书中找到一个论据,如三十二章:“道常无名,始制有名。”然而若以三十二章的“无名”“有名”作为本章标点的根据,则“无名”犹可通,而“有名”则不可通。因为“始制有名”的“名”是指区分尊卑名分的“名”,这种“名”是引起争纷的根源。引起争纷的“名”,则不当成为万物的根源(“万物之母”)。再说,“名”是跟着“形”而来的。如管子说:“物故有形,形故有名。”“有形”不当成为万物之母,所以似不宜以“有名”为读。[1]57
对于第二句“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同样存在两种断句读法。自王弼、河上公始,以“常无欲”“常有欲”断句为多,并有帛书甲乙本为证(帛书本此句为“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自司马光、王安石始,以“常无”“常有”断句渐多,如叶梦得、白玉蟾、赵秉文、俞樾、易顺鼎、马叙伦、高亨、朱谦之、陈鼓应等学者都从此种读法。
我们认为,两种不同的断句读法并非仅仅因为古人的语言习惯不同所致。若仅仅从古人的语言习惯来加以论证,很难深入到老子道论思想整体的义理层面。因此,断句争论深层次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够从老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充分说明老子道体与“无”“有”两种属性的关系问题。
二、“以无为本”——王弼注解的偏失
我们先看一下王弼的注释:对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王弼的注释:“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对于“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注释:“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对于“常有欲,以观其徼。”注释:“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2]1-2
再看王弼对于第40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注解:“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2]110对于第42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注解:“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2]117
联系王弼对老子这三章的注解,可以明显看出王弼关于老子道、无、有的关系的看法:第一,把老子的道等同于一,进而等同于无;第二,无、有乃是逻辑上的上下关系或者先后关系,无与有是本末关系;第三,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体;第四,有和天地万物必将复归于无。按照王弼的逻辑思路,这里存在三个需要阐释的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是“无名”“有名”是否就是等同于“无”与“有”;其二是“无名”与“有名”若等同于“无”与“有”,二者的层次是属于逻辑上的递减层次还是属于同一层次;其三是无与有和始与母的关系,若按照王弼把无与有看作是逻辑上的递减层次的注释,始与母不应该属于同一层次,而是逻辑上的递减层次,可王弼下面又把始与母视之为“两者”,这如何解释。显然,王弼的注解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之处:其一,老子把“无”“有”视之为同一层次,同为道体的属性,而非从无到有的递减层次,这是王弼以其自己的理解强加到老子头上;其二,王弼把“两者”注释为“始与母也”,这又与老子强调无、有之道体属性的思想不一致,所以,按照老子的思想脉络,“两者”应该是“无与有也”,而非“始与母也”;其三,把无名、有名以至无、有视之为逻辑上的递减层次,这必然不能解释为“始与母”“同出而异名”,更不能解释与老子第52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的关系。所以,只有把老子的无与有视之为同样的逻辑层次,才能够使道体、无与有、始与母的关系解释畅通。简言之,王弼的道即无为第一层次,有为第二层次,天地万物为第三层次;老子则是道体为第一层次,无与有为第二层次,天地万物为第三层次。
不可否认,王弼将老子道体与无相等同的观点对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影响巨大,有的学者推断,王弼哲学已经意识到“无”(一般)和“有”(个别)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更有甚者将老子的无、有关系认为就是哲学上的一般与个别关系,“老子的哲学在先秦哲学中巨大贡献之一就是‘无’与‘有’一对范畴的初次被认识。老子在他的五千言里,反反覆覆讲明事物中有个别和一般,有本质和现象的区别。现象是个别的,本质是一般的。个别的东西有生灭,本质的东西没有生灭。就这一点来说,就是人类认识史上一大进步。”[3]39甚至有的外国学者也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以至于“道”“无”并称,“‘道’与‘无’都是没有穷尽的,它们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虽无言无形,但天地万物都依赖它们而生成。如果没有它们的话,我们就不能想象‘有’是什么;如果离开它们的话,一切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所以我们这样说,‘无’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它决定着天地万物的形象、性能及发展变化的方向”[4]128。
对于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的注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以“无”言“始”,“无”是就“天地”的开始而言的,以“有”言“母”,“有”是就“万物”的归终而言的,从老子思想体系来看“天地”与“万物”同义,所以天地万物可以同言。牟宗三这样来描述天地万物的关系:“‘天地’是万物之总称,‘万物’是天地之散说。‘天地’与‘万物’其义一也,只随文异其词耳。”[2]111所谓“常无,欲以观其妙”,是说从“常无”的角度观察道体始成万物的奥妙,此处之“妙”,是就道体分化万物而言,所以以“无”言“始”;所谓“常有,欲以观其徼”,“徼”即“归终”之义。终即有成之义,是说从“常有”的角度观察道体始成万物的归终,此处之“徼”,是就道体有成万物而言,所以以“有”言“母”。即道体与天地万物相始终,天地万物由道体而始,由道体而成,由道体而归,由道体而终。单纯的“无”或“有”,都不可能说明天地万物的始成和归终。
对经典文本的诠释最为忌讳的是只停留于一点上,毫不顾及思想整体和思想义理的脉络。对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句话,我们之所以认同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的注解,是因为这种注解为我们准确理解老子无、有的并列关系提供了一种思想支撑。
三、对老子本义的还原:以牟宗三为例
如果说王安石的注解仅仅纠正了王弼注解的偏失,那么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对于王弼注解之阐释可以说还原了老子的本义。牟宗三认为,对于老子所说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应该这样来阐释:“言道以无形无名始万物”即“无名天地之始”,天地是万物之总称,故说“始万物”亦无不可。“道以有形有名成万物”即“有名万物之母”,成者终成也。王弼注解所说的“无形无名”“有形有名”均指道体而言的,如果说“无形无名”是就道体之“无性”来说的,那么“有形有名”就是指道体之“有性”而说的。说道体之“无性”为天地万物之“始”,这是从总体上说天地万物返其“始”以为“本”;说道体之“有性”为天地万物之“母”,这是散开关联着天地万物向前看。简而言之,即以道体之“无性”“始”万物,以道体之“有性”“成”万物。这样,牟宗三从老子思想义理上把“无”“有”看成是并列关系,超越了王弼把老子“无”“有”看作是本末、体用关系的思想误区。
普通只从“无”或“自然”说道,很少注意此经文所说道之“有性”。说到“有”,则从“物”说,“有形有名”亦从“物”说,盖何以能说道为有形有名,因而为“有”乎?如是,“有”只成一对于万物之虚饰词,无独立之实义。但经文及王注确是就道说“有”,此“有”即道之“有性”也。道亦是“无”,亦是“有”,因而亦为始,亦为母。无与有,始与母,俱就道而言也。此是道之双重性。就天地向后返,后返以求本,则说无说始;关联着万物向前看,前看以言个物之成,则说有说母。[5]112
由此出发,牟宗三对王弼“常有欲”“常无欲”断句及其思想义理进行了纠正。虽然牟宗三并没有完全反对王弼的断句读法,但他已然感觉到这种断句方式不能表达出老子的思想旨意,因此他说:
然“常有欲”,实即“常有”也;“常无欲”实即“常无”也(王读虽有据,然此等处却不必拘)。何必著于欲而言之?故不如常无、常有,点句为愈。“常有,欲以观其徼”,徼性即向性,向性即有也。妙用无方之道即在“向性之有”中终成特殊之事物。有而不有,则不滞于有,故不失其浑圆之妙;无而不无,则不沦于无,故不失去终物之徼。如是,则在此“向性之有”中,即可解“有为万物之母”之义。如是,无、有、物为三层,而由道之妙与徼以始成万物之义,更见确切而精密。道亦是无,亦是有,则道之为始为母义,亦可得其确解。此则更得无而不无,有而不有,有无浑圆之玄义。[5]115
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思路,牟宗三对王弼关于老子“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注解进行了重新阐释。我们先看王弼的注解:“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谓之玄者,取于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2]1-2
牟宗三虽然非常肯定王弼的这段注解,称之为“精美”“畅通”。但牟宗三又引申了王弼的注解,王弼仅仅把“两者”界定为“始”与“母”,牟宗三则把“两者”引申到“无”与“有”,最终把“无”与“有”界定为道体的双重属性:
“两者”王注指“始”与“母”言,故云:“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谓之始”,道之妙也,即道之“无性”;“谓之母”,道之徼也,即道之“有性”。故“两者”指始与母言,亦即指无与有言,以无为始,以有为母也。后返以求本,则以“无”为始,此即王注所谓“在首则谓之始”;关联着万物向前看以明道之生成万物(使个体存在),则以“有”为母,此即王注所谓“在终则谓之母”。“终”即“要终”之终。徼向个体而终成之也,即实现之也。道有双重性,一曰无,二曰有,无非死无,故由其妙用而显向性之有;有非定有,故向而无向,而复浑化于无。[5]116
四、第40章简本的佐证
对于老子第40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王弼的注解是:“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2]110王弼的注解贯穿了其“以无为本”,“无”与“有”是本末、体用关系的思想主旨,按照这样一种思想逻辑,老子的“无”与“有”只能是一种逻辑上的上下关系或先后关系。
郭店竹简甲本老子《道德经》第40章与王弼本第40章文字上不同,竹简本为“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呈现了道体与“有”“无”两种属性的不同关系,按照王弼本的理解,无与有只能是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或者上下关系,而按照竹简本的文本,我们完全可以把“无”“有”的关系看作是逻辑上的平行关系或者是并列关系。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古老的老子版本,竹简本为我们准确理解老子道体与“无”“有”两种属性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文本的佐证。安徽大学孙以楷先生对这句话的解读颇能切中老子之意旨:
“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其中“生于有”、“生于无”之间并不是一种选择关系,如果是选择关系,当作“天下之物,或生于有,或生于无”,“或”字是不可省的。“生于有”与“生于无”是一种并列关系或递进关系,意为:“天下之物生于有,也是生于无”。为什么天下之物既生于有又生于无呢?因为这里的“有”是一般概念,不是指某一具体之“有”,而是指普遍存在,即“有状混成”之“有状”。这个“有状混成”是“混成”,是唯一的无限混沌,是无形无声的,即“寂寥、独立、不改”,也可以称之为“无”。说它是“有”,因为道确实是“有状”;说它同时又是“无”,因为它无形无声无限。“无”是对“有”的规定,这使“有”不落入某一具体之“有”。可见简本《老子》的“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实在是很精彩、很深刻的哲学命题。“有”、“无”是内含丰富而又十分思辨的哲学概念。简本《老子》以有无统一规定了道。后世道家学者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天下之物生于有”又“生于无”,于是重复了一个“有”字,变成了“有生于无”,这样反而把有无统一割裂成无先于有、无中生有,造成了《老子》有无观的内在矛盾,也引发了老子思想研究中的许多争论。[6]154-155
所以,若按照竹简本的“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来说,更能够说明老子并没有把“无”看成是第一性的,把“有”作为第二性的,“如果按更原始可靠的简本理解,‘有’和‘无’并不是相对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而只是同一物种的两种不同表达,即二者都是万物所从出的那个东西。从万物创生来讲,说万物生于‘有’还是生于‘无’,其实是一样的:万物总要有个来处,因此是‘有’;有而不知其名其形,有也是‘无’”[7]116。
五、诠释与文本的契合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无”“有”这样的术语早在老子之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但仅仅是在生活常识领域中使用。老子的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无”“有”提升为哲学概念和哲学术语。正像牟宗三所说的,老子所说的“无”“有”指道体的“无性”“有性”,即道体的两种平行的并列的两种属性,这样“无”“有”就成为老子用来说明道体与天地万物关系的桥梁和纽带,这样我们才能够解释老子道体与天地万物的超越与内在的关系:从“无”来谈道体的超越意义,通过“无”来说明道体的本体论意义;从“有”来谈道体的内在于天地万物的意义,通过“有”来说明道体与天地万物的关联性。明代憨山大师对此义理的注解更为明晰:
老子因上说观无观有,恐学人把有无二字看做两边,故释之曰,此两者同。意谓我观无,不是单单观无。以观虚无体中,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观有,不是单单观有,以观万物象上,而全是虚无妙道之理。是则有无并观,同是一体,故曰,此两者同。恐人又疑两者既同,如何又立有无之名,故释之曰,出而异名。意谓虚无道体,既生出有形天地万物。而有不能生有,必因无以生有。无不自无,因有以显无。此乃有无相生,故二名不一,故曰,出而异名。至此恐人又疑既是有无对待,则不成一体,如何谓之妙道,故释之曰,同谓之玄。斯则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深观至此,岂不妙哉。[8]34
这种对道体之“玄”兼顾有无的解释,更符合道体与天地万物的辩证关系,若仅说道体是“无”,道体就成为绝对的不蕴涵任何内容的虚无,成为“挂空之道”,所以说道体是“无”是指具体之无,而非抽象之无;若仅说道体是有,天地万物就失去了形上之根源,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说道体是“有”是指抽象之有,而非具体之有。天地万物就是从道体的“玄之又玄”的圆成作用中“实现”生发出来,故谓“玄而又玄,众妙之门”。
虽然老子把“无”“有”提升为哲学概念,但老子并没有在《道德经》中过多地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哲学上的阐释。据统计,老子在《道德经》中单独使用“无”仅有三处,其它都是“无”与各种各样的名词术语相结合使用的。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无”“单独使用达二十多次,并多次提出”“以无为本”“以无为心”“以无为用”“凡有皆始于无”等以“无”为中心的哲学术语和哲学命题,“无”真正成为了王弼哲学的核心概念。可以说,王弼“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既是对老子道论哲学的发展,又是对其的误读。由于王弼在老子注解者中的巨大影响,以至于这种误读至今“余音不衰”。
牟宗三先生所著《才性与玄理》,初版于1962年(1962年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此时距郭店竹简本老子出版1998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差36年。牟宗三先生依据自己对老子《道德经》的准确把握,重新阐释了王弼关于老子《道德经》第1章的注解,指明了老子道体与“无”“有”两种属性的并列关系和平行关系,这种独特的义理阐释与36年后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第40章的文本契合一致,是牟宗三先生对老子哲学思想整体把握的必然结果,是这位儒家天师对老子思想义理阐释上的贡献。
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阅读古代文本,不能从一字、一句之义去推断整部文本的思想内涵,以免产生“断章取义”之弊,应从古人的思想整体中去断定一字一句之义。正如徐复观先生论及“研究中国思想史方法问题”时所说的,“我们所读的古人的书,积字成句,应由各字以通一句之义;积句成章,应由各句以通一章之义;积章成书,应由各章以通一书之义。这是由局部以积累到全体的工作。在这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的所谓训诂考据之学。但我们应知道,不通过局部,固然不能了解全体;但这种了解,只是起码的了解。要做进一步了解,更需反转来,由全体来确定局部的意义:即是由一句而确定一字之义,由一章而确定一句之义,由一书而确定一章之义;由一家的思想而确定一书之义”[9]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