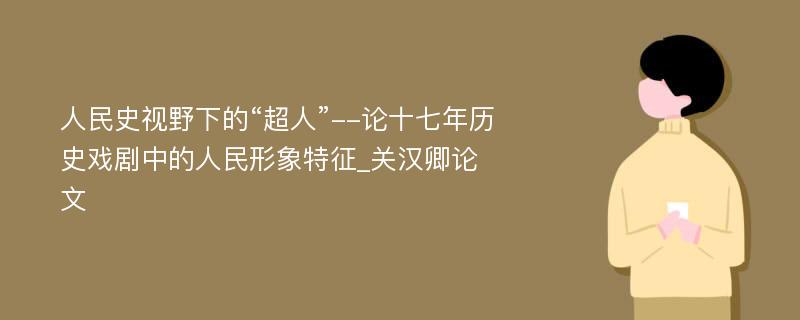
人民史观下的“超级人民”——论十七年时期历史剧中人民形象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时论文,剧中论文,形象论文,历史论文,史观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七年时期的话剧创作普遍受到了“思想内容的政治理念化、非人化从而导致的情节公式化,人物概念化[1]”的影响。创作题材上也大都以“工农兵”为主,表现工农兵题材之外而独辟蹊径的“第四种剧本”仅仅是昙花一现,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十七年时期历史剧自然也难出其彀。历经了1949年后的历次运动后,“人民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确立为当时历史剧创作的指导性思想。在其影响之下,十七年时期历史剧的形象塑造中,出现了一批“超级人民”的群像。这“超级人民”在当时历史剧中是如何呈现的?有哪些特点?本文将就这个问题,结合当时较为典型的历史剧进行一番考察与研究。
一、“出身劳苦”的“人民”
在十七年时期历史剧中“人民”形象的身份设置上,清一色的都是出身贫苦且饱受剥削与压迫的劳苦大众。在古代和近代题材的历史剧中,这些“人民”形象大都被作者设置为三类:农民、城市平民与底层士兵。
田汉的《关汉卿》全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创作《窦娥冤》而展开,其中的人民形象也都是生活在大都的城市平民。比如大都小酒店的女掌柜刘大娘和她被拐走的女儿二妞;关汉卿的老仆人关忠,还有就是朱帘秀和赛帘秀等在大都演戏卖艺为生的民间艺人。他们大都为人忠厚,生性耿直,但又受到官府各种各样的压迫。比如二妞在第一幕中被阿合马的爪牙抢去当丫鬟;《窦娥冤》的演出被以阿合马为首的元朝官府无理查封,并用残酷的手段对演员进行关押与迫害。
《文成公主》的作者是受命创作,剧作主题在于歌颂汉藏团结和西藏的民主改革。于是,剧中设置了一个藏区的小女孩达娃。她本是玉树地区的农奴,为追求爱情,不愿做领主的小妾而逃了出来。因通汉语和藏语,在文成公主进藏的路上被收为小通事。一路上,在文成公主的保护与帮助下,她巧妙地逃脱了领主的抓捕,和母亲重逢与顿珠终成眷属。
《胆剑篇》是曹禺十七年时期创作的第二部剧作,此剧一反以往卧薪尝胆题材作品中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勾践、文种、范蠡、夫差、伍子胥、伯嚭等“帝王将相”身上,而是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其间的作用。在剧中,作者从越国人民受侵略、受侮辱的角度出发,塑造了苦成父子、防风氏一家、匠丽夫妻和西施等一系列的农民形象。他们在吴越战争中饱受战乱的痛苦与来自侵略者的屈辱。越国兵败,吴国就烧毁了他们的农田,西村的施姑娘为了救小孩,挺身而出,不幸被吴王夫差看中,强行掳掠回吴国。战后,吴国将越国彻底当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每年向越国勒索大量的贡品,而且不让越国筑城自守,不得铸造兵器,并且对越国百姓课以重役。在吴国残暴的压迫下,越国人民的生活处境都十分的艰难。
在朱祖贻、李恍的《甲午海战》中,人民形象主要由威海卫刘公岛军港附近的渔村里的渔民与北洋水师底层的官兵组成。在剧中,他们遭遇了日本侵略者与清政府的双重压迫。一开场,就展现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迫下中国人民的处境。通过老水手、李大爷和小顺子之口让观众了解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兵船直接威胁到渔民们的安全,小顺子的父亲就被日本海军打死。可就在这大战在即的时刻,清政府为了庆贺慈禧六十大寿,向百姓每户征银二两。外有海战的一触即发,内有苛政的无情压榨。在中日海战中,英勇战斗的大都是底层的官兵,特别是方仁启所在的贵远号在执行护送任务时与吉野号的战斗中,方仁启临阵退缩,甚至要挂白旗投降,而李仕茂、王国成为代表的水兵坚决反击,并成功打退了吉野号。但返航后,贵远号上坚决作战的水兵反而受到方仁启的诬陷与迫害。渔村百姓难忍日寇欺凌,写了万民折上书皇帝要求与日寇一战,却被当地官府认作是聚众闹事,若不是邓世昌及时出现解救,他们也难逃官府的弹压。
纵观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剧中为“人民”设置的处境,我们可以很有意思地发现:这些“人民”在剧中,很少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大都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下,而这些剥削、压迫势力或是来自外部的侵略,或是源自内部腐朽的统治。
二、“觉悟超凡”的“人民”
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剧中的“人民”形象往往具有超越当时历史局限与文化水平的思想觉悟,特别是对于剥削与压迫者似乎自然就有着积极的斗争精神。
在《胆剑篇》的“人民”形象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突出。全剧一改以往“卧薪尝胆”题材只是围绕吴越两国的“帝王将相”展开描写,而是通过塑造苦成、防风婆婆、匠丽等一系列“人民”形象将越国人民放在全剧一个重要的位置,并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在剧中,越国败给吴国后,勾践君臣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报仇雪恨似乎都是在越国人民的鞭策、感召下同心协力共同完成的。吴越交战,越国兵败,吴国杀到会稽,并将附近的田地一并烧毁,全剧就是从越国人民的哭喊声中开始的。在第一幕中,一名越国百姓拿着一束烧焦的稻子,想要冲进大禹庙求勾践报仇雪恨,却被吴国武士无情杀害。勾践在被夫差押往姑苏前,百姓与勾践相见,在送别之际苦成慷慨激昂:
苦成(举起酒杯)大王,我们只有这一杯水酒,为大王送行。(痛切地)今天会稽家家都有战死的人。活着靠一口气!这气不伸,恨不消,仇不报,我们是活不下去的。我们是越国人,越国人是压不倒,折不断,杀不完的。大王,你要回啊!
最后,望着勾践远去的船,苦成壮怀激烈,奋力拔出夫差插在大禹庙前的“镇越神剑”。第一幕就在他的一句“越国是镇不住的!”中落下帷幕。越国民众们在此的言行,无疑为勾践日后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的行动,埋好了伏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勾践似乎更像是顺应了越国人民的要求才这样做的。
到了第二幕,当年被吴军掳走且已然成为吴国王妃的西施姑娘,还有苦成的次子、越国五千壮士之一的无霸,这两个越国人民角色在这一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施虽然已经贵为王妃,但依旧没有忘记她是一名越国人。西施利用王妃的地位,暗中帮助勾践君臣,偷出夫差的验关金符,想让勾践逃出吴国,并在被离要来杀害勾践时,义正词严地喝退了被离,让勾践君臣转危为安。越国士兵无霸的到来,除了表现他对勾践君臣的忠勇之外,在这一幕的最后,勾践给夫差召去给他牵马坠蹬时,无霸难以忍耐的耻辱感更是代表了越国人民的心声。
在第三幕里,越国爆发旱灾,赤地千里再加上吴国的掠夺与奴役,使得越国发生了饥荒。勾践体恤民情,发米给百姓。可当苦成等百姓从填井的吴国士兵那里得知这米是来自吴国的时候,饥肠辘辘的百姓苦成、匠丽、鸟雍更是“觉悟超凡”地表示要“勒紧裤腰带”死也不吃吴国的米,鸟雍甚至把装米的陶罐扔在地上。苦成气愤不已还要阻止他的儿媳去领米。勾践召见他,苦成慷慨激昂地将越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昂扬、自强不息的“壮志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越国百姓随后杀了扬言要填井的吴国士兵。面对这帮“觉悟超凡”的百姓们所迸发出来的那股昂扬的“民气”,让勾践打消了迁都的念头,还命文种将百姓需要的耕种工具一一安排到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在这里配合天气的变化,试图营造出一种天人感应的舞台效果。
第四幕,苦成一上来就打伤了不让在会稽城上安放战鼓的吴兵,并得罪了吴国的被离将军,差点被泄皋抓起来砍了腿。年轻气盛的被离来到越国,一会儿要求越国铲平新造好的城墙,一会儿又要求贡献肥牛千头,要使越国没有能力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苦成等越国百姓就在勾践与范蠡等人的领导下,保存实力,韬光养晦。牛没有了,勾践与苦成带头用人来犁田!不久,被离又要搜寻当年失踪的“镇越宝剑”。这场全城大搜索使得勾践在城南偷偷储存的兵器岌岌可危,要保存实力,还是要维护国格?面对这两难的境地,还是苦成再一次站了出来,向吴兵自首,并牺牲在大禹庙前。苦成的牺牲让勾践心痛不已,但也促使他坚定了报仇雪恨的决心。
最后一幕中,十五年后,穷兵黩武的夫差在黄池会盟前,带领着大军兵临会稽城下。年轻的士兵都纷纷准备决一死战,可泄皋却依旧劝说勾践卑躬屈膝。这时,奴隶鸟雍跳了出来,怒斥大夫泄皋的绥靖政策,坚决要求一战。夫差的前来提出了许多无理的要求,并偷袭越国的兵船,勾践在无霸的口中听到了英勇善战的越国士兵在鸟雍的带领下奋起反抗,虽然鸟雍最后牺牲了,但激发起了越国士兵的斗志,最终粉碎了吴国的阴谋。为了纪念鸟雍,勾践将他一同配祭在苦成崖上。
纵观全剧,曹禺在这里塑造的一系列“人民”形象,几乎都是刚毅不屈,坚贞爱国甚至还会不顾生理的需要而去“饿着肚子干革命”。并且,从勾践战败到复仇成功的二十五年里,越国人民似乎就与勾践君臣“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在剧中所有的行动,自始至终且不惜一切代价都是为了向吴国复仇。在剧中,这一强烈的自觉意识都超过了越国的“肉食者”们。这一股力量甚至主导并推动着勾践、范蠡与文种为代表的越国统治者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越国复兴大业。对于这一系列的人物塑造,在当时就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
吴、越的矛盾,仅仅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民夺地,扩大势力范围的内部矛盾,它既不具备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事实上那时也没有完整的国家概念),也不是历史发展中新旧势力的斗争,二狗相咬,谁胜谁负,带给人们的,同样是田园荒芜,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对人民没有好处,对历史也不起推动作用。[2]
这样“自任天下之重”的普通劳动人民而且还能与春秋时期的上层统治者走得如此之近,并能如此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大事上来,甚至左右君王的决策。这种无视历史局限性的人民形象真不可不谓“超级”。对此,就曾有学者指出:
一部《胆剑篇》从头到尾只是有知识、有王族血统的人民代表苦成,生前如何圣贤、死后如何神明的“精忠报国苦成传”。而这位一会儿是稻、一会儿是米、一会儿是剑、一会儿是胆的苦成老人……只是孔子《论语》中明确否定过的“怪、力、乱、神”式的神道人物。身份低贱的丧家奴鸟雍在爱国圣战中英勇牺牲,在等级森严的神道秩序中所成就的,更是“配祭在苦成崖上”的更加低级的“怪、力、乱、神”。[3]
《甲午海战》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全剧主要以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为矛盾为主线。其中,被正面突出描写的主战派除了邓世昌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之外,主要还是下层的水兵与刘公岛军港附近的百姓。底层军民坚决的斗争精神贯穿了全剧始终。在第一场老渔民李大爷和老水手就分别表示“咱百姓是不怕什么鬼子的”;“当兵的更不是孬种”。
另外,剧中将丰岛海战中济远号管带(以在史学界尚存争议的方伯谦为原型虚构的)方仁启,被特意刻画成一个临阵脱逃、贪生怕死的海军军官,从而凸显以李仕茂与王国成为代表的水兵在丰岛海战中对日坚决作战的决心与意志。威海卫军港附近小渔村的渔民虽然屡遭官府的弹压,但个个始终渴望与日本一战。他们不畏官府的弹压与苛捐杂税,要上万民表,要求光绪帝对日宣战。甚至在最后一场,北洋海军战败,提督丁汝昌自杀,激愤的威海卫渔民“自己拿起刀枪”自发组织了起来,和以李培青为首的底层水兵杀了投降派与间谍,并在浩大的“人民战争”的声势下落幕。且不说当时人民群众的斗争对甲午战争的进程真正起到过多少作用,退一步来说,人民群众斗争的觉悟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再怎么也是有一个由模糊到明确、由不自觉到自觉、从涣散的到有组织的过程。早在这个戏上演后不久,在京就组织过一次研讨会。在会上,历史学家黎澍就指出:
这个戏里面写群众的觉悟也还有过高和过于一致的现象。近代中国人民的民族觉悟是逐步提高的,不能认为从来就很高;对外国侵略的认识也是逐步清楚的,不能认为从来就很清楚。早期的群众斗争……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都是自发的,缺乏建立独立国家的自觉意识和反对侵略者的全民族的团结……当然,文学作品和科学著作不一样,文学作品可以把群众的觉悟写得高一些,集中一些,但所谓高,所谓集中,也应当力求所表现的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这样一个时代的群众斗争,而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群众斗争。[4]
戴不凡在当时也同样对剧中威海卫居民的觉悟颇有微词:
在当时北洋水师的根据地,消息灵通的威海卫,其居民燃起抗日的怒火,恐怕不一定就完全是由于日舰侵扰渔船的缘故。而他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所表现的觉悟程度,看来不完全符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且又自始至终没有发展的……[5]
除此之外,剧中将海军底层官兵与人民的关系处理成军民一致的情况,是否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还有待商榷。对此,马少波在当时就指出:
水兵有几个骨干分子是写得好,应该这样写。缺点是把水兵写成全是好的,不很符合历史真实,实际上当时的人民对于日寇的仇视,对于官兵也是反感的,甚至说也是仇视的,因为清朝的陆军腐化透顶,无恶不作,不必说了,即使新兴的海军由于社会制度的关系,也是腐化享乐,军纪败坏,使百姓十分厌恶。在当时,人民和海军的关系,作到像今天人民解放军的军民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6]
底层军民的关系在当时也很复杂的情况下,渔民和北洋水师底层的官兵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是否真的会像今天那样“鱼水情深”、“同仇敌忾”?剧中对渔民和底层官兵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未免失于简单。
再来看田汉创作的《关汉卿》。作者从手头极为有限的历史资料出发,结合了自己半生的生活经历,通过合理的想象,天才地创作了这部剧作。此剧和《茶馆》一起,并称为十七年时期话剧创作的高峰。“田汉写关汉卿就是写自己……田汉不仅能体会关汉卿的思想情感,还能用自己的经历来充实《关汉卿》的情节。”[7]关汉卿作为一个底层的文人,生活在元大都的勾栏瓦肆之间,靠着在太医院当差与写剧本为生,自然与底层的劳动人民走得很近。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前坚持“在野”的田汉不谋而合。当时就有评论也指出:
有些历史人物,本身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份子,如农民革命的领袖,或者是出身寒微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要表现好这类历史人物,主要是写好他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显然很重要……因为通过这类历史人物自身的斗争历史,也可以充分地体现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8]
于是,关汉卿就被顺理成章地塑造成了一个“人民剧作家”。虽然此剧对人民的处理上相对另几个历史剧来说自然一些。但还是没能离开那个时代的窠臼。
从全剧来看,人物处理上还是有着“脸谱化”的痕迹,好人坏人始终壁垒分明,立场坚定。剧中人民形象的觉悟与立场也有“过高过于一致”的问题。作者在剧中设置的人民形象始终旗帜鲜明并毫不动摇地站在关汉卿这一边。在剧中,关汉卿的行动始终无不受到大都人民,特别是朱帘秀的影响,在关汉卿为朱小兰的冤死而愤愤不平的时候,“笔不是你的刀吗?杂剧不就是你的刀吗?”正是在朱帘秀的开导提醒下,关汉卿投入《窦娥冤》的创作。而后,以朱帘秀、赛帘秀为首的戏班子成员们对《窦娥冤》这类针砭时弊,甚至会掉脑袋的戏,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个个都是义无反顾地出演该剧。当受到左丞相郝祯修改剧本的胁迫时,整个剧团成员在思想上都没有丝毫的动摇,朱帘秀甚至告诉关汉卿,“你放心,我宁可不要这颗脑袋,也不让你的戏受一点损失”。赛帘秀哪怕被挖去双眼时,仍旧痛骂阿合马。当关汉卿与朱帘秀身陷囹圄之际,两人相见,关汉卿建议她去找阿合马的老太太求情,朱帘秀一口回绝,依旧将生死置之度外。当他们不日就将处以极刑而陷入绝境时,依旧在刘大娘与女婿周福祥的打点下,通过向和礼霍孙送上万民禀,最终在“人民的力量”帮助下,关汉卿与朱帘秀才得以改判为流放杭州。
虽然,剧中朱帘秀作为一名杰出的艺人,受伟大剧作家的影响而愿意为自己的艺术理想而献身。关汉卿在剧中救了刘大娘的女儿二妞,刘大娘一家积极营救也有着合理的心理动机。但是将这些人物置于元朝——这个视文化知识为无物的“马背上的朝代”。来看这些人民形象,其觉悟也不免存在着作者一厢情愿的虚构。
在《文成公主》中人民形象的觉悟也是如此,甚至还成为了剧作的硬伤。在剧中第一场里的那位老大娘曾是在宫中侍候文成公主的侍女,因告假在禄东赞下榻的旅店里帮忙。正是在这位老大娘的帮助下,才使得禄东赞提前得知了文成公主的相貌,顺利地通过唐太宗最后一轮的考验,顺利地将文成公主迎娶到吐蕃。然而,在禄东赞准备用上好的金沙来收买老大娘的时候,却遭到了老大娘的严词拒绝。
老大娘 (傲然地)公主跟别人不同地方就是她经常教导我们对皇上,对大唐要忠心耿耿。怎么着,您想凭这一袋金砂叫我背叛皇上,出卖公主吗?您真是把我老婆子给看扁了![9]
禄东赞赶紧调换辞令,谦虚地从唐蕃人民永世相好的角度进行劝说,并用“最恭敬的礼节”将哈达赠予老大娘,“大义凛然”的老大娘方才将公主相貌的特征告诉禄东赞。禄东赞感激不尽,可老大娘居然还不忘提醒禄东赞要先谢皇上……
第三场的最后,“人民”的表现更为匪夷所思。当唐太宗最终答应吐蕃使臣禄东赞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后,出现了这样的景象:
太宗 (下位扶她)皇儿远嫁吐蕃,乃天下之福。你看唐蕃大臣,满朝文武,长安万民,都在替皇儿欢喜。
[宫娥打开帘幕,但见大明宫外风物群妍,欢声雷动。
群众声音:恭贺文成公主下降吐蕃!唐蕃亲好,千秋万代!
[在炮声乐声中,太宗夫妇,文武,妃嫔,送文成公主凤冠蟒服登上銮舆。[10]
在这个片段的编排上,明显地在常理与逻辑上存在着硬伤。固然,百姓是期望天下太平,人人安居乐业的,唐蕃和亲也是符合人民的期望。但唐太宗仅仅一句“长安万民都在为皇儿欢喜”后,长安百姓就真会有这个觉悟去放下手头的营生而跑到大明宫门口去为唐蕃和好而欢呼不已?况且,唐太宗与禄东赞等吐蕃使臣的交谈都在宫中举行。这样的重大的外交决定刚刚做出,百姓就会第一时间得知?作者这样的场景处理,更是让“人民群众”的觉悟达到了几乎先知先觉的地步。这样的处理,无论是从历史的内在可能性还是从艺术的逻辑上来说,都是说不通的。这背后,除了为达到政治上要求的艺术效果而牺牲其艺术真实,还有就是体现了那个时代,“人民史观”的决定性作用。
三、“居高临下”的“人民”
所谓“居高临下”主要是指,在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剧中的人物设置上,“觉悟超凡”的“人民”在剧中往往会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影响、教育、指导主人公,并具有左右主人公行动的能力,从而主导并影响着剧情的发展。
在《胆剑篇》中,勾践君臣的复兴大业的每一步,几乎都离不开以苦成为代表的越国人民的感召与督促。勾践战败后行将被押赴姑苏前,一位越国的“中年男子”将被吴国烧枯的稻子交到勾践手里;苦成一番壮怀激烈的嘱托,让他不要忘记耻辱,记得要回来重整山河,报仇雪恨。这也定下了勾践君臣在下一幕的最高动作——返回越国。
到了第二幕里,凭借着越国民女西施在吴国王宫中的地位巧妙周旋,才使得勾践君臣逃过了伍子胥的谋害。再加上文种与范蠡在吴国的上下打点,勾践才最终得以返回越国。
在第三幕,勾践回国后,全剧的最高动作就转到了复兴越国,向吴国复仇上来。然而,好事多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危机发生,应对危机,化解矛盾的动力又都来自于剧中的人民形象。越国因大旱而闹起了饥荒,勾践从吴国那里搞来了大米,分给百姓。但当苦成得知大米来自吴国,就不许自己的弟弟黑肩吃,还指责勾践没有骨气。勾践听闻后召见他,苦成依旧言辞激烈地要求勾践勿忘国耻,励精图治。
在第四幕,当吴国将军被离下令全城搜寻当年被苦成拔出的镇越宝剑时。一方面,为了维护越国的尊严,不能将宝剑交出;另一方面,如果吴国军队继续搜索,则勾践在城南安置的兵器库就有被发现并被收缴的危险。在此两难的境地下,勾践君臣束手无策,此时,苦成再次挺身而出,毅然决定牺牲自己后,嘱咐鸟雍要“快快做,少说话”,送苦胆给勾践,并告诉他“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苦成的牺牲,不仅解决了越国所遭遇的危机,还让让勾践顿悟,面对苦成送给他的苦胆和临终前的话,更是坚定了勾践励精图治、一雪前耻的决心。苦成死后,他牺牲的岩石上刻上了他的名字,并称作“苦成崖”为后人祭拜。
最后一幕,经过一番卧薪尝胆之后,越国国力大增,夫差在黄池会盟前,率领大军来访越国。想以借船为名,消灭越国的有生力量,以除后顾之患。在此危急时刻,奴隶鸟雍站了出来,成为了这一幕的剧情的主导者,他一边斥责泄皋的怀柔羁縻,与无霸一起要求勾践与吴国决战。面对强大的民意,勾践只能将灭吴的计划告诉了大家:他就是要让夫差安心去黄池,再趁吴国国内空虚再一举伐吴。可吴国之后企图偷袭越国的战船,还是在鸟雍不怕牺牲的作战中带领越军奋起抗击,最终挫败了吴国偷袭的企图,保全了越国的水军的实力。三年后,越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可在最后,还会从天外莫名传来一声“勾践,你忘掉会稽之耻吗?”勾践不禁悚然,连忙取出苦胆,表示依旧还要卧薪尝胆、自强不息……
由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越国战败后,全剧越国一方的最高动作就是复兴越国,向吴国复仇。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一波三折的矛盾危机发生。而应对危机,化解矛盾的动作,一方面是来自于勾践君臣的谋划,但更多的则是人民形象的直接参与处理。而且,勾践君臣所作的努力显然也是受到了剧中越国人民的影响。有学者对此就认为,作者“对勾践作为统治阶级的局限性考虑过多,这不是曹禺一贯的描写人灵魂的复杂性特色,而是根据‘阶级论’的理论来说明他的阶级局限性。在剧中,许多好的主张、办法都是百姓、臣民们出的,勾践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已。而作为庶民的代表苦成则过于理想化,集剧中众多好事于一身,显然是按照所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时代,拔高了这个人物。剧本不可避免地带上了那个时代对文艺的特殊要求的烙印”。[11]
在《甲午海战》中,以威海卫军港附近的渔民与北洋海军底层水兵为代表的“人民”面对和日本的战争,始终是剧中积极主战的坚定力量。他们坚决要求北洋水师对日作战,在第一场,万民折代表了威海卫渔民们的激愤。并且在第三场里,百姓从王国成和李仕茂这里得知了丰岛海战的原委后,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在渔民李大爷的动议下,百姓们联名写下了万民折,上书光绪帝要求对日宣战。到全剧的最后一场,日军舰队包围了在威海卫军港,在北洋舰队危如累卵的时候,人民群众再次站了出来。祭奠了在黄海海战战死的邓世昌等致远号官兵后,来到提督辕门要求丁汝昌拒绝投降,背水一战。丁汝昌自杀后,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处决了方仁启为首的投降派,拿起自己的武器在浩大的“人民战争”的声势中去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文成公主》中,作者虽然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禄东赞为首的吐蕃使团促成唐蕃和亲以及文成公主赴藏的过程,但剧中始终都在强调唐蕃和亲是顺应民心、合乎民意的,故而剧中的“人民”也都是拥护唐蕃和亲的。比如,禄东赞最后能通过唐太宗的重重考验,顺利地为吐蕃迎娶文成公主,若是没有馆驿里老大娘的帮助,是怎么也通不过唐太宗的最后一项考验的。在西去吐蕃的路上,不仅路途艰险,还要面对一路上来自吐蕃主战派对和亲的干扰,这使得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路途困难重重、一波三折,若当时没有一个熟悉吐蕃当地情况的达娃相助,也是很难平安到达吐蕃并顺利与松赞干布成亲的。
在对十七年时期几部典型的历史剧中的人民形象进行一番探查之后,总结出上述三个特点。其实,这几个特点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剧作者从当时的政治语境出发,建立在这样的逻辑联系之上:人民在“旧社会”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堪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而天生就有着斗争精神。根据人民史观的基本命题: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被置于历史主体地位的人民,自然显得“居高临下”,而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事迹都离不开人民的拥护与帮助。为了确保这一点上的政治正确,作者从这样的理念出发,必然会在当时的历史剧中塑造出具有如此特征的“超级人民”形象。而且,这样的“超级人民”也必然是千篇一律的符号化的形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