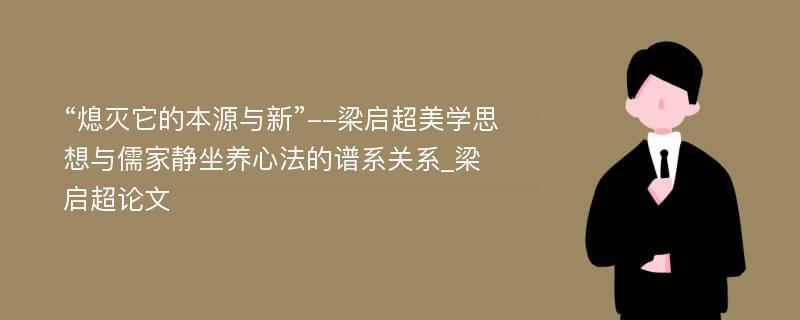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梁启超美学思想与儒家静坐养心法的谱系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谱系论文,养心论文,其所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3)06-0038-08
“淬厉所本有,采补所本无”[1](P.657)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释义》一文中提出的新民原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最基本的创造原则。该原则具有大气磅礴的建构主义意涵,即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渡期中,将传统与西方均视作本土现代性建构的质料,既秉持强烈的文化主体性精神,又保有广阔的开放性视野。作为“本无”之学的美学,其在20世纪初的舶来并不基于学理需要,更非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向本土殖民式的拓进,而是以林毓生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为发生逻辑,以对国民心性这一“大本大原”的培植为根本动因。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林毓生将该逻辑的谱系追溯到儒家心性文化传统,认为儒家根深蒂固的道德心智一元论决定了该逻辑的产生。[2](P.48)对林氏这一论断最具标志性的佐证,是第二代美学家朱光潜在1932年所作《谈美》的开篇之言。他称自己怀抱许多“旧时代的信仰”,其中一个信仰即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心太坏”,因此“谈美”的意义,正在于以审美作为“人心净化”的途径,最终从“大本大原”处下手,以图社会问题的解决。[3](P.6)这种信仰,无论在第一代美学家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还是第二代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内心,均深深怀有,从而决定了他们对西方美学的“采补”意向,进而在中国现代美学与儒家心性文化传统间形成了一条异常清晰的谱系脉络。
梁启超正是这一谱系脉络上的关键人物。与蔡元培、王国维相比,梁启超的美学成就并不引人注目,也无法与他自己在新史学方面的成就相比。由于他从未用功于德国近现代美学①,因此未曾像通过改造康德鉴赏判断“第一契机”而提出“无用之用”命题的王国维那样直接开出中国现代美学的框架,也没有蔡元培那种将美育纳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实践功绩,其早期在小说论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功利主义之致思路径没有脱离“经世致用”、“文以载道”的古代传统,而晚期的“趣味主义”在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20世纪20年代似已失去振聋发聩的效果。然而,梁启超对于百年中国美学的重要性丝毫不容忽视:王国维的审美功能论也好,蔡元培的美育体制构建也罢,中国现代美学的文化谱系和发生逻辑,恰恰由于作为西学道术的美学在纯化动机、提炼情感、升华欲望、扩充境界的“正心”功效方面与绵延两千余年的儒家心性之学高度契合,而毕生推尊陆王心学并以极高分贝影响近现代之交的梁启超,成为儒家心性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关键的连接点。梁启超虽然没有“采补”西方美学理论的文献证据,然而在其对“本有之学”的淬厉过程中却“内生”出可被冠之以“美学思想”的“趣味主义”。这种“趣味主义”与道德、政治论域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一反建筑在康德区隔性基础上的西方近现代美学,从而使其美学思想在中国现代美学诸子中具有最清晰的本土特色。
这种“本有之学”,粗言之即为儒家内圣道术。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称,儒家哲学与西洋主知之学(Philosophy,爱智学)不同,“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1](P.4954)因此他取《庄子·天下篇》中的“道术”二字取代“哲学”,“道是讲道之本身,术是讲如何做去,才能圆满。儒家哲学,一面讲道,一面讲术;一面教人应该做什么事,一面教人如何做去”。[1](P.4956)这种“道术”,按钱穆的话说即“‘人文知行’之学”。[4](P.118)作为“知行之学”的“儒家道术”,又分“内圣”、“外王”之学,梁启超称“外王之学”都带有时代局限,而内圣之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绝对不含时代性”,[1](P.4957)亦即古今通用。此处表明原本“道通为一”的“内圣外王”在近代发生断裂。
然而,“内圣之学”在清末民初对士人知识分子仍具极大影响,新输入的西学远不足以取代古老的内圣之学。正如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一文中所谈到的那样:“政治学术之外的个人修养部分,基本上仍是传统部分。”[5](P.132)王汎森详细考察了清末乃至民国以后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省心风习。他发现,这些士人知识分子虽政治观点各异,然而皆采用儒家“内圣之术”如省心日记、札记、日课、自讼法等多种形式完成个体道德修养。从晚清的士大夫到清末民初的戊戌诸子、蔡元培、杨昌济、顾颉刚、罗培常等人,甚至共产党人如毛泽东、恽代英、刘少奇等,均曾沐于省心风习之中。如果说王汎森梳理了谱系脉络,建构了比较宏观的历史语境,那么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书中则点出了梁启超对儒家内圣之学的继承:“在有关束性问题上,梁仍以某些新儒家理论和道德箴言作为方向。”[6](P.80)需要指出,王、张二氏注意的是儒家内圣之学是否延续的问题,却未曾发掘梁启超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淬厉”。
梁启超在师承上接清末汉(乾嘉汉学)、宋(宋明理学)两大学统,汉学方面师从学海堂陈梅坪而为陈东塾(澧)再传弟子,宋学方面则因康有为而接朱九江(次琦)一脉。当然,在其18岁(1891)拜谒康有为之后,宋学中的陆王心学成为新的“为学方针”,乾嘉汉学反而成为其一度攻击的对象。乾嘉汉学在方兴之时本有“复三代之旧制”以经世之外王诉求,全盛之后流于考据训诂之支离,因此在清末“千年变局”语境中尽管努力调适、但仍显得“不合时宜”,西方政治学、群学等新外王道术的输入随即造成其“断裂”。然而在修己内圣方面,康有为所领戊戌诸子乃至清末许多士人,多乘道、咸以降的汉、宋调和趋势,从宋明理学中寻找思想资源和形式方法,并在民国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讨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萌芽,当以其师从康有为之后、求学于“万木草堂”之中,受康有为讲学时心性省养方法的影响为起点。梁启超“淬沥”“本有之学”以生“美学思想”,精言之即对经康有为传承的儒家静坐养心法之“淬沥”。
根据《长兴学记》(1891),康有为于万木草堂所设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四纲;四纲下各设四目:“志于道”分“格物、厉节、辩惑、慎独”四目,“据于德”分“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四目,“依于仁”分“敦行孝弟”、“崇尚仁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四目,“游于艺”分“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四目。[7](PP.339-351)需要指出的是,康氏四纲十六目,本于其师朱次琦(九江)“四行五学”[8](P.709)而加以增删,其中九江“五学”中“掌故之学”去除后为南海“游于艺”四目,而九江“四行”之“敦行孝弟”为南海“依于仁”首目,“崇尚名节”为“志于道”第二目,“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为“据于德”第三、四目。
“志于道”意即立志,“若大端有立,则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其于为学,思过半矣”,[1](P.343)“据于德”则为修养方法,“德者,得也,即《大学》定静安虑然后能得也”,“依于仁”、“游于艺”则为具体的知行类目。在“据于德”所包含的个人修养方法上,康有为以“主静出倪”为首,即承续宋明儒的静坐养心方法,化周濂溪(敦颐)之“主静立人极”与陈白沙(献章)之“静中养出端倪”二语为一,简言之为静养法。此法紧接于“志于道”最后一目,即刘嶯山(宗周)于《人谱》中所标“慎独”一义。“慎独”与“主静”具有次第关系,康有为称:“学者既能慎独,则清虚中平,德性渐融,但苦强制力索之功,无优游泮泱之趣。夫行道当用勉强,而入德宜阶自然。”[1](P.344)刘嶯山所标之“慎独”为“未发”之前“克己修慝”,因“强制力索”而生“勉强”“无趣”,故康有为以“主静”作为自然进德之阶,个中当含“优游泮泱之趣”——然而康有为并未阐明此种趣味何以能生于“主静”。总之,慎独为省心法,主静为养心法,而紧接的第二、三、四目“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则为省养二法所生由心及身的效果,即养其心而不动其志、改变个体气质、规范日常行为。
省养二法在万木草堂中绝非流于口头教诲,而是以“日课”制度加以保证。“日课”共七目,为“读书”、“养心”、“治身”、“执事”、“接人”、“时事”、“夷务”。论及“养心”一目,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1897)中“依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演其始教之言”称:“养心有二法门:一曰静坐之养心,二曰遇事之养心。学者初学多属伏案之时,遇事盖少,但能每日静坐一二小时,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梦剧不乱,宠辱不惊。”[1](P.114)“静坐一二小时”是为“求其放心”,亦即收束意念,简言之为“敛其心”,此为康有为静养法之主要意图。而对于“治身”一目,梁启超称:“治身之功课,当每日于就寝时,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论行事,失检者几何?而自记之。始而觉其少,苦于不自知也;既而觉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馁,一月以后,自日少矣。”亦即采用省心法②,具体形式为“记过格”。对于日课之成果,学生以此七目设札记,“以朔、望汇缴,商略得失,缉熙光明,庶几日新”,[1](P.115)亦即札记将定期于师弟子间浏览,以检查省养得失。
省养之法本为儒家内圣工夫,在康有为处呈次第关系,二者似无轻重差异。然而静养为自然入德法,康有为称“得此把柄入手,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矣”,即于静养中可开出“与天地同流”之境界。这一方法及教义本身皆为梁启超所尊奉,一方面将静养之教义重要性加以突出,另一方面又在具体方法上多加发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合办于1897年的湖南时务学堂,继承并发展了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的基本教义和方法。在由梁启超所作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下简称《学约》)中,将康有为的“四纲十六目”和“日课七目”简化为“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等十条目。关于“养心”一目,《学约》中称“养心者,治事之大原也”,使教义本身的重要性达到了新高度;同时又进一步细化了方法:
养心之功课有二:一静坐之养心,二阅历之养心。学者在学堂中,无所谓阅历,当先行静坐之养心。程子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今功课繁迫,未能如此,每日亦当以一小时,或两刻之功夫,为静坐时。所课亦分两种: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此是学者他日受用处,勿以其迂阔而置之也。[1](P.107)
至于学堂学生可得而行之的“静坐养心”功课,梁启超将之细分为两种方法:一是“敛其心”,此即对康有为静坐养心法的主要目的——“求其放心”的提炼,其状态为“收视返听,万念不起”,其效验为“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而“纵其心”一法在康有为《长兴学记》中未特别标出,与“敛其心”所主的收束意念截然相反,梁启超将该法又细分为二途,“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系康有为所称“天地我立、万化我出”之由来,实“观”与天地同流之境界,“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则同样强调境界开创,其所不同的是前者依凭本土的形而上学(体道之学)通达天人合一之境,而后者借助想象力虚构砥砺意志之情境。需要指出,梁氏“纵其心”以开境界的方法,在康有为《长兴学记》中虽未单独标举,然而亦有渊源,其“养心不动”一目称:
必通天人之故,昭旷无翳,超出万类。故人貌而天心,犹恐血气未能融液,将死生患难体验在身,在有如无,视危如安,至于临深崖,足二分垂在外,从容谈笑,其庶几乎?死生不知,则毁誉谤讪如蚊虻之过耳,岂复省识?[1](P.344)
其中“通天人之故,昭旷无翳,超出万类”为梁启超“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之效验;而“将生死患难体验在身,在有如无”则启梁任公“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虚构法门。因此,“纵其心”法,正是梁启超对康有为所传承的儒家静坐养心法的进一步发展。
《学约》称“养”为“大原”并标“纵其心”一义,不同于《长兴学记》中“省”在“养”前及以“敛其心”为“静养”之主要途径;其美学思想的早期萌芽——心境说或境界论恰恰蕴藏于其间,可分为“遍观天地之大”所指的形上境界与“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虚构情境。而作于两年之后的《自由书·惟心》(1899),正是对《学约》所标举的“纵其心”法的扩充演绎,该篇亦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梁启超“审美本体论”的出处。在《惟心》中,梁启超开篇即称:“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1](P.361)心可造境,造境心法正是对“纵其心”法的扩充,无论是形上境界还是虚构情境皆由心所造;物境皆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此即康有为《长兴学记》中“养心不动”条目的演绎:“养心不动”,无非是不以一己物境动其志,故而梁启超在《惟心》篇末称“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其所以能如此者,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惟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1](P.362)其标举“三界惟心”,实是以心境去弊物境的内圣存养之术,为人文知行之学,其落脚点在“行”而非“知”,与西方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唯心”、“唯物”之分重点完全不同,因此“唯心主义的审美本体论”皆系以西释中而生的错识。
《惟心》一篇之所以可视之为梁启超美学思想萌芽的标志,全因该篇所标举的“心境”以感性或情感体验为根抵,与“物境”指涉的功利是非脱开距离,又与西方作为“感性学”(Aesthetics)的“美学”自然合契。梁启超称:
天地间之物一而万、万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风自风,月自月,花自花,鸟自鸟,万古不变,无地不同。然有百人于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风、此月、此花、此鸟之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千焉;亿万人乃至无量数人同受此感触,而其心境所现者亿万焉,乃至无量数焉。[1](P.361)
“一而万,万而一”中“物”为“首一”,感性或情感体验为“万”,而“心”为“末一”。“一而万”,是指面对同样的事物,情感或感性体验各个不同,从而同样的事物生不同的面目;“万而一”,则是指差异性的体验以及差异性的事物面目皆生自心之一体。于是在梁启超那里,感性体验虽发自对外物的“感触”,然其源却生自人心。因此“惟心”所源之“纵其心”并非放纵心意于外物,而是要借打开心境——感性体验之境界而脱离物境束缚。此文对感性体验的重视,与三年后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高度一致,该文亦被研究者认为是梁启超早期美学思想的代表性作品。文中梁启超缕析了小说“移人”四功能,曰“熏”、“浸”、“提”、“刺”,皆针对人之感性或情感而言;而小说能摹“现境界之境”,能写“他境界之状”,亦即小说能开境界,与《惟心》一篇在话语上的直接关联性一目了然。
梁启超将感性经验或情感体验作为其美学思想产生的逻辑起点,并将之浸润于清末士人呈现的心性省养风习之中,体现于儒家静养工夫所开之境界中。从《长兴学记》(1891)到《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再到《惟心》(1899),呈现出一条非常清晰的演进线索。演进的结果,是“存养”日益重于“省克”,最终经属于“存养”的“纵其心”途径产生了美学思想的萌芽。这一萌芽充分表明了本土文化传统中道德与审美的逻辑发生关系:儒家静坐养心术原属道德修治法,然而由此法亦可衍生美学思想的萌芽。当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于20世纪初汲汲于德国美学之时,梁启超则继续淬沥其本有之学,完善其修德之法,因而有了作于1905年、同样富含美学思想的《德育鉴》。在该书中,梁启超对儒家静坐养心法及其所标举的“纵其心”途径,在方法论上加以进一步的提升。
《德育鉴》从《四书》《五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摘录先儒修身格言并自加按语,以“欲从事修养以成伟大之人格者”为潜在读者。分“辨术第一”、“立志第二”、“知本第三”、“存养第四”、“省克第五”、“应用第六”六部分。所谓“辨术”,自辨心术是否纯正;所谓“立志”,立“自拔流俗”、“必为圣贤”之志;所谓“知本”,以阳明“致良知”为修德之本,而以朱熹格物致知路线为非;所谓“存养”、“省克”,则继续探讨其从万木草堂中传承而来的道德修治法;所谓“应用”,则针砭德育“无用”的社会认识。六部分中,“存养”与“省克”这两种道德修治方法之关系,得到了更加清晰的阐明。在《存养第四》导语中,梁启超称:
良知之教,简易直捷,一提便醒,固是不二法门。然曰吾有是良知而已具足矣,无待修证,是又与于自欺之甚者也。阳明以良知喻舟之有舵,最为确切也。顾舵虽具而不持,则舟亦漂泊而不知所届耳。修治之功有三,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而存养为之原。[1](PP.1510-1511)
王阳明以舵喻良知,梁启超则借“持舵”喻良知修治之法;修治之法一分为三,“存养”为大原,此处是《学约》中养心教义的持续强调。而在《省克第五》导语中,梁氏称:
存养者,积极的学问也。克治者,消极的学问也。克治与省察相缘,非省察无所施其克治,不克治又何取于省察?既能存养以立其大,其枝节则随时点检而改善之,则缉熙光明矣。[1](P.1524)
“存养”之大本大原既立,省克则为修剪枝节之余事,存养与省克之先后、轻重一目了然。梁启超在“存养”一条中收录的宋明儒语录,进一步佐证“存养”之于“省克”的重要性,如陆象山“涵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吕心吾“涵养要九分,省察只要一分,若没涵养,就省察得,也没力量降服那私欲”等等。而在“存养”法中,梁启超基于其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所述“纵其心”途径,加以进一步的发明:
既明存养工夫之紧要,今当次述其用功之法,先哲所标,大率以主敬主静两义为宗派,以启超绎之,尚有主观之一法门。佛教天台宗标止观二义。所谓主静者,本属于止之范围,而先儒言静者,实兼有观之作用。必辅以观,然后静之用乃神。故今类抄之,以为存养之三纲。[1](P.1515)
此处,梁启超在儒家存养功夫“主敬”、“主静”二法之外,又发明了“主观”一法。“主敬”原出于《周易·文言》“敬以执内,义以方外”,程颐标“涵养需用敬”作为存养方法,宋明儒无论程朱、陆王,均不废此义。“主静”即静养法,康有为《长兴学记》“据于德”首目即为“主静出倪”。梁启超所标举之“主观”,虽言及佛教“天台宗”“止”(samatha,即入定)、“观”(vipassanà,即慧观)二义,又称“古代道家者流,言之最多”,而“儒者则未闻有专提此义为学鹄者”,[1](P.1522)然而其“观”之来源,恰是发明自万木草堂中“静养”法,承续其《学约》标举的“纵其心”一途,并非得自佛、道二家,其直接启思是从康有为处得来,而所摘语录均选自儒家:
大学言心广体胖,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皆以观而受用者,宋明儒言观亦甚多,特未提以为宗耳。如周子言观天地生物气象,二程门下多言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皆是也。第观之法门不一,此其范围尚狭耳。南海先生昔赠余诗云“登台惟见日,握发似非人;高立金刚顶,飞行银汉滨。午时伏龙虎,永夜视星辰;碧海如闻浅,乘槎欲问津。”午时伏龙虎,止也;永夜视星辰,观也。南海先生之学多得力于观,亦常以此教学者。[1](P.1522)
梁启超称“主静”原属于“止”之范围,为《学约》中“敛其心”一途,即《学记》中“求其放心”,亦即康诗“午时伏龙虎”;然静中“兼有观之作用”,亦即《学约》中“纵其心”一途,为“永夜视星辰”。故观生于静,以“观”辅之,“静之用乃神”。观为静之用,“观之为用,一曰阔其心境使广大,二曰睿其智慧使明细,故用之往往有奇效。第非静亦不能观,故静又观之前提也”。[1](P.1522)观之为用,可“阔其心境使其广大”,《学约》《惟心》等篇中的心境论或境界论,即述《德育鉴》中观之效验,《德育鉴》则以“观”为上述两篇中“纵其心”一途的方法论提升。在同属存养法的“主敬”、“主静”和“主观”三法中,梁启超尤为推举“主观”法,称:
人之品格所以堕落,其大原因总不外物交物而为所引,其眼光局局于环绕吾身至短至狭至垢之现境界,是以憧扰缠缚,不能自进于高明。主观派者,常举吾心魂,脱离现境界,而游于他境界也,他境界恒河沙数,不可耽举,吾随时任游其一,皆可以自适,此其节目不能悉述也。此法于习静时行之,较诸数息运气于鼻端白参话头等,其功力尤妙。心有所泊,不至如猢狲失枝,其善一也。不至如死灰槁木,委心思于无用之地,其善二也。闲思游念,以有所距而不杂起,其善三也。理想日高远,智慧日进步,其善四也。故吾谓与其静而断念,毋宁静而善观,但所谓观者,必须收放由我,乃为真观耳。[1](P.1524)
其中“现境界”与“他境界”皆已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出现,“现境界”即为《惟心》一篇中的“物境”,而如“恒河沙数”般的“他境界”即为《惟心》中的“心境”。梁启超认为,主观之法较诸“数息运气于鼻端白、参话头”等传统静养法,“功力尤妙”,妙处体现为四:一为由静所开境界可“泊心”,不至心猿意马;二不至于流于禅定之止思;三可收束游思杂念;四可因境界打开而使“理想日高远”。主观法要求修治者能从物境-现境界之功利纠缠中脱离出来,并优游于基于感性差异的无量心境-他境界,此实解释了康有为《长兴学记》中主静内含“优游泮泱之趣”之缘由。故而,梁启超称“与其静而断念,毋宁静而善观”,亦即不采主静原有之“止”义,将《长兴学记》中静养工夫“求其放心”以及《学约》中所标“敛其心”明确视作“观”之第一步,而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最终独尊开境界、扩胸襟、重感性之“主观”,而康有为的“主静”也变成了梁启超的“静观”。“主观”或“静观”,正是对其“境界论”或“心境说”以及“纵其心”途径的方法论提升,是对儒家静坐养心法的进一步发明。
梁启超美学思想生于对儒家内圣道术——静坐养心法的不断淬厉,由此决定了其思想中审美与道德之间的高度连续性,一反西方美学传统开自康德等人的区分性特征。对于梁启超而言,基于情感体验的“心境说”及“静观论”皆开自儒家静坐养心道术,因此皆不以审美为独立目的,而以道德修治和人格养成的知行实践为鹄的。就此而言,其美学思想实为儒家道术的副产品,一如其“小说与群治”中的文艺思想为政治思想的副产品。当然,当“心境”或“静观”的“旧酒”装入20世纪20年代“趣味主义”的“新瓶”之后,不少不了解这一演进过程的研究者误以为这是一种“采补”西洋道术而产生的“成熟的美学思想”。
事实上,“趣味主义”不但在话语上与其早期论述一脉相承,而且仍秉持着强调审美与道德之间高度连续性的本土理论特色。梁启超的“趣味主义”首先以对感性或情感的肯定为基底,这实是《惟心》等篇的理论延续。梁氏称“趣味是人生的原动力”时,亦称“情感是人生的原动力”;在标榜“趣味主义”、“趣味教育”的同时,也倡导“情感主义”、“情感教育”。[1](P.3921)此种情感融道德情感及审美情感于一体,在作于1921年12月的《“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梁氏称自己的人生观以“知不可而为”的“责任心”和“为而不有”的“兴味”作为基础,又称“责任心”和“兴味”都是“偏于感情方面的多,偏于理智方面的少”。[1](P.3413)“责任心”偏重道德情感,由省而得,孟子“四端”即“仁、义、理、智”的基底即为道德情感,完全不同于康德式的“理性命令”,梁氏此说可见其儒家道术的一贯性;而“兴味”则偏重审美情感,由养而致,为体道之后所生乐趣。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和共通性体现在:道德情感与审美情感可相互转化,转化的可能性是两者皆排斥直接功利,此即“孔子与点”的乐道体验和“孔颜之乐”的崇高体验,皆融道德情感及审美情感于一体。因此,梁启超称:
“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两面,“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1](P.3414)
也就是说,“兴味”与“责任心”是“一体两面”,道德情感与审美情感是一体两面,“合体”之后的“一个主义”即“趣味主义”。趣味主义所包含的这两大构成要素之关系,实际上植根于《长兴学记》中“强制力索”的“慎独”与内含“优游泮泱之趣”的“主静”关系,以《德育鉴》中“省克”与“存养”之关系为先导,包括刘宗周“慎独”、曾子“三省”成就了“强制力索”而得的“责任心”,而梁氏30余年来对康有为“主静出倪”的不断发明则成就了内含“优游泮泱之趣”的“兴味”。
在作于1922年4月的《趣味主义与趣味教育》一篇中,梁启超称自己的人生观是“以趣味作根柢”,此时出现的“趣味”实包“兴味”和“责任心”于一体,系对《“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扩充;又称“趣味教育”一词为欧美教育界所通行,并非自己的发明[1](P.3963)——事实上,此种“趣味”范畴与其说是因王国维、蔡元培等人20多年前引进德国美学而信手拈来的现成范畴,倒不如说是源于30余年前康有为称主静可生“优游泮泱之趣”的思想。而其四个月后所作《美术与生活》乃至更早的《晚清两大家诗抄题辞》中的基本内容,则进一步证明了“趣味主义”源自其对儒家内圣道术的淬厉而非德国美学的采补。
在《美术与生活》中,梁启超称趣味之源泉生自三种途径,其一为“对境之赏会与复现”,其二为“心态之抽出与印契”,其三为“他界之冥构与蓦进”。[1](PP.4017-4018)此三源泉皆为其对早期《学约》《惟心》乃至《德育鉴》中境界说或静观论的扩充演绎。所谓“对境之赏会与复现”,此境既包含对外部世界的观赏,即《德育鉴》中所谓“永夜视星辰”之“静观”,又包含了心中复现之情境;所谓“心态之抽出与印契”,即心态从“物境”或“现境界”的功利纠葛中抽出,并借同感与他人发生“印契”;所谓“他界之冥构与蓦进”,即因现境界之残缺而冥构一完美理想之“他境界”,源自《惟心》篇中“物境”与“心境”之别,而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德育鉴》中亦存在明确的发展线索。在作于1920年的《晚清两大家诗抄题辞》中,梁启超总结趣味的发生机制“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1](P.4927)
总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发生,主要来自其对清末以来儒家静坐养心法的不断淬沥:从康有为《长兴学记》的“慎独”与“主静出倪”,到《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对静养法“纵其心”途径的标举,再到《惟心》篇由“纵其心”途径而生的“心境论”或“境界说”,进而到《德育鉴》以“主观”或“静观”作为对儒家静坐养心法的发明和“纵其心”途径的方法论提升,梁启超早期的美学思想萌芽不断生发,最终产生了其在20世纪20年代标举的“趣味主义”美学思想的主要内涵。
有关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谱系考察,对中国现代美学研究及当代美学发展具有如下启示:首先,就学术史研究而言,学科意义上的美学虽“采补”自西洋,然而其内驱力却来自中国本土的心性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清末的传承和发展不应为研究者忽视。梁、王、蔡三人均“一体两面”,既是开启现代学术的首批知识分子,同时也是脉承清末学术传统的最后一批士人。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可以将中国现代美学史与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断裂带接续起来;这种接续将为研究本土审美现代性的发生问题提供宝贵启示。其次,就个案研究而言,梁启超在“三大家”中是典型的“内生型”美学家,其“美学思想”完全来自对儒家心性文化传统的淬沥。这提示我们,在美学研究过程中,除了对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家保持注意之外,还需要将目光投射于那些并不“直言”美学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如对儒家心性文化传统进行现代性发展的现代新儒家,其对道德与审美的关系亦保持着本土特有的高度连续性,个中资源弥足珍贵。最后,就当代意义而言,从谱系脉络上看,梁氏美学实为儒家内圣工夫的现代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克服了传统工夫论囿于道德约束而不利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毛病,另一方面又因内含丰富的实际操作方法而能有效弥补当代审美教育理论流于空泛、无助于美育实践和德性养成的现实弊端。
注释:
①一些研究者认为,梁启超曾经接触过康德、费希特以及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因此比较粗疏地认为梁氏美学有采补德国近现代美学的成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文献证据表明梁氏曾经阅读、编译哪怕只是介绍过自东西两洋舶来的美学理论——这点迥异于“三大家”中的王国维和蔡元培。
②同样作为“省心”法,“曾子三省”与刘宗周“慎独”有不同之处:“吾日三省吾身”,亦即在心中自省每日思想行为过失,以与人交往方面的“诚”、与友交往方面的“信”、学习方面的“勤”为标准,是在“已发”之后进行反省;而“慎独”则是在“未发”时下工夫,亦即扼杀不善之思想苗头。梁启超此文中虽主要谈曾子三省,然而其后的道德修治中亦结合刘氏慎独,如1900年曾自责“其大病在于不能慎独戒欺”,不足以任事,故而设日记自记每日“身过、口过、意过”,“复为长兴时之功课”。参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标签:梁启超论文; 美学论文; 康有为论文; 养心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儒家论文; 道术论文; 学记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