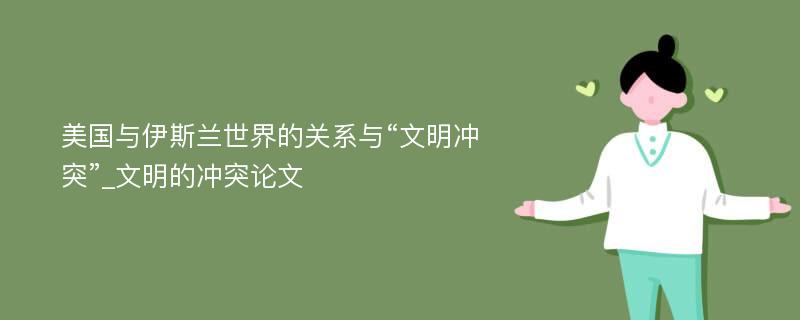
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与“文明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美国论文,冲突论文,关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互不信任、渐行渐远
九一一事件后,西方某些媒体出现大量对伊斯兰教义和穆斯林习俗歪曲不实的报道, 误导了舆论,“伊斯兰威胁论”甚嚣尘上,给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撞”之火又 加上了大把干柴。一项民意调查表明,3/4的美国穆斯林亲自或见证别的穆斯林遭遇过 社会偏见。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但对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 有很大的保留甚至是反感,对美国奉行的价值观感到厌恶。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阿拉伯 -美国协会2004年6月间对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的3300位民众进行的调查,和2002年相比,阿拉伯民众对美国的好感急剧降温。在埃 及,这一比例仅占2%。与此同时,反美恐怖活动层出不穷,且恐怖组织以外的反美暴力 活动也有所发展。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2004年7月5日说,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之间 正在形成一道“铁幕”,如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及穆斯林国家不能根除引起愤 怒和仇恨的原因,那么将会出现“更深层次的混乱和绝望”以及“更多的恐怖主义和一 场逼近的文明冲突”(注:2004年7月6日中国日报网站。)。
伊斯兰世界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不满并非一时突然发生之事。由于美国在1967年 、1974年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保护摇摇欲坠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以及后来派军队登 陆黎巴嫩等原因,美国同伊斯兰世界之间就产生了较大的裂隙。有的伊斯兰教领袖认为 美国是伊斯兰世界一切灾难的根源。伊斯兰世界两派——主张稳定的一派与主张变革的 一派都认为美国是一种威胁(注:马兹哈尔·哈米德:《阿拉伯对美国感到恼怒》,载 《纽约时报》,1984年2月24日。)。由于对外国的政策不满,对外来价值观感到失望, 对外来生活方式感到厌恶,于是一些人在寻找和宣扬“只要伊斯兰”之类的自我认同观 念。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对穆斯林的种种偏见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不断滋长。例如,萨义 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说:正像美国与欧洲批评文学所表明的那样,1967年战 争以来,对阿拉伯世界的描述是粗劣的、简单化的、粗暴的和种族主义的,将阿拉伯世 界描绘成为“低等的‘赶骆驼的人’、恐怖主义者和盛气凌人的阔酋长”的电影、电视 节目不断涌现(注:参见[美国]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3年版,第48页。)。
虽然亨廷顿认为,1979年的伊朗革命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一场潜在战争的开 始。不过在当时,美国主要关心的是同苏联的对抗。为此,它在伊斯兰世界找到了一些 盟国,甚至对一些伊斯兰主义集团也还采取过支持的态度。伦敦大学皇家豪劳维学院南 亚史教授弗朗西斯·罗宾逊教授在《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的结束语中说:“美国在 20世纪整个80年代,因力求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遏制伊朗输出其革命的企图,对 伊斯兰主义一些集团持支持的态度。这说明伊斯兰主义者和西方二者采取非意识形态立 场所达到的程度。”(注:Francis Robinson,ed.,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Islamic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99.)美国对车 臣等地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以及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并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2000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后,情况有所改 变。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广泛恶化,出现了一些在“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 及“民族认同”等方面持较为极端立场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会使人想起,不同的 文明之间,是否真的就不可调和。
这一时期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已成为双方关系史上最紧张的时期之一。从国际关 系的格局看,美国—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这种变动必 然会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亨廷顿1996年曾经预言,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必 然会导致西方阵营的分裂,而欧洲与美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分歧,同样会促进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的扩张(注:参见[法国]《问题》周刊,2004年4月22日。)。
主要应归因于美国的相关政策
不能否认,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疏远与紧张,其中确有“文明冲突”的因素。但 是,不能把全部问题都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或差异。
亨廷顿论证说,在后冷战时代“各国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 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3个集团,而是世界 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 自己”(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 版,第6页。)。这样,就把文化的区别、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抬到过高的地位。人们都 看得到,现实冲突中有一些极端主义行为,如滥杀无辜、虐俘之类,尽管行为主体也受 一定价值观的支配,但很难将它们与任何“文明”、“文化”挂钩。如果将国际冲突全 都归因于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差异,将文化的不同视为导致冲突的“原罪”,显然不 符合历史与当今世界的现实。在亨廷顿所说的不同“文化圈”之间,也并非始终处于势 不两立的状态。就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来说,历史上的确有过穆斯林向基督教世界 扩张,以及西方向伊斯兰世界一再发动“十字军东征”的记录。但是双方关系史中还有 许多相互借鉴的佳话。就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源流而言,双方之间也有许多相互类 同的方面。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东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与犹太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类 同性要比东方其他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类同性多。
同样是“基督教文化圈”,同样是“西方文化”,为什么美国同中东国家关系紧张, 而同“圈”内其他国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却不同步紧张或同等紧张,很值得深思。一位 名为施伯雷·泰尔哈米(“Shiblev Telhami”,黎巴嫩裔)的美国教授在大学作报告时 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阿拉伯人憎恶欧洲,因为它推行殖民主义、“欧洲中心 论”。而有一些人对美国并不那么反感,甚至喜欢上美国的“民主”、“自由”和“美 国生活方式”。所以,他那时很想写一本《人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美国》,但是现在情况 完全不同了,他现在想写的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厌恶美国》(注:参见美国霍普金斯大 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评论》,2001年夏、秋季号。)。其所以如此,与美国和西方其 他一些国家在对伊斯兰世界关切的问题上采取的政策不尽相同有关。比如,在阿以冲突 问题上,在1973年“十月战争”之后,欧洲一些国家调整了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对阿以 双方采取较为“中立”的立场,同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它们同伊 斯兰国家的关系因此而有所改善。
美国无论过去和现在,也并非同中东所有的国家都处于“交恶”状态。至少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史表明:美国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可以同某些 伊斯兰国家合作,甚至结盟;美国也可以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同某些伊斯兰国家对抗, 并不完全取决于所谓的“文明圈”。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拉拢了一些国家,当然同时 也冷落甚至压制了一些不愿追随美国的中东国家。美国同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的原因, 主要应从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史中寻找,特别是要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相关政策中寻 找,而不应主要从双方文明关系史中寻找。
美国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在美国的偏袒下,以色列至今 仍然占据着戈兰高地,以军随心所欲地进出巴勒斯坦,并用各种新式武器对付巴勒斯坦 人。这不能不引起伊斯兰世界对美以两国的严重不满,并使伊斯兰世界成为伊斯兰主义 得以发展、蔓延的土壤。美国在谈到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冲突时,首先想到的是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对美国的挑战。其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包括宗教极 端主义又何尝不认为美国是它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挑战呢?
2004年年初,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讨会在多哈举行。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美国与 伊斯兰世界关系紧张缘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偏袒以色列和美以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在 原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一些政客想当然地把伊斯兰当成替代的敌人(注:参见《人民日 报》,2004年1月14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认为,如果主流的穆斯林认为巴以冲 突得到公正处理,那么全球恐怖主义将会减少75%。阿拉伯-美国协会负责人詹姆·佐格 比说:“阿拉伯人为什么仇恨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愚蠢。”(注:参见《人民日 报》,2004年8月10日。)认为问题出自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 识。
但是,美国并不想纠正它对中东的政策,九一一事件后,受报复主义的驱使,对反美 政权进行武力征服,并对一系列伊斯兰国家采取遏制和全盘改造的政策。前北约欧洲盟 军最高司令克拉克在《克拉克的批评》(The Clark Critique)一书中透露,2001年11月 在华盛顿遇见一位高级军官告诉他,九一一事件后,白宫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准备打 击7个穆斯林国家。布什打算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将矛头对准叙利亚、黎巴嫩、利比 亚、伊朗、索马里和苏丹。
许多穆斯林在解读美国这种征服、遏制和改造伊斯兰国家的政策时,认为它是在把矛 头指向伊斯兰文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也就不足为 奇了。
意识形态斗争未完全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
美国政府之所以会推行这样的中东政策,同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而不能 简单地与“文化圈”挂钩。历史形成的“文化圈”或文明与当今意识形态的关系较为复 杂。亨廷顿所说的“文化圈”是历史形成的,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既成的和不好选择 的,但是当今的意识形态则是五花八门,是可以选择的。同一“文化圈”的人们可以持 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圈”的人们也可以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亨廷顿所说的 “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冲突,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仍是 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有一种看法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在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会淡化。有些国家 的意识形态比过去淡化了,但美国并没有淡化。有学者指出:“我们常说美国抱住‘冷 战思维’不放,以‘民主’和‘人权’为工具推行霸权政策。美国当权者之所以这样做 而又较少受到其国内的牵制,是因为美国从来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本的国家,且在全 球化时代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非但没有削弱意识形态,反而强化了其中某些‘信条’” 。“美国的历史传统和今天的社会现实,决定了美国是绝不会淡化其意识形态的,无论 当政的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治思潮的钟摆偏向的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注 :王缉思:《美国丢不下意识形态》,引自中国日报网站《环球资讯》,2004年10月3 日。)
实际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一直有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认为 对反美政权可以进行武力征服和遏制,对伊斯兰国家推行“民主改革”是“天经地义” 的,只要认为哪个国家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即可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单边主义,“人 权”、“民主”高于别国主权,可以进行军事干涉,为了美国利益可以侵害别国利益, 可以无视国际法。这种“强势民族主义”也即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说的认为一 个民族国家有权将自己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强加给其他所有民族的“现代民族主义”( 注: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说,“现代民族主义”认为一个民族国家有权将自己的 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强加给其他所有民族)。
就伊斯兰世界来说,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架势,不能不做出回应。其中存在着反抗外 来侵略的民族主义者,反对“异教徒”玷污圣地的伊斯兰主义者,有进行武力抗争的圣 战主义者,也有不惜采用恐怖手段的极端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同美国的侵略行为 进行抗争是穆斯林的宗教职责。2004年8月31日卡塔尔一位著名的教职人员卡拉达维(埃 及人)在埃及的一次集会上就同在伊拉克的美国人作战一事说:“美国士兵和平民都是 侵略者,与他们作战是宗教的职责”。据认为他是一位温和的、很受尊重的宗教人士( 注:2004年9月3日中国日报网站。)。温和派尚且持如此看法,更别说激进派与极端派 了。
美苏之间的冷战,是意识形态之争,并非不同文化圈之争。同样,美国现在同伊斯兰 世界进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可以说是一种冷战,也不纯粹是两个文化圈之争。只不过 是美国冷战的对象有所改变而已。美苏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会全 面淡化。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 开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价值观的对立与“碰撞”凸显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之所以继续坚持其意识形态,同美国官方的价值观分不开,甚至 可以说是它坚持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实 际上是它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注:参见李德顺:《简谈什么是价 值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网站。)。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和民族优越感是美 国官方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美国主导,是“美国 治下的和平”,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要普遍推广。
美国官方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的价值观常常“因国而异”,常常存在着相互矛 盾的尺度,即人们常说的双重标准。美国反对阿拉伯国家占领别的国家,但它却可以不 经联合国授权,以未经证实的“理由”出兵占领一个阿拉伯国家。美国政府反对伊斯兰 国家拥有核武器,但是并不反对以色列研制核武器。问题还在于,美国还强迫其他国家 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或按照其人权或民主的价值观行动。它对民主价值的倡导和它对一些 国家的干预侵略,以及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阻挠等反民主的做法也是十分矛盾的。
在伊斯兰世界则存在着另一种价值观。相当多的穆斯林未必反对现代物质文明,但是 他们反对滥用这种文明成果。他们也未必反对民主,但要的是伊斯兰民主,而不是“美 式的民主”。虔诚的穆斯林以维护信仰共同体乌玛为己任,自然不能接受美国的“主宰 ”。而美国不但不了解、不尊重伊斯兰价值观(注:据盖勒普在伊斯兰国家的调查,只 有12%的穆斯林认为美国尊重伊斯兰的价值观,绝大部分穆斯林认为美国不尊重伊斯兰 价值观。),而且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取代伊斯兰的价值观。美国的这些做法不能不引起 人们的非议。这样,在价值观上的对立就被凸显出来了。
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不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批评说,美国的价值观将受到质疑 。当美国由“解放者”变为占领者与征服者之后,激发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感情,不赞成 ,乃至厌恶这种“帝国”式价值观的人不是减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
人们从西方国家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中可以看出,美国与欧洲一些国家之间至少在价 值观上有明显差别。德国哈拉尔德·米勒在一本书中提到了西方文明的裂变:提请注意 欧美间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忽视大西洋此岸和彼岸不同价值的 “侧重点”,便可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错误。他谈到西方内部美欧之间的文化争论,认 为“社会、国家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紧张压力,正在加深欧美间这道固有的‘鸿沟’” (注:参见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 判》(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第128~129页。)。法国《新闻报》月 刊也载文进行评论:“美国在不断疏远老欧洲,疏远欧洲的文化与文明,疏远欧洲的语 言和价值法则。”(注:[法国]《新闻报》月刊,2003年6月号。)
美国在价值观问题上所存在的优越感比西方其他国家更突出,美国一再以自己的文化 价值观作为衡量其他文化价值观的惟一标准,谋求改造别的文化价值观。硬要伊斯兰国 家以土耳其为老样板,以伊拉克为正在诞生的新样板,全都皈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 。但很难得到所有西方国家的认同。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的国际反伊拉克军事联 盟至今,它的离析、重组与再离析的演化史中,人们可以看出美国同它的一些西方盟国 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现在不仅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价值观提出质疑,在“老欧洲”, 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
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到的具有美国特色“国际主义”应反映“我 们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统一”的结果,由于受价值观的支配,国家利 益便有可能成为想象中的利益。美国凯托学会特别研究小组成员阿塔尔撰文说,这一点 “促使我们一味追求中东民主化,而没有考虑这种做法将给中东地区和整个世界带来的 后果”(注:[美国]《国家利益》周刊,2004年8月10日。)。
在价值观的对立与国家利益的对立这两种对立之间实现妥协都具有一定的难度。两相 比较,不同意识形态,尤其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妥协更难于国家利益或想象中的国家利 益的妥协。福格特预言,在今后几年,价值观的分歧将变得非常棘手。国际间可以就利 益问题达成妥协,但是在价值观方面达成妥协却难上加难(注:[美国]《新闻周刊》,2 001年4月6日。)。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不断进行调整,在一定条件下结成的盟友在另一 种条件下也可以予以抛弃,但修正美国傲慢的价值观是困难的。但是不进行这种必要的 修正,要与伊斯兰世界长期友好地相处,也难。
伊斯兰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以做一些政策调整,比如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 在九一一事件后不再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利比亚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解除制裁的条 件等等,但是要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放弃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却是很难办到的。 伊斯兰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毕竟已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积淀与发展,至今仍影响着众 多的人口。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但是要所 有的穆斯林都跟着改变,是难以做到的。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在对外政策上做了不 少调整。总统哈塔米提出了进行“文明对话”的主张。但是哈梅内伊2003年8月18日在 接见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和伊朗驻外大使时仍然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绝不会为了讨好 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而放弃给予伊朗人民尊严的伊斯兰教及其价值观。”他也深 知:“如果伊朗不放弃伊斯兰价值观,美国是不会满意的。”(注:哈梅内伊2003年5月 28日讲话,引自俄罗斯《独立报》,2003年5月29日。)这或许是美国套用对前苏联和东 欧进行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渗透,促使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经验”,对“大中东” 或“广义中东北非”进行民主化改造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价值观并非水火不容,关键是避免强加于人
美国新保守主义主张美国应充分利用目前空前强大的实力,在全球推进美国的价值观 ,以建立美国强权下的世界秩序。布什总统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提出“ 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美国派驻伊拉克最高文职行政长官布雷默2003年11月16日 表示,美国将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新政府,并制定一部“体现美国价值观”的新宪法( 注:《中国日报》,2003年11月17日。)。然而推行要一个伊斯兰国家宪法“体现美国 价值观”这样的举措,并不顺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为什么一定要制定“体现美国 价值观”的新宪法呢?从“大中东倡议”到“泛中东北非计划”,美国推进“民主化” 的图谋一再受挫,也可证明。
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在价值观上存在的尖锐对立有长期化的趋势。200 4年10月8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甚至发表文章说,就像冷战一样,西方同“好战的、 激进的伊斯兰势力”的斗争,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的努力。
不同的价值观并非水火不容,关键是要相互尊重,不能强加于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会不会改变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做 法。美国政府前高官理查德·克拉克出谋划策说:“总统应该在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行 动,对抗‘基地’组织以及其他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通过合作推广真 正的伊斯兰教义,赢得对美国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支持,向大众灌输替代原教旨主义的意 识形态。”(注:理查德·克拉克:《反击一切敌人》,转引自人民网,2004年6月4日 。)但是,美国在忙于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情况下,一时还难以顾及,而且要极 端主义者放弃他们极端的价值观,也不容易。
价值观是文明、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还不能说现在这种价值 观的对立与“碰撞”就已经是“文明的冲突”全面爆发了。亨廷顿也只是说有可能爆发 这种冲突。九一一事件后,他还呼吁不要将反恐战争变成文明的冲突。不过,加强文明 的对话,相互尊重,防止发生不同文明间的全面对抗还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各种文明 之间不管是冲突也罢,还是共存也罢,无论如何都不该拿它当做进行战争动员和加剧冲 突的一种精神武器。
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究竟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如果 美国不调整对巴以冲突的政策,继续偏袒以色列;如果美国继续通过“制裁”等手段对 伊朗、叙利亚、苏丹等被认为具有反美倾向的国家施加压力,进行遏制,甚至进行“先 发制人”的战争;如果美国军队继续驻在阿富汗、伊拉克不走,将军事占领长期化,扶 持过于亲美的政权;如果美国继续向埃及、沙特等在伊斯兰世界极有影响的国家输出意 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那么,美国同中东国家、甚至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则很难有较 大的改善。因为这看起来直接涉及的只是一个个中东国家,但是,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 牵动整个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
标签:文明的冲突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穆斯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