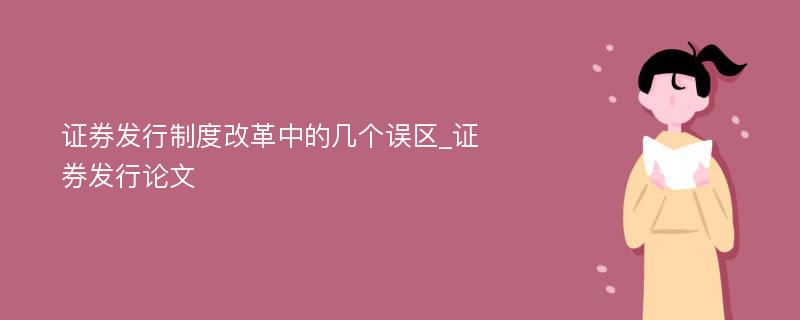
证券发行制度改革的几个思维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制度改革论文,误区论文,思维论文,证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证券市场正在从新兴、转轨市场向成熟市场发展过渡,同时中国处于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以及各项改革驶入深水区的时期,国际上则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证券市场改革呈现出系统性、复杂性、敏感性的特征。在这个特定阶段,改革成为专家学者、财经媒体、社会各界甚至街头巷尾的热门议题。各种意见呼声此起彼伏、政策建议遍地开花、境外经验纷至沓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流行着种种思潮,表现为概念的误读误用、解释的以讹传讹、观点的哗众取宠、结论的似是而非等等。近年来随着信息生成和传播渠道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化,证券市场的语境也或多或少出现集体非理性的“网络暴力”倾向。有些基于国情意识和问题意识的系统性、原创性思考,封闭于传统理论学刊的孤岛,湮没于信息海洋,鲜有问津。
几个思维模式的误区
归纳证券发行体制改革的思维误区,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容易出现概念、观点的简单对立,甚至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误区。在改革之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国人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极端意识形态束缚;在改革的第二阶段,邓小平南行讲话搁置了市场与计划“姓资姓社”的争论,淡化了传统思维对经济领域的控制。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仍有其文化惯性,在国际比较法研究领域亦时隐时现。沈朝晖(2011)曾在《流行的误解:“注册制”与“核准制”辨析》一文中引用法国学者马太·杜甘的话说:“二分法将一切都简化了……它忽略了将此分类与彼分类联系起来的概念轴。除了非此即彼之外,它没有提供其他任何可能性”。在公开发行证券制度方面,当下流行着美国注册制与我国核准制之争议。讨论中尽管不乏严谨的比较法研究和系统性探讨,典型的如包括沈朝晖的《流行的误解:注册制与核准制辨析》,郑彧的《论证券发行监管的改革路径——兼论注册制的争论、困境及制度设计》,黄明、徐芳、阎开的《境外主要市场发行与上市监管中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分工》,付彦、邓子欣的《浅论深化我国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法制路径——以注册制与核准制之辨析为视角》,陈岱松的《论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等等,在此挂一漏万。但也有的观点将问题简单化、对立化。糟糕的是,对立化的思维和论断似乎比严谨分析更吸引眼球、更令人印象深刻。
事实上,无论核准制还是注册制远非其字面含义那样泾渭分明、壁垒森严,两者的历史渊源与动态发展存在诸多交集和融合。例如两者都是由监管机构进行严格、细致的审核,都是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作为基本原则,而信息披露审核的重点,又都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信息——持续盈利能力及相应的风险揭示。美国所谓“注册制”,渊源于在1933年证券法对公开发行证券的注册或豁免要求,而各州证券法下的监管,在此之前及之后仍独立自行其是,有的实行核准制,有的为注册制。尽管全国性公开证券发行适用于联邦证券法的注册制,但发行后的上市申请,须由美国各大证券交易所进行实质审核。另外,在美国之外的发达市场,欧洲大陆、我国香港地区以及2000年以来的英国都实行核准制。不同历史、地理、文化、法制的差异又决定了核准制谱系下不同的特征。但惟其一点,在不同历史地理、文化法制、经济政治的路径差异下,全球各主要市场发展而成色彩斑斓的多元化制度特征,既吸收融合,亦独树一帜,但绝非阵营对立的水火不容,也非妄自菲薄的崇洋媚外。
(二)“抄袭美国”的新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我们常常使用“我们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成熟市场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来表述概括。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证券市场不是由市场自下而上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地发展而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依靠制度移植迅速完成了立法和监管的建章立制、市场和产品的开疆拓土。尤其在技术性制度层面,如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制度、上市规则和交易规则、证券发行审核程序、新证券品种设计等,走过了一条不断重复的制度移植之路。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各种制度和配套措施基本形成。进一步的改革发展,比较和借鉴美国制度规则仍然有益但重要性已大大降低,深层次的改革更需要立足于经济和市场发展程度、法律体系、社会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的国情思维。然而遗憾的是,在学术研究和立法层面上,对美国制度简单移植的倾向依旧严重。对域外经验信手拈来的风气仍然盛行。甚至发展成了新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言必称美国,将美国制度作为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终极方案,将美式经验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
如果放下对美国制度的盲目崇拜,不难发现,在美国市场失灵与监管失败的案例时有发生,说明美国模式本身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注册制更未必是证券发行市场的理想王国。注册制的固有缺陷是过分依赖有效证券市场理论、经济人理性和信息有效传导机制,但这些理论假设和运行机制被证实并非坚实可靠。另外,较低的准入门槛和事前监管的缺位会放任质量较差的企业进入证券市场,占用市场资源的同时还可能加大证券市场投机。
值得寻味的是,我国香港市场近期也出现了是否效法美国经验之争议。近期香港联交所总裁李小加的一段评议,虽起因于阿里巴巴上市的“同股不同权”规则,但背后的逻辑和理念可资借鉴:
“美国的多层股权制之所以运行良好,是因为他们以披露为主的市场机制,与身经百战经验老到的机构投资者和一究到底的集体诉讼文化组合在一起,这些全都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可抗衡同股不同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香港要学习的话,必须有足够的配套组合,既赋予创办人足够的动力,又确保他们诚实可信。如果你问我的意见的话,我认为循序渐进的改变要好过全盘复制美国的制度。”
(三)“碎片化”研究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中国证券市场的立法研究和政策建议一直存在“碎片化”现象。对此,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陈洁(2013)做过精彩的分析:“我国证券法学研究中尽管不乏针对某一具体制度或某一程序环节而进行的技术性的针对性研究,但整体上缺乏根据证券市场的应有建构理念确定证券法的应有功能,根据其应有功能确定其制度结构的体系性的建构性研究。”他指出,“在许多本土性的问题还远没有厘清的情形下,域外各种观念和知识经验的借鉴就纷至沓来。这种碎片化研究的繁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证券市场上的许多重要问题还没有在本土化的意义上进行有效提炼和思考的现实。”虽然此评论是针对证券法学研究,但对更广泛的证券市场立法和监管领域同样适用。
在证券发行体制方面的碎片化研究,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对美国注册制的讨论限于对美国证监会“仅进行信息披露的审核,不设置发行的实质条件也无权否决企业发行申请”的理解,而缺乏对美国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的“双重审核”机制的系统性认识,看不到完整意义上的注册制,是美国证监会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形式审核与各交易所设置上市条件并实质审核相互分工、配合的有机整体。
另外,如果稍稍将视角转移至美国之外,就会发现即使成熟市场也存在其他形态各异的审核模式,例如在英国,证券发行由上市监管局进行形式审核,证券上市则由上市监管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分别进行实质审核;在我国香港地区,证监会、联交所对发行、上市都要进行形式审核和实质审核。世界各地监管模式色彩斑斓的谱系背后的逻辑,是在不同的政治法律、历史文化甚至地理环境中市场和机构长期反复博弈和优胜劣汰的漫长演化过程。因此在比较研究中,除非鸟瞰一个制度的全貌及其发展而来的历史,任何碎片化的“抓拍”和片段式的“截图”,只能是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产生盲人摸象般的结论。
(四)崇拜“先进性”、忘记“适应性”的邯郸学步
不久前,前任深圳证券监管局局长张云东在上海证券报发表“中国资本市场省思”一文,在谈到“先进性”与“适用性”的辩证关系时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该文提到德国的经济学派“坚持强调历史特性和文化特性的重要性,强调任何先进的理论均具有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下,其理论与实际状况高度吻合才是有效的和正确的。任何情况下,适用性都比先进性重要,脱离时空特性现实的‘先进性’,就是南橘北枳,总是在不断地制造‘落后’。”“正是德国经济学家的哲学修养与定力,才创造出了指导德国在古老的欧洲焕发青春一枝独秀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美国证券市场在百年博弈和反复试错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和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包括较完备的信用制度、较强的市场主体约束机制、健全的权利救济制度、占主导地位的机构投资者队伍、通畅的退市渠道等,这些都是注册制存在的制度性根基,需要经济、法律、文化等深层面的积淀和构建,绝非能够“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走过其百年历程”。美国模式在中国的适应性存在重大的疑问。
首先,在诚信文化与市场约束方面,我国2013年上半年进行IPO在审企业财务专项核查表明,拟上市公司会计薄弱、内控不力、信披质量不过关的现象仍比较突出,中介机构未恪守执业规则和未履行谨慎义务的问题时有发生,甚至个别企业财务造假、欺诈上市情节严重,触目惊心。2011年以来,海外上市“中概股”频频遭遇做空机构的阻击,其主要问题点和突破口也是财务造假。由此看来,中国证券市场诚信文化和市场约束机制的建立健全,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第二,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引导功能方面。英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较为分散的股权结构,机构投资者能够发挥外部治理的积极作用。但在中国公司股权相对集中的条件下,尤其是股权集中于国有集团或民营创一代企业家手中,期待中国的公、私募基金履行股东积极主义如何可行?能够观察到的更多情况是,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维持良好的“关系”,即使不为获得内幕信息或者串通炒作题材,也至少在实地调研中不被冷落靠边。在这种关系架构下,试图通过机构投资者的“积极主义”行为改善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三,注册制在准入环节的宽松,需要通畅、便利的退市制度作为配套互补,形成“宽进宽出”、“大进大出”的市场机制。以美国两大交易所为例。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家数在上世纪末最高峰期不过3025家(1999年底),纳斯达克最高曾达5556家(1996年底),随后逐渐减少,在2006年、2007年大牛市之后渐渐稳定在分别有2000余家上市公司的水平,且保持了IPO增量与退市家数大致相抵的状况。我国证券市场短短22年积累了将近2500家上市公司,平均每年退市数量则寥寥无几,近年更是降至2至5家左右。中国市场的交易结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与美国市场完全不同:证券市场交易以个人投资者尤其是散户交易为主,股权结构以国有集团控股或民营实际控制人控股为特征,公司治理方面呈现与行政治理的“混搭”状态,这些特征都决定了“直通车”型的退市制度尚不可行。
另外,美国证券市场依赖无处不在的民事诉讼和无孔不入的律师群体,集团诉讼制度、做空机制及民事和解制度等则是其制度基础。在中国引入上述制度存在若干现实困难。注册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事后的救济、惩戒,来弥补和取代事前审核与事中检查的缺位,这种制度模式在中国尚需谨慎。
(五)“局部性”改革的牵一发而动全身
经过十余年核准制的实施与持续改进,监管机构在证券发行信息披露、证券发行审核流程和审核人员配置、询价与承销制度、上市规则等技术性、程序性制度方面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改进,时至今日与美国的做法已基本趋同或大同小异。但涉及发行监管体制的深层次变革,再度依赖单兵突进、逐个击破式的改革已经无济于事,甚至会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预料不及的后果。
以证券发行市场“三高”问题的出现与治理为例。对于发行环节的市场化改革,在2001年实行核准制初期就有所尝试。2001年4月核准制下首只新股——用友软件发行价格(36.68元)、发行市盈率(64.35)和首日开盘价(75元)引起各界极大的批评。不久后,证监会对发行价回归行政管制。随后中国股市进入漫漫熊市,第一波市场化改革的高发行价、高市盈率和高募集资金问题偃旗息鼓。2009年下半年随着主板、中小板重启和创业板诞生,推出的第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宣布放开发行定价限制,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市场“三高”现象再次上演。(以创业板为例,2009-2011年发行市盈率分别高达62倍,70倍,48倍;超募比例分别达到163.8%,236.49%,142.4%。)
两次“三高”问题,都发生在前端市场企业排队上市,后端市场资金面宽裕的市场环境中,而核准制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节奏控制和质检通道的作用。在“两头市场供需两旺,中间控制发行质量和节奏”的运行机理下,放开发行价管制必然“三高”顺势而起。
在各种压力下,监管机构对某些敏感股票的发行规模和价格进行了直接或间接“指导”。201 2年下半年上市的洛阳钼业、浙江世宝在发行价、发行规模、募集资金量连创“三低”,效果虽立竿见影,但难免行政干预的“痕迹”。另一个负面效应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三低”个股在上市首日即遭遇以散户为主的打新资金狂炒。
对证券发行市场改革的几点认识
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势不可挡,关键是实现什么样的市场化和如何进行市场化。
(一)走基于国情意识与本土问题意识的市场化道路
论及市场化,有关观点似乎不加思索地将“美国化”等同于市场化。跳出这个思维惯性,我们需要思考究竟要以美国为样板的市场化,还是走出一条基于国情、解决本土问题的市场化道路,这是摆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面前的首要课题。
应该看到,在放任自流哲学大行其道的美国,近年来其依赖市场更新淘汰、修复自愈的机制也在面临挑战和反思。无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2003年安然等系列会计丑闻,2008至今仍余震不断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些都一次次表明,在系统性风险的连锁反应、恐慌性心理“自我实现的预言”和会计与监管标准“顺周期”的助推下,一切事后的救济、修复和惩戒措施都显得苍白无力。美国是否真的具备其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所鼓吹的那种“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的弹性,那种化解混乱及迅速修复的能力”,以及这种“弹性”是否像资金、技术一样引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无从证实的命题。中国的市场化模式若以美国为圭臬,当慎思而行。
市场化改革亟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在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尚存缺失、市场主体约束机制尚欠完备,权利救济制度尚未健全、退出渠道尚不通畅的现实环境中,加强监管执法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监管转型的“着力点”。正如证监会主席肖钢今年8月在《求是》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的,要扭转“重审批、轻监管”倾向,将证监会的“主营业务”从审核审批向监管执法转型,将“运营重心”从事前把关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这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改革路径的唯一选择。
(二)实现市场化的过程须循序渐进、统筹兼顾、标本兼治
首先是市场化进程的速度把握。市场化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过程。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市场化既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发演变,也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步到位。市场化的步骤、次序与进程应与中国资本市场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套,保持市场化进程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契合和协调。保守不前与急功冒进对市场都是一种伤害。
其次是市场化进程中各种关系的把握。证券发行市场诸多因素存在矛盾统一、相互制约、因果联动的关系,包括发行市场的停开与二级市场的涨跌,发行前端的“堰塞湖”问题与发行后端的“三高”问题,淡化实质判断、弱化事前审批审核与防范和识别财务造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高透明度与增加上市成本,审核标准化与迎合监管,等等。在证券市场的深层次区域,上述关系的处理已不能依靠单兵突进或者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应秉持“魔鬼在于细节”的态度,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具备“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技巧,统筹兼顾、瞻前顾后、标本兼治。
最后是市场化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持证券发行机制的正常运转是保证市场生态系统吐故纳新、推陈出新的前提和基础。当前首务是恢复证券市场新股发行的“造血”、“输血”功能,在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市场化、法制化改革,并建立改革的反馈和修正机制,根据市场状况适时、适当地调整和掌握改革的力度、速度和市场的可承受度。
(三)对待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态度:保持思想和行动的独立
来自专家学者、市场主体和媒体等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议论与争论、评价与批评,伴随着证券市场发展与改革的全部进程,并起到推动、反馈、监督等诸多积极作用。但在建言献策当中,各种思潮混杂复合,各种利益碰撞叠加,各种诉求纷繁嘈杂,对此,立法者、监管者、研究者须保持独立的思考、判断与行动。
首先,专家学者的长项是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训练有素的分析方法,但除非对国外成熟市场近百年来制度变迁至今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除非对市场和监管一线具有深入、真实和全面的了解和感受,否则“盲人摸象”的片面认识、言必称希腊的态度、碎片化的改革方案、隔靴搔痒的政策建议的有用性必然大打折扣。第二,对于市场各主体,应认识到博弈各方存在复杂的利益诉求取向差异与冲突。例如,即使投资者作为一个重要市场主体,其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至少存在投资未上市企业的VC/PE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等诸多差异。市场任何环节、任何层面的改革不免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重组和分配,必须充分考虑各方诉求差异、意见相左的状态下,各类意见建议的客观性和代表性。最后,媒体充当着“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这一论断最有力的诠释,在质疑和揭露财务造假、维护弱势股东权益、促进透明度提升等方面功不可没、不可替代,但也有部分媒体不时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冲动,甚至少数媒体人存在索取“有偿沉默”或沦为某方面利益代言人的驱动。
所幸的是,立法者、监管者及居于主流的研究者始终保持了对国情和文化的清醒认识,坚持了用历史的、动态的眼光看待问题,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发展道路,包括监管体制的设计(如保荐制度、发审委制度、稽查的查审分离制度等)、重大改革方案的实施(如股权分置改革、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等)、重大创新的推行(如中介机构分类监管、并购重组的“分道制”审核等)、重大风险的处置和防范措施(如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地方交易所清理整顿、IPO财务专项核查等),等等,时时闪烁出实事求是的哲学底蕴和监管智慧。
证券市场进一步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仍需立法者、监管者和研究者秉承保护投资者的长远利益、维护市场三公原则、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原则,厘清市场与监管的边界,既不越俎代庖,也不无所作为,促进中国证券市场从新兴转轨向成熟发达市场的顺利过渡与成功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排除噪音干扰,摒弃浮躁心态,顶住一时一事的压力,放弃取悦大众的诱惑,保持思想的独立、精神的自信、心态的定力、行动的坚韧,让改革经得起各方的考验,经得住历史的回眸,体现着理性的艺术,闪现出哲学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