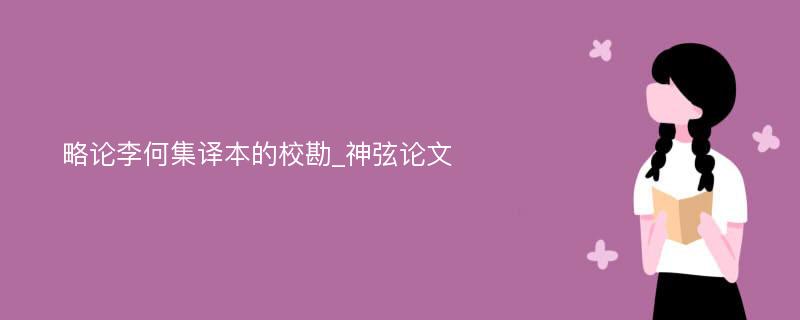
李贺集版本校勘琐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版本论文,李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唐诗人李贺集版本和校勘的研究,古代多散见于各书录题跋,且歧见丛生,很少有较为系统和清晰的说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从历史角度看,李贺集版本传承较为凌乱,唐刻已不可见,宋刻只存宣城本,蜀本两种(蒙古本除外),明清版刻虽多,但多经窜乱,特别是明末书刻,偏嗜割裂,漫改书名,更使人不知其从来。即使是著名的毛氏汲古阁,校勘亦不周详。(注: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卷二云:“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因此,历代研究者对李贺集多抵牾。如吴正子以为“鲍本即宣本”,黄丕烈定赵衍本为金刻,后人已纠之;清丁丙以为明王家瑞本雕印极精,尤振中反之;而尤氏将蒙古本归入京本系统,刘衍又反之等。正如吴慈培所言:“盖自南宋以来,唐人集版刻独夥,又不尽守旧来面目,后之人欲溯流寻源,亦甚难矣。”(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藏汲古阁本吴慈培跋。)
其二,从研究角度看,李贺集的校勘学与版本学的研究也极为麻烦。这一方面因为李贺诗歌用字奇特,出人意料,不同版本文字上的差异常使人们各置一词。另一方面,校勘古籍时由于校勘者为知识所限,容易产生误差。如上面所举黄丕烈校定的金刊本即是一例。
正因为如此,笔者数年来潜心于李贺集之“陈氏本”与“书棚本”的校勘比较,略有所得,今择其要者录出,甚望于李贺集版本校勘有所裨益也。
在李贺集所有的版本中,“临安陈氏本”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版本。
历史上有关它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
毛晋《汲古阁书跋》云:“……继获临安陈氏本,如《勉爱行》二首离为三首,《神弦别曲》、《神弦曲》、《神弦》三处合编一处,诠次倒颠。又如‘空白凝云遏不流’,误作‘空山凝云’,‘杜若已老兰苕春’误作‘茧苕春’,‘泣露娇啼色’误作‘帝色’,‘向壁印狐踪’误作‘孤踪’云云,一一厘正。既而复见鲍钦止手定本,无论《白门前,大楼喜》一篇得未曾有。如‘碧玉破不复’陈本作‘破瓜后’,‘柳脸半眠丞相树’陈本作‘柳阴’之类,虽同是宋版,不啻泾渭之迥别。第《摩多楼子》作‘栖子’,‘试伴汉家君’作‘汉家书’,此又鲍本白璧微瑕矣。”
清代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李贺歌诗编》四卷终有:“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
吴焯《绣谷亭薰习录》著录复古堂《李贺歌诗编》时认为其“遵宋临安陈氏书坊旧本”翻雕。
吴慈培校跋汲古阁本(北京图书馆藏)云:“按《读书敏求记》记载,歌诗编四卷外诗一卷,鲍钦止家本,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行。瞿氏藏书志影宋抄书棚本亦有外诗,外诗出于鲍钦止家,则临安陈氏本即鲍钦止本无可疑者。子晋跋以陈本别于鲍本,误矣。”
缪荃荪校跋汲古阁本(社科院文学所藏)曰:“壬子正月六日假陆勅先校南宋本过,即陈解元本也。”
以上记载中分别出现了“陈宅经籍铺印”、“临安陈氏本”、“陈解元本”等字样。研究者一般将它们视为同一种版本。但正是这一看似没有问题的认识,却造成了李贺集版本上的诸多不解:如果以上所说的陈氏本是同一种版本的话,为什么毛晋以为鲍本与陈本有别,而吴慈培却认为鲍本即陈本呢?即使真如吴慈培所说是毛氏之误,那么同是遵陈氏本翻刻的复古堂本为什么与其它陈氏本又大相径庭呢?看来,简单将所有陈氏本划归于一的做法是大有疑问的。
从李贺集版本演变的实际情况看,当时雕刻于临安的陈氏李贺集刻本绝非只有一种。“临安陈氏本”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陈解元本”或“陈宅经籍铺本”。
随着宋室南渡,临安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事业日趋兴盛,城内书坊林立,仅陈氏书铺较著名的就有四家。它们是:
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又称临安府棚前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
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解元书籍铺,又称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书籍铺、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解元书籍铺。
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
临安府鞔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
据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记载,陈道人名起,字宗之,于睦亲坊卖书开肆,名芸居楼。他在刊刻唐宋诗方面功绩卓著,所刻书字秀纸佳,版本精良,后世视为珍品。陈解元号继芸,潘著以为即陈起之子陈思,并指出:“称陈解元书籍铺经籍铺者,属之起之子续芸,单称陈道人、陈宅书籍铺经籍铺者属之起。”(注: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台湾学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13—215页。)而据南宋周淙的《乾道临安志》,知南棚巷、中棚巷,均在睦亲坊附近,故后世将陈起、陈思所刻俱称为“书棚本”(注:参看施廷镛著《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台湾学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13—215页。)。为了区别,这里我们将其他陈氏所刻名之曰“陈氏本”。“书棚本”和“陈氏本”都不排除刻印李贺诗集的可能性。这点,我们可以通过李贺集版本之间的相互比较进行印证。
本文前面曾引用了历史上与临安陈氏本(包括书棚本)相关的几条记载。据毛晋、钱曾、吴焯、吴慈培等人之论,可知与临安陈氏本相牵涉的本子有元复古堂本,明毛晋所见陈氏本,清述古堂影宋本,缪荃荪借校之南宋本。其中后两种明言是睦亲坊或陈解元本,此是书棚本无疑。缪之借校本无由得见,但笔者曾就其所校出异文(与汲古阁本相校)与述古堂本初步对校,文字多同且与他本有异,如“蜀桐”(《李凭箜篌引》)、“箱中”(《罗浮山人与葛篇》),不同于汲古阁本之“蜀琴”、“湘中”;“弦声浅”(《后园凿井歌》)不同于汲古阁本、宣城本之“丝声浅”等,且外集俱少《白门前》,可定其至少出自同一底本。述古堂本钱曾又云其是“鲍钦止家本”(注:《读书敏求记》卷四。)。毛晋汲古阁本亦据鲍本校刊(毛本卷终刊有鲍钦止书一则),今两本核对,大体相合,可证俱是以鲍本为底本也。那么毛晋所见陈氏本是怎么回事呢?很显然,它与述古堂所影书棚本不是一回事。其文字既与鲍本有较大差异,自然和以鲍本为底本的陈氏书棚本不可能同是一种印本了。当是临安其他陈氏所刻的李贺诗集。
那么是否如吴慈培所言是毛晋之误呢?也不是。吴焯曾言元复古堂本遵临安陈氏旧本翻刻,今据复古堂之翻刻本《锦囊集》,对照毛晋所云陈氏本特征,基本吻合,可证别于书棚本的另一种陈氏本是存在的。吴慈培云:“临安陈氏本即鲍钦止本无可疑者。子晋跋以陈本别于鲍本,误矣。”此言错在没有弄清陈氏书棚本与其他“陈氏本”的区别,即他所说的陈氏本实际上是陈氏“书棚本”,和毛晋所说的“陈氏本”是两种不同的版刻。
考辨临安陈氏本在李贺集版本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弄清李贺集在后世的流承很有帮助。
明代曾出现了多种李贺集刻本,除毛晋本(鲍本系统)、刘辰翁评本、凌驎初本(吴正子本系统)外,还有许多种版本扑朔迷离,难溯其源。如马炳然本、刘廷瓒本、徐董合评要本、于嘉本、曾益本等,一般研究者对其源流所知不甚了了,少有考证之文。尤振中将之大都归于吴正子笺刘辰翁评本的分支(注:尤振中:《李贺集版本考(初稿)》,《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实际上其中不少应归于“陈氏本”名下。
毛晋《汲古阁书跋》中共列举了所见陈氏本十一处特征(与鲍本相较而言)。即:(1)《勉爱行》二首离为三首,(2)《神弦别曲》、《神弦曲》、《神弦》三处合编一处,(3)外集无《白门前》; (以上篇目次序方面)(4)“空白凝云遏不流”作“空山凝云”,(5)“向壁印狐踪”作“孤踪”,(6)“泣露娇啼色”作“帝色”,(7)“摩多栖子”作“楼子”,(8 )“试伴汉家书”作“汉字君”(“栖”、“书”两处汲古阁校刻时已改从陈本),(9 )“杜若已老兰苕春”作“茧苕春”,(10)“柳脸半眠丞相树”作“柳阴”,(11)“碧玉破不复”作“破瓜后”。(以上文字方面)以此特征来校明本,半数以上相符者有:
明刻《李长吉诗集》(黄丕烈校跋本)三册:(6)、(9)、(10)、(11)四处不符,余同。(《勉爱行》此集目录题《勉爱行》,卷内正文题《勉爱行二首》,但内容离为三首。)
马炳然《锦囊集》:(1)、(9)、(10)、(11)四处不符,余同。
明刻《李长吉诗集》(傅增湘题款本)二册:(9)、(10)、 (11)不符,余同。(此集无目录,多《静女春曙曲》、《少年乐》两篇,《勉爱行》卷内正文题为《勉爱行二首》,内容离为三首。)
明弘治十五年刘廷瓒刻本:(9)、(10)、(11)不符, 余同(《勉爱行》此集目录题《勉爱行》,卷内正文题《勉爱行二首》,但内容离为三首。)
明抄唐四家诗本第一册《李贺诗集》:(10)、(11)不符,余同。
明万历四十一年刘华峰刻《李长吉诗集》(徐、董批注本)二册:(10)、(11)不符,(《勉爱行》此集目录题《勉爱行二首》,卷内正文题《勉爱行三首》,内容亦离为三首。)
以上六本前五种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后一种社科院文学所收藏,皆多与吴正子、刘辰翁本不同而多与“陈氏本”相同。因此,与其说它们是吴、刘本的流波,倒不如说是渊源于“陈氏本”更为符合实际。反过来,它们的存在,也证实了“陈氏本”在李贺集版本流传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
六种本子中,《锦囊集》载复古堂识云:“定以鲍本而参以诸家”;徐、董批注本坊刻序云:“兹刻依本云是鲍氏。”似乎与我们所作的结论有矛盾,但此话明显大有问题。两本从体例、文字、篇数、篇目次序上,均与鲍本不合,无论如何也不能归于鲍本系统。除非鲍钦止所传不止一种版本,但从历代藏书家的记载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复古堂可能是把“陈氏本”错认为“书棚本”了,因此才会有此语。而“徐董本”人云亦云,于是沿袭了复古堂的错误。徐、董本坊刻序云:“兹刻依本云是鲍氏,然或京、或蜀、或会稽、宣城,总未可知。”可见其对所刻属鲍本系统的说法是有疑问的,不过囿于条件,不知道所刻祖本到底是何种版本罢了。
最后说一说陈氏本与吴正子本的关系。陈、吴本在篇目次序上基本相同,如外集无《白门前》;《神弦别曲》、《神弦曲》、《神弦》三首相连等;但文字多异。如陈本“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太守行》)、“饮水得相宜”(《咏怀其二》)吴本作“向月”、“得自宜”等。吴本自言以京、鲍两本训注,然与汲古阁本次序不同,可见其次序只能依照京本,由此可推,临安陈氏本与吴正子本一样,都与京本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因此属于此系统的“徐董本”坊刻序才在“兹刻依本云是鲍氏”后,又指出“然或京或蜀,总未可知。”大概也是看到了其与鲍本相差太大,却与京、蜀本有某种相似吧。今见之吴本,经刘辰翁点校,文字上已得到整理,讹误较少。复古堂识云:“笺注则得之临川吴西泉,批点则得之须溪先生,”可见当时他是看到过这个点校本的。但是复古堂仍没有吸收吴本的长处,改正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吴本“野田平碧”(《艾如张》)陈本仍作“野山平碧”,“娇啼色”(《南山田中行》)仍作“娇帝色”等。因此,虽然在明代两本的传刻呈分庭抗礼之势,但在以后的流程中,却逐渐形成“吴”胜“陈”汰的局面。陈氏本因错讹过多,而逐渐冷落没有嗣响。吴正子本却倍受青睐,成为许多李贺刻本的依本,直至入选《四库全书》。
“陈氏本”和“吴正子本”,做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已形成自身独有的特色,成为宋代独立于“蜀本”、“姚氏本”、“鲍本”、“京师本”、“宣城本”之外的另两种李贺集版本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