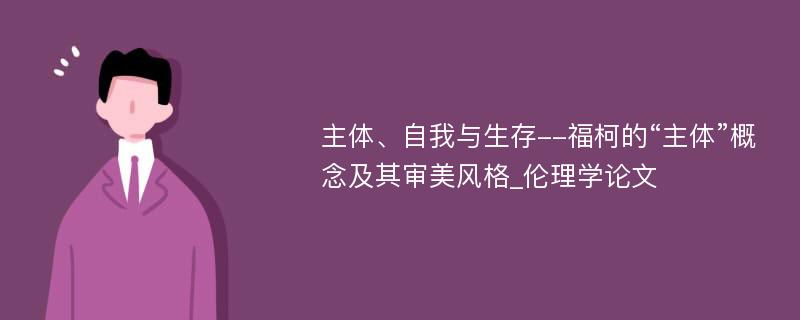
主体、自我与生存——福柯的“主体”观念及其美学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我与论文,观念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3-0035-07
一、主体之死与主体化
传统主体是理性的象征,它代表形而上学。不过在现代社会,“主体已经声名狼藉”。[1]自启蒙运动以来,主体获得了至上权力,然而它也不断遭到质疑。从尼采开始,主体的离心化运动已然兴起,到了福柯、利奥塔那里主体已遭到彻底批判。从哲学方面看,从尼采、海德格尔到列维-斯特劳斯,都对传统主体提出了质疑;而从文学方面看,从马拉美到布朗肖也经历了主体形而上学的断裂。[2]在康德那里,人如何完善自身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在尼采和福柯那里,人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早在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就在其名著《野性的思维》中宣称,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而在《人的终结》(1968)一文中,德里达也写道:“在今天,难以让人们料想的是,人的终结不再是通过真理的辩证法与有目的的否定来组织的,也不再是第一人称复数中的目的论。”[3]大写的人、大写的主体从此被分解,道德、理性或真理将被批判或重新审视。
解构主体是福柯毕生的事业,他“将人类中心论看成是已消失的神话”。[4]在其名著《词与物》(1966)中,福柯宣称人“已消亡”。在该书的结尾,福柯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5]不过这里的“人”并非作为生物的“人”,而是指作为大写的主体之“人”。准确地说,“福柯把人之死看作主体之死,大写的主体之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6]福柯指出,在18世纪末之前人并不存在,人是现代科学和现代知识构成的产物。此后,人逐渐被看作是知识、历史和理性的主体;只是这一主体将随着现代认识模型的崩溃而逐渐消失。当主体的虚构被揭穿后,历史、理性的大厦也就轰然倒塌。福柯所谓“主体的死亡”,“对于言说的我仿佛是一个解放,将之从没有赋予他可以生存之处的构架中解放出来”。[1](6)然而,只有在这一情状下,新的主体才有可能诞生,自由才可能实现。
理性虚设了一种秩序,它将事物、自然和世界都安排在自我意识之内。远古时代的人对自然和世界是敬畏的,而在基督教中,人也不可能获得至上权威。在文艺复兴以前人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和自主,然而现代科学的进展使人逐渐走向对世界和自身的“解蔽”,在此背景下人也终于获得了独一性。“在古典世界中,人始终是处在一个整体的宇宙秩序或存在秩序中,他占据着这一整体之内的特定位置,一个相当崇高的位置;而且他是依据他的自然本性而占据这个位置的,因此,他绝不会僭越自己的位置”。[7]秩序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专制,专制就必须被批判。这是福柯的反叛逻辑,也是一切现代和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路线。当福柯宣布“人已死”时,他首先体验到的是一种自由的快慰:“‘人之死’包含着‘人去死吧’的欢呼和期待”。[8]在福柯看来,主体的真相从未显露,它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在他看来,“现代知识—权力通过主体对现代个体进行奴役,并且这种奴役以真理、科学和理性的面貌出现,从而掩盖了主体被奴役的真相”。[8](185)如此一来,主体的真相就不能被发掘。在主体和理性的权威下,现代人对秩序和整齐划一无比热爱,他们是被秩序、齐一化所束缚的人。不过也正因如此,人在这里慢慢丧失自身。福柯从历史的间断性出发,通过对知识的分析最终发现了主体的“必死性”。在他看来,主体之死是一个必然性事件,但它却出现在偶然的、间断性历史细节中。对他而言,“主体之死”是真实和自由之“人”回返的前提。当福柯指出这一点时,他实际指出了一条自我建构之路。
宣布主体死亡是一件容易的事,问题是之后怎么办。当弗洛伊德说“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时,这句话本身就让人感到无辜和绝望。知识、权力是福柯解构主体的策略,然而它也是建构新主体的可能性起点。准确地说,“通过反思现代性哲学话语,福柯注意到的是实存与知识、主体与概念之间的张力。具体地说,福柯关心的是经验、知识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涉及的是主体如何诞生的问题。”[9]当然,早期福柯尚未真正进入这一主题,不过他已从文学艺术等“外部空间”里发现主体诞生的可能。基于“外部思想”,福柯发现“主体化之线”。德勒兹指出:“福柯发现了主体化之线。……主体化之线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逃离线,它逃离了先前的线,也逃离了自身。”[10]那么,一个新的自我和主体即将生成;然而这些都是凭借“域外”之力才得以实现的。福柯不断用“外边的思想”冲击旧主体,当它被彻底解构之后,一个新的自由主体将慢慢浮现。
新主体不是要成为至上主体,它只是不断地关心自己、自由生存。真正的自由将体现在主体的审美化生存之中,它关心的是当下、直觉和经验。福柯认为,没有所谓至高无上的、无处不在的和作为基础的普遍主体。恰恰相反,主体是实践的、自由的和自在的“个体”。在福柯看来,知识、话语和权力并不能建构真正自由的主体,惟有在生存实践中它才可能出现。主体不是先验和绝对的,也不是至上与不可动摇的,它是始终处在运动之中的经验性主体。对福柯而言,“主体不是经验的可能性条件,而是经验的结果”。[11]同时,“‘主体’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主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治于他人,也可能由于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12]主体是历史和经验的产物,它的位置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之下将会出现不同的面向和特点。因之,“主体的位置也同样是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13]在福柯看来,主体实际经历了一系列自我的构成环节,也经历了一系列逐渐瓦解的步骤。在福柯眼中,“主体是一个意识形态产物,一个话语的功能原则,而非话语的优先起源”。[14]他的工作就是驱除对主体的迷信,同时将主体从意识、话语和权力中解救出来。因此可以说,福柯对主体的批判早已暗含主体建构之目的。
在福柯看来,主体化是主体建构过程,也是自由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不断回返真实、反省自身:“主体化意味着能够反省自身所要达成之真理的历史性”。[15]当然,大写的“主体”也将在此丧失自明性、至上性和绝对威权。主体化就是对自由主体的构建,也是对真实自我的关切。主体化之线需要逃离理性与旧主体的陷阱,它要在越界中寻找生存、寻找自由的秘密。事实上,“外部”暗自契合了这一需要:外部既是解构主体的空间,也是建构自我的场所。如果说布朗肖是通过奔向“外部”来寻求存在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就是通过折向自身、折向内在来寻觅存在的。问题在于,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脱离意识哲学,他只是避开大写的主体而已。由是观之,福柯的新主体才是真正解放和自由的主体,他拒绝的是那种大写的、理性的主体。在他看来,这一“主体”实际遮蔽西方哲学几千年,也压制无数“沉默的”声音和事物。尤其是,这种主体过于自信,以至不能发现自己早已面临深渊:“福柯在《词与物》中谈论‘人之死’,其实死去的是先验主体和意识主体,诞生的是实证主体和历史主体”。[16]
二、自我的技艺
谈论自由,就是谈论生存。生存的前提是生命的存在,而理解生命就是直面死亡。海德格尔认为,我们要自由地面对死亡;而福柯则认为,“如果有意识地去考虑自己生命的终结会使主体具有自律性”。[17]福柯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极端的外部经验,然而这一经验却又是内在的。S·方迪指出:“正像生命冲动离不开死亡冲动一样,生命与死亡紧密相连……生命的每一个表现都是来自死亡并趋向死亡的运动,而死亡本身又是通向生命的跳板。”[18]从这一角度来说,海德格尔的死亡观是极其重要的。虽然海氏是基于此在生存的角度来谈死亡的,但他毕竟看到了死对于生的意义。与前者不同,福柯对死亡本身情有独钟,他甚至要体验死亡。在一定意义上,他“将部分死亡复数化,将死亡变为一种与生命共存的力量”。[19]通过医学话语空间的分析,福柯发现死亡不可怕,它是生命的抒情:“死亡离开了古老的悲剧天堂,变成了人类抒情的核心:他的不可见的真理,他的不可见的秘密”。[20]死亡传达了生之秘密,也指证了自由的岁月留痕。对福柯来说,从19世纪之后,死亡不再是一种普遍、整体、残酷与面目模糊的猝然断裂之点,也不再是生命的对立或破坏;相反,死亡成为构成生命最独特也最差异的核心。[21]生命的差异就在于死亡,而生命的意义也就在于“向死而生”或“向死而在”。在福柯看来,生命是一件自我建构的艺术品。在这件作品中,我们必须敢于面对死亡,从而才能实现自由生存:“如果生命如同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必然是由‘存在在死亡中所取得的怪异积体’所标志,其铭刻着无数充满个体意味的独特病态,且每种病态都是每具肉体上充满差异性的微死亡之重复”。[21](165)
由死亡开始,福柯开始了他对生命的关切;他“特别注目于一种‘生命的权力’,从而将他的权力批判转化为一种生存美学的构想”。[22]生命权力是一种政治权力,是生存的权力,它是伦理性的。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现实生存,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言行、思想都有不可预知性,因此必须将自由与自我联系起来。自由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切实的话语和思想行动。自由是生命的直觉,是伦理的实践。为此,福柯提出“关心自己”的伦理学。在福柯看来,“自我的关切是为了抵抗规范化技术的,所谓的规范化指的是那些监督和调控身心并因此造成人之驯良的权力模式及其相应的自我之实践”。[14](310)这一伦理学首先是抵抗那种对生命权力的践踏之行为,抵抗那些规训的行为。“关心自己”就是回到原初的自由和生命本身,那么福柯的“伦理学”就是思想实践。也正是因为这样,“福柯断言,伦理的自由是必须付诸实践的,他把伦理学定义为‘自由的思想实践’”。[23]
当然,“关心自己”的伦理学是从“身体”开始的。对福柯来说,每个人的现实基础都是“我说”(I speak)而不是“我思”(I think)。换言之,当下的自我生存才是关键。意识哲学将“我说”移向“我思”,反映了人从界内向界外的位移——即人对现实的突围。[24]问题在于,这一转移彻底抛弃了感性和身体,从而也使人不再“关心自己”。事实上,“人类文明就是通过对自身行为的训练开始的,‘自我的技术’和‘自我的教化’,是文化的起源”;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说“福柯开始转向个人的伦理学”。[25]由此可见,福柯的伦理学不是传统意义的伦理学,它指的是个人的生命伦理学。同时,它也是“身体学”,一种自由的身体实践哲学。这种“伦理学”是强调“关心自己”的伦理化实践,也是极具审美化的自由生存实践。对福柯来说,“关心自己”意味着回到自身,回到真实的生活:“关心自己是一种刺激,应该被置入人体内,放入人的生存中,它是一种行动原则,一种活动原则,一种在生存过程中不断担忧的原则”。[26]这就意味着,现代人只是在“认识自己”,而并非“关心自己”。“关心自己”在福柯看来是一种实践性的行为和活动,甚至也是一门艺术。
“关心自己”是自由的伦理实践,是个体化行为,也是新主体之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得以激发和生成。不过,自我却是含混而多元的概念:它既是内在的,又是外显的;既与理性相关,又与非理性密切相连;既是经验的,又是实证的。作为个体,自我自由而自在。但作为主体,自我却囿于伦理和道德实践。故自我需要破除偏见、改变观念,需要调整姿态和立场,也需要从他人与世界那里获得应答和回声。只有通过曲折和迂回的策略,自我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完成自我塑造。换言之,自我构建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关心自己”就是关心生命本身,就是将生命当作生存的本质。自我的技术就是对生命的塑造,也是生存的技艺。具体而言,“福柯关注的是对生命的策划,这种策划相当于一种艺术和技术;福柯称它们为‘生存的艺术’或‘自我的技艺’”。[27]这种生存的技术,也是福柯重新创造自我的策略和路径:“福柯的‘生存美学’基于个体与自我的关系,这里的‘自我’不是现代哲学中理性‘自我’,而是具体的、实践中的、不可替代的‘自我’”。[11](154)同时,福柯还认识到,“关心自己包含有改变他的注意力的意思,而且把注意力由外转向‘内’”。[26](10)这就意味着,福柯开始从外在问题开始转向了“自我”的构建之上了。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人是被动的、消极的,是无法认识自我的。即便在日常生存行为中,“人”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叶扁舟。因而在那时,“认知自己”是最为迫切的任务。不过,古代人所宣称的“认识自己”既是一种渴望和想象,也是一种虚幻和梦想。在古希腊哲学中,世界的无限和不可知性决定了人的有限性。此后,基督教“上帝”的存在预设了其无限、神圣和不可把握……那么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渴望发现和认识自我,渴望获得真正自由和无限的空间。然而当人真正将自己确立为主体、确立为世界的核心之后,他却发现“自我”才是真正需要关心的。
在福柯眼中,自我是实践性的、具体的与可操作的。斯多葛派强调“苦行”,强调自我控制、自我修养和自我塑造,而古罗马人也强调自我修炼的技艺。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日常生存实践中从自身做起,关注自己,培养和塑造自我。为此,福柯说我们需要将自己创造为艺术品。其实,他是想使我们重新关注自身、他人和世界,进而创造新的自我和生存方式。在他看来,“关心自己”就是要正确地生活、自由地生活。当然,“自我的技术”在中世纪是指一种自我塑造的技术,一种“自由的艺术”。不过在当时,“自由的艺术”指的是一些“自我训练”的方式或学问。这种“自由的艺术”有七种:“逻辑、修辞学、文法、算术、几何、天文学以及音乐(包含音响学)”。[28]在今天看来,这些所谓“艺术”其实都是“科学”;但在当时,这些都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艺术”。如此说来,“关心自己”乃是一种宽泛意义的“自由的艺术”。当然,福柯的“关心自己”并非要形成一种规范化的道德理论,也不是要重新回到理性(主体)中心主义。毋宁说,它指的是要使自我“艺术化”。自我的技艺就是自我的艺术化,就是自由的生存。福柯提请人们注意:必须要从自我出发;要像古典的生存那样,我们需要回到生存的原初状态。
三、直觉与自由生存
作为尼采主义者,尼采的一切都让福柯着迷,尼采对主体的批判更使其如醍醐灌顶。沿着尼采的思路,福柯将“主体”思考为人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对自己的艺术构造。[29]在他看来,惟有从当下自身出发,我们才能实现自由的生存。“自我”由此所获得的不再是对外在性的偏执追求,而是对自我技艺和生存自由的迷恋。其实晚期福柯对“性”的解读,恰如其分地表明自我的内在自由性。虽然福柯也将“性”史看成是被压抑的历史,但“压制”的反叛已经不再是重点。晚期福柯真正关注的是如何实现“自我”,如何让生命得以更好实现。自我是内在的,但它也是指向外界的。二者的相互纠缠,不仅实现了主体化,也使福柯看到了自由的曙光。因之,“一旦把内在性从自身中引诱出来,一种外界就会清空这个内在性通常隐退的地方,并剥夺内在性退隐的可能性”。[30]文学、艺术是激发自我内在性的最佳路径,也是逼近自由生存的完美的实践场所。这就是说,福柯在早期作品中已经暗含回归“自我”的设想。列维纳斯说:“自我即内在性。在世之自我有着一个内部和一个外部。”[31]如此说来,自我必然需要被关注,不过福柯在那时并没有切实把握到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历史分析,还是文学解读,福柯都贯彻了尼采作为方法的“直觉”。换言之,“直觉”使福柯发现了理性背后的沉默声音。而在后期哲学中,福柯已将直觉深深印在每一言说中。当然,这里的“直觉”并非是指一种具体的心理能力;毋宁说,它指的是一种感性的本能、冲动或生命的激情。
“直觉”是尼采的根本方法。凭借“直觉”,尼采嘲笑和批判主体、理性和形而上学,也塑造了新的“自我”——“超人”。尼采并不是要通过直觉重回理性和道德,而是要走出一条新道路。实际上直到最后,尼采始终“以一个最坚定的非道德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面目出现”。[32]但是,尼采并非反道德主义者;他是一个提倡新道德的“道德主义者”。因为,“感动着尼采的并非形而上的冲动,而是道德主义的冲动,他目之所及不是存在的本质,而是人的心灵的存在和应然”。[33]关键是,这是尼采从本能和直觉那里获得的直接判断。这一判断给尼采无限的自由,也给尼采无限的激情。尼采从古希腊那里寻找资源,希望揭示人的本真生存,也希望到达真正的自由和真理。不过尼采最终没能穿越时间与历史的界限,将人从经验和工具的自我中解放出来或逃遁。对福柯来说,传统哲学不能提供解决方案,但现象学也不能切中肯綮地设想策略。旧哲学的任何努力要么是重新回到理性的那一边,要么是对破碎主体进行小修小补。因之,“现代人不是要去发现他的自我、他的秘密、隐藏的真理,而是要去发明他的自我、创造自我”。[34]
晚期福柯关注“自我”,走向“内在”,既反映了他所谓“伦理学”转向,也是其思想的必然结果。在主体被彻底解构之后,福柯需要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主体。当福柯最终从感觉、直觉走向内在的“自我”之时,实际他已将“自我”看作是新“主体”了。福柯说:“围绕着自我关注,所有的说话和写作活动都得到了发展,其中自我对自我的工作是和与其他人的交流联系在一起的。”[35]言下之意,通过“关心自己”,主体实现重构,而它也最终成为走向他人、走向世界的自由主体。进而言之,“关切自身必须得到他人的帮助,因此,与自身的关系也就是与他人的关系”。[6](249)如此说来,福柯对“自我”的主体化就是主体的塑造,就是弥合主客二分的途径。“关心自己”是伦理生存的思想,其主要特征就是自我创造。对福柯而言,人没有固定的本质,每个自我从束缚中解脱之时,也面临自我创造的重任。[11](176)自我创造既是一种抵抗、反叛,也是一种自由、开拓或越界的思想和行为。
就这样,福柯走向一种特殊的“伦理学”。福柯说:“这种伦理学的主要目的是美学目的,它主要是个人选择问题。”[36]这是一种“泛审美”,亦即审美化或审美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福柯的自我伦理学仅仅反映“内化”,它并不建立伦理规范或道德标准。它就是生存美学,其要点在于自我的创造和内在塑造。福柯对这一“伦理学”期望颇高:“这种与自我的关系构成了转折的终点和一切自我实践的终极目标,它还属于一种自制伦理”。[35](346)换言之,“内化”(或“主体化”)是福柯哲学的终极目的。因此之故,晚期福柯哲学具有强烈的伦理学和美学风格,而它也再次反驳了大写主体。究其实质,福柯的伦理学只是一种“境遇伦理学”。福柯强调的是一种生存实践,而这种生存实践并不归于规范的道德或伦理规则所掌控之范围。“福柯更多关注和研究的是‘行为道德’而不是‘道德准则’”。[37]如此说来,福柯的伦理学就是广义的审美主义。
然而,自由才是福柯的主题词。“关心自己”、走向内在,这是福柯自我创造的路径,更是福柯试图实现或体验自由的方法。相对于前期肆意挥洒的批判,晚期福柯相对理性或沉稳。经过漫长的解构之旅,福柯发现解构和批判永无止境。关键在于,要在批判中发现一种可能性,一种自由创造之可能性。福柯说:“我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约束的文化是否可能或值得向往,而在于一个使社会发挥功能的约束性的系统是否为个人留下改造系统的自由。”[38]这既是福柯的方法,也是福柯哲学的目的和意义。福柯所谓“自我的技术”,其实不是为每个人提供行为模式,而是一部分人的选择;这一个体性“选择”既表述了福柯的伦理期待,也再次显示其生存美学的自由精神实质。海德格尔说:“人类的伟大本质在于它归属于存在之本质,为存在所需要,去把存在之本质守护于它的真理中。”[39]从晚期福柯的哲学努力和思想走向上看,福柯确实逼近了海氏这一真理。作为此在,它是自由的生命,是通向存在之途的“自我”。它听从自由和存在的召唤,不断反思自身,最终实现自我的构建和超越。如此,摆脱了孤独主体的自我如同驱除了私己个体的自我一样,它们都是真正自由的。
在福柯那里,“抵抗总是个人性的,是对个体界限的反复批判,是让强加于个体身上的界限分崩离析。”[37](261)福柯强调那些越界的生活和生存,也渴望由此带来新的生存方式和思想空间。“关心自己”是“越界”思想,也是一种自由的实践行为。它将“自我”本身变成审美对象,变成创造的对象。这是立场的根本转变,也是一种思想的冒险。意识哲学在强化主体性同时,也将“非我”变成客体或对象。事实上,它从不将自身作为审视对象,因而它始终无法消除主客对立。从“关心自己”出发,我们发现这竟是一条试图弥合主客分裂的可能性道路!如果说这仅仅是福柯的浪漫设想,那么这显然是值得讨论和重视的。总之,从“关心自己”出发的“伦理学”是一种生存美学。这种生存美学与其说关心“道德”,不如说关心“美”和“自由”。福柯的实践性生存强调境遇伦理,强调自我塑造和构建,也强调现实生存。这是一种美学化的伦理学,追求美,艺术的美、生活的美,而不只是道德上的善。根据福柯的理论,我们知道:“审美现代主义的精神产生了一种‘颠倒的文化’。在那种文化中,理性与其他者之间的传统价值对立经历了一次惊人的、而且意义深远的价值重估”。[40]由此可见,福柯的哲学就是一种基于直觉的自由美学。
标签:伦理学论文; 尼采论文; 福柯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文化论文; 道德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