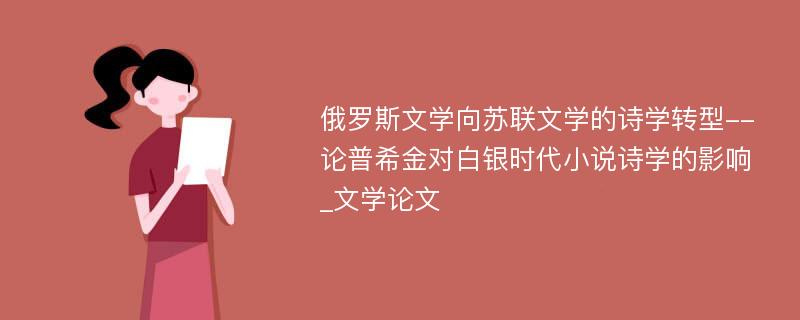
从俄国文学到苏联文学的诗学转换——关于普希金对白银时代小说诗学影响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普希金论文,俄国论文,苏联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文学与俄国文学无论有多大差别,它们与欧美或东方文学是很不相同的。俄国文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不同阶段有相当强的一致性或连续性,这种情形尤其充分地体现在小说文体中。这足以证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俄国白银时代小说起到了连接而非中断的作用。也就是说,白银时代小说的发生发展与19世纪俄国文学传统息息相关。事实上,所谓白银时代(The Silver Age)是相对于19世纪初的黄金时代(TheGolden Age)而言的,而黄金时代与普希金紧密相联。茹科夫斯基(1783-1852)使俄国韵文(verse)臻于完美,并给诗歌确立了将要成为俄国黄金时代诗学标准的规范,但这个黄金时代始自普希金1820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注:Prince D.S.Mirsky,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p.7.)因而称为普希金时代。然而,普希金不仅仅是以诗歌对俄国社会发生影响,他的小说所起的作用同样巨大,列夫·托尔斯泰就认为他的小说更令人惊心动魄。(注:冯春选编:《普希金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第510页。)这样,普希金就必然成为和白银时代小说发展息息相关的人物,不管这种关系是“继承”还是“超越”抑或“改造”,这同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预言也是一致的。(注:陀斯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6月8日普希金纪念像落成典礼上演讲说,“果戈理说过,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中一个特别的,也许是唯一的现象。我要补充一句:是一种带预兆性的现象”。参见冯春选编:《普希金评论集》,第429页。)
普希金对白银时代小说诗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小说语言是最先被感染的。一方面,小说是一种叙事性的语言艺术,小说变革在诗学上的反映必须通过语言显示出来,“研究其他文体等于研究死了的语言,研究长篇小说相当于研究充满生命活力和青春朝气的语言”,(注:巴赫金:《文学批评论文集》(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6),第392-393页。)其实中短篇小说语言也如此,因而巴赫金断言,衡量小说进化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对语言的态度”,(注:转引自凯特琳娜·克拉克和麦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337页。)“小说文体学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艺术地再现语言问题,或再现语言的形象问题”;(注:Mikha-il 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Texa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5),p.36.)另一方面,由于
作者在创作实践中,从来没有企图创作显示完全公正性的作品,不论是公正的轻蔑……还是公正的宽容……古希腊剧作家就从没有把所有人类价值混为一谈。甚至在有道德的、认识的或审美价值的人物中,任何作者都必然是有倾向性的。(注: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1987),p.83.)
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叙事中的语言,使“所有的句子都含有评价,只是其程度有所不同”;(注:张寅德选编:《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第57-58页。)特别是,普希金的语言具有显而易见的“刚健之美、力量和鲜明”,并因文本感情的“率直和真诚”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同胞和世界读者;(注:冯春选编:《普希金评论集》,第516页。)而“优秀作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行为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张它”。(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17页。)因而,普希金在语言上所奠定的诗学传统毫无疑问要成为某种象征,并对白银时代小说发展产生影响,在俄国文学转化为苏联文学过程中发生作用。
一
小说语言由人物语言和叙事者语言两部分构成,叙事者语言即“叙述的声音或讲话者”。(注:Shlomith 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London:1983),p.87.)叙事者不同于真实作者,后者是创作文本的人,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而前者是文本中的故事讲叙者,是真实作者想象的产物、文本中的话语。“叙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纸上生命,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作品中的说话人不是生活中的写作人”,(注: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载《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第29-30页。)因而叙事学断定,所有叙事者存在方式不外乎缺席、隐蔽和公开三种声音形态。
众所周知,西方小说在19世纪中期开始,要求叙事者退出叙事过程成为一种强劲的呼声。经福楼拜和左拉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叙事者声音的确变得非常微弱,以致于文本呈现出价值中立的状态,现实主义潮流退却为现代主义思潮。与此同时,俄国小说发展中的叙事者声音却有增无减,《死魂灵》的结尾处是叙事者公开的疑问:“俄罗斯,你不也就象一辆大胆的、谁也赶不上的三驾马车在飞驰吗?……俄罗斯,你究竟驶向何方?给一个答复吧”。而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所有重要文本,都不断回荡着这类叙事者声音。尽管19世纪末象征主义理论家要弱化甚至消除这种声音,白银时代对文学变革的重要范畴包括要把文学从沉重的生活美学中解放出来,使之变得含蓄,但文学家这种公民使命感却作为传统在白银时代延续下来,而使命感延续主要显示在叙事者声音处理上,即在白银时代小说中还是能听到不同类型的叙事者声音。究其因,还是因为普希金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传统象征力量所起的巨大作用。
我们知道,俄国小说文体成熟于普希金,其文本中活跃着叙事者声音,这个声音基本上是以“我”的形式出现的。“我”常常不是主人公,而仅仅作为叙事者,却不断地伴随着主人公活动参与叙事过程,对主人公行为进行评价。《叶甫盖尼·奥涅金》大段叙述奥涅金醉生梦死的生活情景之后,叙事者“我”便公开质疑“我的奥涅金……是不是真正感到幸福?他如此花天酒地、纵情饮宴,是否依然故我、身体健康?”《别尔金小说集》中所有重要篇目都有叙事者“我”的声音,这种声音甚至影响到小说的叙事视角。《驿站长》就是第一人称形式写就的,“我”直接观察主人公维林失去女儿的不幸过程,更方便地对这种人的悲剧深表同情和疑惑。《上尉的女儿》也如此,“我”为普加乔夫运动辩护,又常表现出不满暴力行为的心态,因而任意一行出自“我”的抑扬格诗句都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没有使上帝看见俄罗斯的暴动/是毫无价值和残酷无情的”。也就是说,叙事者公开地干预叙事过程,并对俄国社会种种现象直接地而不是隐蔽地发表见解,是普希金叙事性文体中叙事者声音显示出的重要特点。这与他的诗歌创作是一致的,从著名的抒情诗《致恰达耶夫》、《书商与诗人的谈话》和《纪念碑》等中可见出,这种现象取决于普希金期望的文学目标(做一个公民诗人)。纳博科夫在其力作《天赋》(The Gift)中声称,“普希金的韵律一个世纪来与生活的节律混合在一起”,或更直接地说:“普希金的声音和其他声音混合成一片”。(注:Boris Gasparov,Robert P.Hughes,Irina Paperno,Cultural Mythologies of Russian Modernism,from the Golden Age to the Silver Age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73-87.)
因普希金在文化史上的声望,这种“首先作为公民,其次再成为诗人”声音构成了俄国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又因普希金在世纪之交俄国的巨大影响力,进一步深刻影响了白银时代文学的发展走向,(注:俄罗斯《乡村使者》通过读者问卷调查和读者来信显示出,普通乡村读者对普希金的兴趣比预期的要高得多,而赫列波尼科夫、弗·伊万诺夫、叶赛宁、高尔基等等白银时代文学家都很关注普通读者的反映。参见Paul Debreczeny,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Alexander Pushkin and Russian Cultur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99-200.)使得小说创作中普希金式的叙事者声音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世纪之交那一长串杰出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安德列耶夫、布宁、库普林和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等,尽管不再在文本中安排专门叙事者“我”,但潜藏起来的叙事者还是常自觉不自觉地公开表露出来,从而显示出与象征主义的区别。当然,最突出的还是高尔基,也正因为他小说创作中充满了叙事者的公开声音,不隐蔽叙事者对叙事内容的干预,被批评界讥讽为“大喊大叫地走向文坛”的人。而高尔基的这一特征,与普希金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1890年以来的历次规模盛大的普希金纪念活动,他都非常关心,(注:从1880年6月8日普希金纪念像在莫斯科落成以来,俄国几乎每年都要举行规模大小不等的纪念活动,甚至“俄罗斯文化节”即源于1921年和1922年移民中举行的纪念普希金的活动。从1924年开始改在普希金出生的6月。)此其一。其二,他很看中普希金这种公民式的诗人特征,高度评价说:“普希金最先感到文学是头等重要的民族事业,感到文学比在机关工作或宫廷服务还要高尚;在他看来,诗人乃是人民一切感情和理智的表达者”,(注: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154页。)也重视这种特征在文学上的诗学反映,“因为他有生活的印象溢于心中……便努力把这些印象反映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上面,而且以莫大的能干达到这个目的”,(注: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178页。)这个“莫大的能干”就包括对叙事者声音的处理。高尔基本人也因此不顾许多人的反对,使叙事者声音处在公开状态,直接发表判断性评论,即叙事者依据某种价值观、道德原则和意识等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进行评价。这种声音一般出现在隐蔽展示主角行为之后或正在进行的过程中,这种现象在作家所有重要文本中都程度不等地存
在着。对巴威尔和他的情人娜达莎(《苦命人巴威尔》,1897)、卢利奥夫和他的两个朋友(《三人》,1900-1901)、叶夫塞(《没用人的一生》,1907-1908)等下层人的悲惨人生,叙事者时常停下来深表同情或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与个人原因表示不满。对巨富老高尔杰耶夫(《高尔杰耶夫》,1916)所涉及到的商人与良心的关系问题,叙述者便趁机中断故事叙述进行一番评述。
良心只有对于性格懦弱的人才是难以抑制的,强者很快制服了它,使它服从自己的目的。他们对良心也奉献过许多不眠之夜,但如果良心偶尔征服了他们的灵魂,那么为良心所击败的他们也绝不会萎靡不振,而是在它的支配下顽强地生活下去,同不讲良心时过日子一个样。
马特维(《忏悔》,1907-1908)在经历了妻子难产而死、儿子误死之后,向大祭司真诚地表白自己对上帝信仰存有疑惑并请求解答,而后者居然嚷道“应该把你送到警察局、送你坐牢、去修道院、去西伯利亚”。此时叙事者“我”便代替经验者马特维说,
一个人要是招呼警察来为自己的上帝撑腰,那可见不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上帝,就一点力量、一点美德也没有了。
类似的判断性评论伴随在主人公行为过程中,这就使得文本产生了剧烈矛盾:一方面主人公要追求“绝对公正的上帝”,另一方面正好发现这种上帝是不存在的,为此,他主张在普通民众中造出真正上帝。这种叙事者声音与叙事过程的矛盾,导致这部作品出现了少有的争议。在晚年最重要的力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中也是如此,尽管此时创作如果公开表露与意识形态不吻合的观点或思想是危险的,但对主人公自由派知识分子克里姆在那动荡的世纪之交岁月中的内心矛盾,叙事者还是中止故事的正常叙述而评论道:
在这好得无与伦比的世纪中,有一个叫克里姆·萨姆金的人正在徒劳地痛苦挣扎。尽管他早已不象从前那样痛心地感觉到自己的探索、激动和不安是毫无结果的,但有时还是觉得,现实生活越来越敌视他、排斥他,把他挤到一边去,从生活中消除掉。(注:《高尔基文集》(21)(莫斯科:19年,俄文版),第428页。)
至于《母亲》更充满了有鼓动性、号召力的判断性评论。这些潜藏在具体叙述之间的评价声音,显示出叙事者在世纪之交的动荡年代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类见解表明他对叙述对象具有深刻理解力,并且有正常的语言能力,字里行间渗透着幽默、讽刺或机智。“在叙述效果中,最重要的差别或许是取决于叙事者本身是否戏剧化(dramatized)、叙述者信仰与性格是否同作者一致(shared)。”(注: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aliforni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7),p.151.)而且“隐含作者(作者所创造的形象)某些方面可以通过文本基调变化来显示,但其主要特点还将依赖于所讲故事中的人物和行动的确凿事实”。(注: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aliforni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7),p.151.)高尔基能够把握住这种叙事声音公开化的分寸,他说,“我主要是利用自传性的材料来写作,但是我使自己站在事件目击者的立场上,避免作为当事人站出来,为的是不要妨碍自己作为生活叙事者”。(注:高尔基:《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261-262页。)他主张叙事者要尽可能用描述性的语言,因为“劳作从来就不是抒情的……在描写劳作过程时使用抒情的词句,任何人听起来都觉得虚伪。”(注: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252页。)但他作为积极投身社会和改造人的战士型思想家、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对所叙述的对象肯定不会无动于衷,自然会在叙述进程中产生评论性的话语行为,因而契诃夫等强调客观写实的作家不喜欢这种评论,致信高尔基说,“您就象是剧院里的观众,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狂喜心情(rapture),影响了自己和其他人对演出的观看和倾听”。(注:The Life and Letters of Anton Chekov(Geogre H.Doran Company,1925),p.262.)托尔斯泰也有类似微辞:“影响人物性格发展,常借助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批评,宛如有些人批评普希金小说“过于朴直”的声音在20世纪初的回应。(注:冯春选编:《普希金评论集》,第471页。)事实上,高尔基也能使叙事者声音完全隐蔽起来,但这会影响读者真正理解其文本。《阿尔达莫罗夫家的事业》(1924-1925)只用具体场景显示这个家庭三代人步入市场经济的奋斗历程,展示俄国东西方文化特征对现代化历程的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因没有叙事者声音的暗示(其实也未必能准确地暗示),结果苏联读者普遍误认为是反映资本主义在俄国的不可能性。
在叙事者声音处理上,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主要关注如何干预叙事主题、叙事内容,而要超越普希金传统的象征主义者在小说创作上却无法超越俄国小说的这种诗学传统。象征主义运动领袖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把普希金视为伟大的艺术家和英明的人,是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基督和反基督者、人神和神人等融为一体的人物,因而其代表作《基督与反基督者》三部曲(1896-1905)充满了尼采式的异教精神(paganism),渗透着莫斯科要充当第三圣经中心的(Christianity of the Third Testament)俄国神话观念,而且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小说诗学,即不断把叙事者声音隐蔽起来并使之指向叙事本身,而不对叙事对象或内容发表见解,因而三部曲变得很复杂。(注:Bernice Rosenthal,D.S.Merezhkovsky and the SilverAge:The Development of a Revolutionary Mentality(Nijhoff:The Hague,1975),pp.89-98.)这种转移叙事者声音的做法,在象征主义文学大师勃留索夫(1873-1924)的力作《燃烧着的天使》(1908)和《胜利的祭坛》(1911-1912)、索洛古勃(1863-1927)的杰作《卑鄙的小魔鬼》(1892-1902)和《创造的传说》等文本中成为普遍现象。不过,叙事者声音这种指向文体叙事过程的现象,发展到俄国象征主义代表安德列·别雷(1880-1934)那儿就变得登峰造极了——叙事者声音已经基本上只限于针对叙事本身,这在他一系列创作中充分地显示出来。
别雷之所以如此,是因普希金对他的影响太深刻了。1899年他年仅18岁时就因《为什么要如此隆重庆祝普希金诞辰百年》一文,被推举参加首都举行的普希金诞辰150周年活动;1916年完成了著名的论文《普希金、丘特切夫和巴拉丁斯基的视觉特征》。作为“持不同政见者”,1920年4月18日他还被谢缅·温格洛夫院士邀请做“普希金与12月党人”学术报告会主席。1924年7月《真理报》和《消息报》称他为“普希金专家”……影响转化小说诗学反映在叙事者语言问题上,就是在象征主义美学中如何改造普希金诗学传统。这种改造,主要由其力作《彼得堡》(1913-1914)来完成。该作主要叙述的不是大学生尼古拉被恐怖组织诈骗,要用一枚定时炸弹去完成炸死作为帝国政府枢密官之父阿波罗的任务,而是在这件事情发展中父子俩那复杂无序的意识或无意识,这样一来,叙事者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作者说,“文本中真正的故事空间是某个人的心灵,这个人没有在小说中出现,他因为大脑的活动而疲惫不堪。”(注:安德列·别雷:《彼得堡》(列宁格勒: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分部,俄文版,1981),第516页。)这个人就是叙事者,其功能转移到关心文本结构上来,即公开提醒读者该文本是在叙述故事,而不是要描述或展示一个真实的事件,因此,该书几乎每一章标题中都使用“叙述”或“讲述”等词。不仅如此,我们说叙事者提醒读者这个文本是在讲故事,还特别体现在叙事过程中,读者不断被叙事者告知“你是在听故事”。叙述主角阿波罗·阿勃列乌霍的史料时,叙事者便提醒读者说,“我们还是转到那些不那么遥远的古代祖先上来吧”;提及他的社会地位问题,又说“我看这个问题提得很不妥”;叙述阿波罗看晨雾中的彼得堡时,又提醒道,“在这开端处我就应该打断叙述,来给读者介绍一个戏剧性事件。预先就该纠正疏忽所致的不准确性,不是作者的错误,而是作者的笔误……”。(注:安德列·别雷:《彼得堡》,第19页。)甚至公开展示作者的构思,第一章结尾便是对这章叙事内容的总结、对叙事过程的评价:“你不会忘记他!”并且说:
在这章里我们遇见了枢密官阿勃列乌霍夫……最后我们还看到了无聊的影子——陌生人,这个影子是通过阿波罗·阿勃列乌霍夫的意识偶然产生的,它在那里的存在是瞬息即逝的,但是阿波罗的意识是影子的意识,因为连他也只有短暂的存在,是作者想象的产物:无用,无聊的大脑游戏。向四面八方展开联想的各种图案后,作者应该把他们清除掉,用哪怕就这样一个句子切断叙述的线索也好,但作者不会这么做,他有这么做的权利……
叙事者这些非叙事性声音,演化成恢复小说何以为小说的元叙事,即不仅给读者理清这一章叙事线索,而且还对作者为什么这么叙述做了说明,当然也故意消解叙事者声音在思想上的价值,以强化叙事本身的意义。这种做法,在文本开场白中显得更加充分:“俄罗斯帝国包括:首先——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和黑土带俄罗斯,其次——格鲁吉亚、波兰、喀山和阿斯特拉罕,还包括——其他的,等等”,“俄罗斯帝国由诸多城市组成……还有——京都及城市之母,京都城市——莫斯科”,“涅瓦大街——是一条笔直的大街。涅瓦大街——在当时俄罗斯非首都城市里——是一条非同一般的大街”……,叙事者这些公开声音没有承担解释事物的功能,本来事情很清楚,用不着解释,但叙事却虚张声势,做出史学家姿态,造成了句子支离破碎,根本起不到判断性评论作用,成了对普希金那种关心主人公行为的叙事者声音的不规则戏拟。所以,当代俄国杰出的文化史家利哈乔夫院士认为该作“最主要是在形式上不断地探索,不合规范地‘流利书写’,而这种现象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大量存在,由此使他常常趋向于强调形式‘风格’、语言‘风格’”,(注:别雷:《彼得堡·致读者》,第6页。)这也是别雷对象征主义文学的最大贡献。
然而,白银时代无论是新现实主义作家还是象征主义作家,他们的叙事文本中普遍少有阐释性评论(叙事者对故事梗概或故事某些细节的意义另外进行阐释),这不仅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言“诗人应该少用自己的身份说话,否则就不是模仿者了”,(注: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7),p.78.)而且也是普希金尊重读者、相信读者阅读能力的叙事传统的延续。到了20年代后期的苏联小说,叙事者这种阐释性评论却大量活跃在叙事过程中,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文学直接教育读者在诗学上的反映,尽管30年代以来苏联还常常举行普希金纪念活动,但这种诗学特征却与普希金传统大相径庭。
二
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进行言语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内心独白、意识流,还是人物之间的交流,都普遍显示出对话性(人物之间对话、人物与叙事者对话、人物与世界的对话等等),而18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是注重生活写实的,因而巴赫金发现“小说中的对话是小说全部经验的中心”。(注: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87),p.151.)这样一来,如何设置人物语言问题就成了如何处理对话性问题。普希金非常注重设置人物语言问题,别林斯基这位对文坛宏观走向敏感的批评家也发现了作家语言的不同凡响,他说:
很难概括普希金在语言方面变革的巨大意义……一切都是丰满的,没有任何言不尽意的、朦胧的、不确切的、不明确的东西。明确性是伟大诗人的特点,普希金完全掌握了这种特点。(注:冯春选编:《普希金评论集》,第31-32页。)
这种“明确性”不仅显示在词汇选择上的大众化、通俗化,而且主要表现在句式上的完整性、规范性。也就是说,普希金小说的人物语言处在一般直接引语或一般间接引语标识之下,人物或人物之间的言语行为有明确的标志、指向,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不产生歧义现象。然而,《叶甫盖尼·奥涅金》尽管主要由“我”的一般间接引语和主人公与周围人之间一般直接引语(对话)构成,但展示出的却是一个孤独者主人公奥涅金形象,而这个形象也不仅仅是反映贵族知识青年的颓废和无奈;在《上尉的女儿》中,主人公与普加乔夫的对话占有重要比重,对话显示出后者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并且充满智慧、有起义军领袖的风度,令人钦佩。占有相应比重的一般间接引语在转述这个问题时,却连同其他细节一道使文本的主题思想复杂起来。《驿站长》主要由维林和“我”之间的谈话构成,从谈话中“我”得知他失去女儿的悲苦,然而“我”以一般间接引语传达出来的却不只是哀叹小人物不幸的声音。这样,“明确性”句式获得的却是深邃、复杂的语义。艾亨鲍姆感觉到普希金诗学的这个特点,即“复杂的语义结构(complex thematic structure)是建立在简单的情节(simple plot)基础上的”,并把这种现象归之于“是在诗歌基础上创造小说”,而“普希金的历史使命是为俄语诗歌语言确立稳固的基础,在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一个综合、稳定、完整的艺术体系”。(注:D.J.Richards and C.R.Cokrell,Russian Views of Pushkin(Oxford:Willem A.Meeuws Publisher,1976),p.142.)而经验又是什么呢?就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氛围及其感受:普希金时代尽管被后人称之为黄金时代,却不是一个能充分对话的时代。1797年沙皇亲自把被流放的拉吉舍夫召了回来,但事隔5年后,后者因不可能与社会对话,最终还是自杀了;1825年,那些切身感受到西方文化之可贵可敬的俄国知识青年,因始终找不到与社会对话的可能性,于当年12月诉诸武力,发生了世界性的历史事件“12月党人起义”;普希金本人一直想要与社会对话,却几次被流放;甚至无伤大雅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爱好者座谈会”和“阿尔扎玛斯社”之争(普希金本人甚至是其中的成员)也不了了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而,普希金有些诗是启蒙社会公众的独白式呐喊呼唤(《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囚徒》等等,这些诗句式非常规范、语汇能指和所指相当一致),而有些则是尝试对话、排泄内心郁闷(主要是表达内在情感的诗作)。而普希金在不具有对话性时代尝试对话,就必然导致语言缺席现象大量产生,著名的《秋季》(1833年)还残留这种痕迹:“手指握着笔,笔触摸着纸张,/一瞬间——一行行诗顺畅地流出来。/在风平浪静中的海船寂静不动,/但你听——水兵们突然急忙行动起来,/上面的、下面的——船帆鼓胀起来、充满着风。//行驶着。我们要驶向何处?……”。但“普希金的散文并不是他诗歌的补充,而是代替他诗歌的某种新的东西”,(注:D.J.Richards and C.R.Cokrell,Russian Views of Pushkin(Oxford:Willem A.MeeuwsPublisher,1976),p.141.)在人物语言问题上表现为改变叙事策略。《叶甫盖尼·奥涅金》想使语言缺席却不可能,第一章发表时,其“前言”后附有诗篇《书商和诗人的谈话》,最后有注释说:“请注意,这篇文章中所有用虚点表示的空白,都是作者自己空出来的”,而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禁止使用虚点表示检查官删去之处,所以作者作了这个注释。(注:《普希金选集5:叶甫盖尼·奥涅金》,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6页。)果然,文本第4-7章中就没这种空白点。在此情形下,普希金就使句子结构表面上完整起来,但语义结构却不指向现实性语境,而指向未来世界或另一个世界(内在心理世界)。
普希金在简单情节中蕴含着复杂语义结构,作为一种传统,对完成俄国文学的诗学转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时代小说要追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并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的目标,但事实上苏联文学的经典文本并不是直观地完成文学的诗学价值的,反映在人物言语行为上是一般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其能指与所指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潜藏着与意识形态不吻合的深层的民族情绪。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显然包括白银时代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性超越中延续了普希金诗学,因为普希金人物语言的诗学传统正好吻合了白银时代作家的选择。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是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现代基督教等不同流派之间的纷争,主流意识形态在现代化运动进程中逐渐失去中心地位,然而构成对话的主体复杂化了,每一种流派都想成为新的中心。在这种情形下,对话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反映这种可能,就成为白银时代作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这种问题与普希金的关系,从1880年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以来的纪念活动中可以看出来(讨论“普希金与现代”是此后半个世纪来历次纪念活动的重要论题,尤其是1899年百年诞辰纪念和1921年逝世84周年纪念中出现的经典著作,如索洛维约夫的《普希金的命运》、勃洛克的《关于诗人的使命》、F·索洛古勃的《普希金之死与俄罗斯知识分子》、古佩尔的《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化》、魏列萨耶夫的《生活中的普希金》等,《普希金与陀斯妥耶夫斯基》论文集更加如此)。
这种关系直接影响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高尔基流浪汉题材小说一经问世便产生轰动效应,重要原因是文本充满着大量一般直接引语,把下层社会言语原貌完整地呈现出来,给读者以直面现实的深刻感受,从而给俄国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即普通人常用的习语、俗语、俚语、口头语等和简单句、判断句等,并建立了新的对话机制——同温文尔雅的上流社会进行潜在对话,还因人物语言行为中暗含着乐观主义而同读者对话。通过人物语言行为显示出的双重对话特征,在《母亲》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它直接采用一般直接引语句式,减少了叙事者干预的可能性,其意义不仅仅是展示正在成长中的工人革命家最本真的思想,还在于通过主人公话语模式本身,同社会进行潜在对话。文本完整地记录下了巴威尔母子四次重大宣言式的言语行为,这些言语并不特别期望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出来对话,或者说并不幻想会有人积极参与对话,而是理直气壮地宣讲自己的主张。选择这种句式来叙述巴威尔母子的语言模式不无道理,因为他们未能置身于能够对话的语境中,他们面对的是两种“听众”:一是他们所要发动的群众,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听众起来在言语上进行对话,而是希望在行动上实践他们言语中所包含的思想,所以他们从考虑听众接受能力方面着手调整话语结构。沼地戈比事件失败的原因与巴威尔大量使用知识分子的书面语有关,五一游行和法庭上的演说之所以有分量、富有鼓动性,与他改用产业工人口语化言语相关,这一情形表明“要表达因为黑暗而生的痛苦心情,并决心用光明来与黑暗作斗争,小说能给一个简单明了的戏剧化了的代言人提供方便。”(注: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p.299.)二是官方意识形态,他们母子没把对方作为平等对话者的奢望,而是当作对抗的对象,事实上对方也确实没有对话的意识。这样,母子这种不经过叙事者中介修饰的言语模式,在句式、词汇、语调等方面显示了人物意识活动本来的语言形态,修饰性词汇则用得更少,因此极具鼓动性。而这些语言模式本身具有两种对话可能性,即有接受能力的工人或工人革命家,或未来社会。《母亲》后来产生巨大反响,与一般直接引语设置中潜藏着对话的机制不无关系。高尔基小说这种人物言语行为特征与普希金“明确性”传统之关系是明显的。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在纪念普希金逝世百年活动中撰写的著名论文《普希金和高尔基》论述了这种继承性。(注:Paul Debreczeny,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Alexander Pushkin and
Russian Cul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38.)这种诗学传统,深入到其他苏联文学初期一些重要现实主义小说中,象扎米亚京反乌托邦文学力作《我们》、普拉东诺夫反思集体化运动杰作《地糟》和《切文古尔》、皮里尼亚克反思国内战争的作品《骑兵军》等,它们在当时被读者广泛地注意,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种现象,与普希金具有“明确性”的作品在上个世纪被俄国知识界欢呼,却不断引起革新派和保守派、现实主义派和纯艺术论者、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等的论争有很大的相同性,其中与文本自身不无关系,即在不同程度上,期望通过在调整人物语言句式中,表达不仅与现实世界、而且与未来世界进行对话的意向。
普希金这种影响,不仅在新现实主义中普遍存在,而且在现代主义文学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因普希金等人文学遗产的作用,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等诗歌创作经历了从语言行为的模糊性到明确性的转变,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保持诗学价值重叠性传统。至于象征主义小说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勃等主要叙事文本,更是注重叙事过程的明晰性,在人物言语明晰性中重建多重对话的机制,增加文本理解的可能性、多义性。譬如《卑鄙的小魔鬼》和《基督和反基督者》等人物言语行为明白清楚,而其语义指向却很模糊,并且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的读者再度体验其语义时,还是发现不能充分对话。通过变革言语行为来掩盖文本真正的价值追求,在勃留索夫创作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勃留索夫此举,与整个象征主义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转换过程是一致的,但更重要的是倍受普希金影响的结果。从1898年他开始在《俄罗斯档案》上发表普希金研究论文以来,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现(论文82篇,还有专著《普希金来往的书信》和《皇村学校时期的普希金诗歌》等)。作为俄国著名普希金学专家,针对1899年普希金纪念(jubilee)活动中的出版浪潮,他发现绝大多数出版物关心的是“语汇,而不是与活人的关系;是书信,而不是文本的精神”,因而在1897-1903年间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和学者热切地探寻普希金真正的“文本”——艺术的和传记的(artistic and biographical)。(注:Boris Gasparov,Robert P.Hughes,Irina Paperno:CulturalMythologies of Russian Modernism,from the Golden Age to theSilver Age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ronia Press,1992),pp.73-87.)这种探索,使他1908年以后的小说《燃烧着的天使》、《南十字星座共和国》(1907)、《胜利的祭坛》(1911-1912)和《莱亚·西尔维雅》(1914)等,叙事过程普遍清晰、语义重叠(表层语义之下还存有另一层或多层),这个特点主要显示在人物言语行为的句式变化上。
《燃烧着的天使》非常完整地叙述“我”(16世纪德国一个名叫鲁佩列哈塔的阅历丰富的青年)和一个神秘女子莱娜塔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性恋爱经历,以第一人称形式如实地展示出“我”在这个经历中的现实状态和心理状态:“我”同通灵术大师阿格里巴及其五个学生讨论神秘主义、情感与理性等问题时头头是道,而同恋人莱娜塔之间却不能用语言交流。她是以基督受难者和弱女子角色出现在“我”视野中的,她对别人的言语行为非常敏感,尤其是对称谓或信仰的某些表述更是如此,并肯定地说,“只有从来就不明白信仰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的人,才有资格讨论上帝和人间关于信仰之争的事情”。然而“我们”却不能进行言语对话,她或要“我”保持沉默,或要“我”陪她参与其祈祷与旧情人亨利希再度恋爱的巫术活动,并说“请让看见”、“请让听见”、“请让亲吻”和“请让紧紧地依偎”之类的话,或发布命令:“鲁佩列哈塔,在我没有叫你过来时,你别想上我这儿来”、“我与你不能有什么共同的事情,你是活人,而我是死人。分手吧”等等。对这些命令式的句式,“我”本该作出相应的反应,然而她的眼神和语气使“我”失去了用语言进行反抗的能力,而只会点头同意。把现实中的对话转化为内心同自我的对话,导致把一般直接引语转化为自由间接引语的现象,而这些自由间接引语证明“我”有正常的语言能力,尤其是离开她后能同他人顺利进行语言交流。统而观之,表述这场恋爱过程的基本上就是一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两种句式,而且每一种句式的句子长短是相当匀称的,句式的规范性是作者有意为之的。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句子长度大约是25个单词,库普林大约是30个,而勃留索夫则是20个……由于他刚健风格中具有简洁和直截了当的特色而受到俄国人赞赏,被称作用青铜铸造句子的人(a maker of sentencesin bronze)(注:Stephen Graham:Introducaion to The Republic of theSouthern Cross and Other Stories,p.v.)
也正因这种句式带有很浓厚的书面语的客观、完整和规范性特征,显示出这场恋爱尽管是神秘的,但爱情却是严肃的;一般直接引语句式反映出,爱情对于当事者来说是无限的甜蜜痛苦,在这种状态中人是会成为失语症患者的,但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人生本质意义的一种体现方式,与俄国文化传统中那种强调人的幸福或意义依附于对上帝的信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也正是象征主义变革文学,追求现实主义的理由所在,这一思想与作者著名的纪念普希金论文《神圣的受难者》充分地一致;同样,从一般间接引语中显示出爱情的深邃是需要不断体验的,这是人生意义或幸福的一种延续方式。句式变化带来语义的复杂化,使文本叙事在指向现实世界的同时也指向人的内在本体世界,隐藏着反对民粹派把唯物主义美学庸俗化的社会思潮——使文学价值追求只停留在外在写实层面上,失去对人生意义的感悟。通过句式变化使主人公形象失去了稳定性,与他的“双重普希金”在观念上是一致的。其实,勃留索夫其他重要文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在规范性句式中语义重叠的现象,也正因为这点,他在白银时代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但在苏联时代却被简单化为从浪漫主义转化而来的现实主义者,这与普希金在苏联时代只被作单一的解释相一致。
20年代中后期尽管照常进行一年一度的普希金纪念活动,但从1924年政府组织纪念活动时不再邀请别雷等人参加这一现象看出,人们对普希金的选择不再自由。普希金对苏联的影响是按意识形态要求进行的,这与完成了从俄国文学到苏联文学的诗学转换过程同步。这样,随着白银时代的结束,普希金对苏联文学的影响也就以新的形式进行。从内战战场上下来的作家更注重人物语言行为中一般直接引语的写实性特征,对一般间接引语把叙事中心指向人物内心世界的诗学则重视不够,其文本“充满着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成为“特写作家”。(注:格罗兹诺娃:《早期苏维埃散文,1917-1925》(列宁格勒:教育出版社,俄文版,1976),第58页。)而叙述是一门艺术,不是一门科学,“小说文本不应该丢失自己那独特宏大的内容和自由的结构,以便使读者有思考并继续从中触及到人类命运、思想和问题之可能性。”(注:特瓦尔朵夫斯基:《论布宁》,载《布宁九卷本文集》(1)(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65),第33页。)后来几十年苏联文学历尽改革,但普希金传统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复活,因而苏联小说诗学探索和文本意义都没有充分地实现。
标签:文学论文; 普希金论文; 白银时代论文; 高尔基论文; 小说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彼得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