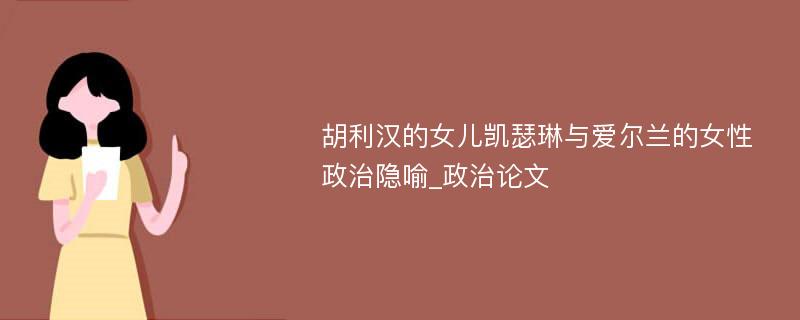
《胡里汉之女凯瑟琳》与爱尔兰的女性化政治隐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尔兰论文,之女论文,凯瑟琳论文,女性化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芝(W.B.Yeats,1865-1939)的剧作《胡里汉之女凯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1902,以下简称《胡》剧)在爱尔兰民族身份的(重新)塑造过程中起着别具一格的作用,值得专文讨论。①该剧是叶芝最具民族主义情感的一部作品。民族主义的情感不仅体现在革命的主题和为了拯救爱尔兰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号召上,还更深地体现在该剧的同名女主人公的爱尔兰文化根源上。“胡里汉之女凯瑟琳”这个本土化的女性名字因为《胡》剧的流行而被重新了解、认识和定义,成为对爱尔兰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隐喻。这一用女性来隐喻爱尔兰的文学手法可以直接上溯到18世纪颇为流行的以盖尔语为主要创作语言的“阿希林”诗歌(Aisling),甚至还能进一步上溯到爱尔兰古代有关“主权女神”(Goddess Sovereignty)的神话传说。
但若将该剧置于爱尔兰文化语境下进行互文性阅读,我们会发现《胡》剧并非如通常所被认为的那么“革命”。在其表层的革命热情与献身主题之下,还潜藏着叶芝等英-爱(Anglo-Irish)知识分子对未来爱尔兰政治走向的复杂心情和少数派文化诉求。凯瑟琳因为迈克的牺牲而从老妇人变身为年轻的女王,但她的合法配偶的身份却存在意味深长的留白。这既体现了爱尔兰时局的复杂性,也隐含了英-爱知识分子希望民众进一步考虑未来爱尔兰民族身份组成的文化诉求:即未来的民族身份要突破窄化定义(“爱尔兰语+天主教”),兼容包括英-爱人士在内的其他爱尔兰政治群体,以文化(而不是语言、宗教)为纲来界定谁是未来的爱尔兰人。深入分析《胡》剧,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凯瑟琳作为爱尔兰的政治能指所具有的文化政治影响力,也能更进一步理解围绕凯瑟琳这一人物形象所展开的现代文化论争。
爱尔兰文化语境中的凯瑟琳
《胡》剧以1798年托恩(Theobald Wolf Tone,1763-1798)领导的爱尔兰起义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名叫“胡里汉之女凯瑟琳”的老妇人如何用言辞打动即将成婚的迈克,促使其放弃家庭幸福与物质享受,转而追随老妇人,献身爱尔兰的独立事业的故事。②
在《胡》剧中,老妇人明确地告诉迈克,她的名字叫“胡里汉之女凯瑟琳”,也有人直接称呼她为“可怜的老妇人”;而她四处漫游的原因是因为“家里太多的陌生人”,她一切麻烦的起源则是被人抢走了“四块漂亮的绿地”。③这些线索直接将老妇人与爱尔兰联系起来,使她成为爱尔兰的一个政治隐喻。而她打动迈克的那些革命话语更是几乎不加掩饰的民族主义话语:
老妇人:那些帮助我的人需要付出极大的牺牲。许多人曾经红颜,如今将面色灰白;许多人曾经在山林沼泽间自由徜徉,如今将被迫远走他乡,行走在异国坚硬的街道上;许多美好的计划将会流产;许多人攒了钱却无法留下来享用它;许多孩子出生后将没有父亲出席其洗礼仪式,或为之命名。为了我,那些曾经红颜的人如今面色灰白,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得到了回报。(她出门;歌声在门外响起)
他们将永被铭记,
他们将永垂不朽,
他们将永远诉说,
人民将永远倾听。(Cathleen:10)
作为爱尔兰政治隐喻的凯瑟琳人物形象并非叶芝独创,而是具有极深的爱尔兰文学渊源。在爱尔兰历史上还有许多类似“胡里汉之女凯瑟琳”的本土化女性名字起着同样的政治隐喻功能。“可怜的老妇人”(Sean-Bhean Bhocht,即Poor Old Woman)、“黑暗之女凯特”(Cáit Ní Dhuibhir,即Kate of Darkness)和“黑玫瑰”(Róisín Dubh,即Dark Rose)等仅是其中几个比较熟悉的例子。④
《胡》剧的故事可直接追溯到18世纪的“阿希林”诗歌传统。“阿希林”的字面意思为“梦境,幻象”。“阿希林”诗歌常用来特指借助梦境或幻象来表达隐晦政治理想的18世纪盖尔语诗歌。诗人伊甘·欧拉西里(Aogán ó Rathaille,即Egan O Rahilly,约1675-1729)被尊为“阿希林之父”,其《光明之光》(Gile na Gile,即Brightness of Brightness)、《梦境》(An Aisling,即The Vision)、《救世主之子》(Mac an Cheannaí,即The Redeemer's Son⑤)不仅是“阿希林”诗歌的代表作,也确定了“阿希林”诗歌的基本模式和标准。以下以《光明之光》为例来分析一下“阿希林”诗歌的主要特点:诗人在梦中遇见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追随她来到一座宫殿,宫殿里的小妖精和仙女嘲弄地将诗人捆绑起来:
他们把我紧紧捆绑,不留一丝余地,
而一个愚笨的畜生正抓住我的女孩的酥胸。
我于是向她直称,句句都是实言
与这个瘦弱憔悴的畜生混在一起是多么不妥
有个最棒的男子汉,远胜其三倍,苏格兰之子⑥
正等着迎娶她为自己的新娘,倍加呵护。
一听我言,她痛哭失声
滚滚珠泪流下她晕红的脸庞。
痛苦、灾难、毁灭、忧伤和失败!
我们温驯、漂亮、纤细、温柔、唇色鲜艳的女孩
委身那个漆黑、长角、异族、令人憎恨的家伙
而求救无望,除非我们的狮子渡海而来。⑦
这首诗里几乎体现了“阿希林”诗歌的全部要素:通过梦境组织全篇的写作手法、弥漫全诗的忧伤情愫、隐喻爱尔兰的女性人物、喻指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的强迫婚姻以及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期冀。⑧其中,与本文的主题密切相关的是该诗将爱尔兰比作女性的政治隐喻。爱尔兰被隐喻为一个失去爱人并且被迫与敌共眠的女性,迫切地等待着爱人(爱尔兰的合法君主)回来将其救赎。而这一隐喻还可以再进一步追溯到有关主权女神的爱尔兰早期神话。女神象征着土地,和土地一样古老,却因为与一代又一代的合法国王成婚而得以不断重获青春与丰饶。国王的登基仪式被称为“国王的婚礼”(banaisrighe,即wedding of the king),即国王与主权女神(由其神物白马代表)的婚礼。只有通过这个仪式,国王才能成为合法的君主。作为主权女神的丈夫,他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权。⑨
史称“有九个人质的尼尔”(Niall Noígíallach,即Niall of the Nine Hostages,约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位)的古代爱尔兰最高王(High King)尼尔获得统治权的故事即是此类传说的一个代表:尼尔的父亲无法决定将自己的王位传给哪个儿子,于是派五位王子(布莱恩、费阿拉、阿里尔、弗格斯和尼尔)一同去打猎。五位王子在森林中迷了路,他们支起火来烤食猎物,并派弗格斯去取饮用水。弗格斯找到一口井,该井却由一位丑陋无比的黑衣老妇人看守。老妇人要求弗格斯必须亲吻她一下才能取水。弗格斯拒绝了她的要求,无功而返。其他三位兄弟依次前去取水,均告失败。其中,费阿拉勉强用嘴唇触碰了老妇人一下。为此,她允诺让他的子孙也仅仅触碰一下塔拉的王权(后来费阿拉的子孙有两位入主塔拉,成为爱尔兰的最高王)。最后,轮到小王子尼尔前去取水。面对老妇人同样的要求,尼尔得体地亲吻并拥抱了她。一吻之下,老妇人变身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面对尼尔的质询,她回答道:“塔拉之王,我是主权……你的子孙将会遍布各个部落。”尼尔回到兄弟们的身边,用水作为交换,迫使那四位兄弟承认自己的尊长地位,并最终成为爱尔兰的最高王。其子孙也从6至10世纪长期统治爱尔兰,史称奥尼尔王族(the O'Neill clan)。⑩
《胡》剧的互文性留白
在尼尔及类似的传说故事中,主权女神在爱尔兰诸王中选择合法配偶(即爱尔兰的合法统治者),而在“阿希林”诗歌传统中,女主人公的合法配偶多为詹姆士二世或其子孙。显然,爱尔兰被隐喻为女性的模式得以延续,但不同的政治气候会影响其“合法配偶”的人选。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奥康纳(Daniel O'Connell,1775-1847)、米歇尔(John Mitchel,1815-1875)、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等在不同时期左右爱尔兰政坛的人物都曾先后“当选”。(11)那么,《胡》剧中老妇人的“合法配偶”是谁呢?
在《胡》剧的最后,迈克决定放下一切去追随老妇人。彼得问站在窗前的帕特里克看见老妇人没有?帕特里克回答道,“没有,但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迈着女王般的步伐。”(Cathleen:11)这句话暗示凯瑟琳像主权女神一样变年轻了。但是和主权女神的传说不一样的是,凯瑟琳的变形不是源自真命天子的一吻,而是迈克等年轻人的流血牺牲。
在主权女神的传说与“阿希林”诗歌中,婚礼或性爱的意象均得到强调。真命天子必须在完成亲吻或性交等标志婚礼成功的行为之后,丑陋的老妇人才会变身为漂亮的年轻姑娘,适宜成为万民景仰的王后,并帮助对方成为爱尔兰的最高统治者。18世纪的“阿希林”诗歌更是进一步发展这种对性爱关系的比喻,将爱尔兰与英国的关系比喻为强迫的婚姻。隐喻爱尔兰的女性人物被迫与其合法配偶分离,沦为征服者的性奴隶。而其救赎的指望就在于自己的爱人卷土重来,赶走入侵者,重续婚姻关系。
但在《胡》剧中这种性爱关系却被刻意淡化。《胡》剧格外强调凯瑟琳与迈克等为之献身的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与性爱无关:“尽管所有这些人把爱交给我,我却从未为他们任何一个铺床置被。”(Cathleen:9)这似乎暗示迈克等人并非凯瑟琳的“合法配偶”,而仅是她的助手和追随者。与此同时,即将登陆的法军也被凯瑟琳视为朋友和援军,而非“阿希林”诗歌中的回归的君主与爱人:“我有一些好朋友愿意帮助我。他们现在正在集结来帮助我。”(Cathleen:9)凯瑟琳似乎孑然一身,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一互文性的空缺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叶芝无法判断时下爱尔兰政坛的“合法统治者”应该是谁,因而只好令其空缺。《胡》剧首演于1902年,剧情虽然设置在1798年托恩起义前夕,但目的显然是借古喻今,表达作家对时下爱尔兰政局的看法。那时,帕内尔突然倒台(12)留下的权力真空虽已被各种势力争相填满,但各派各有主张,谁也不复具有帕内尔“无冕之王”的至高影响力,因而无法产生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得到凯瑟琳的垂青。
但除此之外,凯瑟琳的合法配偶的空缺还可以看作是叶芝等英-爱知识分子对其精英文化主张的一种微妙表达。
与叶芝之前的剧作《女伯爵凯瑟琳》(The Countess Cathleen,1899)相比较,《胡》剧展示了叶芝对爱尔兰农民的一种新思考。《女伯爵凯瑟琳》的同名主人公是受到歌颂的英-爱贵族,是高贵且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正面人物,而该剧的农民则多以负面形象出现:无知愚昧、唯利是图、为了果腹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但《胡》剧的农民形象却是正面积极的。迈克一家白手起家,勤劳能干,心地善良,殷勤好客。凯瑟琳也以农民的形象出现,并求助于迈克等农民。这种将爱尔兰与农民联系起来的做法体现了叶芝对待农民的新看法及其文化政治主张中的新思路。很快在1902年秋天,叶芝即撰文说明“我们的运动就是要回归到人民,就像70年代早期俄罗斯的运动一样……假如你想表现路上人们的高贵,你就得描写大路”(13)。这时候叶芝已经清楚意识到农民在其文化政治主张中的分量。
叶芝持续实践这一思想,在作品中将凯尔特农民描写为与城市市侩相对立的高贵、质朴的文化代表,并最终将其发展成为文化原始主义主张(cultural primitivism)的一部分。在1907年的一篇重要文章《诗歌与传统》("Poetry and Tradition")中叶芝写道:“三种人创造了一切美好之事:贵族创造了美好的生活方式;农民创造了美好的故事与信仰;艺术家创造了其余的一切。”(14)由贵族、农民和诗人组成的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构成了叶芝的文化原始主义思想的核心。
既然叶芝意识到农民的文化重要性,那么为什么《胡》剧中凯瑟琳的真命天子不是迈克呢?这仍然可以在叶芝的文化政治主张中寻找答案。在叶芝看来,农民尽管是其文化主张中的重要一极,但英-爱贵族才是负有领袖责任的一极,并且诗人的文化融合作用也不容小觑。(15)但是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很大。在20世纪初,英-爱贵族的政治和经济根基都已经分崩瓦解;以叶芝为代表的英-爱知识分子(“诗人”)因为代表了新教少数派的精英文化而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而“智慧而单纯的”理想农民形象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一个只在梦里出现的人”(16)。或许是基于这些原因,叶芝对凯瑟琳的合法配偶做了意味深长的留白。叶芝等爱尔兰文艺复兴作家当然希望能以“文化”为纲来塑造未来爱尔兰的国家身份,即以文化而不是宗教或语言等为标志物,赋予农民、乡绅、修士、酒徒、王公贵妇等各色人等以统一的爱尔兰身份认同。这种“文化统一”(unity of culture)的政治主张一旦成功,不仅能够使得人口占少数的新教人士不被排除在爱尔兰民族进程的潮流之外,甚至还可能使得他们携带精英文化的先天优势一举成为未来新国家的文化、政治领袖。叶芝显然认为单靠农民不足以担当文化立国的大任,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迈克只被视为重要的助手,而非凯瑟琳的合适配偶。
相比“阿希林”诗歌对君王回归的强烈期盼,《胡》剧的关注点有了艺术的改动,从而有效地“遮掩”了上述留白。凯瑟琳不再是黯然神伤、空自等待的消极形象。她四处奔走,一贫如洗却仍然尊贵矜持:“如果有人要帮助我,他必须把自己全部交给我,他必须给我一切。”(8)凯瑟琳呼吁迈克(以及观众)要放弃一切个人情感与利益来服务爱尔兰。她强调“血祭”(blood sacrifice)的必要性;强调英雄行为的无上光荣,这种光荣足以令失败成为另外意义上的胜利。同时她还强调这种牺牲的回报:英勇牺牲的行为使得个人超越血肉之躯而化身为传奇与神话,被后人世代传颂与景仰。最后,观众还目睹了这种英雄式牺牲所创造的奇迹:凯瑟琳因之从老妇人变身为年轻的女王。所有这一切清晰直观地表达了革命立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一关注点的改动似乎更加契合当时的民众情绪与政治形势。谁是“真命天子”的问题似乎可以留待以后再谈,当务之急是号召民众行动起来,投身到民族解放的大潮中去。
《胡》剧引发的热烈反响似乎也证明叶芝的这一改动颇为成功。“胡里汉之女凯瑟琳”一时成为最广为人知的爱尔兰的代名词,连带着“凯瑟琳”也成为最时髦的女子名字。(17)胡里汉之女凯瑟琳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许多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尔兰人误以为真有其人。据说,1916年复活节起义时,义军领袖伊万·麦克尼尔(Eoin MacNeill,1867-1945)不得不善意地提醒爱尔兰志愿军(Irish Volunteers)“没有胡里汉之女凯瑟琳这个人,也没有黑玫瑰或可怜的老妇人,没有这样一个人召唤你们去为她服务”(18)。
女性化政治隐喻的现代接受
《胡》剧是叶芝与激进民族主义蜜月期的作品,但是仍然能够从中看出叶芝作为英-爱知识分子的文化异质性和少数派文化诉求。今天,站在21世纪回望,我们可以从凯瑟琳这样的爱尔兰女性化政治能指中读出更多的东西。诚然,如上文所述,将爱尔兰比作女性的做法古已有之,但叶芝在20世纪初的建国关键期重新挖掘这一隐喻并通过《胡》剧使之深入人心的做法和影响却大可探究。
叶芝是现代挖掘“胡里汉之女凯瑟琳”这一文学形象的第一人。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间,凯瑟琳形象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旨在去除英国的殖民影响(de-Anglicization),重建爱尔兰的文化形象与民族精神。他在《胡》剧中塑造的凯瑟琳形象摆脱了以往文本中的负面因素,(19)具有悲剧的感召力和高贵的气质。一个正面形象的爱尔兰的代名词,在20世纪初爱尔兰的民族情感极其敏感的时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还给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来寄喻民族主义理想。
但是细究起来,《胡》剧并没能有效地颠覆英国殖民话语对爱尔兰性的定义。相反,将爱尔兰喻为女性的做法延续了英帝国的文化宣传策略,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与其有“共谋关系”(20)。
乔普·里尔森在《国家性格的修辞》一文中指出国家性格的塑造常常依靠两极对立的建构。(21)英国殖民话语在对待爱尔兰问题上的两极建构就是将英国与男性特质(阳刚、健康、理性、负责、高效)、爱尔兰与女性特质(阴柔、病态、任性、放纵、低效)联系起来,将爱尔兰塑造成英国的对立面和“他者”。迈克尔·德尼在其发人深省的文章《不列颠的病妹妹:爱尔兰性与英国新闻媒体,1798-1882》中的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据德尼的分析,在1798-1882年间,英国的媒体致力于将性别话语与政治话语交织起来,形成了男性/女性、医生/病人的两极对立的主题话语。这个建构的一方是爱尔兰——不列颠的病妹妹。她终年遭受疾病或疯狂的折磨,具有十足的阴柔、疯狂的女性特质,需要不断的治疗。而另一方则是约翰牛医生,他用适当的改革措施,有时则是高压强制手段,来治疗这个棘手的病妹妹,此外,他还将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树为榜样,试图通过榜样的力量引导爱尔兰踏上康复之路。(22)爱尔兰性就在这样的对立策略中被塑造起来,成为英国性的对立面。
《胡》剧将爱尔兰比作凯瑟琳这一女性人物的做法显然对于解构这一两极对立收效不大。凯瑟琳的形象的确有别于疯狂、柔弱的“病妹妹”,具有更多的正面意义和高贵气质,但这仅仅是对爱尔兰的女性气质的修正,而非从根本上颠覆将爱尔兰比作女性和“他者”的殖民话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马伦认为凯瑟琳之类的人物形象是对殖民主义话语的“一种否认,而非解构”。(23)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反映了以叶芝为代表的英-爱知识分子身处英国与爱尔兰两种文化间隙时所必然具有的文化局限性。当两种文化均指向“爱尔兰=女性”这一联系时,英-爱知识分子很难跳出既定的框架,激进地解构这一结构。换言之,它反映了英-爱知识分子的政治“骑墙”态度。他们缺乏本土中下阶层爱尔兰人的革命激进性,更希望在现有框架内进行修正,而非激进的革命颠覆。
伊格尔顿与萨义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谈过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斗争初期所具有的相互依存性,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叶芝的文化骑墙性。伊格尔顿从互为身份定义参照的角度,认为“所有的对抗政治都是在反讽(irony)的标签下行事的,知道自己必然要寄生于对手身上”;“作为政治激进分子,我们的身份随着那些我们反对的人而塑造或瓦解。”(24)萨义德则从领导反殖斗争的文化领袖的角度,认为他们多是“部分成形的资产阶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殖民权力塑造成型的”(25)。不过,叶芝所处的文化立场更加复杂:英-爱知识分子并不像萨义德笔下的反殖斗争领袖一样天然具有“内部人”的身份。相反,由于其与天主教爱尔兰民众间存在的宗教、政治和历史上的隔阂,他们往往被看作“外人”。在一定意义上,叶芝的文化骑墙性与其身份焦虑感相伴相随,互为因果。正是在这种身份焦虑的驱使下,叶芝才会在《胡》剧的革命精神和献身号召的表层之下暗藏自己微妙的少数派文化诉求。面对日益收窄的爱尔兰民族身份界定(天主教+爱尔兰语),《胡》剧中的微妙文化诉求体现了扩大这种窄化定义的努力。
另一方面,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女性主义者对这种用女性人物来隐喻爱尔兰的策略给予了更为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延续了英国殖民话语对女性的轻视与贬低,将女性从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人降级为爱国主义欲望的象征性载体,从而使得女性成为“前他者”(爱尔兰男性)眼中的“他者”,妨碍了女性实现自己的政治与个性自主:“国家的解放暗示了男性的角色从奴隶向主人、从边缘向中心、从‘他者’向‘自我’的转变。而父权制下毫无权力的女性仍被看作‘前他者’的‘他者’,‘后殖民者’的‘被殖民者’。”(26)而爱尔兰建国之初在政治和两性关系上的保守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批评。1937年的《爱尔兰宪法》第41条明确提出保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益,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将女性的社会作用局限于“家中的生活”和“在家庭中的责任”。(27)女性的身体以及对女性身体的掌控(禁止离婚、禁止堕胎等)不再是私人问题,而上升为公共政治问题,成为以男性为主导的后殖民国家用来界定国家权力与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幸,这一局面在20世纪后半期得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的关注与质疑。爱尔兰著名当代女诗人伊凡·波兰德(Eavan Boland,1944-)在受访时宣称“如果你们还是一贯坚持简化妇女,在诗歌或戏剧中将她们描写为国家的象征,那么你们就压制了历史上一大批真实妇女的声音,她们的痛苦与复杂性构成了那个历史的一部分……”(28)
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对《胡》剧以及爱尔兰的女性化政治隐喻的现代批评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令我们了解20世纪末以来爱尔兰学界在冲破单一的、狭隘的爱尔兰身份建构(爱尔兰性=天主教+盖尔语+父权制)方面所做的努力。以《胡》剧为代表的女性化政治隐喻虽然具有很深的爱尔兰文学传统渊源,但也体现了叶芝等英-爱知识分子身处两种文化间隙场中的文化局限性。在爱尔兰的女性化政治隐喻已经淡去其历史语境和政治紧迫性的今天,更多的注意力似乎应该用来关注如何更好地体现女性身份建构的历史特异性,以及如何在爱尔兰民族身份的建构中打破铁板一块的单一性从而体现出更多的异质性。不过正如麦克马伦的恰当警告所提醒的那样,新的批评指向也要避免仅是“否定,而非解构”的做法。在新的语境下,胡里汉之女凯瑟琳不应被简单地“否定”——被改写为具有某种新的定义的爱尔兰女性;而应被“解构”——被展示为具有多样自主性、主体地位和复杂乃至矛盾的主体立场的女性主体。
注释:
①Cathleen Ni Houlihan是盖尔语,译为英语是Cathleen of Houlihan,意为Cathleen,daughter of Houlihan,因而《胡》剧又译《胡里痕的凯瑟琳》,本文选择意译。后文所列盖尔语名称,不再另行作注,直接在正文中提供英文翻译。此外,对《胡》剧的作者身份,学界存在不同看法,笔者特此说明:叶芝承认格雷戈里夫人在该剧创作过程中的合作关系,但一直暗示其贡献仅限于提供了他并不熟悉的农民语言。叶芝同时代的人也多承认这一点,因而许多文学选集在收录该剧时直接署名叶芝。See for example Seamus Deane ed,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Faber and Faber,1991; John P.Harrington ed.,Modern Irish Drama,New York & London:Norton,1991; David R.and Rosalind E.Clark eds.,The Collected Works of W.B.Yeats(Vol.Ⅱ:The Plays),New York:Palgrave,2001.但是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格雷戈里夫人在该剧中的作用可能远大于此,是叶芝名副其实的合作者。See for example James Pethica,"'Our Kathleen':Yeats's Collaboration with Lady Gregory in the Writing of 'Kathleen ni Houlihan'",in Warwick Gould,ed.,Yeats Annual(6),Basingstoke:Macmillan,1988,pp.3-31; Mary Lou Kohfeldt,Lady Gregory:The Woman Behind the Irish Renaissance,London:Deutsch,1985,pp.142-146; Henry Merritt,"'Dead Many Times':'Cathleen ni Houlihan,' Yeats,Two Old Women,and a Vampire",i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3(2001),pp.644-653.
②托恩受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张打破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壁垒,联合两派之力共建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他的这种主张与当时群众基础庞大的“联合爱尔兰人”组织(United Irishmen)的主张不谋而合。在该组织的支持下,托恩成功游说法国革命政府派兵进攻爱尔兰,自己起义接应,以期推翻英国统治,实现革命政治主张。但法军的几次来援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其中,1798年8月22日,一支1000人的法军队伍在基拉拉登陆。大批没有武器的爱尔兰农民前往支援,联合队伍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很快便于9月8日被迫投降英军。《胡》剧的场景即设定在法军登陆当天的基拉拉。迈克先是倾听凯瑟琳的召唤,接着听见法军登陆的消息,这才血脉贲张地奔向战场。可以说叶芝用文学的想象力再现了历史事件中的一个截面。许许多多的迈克在那一天告别父母,抛妻别子,投身到爱尔兰独立事业的战场中。
③W.B.Yeats,"Cathleen Ni Houlihan",in John P.Harrington,ed.,Modern Irish Drama,New York & London:Norton,1991,p.7.后文出自本剧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本文所有引文均为笔者自译。此外,本引文中“太多的陌生人”喻指爱尔兰的英国殖民者,而“漂亮的四块绿地”则喻指爱尔兰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的四个行政区划(阿尔斯特、芒斯特、伦斯特和康诺特)。绿色是爱尔兰的代表色。
④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类似作为爱尔兰别称的本土化女性名称还有Móirín Ní Chuilleannáin,Gráinne Mhaol,Síle Ní Ghadhra,Caitilín Triall,Grace O'Malley,Méidhbhín Ní Shúilleabháin,Cliona na carriage等等。See also Máirín Nic Eoin,"Secrets and Disguises? Caitlín Ní Uallacháin and Other Female Personages in Eighteenth-Century Irish Political Poetry",in Eighteeth-Century Ireland/Iris an dá chultúr,11(1996),pp.7-45.该文令人信服地追溯和分析了18世纪爱尔兰政治诗歌中对爱尔兰的各种隐晦称呼,可供参考。
⑤Mac an Cheannaí按字面英译为The Merchant's Son,此处翻译借鉴托马斯·金萨拉的英译文。他认为merchant在此处不是“商人”,而可能带有“救世主”之意(redeemer,saviour)。See Seán ó Tuama ed.,An Duanaire 1600-1900:Poems of the Dispossessed(with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verse by Thomas Kinsella),Dublin:Foras na Gaeilge,2002,p.155.
⑥该诗在未引用的前文还提到另一称呼“玛丽之子”,应是对詹姆士二世(James Ⅱ,1685-1688年在位)的一种隐晦称呼。詹姆士二世是苏格兰女王玛丽(Mary,Queen of Scots,1542-1567年在位)的曾孙。
⑦Seán ó Tuama ed.,An Duanaire 1600-1900:Poems of the Dispossessed,pp.151-153.中译文为笔者根据金萨拉的英译文翻译而成。
⑧英王詹姆士二世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被信奉新教的女婿荷兰奥兰治家族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即后来的威廉三世,1689-1702年在位)赶下台,但因其信奉天主教,仍然得到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拥护。爱尔兰天主教徒为了他甚至不惜与威廉三世一战,但是这场史称“爱尔兰的威廉战争”(the Williamite War in Ireland,1689-1691)以爱尔兰和詹姆士二世的失败而告终。之后,爱尔兰政治诗歌仍然将救赎希望寄托在詹姆士二世及其子孙重登英国王位之上。直至1745年卡洛登(Culloden)战役之后,这一希望才完全破灭。卡洛登战役在苏格兰东海岸进行,交战的双方是英军与拥护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苏格兰起义军。起义军蒙受致命打击,苏格兰人昵称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1720-1788)的义军领袖(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化装为爱尔兰女侍潜逃,此后大部分时间流亡法国。也因此,“阿希林”诗歌亦被称为“詹姆士民谣”(Jacobite ballads)。See also Lady Gregory,Poets and Dreamers:Studies & Translations from the Irish,Dublin:Hodges,Figgis,&CO.,1903,pp.66-76.
⑨See Irish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The Feminine in Early Irish Myth and Legend",in Discovering Women in Irish History,http://www.scoilnet.ie/womeninhistory/content/unitl/female.html.
⑩See Alwyn and Brinley Rees,Celtic Heritage:Ancient Tradition in Ireland and Wale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61,pp.73-75.
(11)See Máirín Nic Eoin,"Secrets and Disguises?",p.38.
(12)帕内尔的情妇凯瑟琳·欧夏(Katherine O'Shea,1846-1921)于1889年被丈夫起诉离婚,帕内尔与凯瑟琳的私情因而曝光。帕内尔从权力巅峰迅速坠落,并于1891年去世。他的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也分崩离析,爱尔兰靠议会斗争来实现政治自治的尝试失败。
(13)Yeats,Samhain,Dublin:Seely Bryers & Walker,1902,p.9.
(14)W.B.Yeats,Essays and Introductions,New York:Collier Books,1968,p.251.
(15)See also Bernard McKenna,"Yeats,Samhain,and 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Nationalism:'a supreme moment in the life of a nation'",in Irish Studies Review,18:4(2010),pp.401-419.
(16)W.B.Yeats,"The Fisherman",in W.B.Yeats,The Poems(2nd Edition),Richard J.Finneran ed.,New York:Scribner,1989,p.149.
(17)乔伊斯在其《都柏林人》中的《母亲》一篇中就曾影射这一现象,提到凯瑟琳的母亲精明地利用“凯瑟琳”一名的流行来提高女儿的知名度。See James Joyce,"A Mother",in Dubliners,London:Grafton Books,1977,p.126.
(18)F.X.Martin and Eoin MacNeill,"Eoin MacNeill on the 1916 Rising",in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12(1961),p.239.
(19)隐喻爱尔兰的女性化人物形象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所变迁。在盖尔文化时期,她多为高贵的女神或王后。但在17世纪之后,随着英国殖民势力的扩大,代表爱尔兰的女性形象堕落为无耻的妓女或不忠的妻子,抑或是一位抛弃自己的孩子而哺育外国人的坏母亲。在18世纪的“阿希林”诗歌中,她常被描述为不幸的寡妇或被虐待的妻子,忍辱偷生地等待其真正保护者的出现。See Máirín Nic Eoin,"Secrets and Disguises?",pp.7-45.
(20)Seamus Deane,"Introduction",in Terry Eagleton et al,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 Literature,Minneapolis &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p.8.
(21)See Joep Leerssen,"The Rhetoric of National Character:A Programmatic Survey",in Poetics Today,21:2(2000),p.279.
(22)See Michael de Nie,"Britannia's Sick Sister:Irish Identity and the British Press,1798-1882",in Neil McCaw,ed.,Writing Irish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Aldershot:Ashgate,2004,p.175.
(23)Kim McMullen,"Decolonizing Rosaleen:Some Feminist,Nationalist,and Postcolonialist Discourses in Irish Studies",in The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1996),p.40.
(24)Terry Eagleton,"Nationalism:Irony and Commitment",in Terry Eagleton et al,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 Literature,p.26,p.27.
(25)Edward Said,"Yeats and Decolonization",in Terry Eagleton et al,Nationalism,Colonialism,and Literature,p.75.
(26)Ailbhe Smyth,"The Floozie in the Jacuzzi",in Feminist Studies,1(1991),pp.11-12.
(27)Constitution of Ireland,Article 41.2,http://www.taoiseach.gov.ie/upload/static/256.htm.
(28)Gillean Somerville-Arjat and Rebecca E.Wilson,Sleeping with Monsters:Conversations with Scottish and Irish Women Poets,Dublin:Wolfhound Press,1990,p.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