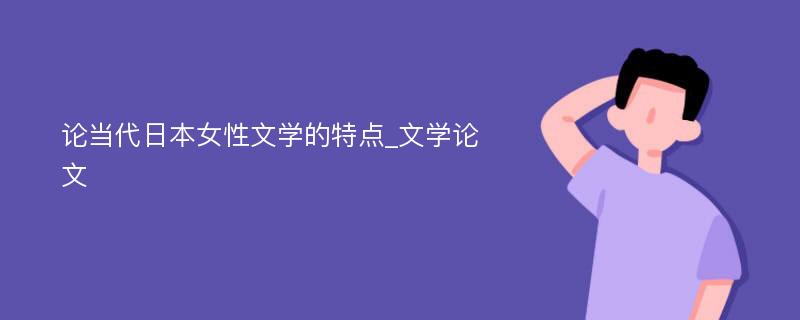
试论当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日本女论文,性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活跃于日本现代文坛的一批新生代作家大多是在80年代后期开始登上日本文坛的。有评论家将现阶段的日本文学称为“新文学”,它对日本文坛的震撼是众所周知的,它的出现对于社会制度稳定、长期以来并无重大变革的日本社会来讲或感突然。然而冰封的河面从不会停止暗流的涌动。笔者认为日本文坛的换代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新的思想理念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这一时期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体制崩溃,日本国内在经历了从“昭和”到“平成”这一年号更替的同时,走向巅峰的日本经济也顷刻间如泡沫般破碎了,这些无疑使敏感的文学人士陷入思考之中。全球化、后现代、网络等新思潮、新的知识体系给人们带来观念上的冲击,陷入一时间的迷茫状态。在传统与“后现代”、本土与“全球化”、精英与“大众化”之间,日本的文学界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新的文学态势异常活跃,继80年代初的“两村上”之后,80年代末山田咏美、吉本香蕉两位未满30岁的年轻女作家相继震撼了日本文坛。特别是吉本香蕉的《厨房》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学的“香蕉现象”。有日本评论家说“预示了新一代文学者的抬头”。[1](P8)这样一批战后出生的新生力量在90年代引领了日本文坛的主流。这些“新生代”作家受美国文化的影响较深,她们是读美国小说、看好莱坞大片、听美国流行音乐长大的,她们对漫画的熟知甚过于日本传统文化。为此这一时期的文坛“显露出与迄今为止性质不同的、新时代的文学动向,……文坛既成的文学概念、理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日本现代文学、就连当代日本亦发生了质的改变。”[1](P9)
80年代由于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日本女性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已经获得了存在的空间。女性作家们从夫妻、家庭、情爱、异文化碰撞、女性意识等多角度切入,创作出不少佳作。富冈多惠子1983年发表的《起伏的大地》、仓桥由美子的《交欢》(1988、1-1989、4)和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三枝和子的代表作《响子》系列,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高扬以及对于“性”的觉醒和追求,体现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山田咏美的《上床时间》(1985)则以其日本女人与开小差的黑人士兵间的恋情及透过女性视角体现的大胆露骨的“性”描写而引起轰动。继之发表的《杰西的脊背》(1986)则探索了无血缘家庭的新问题。李良枝因在《由熙》(1988)中成功地描写了生活在日本的韩国三代人因无民族归属所产生的孤独感和漂泊感而获芥川奖。这是生活在日本的韩国女作家首次获奖。小说揭示了文化血统主义不得不输给文化现实主义的事实。而与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同年度并居销售排行榜首的《厨房》则是刚满23岁的年轻女作家吉本香蕉的作品。这部小说先后获得海燕新人奖、第16次泉镜花奖、文部大臣奖等奖项。《厨房》以简明易懂的文体、女性的丰富感性,描述了一对平凡的年轻人面对孤独、死亡的打击,茫然、无助的心态和挣扎向上的青春体验。这部作品反映了置身在物质丰足的当代背景中,精神匮乏的年轻人终日无所适从的日常心态,因此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共鸣。这一年日本的年轻人之中兴起一股吉本香蕉热,从而被舆论界称为“香蕉现象”。80年代的女性创作也不乏以战争、历史、民族为题材的宏大叙事。曾经获得过芥川纯文学奖的两位女作家林京子和加藤幸子在80年代亦有不俗表现。林京子的《上海》(1983)、加藤幸子的《北京海棠的街》(1983),分别以中国的上海和北京为舞台,以女性的独到视角,反思战争、民族、国家问题,虽然一直未被日本文坛和媒体所重视,但战争结束60年后的今天,重读以女性经验出发审视战争责任、战争灾难的作品仍具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进入90年代直到新世纪以来,一些女作家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不断有力作发表。另有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新秀,以崭新的文学观念、新颖的文学手法在文坛崛起。女作家们以一种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学境界积极地诉说着作家自己、女性乃至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更贴近生命的真实、更具叛逆气质和鲜明的超越时代的强烈意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从题材、主题、人物到艺术表现手法均呈多元化态势。有以“性”的文化层面为轴心,旨在解构男权中心文化、表现性别差异的作家,如松浦理英子、小川洋子;有通过文本叙述婚恋、情恋瓜葛的作家,如金井美惠子、江国香织;也有像富冈多惠子、津岛祐子等反映现时代单亲家庭、无血缘家庭、未婚妈妈等家庭样态的,这是过去文本较少涉及的主题;还有如柳美里、水村美苗等根据自身体验揭示异文化撞击中现代人的彷徨、苦闷、孤独心境的等等。总括起来,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窥探这一时期日本女性文学的特质。
一、私小说
“私小说”是什么?高桥英夫说过:“以与作者几乎是等身大的人物为主人公,或者相似的角色登场,或描写该人物的日常生活、或叙述该人物的恋情和心境,这就是私小说。”[2](P10)日本的私小说是以明治时期的自然主义为源泉兴起的。关于“私小说”及它的“暧昧型”、“多义性”日本文学史上曾有过很多争论,例如:它是不是只有近代日本文学才出现的文学现象?它是日本文学史上的特殊性概念,还是各国普遍存在的概念?它是否总是在某个时代的末期出现,专门表现衰退状态的一种文体?小林切秀雄在《私小说论》中提出了“私小说”具有“末期艺术性格”的特性,并指出法国也在自然主义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出现了私小说运动,有些作家在创作达到顶点后萌生了一种愿望,他们渴望恢复自然主义思想重压下变得形式化的人性,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研究“私”(自我)。他洞察到私小说的特征,高度概括和小说“私”是“充分社会化的私”。对于如何理解小林切秀雄的“充分社会化的私”,高桥英夫精辟地论述道:“私小说是当一个时代的文化达到全盛、成熟后,针对因超越顶点而变质的人性,伴随着将人性再次净化、以期恢复其最初的坚固、纯粹而进行的运动中出现的。”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私小说的“私”是“充分社会化的私”,一个好的私小说作者一方面以“私”充斥作品中,将“私”的经历、感受、思想变化的心迹公睹于书,另一方面,要求作者完全放弃自我、剖析自我,达到一个透明的无“私”境界。也就是说:一部好的私小说应是处于“私”和“无私”的两极。这就要求作者做到客观、冷静。一般说来女性是感性丰富的群体,能否做到客观、高度透明地剖析自我,从而写出高质量的“私小说”?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在日本文坛引起过争论。
由于篇幅的关系,对于女性作家能否写出高质量的“私小说”作品,这里暂不赘述,留待以后做一番认真的论证。在这里,只就两位年轻的90年代较有影响的“私小说”女作家来略谈一、二。
1994年对笙野赖子来说是一个丰收年。这一年她分别以《时光隧道·工业地带》和《二百年祭》获得三岛由纪夫奖、芥川奖。同一年内荣获双奖,在日本文学史上也不多见。由此她成了舆论界的焦点,而实际上1981年笙野赖子就曾以小说《极乐》获得过群像新人奖。对笙野赖子舆论界评价各异,有赞扬她的小说是现在不多见的体裁新颖的纯观念小说,也有批评她的文章几乎不像小说体裁,对作品中冗长的观念说明也多有指责的声音。在这篇作品中、主人公是一个居住在古都洛阳的画家,幼小时受冷落,一心想把自己对周围的憎恶画成一幅地狱图,当多年的努力即将完成时,他沉浸在幸福感中,某晚他猛然觉醒,原来一直以来在无意识中画的竟是一个贪图现实安逸的自己和极乐图。从此他从由憎恨网织的幻觉中醒来,开始注意身边的现实世界。他深刻认识到自己是从极乐境界坠落到现实的人。“由于某个契机得以与日常的、现实的事态相接触,从而启动了观念的现实性”[3](p112),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笙野文学世界的特质。主人公从此真诚地与现实这个“地狱”相碰撞,他“动真情地哭、认真地生气、大动肝火地诅咒”,认识到这个冷漠、孤独的世界也还有值得自己认真生活的价值。在小说中主人公往返于“妄想”和“现实”之间,而这往来之间产生的纠葛正是主人公活下去的原因所在,而这“妄想”和“现实”之间产生的纠葛也正是作家想要解决的课题。清水良典在《极乐〈笙野赖子初期作品集Ⅰ〉》的题解《地域皇帝的逆袭》一文中评论说“这部作品是笙野将等身大的‘我’作为主人公登场的最初作品”。
这位纯文学的女卫士于1998年挑起了历时一年的和贬低纯文学势力的辩论,她自称是“堂吉诃德”,发表了一系列如《太阳的巫女》《东京妖怪浮游》等文章,有力地维护了自己的观点,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同时她的作品被评论界认为是“新难解派”而加以否定。1991年获野间宏文艺新人奖的《什么也没做》是她在文坛奋斗10年后出的第一部作品集。1993年的《无处安身》描写了泡沫经济时期‘我’因一心写小说而无经济收入、依靠母亲的援助度日,无钱交房租,居无定所,在到处找安身之处的过程中,写着‘小说家租房子的小说’,可是找不到适合“我”的空间,加之内心中那份“被赶了出来”的失败感,形成了一股压在“我”精神上的重负。虽然我最终搬到了一个院子里有水池的建筑里,但仍然觉得无安身之处……以“我”的日常生活琐事,家常描写,真实地再现了一个现代都市中的年轻人平庸、孤独、为生存奔波的无奈心像。自说自话、“我”充盈着整个文本,而这个“我”几乎约等于作家的“我”。高桥源一郎称她的作品为“以‘我’为主人公对世界进行素描”的‘私小说’。作品成功地刻画了往来于真实与虚幻之间,在大都市的整齐划一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间漂泊,找寻属于自己的家园的浮躁、永无满足的现代都市人的心迹。柄谷行人将她的作品定位为‘私小说’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力图以真实的世界构造来替代狭窄、贫穷世界”。[4](P111)
水村美苗在1990年《续明暗》发表后于1995年又发表了新作《私小说—FROM LEFT TO RIGHT》并以此获得了野间文艺新人奖,这是以作者长达20年的美国生活为基础创作的,文如其题“私小说”。
作品以《FROM LEFT TO RIGHT》为副标题,因为是英日文混合体,所以采用横版(从左到右)。由于日本语言是假名夹汉字的表记特点,加之文化传统的因袭,小说采用竖版印刷这是一种不成文的规范。《私小说—FROM LEFT TO RIGHT》打破日语小说竖版印刷的常规,单就书写方式来讲就是一种迄今未有过的大胆的新尝试。就此小森阳一评论说:“水村美苗的横写版的英、日文小说《私小说—FROM LEFT TO RIGHT》(新潮社)获了奖。水村的实践打破了‘日语小说’必须是只用日语竖版书写这个自明之理。”[5](P40)采用这种体裁作者并非为了标新立异。仅仅这个标题就包含了太多的“生活”在美国与日本两种文化夹缝间的感慨、无奈和彷徨。表达了作者与母语切断20年后,意识深层里那种对母语文化的怀念和守望。这样一颗孤独的心,如果不是亲身体验过在异文化撞击中认知文化身份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和产生共鸣的。在长达20年的美国生活中,对水村美苗来说能让她感觉到日本的存在的便是铅字印刷的《日本语》了。对美国人来讲,她是会说英语的“日本人”,而对日本人来说,她又是个会说日语的“美国人”。环境使得她不得不在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的边缘境地生存。
《私小说—FROM LEFT TO RIGHT》表达了水村美苗对女性生命本体困境的理解,把曾经是完全压抑与有意忽略了的女性复杂微妙的心理细致地显露出来。作品注重生活在异文化夹缝间的主体生命的体验,以女性话语方式诉说着对历史、人生、生命的感悟,作品中那种深彻的惆怅和孤独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笙野赖子一直耕作于“纯文学”这片净土。这种精神实属不易。水村美苗的《私小说一FROM LEFT TO RIGHT》内容涉及战后50年,对于日本女性文学的历史来说,也应该是值得纪念的大事件。显而易见,私小说和这一时期日本女性文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二、身体叙事
日本女性长期处在在男权菲勒斯机制控制下,一批新锐女学者首先在对历史的反思及对西方女权研究中找到了女性话语切入点。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意识的“身体叙事”构成了这一时期日本女性书写的另一道独特景观。这一阶段隐含在女性文学文本中的反叛色彩更加鲜明,女作家们在文本中渗透出的日益苏醒的性别意识和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也是前所未见的。尽管她们所表现的风格、角度、程度各异,然而,都以自己的最具个性的方式反叛着男权中心的既定传统,张扬着女性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较早高扬“身体叙事”大旗的是年轻女作家山田咏美,她因发表于1985年的《上床时间》获得第22届文艺奖。以其大胆的性爱描写引起文学界及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论,给当时的日本文坛带来一场不小的地震。当然,对此我们应持有独立的看法。
松浦理英子继《本色女人》(1987年)后,1994年因《拇趾P的修炼》获女流文学奖,引起轰动。作品中将“性”的构造分解,展开了作者对生物的性别差异及社会、文化产物的性别差异的剖析。在“性差”的分解上,从这一点上说,可以说是一部前所未有过的作品。她的作品完全打破了两性爱的二元定位,主张表现“性”的多元性,小说多以描写女人间的同性爱见长。动摇了将“性器的结合”视为性爱的正常形式的“制度的性”,设定了身体器官各具特征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登场,表现了一种变异的性。以年轻女性的感觉描写出超越婚姻的性,或者超越性器官的性关系。以文化层面的“性”为轴心,反思二元论的批评方法,批判由男女构成的“制度的”、“规范的”性论观,选择同性结合,“使得恋爱中出现的矛盾纠葛摆脱了男性优越的社会背景。”
1991年1月小川洋子的《妊娠日历》获104届芥川奖。20多岁的年龄就获此大奖,这在战争结束以来是第一人。这部作品描写妇女怀孕后身体各个方面上的变化,这是一种身体的解放。小川洋子所表现的纤细的描写风格、独特的感性绝无雷同。所以说她开辟了一种文学的新的可能性。其作品的特征是将人与人的关系转移到身体器官上来描写,将难以琢磨的男女关系转移到手指上来,通过器官、反映、感觉等感性的想象空间,刻画出比人和人的瓜葛更深层次的内容。同年发表的《余白的爱》,表现了作者对生与死的独特理解。“死亡、孤独”是她切入现实、品评人生的一个独特视角。在这篇作品中,她透过这个“独特视角”反观现实的情感世界,审视故事的进展,颇为新颖。
1995年,女作家们敏感果断地与时代的气息相契合,在这一年的年末,小池真理子的小说《恋》获得了直木文学奖。小说是以1972年震撼日本全国的“浅间山庄事件”和同时发生在避暑胜地轻井泽的“猎枪杀人事件”为线索展开的。她将时代的影子浓缩在一个大事件中。作者处理的手法很巧妙,不是单纯地将“浅间山庄事件”作品化,而是将时代、事件作为舞台,将“恋爱”这种极常见的普通的素材为脚本,让身陷窘境的主人公一个个上场、尽情表演、自由发挥,从中透视出很多社会现象,可说是一部反映时代足音的佳作。
另外,1993年初现文坛的村田喜代子发表的《花野》,则反映了更年期主妇的心态。写一个有家庭的主妇,抱着走出家庭的冲动和强烈愿望,不停地找工作、更换兼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主妇萌生了“放荡”的愿望,小说描写了一个主妇主体观念觉醒、萌生独立意识却又迷失方向,徘徊、淹没在现代社会浊流中的过程。作品体现了20世纪末日本现实社会的时代性和特异性。1994年,村田喜代子突然改变以往的写作风格,创作、发表了《蕨野行》,以独特的文体再现了“丢弃老人”这个古老的传说。
富冈多惠子的《水上庭园》(1991)、多和田叶子的《狗女婿》(1992)、高树信子的《水脉》(1994)等都从不同的视点描写了女人对“婚姻”与“性”的动摇、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身心承受的压力和对未来的迷茫。
深入解析当代日本年轻女作家的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她们不囿于女性经验的表述和女性欲望的彰显,更有对传统的深刻审视、对父权中心文化的解构以及对艺术的独到理解和大胆探求。解构的意义在于重建,日本女性文学自诞生起,就旨在建构一个独立的、充满了性别特征又超越性别对峙之上的艺术世界,它的建构不再归属于性别权力之下,而是在一个多角度、多层面的基准上进行的。性别写作的确立,正是为了表现两性的差异性,以丰富的、活生生的个体来对抗长期被压抑与被遮蔽的事实。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它也开拓了更广阔的艺术天空和对人生、对人性的更真切的探索。女作家的写作态度是审慎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社会,她们每个人的创作个性都应受到我们应有的尊重。她们的创作风格与“黑色幽默”相近似,透过一些荒诞的细节表现一种理念。当然,对于这些细节的描写我国读者应本着客观、全面的态度,结合各国的文化背景加以阅读才能正确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意。
三、“言语论小说”
致力于打乱传统的小说语言规范,在话语表现上独树一帜,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日本女性创作表现在语体上的一大特征。一些作家刻意背离惯常的话语表达、语体叙述模式,以此向男权中心话语宣战。80年代的吉本香蕉、俵万智分别以小说、诗歌的形式开创了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的女性话语文体,轰动文坛。进入90年代后,一些女作家通过文本表达自我、张扬个性的意识更趋强烈,如多和田叶子、荻野安奈、笙野赖子、津岛祐子等。她们的文本在语言表象方面各具魅力,正是西方女权主义关于女性话语言说的一个文本实验。
荻野安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法国文学研究家,她的小说语言诙谐、幽默,具有时代感的流行新语与传统气息浓烈、地域特色鲜明的关西方言相融合,加之作家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夹杂些历史、哲学、电影、绘画、电视剧、漫画等特色语言,营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觉上的听觉效果”。1989年获得文学界新人奖的《我的母亲喝茶》发表后,作家河野多惠子评价其“极尽了用视觉听方言的极致、周到纤细的文章感觉也让人赞叹”。
作家本人将打破规范、开拓小说空间作为努力的目标。无论是《有机体》(1990)还是《古事记外传》(1992)、《桃物语》(1994)等都体现了她打破传统语言规范,建构全新的语言秩序的大胆尝试。然而,过度地追求语体的变化也给她的作品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文学评论家与那霸惠子称她的文体为“荻野版创作方言”。
与荻野同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多和田叶子则将自己常年旅居德国,生活在异文化之中的生命体验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身体体验,形象地表述出来。她对语言、文体表象也有自己的一番独到见地。在文体中努力“打破流畅的日语、漂亮的日语”。下决心做自己的“语言游牧民”。在《字母的伤口》(1993)、《三人关系》(1991)、《无精卵》(1995)等作品中、她大胆尝试将一些语言的游戏和奇怪的形象塑造相结合,以实践自己的理论。在《拉丁字母的伤口》中用日语表达两种语言的摩擦,从而构成一个故事情节,变形的语言、独特的表达使读者感受到在异文化碰撞之中的那种莫名的濒临崩溃的意识状态,加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度。《无精卵》在发表后,得到了多方好评,认为这部书充满了“身体感觉和语言感觉巧妙融合”的多和田式的魅力。
发表于1993年的《狗女婿》将民间故事和现代化的住宅小区社会结合,描绘出虚幻、真实的现代社会。不规范的语言表达恰到好处地烘托了虚、实之间的小说的氛围。有评论说这篇小说动摇了现有的规范小说空间,可称为一种“全新小说”。
而读着笙野赖子的《天国·斯拉茨》(1997),就像是在同时阅读几部小说,变幻的语言是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作品描写的是以他人的不幸为乐的公寓管理员的种种恶作剧,独特的话语结构与小说反映的主题相得益彰,为了衬托管理员的令人憎恶的本性和深化主题,作者选择了充满夸张、超出常理的表现方法。
如果说80年代的日本小说语言已经迈向了近代小说解体之路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女性文学全新话语空间的打造,则大大地加速了小说语言解体的步伐。女作家们的创作体现了摧毁男权话语体系,解构既有的语言模式的大胆尝试以及构建女性话语空间的愿望。然而,是否打碎了既有的话语规范就能够建构女作家们心中所向往的女性话语模式?既有的话语规范是否就等于男性话语体系?女性文学向何处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包括女性作家们也在继续探索阶段,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纵观当代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女性文学的创作园地,可谓千姿百态。女作家们冲破战后文学50多年的传统篱笆,无论在题材上、文体上、语言上、手法上均有重大突破。如“私小说”领域,在承继了传统“女流文学”的基础上取得了可喜成绩。应该指出的是,从早期到现在,女性文学(女流文学)中从来就不乏优秀的“私小说”。如早期女流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宫本百合子的《风知草》等都是享有很高赞誉的好作品。笙野赖子、水村美苗等也是巾帼不逊须眉,她们的作品也会令将女性放逐到私小说之外的吉田精一、平野谦氏刮目相看吧。在“身体叙事”和“打造女性话语”的创作实践中,90年代以来的创作在80年代的基础上实现了很大突破。由于日本女性长期承受的来自男权的压迫比较深重,女性解放的步伐较西方慢、又不够彻底,故此表现在文本中的“身体叙事”在“性”的描写上表现得大胆泼辣,虚实相溶。松浦理英子、小川洋子、多和田叶子等作家在80年代反映“性觉醒”、“性期待”等女性意识层面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对女性经验的大胆披露和对女性心理的细微诠释,构成了对男性权威话语的消解与颠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日本现代女性作为一个长期被压抑的群体进入社会历史、由边缘向中心的强烈要求和真挚企盼。并且通过她们的努力,广大女性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现实。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孕育了这一时期的日本女性文学。进入世纪末以来日本文坛常有舆论感叹说:“好时代过去了,现在没有人能写出好小说了”。我认为,我们应当综合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去评价文学作品的优劣。这一时期的日本女性创作总体来看应是质量高、独创性强、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充满活力的,对此我们应以纯学术的视角给予正确的评价。那么,日本女性文学向何处发展?在评价优劣之前还是要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结合日本社会实际去动态地把握日本文学发展的实际,在此基础上我们只能以准确、客观的眼光注视它的未来,当然对于可以肯定的东西,在认真分析之后应予以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