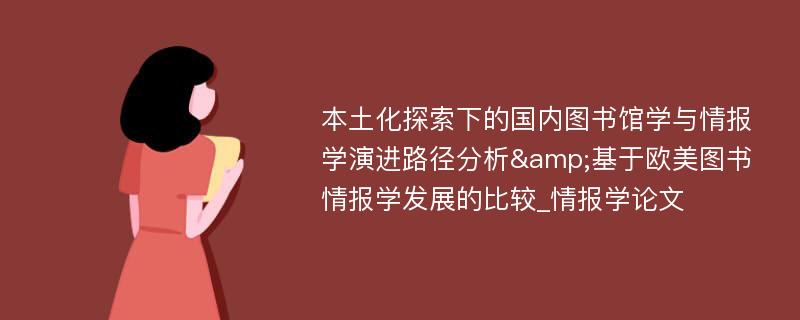
本土化探索下的国内图书情报学演变路径探析——基于欧美LIS发展的对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探析论文,本土化论文,路径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土化”探索一直是国内图书情报学界的目标。早在1925年,梁启超先生就曾提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1]。进入21世纪,国内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愈发体现出借鉴西方LIS理论与方法基础上的新本土化努力: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知识化”趋向日益明显;中国环境下图书馆职业的再思考;经济发展需求下情报学研究中以竞争情报为代表的情报价值的凸显。另一方面,植身于社会大系统中的图书情报学发展会受到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美国图书情报学发展深受技术因素影响,欧洲图书情报学则具有深厚的文献工作传统,我国图书情报学本土化探索又有哪些独特的路径表征?其形成环境如何?本文试图用历史的视角对国内LIS演变路径进行特征的归纳和阐释,并借此提出对国内LIS未来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1 欧美LIS发展的特征分析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分野、交叉渗透和不断整合的过程。国内学者于良芝、王锦贵等人都曾从历史角度论述过欧美LIS发展的特点[2-4]。本文在综合分析国内外资料后提出,欧美LIS发展具有三个核心词(library science,information science and documentation)、四个特点(重视学科历史研究、以哲学为其学科发展基石和基本方法、对技术要素的理性思考以及与社会对学科发展需求的及时反应)。
1.1 三个核心概念
在欧美LIS发展过程中,library science,information science和documentation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核心。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在欧美LIS学科体系中最先发展成熟起来。1926年,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设立博士项目,图书馆学成为高等教育机构中一个研究型学科,标志着作为科学分支的现代图书馆学形成。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影响下的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包括:阅读行为理论、图书馆管理理论(包括藏书建设理论)、图书分类编目理论、图书馆史等[5]。具有美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人文和社会科学传统逐渐形成。与美国相比,虽然是欧洲图书馆学家马丁·施莱廷格最早在教科书中引入“图书馆学”概念[6],但在国际书目工作协会改名并先于美国开始使用“document atom(文献工作)”的影响下,欧洲图书馆学更具有目录学和文献学的研究倾向。“documentation”被认为是一个用来描述被我们今天称为信息存贮和检索的活动的中立词汇[7],不仅关注文献的物理处理,更关心文献中蕴含信息的利用[8]。“information science”起源于由于科学和技术文献的过渡增长而引发的信息需求实现问题[9]。从1945年布什发表“as we may think”到1968年美国文献工作协会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协会,“information science”在美国最终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浮出水面。
时至今日,library science,information science和documentation又从最初的独立走向融合,具体变现为“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或者是以“documentation science”统领原有的library science和information science[6]。
1.2 四个路径特点
1.2.1 重视学科历史研究
从历史视角展开学科研究一直是欧美LIS研究的传统。芝大图书馆学研究生院将图书馆史纳入研究范畴,巴特勒本人更是将目录学史作为图书馆员的基础研究内容。尽管情报学历史研究相对于以图书馆机构史为传统的图书馆史研究而言较为肤浅和非批判性,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情报学开始关注1945年以前的情报工作,不仅关注技术,还关注理论的历史沿革,并唤起了情报学研究的历史意识[9]。欧美LIS的历史研究主要成果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试图用历史方法分析情报学起源问题,支持90年代后情报学和图书馆学的融合。但Hjtrdand B.指出“documentation science”能更好地表达情报学的认识论范式,认为应该用“documentation science”来统领现有的图书情报研究[6]。在遇到学科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时,欧美的LIS研究者倾向于从学科发展历史中寻求支持和论据。
1.2.2 以哲学为学科发展基石和主要方法
欧美深厚的哲学研究传统为图书情报学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支持。研究者们试图用哲学的思想和方法来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包括基本理论的阐释、服务理念和技术的哲学解释。Brookes B.C.提出将波普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11],Nitecki J.Z.以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in Retrospect为题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基础的若干问题进行综述,包括图书情报学哲学基础研究的目的、意义、哲学层面上的图书情报学的基本概念界定和元理论的阐述[12]。从哲学角度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理论和概念基础,被欧美研究者认为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以及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冲击下保持理论体系不变的保障。
1.2.3 对技术要素的理性思考
Saracevic T.和Hjtrland B.曾表达对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学中地位的理性思考。前者认为“与信息技术的密切相关性”是情报学三大特征之一[9],后者则提出“一门学科必须由其研究对象而不是使用的工具来界定”[6]。欧美研究者承认信息技术在促进情报学出现和发展的同时也蒙蔽了研究对象本身,连Saracevic T.也提出情报学面临的最大危险——忽视用户和人,只专注于技术[9]。
1.2.4 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及时反应
欧美LIS研究一直以社会需求为学科发展的指南。美国图书情报学著名杂志Library Trends的论文就多以社会实践为内容,比如Current Trends in Law Libraries、Libraries and Society:Research and Thought、The Human Response to Library Automation、Collection Development in an Electronic Environment。另一方面,欧美LIS研究者在研究中融入实证方法和理念,其定性研究方法也从数据的搜集方法(问卷调查等)转向数据的描述、解释、分析方法,其中代表包括话语分析法(discourse analysis)、框架分析法(frame analysis)、对话分析法(conversation analysis)等[13-14]。20世纪90年代始于医学研究领域的“寻证图书馆学(evidence based librarianship)”更是代表了图书情报学实证理念的最新进展[15]。
在信息技术和社会发展需求双重引领下的欧美LIS发展道路通过不断反思、调整,努力将图书情报学与社会环境和相关学科紧密结合,并试图寻找自己的立锥之地。从图书馆学发展到图书馆情报学(LIS),从图书馆学院发展到图书馆情报学院以及现在的iSchool运动,寻找图书情报学的有机融合已经成为欧美LIS发展的最突出特点。
2 国内图书情报学的本土化路径分析
我国图书情报学的“本土化路径”真正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具有三个特征(以古典文献学和目录学为主的历史研究传统、价值导向的事业与职业阐释、本体导向的学科体系研究)。
2.1 国内图书情报学本土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国内图书情报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标志性事件包括:《图书馆学基础》出版;1984年中国图书馆协会杭州会议的召开;“知识交流”思想[16]、“文献交流”[17]、“情报交流”[18]、“文献信息交流”[19]等新的本土化概念相继出现。情报学方面,开始学习和探讨“三个世界”理论、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20]。20世纪80年代,对图书馆学社会功能研究范式的认同以及对西方情报学元理论和检索技术的引进促成了我国图书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形成,体现出对欧美LIS理论消化吸收基础上的本土理论实践基础的建立。该阶段背景元素包括:(1)国内图书情报学基础理论的空白和实践活动的迫切需要是这种本土化模式的外部推动力;(2)欧美图书情报学理论的研究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对前苏联目录学思想的本土化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处于弱势;(3)此时本土化的内容是对确立图书馆社会地位和提高情报工作技术水平有利的理论和技术。这种“引进来”的模式对图书情报学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并逐渐延伸到管理学、知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为新一轮的本土化高潮奠定基础。
20世纪90年代国内图书情报学本土化路径的最突出特点是“信息化”。标志性事件包括:90年代中期国内图书情报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的普遍改名;“信息资源管理”成为图书情报界的焦点;电子图书馆所代表的网络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成为实践主流。该阶段背景:(1)美国图情界联合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展开的“美国记忆”项目和数字图书馆先导计划,以及信息社会发展环境下的欧美图书情报学院相继改名,是这一阶段本土化的最大外来推动力;(2)1998年本专科专业目录调整使得国内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和教育走上了一条完全“本土化”的道路,也为国内图情档一体化的发展设置了政策性障碍;(3)信息资源核心地位的确立,完全改变了国内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视野,使得在教育体系中处于分割状态的图书情报学在研究空间上出现更多交叉和重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图情档一体化发展。
21世纪初国内图书情报界对知识、事业和职业的思考使得这一阶段的本土化探索具有更多的创新色彩和职业关怀。标志性事件包括:“知识论”、“知识基础论”、“知识社会论”、“知识交流(传播)论”、“知识组织论”、“客观知识论”、“公共知识论”、“知识集合论”、和“知识资源论”,以及情报学的知识化趋势等新观点出现。另一方面,“职业化”导向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即对馆员自身价值的追求、职业存在依据、职业使命的追问[21]。例如:《图书馆学导论》[22],《论重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体系》[23],《面向职业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24],构建面向职业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25]。该阶段背景:(1)国内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者开始反思完全的“信息化”对图书情报学学科发展的误导,在新的逻辑基础上探索学科体系成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必然;(2)来自于管理学的知识管理理论为图书情报学注入新的血液,国内图书情报学开始从管理的视角、企业的视角审视自身的活动和为之提供服务;(3)国内图书情报界开始审视学科理论体系、学科教育体系和职业体系之间的关系,试图从职业和精神的视角出发改变国内图书情报活动的社会认知和学科地位,重塑图书情报学在中国国情下的新地位。
国内图书情报学的本土化探索在这三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学科建设背景下体现出了不同特点,并从最初引进介绍为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到自我探索的突破,最后实现在自我价值审视的基础上进行外来理论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但审视国内图书情报学本土化探索过程可以发现:“本土化”对象更多的是理论、观点和技术,缺乏有益的研究传统和方法,例如历史的、哲学的和实证的思想,如果把这些欧美LIS研究传统的精髓进行有选择的本土化,那么我们的LIS发展道路会具有更多的哲学思辨性、科学理性和社会性。
2.2 国内图书情报学演变路径的三个特征
2.2.1 以古典文献学和目录学为主的历史研究传统
1903年,奥特莱特在《目录学和文献工作》一文中首次使用“documentation”表示向情报需求者提供文献或参考工具的过程[26]。我国悠久的藏书文化使得目录学很早就出现在古代学者的视野中。诞生于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各类目录,使得古典目录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历史色彩。古典文献学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的大文献学家大多也是历史学家。作为古典文献学的最初形式,校雠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书籍形式决定了文献学是在书籍整理活动中形成的与图书密切相关的各种学问的总称,其研究对象也是独特的历史文献。因此,这种由于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决定的历史色彩又与欧美图书情报界的历史研究不同,我们重史实和史料,欧美重学科历史的规律及其原因。
2.2.2 本体导向的学科体系研究
国内本体导向的学科体系研究通过揭示实体的本质来解释和说明问题。据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90年代末有五六十种之多[27]。柯平等人根据文献调研也发现在各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论文占极大比重[21]。近期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知识资源”说[28];“知识集合”说[29];“信息资源”说[30]。西方近代图书馆学的“科学理性特征”,芝加哥图书馆学研究生院推崇的科学实证原则,以及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这个客观实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倾向于找到学科研究基点,试图通过明确学科基点和学科体系来指导实践并确立其科学地位。但国内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却表明:我们似乎并没有掌握西方LIS的理性和实证的精神实质,反而把表象化的“机构”和抽象化的“对象”作为关注点。我们不仅反问:随着图书情报学自身的边界、图书情报学与相关学科的边界的逐渐泛化,本体层面上的工作是对象和边界?抑或是核心领域。
2.2.3 价值导向的事业和职业阐释
如果说本体导向的学科体系研究是国内图书情报学研究从最初延续至今的风格,那么,价值导向的事业和职业阐释则是21世纪初出现的新的研究特征。傅荣贤认为价值论范式是由探寻“图书馆是什么”到“图书馆怎么样”[31]。例如:图书馆和情报机构的社会认知、图书情报人员的职业状态,以及图书情报事业的制度化、人性化和主体化发展。国内图书馆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中角色与定位的调整、情报服务在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中地位日益提升都促使图书情报研究者开始走出纯粹本体研究的藩篱,开始探讨图书情报事业社会生命和职业生命的延续和提升。这种新话语范式的出现将有利于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
3 比较与思考
毫无疑问,强调国内图书情报学研究与欧美的比较会导致忽视自有特征和环境,进而造成盲目西化。具有悠久传统的我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研究是国内图书情报学有别于欧美的最大特色。只是,现有研究究竟在此投入了多少注意力?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和谐社会的全面转型促使图书情报机构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服务和职业,新的本土化领域又有哪些?
注重学科历史研究已经被国内图书情报界所认识,但其目的和范围又是什么?我国近代图书馆出现之前的图书史和藏书史研究只是注重史料,而历史应该为今天和未来的学科发展方向提供路径参考。单纯的文献综述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思辨性的、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分析应该受到重视。
对实证方法的重提是近年来国内对LIS学科研究方法思考的主要表现。在探讨图书情报机构新的职业认同和社会地位时,社会学的、质化的研究方法应该被容纳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中。
事实情况是:随着人们对“情报、信息”术语的理解,国内情报学研究者开始在汉语语境下探讨“information, intelligence”对于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32];国内出现对情报学认知层面、社会层面和研究路径的争论[33]。另一方面,国内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是否融合的问题日益关注,2008年11月召开的2007-2011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重申“将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作为一个学科群来建设”[34],探索新的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经历了30余年的图书情报学本土化探索之后,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情报学学科体系和教育模式应该在不断地思考、重组和调整中建立。
收稿日期:2009-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