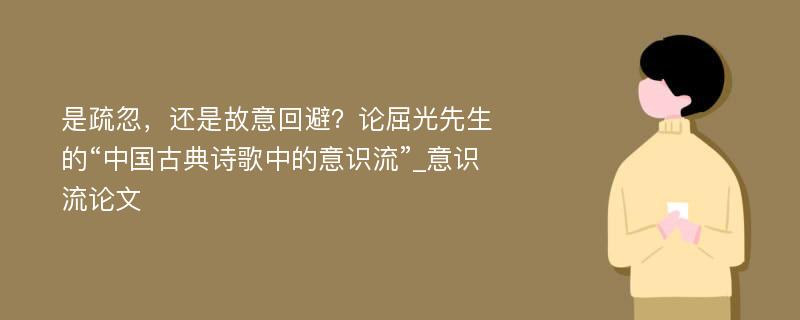
是疏漏,还是有意回避?——与屈光先生《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流论文,疏漏论文,中国古典论文,诗词论文,屈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3)03-0035-03
有幸拜读了屈光先生的论文《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颇为屈先生的学理精神和不懈的求同意识所感动。在文中,屈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意识流无涉”的观点提出质疑,并从西方意识流文学产生的理论源流,到意识流文学的文本实践,再到意识流文学文本的理论反思三个紧密环节,较系统地疏理了西方意识流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状况,“并运用比较的方法,以大量的事实从逻辑和学理两方面充分证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识流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为精妙的、相当完备的意识流技巧和意识流形式”。应该说屈先生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它不仅为我们观照中国古代文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更为我们走进中国古代诗词幽深的意境开启了一条神秘的通道。然而,屈先生在用西方意识流理论审视中国古代诗词是否存在意识流时,却存在明显疏漏亦或有意回避。
屈先生在论及西方意识流文学产生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时,重点观注了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及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对意识流文学产生的意义。尽管屈先生也言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于意识流文学的心理学意义,但却一笔带过。既然屈先生也承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意识流文学的生成具有心理学意义,那么意义何在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应疏漏更不该回避的问题。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对心理学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直接催生了现代心理学的产生,而且对意识流文学的生成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应该说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是一个独特而庞大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有其相应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有其特有的概念和论证方式。其理论体系中最有建树并对心理学和意识流文学最具意义的是两个命题的提出:无意识和性本能。“无意识”是弗氏学说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虽非弗洛伊德创造,但却是他将这一概念提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并赋予它新的涵义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命题是:心里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前常以为心理的就是意识的。意识好像正是心理生活的特征,而心理学则被认为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然而精神分析却不得不和这个成见相抵触,不得不否认‘心理的即意识的’说法。”因此,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显意识、前(潜)意识和无意识,并进一步认为显意识和前(潜)意识可以相互转化,而无意识却不能上升为显意识或前(潜)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的意识(即显意识和前意识),而精神分析则认为人的意识过程在其全部精神过程中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就像大海里的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是能够被人发现的,但却只是整个冰山的一小部分,而藏在水面以下的则是冰山的大部分,无意识就像冰山中水下的部分,在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这种无意识正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弗洛伊德认为,“对于无意识的心理过程的承认,乃对人类和科学别开生面的新观点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在强调“无意识”的基础上,弗洛伊德进一步建立起他的“人格结构”理论。按照人的心理过程的三个层面,人格结构亦由三个层次构成,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的冲动和抑制,构成了人的一切心理活动的最本质的深刻内容,而这一切大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其中“本我”的原始本能冲动构成了最活跃的动力因素。因为“人类最深刻的本质在于初级的、自发的本能动力,这些动力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它指向一定先天需要的满足。”
“性本能”是弗洛伊德的又一重要命题。弗氏指出:“第二个(性本能)命题也是精神分析的创见之一,认为性的冲动,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的冲动,对于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弗洛伊德在其早期著作特别是《梦的解析》、《性学三论》中,对“性本能”作了大量的论证。他认为人在梦中得到满足的愿望不是一般的愿望,而是隐藏在无意识中的种种欲望,主要是性的欲望。因而,无论梦是否与性欲有关,都包含着性的意义。弗洛伊德在他后期著作中对“性”的理解更为宽泛。他认为,一个人从出生到衰老,一切行为、动机都具有性的色彩,都受性本能冲动的支配。他甚至还提出,小至个人发展、心理失常、创造活动等,大到社会习惯、宗教、制度及人类各种行为,都出自性本能冲动的动机。应该说,弗洛伊德的全部学说中充满着性的内涵。
从前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无意识”和“性本能”两个命题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意义,更不难窥见作为精神分析理论核心的“无意识”和“性本能”两个命题对于意识流文学生成的心理学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屈光先生却将之轻易地回避了。既然屈先生也认为意识流文学(主要是指“意识流小说”)是指描绘人物的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那么,这种人的意识流动状态就应既包括清醒意识,更应包括无意识。而这种对人的“无意识”的心理过程的文学关注,自然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发现。意识流小说着力表现的是“心理真实”,而这里的“心理真实”又是指什么呢?它“不是传统小说所描写的合乎逻辑的、可以被理解的、有意识的内心活动,而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变态心理”。我们已经了解,无意识其实就是性本能。“文学创作就是要深入无意识深处,写出人的性本能和原始冲动,写出人心内部的黑暗和变态。”应该说,“意识流作家用自己的小说创作来实现和印证弗洛伊德的主张”,因此,“意识流小说所描写的内心生活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无意识活动,是一种混乱、恍惚、畸形、变态的动物本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对任何文学流派的认识和考察,在观注其创作技巧(怎样表现)的同时,更应认识和考察其有何独特的文学精神(表现什么),因为“创作精神是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它制约着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应该说,意识流小说“心理时空”叙事结构的确立,以及“内心独白”、“感观印象”、“自由联想”等技巧的大量运用,都源自无意识和变态心理这一特定的表现对象。
既然“无意识”是意识流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那么屈先生为何将之回避呢?我想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时代,心理学尚处于传统心理学的时期,因而“无意识”是被遗忘的。诚然,正如屈先生所言:“意识流是人的意识规律,体现的是属于不分时空的人类本身的心理特质,……我们只能说,西方意识流小说家在理论家阐明了这一规律之后有意识地强化运用了这一发现,却不能说,中国人(包括古代的中国人)的意识活动不遵循这一规律”,但是,文学对“无意识”的自觉开掘只能出现在“无意识”觉醒之后。因此,中国古典诗词中尽管也涉及对人的心理过程的表现,但只是停留于”显意识”或“前(潜)意识”层面,而不可能进入更为幽深的“无意识”领域(当然,或许存在,但也是不自觉的)。对此,中国传统的“诗言志”、“诗缘情”的诗歌理论足以证明。可屈先生却无视“无意识”的觉醒对于心理学和意识流文学的发生学意义,认为“意识流诗歌先于意识流小说,本来就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命题”,请问先生的逻辑何在?其实,屈先生对此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其“无意识”的回避便是明证。也正因如此,先生的回避便有有意之嫌。其二,因为无意识的核心是性本能,而“性”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为洪水猛兽,文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指涉呢?中国传统的情爱观是基于三从四德、男婚女嫁的实用主义情爱观,与其说它注重男女情感的相契相合,不如说它更注重男女在婚姻关系中的道德义务、生活责任。中国古代文人在回避“性”的同时,倒不吝啬一个“情”字,但是,这情字到底是何物呢?晚清作家吴研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在《恨海》第一回合中对“情”字有一议论:“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得太轻了。并且有许多小说不是在那里写作情,是在那里写作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在写情,真是笔端罪过。”由此可见,传统文人心中,“情”不过是忠孝大节而已,真正的男女情爱常常是被看作“魔’的,更何况“性”呢?因此,中国古典诗词自然不会将“性本能”视作自己的表现对象(其实,中国古典诗词中亦有性的涉猎,如晚唐五代时期花间词中便有大量性的描写,只是此“性”非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而已)。对此,作为文人的屈光先生自然不会不知。所以,屈先生的回避其实是有意的逃避。因为回避了“无意识”,也就逃避了谈性及由此可能面临的尴尬。
正是由于对“无意识”的回避,屈先生文中有多处令人生疑的地方。一是在用西方意识流文学观照中国古典诗词时,只能是避开文学精神而专谈技巧。这其实是混淆了作为文学流派的意识流和作为创作方法的意识流的区别。意识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意识流早已存在,可以说,当文学开始触摸人类心灵,表现人的复杂心理活动的时候,意识流的表现方法便被作家所发现并自觉运用,只不过未曾冠以“意识流”的名称而已。中国古典诗词既然以主体的情感世界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对象,那么,中国古代诗人大量运用时空倒错和自由联想的结构及表现技巧,自然不是什么值得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令人惊叹的事情。而作为文学思潮的意识流则只能存在于二十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即在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柏格森的“心理时间”以及弗洛伊德“无意识”为核心的“心理分析学说”等理论资源的沃土中产生的意识流小说。文学理论中所指的意识流文学也主要是指意识流小说,其文学理想便是着力于对人无意识的发掘。因此,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意识流文学。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大量的意识流技巧的运用,但不能说中国古典诗词中有意识流。
其次,屈先生在进行作品的横向比较时,模糊了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意识流小说这两种不同文体间的差别。中国古典诗词在其历史的演变过程中积淀下自身特有的审美特征:(1)强调抒情性。应该说抒情性是中国古典诗词最本质的美学特征。自从古人发出“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的呼喊后,情感便成为诗词永不厌倦的抒写对象。不但如此,还特别强调主体性原则,即用“主体的心灵去观照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心灵本身的观感和情感”,因而主体“认识自己和表现自己”,“这就是抒情诗在范围和任务上既不同于史诗又不同于戏剧体诗的主要特征”。诗词的抒情性和主体性原则,决定了诗人的个性在诗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诗人独立的个性和人格的确立,是诗的美学价值赖以获得的前提。诗人的个性和人格闪耀着什么样的光泽,其诗歌也就吐放着什么样的芳香。而意识流小说作为叙事性文体,尽管与传统的叙事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人物性格淡化了,情节淡化了,环境景物主观化了,读者从作品中看到的不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图景,而是客观世界在人物心理上的投影,但是,“叙事性”仍是其根本的特征。它仍然要借助特定的叙述方式(指叙述者怎样展开叙述)来展示人物的心理过程。因为它“几乎总是用来描写某一个人物的个人平凡经历和他对这些事物的纯粹个人角度的反应”,而这种“纯粹个人角度的反应”实际上就是将发生在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故事心理化,把人物的活动压缩到一个较小的场域和一段较短的时间内来表现,作品并不注重人物的活动和所见所闻,而是注重为人物的心理意识流程提供一个落脚点,也就是说,将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故事拿到人物的心理上加以表现,其所表现的正是人物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故事的回忆、思考,这种回忆或思考正是叙述的一种方式。而且在叙述主体(作者)和故事间由于叙述者(故事的讲述人)的存在,因而主体性是隐匿的。正是“叙述者”的存在,人物的“心理真实”(无意识)才有被敞开的可能。而中国古典诗词由于受主体性原则的制约,所表现的情感只能是诗人所独有情感的审美超越和升华。因此,任何的抒情主体只能去抒写自己清醒意识中的情感状态,而不可能敞开其被遗忘的“无意识”。因为弗洛伊德已经告诉我们,“无意识”对任何个体而言永远也不可能上升为“显意识”或“前意识”。屈先生在文中认为,“意识流用于抒情,较之用于叙事,作家更容易‘进去’,更容易曲尽其才,更易有神来之笔”。先生的“进去”自然是进入“意识流”,且就言辞上下文不难看出,先生的“意识流”是指包括无意识在内的人的心理意识流程,如此,岂不有悖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吗?不但如此,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获得理论的支持,引用弗里德曼“在意识流小说里出现了内心独白和感官印象,就立刻标志出诗已经混合在散文当中了”的论述来以期佐证,实在是扭曲了弗里德曼的本意。因为弗里德曼没有任何遮蔽地告诉我们,意识流小说为了更有效地去发掘人的“无意识”和变态心理,便去借鉴诗歌对情感表现的一些技巧,因此,他呼吁“小说家为了把现代小说写成功,应该向其中蕴藏着许多意识流技巧的诗学习,然后,再回过头来写小说。”其实,弗里德曼的论述恰恰说明,作为技巧的意识流和作为文学思潮的意识流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我们以此也只能得出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大量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却不能牵强地得出“中国古典意识流”这一结论。(2)中国古典诗词注重以意象为诗,并追求意象的蕴藉含蓄,旨远寄深,余味曲包,耐人寻味。古典诗词中的意象,是指诗人借助于具体物象,运用比兴手法所表达的一种情思。但由于受抒情性及主体性原则的制约,因而只能以意象为辅,全诗的思想中心还是那个合乎逻辑性的骨架。也就是说,在古典诗词中,主题是主题,意象是意象,二者既非一体,地位也非对等。正因如此,古典诗词中尽管“景”色斑斓、自由联想丰富、想象和幻想瑰丽奇特,但都以情为内在质点,也便不难解读,且大都能在“情”的编织下将非理性、非逻辑性还原成理性和逻辑性。屈先生在文中不正是如此还原的吗?在对曹操《短歌行》的解读时仍然受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制约;在对《西北有高楼》的分析时仍是被“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所羁绊;在对张先《菩萨蛮》的感受时不还是摆脱不了“忆君还上层楼曲”这一骨架的束缚吗?而西方意识流小说文本中尽管也存在大量的“感观印象”、丰富的自由联想、梦幻般的想象和幻想以及呓语般的内心独白,但其“叙事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有同一内在质点,而只能是人物意识流程中不同瞬间且内质不同的无意识活动。因此,它们只能体验不可还原,更不能从“河”“流”中摘取某一朵浪花作孤立的赏析,否则那只能是痴人说梦。屈先生文中对《尤利西斯》中几个片断的解析不觉得太牵强了吗?其实,先生在文中也认识到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文体差异,但一笔带过了。
当然,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特征及与西方意识流小说文体的差别,远不止上述两个方面,由于与本文所论关涉不大,也就不一一论及。总之,历史的风尘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有着种种的遮蔽,这就需要许多的研究者们来着手去蔽的工作。但在去蔽的过程中应坚守实事求是的学理精神,任何的回避甚至逃避,不仅不能使其内在的诗情和审美价值得到显现,而只能使其暗淡甚至遭至扼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