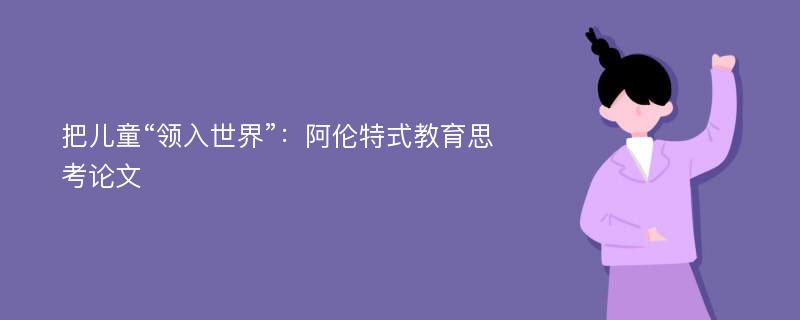
把儿童“领入世界”:阿伦特式教育思考
项继发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太原 030006)
摘 要: 阿伦特将美国教育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归于“没有世界”——儿童看似被给予自主,但事实上他们与成人世界的联系被切断。相应地,成人没有承担好将儿童“领入世界”的角色,没有珍视过去的传统之于当下和未来的意义,没有教会儿童在“物之世界”中使用物质材料和精神材料进行言说和行动。在阿伦特看来,作为“领入者”的教师,应当站在新与旧、过去与未来之间,引出儿童的言说和行动,将儿童领入现世世界。由于儿童还不熟悉这个既有世界,出于对每一个学生崭新的、变革性的利益的考虑,教育必须是保守的。学校作为现世世界的建制代表,也应当重拾权威,珍视传统。
关键词: 阿伦特;现世世界;“领入世界”;教育本质
教师的资格在于了解世界和能够把他关于世界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他的权威则建立在他对那个世界负责任的假定之上。在孩子面前,他仿佛是世界上所有成年居民的代表,指着它的沟沟壑壑,对孩子们说:这是我们的世界。
(51)曲枝大萼苔Cephalozia catenulata(Huebener.) Lindb. 余夏君等(2018)
——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
引言
汉娜·阿伦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老师。《极权主义的起源》提醒我们,极权不同于过往社会的独裁专政,但仍然是这个时代最为恐怖的力量;《人的境况》告诉我们,古希腊人是如何理解政治生活的,他们的理解与现代人的理解有多么不同,以及我们是如何在政治中从追求美德和名望,沦落到追求安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解释了恶是如何在平庸之人中蔓延的。随着她的文笔转入其他主题,她的“教学”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作为不属于任何派别的哲学家,阿伦特的思想要么被误解,要么被忽略。通常被看作政治哲学家的阿伦特,对教育问题的洞见,因其个人性原创和思想的跳跃,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其中也不乏褒贬不一的争论。阿伦特直接着笔教育的文字并不多(1) 另一篇写于1959年的“反思小石城事件”(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是对美国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政策的评论和政治抗议,后收入《责任与判断》一书,中译本可见201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责任与判断》。 ,最早的一篇是她写于1954年的“教育的危机”(The crisis in education),后编入《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 )一书,[1]她在教育思考上的创见和远见,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重估。本文重温阿伦特对现世世界的爱,理解“领入世界”的教育意涵,尝试作出教育本质的理性判断。
一、“没有世界”的教育批判
在问诊美国教育的危机时,阿伦特将病症对准美国的学校教育,却又不依循专业性教育家的那种技术性的回答。她指出,美国的学校教育过多强调儿童的生活,强调儿童的学习过程,强调儿童只有通过自我发现才能获知。而这种灾难性措施的前提假定则是,“存在着一个儿童的世界,一个儿童组成的社会,它本身是自主的,必须尽可能地把它留给儿童自己去管理,成年人只能在旁边帮助他们”[1]169。如此这般的教育是一种“没有世界”的教育,遮蔽了关于世界的所是(what)与所为(what for),成年人被设想成儿童成长的旁观者,儿童则被排斥在成人世界之外,“成年人拒绝为他们把孩子带入的这个世界负责”[1]177。阿伦特指出,进步主义的教育方针将教育理解为交由儿童学习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理解将健全的人类理性规则抛在一边,世界被作为空心化的抽象,人与自己的世界发生疏离,遭致共同感的丧失。这一危机一方面宣告了进步主义教育的破产,另一方面,也引起大众对社会秩序的质疑。
教育不仅仅牵涉杜威式的生长,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中的生长(growing up in the world)。而作为教育者角色的教师或者家长,理应成为这个世界的代表。“教师的资格在于了解世界和能够把他关于世界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他的权威则建立在他对那个世界负责任的假定之上。在孩子面前,他仿佛是世界上所有成年居民的代表,指着它的沟沟壑壑,对孩子们说:这是我们的世界。”[1]176-177在阿伦特看来,教育资格跟教育者的权威并不是一回事。儿童需要被成人,尤其是教师引入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而教师自然就成为世界的代表,承担起引导儿童的天然责任。教育一词的语用起源,往往会回到拉丁文法中的educere或educare,前者意为“引出”和“潜能实现”,后者意指“抚育和养育”。两种语用来源虽然指向不同的教育概念理解,但均暗含了教育的潜在目的:在真实社会世界中的人格养成。在阿伦特的教育理念中,教育者的角色应是作为将儿童领入世界的引路人。那么,阿伦特所讲的“领入世界”(introducing into the world)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的“世界”指的是什么,以及“领入”的目的何在?成人教育者的权威有何作用?在明了这些问题之后,作为教育者,如何在实践中付诸行动,实践所需的外在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阿伦特对教育危机的问诊。
二、“这是我们的世界”
儿童作为教育的主体,本身具有双重特性:“在一个他陌生的世界里面,他是崭新的,同时又处于变化过程中;他是一个新人又是一个成长着的人。”[1]173与这一双重特性相对应的,是一组双重关系,即儿童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儿童与生命的关系。这就意味着,作为新人的儿童,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教育(不管是来自家庭还是学校)的职责在于不仅要维护生命和发展,同时还要确保世界的延续,避免儿童和世界受到伤害和侵袭。家庭为儿童成长提供安全的私人领域,而学校作为公共世界的建制机构代表,真正发挥着将儿童“领入世界”的功能。尽管学校不能完全复刻世界,但学校将世界的规则、原理、逻辑等凝练压缩到日常的学校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世界。学校教育中的成年人,尤其是教师应承担保障儿童个性和天赋自由发展的责任,彰显每一个儿童个体的独特性,使儿童真正体验到,他不仅仅是一个来到这个客观世界的新人,而且是已存世界中从未有过的一个自己。在这个时候,儿童(包括刚出生的婴儿)已经不只是处在(in)外在世界中,他已经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与(with)外在世界发生着联系。成长在一个给定世界中的儿童,“不仅仅与特定自然环境相联系,也与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秩序相联系,后者是由照管他的重要他人中转(mediate)给他的”[2]65。
儿童在进入到既有世界过程中,尽管依然保持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但社会文化因素会持续地、日益重要地对儿童发展产生干预,这恰恰也是人类自身可塑性的彰显。儿童在一个既定世界中要被塑造成什么样子,或者自己能够发展成为什么样子,是由这一世界的社会—文化构造所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儿童在与世界的复杂联系中,建构了自己的本性;人类世代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创造了自身。这一过程,恰恰也是人类“自我”的形成过程。“人类的有机体与自我在一种社会决定的环境中共同发展,这种发展涉及人类所特有的有机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2]67这一特殊关系关涉到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双重身体观:人是一个身体;人有一个身体。前者涉及人类的生物性特征,后者涉及人类对自身身体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主观意义外化。
再次,还要着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人才、智力和技术支持。在科学研究方面,与乡村振兴的目标和要求相适应,地方高校应基于其地方性的特点,以基础研究为导向,在强化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同时,主动调整科研方向和结构,以适应乡村振兴的需求。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把农业、农村、农民遇到的难题作为研究对象。解决地方经济和农村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充分发挥科技优势,主动服务新农村建设。
三、“领入世界”的教育行动
“世界,作为矗立在地球上、取自地球自然提供给人手上的物质材料建造的人造家园,不是由供消费的东西组成,而是由供使用的东西组成。如果自然和地球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一般境况,那么,世界和世界之物就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特有境况,由此,人在地球上的生活才能自在……如果没有自在地置身于那些耐久性的事物之中,没有置身于一个与生命的短暂形成直接对比的世界之中,那么这种生活就不是属人的。”[3]134-135在这里,我们能够理解阿伦特口中的“领入世界”(introducing into the world)的意涵。“领入世界”意味着领入由物(things)构成的世界,由有用之物(world of use objects)组成的世界。这些有用之物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生活所需的物质材料(material things),如五花八门的生产生活用具;也包括精神材料(mental things),理念、概念、规则、规范均属其中。将儿童领入世界意味着让他们熟悉既有世界的物品,进而知道如何使用它们。儿童被领入到这个世界意味着能够使用这个世界上的物品,或者更准确地说,使用成年人选择的有价值的物品。通过使用它们,年轻一代在年长一代创建的世界中变得自在起来。从这一层面来讲,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引领儿童进入有价值的生活。
教育的要义在于,我们要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爱是否足以让我们为世界承担责任,是否要让它免于毁灭,因为若不是有新的、年轻的面孔不断加入进来和重建它,它的毁灭就是不可避免的。教育同时也是要我们决定,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爱是否足以让我们不把他们排斥在我们的世界之外,是否要让他们自行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不从他们手里夺走他们推陈出新、开创我们从未预见过的事业的机会,并提前为他们重建一个共同世界的任务做准备。[1]182
如果将视野转入哲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儿童”这一概念普遍被构念为“未完成”“不完整”“不能胜任”等意象,而其主要依据则源自儿童的理性发展不足、成熟水平不够,或者独立自主性不强。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将理性(热爱并追寻真理的心智官能)、勇气(触发行动动机的激情)和欲望(创造愉悦的生理性渴望)视为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在柏拉图看来,儿童恰恰是缺乏理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很晚的年龄才涉入理性世界。[4]因此,柏拉图的儿童教育观,更加注重儿童身边侍者和教师的角色,教授的内容偏重于对于千变万化的世界的理解,而不是获得一成不变的世界中所谓的“真知识”。与柏拉图看法一致,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生活在欲望的召唤下,对愉悦的欲望最为渴望,易于受到自我沉溺的影响。[5]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儿童还未获得理性,也没有具备慎思的能力,他们需要通过适当的教育来进行引导。儿童的意象在哲学史中一直被描述为缺乏自律,因此也须屈从于成人。
教育危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来自于权威丧失。“权威在最广泛意义上一直被看作一种自然必要性,出于孩童的无助要有人看护的自然需求;权威也被看作一种政治必要性,因为任何建制化的文明要确保它的延续,就必须引导那些作为新来者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穿过前建制的世界(a pre-established world),进入到这个对他们来说实属陌生的文明世界。”[1]87在阿伦特眼中,儿童与作为教育者的成人本应是一种前政治的权威型关系,而权威秩序总是等级制的。“等级制本身是命令者和服从者共享的,双方都认同等级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等级制中他们彼此都有预先规定好的牢固地位。”[1]88儿童与成人并不处在同样的地位上,也因此,在阿伦特看来,行动并不能在儿童这里发生作用。毫无疑问,阿伦特的这一观点当然招致很多批评的声音,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暂存不表。
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单位,是指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政党机关、人民团体,以及国家举办的带有公益性质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及从事有关专项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事业单位。政府会计的“投资”指事业单位在保证正常运转和事业发展的前提下,利用货币资金、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向其他单位的投资,其中的货币资金投资指直接以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作为投入资本进行的投资。
本栏目旨在交流和推广卫生管理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普及卫生管理知识,探讨卫生管理方法和技术,介绍国内外卫生管理科学新进展。
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将教育看作一项政治活动,但并没有区分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on)和教育行动(educational action)。在政治行动中,行动者间的关系是非等级性(4) 原文所用nonhierarchical,以及前文用到的hierarchical,可能译作“非层级性”与“层级性”更为妥帖,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虽然兼顾权威的角色,但完全不对应政治上的等级。本文忠于原书译本的用法,仍作沿用。 的;而在教育行动中,情形并非如此。学校只有在教师与学生的等级结构关系架构之下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教育机构。这样讲的意思是,教师肩负着将儿童领入世界的责任,教师将儿童视为具有可塑性和可教性的对象,他们都具备被领入世界的潜能。当然,教师的“领入”并不是对所有儿童不加区别,这已是学校教学理论早已强调的。每一个儿童都拥有自己成形的开放性,教师在学校中的角色,除了引导和邀请他们使用世界之物进行工作,还鼓励他们通过言说和行动嵌入到世界中。这些言说和行动彰显他们处理的世界之物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体的言说和行动,个体彰显了自己在他者中的在场,即存在。他人的在场向“我”表征了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实在性,因为他们见证了“我”的言说和行动,反之亦然。儿童还不能为他们的未来承担责任,也因此,教育行动总是要在教育者的责任承担下发生,还不能达到成人世界中政治行动中的无等级性。
四、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领入者—教师
教师的权威建基在他理应对世界负责这一假定之上。如果撇除这一假定,教师便不能践行他所代表的教师身份(teachership)。阿伦特引用波利比乌斯的话,教育只不过是“让你知道你真正配得上你的祖先”[1]180,来亮明教师立于新与旧、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身份位置。教育者的职业身份“要求他对过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尊重”,这种自觉意识贯穿在整个罗马-基督教文明时期,并推动教育在其中发挥着某种政治功能。阿伦特在她的文字中一再回溯西方文明传统的源头,但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她倡言每一代人都应该回望过去,并在传统的基础上重建过去的意义,但并不暗示任何恢复传统的意味。教师权威深深扎根于过去本身的整体权威当中。[1]180同样,如果学校的权威丧失,将过去抛至脑后,那么,学校也便不复存在了,它不能悬浮在对世界的责任之外而存在。学校也要向学生透彻地展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不能屈就于仅仅向他们提供机械的谋生手段和技能。
在阿伦特看来,诞生性是一种打断周而复始的流变循环的生命进程并转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她将这种能力称为奇迹,“行动就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3]246,“这个将世界和人类事务领域从传统的‘自然’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奇迹,最终是诞生性的事实,也是行动能力的本体论根源。换言之,是新人的出生和新的开始,是由于降生才可能的行动。只有对此能力的充分体验,才能赋予人类事务以信心和希望……”[3]247新的一代人的降生,也是开端启新的可能,这便是人类事务的希望所在。但是,这种开端启新的可能性并不是自明的。没有成年人将儿童领入世界,领入旧世界,既存世界,新的开端几无可能。阿伦特坚持,教育只能是保守的。尽管表面上看,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但是,年轻一代首先必须被领入到既有世界中,生长于其中,进而要求他们学习使用世界之物进行工作并尝试开端性的行动。由于儿童或年轻一代还不熟悉这个既有世界,出于对每一个学生崭新的、变革性的利益的考虑,教育必须是保守的。它必须保护崭新性并将它作为新事物引入旧世界。同样,她认为,学校理应成为一个保护区(‘protected’ area),应当设置在一个介于其间的空间(in-between space)中,这一空间既不同于排他性的家庭私人领域,也异于每个人可以平等区别的成人世界公共领域。儿童或者年轻一代接受教育,不仅仅是出于家庭(私人领域)的要求,同样也是国家、成人世界即公共领域的要求。由此,学校就成为一个被置于家庭私人领域和成人世界之间的机构,通过这一机构,儿童或年轻一代由家庭被传送至成人世界。在整个传送过程中,成人世界要对儿童或年轻一代的“领入”负责。而“领入”发生的场所,就是这个介于其间的空间(in-between space),应当成为一个保护区。学校应当保护年轻一代免于公共世界的曝光,同样也保护他们免遭劳动世界(world of labor)商品物化的侵蚀。
式中,Qsk为总极限侧阻力标准值(kN),up为桩的周长(m),up 为 3.14×0.5 m;qsi为桩周第i层土桩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kPa);li为第 i层土的厚度(m)。
儿童或者年轻一代学习使用世界之物是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上文所讲,世界之物不仅仅只是物质性材料,也包括精神材料。当儿童在教育上取得进步时,精神材料的重要性就日趋增加了。通过使用精神材料,儿童逐渐学会这些精神材料是什么,以及如何合适应对。学校教育设立的不同科目由种类多样的精神材料组成,数字、语法、算术运算、语言、拼写、基础科学概念、写作、音乐、美术、体育,等等,其中蕴含很多不同的精神性材料。比如,算术运算规则讲求数字逻辑和数感,语言暗含文化惯习与语法规则,写作要求表意与行文规范,等等。通过这些精神材料,儿童和年轻一代从事阿伦特意义上的工作(work)。在这一层意义上,儿童进行写作训练、求解数学题目、设计美术作品都是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儿童同时使用物质材料(工具)和精神材料。然而,儿童在学校中完成的工作还不是彻底的工作。与成人世界的工作相比,儿童完成的工作所产出的产品并不能拿来进行交换和供他人使用。人类生活开始于劳动和工作,但它们仅仅构成人类生活的前提条件,人类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达到自我实现。由世界之物构成的世界,不管是物质材料还是精神材料,都是人类行动于其中的属人环境。“领入世界”就是将儿童和年轻一代领入物的世界,并获得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不需要同样获得人类行动的经验吗?
在《人的境况》(2) 本文引注的《人的境况》相关内容,均出自1998年芝加哥大学版本(Arendt, H. (1998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不再赘述。 中,阿伦特发展了自己关于人的存在的哲学人类学思想。阿伦特之前的哲学传统,将人一直看作思考性的存在。根据这一传统,人类的本质是“沉思”(vita contemplativa )[3]14。但在阿伦特看来,这种传统已经不适用于描述现代人。相反,她将“积极生活”(vita activa )看作现代人的特征。现代人的生活模式理当是一种行动式的生活。阿伦特区分了对于人的境况来讲最为根本性的三种不同形式的人类活动,即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分别对应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基本境况。她将劳动看作人类身体自发的生长、代谢和衰亡过程,相应于人的生物性生活;将工作看作制作与产出过程,相应于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人为对象世界;而将行动看作在公共领域中对他者在场的应对过程,相应于复数性的人的境况,每个个体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行动式的生活摆脱了生物性生命过程的束缚,不再将生活看作在世界中的简单谋生或者生存,而是在开放性、复数的世界中,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展现自己的个性。行动,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境况,拒斥人类社会可预见性的复制和重复。“人类与自身所处环境的关系具有世界的开放性(world-openness)。”[2]64尽管生物构造赋予人类从事生产和劳动的能力,人类栖居于世并不决定于自身的生物构造。行动不是一个自然过程,也不是一种目的手段,它是人类的内在交互过程。单个的个体无法行动,在阿伦特看来,行动是复数的人类境况的本体回应。
前文提及,将儿童领入世界意味着引导他们在物之世界中工作,并且能够言说和行动。学校中的教育,通常会以教授(instruction)的方式传达至学生,采取操练、任务等方式,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学校教育应当鼓励讨论与对话。二者构成阿伦特意义上的自由工作和开端性的行动,二者共同助力儿童/学生形成对物之世界的建构能力。
五、把儿童“领入世界”的教育意蕴
答案是否定的。在阿伦特看来,儿童并没有行动的能力。这也是本文开头提到教育的危机真正的病灶所在。在行动这一人类活动中,儿童与成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成人世界,人类在行动中步入世界。“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嵌入(insert)人类世界。”[3]176阿伦特将这种嵌入(insertion)称作第二次诞生(birth)。这一诞生区别于后文所讲的诞生性(natality),它是人在与他人共享的公共世界中的诞生。在这个共享的公共世界中,人们通过言说和行动(word and deed)(3) 这里,阿伦特取道亚里士多德政治生活的两种主要形态,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将二者视为人类事务的架构。 ,“可以表明他们是谁,主动地揭示他们显示的个人身份”[3]176,从而才能在公共世界中显现出来。一个人只有在这一公共世界中才能成为全人(fully human),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显示自我的主体身份,个人的身份彰显只能出现在纯粹的人类归属感(togetherness)当中。在行动中,(复数的)个体从不同角度同他者分享人类世界的共同经验,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common sense),才能塑造出一个共同世界(common world)。而这种塑造的本质,在阿伦特看来,是政治的。这也可以看出,阿伦特对人类社会的解读是一种事实上的政治人类学。教育危机是一个政治问题,是现代社会整体性危机的一个侧面。教育与政治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关联,教育与政治都在根本上关涉到人之境况的诞生性。但是对于儿童世界来讲,在阿伦特看来,成人并不是扮演与儿童完全平等的角色,双方是一种不对等的等级制(hierarchy)关系。
然而,到洛克这里,儿童的意象得到了重新审度。在洛克看来,儿童生来自由,并具备理性能力,“儿童自呱呱坠地时起就应该习惯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做事行动时不要对这种欲望念念不忘”[6]34。但是,洛克并未正视儿童生来的自然自由与儿童未成熟状态对父母的屈从之间的抵触,即儿童运用理性来控制他们行为的心智能力还远远未达到实践自由的资格。鉴于儿童还没有能力为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做出理性行动,他们的父母,作为理性的成年人,代表儿童的利益行事,并为他们做出选择。除了这个理由,洛克认为,除却儿童被给予养育和照顾的自然权利,父母实际上有义务管教他们的孩子。“父母之于儿童的权力,来自于他们照顾处在不完美的童年期的后代的责任。(父母)启迪儿童的心灵,管控儿童年幼无知的行为,直至理性上位,驱散烦扰。”[7]因此,我们在洛克的文本中容易找到看似矛盾,但又可以理解的论述。他一方面肯定儿童的理性,一方面又强调父母对儿童理性的引导。“人与人之所以千差万别,均仰仗教育之功……”,并且“儿童的心智和源头的水性相近,容易引导,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6]34虽然在是否具备理性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哲学史上对儿童的教育一直强调并尊重儿童作为人的权利,同时这也构成人类教育一条最为重要的经验。
阿伦特将作为介于其间的学校视作前政治(prepolitical)领域。[1]87虽然介于其间,但学校并不是一座孤岛,它内嵌于现时的社会中,社会的进程同样影响到学校的运行。儿童同样也内嵌于社会,他们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免不了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商品社会(劳动世界)和社会化过程威胁着公共世界。学校作为前政治性质的机构,也不是自明的。明显的是,学校不是商业机构或者社会福利机构,学校平等地保护儿童的个性和天赋的自由发展,确保他们每个人成形的开放性。学校需要在抵制社会风气侵蚀中通过不断的矫正(setting-right)来保证教育目的的达成,矫正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规约在学校的自我矫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校的长久存续需要由规约(甚至法律)对教育过程进行框范,规约指明了个体行动者之于他者的关系,如师生关系。如果没有规约,行动也不会发生,不会有对他者的回应,更不会有共同生活的可能。这些规约就像一堵隐形的墙,能够将个体自我与他者区分、规定,不至于陷入无序和混乱。学校的前政治空间也是得益于这些规约而存在。在阿伦特的构想中,学校位于一个介于其间的空间中,“桌子”置于其中,儿童围桌而坐,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世界之物并开始使用这些物展开行动。在这所学校中,年长一代不仅仅承担教育年轻一代的责任,还要承担保护世界不受侵害的责任。阿伦特写道:
“教育的本质是诞生性(natality),即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实。”[8]这一命题与卢梭的智慧极其相似:人类正因为从孩子长起,所以人类才有救。对于儿童的教育,“问题不在于防他死去,而在于教他如何生活。生活,并不是呼吸,而是活动,那就是要使用我们的器官,使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才能,以及一切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存在的本身的各部分”[9]17。诞生性,作为人类存在和开端启新的可能性,内在于人类行动,内在于行动的自由。人类生活的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境况保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绵延的历史创造。这种历史创造建基于人类秩序在“经验层面上的稳定性”[2]68。人类秩序并不会自动产生于自然规律,它只能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产生,是一种持续生成的人类产品;反过来,人类秩序也反映了人类自身的不断社会外化过程。人类自身不断外化形成的社会秩序,逐渐引向了社会发展的制度化。劳动、工作以及行动,都承担着为源源不断的来到这个世界的陌生人做出规划和考虑的责任,他们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而三者之中,行动与人的诞生性境况关系最为紧密。在所有人类活动中,也包括教育,新来者具有开端启新的能力,也即行动的可能性。人类的行动往往会在不断的惯例化重复中形成某种模式,这种模式能够确保个体使自己的行动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世界中的经验保持一致。对于进入社会世界的儿童来讲,父母、教师,或者其他重要他者中转给他们的世界,并不是完全透明的,因为在他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之前,制度就已经形成了,已经是一个客观性的给定存在。
那么,这个给定的、复杂的、客观的制度性社会世界,是如何传承给新生一代儿童的?前文虽讲,人创造了自身。但是,对于儿童来讲,现世的社会构造不是在儿童降生到世界那一刻就能够全盘接收的。在儿童早期社会化阶段,父母、教师或者重要他者将制度世界作为客观事实传递给儿童。儿童对眼中看到的颜色的判别、对父母长辈的称谓、对形态各异的物体的指称,都是以一种被给定的、客观的、自证的方式传达的。爸爸、妈妈、红色、苹果,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和事物都直接与名称联结起来,不能被称作别的任何内容。当儿童从父母那里习得相应的语汇,就可以将这些人类经验看作一种社会结构的正当化。这里的“爸爸、妈妈、红色、苹果”等语汇所携带的正当化信息作为客观的自明性“知识”逐渐被儿童内化。儿童以一种类似于“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初始观念来进入他的现世世界。虽然这种正当化还处于前理论阶段,即尚未形成对世界清晰的理论理解和象征符号化,但这一阶段正是儿童体验世界的重要阶段。父母对已存世界的体认,会以客观化的方式传达到儿童的经验当中。
制度世界对于父母和教师来讲,是已知的,是被社会定义为现实的东西,他们有义务将这些知识传递给未知的儿童,这也构成父母之为父母、教师之为教师的正当性。父母和教师的社会角色,扎根于制度化和惯例化的客观世界中,同时也反过来受到制度和惯例的制约和监督。父母和教师除了自身的伦理角色和职业角色之外,还以制度和惯例的代表的身份来行动,比如对儿童进行教育,将儿童引入制度世界。制度世界是一种外在的现实,个体不可能通过内省和沉思来理解它们。尽管制度世界对于初入世界的儿童来讲是一片悠远弥漫的黑森林,但它始终是一种人造的、被建构的客观性。制度世界首先是一个人为世界,与人的主观性相对,它是客观的。因此,儿童对于制度世界的体认,是儿童“走出去”将制度世界给定的客观性整合到自己的总体经验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不断内化制度世界,在体认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塑造了自身的存在。对于每一个世代的儿童(以及未来的成人)来讲,复数意义上的人创造了社会世界,反过来,社会世界也塑造了人,这也构成阿伦特意义上的开端启新的“诞生性”。
公路桥梁养护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为了提高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的开展效率与开展质量,就必须要加大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的经费投入。首先,有关部门要设立专门的公路养护经费管理中心并让专业人员对公路养护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根据公路桥梁养护的实际建设情况与加固维修状况进行资金的划拨,以此保证公路桥梁养护后续工作资金的充裕性;其次,公路桥梁养护工作需要不断引进高科技维修设备,以此保证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的高效开展;与此同时,公路桥梁养护工作还需要引进具备较强技术性的专业人才,以此保证公路桥梁养护工作的正常运行[8]。
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使用了一个有趣的隐喻来指代共同世界。她讲到,人们在世界上一起生活,根本上意味着一个物之世界(a world of things)存在于共同拥有它们的人们中间。这就好比是一张桌子放置于人们中间,人们围桌而坐。这时的世界,就像是每一个介于其中(in-between)的物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3]52这里将阿伦特关于桌子的隐喻迁移一下,放到学校的场景之中。教师将前文所讲的物质材料和精神材料放置在“桌子”上,让学生能够熟识并使用它们。在这一层意义上,这里的“桌子”,是一个工作的“桌子”,“桌子”与物一起构成儿童言说和行动的中介物。儿童在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之下围桌而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位置(立场)。从各自不同的位置(立场)出发,儿童对物之世界进行言说和行动。在这一过程中,世界慢慢变成一个共同世界(common world),同时,每一个人在他者中显示了自己的在场。引导儿童进入这个共同世界的过程就是教育过程。正如彼得斯所言,“教育的基本任务在于引导其他人进入由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概念构成的公共世界,在于鼓励其他人共同探究以各种较大差别的意识形态为标识的领域”[10]52。阿伦特将这一过程称作人化(humanization),“我们只有通过言说发生在世界和自己身上的事情,才能使之人化,在言说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1]25。阿伦特坚信,就生活和行动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他们可以通过互相交谈体验到生存的意义。这些发生在世界上和人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构成人的境况的不同处境。人是被处境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al beings),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人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处境。人在世界中的诞生也即是人对处境的人化过程。对于儿童来讲,他们接触到或使用到的任何物,都会成为他们存在境况的处境,都构成他们存在的组成部分。教师需要引导他们感触和接受这些处境,与这些处境发生关联,将这些物进行人化,这一过程构成儿童在世界中的诞生性。这一过程回应人类社会的教育目的,即将儿童或年轻一代领入世界,目的是引导他们对物之世界和他们自身进行人化。
六、余论
人类生存于过去与未来的交织之中。阿伦特引用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诗句,“留给我们的珍宝(遗产)没有任何遗言”[1]1,并把这句话看作对托克维尔“由于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照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晦暗中游荡”[1]4一句的改写,表达的是心灵对理解人类自身的困惑。阿伦特没有把过去看作医治现世世界病症的药方,“就如同每个新人都要让自身嵌入到一个无限过去和一个无限未来那样,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1]10,“积极生活”(vita activa)于现世世界,是要从过去拯救值得保存的东西,重新发现过去,赋予它今天的意义,找出“积极的可能性”。现时世界的危机,是由过去与未来的冲突洪流形成的裂隙。教育危机在本质上,是时间的危机。过去不再是未来的指示标,人的切入打破了时间的连续体,把时间洪流打碎成几股力量。“领入世界”意味着将儿童或年轻一代领入到物之世界中,引导他们工作和尝试开始行动。对于他们来讲,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工具恰恰就在他们自己手中:思想、工作和行动。本文不对阿伦特的思想给出判定结论,也没有就其教育思想的是非争辩给出审度,本文的方式也是阿伦特式的:不为传达结论,只为刺激思考;如果能引起思想者们的对话,也可计作这一篇小小言说的功劳。
第五,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和促进农业标准化生产。通过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并针对农业技术相关的问题进行沟通和讨论,从而促使新技术、新品种能够更好地推广[2]。
[致谢] 本文成文得到刘庆昌教授的启发与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参 考 文 献:
[1] 汉娜·阿伦特. 过去与未来之间[M]. 王寅丽,张立立,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 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M]. 吴肃然,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 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M].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1958].
[4] PLATO.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Including the Letters (HAMILTON E,CAIRNS H,Eds.)[M].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683.
[5] ARISTOTLE.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Rev. ed.,Vol.2,J. Bar-nes,Ed.)[M].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1767.
[6] 约翰·洛克. 教育漫话[M]. 杨汉麟,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7] LOCKE J.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Student ed.,P. Laslett,Ed.)[M].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306.
[8] ARENDT H. Men in Dark Times[M].San Diego/New York/Londo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5 [1968]:164.
[9] 卢梭. 爱弥儿(上卷)[M]. 李平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7.
[10] 彼得斯. 伦理学与教育[M]. 朱镜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52.
Introduc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Arendtian ’s View of Education
XIANG Ji-f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 H. Arendt regards the crisis of education as a result of “having no world”. The education appears to foster children’s independence, but actually cuts off their connection to adults’ world. Correspondingly, adults fail to take their role to introduce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to value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 of past upo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to teach children to use physical and mental materials as tools for word and deed in a “world of things”. As “introducers”, teachers stand on the “in-between” of the old and new, and the past and future to elicit children’s word and deed and introduce children into the real world. Since children are not yet familiar with the established world, education must be conservative for the sake of the new and transformative interests of every single child.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world, schools should also recapture authority and cherish the tradition.
Key words : H. Arendt; real world; introduc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nature of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9-06-23
作者简介: 项继发(1982—),男,山西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E-mail:xjf-allen@hotmail.com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个体变迁和村落转型中的教育生成功能研究”(课题批准号:AA160161)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G4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298(2019)05-0003-08
DOI: 10.14082 /j.cnki.1673-1298.2019.05.001
(责任编辑 康永久)
标签:阿伦特论文; 现世世界论文; “领入世界”论文; 教育本质论文;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