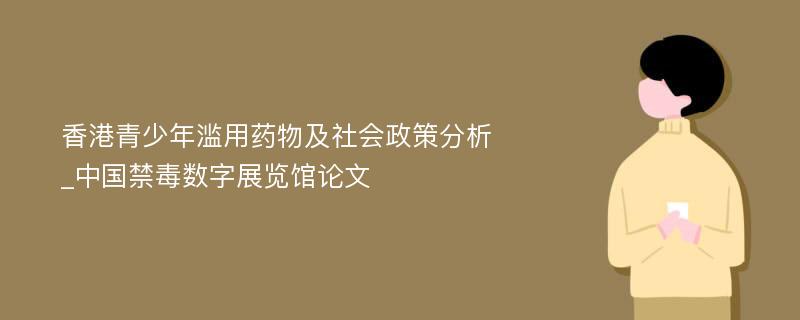
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与社会政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药物论文,青年论文,政策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现状
广义上说,药物指的是所有能够改变人类身体功能的物质。[2] 但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药物又特指那些直接影响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并造成习惯性依赖的物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药物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人的心理功能、情绪、感觉和意识,具有被错误使用可能,并对使用者和社会造成危害的化学物质。而所谓的药物滥用,则是指使用不被社会认可的,或过量、不合适地使用社会认可的药物,并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伤害的情形。[3]
以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具有被滥用可能性的药物范围比我们以往关于毒品概念的界定更为广泛。它既包括非法的大麻、海洛英和可卡因等毒品,也包括通常被社会认可的香烟、酒精饮料和部分处方药品。尽管它们的社会认可程度不一,但对人的伤害程度却有一致性,许多研究甚至认为香烟和酒精饮料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某些毒品。[4] 在香港,被认为具有滥用可能性的药物包括麻醉镇痛剂、迷幻剂、抑制剂、兴奋剂、镇静剂和包括烟酒等六大类。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非法药物分别为海洛英、氯胺酮(俗称K仔)、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称摇头丸)和大麻,它们在滥用药物者中的比例分别为74%、17%、9%和8%。[5] 对于21岁以下的青年,经常被滥用的药品主要为氯胺酮、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和海洛英,其2003年的人数分别为1099、599、499、136和114。[6] 而学生的情况又有不同,根据2000年的调查,除了海洛英,主要滥用的精神药物为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氯胺酮、止咳药、有机溶剂和甲基安非他明,其比例分别为45.6%、41.7%、36.5%、26.1%、23.2%和16.0%。[7]
那么,香港药物滥用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其变化趋势如何?根据香港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汇总统计,1997~2004年药物滥用者分别为17635、16992、16314、18335、18512、17966、15708和14714人。按年龄组别计算,其中20岁及其以下青少年药物滥用者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97年17.9%、1998年16.7%、1999年15.2%、2000年21.9%、2001年21.1%、2002年16.8%、2003年14.0%和14.4%。[8] 尽管中央档案室汇总统计的青年滥用药物者人数及比例有所下降,但与90年代末相比绝对数字还是较大。并且,由于滥用药物人数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因此我们难以对未来青年滥用药物的趋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例如,2004年因触犯毒品罪行被捕的青少年人数上升,同年因严重毒品罪被捕的青少年505人,而上一年仅474人;因轻微罪行被捕的青少年979人,上一年为739人。[9]
近年来青年学生滥用药物问题不容乐观。根据刘德辉等人的研究,尽管学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数较少,但在另外一些药物上却呈增长趋势。例如,尽管吸烟的学生人数从1992年、1996年的26.8%、23.7%下降到2002年的22.2%,但同期饮用酒精饮料者的比例则由73.9%上升到79.7%。尽管与1996年相比,2000年使用大麻、止咳药和有机溶剂者的比例明显下降,但服用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摇头丸)、甲基安非他明(冰)和海洛英的比例则上升;而其中使用摇头丸和冰的青少年比例更是分别从5.2%和10.3%上升到45.6%和16.0%。在1996年的调查中俗称K仔的氯胺酮还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但2000年滥用者的比例则达到36.5%。[10]
当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药物滥用的问题并不是最为突出的。根据联合国药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的研究,世界各大洲几乎都受到药物滥用问题的困扰。在亚洲,药物滥用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鸦片、可卡因、安非他明和摇头丸等药品上,香港滥用者的百分比或者在中等水平以下,或者没有排上名单。[11] 2001~2002年期间,全球非法药物滥用人数为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3.4%;[12] 而在香港,2002和2003年滥用药物的人数分别为17966和15708人,[13] 而这两年的人口分别为678.7万和680.3万,[14] 药物滥用者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0.26%和0.23%,远远低于全球的比例。然而,药物滥用不但对本人及其家庭具有重大消极影响,而且还常常与犯罪等现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药物滥用问题不可轻视。事实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一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我们借鉴。
二、香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的社会政策
药物滥用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国际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都将铲除这一社会毒瘤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政府组织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在香港,政府在保安局设立了由禁毒专员领导的禁毒处这一具有统筹性质的专职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协同处理药物滥用问题。其职责涉及的领域包括立法和执法、预防教育和宣传、戒毒和康复治疗、研究和对外协作。同时,政府还设立了禁毒常务委员会和毒品问题联络委员会。前者属于非法定的政策咨询组织,由1名主席、17名社会工作、社区服务和其他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非官方专业人士以及禁毒专员和卫生署代表2名官方代表组成,下设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常委任主席的禁毒教育及宣传、戒毒治疗及康复和研究等三个小组。后者则是政府与各志愿组织之间起沟通作用、鼓励社会参与的机构,包括戒毒治疗和康复界的代表、药物教育专家、青年团体和机构代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15]
有关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划分方式也各有侧重。在西方一些国家,有的将其区分为防范(prevention)、治疗(treatment)和法制(leagal repression and decriminalization)等方面,[16] 有的区分为防范控制(control strategies)和立法执法(law enforcement)等,[17] 甚至有更为具体的划分;[18] 但总的来说包括事先的防范教育和事后的惩治矫正两个方面。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的社会政策也基本相同,下面着重从宣传教育、立法与执法、治疗和康复服务以及研究等四个方面作简要的介绍。[19]
首先,关于宣传教育。由于青少年阶段是初涉药物的关键时期,因此借助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帮助他们了解毒品的危害、促使他们远离毒品显得十分重要。香港政府在教育机构、新闻界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之下,着重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学校教育宣传方面,教育署出版了《学校行政手册》和《中学学生辅导工作》,规范学校处理药物滥用问题的机制并为教师和社工提供指导。教育署还多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培训,提高学校的药物教育水平。此外,教育署还将有关教育内容融入到小学常识、中学社会教育、经济及公共事务、宗教、科学化学和通识教育课程之中,使得药物知识教育制度化。禁毒处也与教育署合作,通过举办讲座、组织各类课外活动和派发药物教育教材的途径,促进青少年的药物教育工作。
在社会教育方面,政府每年一度组织全港性禁毒宣传运动,派发各种宣传资料,制作播放各种电视宣传教育片和公益广告,开通禁毒咨询热线,广泛宣传毒品有害的思想,告诫人们远离毒品。在这方面,政府近年来一个比较大的举措便是建立了永久性的“药物资讯天地”展览馆,作为进行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的基地。该展览馆由香港赛马会赞助,2002年完工,2004年6月正式启用。展览馆占地900平方米,除了一般的展览以外,还设有互动影院和图书馆等内容。2002年“药物资讯天地”第一期为3300余人举办70多项教育活动,招募会员1900人。2004年6月启用以来,“药物资讯天地”的参观者已达到18689人次。
除了自身组织的大量活动外,政府还通过参与、协助和资助等手段,调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极大地扩展了宣传教育活动的覆盖面及其数量。像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明爱乐协会、启励扶青会、香港戒毒会和香港善导会等组织机构,都在这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二,关于立法和执法。香港在与违禁药物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通常,香港由禁毒处提出建议,交立法会讨论通过完成相应的立法程序。至于执法,则由警务处和海关负责。此外,卫生署在管制药物的医用管理、药剂的进出口以及可供用作毒品制造或违禁药物的化学制品原料进出口方面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香港在违禁药物管制方面的基本法律是《危险药物条例》。它对危险药物的认定、贩运、制造、占有、经营、供应和惩罚等作了具体规定。政府根据药物滥用情况的变化以及非法贩卖毒品的趋势,定期对该条例加以修订。除了《危险药品条例》,相关的条例还包括《药剂业绩毒药条例》、《进出口(一般)规例》、《化学制品管制条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修订附表1)规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豁免)令》、《跳舞派对主办单位经营守则》、《2002年贩毒及有组织罪行(修订)条例》、《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等。
根据上述法律,执法部门近年来持续对滥用和贩卖精神药物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打击。2004年,警方便缴获海洛英35.74公斤、“摇头丸”类药品283568颗、大麻草154.89公斤、甲基安非他明15.67公斤、可卡因55.53公斤以及其他一些违禁药物。2004年因触犯毒品罪行而被捕的人数为8295人,其中因制毒、贩卖或占有大量毒品等严重毒品罪行者2807人,因占有危险药品供个人吸食等轻微罪行者5488人,分别比2003年的8652、2827和5285人有所下降。1995年以来,尽管犯罪人数在2000年略有反复,但总体上呈持续下降水平。
此外,香港还加强了打击毒品方面的国际和地区性合作。在香港出任上述特别组织主席一职期间,史无前例地召开了5次全体会议;加强了与内地和澳门之间以及与海外禁毒机构的合作。
第三,关于治疗和康复服务。除了立法执法和宣传教育,治疗和康复服务也是消除药物滥用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特区政府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矫正与康复相结合以及政府主导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服务方式,对于解决药物滥用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借鉴的是香港的戒毒服务通常都与治疗者重返社会、回归正常生活相联系。为此,他们往往动员家庭等力量参与治疗,并为一些治疗对象提供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与经历方面的服务。特别是所谓的中途宿舍(halfway house),更是为成功接受戒毒服务者与正常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于从根本上实现治疗目标起着重要作用。
政府推行的治疗和康复服务根据其对象、目标以及实施者的不同,主要有强迫戒毒计划、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以及美沙酮治疗计划等三种形式。其中由惩教署负责的强迫戒毒计划适用于法院裁定的轻微违法者并适合这种治疗的药物依赖者。惩教署分别设有接受不同性别犯人的两个戒毒所。一旦犯人经法院判定接受强制戒毒治疗,根据戒毒进展的不同,时间通常在2~12个月。犯人康复后必须接受强制监管,如果再犯将被重新送回戒毒所治疗。2004年进入戒毒所的人共1324人,比上一年度减少3%。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与美沙酮治疗计划的对象都是上述接受强制戒毒计划以外的药物依赖者,分别由非政府机构和卫生署提供,其差别在于接受戒毒服务者是住院集中治疗还是分散“门诊”式服务。香港接受政府资助提供住院戒毒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大,其中包括部分专门提供青少年治疗和康复服务的机构,如明爱黄耀南中心、基督教得生团契、基督教互爱中心、基督教正生会等。对于这些非政府机构的戒毒和康复服务,政府通过《药物依赖者治疗康复中心(发牌)条例》进行资格审查管理,并借助政府拨款进行引导和鼓励。由卫生署推行的美沙酮治疗计划又分为代用治疗和戒毒治疗两种。前者以替代海洛英抑制毒瘾为目的,而后者通过逐步减少美沙酮剂量达到完全消除毒瘾为止。截至2004年全港共有美沙酮诊所20间,年内求诊者2485324人次,比2003年减少了3.5%。当然,美沙酮治疗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模式,其使用受到严格管制,所有求诊者必须在配药人员面前服用。
第四,研究工作。药物滥用不仅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受到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研究的指导和资助工作主要由禁毒常务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小组委员会负责。它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医疗卫生界、社会工作界、教育界、法律界、戒毒治疗和康复服务界、地区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代表。从1993年到2000年,该小组共资助有关药物滥用整体趋势、药物滥用者特点、戒毒和康复治疗以及预防教育等方面共31项研究。2002年拨款资助的项目有5项,其中包括三项新立课题和两项原来已经进行中的项目。2004年资助的研究项目有四项。
三、青少年药物滥用及社会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药物滥用问题的形成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相应的社会政策要想取得成效,必须针对社会问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伦纳德(Peter Leonard)曾经分析了社会问题的形成和发展的前提(pre-conditions)、原因(causes)、结果(effects)和后果(consequences)等四个环节,并提出了三级干预的策略。就药物滥用而言,初级干预(primary intervention)的重点是改变社会的总体环境,从而消除导致药物滥用因素的积聚;所谓的二级干预(secondary intervention),则是将重点放在药物滥用的原因及其结果之间,试图通过相应的对策阻止结果的产生;至于三级干预(tertiary intervention)则是一种事后的范围,也就是尽量减小或消除药物滥用对个人和社会的消极影响。[20] 根据上述思想,要想针对青年药物滥用制定有效的政策,就必须深入分析社会问题形成的各个环节及其形成机制。为此,下面我们首先回顾学术界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研究,然后具体分析当前国际背景下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具体原因,最后探讨相关的社会政策。
1.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
关于药物滥用的原因,西方理论界主要有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的解释。[21] 药物滥用的生物学分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早期犯罪学家隆布罗索等的研究,其特点是强调越轨行为与行为主体生理特征(如头颅形状、体形和染色体组成等)方面的关系。[22] 具体到药物滥用及其行为主体生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对酗酒者的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更可能同时成为酗酒者,两者的比例分别为65%和25%;即使被非酗酒家庭收养,那些父母酗酒的孩子成为酗酒者的比例仍要比一般的人高6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的病症,[23]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可能与个体对酒精的新陈代谢能力有关。[24] 然而,光从生理的角度出发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酗酒行为,更是难以解释其他更多的药物滥用现象。研究表明,60%~70%的酗酒者并不具备上述遗传方面的生理特征,而某些具有上述遗传特征的人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成为毫无节制的酗酒者。[25]
心理学研究注重药物滥用行为形成的心理机制以及人格特征的差异。行为主义者否认药物滥用的生理学结论,倾向于从后天学习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一些研究认为,人们滥用药物是因为他们发现服用药物可以给他们带来正向的激励作用;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用药成瘾有助于某些人摆脱消极的感受。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药物效应的认识不同,但是它们都将药物滥用行为的形成与某种经历的体验及其对其需要的满足相联系,将药物滥用视为这两种关系相互促进的结果。与行为主义注重外部因素不同,人格理论则倾向于从个体的内部特征出发解释药物滥用行为。但是,究竟那些人格特征决定了个体对药物的上瘾,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药物滥用者具有被动、缺乏进取和自尊较低等人格缺陷,倾向于借助药物来逃避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尽管人格无疑在药品成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上述理论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指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对于研究对象偏见的翻版,并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26]
当今对于药物滥用问题较为全面分析源自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传统社会学关于越轨行为的研究为认识药物滥用提供了一种指导,像失范-压力理论(anomie-strain)、差异交往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以及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和亚文化(subculture)理论等,[27] 都对我们认识药品成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有关的介绍来看,上述这些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理论似乎缺乏实证研究基础。[28] 此外,澳大利亚学者摩尔(David Moore)评论指出,目前关于青年人药物滥用的研究对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重视不足,并且缺乏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29]
对于青年药物滥用现象的分析,笔者以为,青年社会学关于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的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青年必须通过社会化掌握社会规范才能获得成人资格。当代社会的发展对青年人的社会化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造成了社会化时间延长的趋势。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青年的地位被边缘化,处于成年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控制之下。青年文化为处于这种状态下的青年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依据,为青年人缓解各种压力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冲突性,某些社会阶层的青年并不能借助主流文化实现其需要。青年亚文化往往为这些青年实现其目标和需要提供了选择,只不过这种亚文化的价值目标或其实现手段往往存在着背离主流文化的可能性。[30] 事实上,这种亚文化对主导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背离并不一定存在于下层青年,它也可能存在于大学生这样的天之骄子;只要其实现社会主导文化的价值目标的行为受到挫折,便存在着亚文化在价值目标或手段上替代的可能性。[31]
2.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社会分析
上述理论对于我们认识青年的药物滥用现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到香港的情形,笔者以为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问题: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大量资本从原来一些发达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影响到资本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产生了大量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32] 这种新的形势下的失业具有新的、被称之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特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往往面临着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困扰,表现为被全面排斥于正常社会生活领域之外。[33] 就香港的情形而言,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以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对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挑战,大批工厂北迁导致失业人口上升。失业对那些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青少年遇到的这种社会排斥及其相伴随的前途失望,无疑增加了失范现象的可能性。
其次,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以及青年的特殊影响。1997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这一事件对于原本面临转型的香港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负资产人士数量大幅度上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青年失业率猛增到4.7%,远远高于总人口的2.9%。[34]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组织的社会发展指数测定也表明,青年已经成为社会中少数社会发展指数倒退的弱势群体之一。[35] 因此,90年代末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人数的增长绝非偶然,它是香港社会发展面临挫折的真实写照,是青年人在这种情景下对前途迷茫的一种反映,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追求其价值的表现。
第三,它是当前药物滥用国际化在香港的反映。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药物滥用从制造、流通到消费等环节来说都有国际化的趋势,世界上很难有哪个地方能够完全幸免于难,更何况香港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加强,药物滥用问题出现跨境的新特点,这也给禁毒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36] 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竞争,总是会使得部分青年在其成长过程中遭遇某种程度的挫折,因此,作为一种亚文化形式,药物滥用现象必然长期存在并常常反复出现。
3.应对药物滥用的政策分析
应该说,香港政府在对付青年乃至整个社会的药物滥用是卓有成效的,它的制度健全、执法有力、教育与打击并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内地学习借鉴。但是,诚如上面分析指出的,药物滥用问题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影响因素,因此光靠事后的防范以及简单的宣传教育是难以奏效的,尤其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改善,需要为青年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机会。应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喜人的迹象。在中央的鼎力支持和香港各界的齐心努力之下,去年以来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明显的起色。同时,政府的社会救助正改变以往简单的济贫性思路,试图为综合社会援助对象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自立自强的跳板(springboard)。[37] 教育统筹局的“毅进计划”等措施,也为中五毕业生及21岁以上青年的进修和就业提供了大量培训和鼓励措施。[38] 笔者以为,这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方向。由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特点,尽管我们不能说香港青年的药物滥用不会出现任何反复,但今年来总体上其人数和比例在下降。这也是一种正确的政策思路的反映。
考虑到青年药物滥用问题的亚文化原因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原因,笔者以为,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应该注重对青年各种形式的投资,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资产的积累等措施,促进青年的自立自强。[39] 我们要改变传统矫正性的单一工作思路,更为强调社会政策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青年的各种投资性政策,确保青年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前途,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因各种挫折而产生对社会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偏离。包括以药物滥用这种不被认可的手段追求虚幻的、社会价值的替代性目标及其体验的可能性。
注:本文选题源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2003~2004学年第一学期“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和社会问题”课程小组的讨论与演讲(presentation)。与同组的四位香港本地同学罗卓蕙、陈慧敏、刘颖璇和黄惠琴小姐的讨论,对于作者掌握香港青少年药物滥用情况及有关资料受益匪浅。特此致谢。
标签:中国禁毒数字展览馆论文; 禁毒知识论文; 戒毒药品论文; 毒品的危害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摇头丸论文; 药品论文; 戒毒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