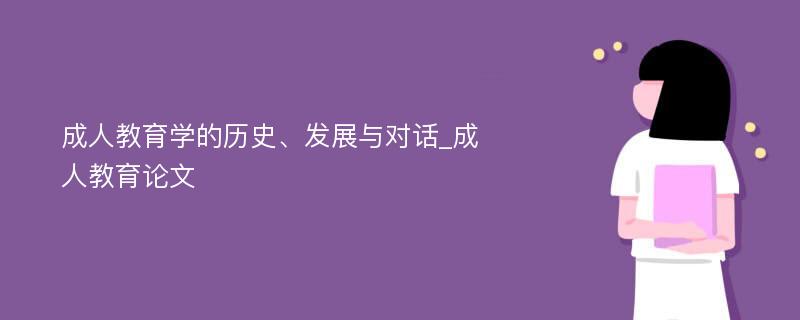
成人教育学的历史、发展与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成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71(2012)03-0005-07
成人教育学(Andragogy)已名列教育谱系学,并成为教育学大家族中的一员。对成人教育学起源及发展史的检讨,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这门新学科,而且有助于将该学科的许多原则应用于继续教育、职业培训及社区工作等诸多领域。
一、什么是成人教育学
在教育学大家族中,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既有相同的根源又有不同的诉求。20世纪20年代,伴随成人教育的系统组织和实施,儿童教育学模式逐渐受到质疑。在欧美众多专业工作者和研究者努力之下,“Andragogy”(成人教育学)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尽管成人教育学远非“如何教成人”(andra)的“学问”(agogy)那么简单,然而自产生以来成人教育学就力图与儿童教育学(Pedagogy)区别开来,并表明自己是为成人提供的教育。
从文字学角度看,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都源于古希腊语。在古希腊语中“pedagogy”与“paidagogogs”同义,都起源于引导孩子到学校去的奴隶,后来则成为“教师”的代名词。单数“pais”和复数“paidos”与“child”同义,加上“agogos”(引导)这个词汇,就形成了“pedagogy”,即通常所讲的“儿童教育学”或“普通教育学”。“andra”这个前缀在形式上等同于“pedagogy”,单数“aner”与复数“andros”都是指“man”(成年男子),于是这两个词的结合便产生了“成人教育学”(Andragogy)。
在传统观念看来,成人是天然的“教育者”而不是“受教育者”。这样的谬见直到终身学习观念普及后才得以修正。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持续学习过程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复杂。因此,用成人教育学来表示这样一种复杂的、专门的学问是适宜的,这也是世界各种语言学词典将其加以永久记载的重要原因。在一定意义上说,成人教育学是一种试图发展有关成人学习这一特殊领域的理论。以诺尔斯为代表的成人教育学者关于成人学习的基本假设,较为完整地描述了成人学习的基本条件和要素。他们认为成人比较明确地知道学习的价值、学习的目的、学习的内容、学习的倾向以及方法的偏好。从实践角度而言,成人教育学意味着从事成人教学的教师需要更多地关注过程而不是所教的内容。因此,案例学习、角色扮演、模拟学习以及自我评价被视为是最适宜成人的方法,成人教师宜扮演辅助者或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而不是讲授者或知识分类者的角色。
基于上述假设,许多研究者归纳和推演了许多规则。譬如:成人需要参与教学设计和评估;经验(包括错误的)为学习活动提供了基础;成人对于与他们工作或个人生活相关的学习具有最大兴趣;成人学习以问题为中心(Problem-centered)而不是以内容为中心(Content-oriented);等等。简言之,成人教育学是一门不同于儿童教育学的学问。成人教育学是被用来表征关于“成人的教育和学习”的一套术语。从历史来看,有人将其视为“帮助成人学习所使用的不同设计策略和方法”;有人至今使用这一术语来表示“指导有关成人学习以及当成人在各种情形和环境中学习时所需考虑的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的一种理论”;也有人认为它是“一套成人教学的技术性工具和技巧”。[1]
二、成人教育学的历史根源
有趣的是,成人教育学的东西方文化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历史时期。诚如著名成人教育学者希尔·侯尔(C.O.Houle,1989)所言,古时所有伟大教师都是成人的教师。例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圣经时代的希伯来先知及耶稣,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时代的西塞罗、欧几里得和昆体良等。成人教育学者杜尚·萨维切维奇(Dusan Savicevic)也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智者、古罗马以及人文主义复兴时期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均存在关于人的一生都需要学习,在生命不同阶段有探求知识的特殊领域和方法的相关思想和见解。萨维切维奇将17世纪的夸美纽斯视为成人教育学的奠基者。因为夸美纽斯希望为所有人提供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和学习,并曾要求为成人设立特别的机构、形式、手段、方法和教师。[2]我国学者高志敏教授也表达过类似观点,认为“成人教育”早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所实践和论述,并将这一历史传统延续至杜威。因为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强调过:“真正的教育起始于离开学校以后,人死之前没有任何理由停止教育!”[3]
在美国学者恩斯克(John A.Henschke)看来,尽管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德国,但组成这一术语的相关概念却早于17世纪的夸美纽斯,甚至可能追溯到古希腊。他声称在耶稣基督以前的时代,希伯来先知所使用的各种希伯来词汇,如学习、教学、教导、引导、领导以及榜样、道路、模式等,为成人教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他甚至期望通过对这些词汇的探究,确立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成人教育学定义。[4]国内有研究者表达过类似主张。在对甲骨文中的“教”、“育”、“学”、“习”等词源考证的基础上,有研究者认为人类教育最初形态实质上包含了成人教育学的基本元素。中国古人使用上述词汇表达的涵义不仅仅是指称“儿童教育学”的,而且是指称包括成人在内的整个人类自身的教育的。但是,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我们渐渐把“教育”的对象狭隘化,错误地理解为仅指“儿童”或“未成年人”。[5]
三、成人教育学在欧洲的起源和发展
达尔普(Draper,1998)认为,追溯成人教育学或成人教育形成的历史,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十分重要。因为这意味对成人教育过程的人性化及理解所作出的努力。[6]
(一)成人教育学在欧洲的诞生
德国班贝克大学教授雷施曼(J.Reischmann)认为,“Andragogik”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1833年凯普撰写的《柏拉图的教育理念》(Plato's Educational Ideas)一文中。凯普以“成人的教育学或教育”(Die Andragogik oder Bildung im maennlichen)为题论及成人终身学习的问题。然而,由于柏拉图从未用过此术语,加之德国著名学者赫尔巴特的反对,“Andragogik”在德语世界并未流行开来。赫尔巴特固执地认为,只有具有可塑性、可教性的儿童,才能通过教育使之形成预期的人格或德行,如若坚持成人教育的观念,那么将会导致一般人过度依赖保护与监督。
“Andragogik”这一术语再次获得新生已经是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20世纪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激进主义者在民众教育领域投入大量工作,并由此提出“成人教育专业化”问题。1924年(也有人说是1921年),法兰克福劳工学院教师罗森斯托克(Eugen Rosentstock)在一份报告中强调“成人教育需要特殊的教师、方法和哲学”,并使用“Andragogik”来指称这些特殊需要的集合。罗森斯托克甚至认为,成人教育学是拯救德国,使德国民众获得“重生”的唯一途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随着理论逐渐运用于实践,成人教育学一定会成为一门不可或缺的学问。罗森斯托克还将“儿童的教育”、“儿童教育学”和“假的成人教育”、“煽动的学说和方法”(demagogy)与“真正的成人教育”(Andragogik)进行了区分。
这里需指出的是,曾经努力将成人教育学放到一个更广范围之下的不止罗森斯托克。20世纪40年代,德国人库尔特·勒温(K.Lewin)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群体动力学的研究推动了成人教育学在德国的应用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伴随成人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发展,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首先在欧洲流行与传播开来。在那个时代,前苏联教育史学家麦丁斯基(Medinski)曾拼凑过“anthropogogy”一词来表示成人教育学。1951年,瑞士精神病医生海恩奇·汉塞尔曼(Heinich Hanselman)在《成人教育的本质、可能性和界限》(Nature,Possibilities and Boundaries of Adult Education)一书中使用成人教育学论述非医疗治法和成人再教育等问题。1957年波格勒(Franz Poeggeler)撰写的《成人教育学导论:成人教育的基本问题》(Introduction to Andragogy:Basic Issues on Adult Education),被里斯曼(Reischmann)称为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的“第三次复兴”。荷兰人藤·哈夫(T.T.ten Have)也曾拼凑过“agology”这一术语来表示成人教育学。
(二)成人教育学在欧洲的传播与发展
“二战”期间,经由雷德林斯基(H.Radlinska)的应用,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家逐渐接受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在上述诸国,一些学者不仅将成人教育学提升到科学讨论水平,而且在理论和应用方面开展了许多研究,使其成为在大学学习和研究的受人尊敬的领域之一。奥格瑞佐维奇(M.Ogrizovic)、萨维切维奇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为成人教育学在东欧乃至世界范围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扎格兰布达大学、贝尔格莱德大学,以及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德布莱森大学相继创设成人教育学系并设立成人教育博士学位。在一定意义上说,贝尔格拉德大学、萨格勒大学、卢布尔雅那大学、萨拉热窝大学、斯科普里大学等引导了成人教育学入驻东欧的进程。“二战”结束后,这些大学的专家大多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理事会的工作,他们成功地将成人教育学的理念带到非结盟国家,因为此时的南斯拉夫是这一组织的政治领袖。
“二战”后,欧洲终身学习实践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成人教育的专业化。新机构的建立,新的研究、出版物及规划的增长,使成人教育学不仅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而且作为一项运动得到推广。特别是在欧洲,成人教育和学习成为欧共体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相关利益、行动和规划整合的组成部分之一。总之,不断成长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增强了澄清成人教育基本概念的需要。这种趋势对于进一步加强成人教育学的地位来说本应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不幸的是,欧洲政治格局的巨变在这一历程中扮演了消极角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东欧还是东欧之外的国家都有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反对任何可能导致触及过去时光的任何事物,这种倾向不幸同样发生在成人教育学身上。“后社会主义浪潮”几乎使成人教育学在这些国家消失。然而,庆幸的是目前有许多学者重新回到欧洲成人教育学遗产上来,并试图挽救“将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悲剧。
四、成人教育学在美洲的传播和发展
成人教育学诞生后的另一“国际旅行”路向是美洲。自欧洲到美洲之后的成人教育学,不仅已是一个广布全球的术语,在欧洲许多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也获得了来自美洲同行的支持,而且由于两个大陆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极大地增强了该术语所代表学科的声势和力量。
1929年至1948年期间,伴随成人教育的发展,美国成人教育协会主办的《成人教育杂志》刊登了大量来自实践第一线的教师如何采取新的态度和方法以摆脱儿童教育学模式影响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学者开始对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并逐步离析出相关原则。马尔科姆·诺尔斯的《非正规教育》(1950)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7]到了20世纪60年代,不仅在北美而且在欧洲,大量有关成人学习的知识还来自于治疗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老年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通过理论家的努力,全面的、结构严谨的成人学习理论得以出现。[8]
(一)北美早期成人教育学的传播和研究
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首次美洲之行据说与林德曼(Eduard Lindeman)有关。林德曼被誉为“美国第一位系统论述成人教育的专家”和“成人教育精神之父”。1926年,林德曼相继发表《成人教育学:一种成人教学的方法》(Andragogik:The Method of Teaching Adults)和《成人教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dult Education)。很明显,前者书名就借用了“Andragogik”这一术语。还有一种说法是,1927年(也有人说是1926年),林德曼与安德森(Martha Anderson)在合编的《借助经验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Experience)一书中共同使用了这一术语。在上述著述中,林德曼强调成人教育是社会活动家最可靠的工具。成人教育体现了一种基本权利的实现及正常期望的满足,而不是对经济、知识水平低下人群的一种施舍,成人教育学是成人学习真正的方法。将林德曼视为最早使用并将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从德国带到美国的英语作者,大概是没有争议的。但是,林德曼的传记作者斯图沃特(Stewart)曾认为林德曼仅仅在两次场合中应用过这一术语。这一新术语似乎没有对任何人甚至其传播者本人产生深刻影响。究其原因,在欧洲成人教育学主要指称“成人教育的研究科目或者成人教育的科学”,这与后来形成的强调“成人学习”或“自我导向学习”的美洲传统或美国式成人教育学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林德曼时代,有关成人的心理和学习问题的研究在美国兴起。桑代克(E.L.Thorndike)的《成人学习》(1928)、《成人兴趣》(1935)开启了成人心理和学习研究之先河。马斯洛(A.Maslow)的自我实现需要层次理论(1954)、舒尔茨(T.W.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1961)分别为成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支持,并对美国成人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诚如布伦纳(E.Brunner)等人在《成人教育研究总览》(1959)这部汇集有关成人教育研究初创时期经典著作中所做的评论那样:北美早期成人教育学是以研究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特殊性为先导,以研究成人学习理论为核心。加拿大著名成人教育学家罗比·基德(J.R.Kidd)的《成人如何学习》(1959)则可被视为对布伦纳评论的注解。
(二)北美现代成人教育学的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成人教育界对成人学习内部过程的持续关注,既是美洲成人教育早期研究传统的延续,也进一步丰富了成人教育学的内涵。真正使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在北美广为人知的是马尔科姆·诺尔斯。准确地说,诺尔斯在《成人领导》(Adult Leadership)杂志上发表的《成人教育学非普通教育学》(Andragogy not Pedagogy)(1968)一文首次使用了“andragogy”这个术语,这与诺尔斯本人的记载也相吻合。①诺尔斯在《成人教育学的行动》(1984)中明确记载了他与这一术语极不寻常的结缘经历:
“……1967年夏……一位名叫杜尚·萨维切维奇的南斯拉夫成人教育家参加了我组织的成人学习暑期研讨会,研讨会行将结束时,他兴奋地说,‘马尔科姆,你正在宣传和实践成人教育学’。我反问到:‘什么学?’因为我以前从没听说这一术语。他解释说,欧洲的成人教育工作者合成了这个术语并将其作为儿童教育学的一种对应,这一术语为成人学习方面日益增加的知识和技术提供了一种标签,那就是被界定为‘帮助成人学习的艺术和科学’。对于我来说,这一术语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标签,于是1968年我在一篇论文中运用了这一术语描述我对成人学习所思考的理论框架”。
在《现代成人教育实践:成人教育学和儿童教育学》(The Modern Practice of Adult Education:Andragogy versus Pedagogy)(1970)一书中,诺尔斯最早提出了关于学习者的四个基本假设。(1)自我概念(Self Concept):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成人的自我概念正从一种独立的个性向一个自我导向的人转变。(2)经验(Experience):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成人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并成为一种学习的与日俱增的资源。(3)学习准备(Readiness):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成人对于学习的意愿是其发展社会角色任务的重要导向。(4)学习倾向(Orientation):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成人对于时间的认知从对于过时的知识的应用转向立即的应用,根据这一倾向,成人的学习从一种主体为中心的学习转向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②此外,诺尔斯还勾勒了成人教育学的基本框架。他以“成人教育学”的原则(即成人的独立人格、成人的经验、与社会职责有关的学习和知识的即刻应用)为中心,详细阐述了现代成人教育的使命、功能、结构和形式,论述了如何从满足成人、组织机构、社区、社会的需要与兴趣出发,正确地组织和管理成人教育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帮助成人学习的可行办法。[9]
然而,诺尔斯关于成人教育学的基本假设及相关概念、原则,引起了很多争议。相关争论的焦点是诺尔斯所谓的“成人教育学是帮助成人学习的艺术和科学”。这样的界定明显与欧洲传统有很大区别。在争论中,诺尔斯吸取了有益的观点,并认为将成人教育学的观点应用到青少年的教育中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立场,认为成人教育学“只是另一种有关学习者的模式,可以与儿童教育学的理论模式同时应用。这两种模式都可以用来检验某些理论是否适应于特定情景。另外,如果把这两种模式看作是一个系列的两个端点,而不是看作相互矛盾的东西,那么对于处在两个端点中间的特定情景,它们更加有用,可以使理论更加切合实际”。[10]尽管许多批评者认为,诺尔斯提出的成人教育学概念造成了关于教成人的方法和技术的降低,以及这一术语并不是指称有关成人教育科学的所有领域和方面,但是,他们却一致认为诺尔斯的概念有助于人们接受成人教育学这一术语,是能够与儿童教育学区别开来的一种科学的观念。
与诺尔斯同时代的希尔·侯尔(C.O.Houle)在20世纪60年代初率先对成人学习动机进行研究,并提出有关成人学习动机倾向的定向理论。《探索的头脑》(The Inquiring Mind)(1961)是侯尔对学习内部过程进行探索的代表作。该成果以22位“继续学习者”为访谈对象,根据访谈结果侯尔将这些学习者分成三种类型。(1)“目的指向”型:这些学习者把教育当做一种手段,并具有清楚的学习目标。(2)“活动指向”型:这类学习者只重视学习活动,并对学习环境中的意义十分感兴趣,但是活动却没有明确的目的指向性,或者根本就没有目的。(3)“学习指向”型:这类学习者是为了知识而学习知识,没有其他的目的。侯尔还认为,尽管这三类人由三个交集来表示是最恰当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11]侯尔在成人参与学习和学习动机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对北美成人教育研究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1962年,约翰·斯通(John Stone)和拉蒙·里韦拉(L.Rivera)对成人教育活动进行大规模普查,并于1965年出版第一部全面分析成人教育活动的专著——《志愿学习者》,强调成人注重学习那些与生存密切相关的东西,这可视为诺尔斯、侯尔研究路径的延续。
(三)终身学习时代的美洲成人教育学
受终身教育思想的启迪,北美成人教育学家艾伦·陶(A.Tough)对成人的自然学习进行了系统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没有教师的学习》(1967)和《成人学习项目》(1971)这两份报告中。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成人每年都从事1个到20个主要项目的学习,平均数是8个;只有大约10%的学习项目与教育机构有联系;普遍存在一种“自然”的学习过程。艾伦·陶认为,在自动学习的过程中,成人都要经历大同小异的步骤序列,并在这个序列的某一点上,成人总是要求助于他人的帮助;当成人求助于教师的帮助,教师总是用儿童学的步骤序列来代替学习者的自然序列并干扰他们的学习。[12]艾伦·陶的研究结果不仅证明了成人自然学习是普遍存在的这一事实,而且说明了用成人教育学指导成人学习的重要性。
终身学习的全面实现需要破除旧的社会体制障碍,20世纪70年代,南美成人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挺身而出”并成为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他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为了自由的文化行动》等著作中,极力主张成人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促进社会和政治的变革。这为成人教育学的功能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其后,西方社会教育学“冲突论学派”兴起,一些西方学者运用和借鉴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诠释成人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是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成人教育要培养学生顺应或批判社会分工和社会变革的品质。弗兰克·杨曼(F.Youngman)及其著作《成人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学》(1986)被认为是该领域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成人教育的西方学者及开创之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在北美进入黄金时期。麦基罗(Mezirow)等人提出与完善的转化学习理论,是继成人教育学概念和自我导向学习理论之后,具有北美成人教育学传统和特色的第三大理论。《观点转化教育:社区学院妇女重返计划》(Mezirow,1978)、《转化:成人生活中的成长与变革》(Gould,1978)、《在成年期培育批判性反思》(Mezirow,1990)、《成人学习转化的特征》(Mezirow,1991)、《理解与促进转化学习》(Cranton,1994)、《行动中的转化学习:来自实践的观点》(Cranton,1997)、《转化学习的理论与实践:一种批判的观点》(Taylor,1998)等一系列著作,不仅深刻体现了北美成人教育学的传统,而且丰富与发展了成人教育学的概念。譬如他们认为,学习是为了指导未来的行动而使用先前的解释来诠释一种新的或重新解读一个人的经验意义的过程;成年期的成人比儿童时期的婴幼儿更具有批判转化的能力。对于成人学习来讲,成人所认知的和相信的以及他们的价值和情感都依赖于一定的背景,也正是在相关背景之下所谓合理性、价值与情感才得到体现。总之,转化学习理论主张,形成对相关经验更加独立的信念,评价这些经验的背景,寻求相关意义与合理性的一致性,根据洞察做出决定是成人学习过程的核心。转化学习应该成为成人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13]
通过上面的追溯,可以看出成人教育学在美洲的迅速成长,其动力源自于该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主题的不断丰富,以及相关知识的快速增长。总之,成人教育学在美洲与欧洲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关注重点和领域,构成了成人教育学在世界范围内丰富多彩的成长图景。
五、讨论
1982年,图什特(Touchette)对世界范围内81所大学开设的654门成人教育专业课程综合分析之后认为,成人教育学作为大学学术研究领域之一,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的和稳定的课程范围:“成人教育与社会变化;成人教育性质、问题及其发展趋势;成人教育领域;成人教育组织与管理;成人教育活动的评价与完善;教学理论、教学手段与方法,成人学习者与成人学习,成人教育工作者”。[14]然而,成人教育学的概念和哲学在不同地区却呈现出不同的含义,并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一)成人教育学概念和哲学的地域差异
诚如雷斯曼(Reischmann,2004)所言,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中,对于成人教育学的使用和发展存在更多隐藏、分散以及不一致的地方。
首先,在美国绝大多数关于成人教育学的研究是基于一种大众化的版本,它起源于诺尔斯的著作。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成人教育学是一种关于成人如何学习的观点和理论,但是成人教育学与有关成人的学习或成人教育的领域并不是同义的。在欧洲,成人教育学更多的是被当做一个社会学概念,远远超越于教育。成人教育学起着一种系统性反思或替代者的角色,它与诸如“生物学”、“医疗学”、“物理学”等其他学术性学科等同。
其次,尽管目前作为大学的一种学术性科目的成人教育学存在于许多国家,但时至今日整个欧洲更多地应用“成人教育”(或“成人教育学”)(Adult Education)、“继续教育”(Further Education),而不是“成人教育学”(Andragogy)。有文献指出,2003年美国成人教育教授委员会下属的成员学校没有一个大学机构使用“成人教育学”(Andragogy)这一名称。即使在德国的35个机构中也仅有1个使用“成人教育学”(Andragogy)这一名称,而在东欧26个机构中也只有6个使用“成人教育学”(Andragogy)这一名称。[15]因此,诚如罗比(Robb,1990)早已提示的那样,美国和欧洲大陆成人教育家的差异,是否能够为一种更加充分的成人教育学的描述铺平道路还值得期待。
(二)成人教育学的共同挑战
20世纪90年代,萨维切维奇曾对10个欧洲国家,包括5个西方国家(德国、法国、荷兰、不列颠、芬兰)和5个东方国家(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关于成人教育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进行过比较。结果显示,在5种不同思想阵营中成人教育学面临如下共同挑战。(1)成人教育学是否等同一般教育科学还是从属其下?(2)成人教育学是否能被理解为一种整合的科学,即它不仅研究教育和学习的过程而且研究其他指导和导向形式?(3)成人教育学是否应该描述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教育和学习情境中如何做的问题?(4)成人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可能性是否可以被驳倒?(5)将成人教育学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科学性学科所做出的努力是否会有期待的结果?
尽管成人教育学的欧洲和美洲版本存在许多差异,以及全球成人教育学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但是,萨维切维奇呼吁通过比较和对比的方式,来理解美国和欧洲的成人教育学,并认为它们的研究都有必要加以充分理解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诚如他在《成人教育:从实践到理论构建》(Adult Education:From Practice to Theory Building)(1999)中所言,成人教育研究的绝大部分价值“对于那些愿意将其当做一种方法的实践者而言,成人教育学在于为了他们自己的成长去发现、学习和评价新的事物;理解和认识到运用这种新鲜的方法将提高他们所从事的成人教育实践的水平;为那些正在全面人道主义服务旅程中的成人教育工作者带来更多的智慧和启迪”。[16]
收稿日期:2012-03-11
注释:
①关于诺尔斯何时何处最早使用“Andragogy”这一术语,国内和国外文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诺尔斯于1968年在《成人领导》一书中正式应用了“Andragogy”这一术语;另一种说法是诺尔斯在撰写《成人教育学非普通教育学》这篇文章时“拼凑”了“andragogy”。上述两种说法都有误:首先,《成人领导》是一本杂志而不是书;其次,“拼凑”之说不准确,因为最早拼凑这个术语的不是诺尔斯,而是德国人亚历山大·凯普。
②诺尔斯于1984年、1989年分别增加了两个假定,第五个假定为学习动机(motivation to learn),即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学习动机是内在的;第六个假定为学习需要不同,即儿童与成人“学习的需要”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