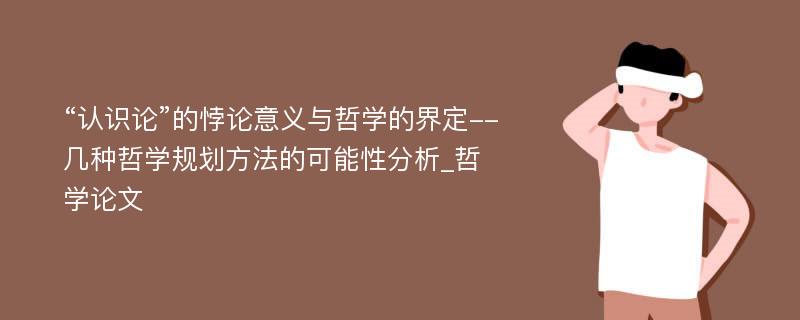
“知识论”的悖论意义与哲学的划界问题——关于几种哲学谋划方式之可能的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悖论论文,几种论文,意义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下中国哲学语境里,“对话”是一个时髦的学术姿态。这种“哲学对话”的主旨实乃缘于近代中国的学术主题,即“东西问题”与“古今问题”②。在如此哲学对话中,我们有以西释中之方法,有以中拒西之态度,也有以今评古之视阈,还有厚古薄今之情怀。观今日哲学话语,可以看到,有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知识论、存在论、生存论等思维预设框架为中、西、马等“在中国”的哲学思想资源进行“井田制”划分的;也有为保住中国文化精神血脉,力拒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循儒、释、道、宋明道学、明清朴学之学脉,力建中国哲学之话语的;也有努力开辟“第三条道路”③的。“哲学”乃西语东来之物,其意义涵项并非仅依某些哲学辞典的词句翻译和解释所能够涵括,要把握其内在思想的奥妙,则需进入西方哲学的传承史中,去体会哲学在西方文化中作为“存在”的意味。如此,才可能进入“哲学对话”的语境,才可能确立我们的对话态度,才可能论说“哲学”对于我们是否“合法”。本文试图以人类的“思想一般”为参照,对西方哲学语境内可能的哲学谋划方式进行梳理,在哲学作为“解释”的知识论的视阈中,来看待哲学的“划界”与“通达”之可能。藉此为我们的“哲学对话”确立一种思想参照。本文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中,哲学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存在方式,实为哲学家们在人作为人的存在中的“哲学谋划”,这些“哲学谋划”实难以走出“逻各斯”的知识论边界。所谓哲学问题就是这些不同的哲学划界方式的自身疑问,可以说,哲学的划界就使哲学作为“解释”在知识论的悖论命运中,不得不走向自身的消解。所以,“哲学谋划”的可能也就是哲学本身的界限确定,因而哲学作为“解释”,可以是建构的,可以是怀疑的,可以是消解的。可以说,哲学谋划的各种方式之间的博弈就形成了西方哲学问题在哲学划界中显现的演化逻辑。
一、“解释”性的哲学谋划方式及其可能
西方哲学与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④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哲学往往从某种预设出发,依据某种人的存在作为“类”意义上的精神需要,以及“以知为信”的原则,以历史的存在为文化背景,来确定某种解释性的前提预设及其意义,如此构成了在“前提预设”笼罩下的哲学问题域,从而构成一种哲学谋划。这些哲学谋划都以“解释”的可能与否作为基本问题。可以说,尽管有的哲学宣称要“消解”某种既定的原则和标准,实际上,这种自称的“消解”本身也是以对“无”前提的设定为前提的⑤。所以,如何构造哲学的解释性前提,就成为西方哲学“解释”性哲学谋划的基本态度。
为了分析西方哲学历史中各种哲学谋划方式的可能,需要确定如下三个分析的前提和语境。
第一,我们认定西方哲学的意义界就是“解释”。纵观西方哲学的历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对历史中的哲学画像的说明是有见地的。“以往的哲学家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对“解释”和“改变”这两个词的意义,哲学界已有很多研究,如何从“解释”进入“改变”并不是哲学自身就能解决的问题。“改变”作为“实践”也是作为一个“概念”在“解释”。我认为西方哲学在思想史的逻辑上,就是以“解释”作为哲学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哲学的存在方式就是“解释”。
第二,哲学的解释是为了解决“何以为信”的问题,西方哲学崇尚的是“以知为信”,所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是处在“知识论”的围城中的。即使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是以“信”为目的的“知识论”式的逻辑论证,即在“本体论”式和“宇宙论”式的证明中,合逻辑地确定上帝的存在。
其三,西方的“解释”性哲学,是以“是”(Being)为叙述工具的。从西方哲学的现代语言转向回溯其因缘,在西方哲学的诞生处已经孕育着这个转向的文化基因。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存在形式只能是从拉丁语传承下来的西方语言,这种语言的根基是Being。在这种语言中所形成的语式是“是什么”的问答逻辑。而从“是什么”如何走进“是”本身是这种语言不可逃避的悖论。可以说,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懒惰的上帝只给了人一套“是什么”的以“Being”为特征的语言系统,所以,人类离不开“是什么”的语式规定。
如果对这三个前提预设可以有一个相对共识的话,那么,对西方哲学作为“解释”性的哲学谋划方式的分析,就可以在古希腊哲学的问题逻辑中得到一个大致的轮廓。因为在西方哲学历史研究中,有一个习惯共识,就是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在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中找到原型。有言曰:“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解”;也有这样的说法:“西方哲学说的是希腊语。”所以,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思想胚胎蕴含了后来的各种哲学谋划的雏形和可能。借用解释学的场景还原方法,到古希腊的生活场景和思维习惯之中,来考察西方哲学谋划方式是如何发生的,可能是一种精神解剖的捷径。
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问题依赖于哲学的发问方式,有什么样的发问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问题。从米利都哲学三杰,赫拉克里特、毕达格拉斯、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思辨,到智者学派的消解性思考;从柏拉图的理念之国,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哲学问题。从哲学问题的演化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谋划方式或思考类型,即:宇宙论、本体论、怀疑论。这些哲学的谋划方式都是出于哲学的原始发问。所谓哲学的原始发问是希腊人对于存在以“是什么”的方式进行的解释性发问。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一方面都在追寻说明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始基、本原、理念、本体);另一方面又都在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试图对那个本原或本体说出“是什么”。这种悖论窘境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说哲学的三种谋划方式就是由这个悖论划定的,也就是我们如何说清楚这个世界,我们能否说清楚这个世界。
所谓宇宙论的哲学谋划方式是以因果律为思考原则,依时间的线性逻辑,对世界作为存在的本原以“是什么”的方式,说出它是“什么”。对本原的追问体现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这样的追问中所形成的解释框架,从追溯本原来说,还难以超越“由果溯因”,并在时空中寻找可以具有解释能力的存在者的思考方式。在宇宙论的哲学谋划方式中,那个“因”只能是具有动变能力的某种存在者。这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历史中表现得很明显。那些对存在之“如何”有着特别“知道”情感的哲学之人,提出了各种本原说,他们用“水”、“空气”、“无限者”、“火”、“数”、“种子”、“原子”等具体在时空中的存在者,解释万物何以如此的问题。这种哲学谋划方式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时间的线性思维从万物的生成来追溯本原;另一类则是在空间的结构思维里把握万物的构成要素。这两类宇宙论的哲学谋划方式,为以后西方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科学,提供了基本的思维逻辑。
本体论的哲学谋划方式是接着宇宙论哲学谋划方式的问题而出现的。沿着“时间”和“空间”的因果律逻辑去寻求对存在万物的解释根据,思维的惯性会使我们怀疑那个具有时空固定的存在作为解释根据的终极性。古希腊智者学派的那些有点“后现代”意味的对“宇宙论”哲学谋划方式的质疑,催生了“本体论”哲学谋划方式对“时空”性的因果律的超越。所谓“本体论”的哲学谋划方式就是在纯形式化地构造两个世界(形而上和形而下)中,分别出实在与非实在,从而为合乎逻辑地解释存在的所以然建立一个框架。本体论的哲学谋划方式有两个构造原则,一个是必须区别出两个世界,并对这两个世界依据思维的逻辑确定其意义;另一个是在纯形式中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形而下,这种超越对纯形式的逻辑赋予了至上地位,这也是“逻各斯”意义的逐步显现。实际上,本体论哲学谋划方式就是依据合逻辑性的理性原则,设定一个可以对现象界进行合理性解释的本体界,为确定现象界的意义,从本体界找到能够赋予现象界以某种意义的根据。柏拉图设定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形式”等,都属于这样的哲学谋划。这种谋划的主旨还是力图在超越时空的语境里,为“解释”万事万物的存在,在形式系统中为存在的“是什么”,构造一个合逻辑的“说”(解释)的“何以可能”的根据。
怀疑论的哲学谋划方式的出现,是藉“宇宙论”、“本体论”对存在总要说出其“是什么”的一种质疑和超越。因为在对存在要指出其“是什么”中,其“是”之“如何”必须要确立“是”的根据。这种“是什么”的思维习惯,来源于西语作为“是”(Being)本身的“问答”逻辑的要求。“是”作为“是”必为“是什么”所显现,而“是什么”的“什么”的确定,只能依据在时空中的存在的经验和对存在形式化的逻辑规定。但是,在这样的“是什么”中就合逻辑地隐藏着“不是什么”的逻辑黑洞。因此,在西语的语式中,在“是什么”背后总有一个对“是什么”的消解。这种消解可以显现为对“是什么”的否定,也可以显现为对“是”本身的质疑,质疑来自于“是本身”的“为什么”发问本身。所以,在哲学史上,这种对“是什么”的消解就成为怀疑主义哲学谋划方式的逻辑根据。在西方哲学史的哲学转型时期,都会出现以消解原来的“是什么”解释模式为指要的哲学谋划方式,如古希腊的智者学派。高尔吉亚以这种谋划方式提出了三个哲学命题,即:“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⑦由对存在的质疑,到认知和意义解释可能的质疑,触及到了西方哲学作为意义解释的尴尬命运。西方哲学的发展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命题的可能与否而构成了各种哲学谋划方式的思维游戏及其博弈。
古希腊哲学形成的这种哲学精神也延伸到了中世纪的哲学中。西方哲学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达“信”的模式,总要有一个前提或出发点的设定,这种哲学的“设定”性就为上帝的存在意义留下了理性空场。所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从学理上,也是基于西方语言的这种“解释”方式。因此,西方的上帝作为一种理性的设定就不得不陷入需要论证才得以存在的尴尬境遇之中。所以,无论是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还是“宇宙论证明”,都是由西语这种哲学谋划方式所决定的。即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系中,“是”(Being)本身和“是什么”是西语中的两种存在方式,所以,上帝的存在也只能是以“是”或“是什么”的方式出现。本体论的证明侧重于以“是”本身为论证工具;而“宇宙论”的证明则更亲近“是什么”的论证方式。
古希腊哲学的这三种哲学谋划方式在历史中发展出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以知识论思维方式为主导的古典哲学以及以消解哲学的“知识论”情结为要义的现代哲学⑧。从哲学作为“解释”的视阈来说,这些哲学谋划方式都是出于西语的可能逻辑,在西语的逻辑中,这三种哲学谋划方式穷尽了Being这种解释方式的可能界限。也就是说,哲学作为解释性的智慧,只能在Being的语言中展开解释的逻辑,由此为“以知为信”的文化建立以“知识论”为基础的解释模式。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哲学谋划方式呢?
二、作为“解释”的“知识论”的哲学问题与哲学的划界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对哲学问题的演变我们往往以一种进化的逻辑给予线性的解释,但哲学问题的变化并不是依进化的线性逻辑进行的,而是在于如何为哲学的意义域划界。可以说,哲学问题的更新与哲学谋划方式的转型就在于哲学发问方式的改变,这也就是哲学划界方式与哲学的意义界的改变⑨。如前所述,西方哲学作为“解释”性的哲学,只能以“是”(Being)为叙述工具,也就是在Being这种语言中所形成的“是什么”的问答逻辑中,在“是”与“什么”的区别与划界中,建立各种哲学“解释”模式。“是”与“什么”所构成的“是什么”的逻辑形成了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的哲学情结。这样,西方哲学就在为能得以“解释”而“以知为信”。可以说,“解释”、“Being”的语言系统和“以知为信”是西方哲学形成各种谋划方式的关键词。由这些基点围筑起来的“知识论”的思维逻辑,使得西方哲学的各种谋划方式,通过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变来确定哲学的意义界。也就是说,西方哲学的问题转型依赖于哲学的划界。我们从西方哲学发问方式的转变中可以看到如此的思想轨迹。
从哲学发问方式来看,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是从对世界万物之“是什么”说起,而“是什么”作为一种本质论意义上的发问,实际上是对万物存在之何为真的发问。这种发问所形成的问答逻辑,划定了西方哲学只能对于存在之如何的“说明”,亦即“解释”。所以,西方哲学就有个从何说起,以及能说到哪儿的问题。从何说起与说到哪儿的问题就是哲学的划界问题。哲学的划界是从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建立开始的,从巴门尼德的“存在问题”到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学说,都是以不同的哲学谋划方式为哲学的意义界划定界限。
继米利都三杰对世界本原“是什么”的发问,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对“是什么”这种发问方式注入了新的理解,拓展了这种说话方式的意义。巴门尼德在《论自然》中讲到:
1.“……只有那些研究途径是可以设想的。第一条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遵循真理。另一条是: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因为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认识(这当然办不到),也不能说出的。”
2.“因为能被思维者和存在者是同一的。”
3.“必定是;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因为它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者存在是不可能的。”
4.“证明不存在者不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要让自己的思想远离这条研究途径。”
5.“所以只剩下一条途径,就是:存在者存在。”⑩
因为他直接对“是”本身用“是什么”的方式进行发问,从而超越了泰勒斯以来的将“是”本身只是作为存在者的预设前提,即仅对“是”以外的具体存在发问,如水、空气、火等。叶秀山先生认为:巴门尼德提出了不同于具体存在者的那个“存在”,不同于“是什么”的“是”本身。“他的问题重点在于:对于变化万千的感觉世界,你可以说‘是’(存在、有),也可以说‘不是’(不存在、没有),但对那个‘是’(存在、有)本身,却不能说‘不是’,‘是’就是‘是’。不过,巴门尼德没有分清‘为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对那个本应‘什么也不是’的东西也要问个‘是什么’,说它‘是圆的’,‘是有边的’等等。这就奠定了古希腊哲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传统。”(11)这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模式,就是用“是什么”的说话(思考、把握)方式对于那个“存在”本身或“是”本身说出“它是个什么”。巴门尼德对“存在”“是什么”的发问,也就是以“存在”之为存在为界,这里的哲学的意义界是“存在”的自身同一性。
西方形而上学作为体系的真正建立,应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的。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都承袭了前人“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为了克服巴门尼德将“存在”作为对象与“是什么”的存在者的言说方式的悖论,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这个范畴。“理念”与具体的水、空气、火、数、原子等存在物相比是“共相”,是多中之一;但又是可以指向的,是与“存在”本身或“是”本身不同的共相。这种共相于是就有了分别的共相(12)。因为这个共相不是那个“存在”本身,而是苏格拉底、张三、李四等所有个别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人的理念”。美的人、美的花、美的画等所有个别的美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美的理念”。可以说,“理念”是巴门尼德的“存在”再加上某一种特殊性(人、美等)的一种规定。柏拉图的理念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巴门尼德的哲学矛盾,即理念作为“存在”的一般是可以用“是什么”进行指向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和叙事结构对理念进行指称,并说出“理念”是个“什么”,具有怎样的意义。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又提出了“本体”的概念,同柏拉图的“理念”一样,他也试图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去追寻万物存在的根据。无论是本体的指向,第一实体、第二实体的划分,还是“四因说”的提出,都是为了对存在的所以然给予合乎理性(逻辑)的说明。实际上,也都是在用“是什么”的思维方式或言说方式指出本体“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并未超出柏拉图的思想框架。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想用“理念分有”和“四因说”超越了巴门尼德的问题,但这种超越是以“遗忘‘存在’本身”(海德格尔语)为代价的,“存在”的问题还是留给了后人。
古希腊哲学以追求世界本体作为“解释”的可能,即为哲学的“解释”可能设定了界限。古希腊哲学尽管有多种谋划方式,但都是在如何设计对“存在之为存在”的各种可能的解释模式。这些解释模式就是为“存在之为存在”限定了意义的可能域限。他们的共性特征是以“是什么”为“解释”的根本原则,并以“是什么”为“解释”的可能与否划定界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是依“西语”的“Being”为“解释”工具,对“存在”以“对象化”的方式进行“是什么”的说明。但这种以“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对“是”本身作出解释,则必然陷入一种我们何以能对“是”说出其为“什么”的理论困境。如此产生了我们能不能说,能说什么的疑问,这也就催生了近代哲学对“解释”主体能够知道什么的反思,而这正是康德的哲学谋划与设计的主题。
康德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理性作为“是什么”有能力去对那个本体(“存在”或“是”本身)说“是什么”吗?在康德看来,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圣哲将理性作为既定的,是无须证明的自明性,人们所使用的“是什么”的概念、判断等知识形式直接就是对本体的把握。但这种形而上学是无批判的,是没有划界的,因而是独断的,最终只能走向对本体的否定。康德认为,在人的僭越本性追求世界的本体作为“是什么”的时候,应该对“是什么”这种对“存在者”言说的知性划界,即为人们用“是什么”只能说什么确定“应该”的界限。有了“应该”的界限,才能在哲学中为“存在”本身留下地盘。叶秀山曾指出:“康德很清醒地看到那个总体的‘存在’不是知识的对象,即不能问‘是什么’,他说‘存在’不是宾词,有关‘存在’‘是什么’的那些‘什么’,只是些理念(观念)。”(13)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的形而上学”。为了区别与以往的形而上学的不同,康德对形而上学以“科学”作为规定,使形而上学能够像任何综合判断所构成的科学一样,通过纯粹理性的“批判”(划界)而成为可能。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在纯粹理性的预设中确定知性、理性的使用界限,亦即: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可能是在其能力所能达至的“应该”的界限内所给予的。康德对理性能力或对“是什么”的语式的使用划界的努力,使他的哲学成为任何哲学都必须面对的一道关隘。诚如陈康先生所言:“关后尽可有方向分歧的路径,但人既至关口必先过关;此外并无一条非危机四伏的道路可以引导至那将来的路线。”(14)康德哲学的结论是:“是什么”只能去说“是什么”;只能对那个“什么”说“什么”,而不能僭越,否则就成为独断。而那个“存在”本身或“是”本身则是“应该”的,其意义在于其作为实践理性,给予人们以“应该如何”的指向。所以,康德哲学的结果是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不是什么”,即“什么”的否定),“应该”不是“是什么”,“应该”只能是“应该”。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依据知识的习惯而对那个“存在”的“应该”问“是什么”,但其具有的“不可回答性”使人从此就进入了道德实践和宗教信仰领域,因为“道德”是“自由”的,是对“只能如此”的必然的“是什么”的超越;而宗教信仰则是知识理性所管不了的。康德的哲学“止于至善”。康德澄明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的矛盾,为“解释”主体的“我”能说什么“划界”,完成了“知识论”意义上的“解释”可能的论证。
哲学的“解释性”和人类本有的知识求解本性,使以后的哲学必须将康德问题作为出发点。康德的问题是:1.古希腊以来哲学的困境(两个世界与言说方式的悖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个困境具体说就是:我们只能用“是什么”这种言说方式去追问感性、现象世界背后的那个本体,但这种言说方式是不可逾越的,因此,那个应该作为“存在”本身的本体,却在这种“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中,成了那个本应该超越的“什么”,即A成为了B。本来区分开的两个世界,却不得不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中还原为了一个世界。因此,哲学应该反身自问:我们到底有什么能力?我们的认知能力或言说方式能把握那个本体吗?如果不能怎么办?2.如果按康德的意向,放弃古典哲学中本质主义的统一两个世界的欲望,即知性、理性在现象界和本体界各司其职,我们用“是什么”的语式只去言说感性、现象,那么,作为本体的“存在”(上帝、灵魂、物自体),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言说呢?如果我们只有“是什么”这种言说方式,如果那个与“存在者”或感性、现象不同的“存在”或“是”本身的本体是不可言说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康德之后,以至于今天的哲学依然沉浸在这样的“解释”困境之中,以至于不得不走向维特根斯坦“不可说就应当沉默”,以及海德格尔的“无之无化”(15)。
可见,西方哲学的哲学谋划体现为哲学的划界,那么,西方哲学何以必须在“解释”的“围城”中不断地为自己的“围城”“划界”(16)?它能不能走出这个“解释”的“围城”?
三、“知识论”的悖论意义与哲学的自身界限
如前所述,西方哲学之所以不断地变更着哲学的谋划方式,之所以必须为“解释”确定合理性的标准,之所以要为哲学的可能意义划界,都源于我们所确立的关于哲学谋划方式的分析前提预设,我们所设定的三个前提预设,规定了西方哲学的可能立场只能是“知识论”的。因为西方哲学之为“解释”,为的是贯彻“以知为信”的哲学原则,而“解释”的可能又离不开西语“Being”的叙述方式。这三个前提预设对西方哲学而言是难以逾越的,“知识论”的悖论意义又是不可超越和消解的,所以,作为“解释”的西方哲学在“Being”的语式的围城里,围绕着“是”和“是什么”的博弈,就会从解释的哲学走向“解释”自身的消解,这里,也就是哲学自身的界限。
高尔基亚的三个命题是深刻的,它道出了“知识论”的悖论意义,当他对物的存在,认识的可能,以及意义的通达发出质疑的时候,也就道出了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使哲学的谋划不得不陷入悖论命运的尴尬境地,这就是依据哲学的“解释”本性,必须要对存在以“是什么”的方式进行说明,作为“解释”的“说明”必须是清楚明白的,但以何为清晰明白的标准却又是需要论证的,需要说明的,这就陷入了一种自身的清楚明白需要自身来证明的解释循环。从哲学上说,就是对“是”本身必须要以“是什么”的方式说出其是“什么”,但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同一律原则的。因此,哲学作为“解释”就走进了不可解释的尴尬境遇。
哲学作为“解释”的这种尴尬,应该渊源于知识论问题的悖论本性,因为“解释”就是要说出“是”本身和“是什么”。实际上,知识论的问题不论是“知道”(求真),还是告诉(理解和解释),在哲学上都表现为对知识所能与不能的自我辩护。这种知识的自我辩护体现为,或者设计一种思想框架,为指出知识“是什么”找到一条路径;或者在某种设计与谋划中为知识的可能找出可信的理由。这里表达出的思维逻辑是:因为上帝也要掷骰子,人只能步上帝的后尘,所以在知识论中,对于预设前提的设计与谋划作为知识的前提是不可缺少的。有了设计与谋划,才可谈得上知识的清楚明白,才会有知识的自明性,才会有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所以,在知识论中,“我觉得”,“我相信”恐怕是不可缺少的。这里所昭示的就是知识论的悖论本性,即知识必依缘于知识以外的“觉”、“信”,才能对知识有所辩护,知识自身不能证明自身。实际上,知识论的这种本性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不可思议的洞察。柏拉图在讨论“美诺悖论”时就触及到了这个知识论的基本问题。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的“美诺悖论”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人既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研究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他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而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不能去研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所要研究的是什么。”(17)把这段话换成知识论的话语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些观念是真观念,所以试图知道,但是既然本来不知道真观念,那么即使遇到了真观念,我们也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想知道而原来不知道的,于是,由于没有用来判别真观念的观念(判别性观念也是本来不知道的真观念的其中之一),结果就总是白白错过了真观念。”(18)“美诺悖论”的实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只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在这句同义反复的语句中却隐藏着知识论的最深层的秘密——知识论规则(同一律和不矛盾律)与知识论悖论。
从意义理论来看,知识的同一性原则或同一律的实质却是个悖论。如果说柏拉图的“美诺悖论”天才地洞察了知识论的基本问题,那么,我们从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和我们对于不知道的是不能知道的知识论的命题中,就可以引申出两个结论:首先,既然我们只能知道所知道的,不能知道所不知道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知道了,知道也就失去意义了(这里隐含的是与知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关联);其次,当我们在确定这两个相对的命题时,我们何以知道什么是能知道的,什么是不能知道的?“知道”在“美诺悖论”中进入了一个不能自我解释的悖论循环中。因为在确定知识的同一性原则时,又必须以知识有不同一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是像法律的制定是以不遵守法律的现象的存在为前提一样。所以,知道是对知道的知道,同时知识也是对不知道的知道。这就是知识论不可逃脱的悖论情结。这两个结论所昭示的问题非常重要,其中隐含着知识论乃至哲学的可能走向。西方哲学后来的发展说明,知识论在对知识所能与不能的把握中,总离不开它的悖论情节和这个悖论所规定的历史宿命。
如此说来,作为“解释”的哲学谋划与设计,以“是什么”的言说方式去为“是”本身划界,虽然可能以“是”(Being)的意义为半径,确定可能的哲学划界和谋划方式,但因其不可逃避的“知识论”的悖论困境,致使哲学从哲学的“解释”走向了“不可解释”,从而哲学也就走向了自身的消解。这种逻辑的必然性论证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处在这个境遇中的我们,自然会生发出对哲学命运的感叹。哲学自身的消解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主流话语,从康德、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基尔凯郭尔,到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等,或者把哲学的自身消解进行到底,或者寻找哲学消解之后的可能及如何。哲学自身的消解使得“历史”、“生活世界”、“无”、“沉默”进入哲学,这种“进入”是以哲学的消解为前提的,如此的哲学就打开宅门,迎接宗教、科学、政治与艺术安家落户。因此,哲学的谋划与设计被哲学的非谋划与非设计所谋划。这就是西方哲学所展现给我们的当代形象。
总之,在西方哲学中,存在各种面对自己认定的问题而提出的各种哲学谋划方式,这些谋划方式在知识论立场上都不得不陷入悖论的窘境。因为这些哲学谋划都是用某种预设的标准给出一个该不该的选择依据。这种悖论的发生源于哲学的使命和意义要为人所面对的世界,作出合乎某种逻辑的解释。这样的哲学作为“智慧”总是表现为对“我与他”(它)说出些什么,这个“说”的欲望就是哲学的存在论意义。一旦从解释的哲学走向“解释”自身的消解的时候,也就找到了哲学的界限,因为只有哲学的自我批判和否定才可能有哲学的消解,在这里,哲学失去了“说”的权利和意义。哲学的现实性在于哲学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为人的精神寻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同时也在哲学作为精神的破坏性中取消了哲学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哲学的存在意义不在于自身的建构,而在于自身的否定和在自身的否定中对宗教、科学、政治、艺术的建构。所以,哲学自身的“不是”可能就是哲学本身。
西方哲学问题与思维的这种特征,对于处在中西哲学比较与对话中的我们来说,可能会激起我们对中国本土文化中“和合”与“圆融”的亲近与渴望。西方有西方的哲学,中国有中国的智慧。在敬畏中的亲近,好像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庄子·齐物论》)这不就是当下哲学界经常不绝于耳的“存在”或“是”本身吗?这不就是我们的文化先贤嘱咐我们的“自然而然”、“道法自然”吗?这不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哲学之道”吗?
注释:
①所谓“哲学谋划”是指哲学思考总是需要确定一个“预设”作为哲学叙述的“始端”,这个预设或者是合乎逻辑的要求,或者是非逻辑的确定。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张蓬:《哲学的始端与视阈——从“所知学”谈起》,《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
②参见张蓬:《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及意义确证原则》,《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③借用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语,意即在东、西方之间的非此即彼之外寻找到亦此亦彼之路。
④“中国哲学”这个提法,需要界定明确其语境意义,否则易改变这个词原有的思想内涵和作为西语东来之思想范畴的意义。这里使用“中国哲学”一词,是借西语来指称中国本土思想的,并非是以西方哲学话语为框架,对中国原有的词汇赋予西方哲学的内涵意义。
⑤西方文化中的“后现代”的“解构”与我国学者赵汀阳提出的“无前提批判”,都属于对“无前提”的设想。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6-57页。
⑧现代哲学虽有多种流派之划分,其哲学主旨要义也各有分别,但其对古典哲学(本质主义)之反动和超越的精神是有共同指向的。
⑨这里关涉到两种不同的哲学史观,进化的线性哲学史观为哲学的演化注入价值性的“优”劣”评判,这样的哲学史写作解释不了现代的哲学问题为什么要回到古希腊哲学中去寻找解释的钥匙,也难以评判西方哲学家对古希腊哲学的敬畏。
⑩以上引文均引自巴门尼德的著作残篇《论自然》,载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著作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32页。
(11)叶秀山:《愉快的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12)陈康先生将“理念”翻译为“相”,可能缘于理念的这种特定意义。
(13)叶秀山:《愉快的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14)陈康:《巴曼尼得斯篇》序,[古希腊]柏拉图著,陈康译注:《巴曼尼得斯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页。
(15)彭富春:《告别海德格尔》(代序),彭富春:《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16)康德和黑格尔之后,哲学走向了自身的消解,但对哲学进行消解的各种哲学又无不是以某种思想的谋划作为宣告哲学失去意义的依据,哲学的消解没有离开对哲学消解的谋划,有一个从哪儿消解,消解什么,怎样消解,和消解之后会怎样的各种发问,这些发问都缘于“Being”的存在意义。此问题是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需要另外行文论述。
(17)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0页。
(18)赵汀阳:《长话短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标签:哲学论文; 知识论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时间悖论论文; 上帝悖论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巴门尼德论文; 宇宙论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