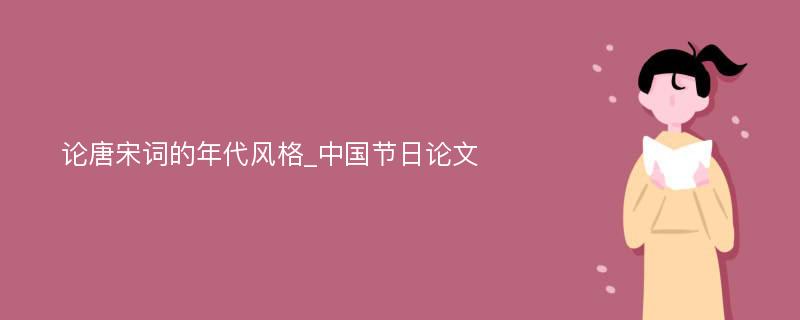
论唐宋词中的纪时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词中论文,纪时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2-0009-07
张炎《词源》卷下列“节序”一条,指出“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如果从词体发展的视野来考察,我们发现,唐宋词中大量的咏节序之作,不仅为词文学增加了一种新的题材类别,而且已构成了词体中一个具有文体学意义的独特品类——纪时体。这一类词也可称为词中的“应时”、“应景”之作,其内容皆与时令节序内容有关,并有着相应的作法和特殊的体式特征,由此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殊的文化功用。纪时体在唐宋词创作中十分兴盛,但历代论词者对这一现象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近年来一些学者或从题材内容方面或从民俗学角度对唐宋词中的纪时之作进行了探讨①,但仍缺少文体学意义上的系统研究,本文论述拟就此作出初步的阐释。
一、曲子词纪时体的形成
纪时体所纪之时,非时事之时,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时日或时代之时,其意近《尚书·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之时,指特定的岁时、时节。故词之纪时体,即谓以岁时节序为表现对象或内容背景的词之体类。以词纪时,既是古代诗歌中纪时传统的延续发展,同时也是唐宋时期岁时文化的产物,更与词体观念的更新和词体功能的扩展紧密联系着。
纪时传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中源远流长,它一方面是诗歌内容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诗歌发生的一个重要动因。在文明程度极其低下的上古社会,作为精神文化高级成品的诗歌,首先是当时社会的文化代表——巫祝——进行祭祀卜筮活动的重要手段,而非一般人抒情言志的工具。进入农耕社会后,随着历法的发明和节令的确立,为顺应自然变化以求吉祥而举行的岁时祭祀,便成为巫祝最重要的常规活动——这也是早期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为了便于记忆和接受在仪礼中配合歌舞的卜辞祝文,古人往往采用整齐简明的韵文形式,最早的“纪时”诗便由此而产生。《吕氏春秋·古乐》所载“昔葛天氏之乐”的八阕古乐章很可能是当时岁祭节祀的组曲②,虽然这类乐辞内容可能不是直接“纪时”,但它应“时”而作,为“时”而歌,从而为“纪时”诗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和环境。
春秋之后,“礼崩乐坏”,文化下移,乐辞写作已为中下层士大夫所掌握,乐辞作为宗教祭礼工具的性质大为减弱,而主要成为一种言志纪事的介体,《诗经》即是这类乐辞的总集。正如《文心雕龙》所言:“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③ 言志之诗已不再是祭礼的附庸,但其世俗的情怀与宗教祭礼一样,关注和感受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豳风·七月》是一篇典型的纪时之作,更多的作品则是将岁时风物用作比兴抒情的喻体和兴体。伴随着文学的自觉,魏晋后,岁时节序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在诗歌创作中被逐渐确立,纪时性作品大量涌现;至唐宋,纪时诗已成为诗歌家族中一个专门的体类,南宋人蒲积中曾集魏晋迄唐宋人咏岁时之作编为《岁时杂咏》46卷,由此可窥其创作盛况。
唐宋时期,作为通俗歌曲歌词的曲子词也加盟到了咏岁纪时的大合唱之中,入宋后创作日富,体格渐丰,蔚成大观。据统计,《全宋词》2万余首词中节序题材之作达1310首之多,占《全宋词》6.2%,在36种基本题材中位列第7(前6位分别是祝颂、咏物、艳情、写景、交游、闺情)④。其实,在其他题材的作品中,岁时节序方面内容也往往掺入其内。从古代纪时诗的发展轨迹看,纪时词实为中国古代传统纪时诗脉绪的续延和支蔓,也是纪时诗的一个新品种。不过,曲子词中纪时一体的形成,并非纪时诗的简单承继与移植,还有赖于适宜的文化环境、词体的内在基因及词体功能与观念的变易等诸多因素。
岁时节令得以进入曲子词的观照视野,首先与当时词体的世俗化特性和应歌娱乐的功能有关。词所附着的燕乐,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性的通俗音乐,广泛流布于当时公私宴集和民间娱乐场所。而各种节日是这些娱乐活动最集中的时间。唐宋时期,由于城市商业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城市娱乐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起源于农耕生产和鬼神祭祀的传统节日此时已完成了它向娱乐礼仪型的转化,成为真正的社会性的佳节良辰。从此,节日变得欢快喜庆,丰富多彩,许多竞技、游艺等文娱活动内容参与其中,并很快成为一种时尚风俗而流行开来。《幽怪录》里有一段故事颇有意味:唐开元十八年的元宵节,唐明皇欲赴扬州观赏夜景。念头刚出,只见眼前虹桥已成,明皇过桥而至,十分开心,于是命乐官演奏了一支《霓裳羽衣曲》。故事所言固然荒诞不经,但从中却可窥见节日间燕乐新声的演奏情景。都市的节序风俗文化,对于作为词曲的燕乐新声的繁衍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节序风俗中的娱乐活动,自然少不了乐工歌伎的丝管歌舞。如果没有节日娱乐的推动,“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柳永《木兰花慢》)的局面是不可想像的。
由于“娱乐”的需要和推动,以娱宾遣兴为己任的曲子词就这样与娱乐性的节日结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感时应景的曲子词也就很自然成了节日演唱的节目。曲子词直接介入节日的娱乐活动,为词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活力,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节序文化。宋人词集有不少是作为唱本而传刻的,如周邦彦的《片玉集》,依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单题、杂赋几类编排。南宋最流行的坊间选本《草堂诗馀》,前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类,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每一类又分子目,凡六十六目。如节序类分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等十个子目。按时令节序编排词集,就是为了便于人们按照不同的时令来选词备唱。据《古今词话》载,柳永初到杭州欲见在此地作知州的老友,但“门禁甚严”,于是便作《望海潮》一词,请名妓楚楚于中秋府会上歌唱。此事或为小说家言,但也可证明节日唱词是当时都市节庆的常例。由上可知,节令唱词已是当时普遍风气,咏时令节序也为词之一大宗。
宋时纪时词蔚成大观的社会大背景是宋代城市的高度繁荣和节日的进一步娱乐化、民间化。两宋城市之繁荣已频见于宋人记载,此不赘述。需要提及的是,与发达的城市商业相伴随的是娱乐业的隆盛,并由此促进了各类节庆活动的兴旺。这种情景在《东京梦华录·序》有关元宵节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城市的繁荣和节日的娱乐化为纪时词的创作铺垫了基础,但是,娱乐性的词与节日娱乐的联系,并不意味着作品内容必然与岁时节令有关,所唱之词也可能与于此无涉。事实上,在曲子词产生的早期——唐五代时,专门歌咏岁时节序的作品并不多,据统计,在《花间集》中有关节序的作品只有3首,仅占所收500首词的0.6%,在22类题材中排第18位。这是因为,早期的词只是在勾栏、宴会等娱乐场所付与歌女演唱的应歌之作,所表现的多是风花雪月这类普泛化、类型化的情事,缺少作者主体意识和真实生活场景的表现,而时令节序则是具体的实在的生活内容,由于这个原因,早期词作的内容也就较少涉及到具体节序景象与感受的描写。虽然词人也常写到岁时变迁与人生感慨,但多为泛泛之语,这表明当时的词还没有真正进入词人自身实在的生活,实际上这时文人也未广泛地参与词的创作;此时词体尚未完全成熟,因而词本身也无力取代诗歌来即时性地直接表现变化着的时令节序。
可见,文人的广泛参与是纪时词繁盛的一个必要条件。纪时词在节日娱乐中特有的文化功用促使文人们积极投身于创作之中。公私宴饮、勾栏歌场,是节日里重要的娱乐场所,也是曲子词的主要演唱之地,节日里由歌女演唱感时应景的曲子词,无疑将大大增强节日的气氛,为人们所欢迎。因此,纪时词也就成了节令佳日里点缀景观的常备节目。两宋名家,几乎没有不作纪时词的。柳永的元夕词宫内应制,苏轼的中秋词遍行南北,都是宋代节令的胜事佳话。纪时词的演唱丰富了节日娱乐活动;同时节日里唱词,也成为词作传播的一个重要形式,许多名篇佳作由此而传唱遐迩,远播人口。这也必然大大刺激起文人们的创作欲望,催生出大量的纪时之作。
宋词节令之作繁盛的关键,则在于词体功能的转变和扩展。北宋时,曲子词虽然仍然像唐五代一样以应歌娱人为能事,但新变已悄然发生,一个主要征象就是词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也就是说,以往多以比兴手法表现类型化情事的曲子词,更多地与词人的真实生活(包括词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现实与自然环境)联系了起来。时令节序是生活中最易引起词人兴奋和感慨的时刻,于是在节日娱乐需求的推动和节日娱乐气氛的感染下,大量的纪时词便随“时”而生,应“景”而出。宋代词体表现形式和手法的发展,也为纪时词的繁盛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技术条件。因为时令节序具有特定的时空规定性,所以纪时词也多具一定的叙景纪事性特点。显然,传统的小令词受其形式限制,对此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以铺叙赋物见长的慢词正弥补了这一缺憾。在柳永、苏轼等词人的努力下,慢词在北宋迅速流行,从而使曲子词的纪事写实的功能得以提升,这使词作对节令景象和气氛的描写变得更为生动和具体。
二、唐宋纪时词的发展
纵观唐至宋金时期的词史,可以看到,伴随着词体的演进和词学观念的变化,纪时词的创作也经历了一个由寥落到繁荣、由程序化应时到个性化写实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与唐五代、北宋和南宋三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纪时体词的发展大致可分为粗成、成熟与繁荣三个阶段。
就总体创作态势而言,唐五代是纪时词粗成形体、初具规模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纪时之作基本上属于对时令景象的普泛化描写,所表现的情感还停留在粗线条的季节感受之上,很少涉及具体的节令;词人们对春秋二季似乎有着特别的敏感,万象复苏的春日,总是与爱情相关,花开花落又总是牵动着离别的愁苦;萧瑟寥落的秋天,常常是思乡的时刻,秋风秋月更引发出无限的漂泊孤寂之感。与早期词的抒情特征相吻合,季节在词里往往构成一种象征性的环境背景,以烘托作品所描写的情事,寄寓主人公的感怀。敦煌抄卷中失调名的组词《十二月歌》当为早期词中的纪时作品,组词从“正月孟春春渐渲”始,一直写到“十二月季冬冬极寒”。作品通过十二个月令的时节变换,反复吟咏女主人公的思人念远之情,民间文学通俗、流利的语言特色十分明显。十二篇作品皆为七言四句为一章的齐言诗形式,与典型的曲子词有别。唐庄宗李存勖有一首大石调《歌头》:
赏芳春,暖风飘箔。莺啼绿树,轻烟笼晚阁。杏桃红,开繁萼。灵和殿,禁柳千行斜,金丝络。夏云多,奇峰如削。纨扇动微凉,轻绡薄,梅雨霁,火云烁。临水槛,永日逃繁暑,泛觥酌。露华浓,冷高梧,凋万叶。一霎晚风,蝉声新雨歇。惜惜此光阴,如流水。东篱菊残时,叹萧索。繁阴积,岁时暮,景难留。不觉朱颜失却,好客光。且且须呼宾友,西园长宵。宴云谣,歌皓齿,且行乐。
此词为唐五代文人词中一首难得的专咏节序之作。作品依照春夏秋冬的顺序,分别描述四季的风光景色和宴游活动,突出地写出了各季节的风物特征,以雅丽的语句表现了作者准确的时序感受,与民间词风格迥然有异。韦庄名作《思帝乡》(春日游)写一位少女春天郊游时芳心萌动的情景,颇有风致,可称这时期词中写岁时之妙品。
严格意义上的纪时词是北宋时才出现的,这是纪时体词发展与成熟的阶段。随着节日娱乐性和词人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增强,纪时词的创作由早期以表现普泛的季节之感为主,转向了对具体节令景象及其感受的个性化描写,此类词创作中“应时纳祜”的俗套也有所突破。
柳永在这方面的贡献应特别提及。其词中有关表现羁旅行役之感和城市生活及市井风情的内容,许多与节令有关。悲秋是柳词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柳永对秋天的描写不再满足于类型化的风景和情感的表现,而是借助于慢词的形式,运用铺叙的手法,通过描绘身临其境的实地景色来表现其独有的心理感受,有时则是描写具体节日的景象与情事,如《玉蝴蝶·重阳》一词写的即是作者在重阳节这天漂泊他乡身为“楚客”的感慨:“对残晖、登临休叹,赏令节、酩酊方酬。且相留。眼前尤物,盏里忘忧。”这里的节令咏叹较之以往空泛的应时之语,显得真实而亲切了许多。在城市生活的描写中,柳永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有关节庆盛况的篇章,如写元宵节的《倾杯乐》(禁漏花深)、《迎新春》(嶰管变青律),写清明节的《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等,词中具体生动的画面为我们了解北宋中期社会城市风情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晏殊、张先、欧阳修等人在纪时词的创作上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特别是欧阳修以传统的令词形式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渔家傲·七夕》、《御带花》(青春何处风光好)等。值得提出的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渔家傲》“鼓子词”,具体地描写十二个月中的节令及其民间风俗和自然景象,与敦煌词中的《十二月歌》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词体纪时功能的发展。
北宋词坛上,苏轼对于纪时词的新开拓应予高度重视。在《东坡乐府》中,以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腊八等节令为题的作品有多篇,皆写词人节令中的感怀。在这些作品里,词人由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时令而感兴发端,但并不拘泥于时令景象的具体描摹,往往是借时景写怀抱,以节令言人生,从眼前的一时一景传达出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思考与感怀。《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一首中秋词,但其意义远非一般的中秋怀人之作所可涵括。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的纪时词创作也颇有可道之处。秦观写七夕之节的《鹊桥仙》表现了一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真正爱情模式,将男女情爱由世俗的情欲追求升华到崇高的精神境界,赋予传统的节令以崭新的意义。周邦彦《解语花·元夕》深得张炎赞赏,被认为“不独措辞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词源》卷下)。
较之北宋,纪时体词在南宋(金)时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了它创作的繁荣期。据统计,有关元宵节的篇目,两宋词约有297首,南宋人之作达五分之四以上。不仅数量增多,这一时期的纪时词在内容上也更为丰富,表现手法也更为多样化,许多名篇佳作传诵古今。李清照在《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行香子》(草际鸣蛩)、《永遇乐》(落日熔金)、《蝶恋花·上巳召亲族》等以节令为题的作品中,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她在节庆之日里孤独、痛苦的心灵,展示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节令欢娱中女性的心态与情怀。纪时之作在辛弃疾笔下仍不失其英雄本色,如在一首“重九席上”所作的《念奴娇》中写道:“龙山何处,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莫倚忘怀,西风也会,点检尊前客。凄凉今古,眼中三两飞蝶。”节日欢会勾起的是他恢复中原的抱负。又如《水龙吟》:“只愁风雨重阳,思君不见令人老。行期定否,征车几两,去程多少。”时节的交替,唤起的是他作为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世俗的节令如此恰切地与政治抱负联为一体,表明纪时体词已臻圆熟之境。
吴文英是南宋风雅派词人中歌咏节令最着力的一位,也是宋代词人中写作节序题材最多的一位,在梦窗词中,从岁旦到除夜,几乎一年中重要的节令都有吟咏之作。吴文英纪时词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善于以绮丽的语言和错综的词境,将节令物候的描写与相思别恨的恋情融为一体,如《烛影摇红·元夕雨》:
碧澹山姿,暮寒愁沁歌眉浅。障泥南陌润轻酥,灯火深深院。入夜笙歌渐暖。彩旗翻、宜男舞遍。恣游不怕、素袜尘生,行裙红溅。银烛笼纱,翠屏不照残梅怨。洗妆清靥湿春风,宜带啼痕看。楚梦留情未散。素娥愁、天深信远。晓窗移枕,酒困香残,春阴帘卷。
灯火深院,笙歌彩旗,在欢腾的元夕之夜,这位女子狂舞“宜男”,表求子热望,然而回府“洗妆”后,“天深信远”的现实又让她陷入相思的愁苦。梦窗词常常用这样一种类似梦境的构思来表现这节令变换给人带来的迷惘和感伤的情态,为纪时体词开创了一片全新的艺术天地。
与南宋共时的北方金朝,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和文化风俗的差异,在纪时词的创作上则形成了不同的特色。《蕙风词话》卷3云:“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地域文化环境的不同,也造成了纪时之作在审美风范与题材内容方面的南北差异。且看下面这首《水调歌头·闰八月望夕有作》:
空凉万家月,摇荡菊花期。飘飘六合清气,欲唤紫鸾骑。京洛花浮酒市,初把两螯风味,橙子半青时。莫话旧年梦,聊赋倦游诗。玉盘高,金靥小,笑相窥。市朝声利场里,谁肯略忘机。庾老南楼佳兴,陶令东篱高咏,千古赏音稀。手捻冷香碎,和月卷玻璃。
此篇为金词开创者蔡松年所作,其清冷高爽的词境及其超旷忘世的心灵追求,既展示了北方秋节的特色,又体现了金词在苏轼词风影响下诗化、言志化的倾向。北方词纪时之作中所表现的节令景观和风俗也值得注意,如晚清著名词学家况周颐曾谈到元初词人王恽《江神子》序中所提到的“金源雅故”,其序曰:
金朝遗风,冬月头雪,令僮辈团取,比明,抛亲好家,主人见之,即开宴娱宾,谓之撇雪会。去冬无雪,今岁初白如此,灯下喜赋此词,录奉达夫,且应撇雪故事,为一觞之侑也。
正是王恽的词作,让我们知道了这种“流传绝少”的宋金时北方“撇雪”的风俗,况氏见之喜甚,于是“亟记之”。
三、纪时词的文体特征
从《诗经》以来的咏岁感时之作,皆属纪时文学范畴,而纪时词由于其特定的文化性质及功用,在作法和体式上又有着自己较为鲜明的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即时性与实用性
我们今天的语言中有“时装”、“时鲜”之说,纪时词就像曲子词中的时装和时鲜,多属于应时、应景之作,创作于或传播于节序更替之际或节日之中。春夏秋冬四季,二十四节气,特别是立春、元旦、元宵、上巳、清明(寒食)、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重要节令,人们在嘉庆之时或前后,往往以词来纪盛事、写美景、数掌故、述感慨。这种“即时性”赋予了纪时词某种写实的性质。早期的纪时词中情事物景多为类型化描写,入宋后随着词作主体性的增强,其节令之作的写实色彩也逐渐明显,节序中的眼前之景、身边之事、一己之情及当时的习俗风物,更多地进入了词人的视野,如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风味应无价。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乍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词中回忆的“灯火钱塘三五夜”情景和眼前“寂寞山城”“击鼓吹箫”的场面,都是作者亲历之事,已非一般应歌之词中的泛泛之语。
纪时词的这种即时性与其实用性功能相关联。节令是人们团聚交往的重要日子,即便不能见面,人们也往往寄信捎话以问候,而通俗易晓且长于抒情的曲子词无疑正是传语寄情的极好媒介,从而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交际的职责。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中说:“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这一点在纪时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作品不仅是作者节日情怀的表现,同时也如同“羔雁”一样具有一种寄赠亲友的节日礼物之性质。王国维从词的抒情性角度批评词体的这种实用性演化,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词作为一种文化凝结体,承载某种实用性的社会功能也是应有之义。
纪时词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交际方面。觞咏唱和是纪时词创作中一种常见的形式,如辛弃疾纪时词21首中明确标示与人唱和的有《好事近·中秋席上和王路钤》等4篇,朱敦儒27篇纪时词在题序中写明的唱和之作有8首,其实更多的唱和之作并未在题序中明示。寄远投赠是纪时词交际功能的又一体现形式,如苏轼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即是寄赠远方胞弟苏辙的。有的词作为奉赠显宦或前辈而作,如黄机《鹧鸪天·元日呈王帅》;还有应歌妓所乞而作,如赵长卿《鹧鸪天》小序云:“初夏试生衣,而婉卿持素扇索词,因作此书于扇上。”《月令》记古有四月八日“服生衣”的习俗,唐宋时仍流行,婉卿据词意可知其歌妓身份。此外,节庆之时文人还常常以词应制祝颂,康与之(字与可)因“有声乐府”,“待诏金马门,凡中兴粉饰治具,及慈宁归养,两宫欢集,必假伯可歌咏,故应制之词为多”(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1),其《瑞鹤仙》就题作《上元应制》。此外,在节日娱乐活动中演唱,也是纪时词一个重要的实用性功能。如以北宋生活为背景的《水浒传》第三十回,写张都监让玉兰“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玉兰执着象板,向前各道个万福,顿开喉咙,唱一只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节日中唱应时应景的纪时词,显然比唱无关时节的作品更能感动人心。
(二)通俗性与习套化
节序更移,无关人世贵贱,多数节日实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当时许多重要节日可谓普天同庆,朝野同贺,节日的全民性也使得通俗流行的曲子词有了大显身手的天地。正是这种创作背景导致了纪时词通俗晓畅的风格特点。纪时词作为民俗世情的产物,从总体上说,体现了鲜明的“俗”性:记俗事——记叙民间习俗之事,写俗景——描写节序常态之景,状俗物——刻绘节日习见之物,论俗理——谈论世间常规之理,表俗情——表达人生恒常之情。在语言形式上,纪时词出于其创作与传播环境的需要,大都浅白晓畅,多用熟典习语,即使像平常用事成癖且时用僻典的辛弃疾,在其节令之作中也多为熟语常事。如吴文英被认为“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⑤,但检其纪时词,则少见晦涩难懂之作。
随着词体的雅化,许多纪时词的内容也多了几分雅趣与寄托,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和吴文英等人的作品,但相对其他类别的作品还是显得“俗气”十足。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炎在《词源》中对纪时词作出这样的批评:
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拆桐花烂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谢”,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未然。
率俗即庸俗,主要指创作上的陈因性与习套化,张炎的指责可谓一语中的,多数纪时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率俗的弊病。不过,换一个角度看,正是这种率俗使纪时词的创作具有了技术上的易操作性,能够及时地大量地生产,并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在节序文化活动中发挥重要的实际效用,同时也成为人们感情表达和交流的重要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率俗并非只有负面的价值,它恰好道出了纪时词浅易通俗的特点。
纪时词与通俗性相关的另一个特点是习套化,张炎所谓“应时纳祜之声”的指责即是就这种习套化而言的。由于纪时词表现内容为循环往复的岁时节令,所写景象与风俗有着重复相似的特点,人们的感受也有相近相类的可能,所以创作中便形成了一些大致固定的套路,积累了一些可供反复使用的意象和成语熟典。这种习套化的形式,对于即时性的应景创作,提供了便于操作的模式,也易为受众的期待视野所接纳。但是这种习套化往往会削弱纪时词艺术个性的创造,而优秀的纪时词则要求在借助这些习套的同时又能突破之。
(三)景、事、情一体化
词是古代诗体中抒情“纯度”最高的一种,但在节令之作中写景与叙事的成分明显要比其他类别的作品多,这与纪时词即时应景的功用有关。节序的变化首先是由物候的变化表现出来的,因此描摹风光刻绘景物就成为纪时词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又由于节令伴随着一系列的民俗活动,纪时性的纪时词也必然会将作者节日中的所见所闻及本人的活动作必要的描述。如晁补之描写当时春节风情的一首词(失调名):
残腊初雪霁。梅白飘香蕊。依前又还是,迎春时候,大家都备。灶马门神,酒酌酴酥,桃符尽书吉利。五更催驱傩,爆竹起。虚耗都教退。交年换新岁。长保身荣贵。愿与儿孙、尽老今生,祝寿遐昌,年年共同守岁。
作品十分具体地描绘了春节期间的事情,其中提及的“灶马”、“门神”、“酴酥”、“桃符”、“驱傩”、“爆竹”等事物,都与当时春节风俗有关。由此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千年前人们欢度新春佳节的盛况。
不过,叙事写景成分的增多,并没有改变这类节令之作的抒情诗性质,事与景在作品中只是抒情的材料,在情的统领下,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如前面提到的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先回忆杭州上元之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的盛况,又写了“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密州上元夜景;还写两地“帐底吹笙”与“击鼓吹箫”的节庆之事,作者正是在这两地景与事的比照描写中,使其寂寞忧老的情怀幽然流出。又如前文提到的欧阳修所作两套《渔家傲》鼓子词,依序逐月描写十二个月中的节景、节物与节事,如其中写七月的一篇:
七月新秋风露早。渚莲尚拆庭梧老。是处瓜华时节好。金尊倒。人间彩缕争祈巧。万叶敲声凉乍到。百虫啼晚烟如扫。箭漏初长天杳杳。人语悄。那堪夜雨催清晓。
词里写到了旧历七月间特有的“新秋”之景和“祈巧”之事,而这些事景又都与这一收获时节里人们喜悦、满足又“不堪”凄凉将至的心情相一致。
纪时词作为纪时诗的一支,其某些文体特征也体现在近体或古体的纪时之作中,但由于词体特殊的社会文化功用,这些特征之于纪时词的意义也自有不同。在唐宋时代,近体或古体之诗,属于雅文学,主要流播于文人士大夫之间,对于文化程度低下的民间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即使感时应景的诗篇,也主要用于文人士大夫(包括粗通文墨的乡绅)之间的交际或自写心志;而纪时词的实用功能则往往是在节日间大众娱乐场合通过演唱实现的,即使用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际,也多是付之以管弦。纪时词这种娱乐性质及大众化的传播环境,决定了其语言要求通俗浅易,意象语汇也往往习套陈因;同时也决定了作品所写情景往往较为普泛,个人化色彩较淡。而纪时之诗,由于主要表达作者个人的节令感受并传播于文人之间,所以语言多以典雅为尚,如杜甫作有大量节令诗,其文字的精警、意蕴的厚重与其他题材作品并无二致。可以说纪时言志之诗缺少文体学意义上的明显特征;而纪时之词由于其特殊的创作环境和文化功用,较之于一般词作,其作法与体式形成了较鲜明的特色,因而构成了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词体品类。
收稿日期:2009-11-14
注释:
① 如高建中:《节令词四题》,载《泰安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余敏芳:《节日民俗与宋词创作》,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周淑芳:《节令词:诗人对理想人生的殷切祈盼》,载《船山学刊》2003年第4期;易蓉、陈扬燕编著:《宋代节序词研究与欣赏》,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
② 参见萧放:《中国上古岁时观念论考》,《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刘勰:《文心雕龙·特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④ 许伯卿:《宋词题材“狭深”论辨正》,《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⑤ 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9,《词话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