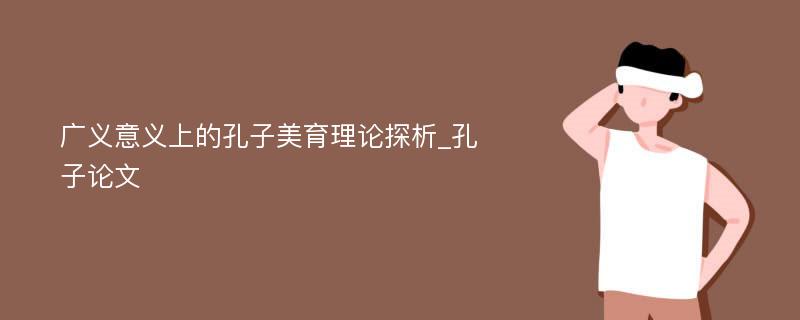
孔子广义美育思想理论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美育论文,广义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08)03-0051-06
广义美育是指把美学原则渗透于对人的影响,从而形成人们高尚审美素养的影响活动,包括高尚思想道德教养、政治艺术美学以及陶冶人们美好心灵的文学艺术教育。其美的教育内容与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善良心性的向往密切相联。孔子构建了极具特色的广义美育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美育实践,首开中华民族广义美育之先河,为中国美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鉴于此,我们从中国古典教育文明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以期获取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可资利用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一、孔子广义美育观的内涵揭示——文、美、艺
孔子的广义美育思想理论与实践形成于春秋末期,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美的教育是孔子以人为教育对象,以“成人(完人)之美”为教育目的的教育。其美育,在概念内涵、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等方面与当时广义之美的追求和人类主体性美育内容的要求一致,包括德、智、体(射、御)、美、劳(耕、畜)五育,即包括思想道德、政治法律、社会行为规范、体能锻炼、文化艺术、劳作实践技能等培育“成人”美性的一切内容和方式。“美”与广义的文化、艺能相通,形成人的本体全面美化的广义美育教育传统。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空前发展繁荣的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审美逐美的重点在人这个本体,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使人美化,以“成人之美”为理想诉求,同时符合时代发展需要,达到人类自身成为“仁人”、社会“仁和”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期求,是人们在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伦理生活中共同追求的。从已发现的文化遗存可见,中国上古时期,对美的追求十分强烈,对美的艺术化表现形式极为重视,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美化艺术化表达功能有极高的估价,甚至夸大、神秘化,尤其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礼仪礼制性、美化艺术化的张扬、神化更为突出,而且都与如何把统治者培养成为理想的圣人君子的基本要求紧密相关。孔子的广义美育思想,既是对三代以来中国传统政治美学思想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其美育经验体悟的理性化提升和创新性建构。
从春秋末期和整个战国时期留存下来的浩瀚典籍看,这个时期,人们极其重视文学(诗、歌、典礼词、讥译典文)、艺术(音乐、舞蹈、典仪剧等)的“政治场”的艺术功能和实用功能,从而构成了这个时期美学思想的基本特质,成为完美政治人格培养的主导性内容。只不过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考问题的思维逻辑起点不一,导致儒、墨、道、法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教育家对文学、美学、艺术对人性化育作用的评价观点迥异。儒家(以孔、孟、荀为代表)认为,文学、美学、艺术提升了人的人格素养,带来了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为育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方策。而道家、法家、墨家则或者认为它泯灭人的本性,招致社会腐化、伪善、巧诈、倒退;或者认为它的发展与经济、政治、国富民强相矛盾等,主张从根本上取消美育,取消文化艺术,或限制其发展。
就总体而言,不论是基于入世的积极有为的人生观,还是基于出世消极无为的人生观,都强调或夸大文学、美学、艺术的积极或消极社会乃至政治功能,都将其与人性、物欲关系的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儒家认为,通过文学、美学、艺术的修养和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按照礼制,过等级差次的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等级差序的格局下实现和谐。道家则认为,只有“绝圣弃智”、“绝文弃艺”、“无欲无为”,舍弃一切后天人为的加工,使人的本性去掉伪饰巧诈的恶染,还原于自然,人才能成为本真的人,社会才能进入理想的境界。通过美育而“成人之美”和去人为美而天地自然化育,是此时形成的两种针锋相对的美育观。可以说,与没有社会选择性和违背人文发展规律的道家相比,儒家的具有社会选择优势性和与人文发展规律相契合的美育观集文学、美学、艺术的优势于一身,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功能,至今仍有普遍价值。儒家的教育宗旨是塑铸人的仁者人格和主政君子的政治人格。因此,其广义美育观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干,寄意于邦人国人通过“大美育”以节欲治情、礼治治国,推动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此,儒家积极探究和深化美育的内容、方法、规律。对此,孔子的建树最大,创新性思考最多。比如,在美育与政治伦理的关系上,孔子提出礼、乐相辅相成,确立了通过美育培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 的理想人格的结构原则;在育人成长的阶梯层次上,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② 的培养治国理政君子的智力、德性的基本要求;在美育功能的分析上,作出了“兴”、“观”、“群”、“怨”的精辟概括;在审美标准、美的鉴赏尺度上,区分了美丑、美的层次,强调中和之美,倡导“文质彬彬”的美感形象。
二、执政君子的理想人格——道、德、仁、艺
孔子对文学、美学、艺术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关系的认知和对理想人格结构的期望用12个字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般解读,即有理想、有道德、有仁性、有智慧。其中,以行天道人道之大道为理想,以自我德性修养为主观依据,以做仁人为行为准则,并具备六艺的智慧和才能。
“志于道”。“志”即人生理想,孔子主张立人首要在立志。“道”包括天道、人道的合一,即“大道”——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孔子所崇尚的“有道之世”,即尧舜禹的揖让之治,“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初年的盛世。“志于道”,即具有为实现“有道”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
“据于德”,即以道德为支撑,以行为中自我德性为依据。德字古为惪,即心地正直、正义,持中而不偏不倚,既不“过”也不“不及”,持中而用命,是谓中庸。儒家所谓德,其内容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是指西周制定、延续、发展而来的有关君臣、父子等的政治伦理准则。孔子强调以德治国,要求人们遵从礼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且“思无邪”,从而主动自觉地合于道德的基本要求。
“依于仁”,即依从“仁者”的行为范式和内心的道德文化自觉来立身行事。“仁者”的基本德行要求是“孝悌”、“爱人”、“克己内省”。“仁”作为最高的道义标准、人生境界,是孔子对“德”的发展,是其一切学说、认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于仁”是“据于德”的前提、基础和根本动力,“依于仁”才能真正切实地通过“游于艺”实现由“仁者”构成的“天下归仁”,邦国之内“仁和”,以“仁和”“协和万邦”。
“游于艺”,是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客观学习环境、途径和主观可能具备智力、技术条件。孔子将美育置于政治伦理之下认知和运作,经历了一个体悟、总结历史经验和辨析古代人们对“艺”的不同理解的过程。在我国古代,“艺”最初指具体地对某一方面实践规律的把握,是一种泛指。进入农业社会,主要指农艺——农业生产活动的技艺,逐步被用来指称整个生产实践活动,直至扩展到一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活动领域。再后来,由于出现阶级的对立,出现劳心、劳力的划分,“艺”也一分为二:对物质生产劳动中所用器具的制造和使用规律的熟练把握,被视为低下的技艺,被看作与自身力量对立的表现;而对与体力劳动相分离的精神生产中一定规律的认识、把握、运用,则被视为高尚技艺——雅艺,被视为真心体现自身本质力量的行动。因为在劳心者看来,创造、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是精神生产实践。这种认识后来便形成了道、艺的形而上、形而下之分。既然精神方面内容的规律性把握才真正体现人的精神生命主宰、支配人的肉体生命的这一本质所在,那么以往以物质生产实践规律把握的熟练程度衡量人的素质水平高低的状况,自然就为精神上内心世界的充实、完美、高尚状态的把握所代替了。至孔子时,以其广义美育观,将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融为一体,将美育的内容概括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如此范围广大的美育内容,既含道德教育,也有知识技能教育;既有文学、音乐、舞蹈、体育等艺术教育,也有政治、法律等的教育。这些内容分别地看各具特色,但都围绕一个中心——内心充实、德性完美,就连射、御这些军事体能训练的内容,在“六艺”体系中,也都与君子心性公平、德性正直、志高道远的“修德”、“务道”联系在一起,改变了它们的单纯物质实践特征,由低俗走向了高雅。
综上可见,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构建了孔子广义美育的主体结构,这一结构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总结了以往美育的历史经验,较为细化地区分、设置了圣人君子平时应注意学习、修养的主要内容,并将其建构成统一的结构功能性整体,期望美育内容一体化于一个目标。二是将尧舜之治、文武之政的理想提升至合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以对人们修养行为进行制约,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协调呼应。“道”的概念提出,标志着集哲学、伦理、政治于一体的美育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支持个性解放,将个人自由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并纳入礼制社会的规范秩序的范围内,而非礼治的绝对约束。三是对于道、德、仁、艺四者的特征、地位、作用做了简明、准确、深刻的概括,并突出了道之志、艺之游,既是对西周以来政治教育经验的概括,也是孔子个人育人经验的总结。这种概括和总结,树立了历史的完备的政治人广义美育的典型,并在两千多年来世代传承,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三、“成人之美”的阶梯层次——诗、礼、乐
对于“成人之美”的依次递进的发展过程,孔子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通过不同时段不同内容的美育,逐步形成并不断提高执政君子的智力水平、行为规范化程度和道德文化的自觉性,从而进入个性自由发展的境界。如果说,道、德、仁、艺是从横向联系上规划美育,那么,“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是从纵向上确定君子成长完美人格的逐步提高过程。纵横两方面交互作用,显示了孔子建构的广义美育体系的功能结构和特点。
第一,“兴于诗”。孔子认为,人类在先天禀赋上是“性相近”的,后天学习才使人显示出差异:“习相远”。人的天赋固然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别,有上智、下愚之分,但并无不可变的界限。因此,他主张“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孔子十五岁“志于学”,少年时代感性认识、形象思维比较发达,从具体形象思维的培养入手应该是教育的主要逻辑路径,因此,个体接受教育应从学诗开始。孔子这样考虑也是从实际出发。当时,各种文学形式中,首先出现的是来自民间的诗歌(经孔子整理而成为教材)。诗教对象大体上是两类人:一是统治阶级政治集团中的人士;二是奴隶主、封建主等有身份地位的自由民。普通民众是诗歌的原创者,他们通过歌诗进行自我教育。在这个意义上说,诗教又是有类的。即学诗主要是适应国君、公卿、士大夫治国理政的需要,即“劳心者治人”的需要。
孔子何以将学诗作为受教之始?原因有三:其一,诗具有知识性。春秋之前形成的简书不多,比起流传下来的有限的政治性文诰典册,经筛选整理的《诗经》在当时可以说是知识信息含量最高的经典之作,它既汇集了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农业、水利等),又凝结政治伦理道德的精神,对于那些脱离生产实践又与大众分离的君子们而言,通过学诗可以间接地掌握先人的经验,获取知识营养。尤其是从诗中可以学到社会政治知识。《诗》中表达君臣、父子等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诗》中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描写、运用,也是为了讽喻或赞美、颂扬一定的社会政治现象,透露一定的政治文化意蕴,表达一定的社会政治情感,抒发某种社会政治抱负。因此,通过学诗会有助于人们掌握事君事父、参与政治、外交和社会交往的能力。其二,诗具有高雅性。诗是一种经过加工提炼,表达情感、志向、气质的语言。春秋时期,吟诗常与行礼、作乐伴随,盛行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定政治活动场合。相对于粗朴的民间俗语来说,诗是一种尊贵者的特殊语言——“雅言”(当然也包括自民歌民谣经过改造加工成为“雅言”的)。士大夫们学诗、吟诗,用诗表明政治意向,既可以区分贵贱等级身份,又能显示尊贵者特有的心胸、风度和高雅气质。其三,诗具有情趣性。诗与乐相比,乐比诗的感人明理程度要深,但乐的形式和内容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只能作为高级课程列入育人的最后一个环节,即“成于乐”。诗则由于它的口语化、寓意化、情性化表达方式,其蕴含的内容易于被人即时了解和回味,为学诗者乐意接受。明代心学家王守仁指出,在诗教中“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如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条,日就枯槁矣。顾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③。要而言之,诗的知识性、情趣性、高雅性,是孔子之所以育人首先“兴于诗”的理由和依据。
第二,“立于礼”。礼教是培育理想君子的中间环节,其特征是进行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教育。礼的由来与祭祀有关,礼起源于祭祀仪式。礼的本质在于其内涵政治原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力的崇拜与传承,以及对自然规律的尊崇,它直接与古代农业经济对天、地的依赖和现实政治的稳定、国家的兴衰相联系。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首要在“祀”,其缘由显明。礼一方面具有祭祀的神秘性,另一方面它淡化为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礼制则具有人文理性:形成夏商西周三代的礼制和治国方略之一的礼治。春秋末,礼的祭神观念逐渐淡薄和形式化,成为维系政治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孔子一生致力于维护礼制、礼治,并因时改革,他不断忧虑“礼崩”,对一切违礼行为表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④ 正因为如此,孔子育君子人格,重视“立于礼”。
孔子十分重视对夏礼、殷礼有所损益的周礼,认为周礼“郁郁乎文哉”。他认为,礼的内涵在于它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理性,在于人的思想行为的不断加工美化。行礼多与作乐(歌舞)并行,“礼之外作(外部约束),故文(内涵一种社会政治文化)”,又称之为“礼文”,“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⑤,通过礼乐由外在约束而内化,把人加工雕琢为内外兼修的“圣人”、“君子”,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倘若人人如此,社会政治伦理将有序不乱,“有道之世”就将达成。孔子“立于礼”的教育传统,到战国时期的荀子发展为“隆礼重法”。荀子强调:“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⑥ 从孔子到荀子,自春秋末至战国,儒家显然认定:礼作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多方面具体规定,其教化作用在于由外而内、由外在强制被迫不自由到礼制的理性“文化自觉”的过程,使人由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逐步进入自觉自动习惯的高境界,与内心对理性、道义的愉悦和情理一体相融。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是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育人的一体化过程进行阐释说明的,三者是紧密结合的。“立于礼”不仅是育人的中间环节,而且礼的理性精神贯穿着育人的全过程。诗受礼的制约,才能够兴、观、群、怨,离开礼的制约,诗教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成于乐”也必须结合“立于礼”,才能体现情与理的交融,外部制度规范与内在心灵觉悟的和谐统一。因此,“立于礼”是就社会整体而言对个人的要求,兴于诗、成于乐,则既可以个体化,也应该社会化。孔子本意在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循礼而行,是个人作为社会成员主人之本,以礼为导向,并将礼教与诗教、乐教结合,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第三,成于乐。春秋时各邦国都有专职乐官和专门机构,乐由器乐声乐构成,通常伴以舞。孔子非常重视乐教对“成人”之特殊作用,认为乐对个人情操修养至为重要,对国家治理理想境界的形成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孔子之所以重视乐教,源于他对国家兴衰、政治治乱中乐的作用的认识。一是他接受并发展了周初以来的传统观念,夸大周初制礼作乐对政治的反作用,认为只要坚持“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⑦,就可以阻止新的社会势力新的观念的兴起,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二是孔子自己十分熟悉音乐,并深受其熏陶。他经常出入太庙观礼闻乐,《论语》中记载孔子曾经师事、学乐于师襄、苌弘,在周游列国期间,“讲颂弦歌不衰”。《论语·八佾》专门记载了他视听国君朝议时的乐舞情景,对诸侯行天子之礼乐公开表示过不满,表明他所学所习之乐主要是雅乐,即宫廷音乐,但对各邦国民间音乐也有所了解,对所谓“正乐”、“淫声”都有所评价。史载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反映出他对雅乐的情有独钟、思有专注、趣有所骛的特有性致和情趣,以及政治美学化的向往。
孔子是中国愉快教育的首倡者。他认为,理性说教是必要的,但一切说教都比不上乐之教,其他任何艺术美感教育的作用也都比不上音乐教育,包括吟诗比不上有音乐伴奏的歌诗。《论语》中多处记载他对音乐巨大功能和特点的评价。他明确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⑧ 意思是从接受教育的主体的感受状态来说,理性认知不如情感的欲求,情感的欲求不如发自内心深处的由衷喜悦欢愉。在孔子看来,礼与乐不可分离。乐这种艺术不仅由于它本身的特殊形式使人们乐意接受,而且在于乐与乐舞之美体现的内容和“和谐律动”特点,高于诗和礼的单向要求,包含着最崇高的思想理想——天下归仁、仁和政治理想,以及天道人道的最高道义的合一。这当然不是指一般的乐,也不是俗乐,而是具有政治意味的《韶》、《武》一类的乐。据《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到武城,闻弦歌之声,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的意思是,在乐教中,君子和小人都可以由于受美育有美感而把握“道”,共同持有对“有道之世”的追求和信念,只不过在等级制社会中,由于贵贱尊卑的社会地位不同,一个因秉持道义而生仁爱之心,以“和”万民,实现“政通人和”;一个因认清道的导引,认可现实所处地位,在等级差序的格局中甘愿献力,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服从管理。孔子乐教对象的重点在君子,按其重民的民本理念,庶人富而后教的方针,乐教的对象范围也包括民众在内。孔子将来自民间的民歌民谣民谚编订入《诗经》,证明他并非空言。
综上所见,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维是与其政治思维融为一体的,这种综合的整体思维方式,既登高望远,又立足于现实,既是高度抽象的精神凝聚,又是具体可感、人人可为共享的物质依托。在孔子的乐教中,将诗、礼、乐贯通融合,对道的喜悦、把握是基于形象思维升华至理性、典模的追求,极具启发意义。
收稿日期:2007-12-17
注释: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泰伯》。
③ 《语录·传习录中》。
④ 《论语·八佾》。
⑤ 《论语·宪问》。
⑥ 《荀子·大略》。
⑦ 《论语·卫灵公》。
⑧ 《论语·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