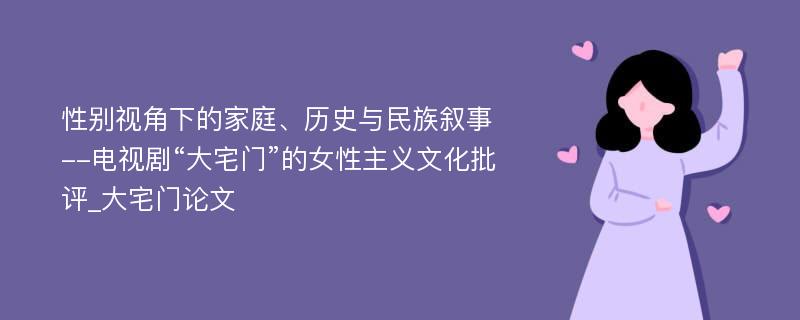
性别视角中的家族、历史、民族叙事——对电视剧《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宅门论文,视角论文,批评论文,性别论文,电视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J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4-0086-06
性别 家庭伦理 叙事
一部历史,从来是“他”的历史,男性的历史,也是权力者的历史。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精神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伦理本位主义。这种伦理本位是以人伦秩序为绝对价值和标准并建立在家庭伦理之上的专制式的伦理政治。正因为如此,“家”是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奥秘的一把钥匙,因为家庭或家族血缘关系乃是传统中国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因而家庭伦理原则也成为统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首要原则,那么,中国的家庭伦理原则有什么特点呢?有学者归纳总结为五大特点:“第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定位;第二,生育男性后代以继承私有财产的道德义务;第三,‘男恕风流,妇戒淫邪’的双重两性道德;第四,‘女子无才便是德’;第五,‘父母之命’的婚姻。”[1]4
可以说,建立在“父权至上”、“男尊女卑”观念基础上的家庭伦理原则显然是一种“不平等条约”,它是单方面的,具有强制性和统治性意味,正因为如此,传统的封建制度才暴露出它的“吃人”的一面,“专制”的色彩,才受到“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批判。
而在《大宅门》中,叙事者为我们讲述的并不是“家”的寓言,而是“家”的神话,并不是对“家”的批判、质疑,而是对“家”、“家族”的赞颂和歌唱。同时,《大宅门》也不是一部如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而更像利奥塔所批判的“宏大叙事”,其目的就在于重振男性衰败的“雄风”,以及挽回那早已失落的“声威”。
在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家”作为“国”之本,担当着重要角色。正如学者殷海光指出的:“自古来,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单元,也是政治组织的基础。在所谓‘专制时代’,中国就是以一个家庭作中心统治着所有的家庭,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家庭在中国文化的建造和发展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2]98
生活现实中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存和生命都离不开家的庇护。然而,家庭,乃至家族,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便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为组织因素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3]57 的确,正是这种绵延至今,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审判的存在,使得女性一直处在物、工具、奴隶的位置上。
《大宅门》中的女性同样具有上述特征,她们“在婚姻里被赠送,在战争中被掳走,被用来交换恩惠,被作为贡品献出,被买进,被卖出。”“这些习俗远非仅局限在‘原始’世界中,而似乎是在‘文明’社会中变得更明显,更商业化。”[4]39 因而,在《大宅门》也就是“家”中,女性是没有自由的,她不属于自己,女性没有享受幸福的权力(大奶奶),没有追求爱情的自由(白玉婷),更没有做人的尊严和平等(如槐花),倘若不符合父权秩序,连做母亲的资格都要被剥夺(如大格格、杨九红)。
相反,在这种封建专制家庭中,男性却享有一种“特权”,而“这种男性中心的特权主义,一直被传统维护着使不敢受到侵犯”。这种特权就是“可以享受应有的声威、尊敬、利益和支配权”[2]101。尤其是对“声威”的追求,不但是“雏形的权威主义之所自然的养成”,而且是“中国文化发展并且表现得最强烈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殷海光先生曾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文化分子历来少管外事。他们锐意经营社会地位和声威。中国文化分子将思想发展、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对外看法,以至于室第形式及服饰式样,都辐辏于声威的建立、巩固和扩大。而声威的心理基础是虚荣。所以,声威一经制度化,便牢不可破。”[2]135 那么,到底什么是声威呢?殷海光先生认为,地位和声威的外表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子”,而“面子”是中国文化分子的第二生命。中国文化分子最“爱面子”。为了“面子”,不但争得你死我活,而且没有了是非、善恶、曲直,[2]132 在这方面,《大宅门》表现得尤为明显。
故事一开始即是围绕“面子”问题而展开。白家老二白颖轩给未出阁的詹王府家的大小姐诊出了喜脉,詹王府为此恼羞成怒,认为丢了脸,传出去,让詹家无法做人,为此杀了他的马砸了他的车。而白家认为詹王府这样做也是不给“面子”,在白老爷看来,“他砸的不光是白家的车和马,他砸的是白家的老牌子,现在没有人不知道的,白家栽给了詹王府,今后不光老二没法露面,祖宗的脸面也让他给丢尽了”,因此双方为了争得自己的“面子”而斗得你死我活,并引发一连串悲剧。
而女性则成为这场“争面子”战争中的最大牺牲品,没有人关心她们的死活,更不会有人顾及她们的“脸面”和尊严。大格格在所谓的“丑事”暴露后,不但一双儿女被送人导致亲生骨肉永久分离的打击,同时也遭到被亲生父亲放逐的噩运。她在故事的第一、二集出现后直到三十四集才又重新出场,而此时的她已由一个美丽的少妇变成了一个满脸沧桑的老妪。这几十年她是怎样过的,剧中没有交代,也不会交代(这点不同于对大爷白颖圆的刻画),但我们却可想而知。而另一个“面子”的牺牲品杨九红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因为当男性将她们作为一个筹码以衬托自己的威仪,炫耀自己的声威时,她的命运也同样是可以预见的。白景琦以“一掷千金”的“豪迈”,以不惜得罪总督大人的“活土匪”作风,将全济南城最有名的窑姐杨九红作为猎物猎获之后,很快就弃之一旁,不顾其死活了。虽然他最终迫不得已无奈地接纳了她,但却将一个充满希望的活生生的女人,将一个自以为找到了一个“有情有义”,可以终生依靠的男人的做梦的女人,变成了张爱玲笔下的“绣在屏风上的鸟”,变成了林幸谦所描述的“铁闺阁”中的一具行尸走肉。她的生命从此不再有光华,也不再有灵魂,只有一副空洞洞的躯壳被无声的时间所剥蚀,在无情的岁月中沉寂和凋零,而她自身也变成了一个被虐与施虐的恶魔般的女人,而这也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甚至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所有女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家族 历史权威 秩序
已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是血缘、生活及感情缠织起来的蜘蛛网。在这个网里,浓密的情感核心中有一个不可渡让和不可侵犯的父亲意象。这个父亲意象辐射出一股权威主义的气氛”[2]102,这种气氛就像空气似的,覆盖乃至笼罩、扩散到整个生活圈子。在《大宅门》中,这种“权威”正是叙事者有意展现给我们看的,也是编导极力张扬和为之赞叹的所谓“阳刚之气”,这种“权威主义的父亲意象”,从电视剧一开始,便能强烈地感受到。白荫堂作为大宅门一家之主:一脸严肃、口衔画笔、凝神作画。同时还借着仆人安福之口道出了他的规矩:谁搅乱了他作画的兴致,是要挨板子的。孙子白景琦出世,女儿白雅萍前来道喜,他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劈头盖脸、一顿呵斥,“生了就生了”“谁让你进来的,出去!”这些画面不但渲染了白老爷白荫堂在家庭中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地位,同时也使整个家庭笼罩着一层“声威”的影子,这就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地对女性说话的口吻。如训斥白文氏:“你一个女人家懂什么,你是哪家的媳妇,尽替人家说话!”就连一向老实忠厚的白家大老爷白颖圆对自己的妻子也是恶声恶气:“我们男人说话,哪有你女人插嘴的份!”由此可见,在男权意识浓厚的大宅门中女性根本没有地位和尊严可言。
“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不仅导致女性在语言、文化方面的次等或卑下地位的形成,而且长久渗透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之中,深深影响着女性的生活、心理与人格发展。即使有表面上的尊重,如花五百大洋买来的抱狗丫头香秀,表面看吃得香穿得好,而其实质上的地位和命运仍然还不如一条狗。遗憾的是,这一点却被过度维护男权的叙事视角所遮蔽而无法得到充分的揭示,反而成为编导者津津乐道展示其“声威”的一个重要证明,这种误导在《大宅门》中比比皆是,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平等,独立个性意识,在《大宅门》的历史叙事中是一个缺席的存在,更是一大盲区。
也正是这种“盲区”的存在,导致叙事者给我们营造出另一种表象,我们看到在竭力渲染男性“权威”的同时,展示的是女性的温柔顺从、逢迎、压抑及投合。剧中多次出现女性服侍人及为其洗脚,刷牙,洗脸宽衣,示爱等镜头,从中不难看出叙事者的性别价值观。同时这些影像符号似乎也在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告诉我们在大宅门中也存在着爱。然而,这真的是爱吗?恩格斯指出:“形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情性等等,都曾引起异性对于发生性关系的热望……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由此看来,编导让我们看到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3]56 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爱是建立在两性平等之间的,是建立在男性“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女性“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3]85,以此标准看,《大宅门》中白景琦和四个女性之间的爱远没有达到这样爱的高度。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我们能看到表面上的尊重,如抱狗丫头香秀能享受到和主人同桌吃饭的荣耀,但究其实质这仍不是爱,“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
如果说,在“性——性别体系思想的架构之中,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定位,导致女性在语言、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中遭受被压抑和被剥削的命运”的话[5]11,那么,在另一方面,父权制势必竭力推崇男性主体的利益和价值。
“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礼记·郊特牲》)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晏子春秋·家人》)
“天”在此成为“君”、“父”的象征,男性在“人”的统一自我中,被置于宗法的中心位置。从而,使男性作为宗法“菲勒斯”的文化象征得以权威化和合法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尊阳贬阴、男尊女卑的宗法观念下,男女主从关系已和天地、阴阳、君臣、夫妇等关系联结成完整统一的男性宗法中心体制。在象征意义上完成了男主女从的定位:男性以主体身份进入宗法‘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女性则被收编在家庭婚姻之内,扮演男性主体的他者。传统宗法上的性别秩序和礼教规范,据此得以在文化、语言和社会中得到正名,并对女性进行礼教与规范的宰制。”[5]203
而支持着“天”、“阳”、“刚”、“乾”的具体道德伦理准则可简单地概括为忠孝节悌仁义礼智信等,尤其是对“孝”的强调和推崇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也是“家庭中心主义的灵魂和基本命题”。而“孝是非对称性的,也就是说,尽孝永远是下一辈向上一辈仰视的事”。在《大宅门》中,编导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什么是“孝”,那就是绝对的服从和听从。白景琦再桀骜不驯,任性乖张,但对母亲却是绝对的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即使杨九红在那边上吊寻死,他也能安然地陪老太太看戏、听戏,老太太让他去车站阻拦杨九红去济南,他也不敢不听。总之,《大宅门》竭力美化和歌颂白景琦的这种“孝”,无疑是强调一种伦理秩序和纲常秩序。然而这种“孝”却是建立在戕害女性、侮辱女性之上的,同时也有悖于个性独立、自由等现代道德准则。考虑到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地——北京,以及讲述故事的时代——即将跨入另一个新千年,作品所显现的价值观和男权意义更不能不让人感到人本主义思想的倒退。因为早在“五四”时期,我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就对这种“愚孝”及家庭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危急中的家庭:1920~1940年中国知识分子论家庭》一文中,白佩兰认为:“中国人在强权面前的屈服关键在于儿女孝顺这一儒家传统的最高美德。”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历代统治阶级都大力提倡孝道,以便使其臣民学会盲目地服从一切。”[6]48因而,在从家庭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向个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转型中,孝悌伦理受到现代作家的激烈抨击,一大批作家如鲁迅、巴金、曹禺、老舍、张爱玲等对家庭专制、君主专制与忠孝伦理都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然而《大宅门》的编导却将“忠孝仁义”写得有声有色,并声称这不但是维持传统的需要,也是张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砝码。问题是,这是什么民族精神?站在性别立场的角度很有必要考察一下这种传统文化和所谓的民族精神到底是什么?
民族叙事 想象共同体 性别
《大宅门》通过白景琦的一生,从1880年到1980年的一百年的家庭回忆(播出的上部,至1937年终止)表现了特定时期的民族生活,而这种民族生活是通过地道的京腔京味、对民间艺术的玩味,通过“中药”这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行业所表现出来的,其中不难看出编导者的民间情怀和民粹主义的立场。可以说,《大宅门》以具象的方式再现了历史,召唤或激发了本土文化的想象,同时作为一部被誉为“具有豪迈民族气势的作品”体现了共享的民族价值,也暗含了作为民族总体的种族记忆。那么,什么是民族呢,从一般意义而言,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然而,在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民族”只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因此“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7]5-7 《大宅门》的民族叙事也正是这种“想象共同体”的产物,尤其是电视剧的最后二集表现得更为明显。
叙事者通过白颖宇、白景琦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英雄”壮举,一方面“给予男性以新的自我定义”,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话语通过赋予他新的主体位置,从而使这个男人获得‘阳刚之气”,[8]299。转瞬间,一个吃喝嫖赌、为非作歹,一生在家里家外都是败类的白三爷,由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自杀,一跃成为“抗日”楷模和家庭中的英雄,而白景琦慷慨悲壮的陈述遗嘱之举,为这个“传奇”人物的一生涂抹上了最后一层绚丽的光彩。然而,当《大宅门》的民族叙事将男性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主体”的时候,“女性却因为自身被男性所占有,所以并未自动地共享着那种男性中心的领土感。”因为民族主义、革命本身也是男性化的,“国家的劫难不能解释,也不能抹去女人身体所承受的那种苦难。”[8]296 因为无论是在占领前还是日据时期,女性的命运都是相同的,雅萍在八国联军时遭蹂躏,杨九红在战争来临之际遭贬逐,可是这一切都动摇和改变不了男性亘古不变的“特权”。白景琦的儿子虽然竭力反对自己的父亲再娶亲,但他自己却在济南娶了二房姨太太,白景琦国难当头又年近六旬但照样不顾众人反对娶到一个如花似玉的丫环,因而,虽然是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但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却存在着永远的变和不变,同和不同,“因为女性的困境在于她们面前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因此,当男性通过民族叙事获得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获得骄傲和身份认同以及一种民族的归属感和荣耀感时,女性却只有沉默而冷漠地看着这一切。从而,电视剧的最后一幅画面成为一个绝好的隐喻。当白景琦召集全族人慷慨激昂地发表最后的“演说辞”(遗嘱)时,一个全景慢摇镜头掠过,我们看到白家上下老少所有的男性,无不群情激愤,摩拳擦掌,只有杨九红一个人坐在那里无动于衷手捻佛珠,面无表情,仿佛置身世外似的麻木地看着这一出出“表演”。
这也再一次印证了一个真理,当男性为家园、为民族去献身、去斗争时,“一个女性注定由于她的性别戳记而永遭放逐,她无法将‘家’等同某个特定的地方”。这一点女性的感受是共同的,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在其《三枚金币》中就表达了这种女性主义立场。伍尔夫认为,“作为女性,她不可能分享这一民族斗争所提供给男性的光荣、利益和男性的‘成就感’,因而当女性被要求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员时,她回答,‘我们的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视女人为奴隶、剥夺她的教育权和财产分配权,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感谢英格兰。”在我国,也早已有学者发现,30年代即蜚声文坛的著名女作家萧红也持有同样的女性主义立场,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不但“深刻地揭示出民族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空间”,同时“还拒绝将女性的身体升华或置换为一种民族主义话语”,并且“从女性身体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度,这一角度使得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场所和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9]。的确,民族问题取代不了性别问题,阶级压迫也置换不了性别压迫,因此,当大宅门的民族主义叙事将白颖宇这样的男性塑造为民族国家的主体及爱国志士时,作为一个女性,却无论如何难以苟同他那慷慨赴死时的临终宣言:“人生一世图什么呀,吃喝玩乐呗,有了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抽大烟,逛窑子,山珍海味,绫罗绸缎,有钱干什么都成,可就有一样不能干,就是不能当汉奸!”
真的“有钱”干什么都可以,“有钱想干什么都成”吗?从这种对钱的崇拜心理中我们不难看出编导者的价值取向和情感立场。由此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整部《大宅门》虽然竭力想弘扬传统文化,歌颂其民族精神,但由于编导者人本主义价值立场的失落和性别视点的盲区,使得它只成为了一部充满男权话语和封建思想糟粕的历史叙事。
“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的确,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民族”虽然是一种“想象共同体”,但我们要“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民族化的“想象”,“传统文化的建构”其目的是什么,它是否被各种意识形态所利用,是否“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并和“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因为“民族主义的魔法”,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它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过去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因而,安德森主张“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加以理解。”[7]13 的确,早已有女性主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深刻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它将主体位置赋予到男人身上,促使他们为领土,所有权以及宰制的权利而战。”[8]285 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及民族叙事作为一种权威话语,是为男性的价值、利益、权利辩护的,而这种话语的形成“既不神秘也非自然形成。它被人为构成,被辐射,被传播;它有工具性、有说服力;它有地位,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它实际上与它奉为真理的某些观念,与它所形成、传递和再生的传统、感知和判断无法区分。”[10]26 无疑,这即是约翰·加尔顿所指出的“文化暴力”,它是“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包括宗教、艺术、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等等一系列‘象征领域’。加尔顿强调,把‘文化暴力’的问题提出来,就是要充分引起人们对那些使‘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显得‘自然’、‘合理’的观念、体制、习惯、价值产生批判意识,并由此而推动社会和政治的变革。”[11]2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流行着一种极力赞美传统社会的家庭制度和伦理道德,借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有人就这样认为:“西方近代启蒙学者,因为‘怀乡情结’,‘家庭感情’等无法被经验科学所证实,而对其采取否决的态度,其结果,是证明了科学的无力或失败。而中国的反传统者,或者将‘娜拉的出走’扩大为对家庭的反叛,或者因为反对专制性的权威而倡导绝对的‘反权威’,或者将个人的孤独建立在可以舍弃友情和亲情之上……其实都体现为‘反传统’问题上的情绪性和盲目性,其结果,也自然是以偃旗息鼓告终。换句话说,由于我们没有将对生命的解放与生命本身对安定感的寻求,都作为生命本身的要求来看,结果,我们就‘反’了不应该被反的传统,也‘反’了永远也反不掉的传统。”[12]187
真是这样吗?我们传统中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腐朽的权力等级制度,扼杀人性的礼教束缚不该反,反错了吗?或许还是这位学者看得清楚:“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强大的男性社会是通过对女性的压制、贬抑、排除才建立起来,柔弱的女性是男性的永久有效的证明。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及其相互之间的对立冲突,构成人类生存的那些习以为常而又惊心动魄的基本事实,因而也构成我们文明中的那些特定的禁忌、规范和礼仪;当然也构成我们社会中蛮横而和谐的等级秩序;它们强有力地影响并支配我们的思考对象和思维方式。”[13]112
人类是健忘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早已忘记或忽略了这段历史。因此,恩格斯的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是一个必要的警醒:“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3]66
可以说,神话包括历史的最主要的功能似乎是:对秩序及维护秩序的需要,因为“正是年代久远才使所有的东西包括物理的东西和人类的制度获得了它们的意义、它们的尊严、它们的道德和宗教价值。为了保持这种尊严,就绝对必须使人类的秩序以同一不变的形态延续和保存下去”。[14]284 无疑,历史的书写或叙事是保持这种需要的最为有效的统治工具,它既可以反映社会层面的问题,又可以作为实施权力的符号发挥隐蔽而巨大的作用,尤其是电视剧以故事和神话的形式较之强加于人的历史记录更易被接受,但是由于支配性文化的操纵作用,叙事者若没有某种批判意识,就会在这一影像符号编码之中迷失自己。
因此,当今天男权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话语、商业话语合谋,以家族、历史、民族叙事为表象进行一种新的“再叙事”时,当它成功地转移充斥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危机(如失业下岗、家庭暴力)与身份焦虑时,同时当它有效地遮蔽了新的、剧烈的阶级分化及性别秩序的重新建构过程时,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对这种叙事及男权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和挑战。
收稿日期:2008-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