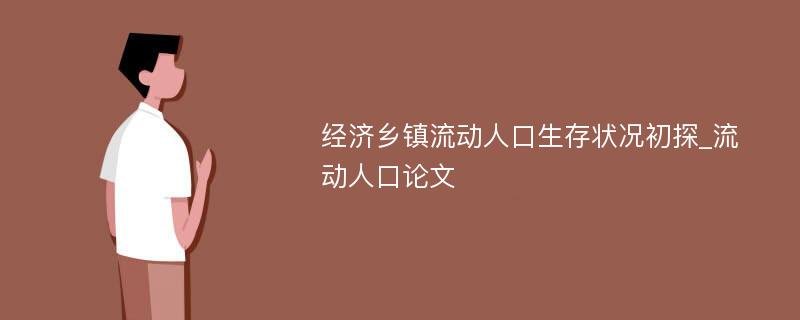
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生存状态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经济型论文,生存状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是指以从事经济活动为手段,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从农村流入城市,但不改变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口。本文以下的叙述即是严格按此定义展开的。80年代以来,流动人口以加速化的迅猛之势席卷大江南北,引起政府、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也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但此前的研究多从流动人口的结构、流量、流速、动因等人口学特征及其对城乡社会影响的角度展开。把流动人口特别是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作为人口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其生存状态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拟在这方面作点努力,但因统计资料的有限,本文只能侧重于定性的、粗略的、初步的研究。
一、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之势不可逆转,并将成为中国21世纪上半叶面临的严峻人口问题。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对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特别的关注。
据统计,目前我国长年飘泊在外的流动人口已达8000万(注:辜胜祖、成德宁:“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镇化”,《经济经纬》1998.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增长,流动人口数量仍将增长,20世纪末达到9000万左右,估计到2010年将达到1.2亿(注:李竞能:“21C中国人口理论展望”,《人口研究》1998.2。)。相当于整个德国或日本的人口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同时,流动人口进城已有从个体化变为家庭化的倾向,在一些大城市已形成“移民社区”雏形。
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经济社会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首先,为流入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弥补了城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据调查,早在1995年,上海市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已约占本市职工总数30%,在建筑、纺织行业的一线工人中,约40%以上是外来民工(注:李维平:“流动民工体制外在生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5。)。而在中国最大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之一的珠江三角洲,流动民工在当地劳动力构成中占的比重还要更大些。其次,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为流入地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据江苏无锡市测算,每个民工一年创造的价值,除去工资以外,约为地方和企业挣下4000元利税。据此推算,全国8000万流动民工为所在地创造的利税将高达3200亿元(注:李维平:“流动民工体制外在生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5。)。第三,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以其灵活多样的服务,丰富了市场,便利于市民的生活。第四,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以其特有的压力方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不仅如此,笔者认为更主要的是,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通过对城市的冲击,沟通了城乡关系,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对于这个规模巨大,恒常变动,对城市发展、社会稳定举足轻重的特殊人口群体,他们自身的生存态势如何,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关注。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客观地对待这个群体,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
二、简陋拥挤的住宿,温饱型消费,单调枯燥的业余生活;工作劳动强度大,报酬相对低,工作稳定感差,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与流入地市民交往隔绝,不能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生活;长期漂泊在外,季节性往返流迁;现实与希望反差强烈,内心处于常态失衡,他们被称为“盲流”、“民工潮”、“边缘人”、“两栖人”、“候鸟型人”。
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虽以其汹涌如潮之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虽然在流入地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在城市的处境十分艰难。
1.基本生活状况
衣、食、住和文化娱乐等无疑是基本生活状况的主要内容。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用工单位提供的住房,出租房屋及自建棚屋内。其中以用工单位提供住房为主。据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调查组1996年调查显示,79.9%的外来务工者享受免费住宿(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但用工单位提供的宿舍及建筑工地临时房大多简陋拥挤;出租屋和棚户区则卫生条件普遍较差,并潜藏着火灾、违法犯罪等许多不安全因素。
衣、食方面倾向于温饱型消费。经济型流动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挣钱,因此其收入的40%以上被节省下来,在吃、穿方面的标准是谋求温饱。
业余生活方面,据调查,即使在象浦东新区这样比较规范,发展较快的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业余生活亦比较单调枯燥,以住家娱乐为主要活动方式,看电视则是娱乐活动的主项,娱乐消费水平较低,流动人口本身对目前业余生活的满意度评价亦很低。
2.职业生活状况
我们可以从就业途径、工作领域、工作报酬、工作稳定性及劳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考察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生活状况。
目前,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其就业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1)有组织的劳务输出;(2)通过“包工头”;(3)通过职业中介机构;(4)通过劳动力市场;(5)通过私人关系。上述途径中除用工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现场招聘及私人关系外,其余途径都是有偿服务。据估计,为谋到一份工作,往往需要支付一百到数百元甚至更多的服务费用;如果中介机构违法经营,在付出高额中介费后,就业仍不能落实。
就工作领域来看,在流动初期,农民工多集中于劳动力较少,劳动强度大的生产第一线及苦、脏、累、毒、险等工种。随着产业的发展及结构的调整,以及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浦东等发展较快地区,流动人口的工作出现向技术性工作延伸的趋势。
在工资和待遇方面,如果以其在农村的收入为参照看,一般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都偏高;但若是与其劳动付出比则存在着“多劳少得”的情况;与当地市民比则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据调查,上海浦东新区外来人口中有42.1%的人抱怨报酬稍低或远远低于作出的贡献,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认为与上海人同工种的活,自己拿的比上海人低(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另据马西恒分析,在国有某些企业中,固定工的月工资收入是同工种同岗位农民工的1.5—2倍(注:马西恒:“关于中国入城农民工就业问题分析”,《江海学刊》,1996.1。)。同时,流动人口在职务升迁、奖罚标准、劳动保障等方面也受到区别对待,面临狭窄空间。
工作的稳定性是考察外来人员职业生活状况又一重要内容。据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调查组的调查,在回答“认为您的工作是否稳定”时,认为“讲不清,不稳定,很不稳定”的占38.9%(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如果考虑到浦东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及此次调查是以外来流动人口比较稳定的住居地和工作来进行抽样的话,感到工作不稳定的实际情况可能还高。
劳资关系是流动人口职业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由于社会的行政、经济组织给予民工的帮助甚少,民工间无法形成紧密的联系渠道及社会网络,加上自身素质所限,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一般比较顺从,遇到不公平待遇,敢怒而不敢言。即便如此,在一些地方,民工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亦时有发生,如拖欠工资。据广东省执法大检查(1996.12.25—1997.1.15)的结果, 拖欠工资的企业占被查企业的65.4%,拖欠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刘德骥、郑国墨、李新:“四川民工输出和管理面临的新情况及对策”,《社会科学研究》1997.5。)。又比如,任意延长工时,强迫民工无偿加班加点,不重视民工劳保,不办理人身伤害、医疗保险,民工生病,因工致伤,老板仅应付性处置一下,恶劣的甚至置之不理。在执法检查中,被查2572家企业,违法加班加点74.3%,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36.8%。东莞市1996年因工致伤民工500多人, 由于企业未按规定办事,上诉1645人次(注:刘德骥、郑国墨、李新:“四川民工输出和管理面临的新情况及对策”,《社会科学研究》1997.5。)。
3.社会生活状况
由于政策、经济、心理、语言、文化、地域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市民实际上处于近乎隔绝的状态。流动人口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同乡或亲属,与当地居民交往的频率较低,交往的面较狭,仅限于同事关系和邻里关系。由于交往的隔绝,以及基于二元社会结构的身分地位的不平等,流入地市民对流动人口存在歧视倾向。如一项上海市民对外来人口的心理接受能力的调查显示:78.2%的居民能够接受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公平竞争就业岗位,但认为外来人口同工报酬应等同于居民的仅占53.7%(注:丁金宏等:“论外来人口与城市社区整合——上海市民对外来人口的心理接受力调查”,《人口研究》1996.2。)。
在社会生活与组织上,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离开原来的家庭、社区、行政等社会系统到就业地,除“干活有人管”之外,他们在就业地往往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以外。在户口、饮食、子女上学等方面缺乏社会安排;个人无法正常参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享有应有的权利;同时也得不到组织的教育、监督,没有社会的约束,也缺乏保护。
由于与流入地市民的隔绝,长期游离于流入地主流社会以外,为寻求帮助和心理上的归宿,流动人口的团体性和帮派性便显性化。来自同一源地或从事同一职业的外来民工,常由一至二人领头,集居在一起,相互关照,同操家乡方言,形成具有一定人口数量、共同的利益和某些集体的意识行为的“外来民工社区”的雏形(注:徐长乐、罗祖德、袁雯:“上海市民工潮的形成机制及预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96.1。)。
4.生活的稳定程度
由于乡城经济社会“推拉”效应的恒常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城市化完成及二元社会结构消失之前会恒常地流入城市。但由于阻碍和制约因素的存在,他们始终不能融入城市,这就决定了流动人口生存状态的一个重要特征,长期飘泊在外,季节性往返流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短则三、五月,长则数年。但由于他们的社会身份始终无法改变,他们的户口仍留在乡村社会,没有割断与土地的脐带,因此,长年的飘泊岁月被季节性的回流分割成一个个片断,整个生活缺乏稳定,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据部份城市调查,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平均在外滞留195天,其中从事家庭服务业307天,建筑施工297天,其他雇工236天,小商小贩225天,各项修理业207天(注:李梦白:“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23。)。
5.内心常态失衡
据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一书中的分析,“良好的品行、健康的精神,还有其他看上去象个人品质的东西,实际产生于社区结构中,产生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而并不是基于个人本身的。”(注:〔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上)刘云德、王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6。)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后,既脱离了其原来的乡村社会,又无法融入其现存的城市社会,因而其心态平衡便失去了良好的社区和人际关系基础,内心处于常态失衡。这种失衡表现在:不能融入城市社区及获得良好发展的挫折感;受到来自市民社会的主观上和客观上不平等对待的被剥夺感;生活的飘泊不定及主观上疏离乡村生活,客观上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无归宿感;基于上述内心感应的反抗意识和报复心理以及茫然卑弱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一些城市刑事犯罪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居高不下看作这种心态失衡的外在表现。
三、社会结构不开放是民工不能平等地融入主流社会的根源;观念上不平等意识强化了流动人口与市民社会相互认同的难度;流动人口融入市民社会的自身条件尚不成熟。上述制约因素长期存在,使得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目前的生存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
建国初期,城市对农村人口是开放的。1958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后又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辅助性的行政措施,如城市人口“定量商品粮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条例》为核心,其它辅助性措施为补充的户籍管理制度。(注:辜胜祖、成德宁:“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口城镇化”,《经济经纬》1998.1。)这种户籍制度把全体公民划分为农业人口的农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市户口,从而人为地形成了彼此分割的不平等的两大社会集团,强化了二元社会结构,从而使农村人口流入并融入城市受到阻碍。
由于传统户籍管理制度将户口与社会地位和福利直接挂钩,使户口成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分的象征。市民社会对农村社会的不平等意识由此而生,而且由于其具有相对滞后性,即使在户籍管理有所松动甚至根本变革的情况下,这种不平等意识仍可能延续,因此,流动人口与市民社会的相互难以认同便强化了。
农村与城市的长期隔离,使得农村人口与市民在文化素质、思想意识、生活习性、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据浦东新区流动人口的课题组调查,浦东新区流动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达81.5%(注:浦东新区流动人口课题组:“浦东新区外来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6.1。)。思想意识、生活习性等带有浓厚的源地农村社会色彩。在与当地人交流中普遍存在语言障碍。这一切在客观上都阻碍了流动人口融入市民社会。
由于传统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尚需时日,观念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滞后性,以及全面提高流动人口素质尚有诸多困难,因此,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
四、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中孕育着流动的无序及流入地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此应逐步改革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强正面宣传教育,淡化城尊农卑的不平等意识;采取措施全面提高流动人口素质,谋求流动人口生存状态的改变,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由于流动人口不能被流入地主流社会所接纳,其流动的动因便简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谋求更高经济利益的心态和信息不畅等因素作用下,流动便呈现出无序状态;乡城往返迁移无序;对流入地的选择盲目无序;在流入地择业时无序——频繁的就业和失业。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的无序流动,其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因素。
由于流动人口与市民社会不能整合,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便会产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流动人口由于在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得不到公平对待,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内心处于常态失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的提高,自身组织能力的增强以及在流入地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劳资冲突和磨擦将会逐渐增多,与市民的矛盾也会增加。另一方面,外来民工多以籍贯而居,以职业合伙,具有一定的团体性和帮派性,易形成具有一定人口数量,具有共同利益和某些集体意识行为的“流动人口社区”,这种社区往往具有反主流社会的倾向,如北京的“浙江村”等。如果上述矛盾和倾向得不到缓解和扼制,势必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改变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
(1)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逐步消除流动人口融入市民社会的政策性壁垒。目前一些城市如重庆等的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启动,其特点是为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提供更大的自由度。
(2)加强正面宣传教育,淡化不平等意识。 改变过去简单地把违法犯罪、超计划生育等与流动人口紧密联系的研究、宣传模式,加强正面宣传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积极意义和平等对待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群体的思想,从而淡化不平等意识。
(3)采取措施提高流动人口各方面的素质。 利用各种形式对流动人口进行法制、道德、城市生活知识的教育,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素质,引导他们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秩序,正当致富,逐渐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生活。
总之,笔者认为,与流动人口有关的社会问题都与其生存状态有关。认真关注经济型乡—城流动人口这个特殊的群体,研究其生存状态,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谋求其改变,如此,则近可缓解与流动人口有关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远可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