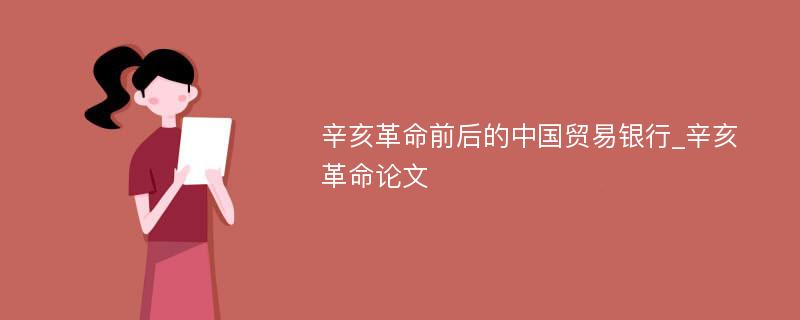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通商银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中国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一场社会政治革命,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有因政权的更迭带来的人事的代谢,而且也有社会企事业的经营管理的推陈出新。这里,就辛亥革命对中国通商银行(以下简称通商银行)的影响略作论述。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银行开办后的头几年,因得到清朝户部百万两定期存款和发行货币以及可以揽存汇解官款等特权,加上盛宣怀控制的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仁济和保险公司、中国电报局等企业营业较好,在通商银行存款较多。仁济和保险公司在银行开办的当年,一次存款即达40万两,后又陆续增至70万两。轮船招商局在银行开办不久,也暂存了32万两。所以,银行经营状况大致不错。“银行开办两年有余,据商呈报,每六个月结账一次,除开销外,收银发给商利四十万两,缴呈户部利银十万两,尚属平稳。”①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三年盈余所得即达40多万两。②但好景不长,此后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日人山下忠太郎等一伙伪造行钞引发行钞遭人挤兑风潮③等一系列事件,银行损失惨重。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分行先被“拳匪”、清兵抢劫,继遭“洋兵蹂躪”,所存银行钞票被一抢而光,所有账册荡然无存,直接损失高达41万多两。后虽经交涉收回武卫中军抢去的部分存款及追回部分放款,但亏欠仍有20多万两。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天津分行即关门歇业。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大班梁景和逃至上海,不久病死。总行在清点天津分行账目时,发现梁景和私自挪用行款高达31万两,因梁氏已死,后虽向粱的保人、远在香港的梁志刚索赔,但官司一直打到英国联邦法院,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最后不了了之。④这次上诉非但亏款未能追回,而且新增诉讼费7万多两。此后又发生镇江分行大班尹稚山亏挪行款高达64万两的事,盛宣怀在两江总督端方、周馥等人支持下,通过镇江府、扬州府查抄尹氏家产、将其变卖、发行彩票等手段,方才收回大部行款,但亏空仍高达21万两之多。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银行收支两底,亏短仍多达70余万两。盛宣怀承认“本督办奉旨招股选董承办此举,原欲为中国开利源,不料迭遭患难,致亏巨本,始愿难偿”。⑤由于银行经营不善,盛宣怀曾一度打算将银行资本移作萍乡煤矿商股,将银行关闭,但最终未获清政府同意。
通商银行在创办之初,即遭外国的重重阻挠,英国曾鼓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创办一家由英国资本操纵控制、由赫德督理的“中华汇理银行”,劝告中国不必另开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则要求盛宣怀将银行股本移入该行,由中俄合办,不必另行开设通商银行。在这些阴谋活动遭到失败后,列强侵害通商银行的事始终不曾停止。通商银行开办的第二年,英商福公司就向清政府提出由它代中国筹办官银行,由于商通银行刚刚开办,清政府没有同意这一要求。义和团运动后,有见通商银行经营严重亏损,法国、奥地利等国认为有“机”可趁,再次提出吞并通商银行的无理要求。1904年1月,法国驻沪领事向盛宣怀提出“请将通商银行归并法国银行合办”。⑥同年2月,奥地利政府派商人卞宜德大携带拟好的合并通商银行章程草稿找到盛宣怀,说:“目下通商银行如一人患痼疾,奧商现有四百万资财,不啻精壮之人……华奥合办,有此成规,便觉易于措手”⑦盛宣怀和银行总董们以“中国商务大,近来各国到此(指上海)添设银行不少,中国是一主人,仅一通商银行,论面子亦不能少”为由,加以拒绝。⑧
为了维持银行业务,弥补行亏,盛宣怀和银行总董们被迫采取以下措施:
一、裁撤洋帐房。银行开办之初,盛宣怀雄心勃勃,计划将通商银行打造成中国的汇丰,成为一家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及日本东京、南洋新加坡等地均开设分行的国际银行。为了扩展与外国的业务,取得外国银行对通商银行的承认,特聘英人美德伦为银行洋大班,组成洋帐房,此外,北京分行、香港分行也先后聘请了洋大班。然而,银行开办后,与外资业务往来较少,外资银行大多拒绝与通商银行往来,当时(即使在辛亥革命后),钱庄、票号是外资银行认可的唯一的金融机构,势力很大。钱庄的“庄票”和钱业公会的“公单”在金融市场上信用很高,通商银行的钞票必得钱庄和钱业公会的担保,外资银行方肯收受。所以洋帐房设立后,对外业务并不多。洋大班日常事务“仅止钞票签字、遇有交涉控案为本行出面,及所作押款核对洋栈单,三事之外,余皆无关轻重”。⑨业务虽不多,但开销却很大,年约银3.6万两。这对资本只有250万两的通商银行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节省经费,从1905年起先后裁撤总行洋帐房(保留洋大班),以及裁撤北京、香港两分行的洋大班。
二、减息。通商银行开设后,每股年息八厘,为了早日弥补银行亏空,总行决定从1905起将年息由八厘减至六厘。减息之举每年可为银行节省开支5万两,到1914年,十年减息,共为银行节省50万两。
三、增发钞票。从1905年起到辛亥亥革命爆发,通商银行发行钞票约870万元。其中没有准备的部分,每年约有140万元,按当时贷放利息8%计算,通商银行所获利润至少在80万元以上。这种虚本实利、将自己的亏损转嫁到社会头上的做法对弥补行亏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裁撤大部分行。通商银行成立之初,盛宣怀为了垄断国内的金融业务,先后开设北京、天津、烟台、汉口、镇江、福州、广州、汕头、宜昌分行,无锡支行,聘用各地钱庄、票号老板为分行大班,开展业务,企图将这些地方金融活动纳入通商银行经营活动范围之内。然而与盛宣怀的想法正好相反,这些分行大班大多借通商银行拨存分行的行款去从事自己的私人业务,以至分行徒有其名,平日银行门可罗雀。或干脆被人称为“大钱庄”。不少分行大班以银行名义私自挪借钱款,经营私人其他业务,结果造成一系列严重亏空事件。如前面提到的天津、镇江两分行的严重亏空。此外,还有上海总行韩祝三亏空事件、广州分行周石逋欠款事件、香港分行石何三欠款潜逃事件等。有见各分行盈利有限,而事故频频发生,为了弥补巨额亏空,从1905年起先后裁撤大部分行,祇留下烟台、汉口两分行。经过这一番裁併,银行业务活动大为收缩,此后业务活动主要集中于上海、江、浙地区。
在通商银行采取各种措施努力设法弥补巨额行亏期间,国内的金融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5年,清政府先后成立户部银行(即后来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07年后地方上也先后成立了股份制银行。中国金融不再是通商银行“天下独霸,只此一家”的局面。它们的开设对通商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通商银行的业务经营变得更加困难。户部银行“赋以代国家发行纸币并代理国库的权限”,总揽金融,推行货币,俨然如国家银行,且具中央银行性质。交通银行则以“管握轮、路、邮、电四政、收回利权为主旨”,除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外,还经营各种官款的收付兑放存储和发行钞票。两行均“挟国库、藩库(地方)之力”,因而资财雄厚。两行的开设,使通商银行所拥有的诸如发行货币、经办官款汇解存储等特权均被分割,通商银行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而生意大为减少。从1907年到辛亥革命前夕,地方股份制银行已达十多家。通商银行在有关省区的金融活动无一例外地受到这些银行的挤压和排斥,业务活动范围日益缩小。从1907年起到辛亥革命前止,银行每届收支都是入不敷出。1911年上半年收付两抵,尚亏短7万多两。
面对外国资本窥伺、图谋吞并、内资银行挤压,银行营业日益萎缩,入不敷出的景况,通商银行总董们忧心如焚。当时盛宣怀正督办全国铁路总公司,经手外债借款修路活动。总董王子展(存善)等建议盛宣怀能否将铁路外债借款的一部分拨存通商银行,以之挹助。通商银行是盛宣怀一手奏请开办,虽不是他的私人银行,但银行的成败与他的事业息息相关,且个人所认股份也较多,当然不会见危不救。他答应了总董们的请求,从1905年起,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修路外债的大部分款项交由通商银行存储。不过,存款数目虽大,但因随到随拨,存款余额并不多,银行获利有限。此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据通商银行账册记载,卢汉、粤汉、卞洛、正太、沪杭甬、沪宁等铁路的兴筑费用收支拨解都有一部分由通商银行办理,其中以沪宁铁路款项进出最大。1905年6月,沪宁铁路管理处交存通商银行25万英镑。此款按工程进展提存,双方协定每期5万镑,每次交解规元,收银不收镑,周息三厘半。同年7月,沪宁铁路在通商银行存款高达260万两,占银行全行存款的76%。同月14日,沪宁铁路管理处另将购地款9万镑也一并交通商银行存储。此后通商银行与沪宁铁路管理处进一步达成协议:每次提款不超过10万两,且须提前一个月通知。1909年(宣统元年)盛宣怀当上邮传部尚书后,权力更大,又为通商银行争得大批存款。1911年3月,清政府向日本正金银行借得整顿铁路款项1000万日元,盛宣怀将其中一部分拨存通商银行。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邮传部在通商银行的存款高达248万两,由于存款数目大,利息轻,又有一定的周转期,因此通商银行获得余利不少。银行总董李鍾珏等说:“盈余铁路存款,以两年计之,格外少算,约15万两”。“银行近年进出不过三、五十万,自宫保(指盛宣怀)照约存路款两宗后,骤添两百余万,其救银行者不浅。”⑩盛宣怀也承认:“银行得此巨款,出入汇划灵通,生意亦大有起色”。(11)到1910年2月,通商银行旧有亏空已减至15万两,到1911年10月,再减至7万两。可以说,该行是盛宣怀和清政府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借债筑路的实际获益者之一。
正当通商银行快要弥完亏空,踌躇满志大展经营时,又一场风暴——辛亥革命再一次打断了它的计划,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起响应,宣布独立。通商银行因受邮传部尚书、银行“督办”盛宣怀的牵连,遇到了自银行开办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二
1911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清政府内阁改组,盛宣怀被授为邮传部大臣。盛氏“向以勇猛精进任事”著称,就任数月,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划官建铁路,展拓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给事中石长信疏请将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支路听商民量力自办。旨交邮传部复议。盛宣怀复奏称“所筹办法,尚属妥协”,表示赞同。于是清政府未经交付资政院讨论,径直以奕劻、那桐、徐世昌署名正式公布。铁路国有,本身无可訾议。但这一政策一经宣布,立即遭到内阁和各省商民反对,但盛宣怀对之悍然不顾。旋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数额高达600万镑,规定若不敷用,还可续借400万镑,将湖广铁路和川汉铁路湖北段的修筑权出售给列强。各省反对铁路国有政策,初旨在争商办,抵制借款。现在看到清政府与盛宣怀借款列强,强行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于是湘、粤、川、鄂各省绅商士民纷纷表示抵制,相约开会,开展罢工罢市,以示抗争,结果酿成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为了平息风潮,清廷一面派端方为督办大臣,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一面以盛宣怀“不能仰承朕意,办理诸多不善、违法行私,贻误大局”为由,将其革职,永不叙用。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后,资政院议员和御史们再次奏请将其“明正典刑”,加以处死,以谢天下。盛宣怀见此惊恐万状,求助于列强,在驻英、法、德、美使馆的协助下,坐火车逃往天津,接着由德国派兵轮送到青岛,继而又被日本接到大连,再用轮船送至日本神户盐屋山,为防被人刺杀,盛氏改着和服,化名须磨布衲。
还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不久,盛宣怀预感时局将有大变,担心他经营的“公私产业”有损,急令所属企业负责人谋求对策。以目下时局将有重大变化,致函通商银行总董王存善、顾詠铨等“稍作准备,务使通商设法保全”。辛亥革命爆发后,特别是盛宣怀被革职和逃走后,使通商银行的未来前途存亡未卜,难以预料。为了设法保全银行,总董们采取了以下几个救急措施。
一、加紧行内人员的联络,规定无论有事无事,总董们必须每日到行视事;事无巨细,必须共同商讨决定。
二、本着稳妥谨慎的方针,采取一切手段,设法同盛宣怀取得联系,以便获取其“指示”和决定银行日后的行动方针。
三、鉴于目前市面不稳,人心慌乱,百货拥塞,规定银行银钱出入、行款押放,须加倍谨慎小心,以防坏帐、呆帐。
四、抓紧催收放款。自武昌起义爆发,银行就开始向有关厂矿店铺催收放款。11月,总行与盛宣怀取得联系后,根据盛氏指使,银行“立将裕太、集成、刘长荫、萧公峰、王眉伯、黄绩记、信大庄、协和公司各欠款设法紧催,以金蝉脱壳之计而保我通商头等名誉”。
五、与外商联络,将行产暂行抵押。盛宣怀逃到日本后,江苏都督府和沪军都督府分别没收了盛氏在苏、在沪资产。总董担心革命党人下步将会没收银行,于是决定由洋大班马沙尔出面,暂将银行外滩总行大楼抵押给外人。为此,总董顾詠铨和钦玉如就此先后与美商接洽数次,说明先行抵押,待事平后再设法收回。此举遭到美国驻沪領事反对,抵押一事最终未能成为事实。
六、积极拨款援救汉冶萍公司。武昌起义爆发不久,10月23日,江西独立。萍乡工人响应辛亥革命,举行罢工,致使煤矿生产停顿。通商银行得息后,根据盛宣怀的指示,总行先后三次从银行存现中拨款8万多元,并调拨江宁造币厂新币三十万元,雇用日清公司轮船装运至长沙,进行挽救。由于“措施及时”,使萍乡煤矿生产得以恢复。
七、刊登广告,更改英文行名。11月4日,上海光复。次日,上海都督府成立,由革命党人、同盟会员陈其美任都督。沪军都督府成立后,立即查封了上海的大清银行(即原先的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沪军都督府这一招着实让通商银行吃惊不小。因为通商银行的“督办”盛宣怀是“革命罪人”,且银行系奉旨开办,并领存过部款,享有承汇揽解官款和开铸发行货币等种种特权,因此,总董们担心沪军都督府下一个查封的对象很可能就是通商银行了。为防止万一,总董们决定先发制人,在报上大登广告,声明通商银行早已还清官款,并非官办银行,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堵住沪军都督府之口,不来查封。广告固然阻止了都督府接管该行,谁知银行此举却引来一件意外的事情,即更换银行英文名称。通商银行的行名取自“通商惠工”之意,但在创办之初,为了扩大影响,推广行钞,求得外国承认,将其英文行名写成“中华帝国银行”,意思就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天津分行英文行名干脆就写成中国银行。而且通商银行钞票上也印有英文行名,这点是公开的事,人人知道。所以,通商银行的广告一经刊出,即被人指出既为商办,为何英文行名取“中华帝国银行”?总董闻言,大起恐慌,在股东的纷纷要求下,于是银行再次刊登广告,将英文行名“中华帝国银行”更改为“中华商业银行”,并用双条墨线将行票上的“帝国”二字删去,另外加盖“商业”二字。
八、被迫接受沪军都督府的调查监督。沪军都督府原本并无接管通商银行的意思,但通商银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广告反倒引起沪军都督府的注意,直接招来都督府对银行业务的干涉。11月7日,陈其美照会通商银行:将派代表会同华大班共同管理银行账目,其调查结果直接向都督具报,规定此后凡银行改易名称、用人行政等均归都督府财政总长节制。银行总董接到都督府的照会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对策,一致决议呈文都督府:一、通商银行系属完全商业性质,请都督府不必干预;二、召开股东大会,公举董事,以合完全商股商办性质。在股东大会未正式召开之前,银行的用人行政一任本行董事公议,不必听诸都督府的命令。
通商银行总董的一纸呈文,并未能阻止都督府代表的“驾临”。11月13日,沪军都督府正式派遣代表来行调查帐目,并很快查出度支部币制局存在该行购买铜价银60万两。
关于这笔银款存储通商银行的经过是这样的:还在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试图统一全国的币制。当时担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兼任“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的差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911年1月,清政府从美、英、法、德贷到币制实业借款1000万镑。同年4月,盛宣怀指示通商银行总董、副大班顾詠铨同日本商人高木六郎洽商,购买日本生铜。同时拨出120万两币制借款(江宁造币厂所铸新币)存储通商银行作为购铜费用。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将120万两中的30万两拨存上海道,以供上海道作“急时之需”,对付革命。另外顾詠铨又开出30万两支票给上海日本正金银行,作为笫一批购铜价。支票虽已开出,但并未付现。所以,度支部币制局存在通商银行的购铜价实为90万两。而沪军都督府代表从账册上只查出60万两。
盛宣怀在革职逃往日本前,因南北大乱,日铜不能成交,曾电令顾詠铨与日商高木协商,建议暂缓六个月,在此期间,不妨先将江宁所造新币暂时“接济汉冶萍之急”,但当时汉冶萍不需要这么多款项,最后盛宣怀要高木“仍以铜价名义拨存正金,以后再行动用”。盛宣怀得知此款被沪军都督府查封后,急得直跺脚,电令顾詠铨与日本驻沪领事商洽处理,但日本领事以60万两系“官款”,不便插手为由加以拒绝,结果日商高木未能照盛宣怀的意图去做。购铜款60万两(实为90万两)仍存在通商银行。
沪军都督府查出60万官款后,因当时都督府财政紧迫,急需经费,要求通商银行立即付现,交给都督府使用。“银归革(都督府)而铜可勿交”。盛宣怀得知后,急电洋大班英人马沙尔“坚守”,拒绝交出。但在都督府的强大压力下,通商银行最终还是交出30万两,其余30万两因早被银行当着行钞使用,无法交出,直到此时,银行同都督府的这一交涉才基本告一段落。对银行来说,此举都是自己“自扰”酿成的,不过沪军都督府虽查出并没收度支部所存币制“官款”30万两,但对通商银行自身的其他经营活动并未加以限制和干扰。加上都督府的李锺珏、王一亭等均为银行总董,所以,对通商银行而言,可说是有惊而无险,不幸中的万幸了。
总体来看,由于总董们的努力,通商银行在辛亥革命这场大风暴中,不但平安地保存下来,而且营业也未受到什么损失,相反,由于辛亥革命是一场带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暴力排外的义和团运动,随着清朝灭亡,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通商银行的经营非但没有萎缩,反而有了较快的发展。
三
辛亥革命后,通商银行一步步地向普通商业银行方向发展,不过道路并不平坦。作为通商银行的创始人、“督办”盛宣怀始终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和放弃对自己原先开办经营企业的控制。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身份掌握了国家政权。同年10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杜门而不见客”,首以赈灾为名,独自捐款100万元。继以报效20万元“水利费”给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博取民国政府的“好感”。程德全遂下令发还盛氏在辛亥革命中被没收的全部资产。1913年,他通过自己党羽的活动,再次当上汉冶萍公司董事长,继而又谋得轮船招商局董事会的副会长。“二次革命”发生后,他诬蔑革命党人是“革命流毒忽又剧作”,利用招商局轮船积极地为袁世凯运送军队和武器,肉麻地吹捧袁世凯“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之而无不及”。(12)袁世凯与盛宣怀积怨甚深,对于盛宣怀的吹捧献媚根本不予理睬。因无政治靠山,所以,他的许多企业常常遭到地方政府的侵蚀、刁难,经营极为困难。
对于通商银行,盛宣怀当然不会放手,银行系他奏请开办,虽经营不善,但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才使之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回国后,便通过自己的外甥、总董兼副大班顾詠铨仍牢牢地将通商银行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过由于他原先控制的企业在辛亥革命前后经营不善,通商银行的股票早已作为这些企业的股息发放给股东,遂造成通商银行股东成分发生重大改变。
辛亥革命前,通商银行的资本主要是半官半商的洋务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的投资和部分官僚买办私人认购,一般中小企业认购的并不多。辛亥革命期间,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洋务企业拥有的股份大幅度下降,中小工商业者的股份有了显著的增加。辛亥革命期间,因为长江航运中断,江轮停驶,轮船招商局营业锐减,亏损严重,股东股息无法发放,不得不将所购通商银行股票80万两,于1911年、1912年作为商局股息搭发给商局股东。而中国电报局所认购的20万两通商银行股票早在1898年就作为电报局股票股息搭发给了股东。这样做的结果,使通商银行的股票被分散到更多的人手中。商股股东的增加,遂引发要求换名过户之事的发生。手持通商银行股票的股东们纷纷来通商总行要求更名过户。仅1911年6月,换给新股(票)者四十多万两。1912年初又换给新股(票)三十多万两。两年换户达七十多万两,“为数甚巨”。据不完全统计,到1912年4月为止,总计更换股票1万张,换名过户的股东约有1246户,加上原有的商股股东,总计约有1591户,拥有通商银行股票9700多股,约占通商银行全部股本的40%。由于商股比重成分的增加,从而使通商银行资本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式具备了普通商业银行的性质。
通商银行的章程规定,该行是按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商股商办,定期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总董,负责管理日常行务。但在辛亥革命前,银行实际由盛宣怀一人“督理”把持,从未召开过股东会议。辛亥革命期间,银行总董为了拒绝沪军都督府接管银行,插手银行用人行政,曾一再表示,并刊登广告说明银行纯系商办,表示要定期召开股东大会确定银行人事。辛亥革命后,银行商股股东比例增多,要求有权过问银行事务,特别是有关人事安排的呼声越来越高。1913年2月10日,香港地区的股东就写信给盛宣怀,以“今时移事异,自应按照商律,完全商办”。(13)
除了广大股东要求外,原先的银行领导层经过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政权更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民国后,盛宣怀的银行“督办”一职无形中被取消,他虽然千方百计想重新控制该行,但因无政治靠山,再也无法也不可能像辛亥革命前那样影响和左右通商银行了。此外,原先银行10总董中,首席总董张振勳(弼士)远在南洋经商,从未到行视事,并早在1904年就宣布辞去该行总董。而其余总董如叶澄衷、严信厚、刘学询、严瀠等也相继去世。银行领导的实际状况也迫切需要重新调整和补充。
在广大股东的强烈要求下,通商银行于1913年初正式召开首届股东大会。参加会议的多为上海地区的股东,其他地区与会的股东很少。由与会股东“投票”选举董事,组成新的董事会,除了现任董事外,又增补了严义彬、周晋镰、朱宝奎、傅筱庵(代表轮船招商局)等人为新的总董。不久又增补了盛艾臣为副董。在盛宣怀任“督办”时代,担任银行总董的“大都是道台班子,红顶花翎,箭衣外套,亦官亦商的”。(14)至此,无论从银行所持股票的股东成分来看、还是银行领导成员的更动,都表明了通商银行已成为纯粹的一家“商股商办”的商业银行。
民国以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通商银行新的董事会及时抓住机遇,除了继续保持同钱庄、票号的业务往来外,加大了对新兴中小企业的放款。为此,加大和扩充了华帐房的力量,华帐房由原先的6人增至14人。新增陈福保、田洪泉、朱襄程、顾松亭、赵震为华帐房管理人员,新增与中小企业、商家、店铺进行业务联系的“出店人员”10人。为了确保华帐房的领导,董事会又增补原华大班谢纶辉之子谢光甫为总行华大班的副大班,借以“商议改良一切”。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底,全国民族工商业较集中的上海,武汉、广州、杭州、无锡、天津等城市历年设立的民族工商企业有549个,(15)其中与通商银行有业务往来的中小厂矿企业商家约有110家之多。(16)当然其中不乏银行股东们所开办的企业。
与经营管理变化的同时,银行营业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变,到1912年上半年,银行收支两抵,已出现盈余。到次年底,不仅弥清了全部亏空,而且出现了近20万元盈余。(17)股票每股年息也于1914年由六厘恢复到原先的八厘。(18)
1916年4月,盛宣怀因病在沪去世。他死后,通商银行的实际领导权落到了傅筱庵手中。自此,通商银行可谓进入了“民营”的“商办”时代,成为当时中国众多的商业银行中的一员。
注释:
①盛宣怀:《推广通商银行以流通自铸银元折底稿》(光绪二十五年九月)见谢俊美辑《盛档》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纪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
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02年12月(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日本大阪的山下忠太郎、菅野原之助、上田元七及中义之助等四人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上海,与华商交往多,颇熟悉中国商情。四人决定合谋伪造通商银行钞票10元、5元两种,由上田将大批10元伪钞携至上海。1903年2月4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通商银行总行在营业时便发现了这些伪钞。消息传出后,市场人心大乱,第三天全市钱庄一致拒用通商银行钞票,而持有通商银行钞票者更为恐慌,于是持钞蜂拥至银行总行营业部要求兑换。由于银行当时库存现金准备不足,通商银行只好以金条、银条作抵,向汇丰银行借款70万元,方才保证了兑换。2月6日,上田又派一名日本人手持伪造的通商银行钞票到汇丰银行兑换,被当场扭获。在日本,菅野等则将5元伪钞在神户秘密转售,不久也被人发觉举报。由日本当局探知,并抄出全部未脱手的大批伪钞及制作伪钞用的机器、用纸等。山下一伙伪造通商钞票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曾应盛宣怀奏请,同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提出交涉,要求引渡山下等罪犯,赔偿通商银行损失。日本政府以“伪造他国钞票,日本法律无专条”为借口,加以拒绝。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对日交涉无果,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对于此事件,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及陈度的《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纸币篇》两书均语焉不详,可详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通商银行总董会议纪录。
④梁氏保人系粱的伯兄梁志刚,居住香港。通商银行向香港殖民当局提出交涉,向香港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但香港地方法院以梁志刚已加入加拿大国籍,不予受理,后又向英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驻英公使李经方曾与英国外交部就此事提出交涉,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通商银行的这次伦敦上诉,最终也不了了之。详见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纪录。
⑤盛档:盛宣怀致顾詠铨、王存善函。(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二日)
⑥盛宣怀:《愚斋存稿》卷61,第20页。卷62,第23页。
⑦盛档:《信义洋行洋东德满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
⑧盛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六日,银行总董致盛宣怀电函。《通商银行总董公信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
⑨盛档:李鍾珏、顾詠銓、王存善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⑩盛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七日,盛宣怀致温颐电函。盛宣怀:《愚斋存稿》卷61,第20页。卷62,第23页。
(11)盛档:《盛宣怀致孙宝琦函》。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1-298页。
(12)盛档:《盛宣怀致孙宝琦函》。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1-298页。
(13)盛档:《温佐才致盛宣怀电函》(民国元年十月)。
(14)毛啸岑:《通商银行五十四周年行庆感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
(15)汪敬虞:《近代中国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12—13页附表。
(16)盛档:据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年(1913)洋帐房、华帐房帐册往来客户名录统计。原件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
(17)盛档:据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年(1913)洋帐房、华帐房帐册往来客户名录统计。原件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
(18)盛档:见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会议纪录、公信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档案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