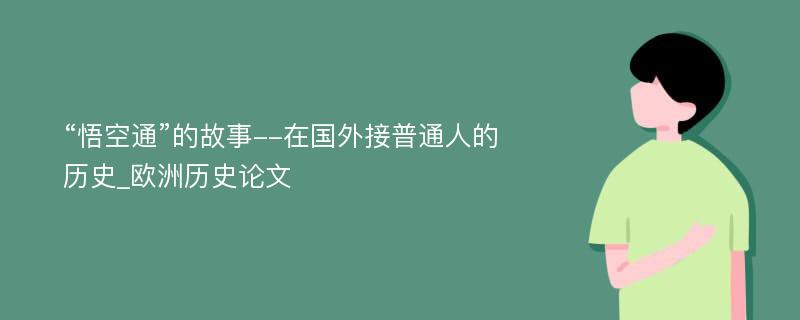
quot;Whang Tongquot;的故事——在域外捡拾普通人的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普通人论文,故事论文,历史论文,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K8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2-0106-11
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海外华人活动时,人们的眼光往往聚集在有特色的人物身上。欧美学者由于具备语言的优势,可以更方便地利用天主教会档案,从中找到一些被耶稣会传教士带到欧洲的华人的踪迹。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有Michae!Shen(一般音译为沈福宗或沈复聪),(注:Theodore N.Foss,The European Sojourn of Philippe Couplet and Michael Shen Fuzong,1683-1692,in Jerome Heyndrickx(ed.),Philippe Couplet,S.J.(1623-1693):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Sankt Augustin and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Louvain,1990,pp.121-142;另参见韩琦《17-18世纪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关系——以英国皇家学会和在华耶稣会士的交流为例》,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1-165页,第142-146页讲及沈在牛津的经历。)黄嘉略(又作黄加略,乃其西文教名Arcadio的音译)。(注:许明龙《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嘉略——一位被埋没二百多年的文化使者》,《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3期。)还有就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著的《胡先生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Hu)的主人翁John Hu(一般译为胡若望)。(注:胡可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1772年被一个耶酥会神父从广州带到巴黎,原来答应为该神父整理中国图书,后来因为行为举止让当地人难以理解,被看成发了疯而遭监禁在疯人院里达两年半之久。见Jonathan D.Spence,The Question of Hu,New York,Alfred A.Knopf,1988年。)史景迁还提到其他几个跟随天主教士到过欧洲的中国人。(注:参见史景迁著、王海龙译《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赴法国的中国人》,《跨文化对话》第七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69-187页。国内有关这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可参见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清廷曾经多次颁布禁止洋人偷载中国人出洋的命令。据《粤海关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议准“贸易番船回国,除一应禁物外,不许搭带内地人口,及潜运造船大木、铁钉、油、麻等物”;康熙五十七年(1718)又议准“澳门夷人夹带中国之人,并内地商人偷往别国贸易者,查出之日,照例治罪”;其后,雍正三年(1725)议准“附居广东澳门之西洋人,所有出洋商船,每年出口时,将照赴沿海该管营汛挂号,守口官弁将船号、人数、姓名,逐一验明,申报督抚存案。如出口夹带违禁货物,并将中国之人偷载出洋,守口官弁徇情疏纵者革职。……又复准西洋人附居澳门,如有夹带违禁货物,并中国之人偷载出洋者,地方官照讳盗例革职。”本文讨论到的几个中国人皆在18世纪后期赴欧,可能表示这些禁令到此时已经日形松懈,而黄嘉略更早在1702年便已出洋,似乎更显示这些禁令一直无法严格执行。见梁廷楠总纂《粤海关志》卷17禁令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又见道光《广东通志》卷180经政略23。)其实,在17世纪以后,以广州为中心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种种偶然的机缘,把一些比沈或胡更名不见经传的华人带上了欧洲的商船。他们经风抵浪,踏足欧洲国家,在当地只留下雪泥鸿爪,回国后也没有干过什么足以青史留名的事,自然就入不了后世中国史家的法眼了。不过,这类人物在当时华人足迹罕至的欧洲社会里,却往往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笔者2002年春在伦敦阅读文献时,便无意中“碰”上几位这样的人物,他们当时在英国的踪迹,零碎地留存在不同类型的英文文献里,如今捡拾起来,颇堪玩味。
“Whang Tong”:一个致函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的行商食客
在伦敦大英图书馆手稿部收藏的《班克斯函件》(Banks'Correspondence)中,有一封1796年6月18日发自广州,署名“Whang Tong”的英文信件。(注:本文所用的中国人名的拉丁拼法,皆沿用原文的写法。由于当时的中文拉丁拼音尚未统一,又受方言发音的影响,下文陆续出现的各种拼写略有差异的人名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物的名字。)这封信字迹清晰秀丽,语法略有瑕疵,如果不是受过相当程度的英文教育的中国人手写,就是当时在广州专门为行商服务的中国或外国英文秘书代书的。这封信的意义更在于,收信人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1820)时任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主席,(注:皇家学会于1660年成立,是英国历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科学团体。班克斯爵士在1778年至1820年担任该会主席,见该会出版之The Royal Society at Carlton House Terrace,London,1967.班克斯是目前欧美历史学家研究18世纪欧洲科学史最重要的对象之一,除了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外,还是英国多个科学组织的创办人。)是当时推动欧洲科学发展首屈一指的人物。以下是该信的全文翻译(按原格式):(注:大英图书馆手稿部藏Banks Correspondence,Add.MS.8099.209。本文所有英文文献由笔者翻译。)
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从男爵
先生:
归国以来,曾接先生鸿雁,不胜感激,惜当时未能马上回复,今但投尺素,以示来函早已收悉。为表谢意,谨乘布朗先生搭乘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回英之便,托其送达以下各物。(注:据Hosea Ballou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Vol.II,"East India Company's Ships at Canton,1775-1804",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于1795年到达广州。)乞祁鉴领,望勿见弃。
中国史书一套
茶叶一盒,共三种
珠兰茶两盒,装于一箱,上书先生地址
Nankeen花两盆,中国人称之为牡丹花,布朗先生将代为照料
吾今羁旅广州,住行商Chune Qua家中,Nankeen人。若能为先生效劳,当随时候命。谨候先生及先生家人身体安康,万事如意。
您最服从的仆人
Whang Tong
广州 1796年6月18日
信中提到的Nankeen行商Chune Qua,估计是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中提到的东生行的Chunqua刘德章(?-1825),其充当行商的时间是1794至1825年,(注: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初版193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302页。)与上述Whang Tong在广州发信的时间吻合。至于“Nankeen”,很可能是“南京”,即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的南直隶,(注:在Banks Correspondence许多发自中国尤其是广州的信函中,都提到来自Nankeen或Nankee的人或物(特别是行商和牡丹花),估计是南京,即南直隶。)据陈国栋查考,Chunqua祖籍安徽桐城,(注:Kuo-Tung Anthony Ch'en,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 ,1760-1843,Nankang,Taipei,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1990,p.352.)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Whang Tong所说的Chune Qua极可能就是东生行的Chunqua;而所谓Nankeen花,就是来自南京的牡丹花。在这里也值得补充的是,清廷曾经颁布过“外国来使不得私买违制服色、兵器、史书、一统志、地理图及凡违禁之物,伴送人员亦不得将违禁货物私相贸易,违者俱按律治罪”的禁令。(注:梁廷楠总纂:《粤海关志》卷17禁令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56页。)Whang Tong向班克斯馈赠中国史书一套,如果不是违禁,也是看准外国人因为中国史书不易得而对之渴求的心理。
Whang Tong这封信,是夹在数以万计在1765至1821年间与班克斯有来往的英国及欧洲各地著名科学家、航海家、文人、学者和商人的函件里的其中一封。据英国所藏班克斯信函的有关目录显示,在这批信件中,只有两封是由中国人发出的,除了Whang Tong之外,就是广州著名的行商潘启官。该目录说Whang Tong大约活跃于1770至1796年间,曾在1775年到访伦敦,并与英国的文士和科学家会面,他极有可能在这类场合中见过班克斯。(注:参见Warren R.Dawson (ed.)The Banks Letters:A Calender of the manuscript correspondence of Sir Joseph Banks preserved in the British Museum,the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and other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London: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8.有关潘启官的信函及当时其他广州行商与班克斯的联系,笔者将另文讨论。)不过,目录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参考文献或根据,笔者只能凭这几句按语特别是“1775年到访伦敦”这条线索追查。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向正在伦敦的自然史博物馆主持“班克斯档案计划”的Neil Chambers请教,Chambers先生帮我翻阅有关档案和数据库,一时亦无头绪。(注:班克斯死后遗下大量手稿、书信和动植物标本,大部分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自然史博物馆和皇家植物园,亦有部分存于英国其他博物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目前,伦敦的自然史博物馆正由Neil Chambers统筹“班克斯档案计划”,编辑出版The Scientific Letters of Sir Joseph Banks 1743-1820共6巨册,预计在2006年全部出版完成。)
“Quang at Tong”:一个亲访英国皇家学会的中国人
笔者同时又向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查询,该会的助理档案员建议我或可翻阅皇家学会1775年前后的会议记录和日志。结果,我在该会1774年末至1777年初的日志里,找到1775年1月12日接见访客的名单,其中获当时皇家学会主席约翰·普林格尔爵士(Sir John Pringle,1707-1782)接见的4名客人中,有一位注明是“来自中国的Quang at Tong”。(注:Journal Book of the Royal Society.Volume XXVIII,From Feb 17th 1774 to Feb 13th 1777,The Presidents Copy,pp,149-150,英国皇家学会图书馆藏。)
当时,班克斯虽尚未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但肯定是该会一名十分重要的成员。在当日接见访客的皇家学会会员中,其中一人应该就是班克斯。(注:登记的名字是“Mr Banks”,笔者未敢肯定其与约瑟夫·班克斯为同一人。)如果此Quang at Tong就是上述的Whang Tong的话,他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天与班克斯会过面,也很可能在此前后与班克斯有所接触。由于日志是一誊钞本,其记载的“Quang at Tong”一名,并非当事人自己的签名,因此写法和“Whang Tong”有出入是完全有可能的。假设这两个名字同属一人,这位Whang Tong先生,至迟在1775年初已经抵达英国,也很可能在其英国朋友的介绍下,有幸拜访连普通英国人也难以亲近的皇家学会,其后重返广州,并在1796年及以前,与班克斯有通信来往,也就是说,他在英国逗留的时间可能有20年之久;我们更不妨大胆推测,他有相当的英语能力,能够和当地的文人学士沟通。
“Hwang-a-Tung”、“Whang-y-Tong”或“Whang at Tong”:
西洋画里的中国小男孩
正当“Whang Tong”和“Quang at Tong”这两个名字在笔者的脑海中不断萦绕之际,笔者在追查另一个与18世纪广州历史有关的英国人布莱克船长的生平时,又碰到另一个类似的名字——“Hwang-a-Tung”。这个名字是在1936年1月4日出版的《札记与提问》(Notes and Queries)“文史随笔”一栏的文章上出现的。(注:自1849年首次在英国出版至今,《札记与提问》一直是英语世界作者与读者、藏书家与图书馆学专家间重要的交流园地之一。)这篇题为《布莱克船长的中国小男孩》的文章的主角,是一名叫“Hwang-a-Tung”(又名“Wang-y-Tong”或“Whang at Tong”)的中国男孩。(注:Geraldine Mozley,"Captain Blake's Chinese Boy",Notes and Queries,January 4,1936,pp.2-4。)布莱克船长(Captain John Bradby Blake,1745-1773)服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1766年被派往广州任商务总监。他对自然科学和中国的工艺技术兴趣浓厚,公余时积极收集植物标本,雇请当地画师画成植物画,并不断将这些标本和植物画托人带返英国。布莱克船长对中国瓷器也甚感兴趣,甚至把制造中国陶瓷的原料,寄给英国著名的陶瓷商乔舒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帮助他窥探中国陶瓷的奥秘。(注:韦奇伍德(Wedgwood)始创于1759年,至今仍是英国最有名的瓷器商之一。参见Sotheby's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orcelain(London,Chancellor Press,1998 edition),p.179.班克斯爵士与韦奇伍德相识,见Rüdiger Joppien,"Sir Joseph Banks and the World of Art in Great Britain",in R.E.R.Banks,B.Elliott,J.G.Hawkes,D.King-Hele,G.Li.Lucas(eds.),Sir Joseph Banks:A Global Perspective,Kew,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1994,p.98.)其后,布莱克船长客死广州,年仅28。据说,在他逝世前不久,皇家学会正准备选他为会员。
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是布莱克船长的外曾孙,他在1936年发表此文时,对于Hwang-a-Tung的真正身份,已经不大清楚,但他还是找到不少材料作出颇为详细的考证。以下是该文叙述的有关Hwang-a-Tung的基本事迹:
约翰·布莱克在其中一次返英时,带来一个中国男孩,引起了才华横溢、出身高贵的约翰·萨克维尔(John Frederick Sackville)的兴趣。萨克维尔是多赛特郡第三任的公爵。(注:此约翰·萨克维尔于1745年继任为多赛特郡公爵,于1799年在任上逝世。参见Victoria Sackville-West,Knole and the Sackvilles(London,Lindsay Drummond Ltd.,1949),Ch.8.)公爵把这个男孩带到他在诺尔(Knole)的宫室作僮仆,并让他在七橡文法学校(Sevenoaks Grammar School)读书……(注:Mozley,1936,p.2.)
萨克维尔家族在诺尔的宫室,在英国贵族社会中十分有名,其后人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Victoria Mary Sackville-West,1892-1962)在1940年代更专门著书,讲述这个家族及其诺尔宫室的历史。(注:Victoria Mary Sackville-West是20世纪初的文学家,与另一著名的英国文学家Virginia Wolf友好,其生平可见于Suzanne Raitt,Vita and Virginia:The Work and Friendship of V.Sackville-West and Virginia Wolf(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Appendix A.)在这本书的第八章“18世纪末的诺尔:约翰·萨克维尔,多赛特郡公爵三世”中,作者详细地记载了约翰·萨克维尔的事迹和悬挂在诺尔宫室里的多幅绘画。谈到这位公爵所拥有的18世纪不可或缺的“附属品”时,作者所列举的,除了“钻石、围巾别针、意大利情妇”外,就是“他的中国僮仆”。当公爵命人为他的意大利情妇作画时,画家在起草时把那个中国男孩也画进背景中去。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想像,当时这位情妇多半是由那个“中国小男孩”侍奉,为她拿扇、手套和阳伞。(注:Sackville-West,1949,pp.176-177,189,191.)由于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自己就出身于萨克维尔家族,对于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和这个小男子一些具体情况也很为熟悉。她说:
当时,拥有一个中国僮仆,比拥有一个黑人僮仆更显新颖,毕竟,人人都有一个黑人僮仆。德文郡的公爵夫人写信给她的母亲说:“亲爱的妈妈,乔治·汉格给我送来一个黑童,11岁大,人很老实。不过,公爵不喜欢我有一个黑童,我也不能忍受这可怜的家伙遭颐指气使。如果你喜欢用他来取代迈克尔的话,我可以把他送给你。他会是一个很廉价的仆人,你可以把他转化为教徒,让他变成一个好孩子。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据说,罗金厄姆夫人想要一个。”
明显地,“中国小男孩”在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中,和非洲儿童一样,是一件充满异国风情的玩意儿。Hwang-a-Tung大抵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进入萨克维尔家的。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接着上面的话说:
自安妮·克利福德夫人的年代,诺尔宫室就有一个黑人僮仆了。不论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人人只管叫他约翰·摩洛哥。有一次,黑人僮仆间打起架来,约翰。摩洛哥被管家杀了。从此,他便被一个中国人取代。这个我已经提过的中国男孩,真名是Hwang-a-Tung,但英国仆人为求方便,称呼他为Warnoton,就好像他们(把意大利舞蹈家Giannetta Baccelli)称呼为Baccelli Madam Shelley一样。这个中国男孩来到诺尔的时候,幸运得很,不但得到乔舒亚爵士为他作画,公爵更花费让他在七橡文法学校读书。(注:Saekville-West,1949,pp.191-192.)
《布莱克船长的中国小男孩》的作者Geraldine Mozley还搜集了许多其他有关的资料。在一封由一位名为德莱尼太太(Mrs Delany)在1775年6月11日寄给友人的信中,有这样的描述:
上周五我家来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客人:Whang at Tong先生;他是这样写自己的名字的——你知道中国人写字是由上至下的。他是由一个叫布莱克的船长带来的,布莱克船长对他庇护有加,还授予他所需的知识。他是一个少年。我相信我在较早前已经向你描述过他和他的衣着。
Mozley据其他资料,得悉这位德莱尼太太当时还抄写了这名中国少年的中文名字。他写道:
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国立肖像画廊的首任馆长乔治·沙尔夫爵士(Sir George Scharf)在1878年把德莱尼太大这些字迹送交大英博物馆的伯奇博士(Dr S.Birch)看,后者报告说德莱尼太太天真地把那几个中国字倒过来写了。无论如何,伯奇博士相信这几个字是Hwang(意思是“黄色”)e tung,并说:“我自己则会念成‘Hwang ya Tung’”。(注:Mozley,1936,p.2.)
到底这个中国少年是什么模样的呢?他在贵族之家当僮仆虽然身份卑微,但这样的角色却使他有机会成为英国当时最著名的肖像画家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模特。据Mozely说:
公爵还让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为这个小男孩作画,这幅著名的“中国男孩”绘画,走萨克维尔家族在诺尔宫室的珍藏之一。画上的这个男孩,显得庄重高贵,却又满怀心事,他的思绪仿佛已从诺尔这片可爱之地,神游到他在远东的家乡。他手持一扇,交腿坐在一张竹椅上,他那双红色的鞋子方形的鞋尖,与他深红色和蓝色交错的袍子相映成趣。这个男孩和他那顶圆锥形的帽子,在盖恩斯巴勒(Gainsborough)为Giannetta Baccelli(即上文提及的“意大利情妇”——引者)所作的全身肖像画的铅笔草稿上再次出现。Giannetta Baccelli是一名舞蹈家,在英国停留时得到公爵的庇荫。该画稿藏在诺尔,最终完成的绘画(男孩并没有在该作品上出现)则为斯温顿子爵夫人(Viscountess Swinton)拥有。在诺尔,主仆二人的画像共处一屋:盖恩斯巴勒绘画的公爵肖像,细腻精致,挂在舞厅里;男孩Hwang-a-Tung的肖像,则挂在雷诺兹厅内。
乔舒亚·雷诺兹爵士(1723-1792)并非等闲之辈,他是18世纪蜚声欧洲的肖像画家,也是英国皇家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兼首任主席;欧洲各国的皇室和贵族成员、社会名流包括上述的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爵士和许多其他皇家学会会员的肖像画,都出自他的手笔。(注:有关Reynolds 之生平,参见Nicholas Penny,"An Ambitious Man:The career and the achievement of Sir Joshua Reynolds",Nicholas Penny (ed.),Reynolds,Royal Academy of Arts,London,1986,pp.17-42;有关其为皇家学会成员作画的事迹,见 Rüdiger Joppien,"Sir Joseph Banks and the World of Art in Great Britain",in R.E.R.Banks,B.Elliott,J.G.Hawkes,D.King-Hele,G.Ll.Lucas (eds.),Sir Joseph Banks:A Global Perspective,Kew,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1994,p.87.)正由于雷诺兹爵士声名显赫,200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乔舒亚·雷诺兹爵士作品全录》两巨册,我们才有机会一睹这位中国小男孩的庐山真貌,感受到上引Mozley的那段文字描述是何等生动贴切。(注:David Mannings,Sir Joshua Reynolds:A Complete Catalogue of His Paintings:Tex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p.461,cat.no.1828,1829,1829a; Plates,fig.1198,1199.有关fig.1198的肖像画的价钱,据目录编者考,一说是70畿尼,一说是50畿尼。畿尼(guinea)即英国在1663至1813年间发行的金币,自1717年起,1畿尼的价值固定为21先令。)据该目录载,雷诺兹爵士为这位Wang-y-Tong至少画了三幅肖像画,其中两幅载入图录的,属私人所有;另一幅据称只显示Wang-y-Tong的头部和肩部的作品,曾在1926年一次拍卖会上拍卖过,在1935年由《布莱克船长的中国小男孩》的作者Geraldine Mozley购入(这可能就是Mozley撰写该文的原因),目前下落不明。
Mozley据1899年出版的《雷诺兹爵士作品史》,知道这幅画曾经被标签为“Wang-y-Tong或Tanchequa”。到底“Wang-y-Tong”和“Tanchequa”是否同一人呢?如果并非同一人,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会被联系在一起呢?二人是否有关系呢?Mozley根据《雷诺兹爵士作品史》及其他资料,作了进一步的考证。据该书,这幅肖像画的详情是:
Wang-y-Tong或Tanchequa。半身像,画在画布上。31.5×25英寸。一个在院方支持下,被选为皇家学院院士的中国人。脸露出四分之三,朝右,头戴中国帽。绘于1770年……。据汤姆·泰勒提供的皇家学院院士名单记载的相关名字是Tan chet qua。
上述这条资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画中人拥有“皇家艺术学院院士”的身份的这个说法。在英国,拥有这一身份是艺术家最高的荣誉之一,一个中国人能够取得这种身份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由于皇家学会和皇家艺术学院彼此地位相当,成员互有交往,我们可以不妨追问,假设这个Tanchetqua和皇家艺术学院有什么关系,他会否就是本文第二节的主角,即拜访过皇家学会的“Quang at Tong”呢?又是否等于本文第一节的主角,即与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爵士有交往的Whang Tong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最后才考究。以下我们先跟随Mozley的思路,先了解一下这位Tanchequa的事迹以及他与“中国小男孩"Wang-y-Tong可能有的关系。
“Tanchequa"、“Tan Chet-qua"或“Chitqua”:一个来自广州的陶塑工匠
Mozley的基本立场是,Tanchequa和Wang-y-Tong并非同一人。根据其他资料,Mozely知道这位Tanchequa又名Tan Chet-qua、“Chitqua先生”或“Checqua”(为简明起见,以下除引文或特别说明外,笔者统一按皇家艺术学院18世纪的文献称之为“Chitqua”),是一位到过英国的广州陶塑工匠,其事迹在1771年5月号的《君子杂志》上有以下的记载:
这位先生在1769年8月初搭乘由詹姆森船长驾驶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哈里登号抵达英格兰。他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离境(中国政府有关其国民出境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前往巴达维亚。结果他没有去巴达维亚,却来了大不列颠。他对英国人的好奇和崇敬,促使他造访这个岛屿。他是一个中年人,中等身材,脸和手呈铜色,按照他本国的衣着习惯,他穿的是幽雅的丝质袍子,讲的是混合方言,(注:这里用的是“lingua franca”一词,原意是通用于地中海的某些港口、集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希腊、阿拉伯、土耳其等多国语言的混合语,亦指不同民族之间交往或进行交易时用的混合语。)夹杂着支离破碎的英语。他敏锐机智,观察入微。他尤其擅于运用他本土的方法,利用中国某种泥土制造小型的塑像,许多都栩栩如生。他凭着记忆,把人物的神韵捕捉下来。(注:Gentleman's Magazine,May l771,vol.xli.,p.238.该杂志以英国及欧洲的文人学士和社会名流为对象。)
Chitqua大抵就是18世纪在广州口岸为欧洲人服务的被称为什么什么“呱”(qua)的艺匠。关于当时广州制作外销画和外销瓷的盛况,已有不少著述,在此不赘。(注:西文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多不胜数,较为经典的例子是Carl Crossman,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Suffolk,Antique Collectors Club,1991).)自16世纪以来,来自中国的瓷器由于品质远较欧洲瓷器精良,让欧人趋之若鹜。Chitqua抵达英国的时候,欧洲包括英国的瓷器制作技术刚刚取得突破,据Mozley查考,Chitqua造访英国,也引起上文提到过的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瓷器制造商乔舒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的重视。1769年11月,乔舒亚·韦奇伍德接到他的合伙人发自伦敦的来信说:
我们天天都在找一些当地人或工匠的巧手妙作,以提高我们的制成品的品味,务求精益求精。我没有时间说我们看见什么,但有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是我不能不提的,我指的是最近从广州来的一个塑像工匠。他就是制造那些运来英国的中国官员塑像的艺术家之一。你也许还记得,你在沃利先生(Mr Walley)的商店见过一对这样的塑像。
他打算在这里逗留数年。他穿着中国的服饰。他制作肖像(用粘土制作的小型塑像,他会上色),技巧敏捷,迅间即维肖维妙。我曾拜访过他三次,并和他作了不少对话,因为他懂一点英语,而且是一个心地善良、理智十足的男子。他脾气温和、举止文雅。他的衣服主要是用绸缎做的,我见过他穿着深红和黑色的衣服。扇上的印度人像栩栩如生。他皮肤黝黑,睫毛整天在闪动。他手臂苗条如纤弱的妇人,手指细长,四肢柔软。他的长发曾经修剪过,背后悬着一条长长的辫子。他曾经拜见过皇帝和皇后,他们对他感到相当满意。他将会为皇家步兵团造像,报酬是每件小塑像10畿尼,可说是微不足道。(注:引文见William T.Whitley,Artists and their Friends in England 1700-1799,London & Boston,The Medici Society,1928,Vol.I,pp.269-270.此份材料承蒙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提供。)
似乎,这位Chitqua不但懂得讲英语,更能够用英语写作,并且曾经给牛津三位女士写过一封信;当时,这三位女士的朋友正要为他向东印度公司找一个船位,让他回国。二十世纪初一位研究者引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说其英文书法“清楚、字迹清晰,但表达得离奇有趣”。笔者暂时无法看到这封信的原件,从以下引文看来,Chitqua书写的就是当时广州口岸的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用的所谓“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
The two Wife-Women and,the Single-woman Chin Chin Chitqua the China gentleman - and what time they quiere flirt those nice things truly never can forget for him.Some time he make voyage to Oxford,Christchurch will then open his gates and make Chitqua so welcome he no more tinkee go Canton again.There he find much bisn as he so well savee Art of Mod elling Heads,thing much wanted among Mandarinmen of that place.Once more tankee fine present,Adios.(注:Whitley,1928,p.270.作者没有注明出处。这封信的大意可能是:Chitqua致信给两位太太、一位小姐,她们曾经送他很好的礼物,让他永志难忘。他如果有机会造访牛津,那里的基督教堂将打开大门迎接他,教他再不愿意返回广州。因为他塑像技巧精良,深受当地的官员喜爱,生意很好。再次感谢她们的礼物。再见!)
Chitqua抵达伦敦后,似乎在当地的艺术界刮起一阵小小的旋风。在皇家艺术学院于1770年举办的一次展览中,他的一件作品也参展,并补记在该展览目录上,标明“Mr Chitqua,Arundel Street,a Portrait of a gentleman,a model”(Chitqua先生,阿伦德尔街,一尊绅士塑像,一个模型)。(注:在皇家艺术学院为该次展览印行的目录中,Chitqua这件展品是记录在“补遗”一栏,并且是手写的,估计是临时加上的。见The Exhibition of the Royal Academy,MDCCLXX,The Second,Printed by W.Griffin,Printer to the Royal Academy,p.22,item 245.此份材料承蒙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提供。)同年4月23日,皇家艺术学院举行晚宴,庆祝翌日开幕的周年展览,宴请的客人非富则贵,“Chitqua先生”居然也是座上客。(注:Whitley,1928,p.269.)就在这同一日,上述的英国著名瓷器制造商乔舒亚·韦奇伍德致函他的合伙人,请他转告Checkaw,他需要稍后才有可能与之会面。1771年2月16日,韦奇伍德在他伦敦的办事处的记录上,记下他向Checqua支付了10畿尼一事,Mozley估计,韦奇伍德可能曾经请Chitqua造了一个塑像。Mozley更进一步推敲,由于Chitqua来自广州,布莱克船长又素来爱好中国陶瓷,Chitqua一定认识布莱克。(注:Mozley,1936,p.4.)
1771年春,Chitqua拜访皇家艺术学院,不但得到礼貌的款待,并且被来自德国的画家约翰·佐梵尼(John Zoffany,1735-1810)画进一幅名为《皇家学院院士群像》(“The Portraits of the Academicians of the Royal Society”,又名“The Life School in the RoyalAcademy”)的作品中,此画后来被英皇乔治三世购入。这幅绘有多名皇家艺术学院艺术家的肖像的绘画,似乎并非某次皇家艺术学院艺术家济济一堂的场景写照,而是佐梵尼凭他的艺术想象力把他见过又想到的人物逐一加入画中的创作。在这幅画中,Chitqua“成熟的、具有东方味道的面容,从后排左侧的英国‘同行’中露出”,(注:Mozley,1936,p.4.)“在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和杰里迈亚·迈耶(Jeremiah Meyer)二人的肩膀上隐约出现”。(注:Whitley,1928,p.271.Benjamin West(1738-1820),美国著名肖像及历史画画家,后在伦敦定居,1792年担任皇家艺术学院主席。Jeremiah Meyer(1735-1789),英国画家。又参见Lady Victoria Manners and Dr.G.C.Williamson,John Zoffany,R.A.His Life and Works,1735-1810,London,John Lane,The Bodley Head,1920,p.28-33.此份材料亦蒙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提供。)该画为英国皇室温莎堡藏品,从已出版的图册所见,画里的Chitqua头戴清代式样的帽子,模样和姿势基本上和以上的文字描述相符。(注:The Royal Collection Paintings from Windsor Castle,National Museum of Wales,Cardiff,in association with Lund Humphries (Introduction by Christopher Lloyd,Catalogue by Mark Evans),London,1990,p.132.)Mozley据此认为,上述《雷诺兹爵士作品史》的作者指Chitqua被选为皇家艺术学院院士的说法,可能是由于这幅画的误导所致。
Mozley推断Chitqua与个中国小男孩Whang-y-Tong并非同一人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他自己购入的那幅名为“Wang-y-Tong或Tanchequa”的肖像画绘于1770年,就上述有关Chitqua的资料看来,Chitqua在1769年抵达英国时,已经是中年人或至少是成年人了,而Whang-y-Tong在1776年被雷诺兹爵士入画时,则还是少年模样。Mozley推测,如果Chitqua和Whang-y-Tong有什么亲属关系甚至份属父子的话,那么Chitqua就是把他这个儿子(或侄儿或表亲)留在英国多年了。虽然Mozley认为Chitqua和Whang-y-Tong并非同一人,但他在脚注里引用了乔舒亚·韦奇伍德的摘记,摘引子以下两段字句:“来自一个中国人的资料,在布莱克先生伦敦的家(1775年),有关中国人制作他们的陶瓷的方法”,“Whang at Tong先生说南京的青花瓷一般是先上色后入窑烧制的,故瓷器上的蓝色永不脱落;但红色、金色和其他颜色则会脱落,因为这些颜色是在烧制后才上,然后再烧制或烘焙的。”(注:Mozley,1936,p.4.)到底这个具有陶瓷知识的Whang at Tong是否Chitqua之误呢?还是Whang at Tong本人对陶瓷也有认识呢?Mozley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说明,以笔者目前所能找到的材料亦无从判断。
陶塑匠Chitqua后来的经历颇为曲折。他与佐梵尼会面后,原打算坐上东印度公司的格兰维尔号(Grenville)回国的。岂料,当他穿上一身中国服装正要上船的时候,船上的水手认为他会带来不祥,要把他赶走,船长为免生事,乃命舵手陪他乘马车回伦敦。Chitqua因为惊慌过度,已经记不起他原来的住址,他们的马车旋即被一群暴众包围,陪同他的舵手亦被指诱拐外国人(指Chitqua),幸好这时候有一个绅士经过,认得Chitqua,把他带回他在阿伦德尔街的住处。据说,他后来在上另一艘船回国之前,已经“聪明地换上欧洲的服装”。(注:Whidey,1928,pp.271-272;Arundel Street位于伦敦西区,比邻皇家艺术学院旧址。)
Chitqua的故事,至此还没有结束。他的名字(此次以“Tan Chet-qua”的名字出现),随即又和皇家艺术学院另一个创办人威廉·钱伯斯爵士(Sir William Chambers,1722/23-1796)的名字挂上钩。威廉·钱伯斯爵士是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建筑家之一,是当时英国建筑工程部的总监督,英皇乔治三世在建筑事务方面的“密友”。18世纪英国多项大型工程,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英国建筑,都是由他设计的。1748至1749年间,他在瑞典东印度公司担任第三商业事务负责人,在广州停留,并在此时认真学习中国的建筑和园林知识。他在1757年出版的《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器及用具设计》一书中关于中国庙宇和楼房的描述,据说就是以他在广州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一些庙宇平面图,应该就是按照广州河南的海幢寺绘画的。(注:见William Chambers,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an Utensils,London,1757,reprinted by Greg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imited in 1969.)不过,也有研究者质疑他这本书的绘图是否真正根据他在中国的实地观察绘制,因为他在1756年还写信给他的兄弟询问在那里可以找到中国房子的绘图。(注:John Harris,"Introductionn",John Harris and Michael Snodin(eds.),Sir William Chambers:Architect to George III,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4.)无论如何,这样的经历使他后来成为英国的中国建筑和园林设计的权威,在欧洲刮起“中国风”(Chinoiserie)的热潮时,他有关中国艺术的知识,不管是否正确,都教英国和欧洲人趋之若鹜。钱伯斯爵士后来成为皇家植物园(又称凯园,Royal Botanic Gardens,Kew)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在1760至63年间,为该植物园设计了一个中国式的湖心八角亭和十层高的宝塔。(注: Ray Desmond,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The Harvill Press with 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Kew,1995,pp.47-52.)这个历经修葺迄今尚存的宝塔,是为乔治三世的母亲而建的,被后人认为是“洛可可式发明的产儿,是九胡子大人(时人对钱伯斯的戏称)从Tan Chet-qua的中国编造出来的事物。”(注:John Harris,"Sir William Chambers and Kew Gardens",John Harris and Michael Snodin (eds.),Sir William Chambers:Architect to George III,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65.)
Tan Chet-qua的名字之所以会和钱伯斯爵士联系上,是因为钱伯斯在1772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东方园林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的著作,在1773年再版时,附了一篇名为《广州府Tan Chet-qua的解释性论说》的长文(“An Explanatory Discourse by Tan Chet-qua,ofQuang-Chew-Fu,Gent.”),以加强他在中国园林方面的知识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在这篇《论说》里,钱伯斯以Tan Chef-qua为第一身作论说、自己加以注解的形式,向欧洲读者推广中国园林的知识。在导言部分,他是这样介绍Tan Chet-qua的:
全世界都认识Chet-qua。全世界都知道他在二十八年四月出生于广州府,知道他是一个天生的塑像家,知道他有三个妻子,其中两个他特别钟爱,第三个则没有那么爱惜,因为她是个泼妇,而且有一双大脚。他穿着得体,经常是厚身的绸缎;套着九根胡子[原文是“wore nine whiskers”],四根长指甲,脚踏丝靴,下裳是棉布裤子,还戴有官员佩戴的各种饰物,好比这里的纨绔子弟。他不但是广州府的万事通,更通晓江宁府和顺天府。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他算是一表人才,谈吐优雅;他学问渊博;于一个粗野的人来说,他算是个圆通的君子。他闲来吟诗作对,辞藻艳丽。他懂得用满文和汉文背诵诗词,还会用许多种语言唱吟情歌。他会跳最近在澳门流行的fandango舞,会庄严地演奏风笛,更作出精彩的评论。他在马尔先生(Mr.Mart)在河岸上的家下榻时,经常会用笛子重复演奏这些乐章,只要他们高兴,他就会演奏。他喜欢吸烟,只要烟草质量够好。在这些场合中,他经常都很快乐和很容易沟通。
他最爱谈论的话题包括绘画、音乐、建筑和园林。对园林他尤其情有独钟,经常谈到疲倦方休,而他的听众也昏昏欲睡。因为他的声音对听者而言好像鸦片一样,他说话像细水长流,他讨论的课题尽管很好,总的来说却不算特别有趣。
有一天,他详细讲述东方园林的情况,特别是他自己的国家的园林,那是他极为偏爱的。在结论部分,他把中国园林比作一顿摆满丰富的食物、色香味俱全的盛宴,而说我们的花园就像斯巴达的杂菜肉汤一样,除了适合斯巴达人的口味外,人人都觉得倒胃。……最后,他极力推荐中国(园林)的品味,认为没有别的园林能与之相比。
他这番话内容奇特,见解新颖,我们都被吸引住了。不过,由于他的见解和英国(园林)的一般主张和习惯大相径庭,他给我们推荐的(园林)设计对于我们来说,又宛如空中楼阁,难以落实。我们不论对他说话的内容或他本人,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判。
我们严厉的批判,最初教可怜的Chet-qua惊惶失措,他看来有点困惑,并且沉默不语。未几,他重拾他一向幽默的作风,略整仪容,起来向观众鞠躬,敲敲他的九胡子,开始以下这番论说。(注:"Introduction",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By Sir William Chambers,The Second Edition,with Additions,to which is annexed,An Explanatory Discourse,by Tan Chet-qua,of Quang-chew-fu,Cent.,London,Griffin,Printer to the Royal Academy,1773,reprinted by the Augustan Reprint Society,Publica-tion Number 191,1978.)
紧接着这篇导言的,就是Tan Chet-qua长达数十页的“论说”正文。“论说”一开始便引用了据说是Tan Chet-qua十分喜欢吟诵的四句出自乾隆皇帝的诗句,钱伯斯以注解的形式,用拉丁拼音的办法收录了这首五言诗的全文,并附以英文翻译,说明是乾隆皇帝于十三年九月十二日撰写的赏花品茶之作。笔者曾查阅《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收入的乾隆十三年的作品,一时未能找出读音类似的五言诗,无法考证这首诗是否真有其事。笔者亦明白,要判断这篇“论说”的真伪——是否出自Tan Chet-qua之口——并不是仅仅查证乾隆皇帝是否曾经写过这样的一首诗便足以说明的。要读懂或看穿这份18世纪的文献,需要对当时的英国艺术和文化甚至政治有很深刻的理解,这是笔者目前不能企及的。
根据专门研究钱伯斯的John Harris分析,钱伯斯当时出版这部书,目的是与有幸参与设计皇家植物园的英国著名风景园林(landscape gardening)学家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1716-1783)分庭抗礼。John Harris说,虽然Tan Chet-qua在1770年的确和钱伯斯在牛津见过面,但他相信,该篇“论说”是钱伯斯为了应付人们对他的中国园林知识的疑问而借用Tan Chet-qua的名字杜撰的。在私人通信里,钱伯斯承认他在《东方园林论》提到的树木和植物并没有在中国文献上出现过,但在公开的场合里,他还是以中国园林专家自居。Harris认为,钱伯斯在1773年出版这篇“论说”,是因为他看准了Tan Chet-qua年前离开伦敦时被暴众骚扰,一时变得街知巷闻。“Tan Chet-qua”这个名字大大提高了他在中国园林知识方面的权威,使他再版的《东方园林论》远较第一版轰动。(注:John Harris,"Introduction",William Chambers,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1772,reprinted by Greg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imited,1972.)
我们不必介入这场真伪与否的论争,在笔者看来,种种来源不同的材料均显示,的确存在着Chitqua这个中国人在1769至1772年间到过伦敦,并引起一阵热潮的事实。我们可以肯定的是,Chitqua即使不一定曾经或有能力与上文提及的人物作过深入的交流,但他在英国两至三年的经历,他的衣着、言谈和举止,多少让没有机会亲自到中国的英国人有一个较为直接的途径了解中国。钱伯斯上述有关Chitqua的介绍,实际上是一幅结合观察和想像的异国风情画。同样我们也可以想像,Chitqua回国后,也会成为没机会到外国的中国人了解英国的一个最佳征询对象——不管他对英国的了解是如何的片面和扭曲。
还有多少“Whang Tong”?
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Chitqua(Tanchequa或Tan Chet-qua)和小男孩Wang-y-Tong(或Hwang-a-Tung)并非同一人,而Chitqua和本文最初论述的Whang Tong和Quang at Tong也似乎并非同一人。那么,Whang Tong、Quang at Tong和Wang-y-Tong或类似的名字,又到底是否同属一人呢?我们也许可以综合以上几份不同来源的材料,作些推测:
一,Whang Tong在1796年从广州发信与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如果他就是1775年拜访皇家学会并留下芳名的Quang at Tong,那么,他在英国最多停留了21年。
二,布莱克船长的英年早逝让我们知道,在诺尔作僮仆的中国小孩Wang-y-Tong(Hwang-a-Tung)抵达英国的时间应该是在1766至1773年间。假设他在1766年左右到达英国,则至1775年时,他至少已十多二十岁(这从那幅作于1776年的肖像画也可以得到证明),并且接受了一定的英语教育,即使他身为僮仆,但在较有地位的英国人陪伴下到访皇家学会,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三,在笔者翻阅过的皇家学会日志所载的1775年1月12日接见访客的名单中,当日获皇家学会主席约翰·普林格尔爵士接见客人,除了Quang at Tong外,还有一个叫“布莱克先生”的。布莱克船长死于1773年,这位布莱克先生很可能是他的亲属,当时正陪同Quang at Tong拜访皇家学会。
四,假设Whang Tong、Quang at Tong、Wang-y-Tong(Hwang-a-Tung)是同一个人,我们或许可以这样重构他的生平:
(1)1766-1773年间:他是一个小孩,被一个在广州工作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带到英国当僮仆,并接受英语教育;
(2)1775年:他长大成人,有机会拜访英国皇家学会,认识了誉满欧洲科学界的班克斯爵士;
(3)后来,他返回中国,由于他通晓英语的缘故,得以在广州与一个行商结交,或为他服务。期间他接过班克斯爵士的来信,并在1796年回信。以他对班克斯和英国的认识,他知道送什么礼品可以投其所好,有助他的主人与英国的上流社会和商人维持良好的关系。这时,他已到中年。
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Whang Tong、Quang at Tong和Wang-y-Tong(Hwang-a-Tung)并非同一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值得玩味的是,这一个或几个中国人,本来就出身寒微,因此可以不顾风险地远赴异邦,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相比,他们难得地接受了英语教育,并得以接触英国上流社会,但他们并没有像一个世纪后的容闳一样,回国后遇上适当的时机,声名卓著,青史留名,他们充其量只能当行商的助手。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在史册中完整地出现,只能被称呼为“亚”什么或什么“呱”。其实,那些财富多得使西方人也瞠目结舌的行商,尚且难得在中国史籍中留下雪泥鸿爪,又何况这些“小人物”呢?(注:十三行行商资料难觅,向来是令史家大感头痛的难题。张仲礼比照几种材料,说明出身行商的官员原来的身份如何在中国史料里被掩盖。张据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引蒋廷黻考,得悉太平天国初期出任苏松太道的吴建彰原为广东十三行叫作爽官(也作三官)的行商;从马士《在太平天国的日子里》所见,吴在上海任职时西方人也以他经商时的名字来称呼他。不过,上海的地方志只载录了他做官时的名字,说他是广东潮州人,是位监生,并无只字提及他曾当过商人。见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36-337页。)不过,在欧洲对中国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年代,即使像班克斯爵士这样消息灵通的人士,也只能靠不断地写信给在广州工作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人员,来满足他对中国事物的求知欲。那么,像Chitqua在皇家艺术学院的饭桌上大谈中国艺术,Whang Tong给班克斯寄赠中国历史书籍、与Chune Qua分享他在英国的耳闻目睹,“中国小男孩”向充满好奇的公爵主人描述他对中国的回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类似的人物的零碎的踪迹,交织起来,不会比一向为史家所重视的伟人事迹逊色。更何况,这几个小人物会见过并且直接对话的英国人,都是当时英国甚至是欧洲最显赫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如果这些“小人小事”不能让我们写“大历史”,至少有助于丰富我们对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想像,启发我们循另一些途径去捡荒拾遗。
附记:笔者在查询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研究员Neil Chambers先生、皇家学会助理档案员Clara Anderson女士、皇家艺术学院图书馆、多伦多大学宋怡明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周立基博士的帮助;本文初稿得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江滢河博士指教及提供参考文献,谨在此一并致谢。
标签:欧洲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