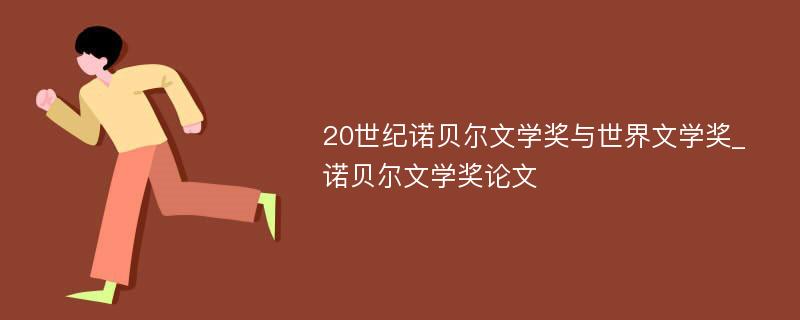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与20世纪世界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文学奖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已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该奖作为世界性的文学奖项,也已经为中国文坛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所关注,并在近年来形成了见诸报端刊中的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在20世纪内,长长的97人的获奖名单中还没有中国籍作家的身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这一奖项的历史地位、文学价值的了解,也不妨碍我们以客观的目光评析这一奖项对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影响。
诺贝尔文学奖鸟瞰
所谓“鸟瞰”意谓以全方位、纯客观的目光去了解100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总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它的历程和演变,对于加深我们的认识和判断是有益的。
先让我们来罗列几组数据:
(一)按获奖作家的国籍统计(以获奖作家数目多少的顺序排列):
①法国14②美国11③英国8④瑞典7德国7⑤意大利6⑥西班牙5⑦爱尔兰4⑧苏联3挪威3波兰3⑨瑞士2丹麦2希腊2智利2日本2⑩芬兰1冰岛1比利时1南斯拉夫1以色列1印度1澳大利亚1危地马拉1哥伦比亚1捷克1尼日利亚1埃及1墨西哥1南非1圣卢西亚1葡萄牙1
(二)按每20年为一时段,五大洲获奖作家人数统计,其中括弧内的为女性获奖作家人数:
1901~1920:欧洲19(1) 美洲0 亚洲1 非洲0 大洋洲0
1921~1939:欧洲15(2) 美洲3(1) 亚洲0 非洲0 大洋洲0
1944~1960:欧洲14 美洲3(1) 亚洲0 非洲0 大洋洲0
1961~1980:欧洲13(1) 美洲6 亚洲2 非洲0 大洋洲1
1981~2000:欧洲11(1) 美洲5(1) 亚洲1 非洲3(1) 大洋洲0
合计:欧洲72(5) 美洲17(3) 亚洲4 非洲3(1) 大洋洲1
(三)按获奖作品体裁统计:
小说54诗歌28戏剧11非文学类4
数字统计是枯燥的,但数字统计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说明问题,从上述统计中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获奖作家的地域分布是极不平衡的,欧洲作家占了总数97名中的72名,为74.22%,几乎占了四分之三,且除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是个例外,其余71名作家都是正宗的欧洲人;尤其是在20世纪前20年,泰戈尔是惟一的非欧洲获奖作家。在72名欧洲作家中,除东道国瑞典以外,英、法、德、意几个国家共有35名,如果加上美国的11名获奖作家,则西方五大国占了总数97名中的46名,比例达到47.42%。
第二,再从获奖作家的个人声望与创作成就而论,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中有不少伟大的作家都没有能够获得这一荣誉,例如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苏联的高尔基、美国的德莱塞等,他们并不是没有资格获得这个奖,而是被某些西方学者的偏见所扼杀了,中国的鲁迅、老舍、沈从文等恐怕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相反,有一些并没有出色成就的作家,却由于某些非文学原因而获奖,因而也使人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是否都授予了“曾经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产生怀疑。
第三,文学奖还授给了几位从事非文学类创作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或政治家,因为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解释,只要能写出“有理想倾向的作品”,即使是非文学类的著作也可以列入获奖范围。这一观点的产生显然是出于一种政治上、哲学观念上的考虑。由于早在1902年就开了这个先例,因而历年来至少有4位属于非文学类的作家获奖,最明显的莫过于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了。他之所以在1953年获奖,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记述,同时也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倒不如说是因为他那鲜明的政治立场。
然而,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获奖作家的地域已逐步走出欧洲而面向世界,这一变化至少在60年代以后有了明显表现。假如说在前60年内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关注的还是欧洲作家和与欧洲文学有着密切血缘关系的美国作家;那么在此后的40年内,他们的视野开始扩展到了其他几个大洲的一些文学大国以及在文学创作领域中有杰出建树的作家,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获奖)、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获奖)、智利的聂鲁达(1971年获奖)、澳大利亚的怀特(1973年获奖)是典型的例子;80年代马尔克斯、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和沃尔科特这些拉丁美洲、非洲作家的获奖更体现了这种倾向。
第二,获奖作家的创作风格也逐步从单一的西方正统文学走向各种流派。有人认为1969年荒诞派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获奖标志着现代主义作品正式步入了西方文学殿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如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所指出的,贝克特的戏剧作品《等待戈多》和《啊,美好的时光》都可视为对《圣经》的注释,是比较富有人性的剧本。此后获奖的马尔克斯、西蒙、索因卡分别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和非洲黑人戏剧的流派代表,表明评奖委员会已经认识到这些作家对于整个世界文学的贡献与影响。这一点在90年代获奖作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托妮·莫里森的美国黑人女性小说,大江健三郎的日本心理小说、达里奥·福的意大利社会喜剧、格拉斯的德国象征主义荒诞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推动整个世界文学多元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对于女性作家和小语种的作家也有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90年代有三位女作家(戈迪默、莫里森、希姆博尔斯卡)获奖,占了全部获奖女作家的三分之一,表明女性作家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而埃及的马哈福兹和葡萄牙的萨拉马戈的获奖,也表明了对于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小语种文学创作的肯定。
第四,对小说家地位的充分肯定可以从获奖作家中小说家几乎占了五分之三予以确认。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文学创作的最重要文体,代表了文学的最有影响也最有艺术魅力的创作体裁,它不仅在文学中起到旗帜作用,还对戏剧、电影、电视等其他艺术载体起到极大的影响。许多获奖小说家的重要作品通过改编,在舞台上,银幕上、屏幕上供广大受众欣赏,而它的基础就是优秀的小说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
关于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当初在设立诺贝尔文学奖之际,遵照诺贝尔的遗嘱,它将授予创作出有理想倾向的、有文采和世界性影响的作品的、仍然健在的作家。也许是缺乏经验,或是对这一标准的不同理解,在第一年宣布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获奖时就引起过强烈的反对之音。在今天后辈评论家看来,假如19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列夫·托尔斯泰或是托马斯·哈代或是易卜生,也许这个开头会圆满得多。将1901至1920年获奖的20位作家做一分析,我们首先发现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忠实的继承者,部分作家(主要是诗人)还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色彩,也许比利时象征主义戏剧家梅特林克是惟一的例外。其次,作家几乎清一色出身于欧洲传统文学大国,泰戈尔也许是惟一的例外,然而众所周知,他出身于多年受到大英帝国统治的印度。这说明,当时评奖委员会还是从19世纪固有的文学观念出发在欧洲文学大国内寻找符合获奖标准的作家。何谓“有理想倾向”?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标准,所以近年来有文章披露说,当年就以作品缺乏理想为由否定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获奖资格;也许这正是观念上的差异,就像两条平行线,方向一致但总不会交叉重叠。
第二,在1921至1939年内,除了授予三位美国作家之外,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依然坚持他们原有的传统观念,即获奖者应是欧洲文学大国的传统作家。假如说当时能使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或D.H.劳伦斯获奖的话,也许后人评论不至于如此愤愤不平。相比之下,获奖的某几位,譬如黛莱达、蒲宁、马丁·杜·加尔、西伦佩以至像珀尔·巴克(即赛珍珠)这样有一定争议的作家,无论是声誉影响还是作品价值,恐怕都无法与乔伊斯等人相提并论。要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现代主义已经在文坛上占据了半壁江山,但评奖者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和影响,已是五六十年代的事了。也就在此期间,苏联的高尔基、中国的鲁迅、美国的德莱塞都成了文学巨匠,可是他们仍被评委会视而不见,这中间不能不说没有国别歧视、政治立场等非文学因素作崇,因此,也成了后人非议的话柄。这证明在左翼文学轰轰烈烈的3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依然坚持了他们原有的思想立场。以上所述两点正是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不良表现。
第三,二次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至1960年,似乎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开始走向世界的一个过渡。智利的米斯特拉尔的获奖可以视为一个标志。她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奖作家,她那“富有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拉丁美洲理想的象征”,这一赞美词可以理解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理想作品”的一种新理解的确认。但这段时间出现了几个引起后人争议的现象:一是1950年授奖给英国哲学家罗素;二是授奖给英国的丘吉尔;三是1958年授奖给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罗素是贵族出身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与丘吉尔相继获奖几乎令人怀疑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应该改名为诺贝尔贵族哲学政治奖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得奖当即引起轩然大波,一是苏联当局的抗议,说颁奖给反苏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是不折不扣的冷战挑衅;二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赶紧声明“自愿谢绝”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也仍难逃劫数,在全国受到大规模的批判后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两年后死了。当然,T.S.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和加缪的获奖,的确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和地位,对于推进20世纪的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1960至1980年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逐渐向世界开放的势态。在这20年里先后有智利的聂鲁达、以色列的阿格农、日本的川端康成、澳大利亚的怀特、美国的斯坦贝克、贝娄和辛格获奖,这表明评奖者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整个世界文坛,摆脱了过去“欧洲中心论”的狭隘观念,使该奖真正成为拥有世界性的权威奖项。即使在欧洲的获奖作家中,法国的贝克特、德国的伯尔和意大利的蒙塔莱,也都属于具有世界影响的流派文学的代表人物。这20年是世界文学流派纷呈丰富多彩的时期,如前所述,贝克特的获奖是西方正统文坛对50年代“荒诞戏剧”的肯定;同样,肖洛霍夫、川端康成与贝娄、辛格的获奖也是对苏联现实主义文学、日本“新感觉派”和美国犹太小说成就的肯定。还须一提的是1964年法国作家萨特的获奖,他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绝领奖。多数评论家认为这是萨特一向持有的反抗精神的表现,也是对诺贝尔文学奖以往评奖“不能平等地代表了具有所有意识形态、来自所有国家的作家”的批评。萨特应该是惟一真心拒绝领奖的作家,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与贡献,相反对于评委们的反思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五,20世纪的最后20年的评奖结果进一步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开放性,评奖委员会更加关注的是作家的流派风格、创作成就和区域影响,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捷克的塞费尔特、埃及的马哈福兹、墨西哥的帕斯、南非的戈迪默、圣卢西亚的沃尔科特都成为该国的第一位获奖者,使诺贝尔文学奖在代表性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即使像英国的戈尔丁、美国的莫里森、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爱尔兰的希尼、德国的格拉斯,尽管出身于西方(含日本)传统文学大国,但他们的文学成就与在流派创作中的地位是世人皆知的。意大利的社会喜剧家达里奥·福以反政府的激进立场闻名,他又兼导演、演员,1997年获奖结果一揭晓也多少引起一些议论,但笔者认为这正是评委们注重作家风格和作品内涵的产物。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20年的评奖结果与20世纪末期文学的趋同与融合的现实是一致的,至少是基本一致的。这些获奖者尽管个别作家在揭晓前并不为人们普遍看好,但大多数是当之无愧的。
诺贝尔文学奖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与贡献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把20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分成下列几种类型:
Ⅰ.在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著名作家;
Ⅱ.在各国(地区)文坛上有过重大贡献或在一个时期内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
Ⅲ.由于某种原因而获奖的作家;
Ⅳ.不知什么原因或少有理由获奖的作家;
Ⅴ.勉强获奖、影响不大的作家;
Ⅵ.不属于文学家而获奖的非文学类作家。
当然,从数量上来说,上述Ⅰ、Ⅱ两类作家占了获奖作家的大部分,这正是我们要肯定诺贝尔文学奖的出发点。自从该奖设立以来,由于多年来形成的传统、严格的科学性和强烈的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也和其他各项诺贝尔奖一样,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荣誉,始终保持着它崇高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它的存在,推动了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它已成为全世界作家奋斗与努力的一个目标,能否获得该奖及获奖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文学在全世界的地位与影响。仔细想来,诺贝尔文学奖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与贡献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推进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轨迹。假如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看做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的话,那么文学奖项的评比可以视为文学创作的推动力。文学评奖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虽然狄更斯、巴尔扎克们没有获过任何奖项依然充满创作活力,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正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为数众多的文学评奖活动,极大地激励了文学家的创作热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文学列车向前行驶的润滑油。在为数众多的文学评奖中,诺贝尔文学奖是惟一为人们公认的世界级文学奖,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标志、一座高峰、一面旗帜。
第二,倡导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创作风格。文学创作是完全的个人行为,但作家在时代的影响下必然会通过一定的创作手段形成某种风格。诺贝尔文学奖对获奖者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世界文坛风格的一种引导和提倡,有时是对已经形成自己风格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的肯定,有时是对正在形成自己风格的优秀作家的褒奖,有时是对曾经在一个时期有过重大影响的作家风格的追认,而以上述前两类情况居多。现在每年九、十月都成了各国舆论关注诺贝尔奖揭晓的时刻,每当获奖作家名单公布,该作家的作品会迅速在世界各国用多种文字出版,评论家们会一窝蜂地去研究他们的作品,无数评论介绍研究文章顷刻占领报刊网络舆论,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学艺术导向。每年十月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必然出现一个阅读当年获奖作家作品的热潮,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对该作家本人的魅力研究,也必然带动人们对文学艺术魅力的再次关注,所以有人戏称每年十月是“世界文学节”。
第三,加深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历史内涵。纵观人类产生文学作品以来,20世纪肯定是最活跃最丰富最激荡人心的时代,但光是活跃丰富激荡人心是不够的,文学作品还应该有它对时代思考探索的深刻内涵。一部经过历史考验的文学经典应该是人类一个时代的深刻的记录。我们不能说每个获奖作家的代表作都具有经典性,当然更不能说这些作家的作品都经得起历史考验,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无愧于“20世纪文学经典”的称号。这些作品加上那些同样拥有经典性的未获奖作家作品构成了伟大的20世纪文学的最高峰。
我们肯定诺贝尔文学奖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是要回顾分析百年来评奖活动及其结果对整个世界文学发展的客观效果,不是对它的全方位的赞美。自然科学多有客观标准,意识形态则易受主观色彩的影响,诺贝尔和平奖如此,诺贝尔文学奖也如此。由于历史、阶级、地域、种族等等原因,一个完全由少数西方学者评定的文学奖项要完全公平、公正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确已看到评奖过程和结果自70年代以来已有较大的改进。
诺贝尔文学奖既然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最高文学奖项,人们自然期望诺贝尔文学奖能更好地代表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使世界五大洲最杰出作家都能成为获奖作家,避免重犯20世纪初期评奖过于世俗化、地域化的缺陷,以不辜负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创立文学奖的初衷。对于新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期望,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于新世纪世界文学的期望。在20世纪中,人们可以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欢呼鼓掌,但有时也不得不因文学的软弱、文学被战争与集权蹂躏时的痛苦而发出悲哀的叹息。诺贝尔文学奖也有过软弱和悲哀,但愿今后不再重演这一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