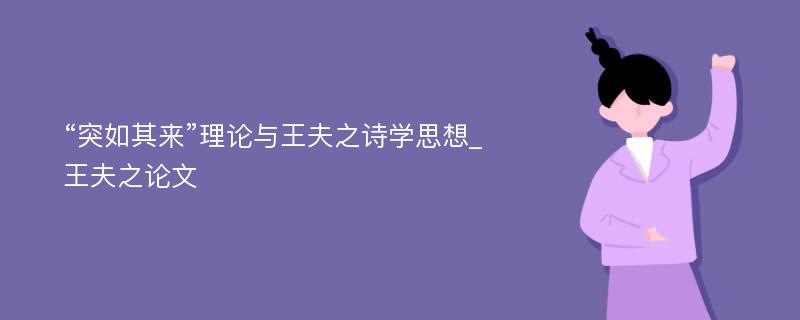
“遽情”理论与王夫之的诗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王夫之论文,遽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端于先秦思孟学派的“性情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理论命题之一,汉代“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及西晋“诗缘情”等观点,是性情论与早期诗学理论结合的结果。此后,“吟咏情性”、“诗以道性情”等诗学观点被广泛接受。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尚情”文艺思潮,虽然将“情”从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下解放出来,却又导致了明末纵欲、滥情等文艺流弊的产生。针对这种情况,明末清初的学者如黄宗羲等人,大多借助传统儒家性情论中“约情复性”、“性为情节”等观点来批评、纠正这些流弊。与众人不同,王夫之在探析性、情、欲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遽情”理论,从深层次解释了情欲泛滥的原因。
一、遗民情结与“遽情”论的提出
王夫之是坚贞的明遗民,他身历易代之痛,保节山中数十年潜心著述,思想带有明显的遗民情结。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禽之辨、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①等问题的执著探求上。王夫之五十五岁时作《礼记章句序》强调中华礼乐文明乃立国之本,把“仁”和“礼”作为人禽之别、夷夏之别的界限。但随着清朝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渐趋稳定,遗民意识随着“明遗民”逐渐离世而慢慢淡化。此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现实,开始与清廷合作。然而王夫之一直拒绝承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他进一步深化自己的思想,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十五岁时提出“遽”的概念,并以之作为人与禽狄的本质区别:“奚以知人之终为禽狄也?遽而已矣。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而别者,别之以度乎?君子舒焉,小人劬焉,禽狄驱焉;君子宁焉,小人营焉,禽狄奔焉。”②不同于朱熹等宋儒对“人欲”的全面否定,王夫之肯定“人欲”的合理性,但指出君子之欲在度内,而小人与禽狄对欲望则有过度的迫求,这就是“遽”。
按照王夫之的理论,“遽”具体表现为“弗能待”和“弗能择”两种倾向:“所恶于遽者,恶其弗能待也,尤恶其弗能择也。”③所谓“弗能待”是指强烈的目的性追求,“弗能择”是指无原则的选取。“无择”之“遽”,就是人对私欲的无原则、无限制的强烈目的性追求。王夫之认为,“遽”不仅使人的情感以及伦理道德等规范出现混乱,还渗透到学术、宗教、治国等诸多层面,最终导致人道废、纲纪乱的结果。他说:“故诸儿之禽行,遽焉耳;嬴政之并吞,遽焉耳;陈仲子之哇其母食,遽焉耳;墨翟之重趼止攻,遽焉耳;释氏之投崖断臂,遽焉耳。天下有遽食遽色而野人禽,天下有遽仁遽义而君子禽,遽道愈工,人道愈废。”④王夫之从个人道德、学术思想、社会伦理、国家教化等不同层面分析,认为大凡不符合儒家礼制规范的治国之术、修身之道、名利之举等,多是“遽”的结果。就人之性情而言,王夫之将受私欲影响的情称之为“小人之遽情”:“世无足与言情,大德而不为怨者鲜矣……先之而忿其傲,捽之而忌其凌,损之而怼其吝,小人之遽情也。”⑤他认为“情上受性,下授欲”,但过“度”的私欲会对情产生影响:“降其志以从康,降其情以从欲,均之乎降,而贞士之去淫人也无几矣。”⑥其中“从欲”之情,即“遽情”,是贞士、淫人的区别所在。
“遽情”论是王夫之以诗学理论寄托遗民情怀的需要。王夫之把对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反思融入诗学理论中,对诗歌的价值赋予更高的期望——以诗歌作为存续中华传统礼乐文明的重要途径。首先,王夫之将《诗经》视为圣人达情、君子函情的基本方式:“圣人达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⑦他认为读者通过对《诗经》的学习和诗歌创作实践,可避免因“遽情”而沦为小人、禽狄,进而实现以诗歌来“存情”、“存礼”的价值追求:“情在而礼亡,情未亡也。礼亡而情在,礼犹可存也。礼亡既久而情且亡,何禽之非人,而人之不可禽乎?”⑧倘能以诗存情、存礼,则国虽亡而国人可以不被夷狄同化,中华文化之命脉仍能得以存续,也才有可能在将来实现逐虏光兴的愿望。这与顾炎武入清后提出的“存道”主张有相通之处,只是顾炎武等人强调的是学术研究,而王夫之把诗歌阅读、创作为主的人文活动都视为存情、存礼的途径。王夫之所说的存情,指的是存华夏之情而弃夷狄之情,存君子之情而消小人之情。他以“遽情”作为分别两类情之界限,是提出“以诗存情”主张的理论前提。
王夫之在构建自己思想体系过程中提出“遽情”论,推进儒家性情理论向纵深发展。从儒家思想发展历史来看,沿着孔子“克己复礼”的理论方向,郭店楚简中的“情生于性”,《毛诗大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理论主张,均强调以德性层面的道德修养来约束人之情欲。宋代朱熹等人又持“四端皆情”的观点,将性对情的约束力提高到极致,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情的独立性与主动性。一方面,王夫之继承先儒性情论,承认德性对情的主导性、约束性作用,相应地提出了“性为情节”主张。同时,他又针对“性失其本”的情况,在借鉴明代“尚情”论成果基础上提出“情以养性”主张:“大本已失,而唯反躬自修以治其末,则由外以养内。”⑨其中“大本”,指人德性的根本;“自修”,指调治一己之情;“由外以养内”,指通过“治情”来达到完成德性修养的目的。王夫之力图通过调治人情来达到存养德性的目的。而“遽情”论解决了分辨贞情与淫情的问题,是王夫之“治情”主张的重要理论基础。
王夫之在遗民心态影响下提出“遽情”论,是对明代情论的反向观照:既延展了明代情论的内涵,又对明代情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拨。明代情论是心学在文学领域影响与渗透的结果,“情”因此成为明代中后期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范畴⑩。尤其是李贽提出“絪缊万物,只是一个情字”的主张后,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人的文学理论都把“情”作为重要的理论核心(11)。王夫之虽然批评明代心学与尚情思潮,但他仍将“情”作为构建诗学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并未脱离明代文学思想的内在理路。因此,“遽情”论除了延展“遽”的人性论内涵以外,也是王夫之反向观照明代诗学情论的结果。
结合“遽情”论的内涵和产生背景来看,王夫之的“遽情”论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和理论指向。他把“遽情”论落实到诗学批评实践中,使其诗学批评在明末清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二、“遽情”论的诗学批评实践
王夫之主张“诗道性情”,但其中的“情”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指正情、贞情。而属于“遽情”范畴的淫情、伪情,则是被王夫之指斥的对象。王夫之认为,“情”之贞、淫与否,直接影响了诗歌内容与表现过程。因此,他以“遽情”区别君子之诗与小人之诗,更以之区别风雅之音与亡国之音。
(一)王夫之从性情的角度探求诗学弊端产生的原因,认为淫诗、伪诗皆根源于作者的“遽情”。这体现在他对杜甫等所谓“淫人”、“小人”的批评上。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其所作“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等诗句历来被认为是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的体现。而王夫之所见颇异于公识,认为这些诗句是杜甫“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12)。他说:“若夫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设于醉饱之情,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13)他认为杜甫之诗追求私欲,非君子之情;同时又矫饰为文,有悖诗道,对后世影响很大:“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是何甫之遽为其魁哉?”从“遽情”论的角度看,“诗圣”杜甫被王夫之斥为“诗亡于天下”罪魁,并非是诗歌风格、审美旨趣等方面的问题(14),而是诗人情性的问题。
在王夫之看来,“遽情”不是产生于某一历史时期的个别问题,故而他从《诗经》开始梳理并批评历代诗人中的“遽情”小人。他认为《诗经·北门》中“终窭且贫”、“室人交遍谪我”等诗句,与杜甫“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等诗句本质相同,都反映出作者渴求财货的私欲。故王夫之将《北门》一诗视为后世“遽情”之诗的源头:“(杜)甫之所奉宗祧者,其《北门》乎?”(15)除杜甫之外,王夫之视孟郊为淫人、小人的代表,于著述中批评孟郊共见十五处。王氏称孟郊为人“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丧”(16),“如此其龌龊”(17),故直斥孟郊为“淫人”。他在《论采绿》中云:“淫者,非谓其志于燕媒之私也,情极于一往,泛荡而不能自戢也。”(18)“知不伤之乃以不淫者,可以言情矣……孟郊、曹邺之为淫人,谅矣。”(19)不同于朱熹等理学家否定人情欲的基础上视男女私情均为“淫情”,王夫之肯定人情欲的正当性,只是将私欲影响下无所收束之情称为“淫情”。其斥孟郊、曹邺等人为淫人正缘于此论。
除了批评淫人、淫诗,伪人、伪诗也是王夫之“遽情”论重点批评的对象。出于总结和纠正明“七子”诗学流弊,诗歌的“真”、“伪”之辨成为明清两代诗学的重要论题。如黄宗羲视“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20)为伪诗,从诗歌创作方法的角度认为:诗歌在语言上蹈袭故人,不能真实表达出诗人真性情,故而成了伪性情之诗。此观点在明清两代被广泛认同。与此不同,王夫之认为诗歌出现伪性情的弊端,是小人虚伪表现的结果,其根源仍在于“遽情”:“人即无以自贞,意封于私,欲限于小,厌然不敢自暴,犹有愧怍存焉,则奈之何长言嗟叹,以缘饰而文章之乎?”(21)王夫之从情欲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小人因内心存在私欲,心中有愧,不敢在诗中真实地表达其性情,故而“缘饰而文章之”,于诗文中表达冒充“忠孝”的伪性情,于是就有了伪人所作的伪诗。比较来看,黄宗羲等人普遍将“伪”视为诗歌创作方法造成的弊端,而王夫之将“伪诗”视为“伪人”创作的必然结果,属于诗人性情方面的问题。换言之,王夫之认为“遽情”是诗人性情真、伪之别的根本所在。
出于对明朝灭亡的深刻思考,王夫之认为伪人所作“遽情”之诗隐藏了个人真实的私情、私欲,形成社会风气后,终成教化之失:“音之所感,人心应之,下欺其上,各营其私,而不相辑睦。成乎风俗,虽有峻法,莫难禁止也。”(22)王夫之据此来解释明末亡国之音生成的缘由,流行于明末诗坛的竟陵派诗学自然难辞其咎。他在《古诗评选》卷三评《子夜春歌》云:“《子夜》、《读曲》等篇……自竟陵乘闰位以登坛,奖之使厕于风雅,乃其可读者一二篇而已。其他媟者如青楼哑谜,黠者如市井局话,蹇者如闽夷鸟语,恶者如酒肆拇声,涩陋秽恶,稍有须眉人见欲哕。而竟陵唱之,文士之无行者相与敩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竟陵灭裂风雅、登进淫靡之罪,诚为戎首……推本祸原,为之眦裂。”(23)王夫之从《子夜春歌》一诗“从景得情”的创作成就出发,引申出对竟陵派钟、谭推崇《子夜》、《读曲》等小诗的批评,结论认为:竟陵派诗学灭裂风雅,社会影响很大,以至于明末诗风词诬情伪,终成亡国之音。王夫之“推本祸原,为之眦裂”的激烈态度绝非仅就竟陵派的诗学主张、作品风格而言,而在于他把遗民的亡国之痛倾注于对“遽情”之诗的批判之中。
(二)以“遽情”论为基础,王夫之认为历代诗法出自“伪人”之手,诗法论不但违反诗歌的创作规律,而且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和社会道德的滑坡:“拂天地之位则乱,刓万物之几则贼。贼与乱,非伪人不能,然且标门庭于辞之中曰:吾能为位置也,吾能为开合也,吾能为筋脉也,吾能刮摩以净也,吾能立要领于一字而群言拱之也,吾能萦纡往来而不穷于虚也,吾能剖胸噀沫而使老妪稚子之无不喻也。呜呼!伪人逞其伪辩之才,而烦促捭合,颠倒黩乱,鄙媟之风中于民而民不知,士乃以贼,民乃以牾,盗夷乃以兴,国乃以亡,道乃以丧于永世。孰为此者?而‘不实于亶’之祸亦酷矣!韩愈、李翱、元稹、白居易、苏洵、曾巩之辞兴,而天下蔑不伪。知言者可弗距哉?”(24)在诗歌创作上,王夫之认为诗情的激发,或因于外物感召,或因于性动于中,皆是自然生发而出。在创作过程上,王夫之主张因势而为,以求情之自然流动。而皎然、韩愈、李翱、元稹、白居易、苏洵、曾巩等“伪人逞其伪辩之才”,于诗文立法在先,刻意为之,限制了情感的自然生发与流动,导致情、文关系割裂,使得诗文成了情、思虚伪表述的载体。故王夫之云:“一虚一实,一景一情之说生,而诗遂为穽,为梏,为行尸。”(25)诗文之法桎梏人情,以至于诗文“烦促捭合,颠倒黩乱”,其风行结果则是“天下蔑不伪”,终至亡国。
王夫之视皎然为诗法论的代表,其三种诗歌评选中有九处对其批评,如云:“又其下者,更有皎然《诗式》一派,下游印纸门神,待填朱绿者,亦号为诗。庄子曰:‘人莫悲于心死。’心死矣,何不可图度予雄邪?”(26)又云:“皎然,一狂髠耳!目蔽于八句之中,情穷于六义之始,于是而有开合、收纵、关锁、唤应、情景、虚实之法,名之曰:律。钳梏作者,俾如登爰书之莫逭。”(27)王夫之对皎然的批评言词激烈,也缘于将诗法论之弊害与亡国之音相联系。
(三)“遽情”导致诗歌呈现出“迫”、“促”等特征,有违风雅之道,这是王夫之诗歌风格批评的重点。在王夫之所著《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及《诗广传》、《楚辞通释》等五部著作中,直接用“迫”字评诗之弊病共见四十七处,如“其词迫而不舒”(28),“裁成不迫促,正使曲终尽三叹之致”(29),“小诗本色,不嫌迫促”(30),“气局拘迫”(31)等。王夫之以“促”字评诗之弊病共见二十九处,如“音促而不舒”(32)、“风烦韵促”(33)、“疑伤于促”(34)、“促声窭貌以为文”(35)等。王夫之又多以“不迫”、“不促”来肯定诗歌的成就,如谓“不滞不迫,才是作者”(36),“不矜不迫,乃可许为名士”(37)。又谓“一气不待回换,自不迫促”(37),“结语峻而不促”(39),“句句用韵,正以不促称圣”(40)等。王夫之甚至把诗中“迫”与“不迫”看成是雅俗之辨的分界:“雅无逾此:惟不迫,故无不雅。”(41)
遽与迫、促,均为急促之意。王夫之认为,情、欲之“迫”是诗歌音词“迫”、“促”产生的原因,故其称杜甫之诗“迨其欲之迫而哀以鸣也”(42)。其论《定之方中》云:“虑重情迫,上下相切而寻于货财……先公温厚之教亦自此而无遗矣。”(43)诗歌音词的迫、促特征又是诗人“遽情”的外在表现,故其评《采葛》诗云:“何以知情之淫也,其诸词不丰而音遽者乎?”(44)可见,王夫之以迫、促评诗,是他批评“遽情”的外在延展。
基于“由外养内”的性情论主张,王夫之认为君子之诗应舒缓自在,并力图以诗歌的“舒”气来规戒“遽情”之诗的音词迫、促,以达到治情的目的。其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伤”的原因在于:“(诗人)情挚而不滞,气舒而非有所忘,萧然行于忧哀之途而自得。自得而不失,奚淫之有哉!”(45)认为作者情挚、气舒而又萧然自得,则人之淫情自没。即其所言:“《行苇》舒,而戒君子者也。”(46)王夫之以舒缓和敛为周公治国之道的体现,其云:“澹以不忘、舒以成、柔以则者,周公之道也。昌而缓、清明而和、微至而敛者,周公之《诗》也。”(47)故诗之舒气,又可保国家舒气之和平,从而完成以诗情达于治国之理。可见,不论是迫、促诗风的批评,还是舒、静诗风的推尚,皆是王夫之“遽情”论在诗歌风格批评上的体现。
三、“遽情”论的诗学价值
王夫之诗学“遽情”论的提出,在诗学理论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既从理论上完成了对明末诗学的批评,又重新构建起独具特点的儒家诗学理论,使其诗学思想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
(一)借助“遽情”论否定了明代情论的理论基础,王夫之批判、收束情欲放纵之弊的同时,在理论上完成了对明末诗学的批评。随着阳明心学向诗学领域的影响与渗透,以及明代中后期思想界对“情”的高度认同,诗情论在明代被广泛接受。李贽等人崇情抑理,将“情”提升到高于“理”的位置,于是诗中之情与世道人情一样,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内外规范,并产生了滥情、泛情、私情等文学流弊。对于“尚情”思想在纵欲、滥情等方面的弊端,刘宗周、黄宗羲等人谋求从理欲关系角度对之加以修正,但都没有将理欲关系探讨与诗学中的性情论相融合。王夫之以情、欲之辨为出发点,从人性论角度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小人等层次。其中圣人不可为,而君子与小人之界在于“遽情”与否。在此基础之上,王夫之进一步升华了儒家礼乐教化理论:发挥礼的约束功能,从外在行为规范来严格人与禽狄的区别;发挥诗歌的教化功能,从内在“情”的角度来分判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可见,“遽情”与否,既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更是诗学思想的本质区别。于是明代各家诗论所主张的“情”,被王夫之细分为贞情与淫情。这不仅解释了明末诗学弊端一个重要根源,也为王夫之自己诗学理论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基础。
(二)在“遽情”论的基础上,王夫之提出“修文治情”的主张,重新构建了儒家诗学理论。历代学者对于儒家诗学的阐发各有不同,但都公认诗歌有教化人伦、补益时政的作用,此系《诗经》被尊为“经”的重要原因。王夫之将《诗经》中的作品与史实相关联、印证,归结出周代兴亡的根由,认为:“周以情王,以情亡,情之不可恃久矣。是以君子莫慎乎治情。”(48)情不可久“恃”的特点,容易产生降情而从欲的“遽情”。王夫之将之视为东周由衰至亡的原因。《诗广传》多以周代衰亡为例批评亡国之音,书中明确言及“周衰道驰”、“周乱”、“周溃”等语达十余次,均认为是小人“遽情”所导致的结果。与此相对,王夫之发扬周代以王道治国的经验,提出“治情”作为后世师法的具体途径。
区别于前儒从德性层面“治情”,王夫之将“治情”进一步落实于“修文”的层面,并指出修文治情的两条路径。一是“勉于文而情得所正”(49),即通过不断学习《诗经》和历代优秀诗歌作品来调治人情,此系王夫之强调诗歌“兴观群怨”功能的理论基础;一是“文以节情”(50),即通过诗歌创作实践来调治诗人之情,此系王夫之诗歌创作论的重要理论基础。王夫之思想的特点“在能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51),与之相应,从个体层面生发“修文治情”主张最终指向治国:“治人之情而图治之道尽矣”(52)。总的来看,王夫之继承儒家“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理论传统,重新阐释了诗歌的社会功能:以诗歌引导君子之情、规戒小人之“遽情”,并以之教化人伦,以达到治国的目的。其儒家诗学理论之内在理路生成为:以诗节情——治世人之情——治国。
“遽情”与王夫之的人性论思想、礼乐思想、治国思想等均有内在联系,使得“遽情”基础上构建的诗学理论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在“遽情”论观照下,作品的意义已经不限于狭义的文学范围,如诗歌的思想情感、语辞结构、外在风格等。王夫之将以上诗学元素视为作者内在性情的外现以及国家、时代特征的表象。他认为诗歌创作过程不仅是如何达情的过程,更承载着对作者之情、对社会风化的引导、约束作用:戒淫归正。因此,王夫之诗学批评的着眼点和最终指向均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范围。以其批评竟陵诗派为例。后人对竟陵诗派的批评多着重于诗歌的情感内容、创作方法、意象选择、外在风格等几方面,而王夫之认为:竟陵派诗歌从情感内容到外在表现都根源于“遽情”,不仅作者自失本心,而且诗歌影响世道人心,最终成亡国之音。可见,王夫之从“遽情”角度对竟陵诗派的批评以及对杜甫、孟郊等诗人的批评,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学批评,其中蕴含着社会伦理道德的评价,以及对明朝亡国根源的解读等,其最终指向则是儒家的礼乐教化。
近年来,研究者多从理论水平和批评实践的矛盾出发,对王夫之诗歌审美判断力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王夫之诗学批评存在缺陷,或认为王夫之诗学理论与批评实践不平衡。从整体上看,这些观点都立足于以审美为核心诗学价值观来审视王夫之诗学批评,与王夫之多层次、多维度指向的诗学理论体系原貌存在差距。必须承认,王夫之对诗歌美学的体悟与解读自有其过人之处,他的诗学理论价值核心虽然不能与诗学发展史的美学趋向完全印合,但其诗学对儒家诗学理论的建构,对明末诗学弊端的针砭等,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论者以为,王夫之评选诗歌过严、过酷。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的确是王夫之的诗歌选本出现中的一种现象。但结合“遽情”论的生成背景及其在诗歌批评中的体现来看,这种现象又似乎并非单纯的出自“严苛”。王夫之在文学的表象下,看到的是人性的差异以及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他的诗歌批评中蕴含着一颗明遗民的救世之心。从另一个向度来看,王夫之基于“遽情”论的诗学理论批评,虽然无法完全弥合审美与救世之间的裂缝,但为其身后的诗歌创作乃至当今诗坛都提供了一个理论参照。当下诗歌在追求情欲之真与肉体之真的境遇中滑向沉沦时,是否需要批评家站出来区分一下“遽情”与真正诗情的差异呢?因为,诗歌的功能究竟是引人走向健康的生活,还是鼓舞情欲的肆意宣扬与发泄,既是王夫之于明末清初时所面对的问题,亦是当今诗学的一个沉重话题。
注释:
①⑨(22)(52)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0页,第898页,第894页,第895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13)(15)(18)(19)(21)(24)(32)(33)(42)(43)(44)(45)(46)(47)(48)(49)(50)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3册,第375—376页,第354页,第354—355页,第418页,第375页,第307页,第377页,第326页,第326页,第433页,第434页,第325页,第461—462页,第515页,第434页,第326页,第332页,第344页,第433—434页,第453页,第507页,第342页,第308页,第308页。
⑩严寿徵于《船山思问录导读》中延展刘咸炘《推十书》中的观点认为“重情是明代思想的一大特点”(王夫之撰、严寿澂导读《船山思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11)相关论述参见傅小凡《追求情的普遍意义——试论晚明思潮路向的转变》(载《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左东岭《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李双华《论冯梦龙之情教思想》(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
(12)(31)王夫之:《唐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第1021页,第1006页。
(14)关于王夫之对杜甫批评的原因,学界看法不一:邬国平《王夫之评杜甫论》认为杜诗不符合王夫之的审美标准(载《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郭瑞林《千古少有的偏见——王夫之眼中的杜甫其人其诗》认为杜诗不符合王夫之所认同的风雅之道的诗学传统(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涂波《王夫之杜诗批评衡论》认为王夫之不满杜诗言语卑琐、夸大其辞,亦不满后入学杜产生诸多流弊(《中国诗学》第8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绪义《萧条异代不同时——王船山为什么瞧不上杜甫》认为杜诗忧眉不忧心有违王夫之知行统一的哲学主张(载《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3期)。
(16)(26)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船山全书》第15册,第809页,第833页。
(17)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船山全书》第15册,第855页。
(20)黄宗羲:《张心友诗序》,《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7页。
(23)(25)(27)(29)(30)(35)(37)(38)(40)(41)王夫之:《古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第617页,第749页,第830页,第555页,第622页,第694页,第754页,第785页,第525页,第704页。
(28)王夫之:《楚辞通释》,《船山全书》第14册,第326页。
(34)(36)(39)王夫之:《明诗评选》,《船山全书》第14册,第1331页,第1320页,第1338页。
(51)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2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