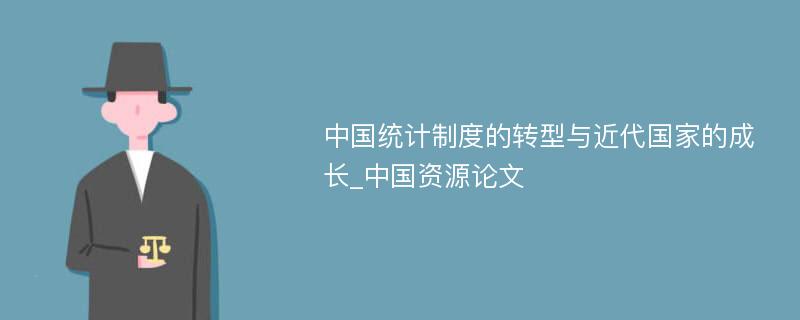
中国统计制度的转型与现代国家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制度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统计现代转型的缘起及特征
(一)前现代时期的混溶型统计及其特征
前现代时期,国家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技术和传统,整个统计是与其他行政行为和会计混溶在一起。“按照现在的说法,当时的统计调查属于‘行政记录’的性质。”①这一特征与艾森斯塔得在《帝国的政治体系》所创设的“混溶”②概念比较吻合。混溶型统计的特征如下:
1.统计机构与其他部门混溶在一起。前现代时期没有专门进行统计的必要,因而也就没有专门的统计机构。刘邦时期的西汉设立的“专主计籍”的“计相”与统计比较贴近,不久,这一名称便更名为“主计”。事实上,这一职务更接近于“总账会计”。由于没有专设的机构,信息的搜集与传递工作,其实就是官僚体系中工作人员的兼职行为。如唐、宋两朝,由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兼管全国综合统计与业务统计工作;元、明至清代前期,全国行政由六部总揽,统计业务也相应由六部兼管,其中,户部兼管的统计业务最多。此外,王朝还会非制度化地做出安排,令相关人员临时性地开展户口和土地的统计工作。如南齐萧道成(高宗)曾令黄门郎和傅坚意二位骁骑将军审定户籍,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到各州郡去核定户籍;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国子监生周铸、武淳等人主持浙江西部的土地丈量任务。
在官僚机构的下层,信息的搜集、加工、上报虽然是正式官吏的职责所在,但这项权力却基本旁落于非正式官僚之手。比如在宋代三年编制一次的户籍工作中,“登记男丁和财产的工作,由职役系统的耆长、里正和保甲系统的保长、坊正等乡村负责人进行”③。“明清时代,在州县衙门里有一批‘攒造田册’的专职人员。”④正是这批非正式官僚承担了统计信息的源头采集工作。
2.统计方法主要是登记式的信息收集。事实上,前现代国家没有对统计活动的制度规定,只是在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对官吏的考课制度、兵役制度、保甲制度等相关制度之中有分散的关于统计数据的采集、上报以及使用的规定。从秦朝发明“使黔首自实田”以来,“上计制度”一直是前现代国家信息采集的主导方式。其具体做法是:土地和人口的数据一般是由被统计对象自己填报,并由基层汇总后逐级上报至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资源的控制,前现代国家也会不定期地对户籍和土地登记中的隐匿行为进行清查。如辽代的“检括”,金代的“通检”、“推排”,南宋李椿年、朱熹等先后举办的“经界”等等都是清查土地的行为,隋代的“貌阅”、唐代的“团貌”,则是国家针对人口统计中的弄虚作假而采取的核查行为。与现代统计相比,前现代统计只是一项没有太多专业性的计数技术,统计方法比较原始,统计行为缺少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的支撑。由于王朝对统计并不重视,加之缺少对数字制度化的核查手段,统计上报就逐步演变成因循旧例的做法,地方官吏经常是将往年上报数按照惯例加个数字就逐级向上呈报。
3.统计对象狭窄。王朝时期的统计主要以维持其统治所需的土地和人口等资源为主,兼及皇室所需的奢侈消费品。人口和土地是前现代国家的主要资源,因此这两种资源的数字是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并都掌握的资料。在不同的时期,王朝统计的重点究竟是土地还是人口,要根据其对资源的需求来确定。从秦汉直至唐初期,以“民数”为重点,兼及土地;唐中叶实行两税法开始,“地数”逐渐成为统计重点,特别是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后,土地的统计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由此可见,王朝的需要决定了统计范围的变迁,当王朝存亡的基础立基于“人丁”时,统计就将统治范围内的每一个人头都计算在内;当土地成为权力配置的首要资源后,田亩就成了统计的首要对象。有的朝代还把赋税、漕运、矿产、盐税、军费也作为统计的对象。此外,皇室所用的奢侈消费品也成为统计的对象。
(二)统计现代转型的原因及特征
混溶型统计虽然比较简陋,但却基本满足了前现代国家简约式治理的需求。但随着现代化的启动,作为现代化主要推动力量的国家对信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如果国家的目标很小,那么它也无需了解社会很多……但是如果国家雄心勃勃……那么它就需要更了解社会和更多干涉社会。”⑤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统计的现代转型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且,现代统计的开展与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也紧密相关。晚清政府之所以开展现代的土地测量,就是在西方的压力下为了保护民族的利益而被动进行的。“当时以万国舆地协会有代测我国土地之要求,满清政府为之警惧,因而自动创办测量机构,并令各省同时举办,藉以拒绝该协会之要求。”⑥南京国民政府在部署土地和粮食调查统计时,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焦虑心理,担心由于没有现代统计、缺少统计数字不能列于世界之林,从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向西方学习,与此相似,中国的统计现代化也是学习西方的结果。统计制度的变迁过程经历了简单的制度模仿到深层次的制度创新的转变。其主要特征有:
1.统计机构专门化。从晚清在宪政编查馆设立统计科开始,中央政府就按照其政府架构的模式自上而下地推进统计机构的建设。新中国以前,中央与省级统计机构的建立虽然彰显了中央政府对现代统计机构的重视,但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还未延伸至基层,所以基层的统计机构也未能建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增强,村、居以及基层单位都建立了统计机构,一张遍布基层单位的统计网络正式建成。从总的趋势来看,国家对统计的控制和影响是不断强化的。如果说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对统计的使用还处于自发的状态,还只是一种对西方统计的简单模仿;那么,南京国民政府对统计的使用已经是非常地自觉。国民政府充分重视统计与“行政三联制”的关系,主动把统计引入政策设计和汲取资源之中,并成功地发挥了统计在战争动员中的作用。1949-1978年间,新中国进一步挖掘统计的价值,不仅注重发挥统计在编制和检查经济计划中的作用,而且还赋予其政治动员的功能,使其较好满足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对信息的需求。197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能够执行“信息、咨询与监督”任务的工作体系,组建了既能保持中央权威性又能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工作系统。
2.统计方法的现代化。方法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征。晚清政府,为了实行君主立宪而效仿西方进行人口普查,开启了统计方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以现代化为使命的政府,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时期以土地和人口为主要对象的不及时的上报信息,开始引入数理统计、概率论、指数等统计技术,运用普查、抽样调查等现代方法来开展国情调查。民国时期,基层需要填报的统计报表非常繁多,以致基层用“临表涕零”来形容他们的压力。新中国时期开展的一次性调查、全面的报表制度、渐趋繁多的普查,进一步展现了统计方法的现代化。但是,制度方法的现代化只是为国家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究竟选择什么方法还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当统计被看作是政治性的工具时,统计方法的选择就不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政治的需要直接影响到统计方法的选择。
3.统计范围不断调适。随国家职能和中心任务的不同,统计范围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着适应性的调适。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起步,为了完成政治整合的任务,中央政府面临着经济动员和政治动员的双重任务,当经济动员作为主要任务时,统计对象就以经济资源的汲取和分配情况为重点。国民政府时期的资源委员会对战争资源的调查统计,反映战时经济对统计对象的影响。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指令性计划时期,对资源控制与分配的需求,使物质的生产、分配与消费成为统计的主要对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统计的对象扩大到经济、社会、科技等方方面面。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统计数字是公共产品的新理念的确立,统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为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微观信息。而当政治动员成国家的兴奋点时,统计就必须围绕政治运动的对象与进程开展。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就进行农民阶级状况和政治表现的统计,为了反映“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就开展“中心工作进度”统计并进而刮起了“浮夸风”;“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也都对统计内容提出了政治性的要求。
二、统计现代转型的范式分析
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外部环境、国家的使命、执政者的理念等因素的影响,统计现代转型之旅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政治与技术相互影响、前进与迂回迭现的复杂面相。但总的来看,根据国家统计的主要特质,统计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技术型、动员型以及公共产品型三种不同统计范式。
(一)技术型统计范式
技术型统计范式是中国传统统计向现代统计转型的第一个阶段,涵盖了晚清、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基本对应了中国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在这一时期,统计作为技术工具的特征始终是第一位的功能定位。为了发挥统计信息对行政决策的作用,国家在统计机构设置、制度方法的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形成了技术型统计范式。其特征如下:
1.现代统计机构开始设立,并自上而下地从中央往地方延伸。1906年,清政府在宪政编查馆内设置统计局,“是为我国统计定制设官之嚆矢”⑦。从此,我国告别了统计机构混溶于其他机构之中的历史。自此,统计机构不断向着独立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到国民政府时期,统计机构已呈现出制度化、精英化的色彩。经过立法院统计处以及中央统计联合会事实上代行中央统计局职能的过渡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构建所谓的“超然性统计体制”。1931年,成立了国民政府主计处,统管全国统计工作的建设工作,指导中央各机关和地方省、县各层级建立统计机构,并统一规划全国通行的统计表格和统计方法。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发挥专家学者在统计系统内的作用,国民政府统计主计处掌门人刘大钧是专家型领导,曾经在第19届国际统计学会上就《中国统计之事业》进行过交流,而承担战争资源统计的国防资源委员会更显精英化的特征。但是,这一时期的统计的最大缺陷是网络还不健全,虽然中央层面机构相对完善,但基层却是严重不足。北洋政府时期,许多地方都无力按时完成中央的统计报表任务,农商部布置的《农工商调查》竟因“地方既无专人负责……往往视为具文,迁延误期,或竟不报”,最后,该项统计任务因无法坚持而被废弃⑧。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统计力量有所加强,但统计工作仍然受到基层组织不健全的制约,以致中央统计机关要通过向各地邮政局长或县长发信函来搜集数据,有时还要借助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来开展社会调查。
2.现代的调查统计方法广泛使用。前现代时期“自实上报”的统计方法显然不能满足现代国家汲取资源和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晚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执政者都转而通过统计报告与专项调查相结合、定期报表与普查相并行的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国情调查,对土地、人口、粮食、森林等各种资源进行了详细的清查。在现代调查统计中,数理统计的方法广为采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多达50多种的指数编制、农产品产量预测分析、土地统计中现代航测技术的应用,从不同侧面彰显出统计方法的“现代性”;但与此同时,传统的方法仍然沿用,整体上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比如,土地统计中既有现代的土地普查,也有传统意义上的土地陈报,而在户籍统计中,则是“警察调查户口”、“户籍及人事登记”与“保甲户口编查”三者并存⑨。这一时期,统计技术虽然也与政治建立了偶然性的勾连,但政治还没有对统计进行制度化的干预。突出的例子是,当国民政府因达成中日关税协定而宣称取得外交的巨大胜利时,立法院《统计月报》却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就这个协定来说,中国是十分失败的了”的结论⑩。
3.统计范围急剧扩大。统计对象大大突破了传统时期的土地和人口等核心资源,迅速扩展到现代生产过程的各种生产资料以及动员国民所需要的各种人力资源信息。晚清时期的民政部、度支部、商部、农工商部等通过定期报表对全国的户口、财政、商业和矿务等内容进行制度化的统计,甚至还为了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而开展了中草药调查。到民国时期,统计范围进一步扩大。从立法院及国民政府主计处公开发行的《统计月报》可以看出,举凡土地与人口、生产事业、商业、货币金融、财政、交通、教育、政治、国际比较等众多内容,皆成为统计的对象,而且每一具体的名目之下,还有更细的分类。就人口统计而言,人口密度、人口性别比、生育状况、自杀统计、失业统计、各地生活费指数、工人和农民和生活概括调查都已经程度不同地进行;就生产事业而言,不仅开展了桐油产销、纺织工业、矿产调查等工作,还着手进行粮食和棉花产量的预测工作。不过,这一时期的统计重点无疑是战争资源的调查统计。国民政府利用国家资源委员会(特别是其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对全国的粮食和煤炭生产运销、消费状况进行了全面的统计,还对钨、锑、锡、铜、铅、锌、铝等重要战略矿产资源以及边疆地区的资源、交通、人口等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战争资源的统计体系。
(二)动员型统计范式
该范式是中国传统统计向现代统计转型的第二个阶段,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根据国家政治动员和经济动员的需要,统计工作及时调整统计对象和统计方法,按照“党指到哪里就走到哪里,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要求,努力“成为党的驯服的、得心应手的工具”(11)。其主要特征是:
1.统计机构频繁地进行非制度化的调整。由于国家权力的成功下沉,新中国在村、居层面以及基层单位建立了统计机构,统计网络向基层渗透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了更好地适应动员的需要,统计机构随着国家权力的“收与放”不断进行着调整:为了加强经济计划的统一性与权威性,国家支持统计部门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的斗争,强调优先完成国家统计任务,并于1964年推进了高度独立统一的“一垂三统”(12)的统计体制;而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家又转而推行分散式的统计,强调统计要满足地方的需要。比如“大跃进”期间,下放对统计的管理权,强调统计对象、统计方法完全听地方党政领导的,甚至强调“统计什么、如何统计”都是谁布置就听谁的。在分散型模式下,甚至对统计的专业化思想进行批判,并通过动员群众参与的方式来弥补统计力量的不足。
2.制度方法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时期强调“政治挂帅”,通过政治与技术的紧密结合,创造出了能够灵活地进行经济动员和政治动员的一套方法。新中国在“从政治上把数理统计送上了审判台”的同时,又一边倒地引进了苏联式的社会经济统计方法,建立了服从和服务于计划经济的报表体系及制度框架。其后,随着对苏联经验的反思,又转而推崇能够贯彻领导意志的典型调查。根据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为统计方法贴上了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不同标签,对统计方法进行了严格的政治规训,如果只是遵循数理的方法,则被批判为“为数字而数字”、“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在政治的强力规训下,统计工作牢牢地确立了“政治第一”的方针:“在统计工作的进行中,必须无条件地服务党的领导,并无条件地为党的领导工作服务。”(13)到了“文革”时期,统计对技术特性的坚持则进一步被升格为“向党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而遭受更严厉的批判。
3.统计范围随国家“中心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建国初期,出于摸清家底的需要,各地自发开展了对接收遗产的统计。而随着计划经济的起步,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一次性调查工作,重大的调查如国营工业普查、工农业总产值和劳动就业调查、全国人口普查、手工业普查、私营工业普查、私营商业普查、农业合作社的收益分配调查、职工家计调查和农民家计调查等,小的专项调查如黑金属、废金属的库存量调查、车辆数量调查、工厂机器数量调查等。实施计划经济以后,则根据计划管理的需要,建立了覆盖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国民经济平衡统计指标。从统计指标体系来看,“反映生产建设的多,反映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少,反映数量的多,反映质量和效果的少,反映实物量变化的多,反映价值量变化的少,反映全民所有制情况的多,反映集体所有制和其他经济类型情况的少……有很大一块还是空白。”(14)这一时期,统计工作经常紧随一个个的政治运动而调整统计对象。开展除四害运动,就要对消灭苍蝇、蚊虫、老鼠、麻雀的数量与进度情况进行统计;北戴河会议部署了深翻土地、大炼钢铁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统计就增添了深翻土地进度表和人民公社建立情况调查表,钢铁进度统计也从月报先后改为十日报、周报和日报。因此,统计工作的对象变化比较大,一次性调查任务频繁,多变的工作常常使基层无所适从。
(三)公共产品型统计范式
1978年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政治挂帅,统计范式出现了转型。随着公共产品理念的逐步树立,统计信息从为政府服务拓展为面向国家、社会以及公民服务。随着统计职能这一硬核的变化,统计机构、统计运行规则和统计范围这些保护带都随之调整,公共产品型范式逐步确立起来。其基本特征是:
1.统计系统形成了以国家统计系统为主、以民间统计为补充的多元格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加强统计机构,充实统计力量,先后作过多次指示,统计机构逐步得到加强。1983年《统计法》实施后,统计机构建设走上了法治化的轨道。目前,以各级政府统计局及直属于国家统计局的农村调查队、城市调查队和企业调查队组成的政府统计体系不断趋于完善,由相关部门自上而下设立的部门统计体系也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在重大普查时期还制度化地成立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如第三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业普查、农业普查、经济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在此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也利用国家统计系统开展地方统计业务,及时获取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所需要的统计信息。近年来,民间统计机构这支新生的力量开始在统计舞台上崭露头角。不仅国外一些知名统计调查机构开始在我国建立分支机构,国内自发组织的统计咨询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先后出现。从总的趋势来看,由于统计工作有《统计法》的保障,统计组织的自主性、专业性不断增强,统计从业人员的数量稳步提升。
2.统计的科学性受到尊重与保护。在“去政治化”的影响下,统计开始向技术工具回归,统计方法采取了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方针,统计分类标准也比较注重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开始实施,报表制度的范围不断缩小;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日益多元化,导致以抽样调查为主的综合性调查方法被大量使用;数量统计方法在统计工作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15)与此同时,统计的规章制度不断完善,统计的分类标准、单位编码、地址编码都越来越完善。这些正式规则为统计的自主性提供了保障。但是,由于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统计行为仍然受到地方党政领导的干扰,有些地方的统计行为已经从以规章制度为准则演变为以领导旨意为准绳。随着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推行和考核力度的加大,“有些党政干部或企业负责人,便打着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争名夺位的幌子,不以身试法,默许、暗示甚至公开怂恿、授意、胁迫下发虚报、虚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形成了‘官升数据、数据升官’的恶性循环机制”(16)。
3.统计对象的内涵极大丰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巨大变化,统计对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生产统计发展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基本建设统计逐步发展成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商业和物资统计转变为社会商品和物资流转统计。至1994年,我国正式放弃了苏联式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体系,转而向西方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普遍使用的《国民账户体系》(简称SNA)转变。国民经济的核算范围从MPS体系中国民收入的生产情况扩大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情况,统计范围从物质生产部门扩大到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构成全领域(17)。这一变化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统计的数量变化,还带来了质的变化,那就是从对物质的生产、分配为重点的实物型统计向以GDP为核心的价值型统计的转变。近年来,随着对科学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重视,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逐步代替了以发展为中心的政绩评价体系,民生福利的统计成了重点内容。随着民意社情调查的悖兴,各地纷纷开展群众安全感、干部评议、行风评议和民生问题、政绩调查、小康指标调查等民意调查,进一步丰富了统计的内容。
统计范式的现代转型表明,主要动力是现代国家成长的需求。而从统计系统自身来看,统计职能在统计范式转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相当于拉卡托斯所说的“硬核”,而统计的组织结构、制度方法和统计范围都相当于“保护带”,它们的调整受制于统计职能这一硬核的需要。在同一种范式下,保护带的调整就是量的变化,而当保护带的调整也无法适应硬核改变的速率时,统计范式就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某一种范式虽然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但也包含了其他范式的某些特点。因此,统计的不同范式并非是排它的,而是兼容的;统计的范式转型也并非不同范式的相互替代,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比如,在技术型范式中,统计也具有政治动员的特征,而动员型范式之所以能够发挥动员的功能,也正是以统计的技术特征为基础的。
三、现代统计对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影响
随着统计的现代转型,统计这一技术工具也对权力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效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而成为现代国家成长的推动力量。
(一)提高了国家的整合能力
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的行政力量,如果没有信息基础作为反思性自我调节的手段,就无法生存下去。”(18)在他看来,前现代国家是“裂变”性质的多个地方共同体组成的,只有到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国家机器和权力体系并借助现代交通、信息、学校等现代工具,国家的权力才能真正覆盖到所有的国家疆域,行使对主权国家的统辖(19)。前现代时期,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士绅等“中介”而进行的间接式统治,传统的中国人是不知道有国家的,甚至就连纳税行为也是通过胥吏、书吏、催征吏等非正式官僚实现的。而税收控制在非正式官僚手中,则“不仅意味着中央经济权力的削弱,且意味着政治离心局面的造成”(20)。现代国家为了进行政治整合,在推进官僚机构向下延伸的同时,也注重提高以信息为基础的反思性监控能力。现代国家通过开展人口普查、资源普查等各式各样的统计调查行为,使统计对象直接感受到国家意志的存在。以倍受关注的人口普查为例,1953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动用了250多万人的普查员队伍,到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超过500万人,刚刚进行的“六普”则又上升到650万人。如此规模庞大的调查员队伍逐家逐户地进行入户调查,不仅仅直接展示了国家的权力,而且通过“数字化”的方法对国民的认同和身份进行了重新分类,大大强化了政府对国民的控制。当然,国家权力的“数字化”并非一帆风顺,地方和民众以多种形式进行了“弱者的反抗”,这些反抗不仅仅有对“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工资“被增长”的质疑,还包括数据上的虚报、瞒报和浮夸。但通过持之以恒的“数字下乡”行为,国家顺利地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传送到基层,使每个公民都感受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而且,还成功地将民众从他们的传统地方性生存场景中“抽离化”出来,从而打破了地方对信息的封锁,推进了对社会的政治整合。
(二)增强了国家的汲取能力
国家汲取能力是指政府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可靠的手段了解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不能知道他们的财富状况、不能用地图表示出其土地、资源和居住状况,那么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必然是拙劣的。”(21)由于“缺少数目字管理技术”,前现代国家的确在资源汲取过程中表现出“拙劣”的一面:名义上为国家所有的资源很容易被地方所截留,甚至是被掌握了真实信息的非正式官僚所掌握。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发现,在中华帝国时期,“除非帝国是在一个精力过人的统治者的支配之下,否则官吏往往少报可课征租税的田地面积与纳税的人数,少报之数约是已公布的土地户籍登记数字的40%”(22)。由于缺乏对资源的数目字管理技术,田赋征收中“包办隐瞒遗漏中饱种种弊混,乃属必然,人民所出,不能涓滴归公,政府收入,遂日趋疲困,欠不在民,收不入官”(23)的现象亦在所难免。从北洋政府设立经界局开始,中央政府就试图通过土地陈报与土地清丈活动,向“隐瞒地产、逃避赋税”的行为宣战。通过不断扩展统计范围,现代国家成功地描绘出一张关于土地、人口、收入、职业等各种资源的总清单,实现了对资源的编码管理,将它们变成了可以由国家精确计算的可控之物,从而大大提高了国家对资源的汲取能力。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资源管理委员会对粮食和各种战争资源进行的调查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统制,从资源上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加强农业统计,实现了对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发展,为新中国启动赶超型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以GDP数字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中央政府成功地实现了对地方的激励,进一步增强了对地方资源的汲取能力。
(三)提高了国家的决策水平
传统政治管理方法基本限于模糊的经验论层次上,注重从人的主观动因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现代政治管理则强调定性管理与定量管理相结合。现代国家注重发挥统计在决策中的作用,以统计数字作为定量分析的前提,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对此,民国时期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我们若要提纲挈领,执简驭繁,使政治上的举措不致如盲人骑瞎马一样的乱撞,自然只有根据客观的统计资料分析比较,鉴古以观今,惩前而毖后。为政者之有统计,正如工匠之有刀斧,商人之有秤斗,农人之有犁耙一样。”(24)“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统计学是一种为达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目的用于制定长期和短期计划的工具。高深的统计技术用于做出人口和预测以及商品消费和流通需求的预测;更进一步,为了达到社会福利所希望的目标,高深的统计技术也用于由适当的模型制定经济计划。”(25)事实上,现代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越来越离不开统计数据的支撑。为发挥信息对决策的引导作用,我国近年来开展了高密度的普查工作,2004年开展了经济普查,2006年底开展了被称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业普查”,2007年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2008年开展了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10年开展水利普查,2010年开展第六次人口普查。这类普查的共性是提供了科学决策所需要的相关信息,避免了因情况不明而出现的错误决策。不仅如此,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社情民意调查,通过民意调查来掌握民众的预期反应,避免公共决策的失误。
纵观中国统计现代转型的历史,可以发现统计制度变迁的两个面相:一方面,为适应国家的需求变化,统计积极调整着自身的职能及整体框架。可以说,是国家的需求决定了统计变迁的方向。因此统计技术被打上了权力与利益的烙印。另一方面,统计也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国家的影响。统计不仅仅通过提高国家能力而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也通过发挥其技术所长为自身争取到了一定的自主性。可以预见,随着对信息的需求增加和信息供应能力的提高,统计将会在公共服务的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参见莫曰达:《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史》,[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序第2页。
②参见[以]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③[澳]苏启龙等:《宋代的户口统计制度:对有关制度的综合分析》,载[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④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总序第11页。
⑤(21)[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第102页。
⑥李春培:《广西土地面积整理概况》,载广西省政府总务处统计室编《广西统计季报》第二期(1937年6月)。
⑦吴大钧:《我国统计制度之研究》,主计处统计局《统计月报》,第九、第十号合刊(1932年10月)。
⑧万国鼎:《农商统计表》,载中国地政学会出版《地政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2月)。
⑨《三元县户口调查统计实验办法说明》,载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统计副镌》第二十四号(1940年8月)。
⑩童蒙正:《中日关税协定的研究》,载立法院《统计月报》,第二卷第五期(1930年5月)。
(11)《为加强统计工作的党性而努力》,载《统计工作》1959年第14期。
(12)“一垂三统”即国家统计局对地方统计局实行垂直领导,统一管理编制、人员、经费。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1962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的决定》作出的规定。
(13)贾启允:《关于我国的统计工作的方针问题》,载[北京]《中国统计》1959年第10期。
(14)《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和改革统计工作报告的通知》(1981年9月15日),载[北京]《中国统计》1981年第5期。
(15)徐国祥等:《新中国统计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6)《大力推动统计科技进步,切实加强统计法制建设——张塞同志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一九九五年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第4页。
(17)参见宗平:《谈谈〈国民帐户体系〉和〈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核算国民收入的差别和资料换算方法》,载[北京]《中国统计》1980年第5、6期合刊。
(18)(19)[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1页,第20页。
(20)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22)参见[德]韦伯:《韦伯作品集5: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3页。
(23)《新闻十七则·江宁自治实验县举办土地陈报》,载中国地政学会出版《地政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3年4月)。
(24)陈藻潭:《如何促成统计的迫切需要》,载社会部统计处编印《社会行政统计》第三十一号(1947年4月)。
(25)[美]C.R.劳:《统计与真理:怎样运用偶然性》,李竹渝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标签:中国资源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基层反映论文; 统计调查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经济学论文; 范式论文; 经济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