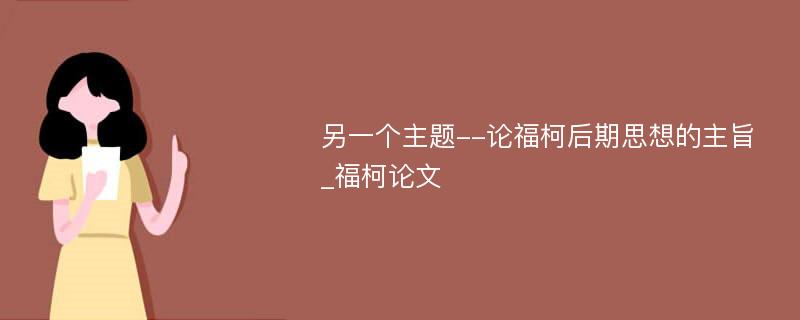
别一种主体——论福柯晚期思想的旨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旨意论文,晚期论文,主体论文,思想论文,论福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几何时,学界非常关注福柯有关主体离心化的学说,“死了”的声音就好象盛夏的 “知了”一样搅得人心烦噪。然而,在福柯临终之前,一阵“回归主体”之风又刮得学 者们晕头转向。面对众声喧哗,我的看法是:既不应该简单地谈“回归”,也不能够拘 泥于“主体”的不变含义。在本文中,我们首先对德勒兹的有关观点作一述评,进而从 主体与自我认识、自我关怀的关系角度进行清理,力求较为全面、清楚地向人们揭示出 福柯晚期思想的旨意和脉落。
一
德勒兹认为:福柯晚期关注的是主体化而非主体。
简单地说来,问题是这样发生的:许多学者认为,福柯早期抛弃主体,晚期重新回归 主体;而德勒兹则坚持认为,不管认为福柯早期抛弃了主体,还是主张他后来回到了主 体都是一种误解。德勒兹有这样一些说法:“福柯的哲学毕竟还很难说就是关于主体的 哲学。至多可以说,当福柯发现作为第三维的主体性时,他的哲学‘或许是关于主体的 哲学’。”(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 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5、129~131、113、113、128、120 、120、112、128页。)“认为福柯重又发现,重又找到他最初所否定的主体性,是一个 误会,是一个与对‘人的消亡’的理解同样大的误会,我甚至认为主体化与一个主体很 少关联。”(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 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5、129~131、113、113、128、120 、120、112、128页。)“在其最后的著作中,人们发现了一种作为‘主体化进程’的思 想:将此视为对主体的回归是十分愚蠢的。”(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对 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5 、129~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或与之相近的说法:“说福 柯在否认了主体之后又引入了一种隐蔽的主体,是愚蠢的。没有主体,但是有主体性的 产生。”(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 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5、129~131、113、113、128、120、12 0、112、128页。))显然,这些说法一个比一个强化,一个比一个明确,最终说来就是 ,福柯晚期并没有向主体回归,福柯的晚期哲学不是一种关于主体的哲学,而是一种探 讨主体化的哲学。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一是主体化(法文原为subjectivatio n,或译主观化),一是主体。我们必须首先明白德勒兹谈论福柯的旨意何在,才能够把 握他区分这两个概念的语境。德勒兹的看法之核心是:由于接受尼采的影响,不管提出 主体终结论,还是揭示主体化进程,福柯的目标都是为了弘扬生命,它们分别对应着两 种不同的生命主义。
德勒兹指出,人们就“人的死亡”产生了这样两种看法:①这并没有涉及到真实的人 的问题,它涉及到的只是人的一个概念;②福柯和尼采看到了真实的人对他自身的超越 ,并且他们希望他成为一个超人。德勒兹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对福柯和尼采的误解。 (注:吉尔·德勒兹:《福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88、132、 92、106、115、101、96、110、119页。)依据他对福柯思想的阐释,问题和答案都在“ 超人”这个概念中:超人远远没有达到活着的人的消失,又大大超出于人的概念的改变 ,它是既不同于上帝也不同于人的一种新的形式的降临。(注:吉尔·德勒兹:《福柯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88、132、92、106、115、101、96、11 0、119页。)“人”在古典时期(17—18世纪)并不存在,存在着的只有上帝或者无限性 ;“人”在现代时期(19世纪)开始出现,上帝让位于人或者有限性。超人不仅要摆脱上 帝的无限性(——尼采于是说:上帝死了)而且要克服人的有限性(——福柯进而指出: 人死了)。一个顺理成章的思路是:“人束缚着生命”,但超人“把生命从人本身之中 解放出来”。(注:吉尔·德勒兹:《福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 ,第88、132、92、106、115、101、96、110、119页。)于是,福柯的主体终结论并不 单纯是消极的,而是包含着一种积极的指向:“将死亡变成为一种与生命共存的力量” ,这是一种“在死亡主义背景上的生命主义”。(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 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 5、129~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换言之,生命恰恰是在传统 主体死亡之后才真正恢复了生机。
德勒兹进而表明,福柯晚期思想尤其表现为对生命的关注:“当福柯到达‘主体’的 最终主题时,‘主体’最重要的就在于创造生命的新可能性,即如尼采所说,构成生命 的真正风格:一种在审美背景上的生命主义。”(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 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 5、129~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这种生命主义明确地表达了 一种审美的姿态:“在其最后的著作中,人们发现了一种作为‘主体化进程’的思想… …这是存在方式的构成,或是尼采所说的生命新可能性的创造。存在不是作为主体,而 是作为艺术创造,这最后阶段即是艺术家思想。”(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 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 115、129~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在尼采那里,所谓美就是 与强力意志、与生命满溢相关的东西,是与创造性相关的东西。德勒兹将福柯思想与生 命的可能性之创造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作为一个尼采主义者,福 柯思想中理应包含这种指向。德勒兹同时表明审美与伦理相一致,但与道德相对立:“ 生存方式或生命风格的构成不仅是审美的,也是福柯称之为伦理的,这与道德相对立。 ”这是因为,道德与强制性规则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行动和意图必须接受超验的价值原 则的评判;而“伦理是一套非强制性的规则,这些规则按照我们所言、我们所行导致的 生存方式来评价我们的言行”,它意味着“一种生命可能性的创造,一种生存方式的创 造。”(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 、107、110、128、105、105、110、114~115、129~131、113、113、128、120、120 、112、128页。)简而言之,审美与伦理指向的都是“生命的可能性”的创造,而道德 则是对生命的压制。
按照德勒兹的意思,生命、审美和伦理要求的是摆脱知识、道德或者强制性的规则, 这体现为一种主体化进程,但并不意味着主体。于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主体化,什么 又叫主体。关于主体化,德勒兹这样说道:“主体化进程是五花八门的。基督徒的方式 与希腊人的方式截然不同……对福柯来说,重要的是主体化区别于一切道德,区别于一 切道德法则。与知识和权力性质的道德相反,主体化是伦理的和审美的。”这样的说法 当然还是抽象的,具体而言,德勒兹用了一些比喻性的说法来进行界定:主体化可以说 是“一种气氛的变化”、“一个事件”、“一种电场或磁场”,是“闪光,闪耀、闪烁 ”,是“光的效果”,意味着“激情”,“激情状态”,“无主体的个人化”,如此等 等。(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 107、110、128、105、105、110、114~115、129~131、113、113、128、120、120、1 12、128页。)德勒兹并没有明确地对主体概念加以界定,但在与主体化进行的比较中这 样说道:“一个主体化的进程,即一个生存方式的产生,不能与一个主体混在一起,除 非去掉主体的一切内在性,甚至一切同一性。主体化甚至与‘人格’也毫无关系……这 是一个强化的方式而非人格的主体。”(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对话》, 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5、129~ 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勒兹把主体与精 神性的、作为变中之不变的人格相等同,于是,主体的含义就是“内在性”、“同一性 ”、“实体性”。主体化作为对于生存方式的寻求恰恰要突破主体,某种意义上也可以 说是要突破主体与知识、与权力的结盟,“主体化的进程……是一个特别的维度,没有 它,人们既不能超越知识,也不能抗拒权力。”(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 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 5、129~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德勒兹在另外的地方则指出 ,福柯事实上已经把主体界定为一种派生物,一种从陈述中派生出来的功能。(注:吉 尔·德勒兹:《福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88、132、92、106 、115、101、96、110、119页。)按照他的意思,假如说存在着某一主体“我”的话, “我”并不意指普遍性而是在某人说、某人看、某人正视、某人生活中占据的一系列特 定的位置。(注:吉尔·德勒兹:《福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 第88、132、92、106、115、101、96、110、119页。)显然,如果说主体化与生存方式 相关,尤其是与审美生存相关,那么功能化同样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知道,福柯晚期探讨的是古希腊、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自我技术问题,有些学者 由此认定福柯晚期思想主张回归古希腊,进而认定福柯主张主体的回归。关于这个问题 ,德勒兹有这样一些表述:“希腊人创造了审美的生存方式……这样我们便有了使在其 他方式下不可生存者得以生存的手段。”(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对话》 ,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5、129 ~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希腊人发现了“审美的生存——折 回自身或与自己的关系,自由人的任意性规则”。(注:吉尔·德勒兹:《福柯》,美 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88、132、92、106、115、101、96、110、119 页。)“主体化不是向主体的理论回归,而是对另一种生命形式、对一种新风格的实际 探寻。这种探寻不是发生在头脑里面,那么今天,集体或者说个人以及自我生存的胚芽 出现在什么地方?是否有这种胚芽呢?这当然应该询问希腊人……曾有过一种希腊的经验 ,一些基督徒的经验……但是既非希腊人,也非基督徒会为今天的我们做出探索。”( 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 110、128、105、105、110、114~115、129~131、113、113、128、120、120、112、1 28页。)德勒兹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福柯对于主体化的关注的确受到了希腊人和基督 徒的启示,尽管如此,应该强调的是,福柯感兴趣的不是回归希腊人,而是反思今天的 我们。当然,希腊的经验,基督徒的经验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主体化进程无 疑具有借鉴意义。
二
我们的看法是:主体化概念意味着一种新的主体观。
德勒兹的主要思路是这样的:首先,他严格地区分主体化与主体两个概念,前者意味 着一种审美的生存,与过程联系在一起,后者意味着一种人格,与实体联系在一起。第 二,福柯思想中存在着不断更新,先是集中于知识归档分析,然后是权力问题,最后是 主体性的形成(主体化)问题。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福柯还需要另一个维度, 为什么他要发现既区别于知识又区别于权力的主体性?”(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 权力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 14~115、129~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第三,主体死亡观抛 弃的是主体,关于知识和权力问题的探讨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主体性形成问题的探 讨与前面两者的探讨有别,旨在突出生存方式的构造,表明的是主体化进程,然而这并 不意味着对于主体的回归,因为福柯的“思想的确经历了一种危机,在各个方面,但这 是一种创造性的危机而非一种悔悟性的危机。”(注: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 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110、114~11 5、129~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
按照我们的理解,在福柯晚期思想中的确可以说不存在回归。福柯思想的演进历程大 致上区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以知识型为核心,中期以权力策略为着眼点,晚期则以生存 伦理为归宿。于是,不管是德勒兹还是其他研究者都认定福柯思想中包含着知识、权力 和伦理三个维度。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三者的关系如何:出现了质变,还是始终只有延续 ?变化的是什么,延续的又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福柯以主体问题为始终 不变的宗旨,但探讨的角度或方式明显不同。所以我赞成福柯晚期探讨的是主体问题这 样的观点(这与德勒兹相反),但不谈主体的回归(这与德勒兹一致),理由是:主体问题 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这对立于德勒兹看法:他认为福柯重来不谈主体)。福柯最初是以知 识问题为中心,但权力问题隐含其中(探讨的实质上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诸如疯 人院、医院、道德、理性等概念都暗含着权力机制的运作,但福柯没有明确使用权力概 念),接下来是权力问题为中心,但直接涉及到知识问题(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或者 说是在知识领域中探讨权力问题)。那么这两个维度与伦理维度,或者说知识问题、权 力问题与主体化问题的关系何在呢?我以为前两者是以批判为着眼点,探讨的是主体化 的误区,或者说人的个体生存是如何被知识、权力(真理或德性等普遍性原则或要求)所 覆盖、所遮蔽的,可以说是从反面着手;而后者则直接为我们展示了个体生存的可能方 式,正面地为我们提供了审美的生存的可能选择。
所以,福柯自己在晚期总结说,他的全部思想都涉及主体化问题,因此第一维是知识 主体的构成,第二维是权力主体的构成,第三维是伦理主体的构成。他在《主体与权力 》(1982)中说道:“我想首先谈谈在过去二十年里我的工作的目标……我无宁是在力图 撰写我们的文化中人的存在的主体化的不同模式的历史;按照这一观点,我探讨了把人 的存在转变为主体的三种主体化模式。”(注:米歇尔·福柯:《言与文》第4卷,法国 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法文版,第222~223、697、706、703、223、786、172、731~732 、732页。)在《道德的回归》(1984)中,他又说道:“我试图提出三大类问题,即真理 问题、权力问题和个人行为问题。这三个经验领域只有彼此关联才能获得理解,否则就 不能获得理解。前面的著作让我感觉到不安的是,它们考虑了前两种经验而忽略了第三 种经验。在使第三种经验出现时,我觉得在三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连贯,这不需要诉诸 于人们借以避开三种基本经验领域的一种的随意的修辞方法来证明。”(注:米歇尔· 福柯:《言与文》第4卷,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法文版,第222~223、697、706、7 03、223、786、172、731~732、732页。)显然,福柯的全部工作都旨在探讨主体是如 何构成的,因此针对的不是主体的属性与本质,而是主体“化”问题。福柯是这样来界 定主体化的:“我把人们据以构成一个主体或更确切地说构成一种主体性的过程叫做主 体化。”(注:米歇尔·福柯:《言与文》第4卷,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法文版,第 222~223、697、706、703、223、786、172、731~732、732页。)于是三个维度的探讨 都以瓦解传统意义上作为人格的主体为宗旨,强调了主体是过程的结果,而非先在的实 体。
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按照德勒兹的理解,主体化仅仅与审美和伦理相关,因 此是后来才出现的,“在一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跨越了知识与权力的阶段之后,正是 这些阶段迫使我们提出新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此之前提出。”(注:吉尔·德勒兹:《 哲学与权力的对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版,第106、107、110、128、105、105、 110、114~115、129~131、113、113、128、120、120、112、128页。)按照我的看法 ,福柯承认了三种形式的主体化,但他并不是客观地、公正无私地、冷眼旁观地从历史 中发掘出这三种形式,而是要为人们提供某种选择,他实际上是带有倾向性的。伦理的 、审美的维度是福柯在排除知识主体和权力主体的情形下为我们展示的可能生活图景。 假如只是追求知识,他无疑会将审美经验唯智化,假如他只对权力关系感兴趣,他无疑 会将生存政治化,这都不是他的选择。于是,如果德勒兹强调伦理、审美这一主体化维 度的意义,无疑把握了福柯思想的实质和核心,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另外两个维度同样涉 及的是主体化问题。事实上,德勒兹自己在《福柯》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第三维度是 一个不同于知识和权力轴心的新的轴心,但它“不是一个取消所有其它轴心的轴心,而 是一个已经与其它轴心同时起作用的、阻止它们完结在死胡同中的轴心。或许这一轴心 一开始就在福柯那里被表达出来(正象权力一开始就被表达在知识中)。但它只能通过设 定一定的距离、并因此可以折返到另外两者才能够呈现。福柯感觉到有必要进行重组, 以便解开完全与其它两者纠缠在一起的这一通道(它隐藏在它们的背后):福柯在《快感 的享用》的一般导言中提出的正是这种重新确定中心。”(注:吉尔·德勒兹:《福柯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88、132、92、106、115、101、96、11 0、119页。)可以看出,德勒兹在这一段话中强调的是统一性,这不仅瓦解了主体回归 问题,同样也否定了主体化在晚期才出现这一判断。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主体和主体化这两个概念。我们应该明白,在笛卡尔主义传统 中,主体当然不具有福柯意义上的主体化含义。但这个概念的内涵实际上不断在发生着 变化,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中,主体概念的传统内涵基本上已经被掏空。比如,在存 在主义那里,主体性就已经不是一种静态的规定,而是具有与选择、设计联系在一起的 动态含义。德勒兹把主体性仍然等同于实体性、同一性和内在性,这种理解明显停留在 笛卡尔时代。在笛卡尔那里,我思主体当然是实体的、内在的、同一的,但在后来的发 展中,康德的先验统觉开始排除实体性,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在此基础上放弃了同一性 ,在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那里,由于强调在世存在,内在性的含义也已经消失了,而 勒维纳斯更明确地强调了主体的外在性。按照一个过时了的主体概念来否认福柯思想中 包含的新主体意味显然是有问题的。福柯的其他评论者恰恰是在德勒兹自己关于审美、 生存、伦理的含义下理解主体的。如果说这样的理解存在着什么问题的话,也不过是概 念的使用问题,并没有误解福柯思想的本意或实质。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同等地使用“ 主体化”和“主体性”来概括福柯晚期思想。
德勒兹将福柯思想纳入两种意义下的生命主义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它们与“主体”没 有关系吗?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形式的生命主义纳入以强调主体性著称的存在主义范畴, 大体上也不算过分。我们通常只看到福柯接受了尼采的影响,但没有考虑到福柯思想的 存在主义背景。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福柯最初是从海德格尔出发的 ,随后才转向了尼采,不排除福柯是透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才领会到了尼采的生命主 义旨意。福柯曾经谈到,他虽然对尼采的理解要胜过对于海德格尔的理解,但阅读这两 位大师依然是他经历过的两种根本的经验,他并且表示:“如果我未曾读过海德格尔, 可能就不会读尼采……在50年代我曾试着阅读尼采,但单是尼采并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 !然而尼采和海德格尔结合起来,这乃是一种哲学上的冲击!”(注:米歇尔·福柯:《 言与文》第4卷,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法文版,第222~223、697、706、703、223 、786、172、731~732、732页。)福柯声称他的整个哲学发展是由阅读海德格尔引起的 显然不是戏言。德勒兹也承认,福柯尽管拒绝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但他的一些重要主 题明显地从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理论灵感”。(注:吉尔·德勒兹 :《福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88、132、92、106、115、101 、96、110、119页。)
存在主义明显地抵制文化传统、社会规范、理性知识对于人生的先在的规定,但它实 际上承认这是人的某种处境,是自由选择的条件甚至前提。原因在于,存在主义并不是 认为人首先是本真的,然后降格为非本真的,相反,所谓的非本真处境倒是在先的,只 是自由选择导致了改变这种在先处境的可能性。于是,在先行向死而在中,人才能够由 “畏”而听从良心的呼唤,把自己从沉沦状态中呼唤回来,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里的“死”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真正“终了”,它更多地包含有摆脱社会规范、文化传 统、理性知识的含义,是要让个体从大写的人中解脱出来,实际上也意味着审美意义上 的人生升华。福柯和海德格尔、萨特差不多发现的是同样的事情:现代性意义上的人是 普遍规定性的产物,透过置大写的人于死地,个体就能够回归经验的、审美的、伦理的 生存。福柯并没有真正远离现象学-存在主义,如果说福柯那里不包含“主体”,而只 有“主体化”之含义,那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如此,要求的都是以一种审美的主体化 取代规范的主体化。我们甚至可以泛而言之:福柯思想不过是黑格尔之后的各种抵制理 性主体的倾向的批判发挥。
林赛·沃特斯在其《美学权威主义批判》中特别强调了福柯晚期“回归主体”对于思 想和批评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他主张由智性知识回归经验,因为经验具有审美的含义 ,“是某种人们只能经历而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注:林赛·沃特斯:《审美权威 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2、12~13、16~17、22页。)这无疑意 味着福柯意义上的主体化。但他显然没有撇开“主体”概念谈经验,他认为“主体”是 “某种曾被人们丢弃但却必须重新捡回的东西”,福柯“很快就从试图摆脱人而转向‘ 对自我的关怀’。”(注:林赛·沃特斯:《审美权威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 0年中文版,第2、12~13、16~17、22页。)沃特斯并没有简单化地读解福柯,他的理 解是:虽然“精明正确的主体”已经死去了,但“我们必须拯救那个能够被感动的主体 ”,“笛卡尔式的认知主体确实是某种过时的东西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应该放 弃一切对主体性的关注。”(注:林赛·沃特斯:《审美权威主义批判》,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2、12~13、16~17、22页。)事实上,他也承认“反人类主义” 这一概念的“积极的一面。”(注:林赛·沃特斯:《审美权威主义批判》,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2、12~13、16~17、22页。)于是,沃特斯正确地指出,福柯 批驳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目标却是引出一种新的主体。换言之,在批判知识和道德的 基础上强调经验和审美,福柯无疑使主体获得了“新生”而不是“再生”。
三
我们认为:福柯的旨意是由知识回归伦理。
在拙文《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米歇尔·福柯的生存哲学研究》中,我这样写道:“ 从方法论上讲,他拒绝接受强调先验意识的现象学方法,提出了主体终结论;从主要工 作来看,他致力于揭示主体的真相:不存在所谓的我思或者先验的自我,主体实际上是 现代性进程中的构成物——知识主体、权力主体是通过掩饰个体的身体经验而得以诞生 的;从最终目的来说,他似乎要提供某种替代性的选择:超越现代性,向关注原始身体 经验的个体,即自我关怀的伦理主体回归。简言之,福柯要揭示人在现代性进程中作为 大我(理性主体)的工具性地位,确立自我关怀的小我(身体经验)的审美生存形象。”“ 福柯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揭示主体的真相,并为我们指出通向个体生存之路。”(注:杨 大春:《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参《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第117页。)非常明显,我们承认了主体问题在福柯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我的基本 看法是,严格地说,福柯从来都没有真正抛弃主体,他不过是抛弃了近代以来的主体概 念中固有的含义的某些维度而已。因此,他晚期继续探讨主体问题,但方式并不同于早 期。
福柯早期提出主体终结论,晚期似乎又重新“回归”主体,这只是一种表面的、不难 消除的矛盾。我们必须再度强调,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主体置于一边,而是从新的方法 论视角重新审视主体的命运,并最终指向生命主义。福柯主要从三个角度为我们揭示了 主体的真相。首先,在古希腊哲学中,以“自我关怀”为主导的“知”“行”合一意味 着一种自由的、审美的伦理生活,伦理主体具有自发性、自主性(福柯也曾表示,并非 整个古希腊时期、并非所有的希腊人都是如此)。其次,近代以来的以“自我认识”为 中心的“知”“行”合一把人导向与原始经验疏远的智性生活,知识主体表现出规范性 、被动性。再次,知识主体取代伦理主体,其根源在于“自我认识”取代“自我关怀” 的中心地位,而在种种关于自我的知识背后暗含着某种区别对待策略(分化实践),其实 质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严格区分,这就导致了权力主体。福柯的全部努力是要揭示伦理 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的真相。表面上的对立是伦理与知识,深层的冲突则是伦理 与权力。
福柯早期和中期集中探讨的是知识主体、权力主体的发生学,但这实际上也就是在揭 示伦理主体的沉默史。前两者是一致的,因为知识和权力在福柯那里不可分离,这不是 说知识产生权力,或者说权力带来知识,而是说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知识与权力不可分 割,关联在一起。启蒙理性让人们告别盲从和迷信,反对的是宗教和神学的权威。但是 它并没有让人们真正抵制服从。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由盲从演变为自觉服从,在自我 判断的基础上服从;二是服从的不是非理性而是理性,服从的是资产阶级秩序。于是, 现代性将唯理化(求知与求真)和社会化(规范与纪律)合二为一。唯理化使人在认识到自 己的权利的同时,让人们认同于某种所谓的普遍规则,由服从天国转而服从社会,而社 会化可以等同于这种唯理化,因为社会化就是对普遍理性秩序的认同,而抗拒理性则导 致对社会的离心和疏远。
我们不难明白,在人的这种唯理化和社会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不是纯粹知识,不是 关于自然、自在对象的知识,而是人文科学知识、人学意义上的知识,其中也包括一些 与人的命运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福柯着重分析的是生物学、经济学、 语言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精神分析学、犯罪学,这些学科都与人的某一维度 密切相关。通过分析近代知识和社会规范对人的建构,福柯揭示了主体的实质性含义: 主体是知识与文化的构成物,这就出现了主体化而非自在主体的问题。但这是一种让人 消失其生存的独特性和审美含义的主体化,激情和感受在知识和规范的包裹中丧失了活 力与生机。
揭示知识主体和权力主体如何产生,既暗中表明了伦理主体被淹没的历程,也为伦理- 审美主体的重新浮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略。到了晚期,福柯只不过把以前做的工作来 一个总结而已。所以他自己这样说到:“主体构成为我的研究的总主题。”(注:米歇 尔·福柯:《言与文》第4卷,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法文版,第222~223、697、70 6、703、223、786、172、731~732、732页。)当然,首先必须否定近代思想中的创造 性和支配性意义上的主体,通过分析,这种主体不过是被构造者和被支配者。有关主体 的哲学思考实际上以社会构成物意义上的被动个体来否定人的生存。于是,在近代以来 的思想中,主体只不过充当着某种功能。福柯要进行的大量工作是揭示主体的真相,也 即主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角色是如何形成的,“我不想排斥主体问题,我想界定 主体在话语多样性中所能够占据的位置和功能。”(注: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 》,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69年法文版,第261页。)主体在近代社会中归根到底扮演的是 资产阶级普遍理性秩序的载体的角色,理性规范和道德原则指导着他的一切言行。主体 从表面上看是积极的、主动的,但从无意识角度看,则意味着消极性、被动性。这乃是 福柯所揭示的知识维度和权力维度主体的实质。
在福柯晚期思想中,通过剥离,伦理生活与伦理主体终于浮出水面。从表面上看,重 视个体生存伦理问题似乎是福柯思想中出现的转向,而就其实质言,此乃福柯思想的出 发点和归宿。福柯力图探讨个人把他自己变成为主体的方式,希腊人的性受艺术可以为 我们提供某种启示。在古希腊时期,性与养生之道、家政管理、性爱技术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生活的艺术”、“行为的艺术”和“快感享用的艺术”。(注:米 歇尔·福柯:《性史卷三:快感的享用》,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84年法文版,第321页 。)古希腊无疑是生存或生命伦理的黄金时代,但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这一倾向被改 变了,出现了智性化倾向,知识主体及其暗含的权力主体取代了伦理主体。福柯力图通 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判,重新寻找到回归个体生存之路。
我们可以从“爱护你自己”或“关心你自己”原则与“知道你自己”原则之间的关系 看出古代人对个体生存的关注。在福柯看来,现代学者常常将“知”“行”分离,认为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强调的是德尔斐神庙中的“知道你自己”原则,而忽略了“爱护你自 己”原则的意义。而他自己的看法是:在希腊和罗马文本中,“应该认识你自己”的命 令总是与“应该爱护你自己”这一原则联系在一起,正是出于“爱护你自己”的需要, 德尔斐格言才得以运作和发挥作用。尽管柏拉图把“认识你自己”置于优先地位,古代 思想的总体倾向则是强调“爱护你自己”,强调“认识你自己”应该服从“爱护你自己 ”。(注:米歇尔·福柯:《言与文》第4卷,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法文版,第222 ~223、697、706、703、223、786、172、731~732、732页。)但是,在西方文化的历 史演进中,“知”“行”关系最终产生了转换。先是由于基督教的自我揭示技术,继而 是由于人文科学的诞生,知识主体取代了伦理主体的地位,“行”也就让位于“知”。 自我认识与自我解释逐渐占据核心地位,继而产生了自我揭示与自我抛弃之间的关系。 福柯这样来表述基督教的自我技术的实质:“我们越是发现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我们 越是应该抛弃我们自己;而我们越是愿意抛弃我们自己,我们越是有必要将我们自己的 真实置于光明之中。真理的表述和放弃实在的这一螺旋乃是基督教所实践的自我技术的 核心。”(注:米歇尔·福柯:《言与文》第4卷,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法文版,第 222~223、697、706、703、223、786、172、731~732、732页。)在以后的岁月中,性 欲逐渐成为认识的对象,性艺术开始让位于性科学。现代人文科学不过是这种自我揭示 技术的科学化。西方文化于是完成了由伦理自我向知识自我的转换,审美生存也就让位 于求知和求真。
在福柯看来,基督教道德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古代道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从 古代到基督教,我们从实际上是寻求个人伦理的道德过渡到作为对法则体系的服从的道 德。”(注:米歇尔·福柯:《言与文》第4卷,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法文版,第22 2~223、697、706、703、223、786、172、731~732、732页。)个人体验的道德向规范 道德的转化与知识主体的形成互相促进,是知识与权力相互作用的产物,现代性进程则 是这种转化的强化。不过,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个体应该从普遍性 和规范的约束中摆脱出来,并且恢复其自由的、伦理的、审美的个体生存。福柯力图在 当代西方文化中探寻这一趋势,而古希腊和罗马(甚至包括早期基督教)为他提供了某种 参照。他说道:“如果说我对古代感兴趣的话,这是因为,由于整个一系列的原因,作 为对法则规范的服从的道德观念现在正趋消失,甚至已经消失。对一种生存美学的道德 的寻求回应着也应该回应这种道德的缺失。”(注:米歇尔·福柯:《言与文》第4卷, 法国伽利玛出版社1994年法文版,第222~223、697、706、703、223、786、172、731 ~732、732页。)显然,我们可以同意德勒兹的说法,福柯并不主张回到古希腊去,而 是说,谱系的清理可以为我们的未来生存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针对现在并且为 了抵抗现在而思考过去,这不是为了回归而是‘为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尼采),也即通 过使过去活跃起来并使现在成为外部的,以便某种新的东西会最终产生,以便思考会获 得思想。思想思考它自己的历史(过去),但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摆脱它正思考的(现在), 并能够最终达到‘以另外的方式思考’(将来)。”(注:吉尔·德勒兹:《福柯》,美 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文版,第88、132、92、106、115、101、96、110、11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