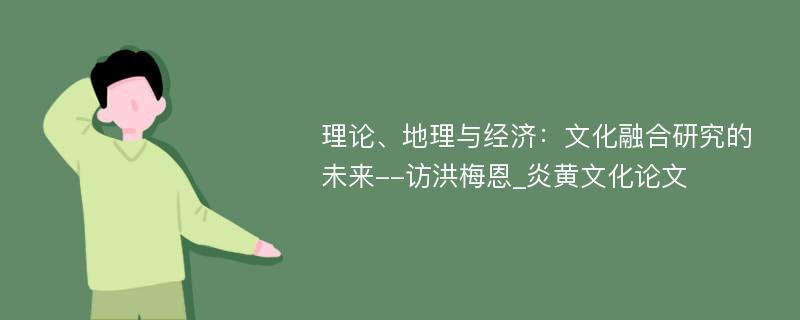
理论、地缘与经济:走向整合的文化研究之未来——洪美恩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访谈录论文,走向论文,理论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访人:洪美恩 西悉尼大学教授,文化研究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 采访人:王毅 西澳大学副教授,博士师从洪美恩教授 时间:2014年7月10日 地点:澳大利亚西澳大学 王毅:您的《观看“达拉斯”》(Watching Dallas: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一书出版快30年了。 洪美恩:我知道,很长时间了! 王毅:在您看来,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现在发展趋势如何? 洪美恩:澳大利亚,也包括国际上吗? 王毅:是的。 洪美恩:哦,好吧。这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我认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因为它相当难界定,正如你所知,这是一个广泛的领域——跨学科,因此有的人研究传媒,有的专注青年文化,还有多元文化等,文化研究的研究者可以侧重于很多不同的问题。文化研究的扩张性从一开始就存在,它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并且现今仍是如此。是什么把人们聚在一起进入文化研究呢?我认为思考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不仅仅思考一个特定的领域,而是要进入更广博的语境,无论是经济语境、意识形态语境还是社会语境。比如说,无论研究媒体或研究观众,某种意义上可以发现过去30年中,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观众研究的领域。 王毅:对,比如粉丝文化…… 洪美恩:粉丝文化或诸如此类的研究。文化研究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跟许多其他的领域一样,它于是自成一家,成了一个专门领域。青年文化和多元文化亦是如此。如果研究者在某一个领域钻研越深,越容易使他们独立于其他领域,这实在令人惋惜。因为我认为文化研究作为整体在对待所有不同问题时,理想的状况是,不同文化领域之间应有更多的交织与对话。例如,对媒体感兴趣的人中很多只参加与媒体有关的会议,而不关心其他的领域。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文化研究的碎片化正在澳大利亚发生,国际上亦如此。就像现在你参加的这次会议,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文化研究会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相互间却无交流。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应该做得更好些。我仍觉得虽然文化在扩展,社会在扩大,但还是一个整体,所有这些事情也处于一体化……我常想失去了宏观的视野,我们所以感到羞愧,对吗?但另一方面你也看到,在文化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话语分析、定性研究及定性的民族志访谈,等等。这些我30多年前研究的时候尚不流行,甚至不被看好。当时的主流方法是大量的定量分析。 王毅:需要数据来证明一切。 洪美恩:数据,是的。所以我觉得话语分析已被更多人接受,不仅仅是在文化研究,还有其他的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某些方面文化研究方法已成为主流,这很有意思。但有时候却不能针对性地指出文化研究的影响,你肯定注意到人们很流利地使用话语一词,它现在是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正常部分。所以我认为文化构建的整个思想现在得到相当普遍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文化研究作为关键学科在澳大利亚影响了许多其他学科。但文化研究本身还很难定义,因为它如此分散。 王毅:如果我们回头看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自英国的第一代学者,有些人现在开始退休了。你认为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或年轻的研究人员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吗? 洪美恩:哦,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的。我认为差异之一……在第一代中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研究学者,尽管他们的第一学位并非来自文化研究,通常来自另一学科如文学、传媒、历史、人类学等。这些人首先用首个学位作为起点,然后转向文化研究。现在情况变了。很多情况下文化研究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年轻人从一开始便进入文化研究,例如在默多克大学,多年前其传媒研究实际上有很强的文化研究的影响。我的首个学位是心理学。我不喜欢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所以最终兴趣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更多的学科交叉性;不仅仅是文化研究,而且还有文学研究、符号学等。我认为年青一代很少意识到过去的文化研究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只知道澳大利亚老一代的文化研究者,如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或约翰·哈特利(John Hardly),几乎都认为了解其他学科相当重要;否则,你只知道文化研究。因此有人认为文化研究最好作为研究生学位而不是本科学位,这样在某些方面文化研究会做得更好。最好的方法是首先要了解人类学、文学和语言学,当然还有传媒,即对多个学科的了解。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变化,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我认为因为文化研究现在已经变得更为主流,很多人将它作为一种合情合理的选择。然而对第一代研究者来说,当时做文化研究是一种兴奋,因为它新颖而与众不同,感觉这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和学术成果。而现在我想做文化研究则普通得多。 王毅:斯图亚特·霍尔去世以后,不少人担心文化研究的未来趋势。在中国有不少文章发表。我阅读了您在《连续统一:文化和媒体研究》2012年第6期的文章,您认为文化研究变得太复杂了。为什么呢? 洪美恩:嗯,我其实是批判文化研究中的某些趋势。我认为现在对文化研究学者来说重要的是思考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多,就是说如何与学术界以外的人接触,我认为这很重要。为什么这点对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很难?就是因为文化研究人士看复杂事物时有一种倾向,喜欢说“我们想要构建复杂性”。我的经验是当你跟圈外人谈某事的时候,他们不认为是复杂的。他们只想知道如何处理复杂性,要找到……不完全是解决的办法,因为寻找解决办法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找到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通过了解其复杂性,我们希望可以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蛛丝马迹,而不只是囿于它是否复杂的问题上。但可以以某种方式,通过一些战略性的简化方式处理。你需要做出一些选择。任何事情……当你的事情太复杂时可以令人感到瘫痪。我知道一些博士研究生,他们会变得注意点非常集中,“哦,但这是我所关注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此复杂,他们变得越来越被问题的复杂性所困。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些明确的结论,以及前进道路上有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告诉外面的世界关于复杂性现实,但我们还需要找到处理它的方式。为什么我认为这点很重要?因为世界已经改变,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时代。我认为作为学者,包括文化研究,我们的使命是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一些清晰性,并不仅仅是提出一些通俗的解决问题的结论,而是为人们的困难找到交流的方式,以及让人们如何找到实际上与困难共存的方法。 王毅:中国学术界有些关于文化研究理论发展的困惑。2004年德里达去世后似乎理论大门也关闭了。最近有什么新理论吗? 洪美恩:我知道有一些书籍和作者,像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现在非常受欢迎。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他。有趣的是,这个法国哲学家认为社会是一种装配的整体,就是说社会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而是许多不同元素的组合或集合,而这些元素相互间不一定适合,或根本没必要装配。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值得关注。它反映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真实体验,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不适合的东西。 王毅:我读过他的《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洪美恩: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组合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我认为环境正成为文化研究一个重要的课题。 王毅:是的,环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理论是什么? 洪美恩:理论上环境也同其他领域一样涉及布鲁诺·拉图尔。他谈论的自然文化、自然的关系,自然与文化总是相互关联。我认为理论上强调布鲁诺·拉图尔,还因为他谈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这就是我能看到的趋势之一。不过纯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王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洪美恩:是吗?你可以再进一步吗? 王毅:我相信文化研究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很多学者和学生在走出旧研究体系时,比如哲学、文学、社会学或其他领域,突然发现文化研究是一个新途径。现在他们走到这个阶段却发现理论到了尽头。我们可以没有理论继续前行吗?但你说纯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听起来就像曾说过的高雅文化。 洪美恩:是啊,就像我们曾说的像拉康、福柯、德里达…… 王毅:他们是昨日的英雄…… 洪美恩:是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老的理论仍然是影响,但影响更多是在一些诸如经验或体验方面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理论有更好的指导性意义。但是问题本身比理论更重要,你明白吗? 王毅:您说了一个很好的观点,我试着来理解。要是有一个很好的课题,没有理论如何进行呢? 洪美恩:对啊,确切地说,许多现有理论已被大量使用,或者混合使用,所以颇有些理论折中主义的味道。过去我们谈论高深的理论,很抽象。我认为现在理论更多的是一种语境,以及更多低层次的理论。 王毅:但是布鲁诺·拉图尔的理论…… 洪美恩:哦,很难!但他是唯一的一个。为什么他受欢迎,因为仍有很多学生热爱高深的理论,真的,尤其当他们有哲学背景。哲学家的训练就是与相当抽象的概念打交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喜欢理论。但我认为应该更多强调应用理论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王毅:应用理论?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洪美恩:我想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供了大量的应用理论。 王毅:如果一个博士研究生做开题报告,“你的理论框架是什么”的问题往往不容易回答。应用理论似乎是不够的。 洪美恩:不,那也是一种理论……你把理论看得更像是一种……你使用理论元素来理解某些问题,有时你使用……或许有些想法,有时你也使用一些其他理论,将其组合在一起使用。 王毅:您的意思是类似话语分析也是一种理论吗? 洪美恩:是啊,但我们说话语分析更像是一种方法。斯图亚特·霍尔后期没再写理论。他当时更关注英国社会的现实,比如黑人艺术家、多元文化主义等,所以当他谈到各种现实社会问题时,他为如何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理论工具包。但是通常是含蓄的,而不是说“我使用了这种或那种理论”。实际上,他含蓄地利用这些理论概念解读各种问题。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甚至不必提及理论。因为更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本身作为一种话语,而你在发展这种话语。例如,当你谈论文化研究中通常的身份认同时,去挑战任何本质主义的假设,这就是一个理论的起点,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对现实的评判。我认为它与民族国家的研究类似。某种意义上,我们这次的亚洲研究会议中谈到关于中国、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很大意义上是一个假定的统一实体,而这正是解构主义的用武之地。所以理论概念方面,不一定会明确地阻碍我们对现实理解的有效性。 王毅:您觉得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的未来如何?名称是否重要? 洪美恩:名称重要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不知道名称是否重要,它取决于我们如何考虑问题。就目前来说,名称仍旧重要。因为文化研究现在公认有自己的领域,当你申请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ustralia Research Council)的研究基金时,你可以将自己的领域放在文化研究的代码中,说明我的领域是文化研究。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文化研究的合法地位。我认为这说明在某些方面,很显然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相当成功地得到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认可,也许,被使用? 王毅:还需要游说政府,得到更多的研究资金? 洪美恩:就是这类事,绝对的。需要展示文化研究的相关性。原因之一就是文化研究的确关注当下的问题。这要追溯到文化研究的源头。我认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仍然对大背景感兴趣,所以不只谈论非常专业的问题,当然很多个人会这么做。关键是我们也了解社会的总趋势,对社会各界的相互影响有深刻认识。比如说不了解消费,不了解资本主义也就不了解环境的问题。我认为这很重要。 王毅:您喝点茶。让我们回到中国。您的《拼死寻观众》(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s)一书在中国很受欢迎。 洪美恩:是吗? 王毅:是的。中国电视台的收视率无处不在。因为收视率是电视台的命脉,收视率带来的金钱是电视台赖以生存的保障。专家和学者的评论与关注不少,电视行业中无人理会他们。当年您写这本书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观众研究如此重要? 洪美恩:嗯,为什么如此重要……好,开始的时候我想观众研究很重要,因为人们与媒体协商的方式,就是观众研究描述的方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进行活动,当代社会如何构造日常生活,我们在当代社会中如何成为消费者,以及通过媒体我们如何发展与其他社会的联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观众是一个理解文化语境的好位置。而另一方面,也如你所说,电视工业认为节目越被观看,业界就越赚钱,这点是由收视率来衡量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观众与媒体的日常协商,另一方面是媒体对观众的控制。当然不是直接的,因为无法做到,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收视率高的节目。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媒体和观众之间的持续斗争。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解观众与传媒的视角。传媒产业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商业化的媒体,因为需要赚钱而只强调最高收视率。有时候节目仍然可以非常成功和令人愉快,但制作更为困难。严肃的节目对媒体来说更不太可能。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我不清楚中国是否有同样的问题。 王毅:在中国这一问题是,正如您所说,当观众与传媒界商议时,知识分子其实是缺席的。我的意思是他们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所以没人听他们的声音,他们基本上不存在。 洪美恩:在我的第一本书《观看“达拉斯”》中,我谈到亚文化的意识形态。“达拉斯”被知识分子所唾弃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节目质量低下,如此等等。中国知识分子也一样吗? 王毅:我不清楚。有一次在中国,我看了一个电视慈善节目。赠予人始终是镁光灯的焦点,而被捐赠者的出镜拍得非常悲戚与“感恩”。在我看来这不对头。节目展现的是“我们”与“他者”的两种不同身份。知识分子在哪里?能否在文化研究中找到某种可用的东西? 洪美恩:我不认为现在有很多……研究某个节目已经不太重要了。我的意思是,很多人仍然在做这类研究,就是观众看好的节目。在我看来这就是我说的观众研究已经自成领域。我认为研究粉丝或观众时,最重要的是考虑广泛的行业语境,广泛的意识形态语境……我不太了解一些新研究,例如关于社交媒体…… 王毅:年轻人越来越多聚集于社交媒体。 洪美恩:但这是很有趣的研究,比如“民族主义在中国”,这样,用亲密的……我认为这就是观众研究有趣的地方。在过去我们谈论有关积极的观众。观众研究的假设是我们需要得到观众的积极主体,得到其意义的生产作为创造意义的学科。现在有互联网,社交媒体参与之类的东西已无法控制! 王毅:社交媒体是完全不同的。使用它的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洪美恩:就是啊!所谓“产消合一者”(Prosumer)。 王毅:是的。 洪美恩:那么这意味着整个有关积极观众的主张如今有了非常不同的意义。因为现在观众总是活跃的,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一种可见的方式,就像在看电视的同时使用推特,用某种方式调换节目。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年纪大的人来说,比如我,我们不是来自同一时代…… 王毅:您认为他们超出了文化研究的范畴吗? 洪美恩:可以思考文化研究范式是否能够解决所有21世纪的进展问题。我认为社交媒体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已经提到的另一个领域是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非常重要。再一个重要领域是地缘政治的变化。 王毅:族裔散居呢? 洪美恩:族裔散居也是,包括中国作为一个强大实体的崛起。从亚洲总体来看,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一点点西方的衰落。 王毅:地缘政治吗? 洪美恩:对,地缘政治。我认为那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我在思考何种程度上文化研究可以参与其中。我真的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也发现自己因此采用其他的学科如国际关系、地理学等的资料。这就是为什么我仍做文化研究。过去我使用更多的人类学资料,但现在我更多的是用地理学。那么也许你可以说,我刚想到的,文化研究在研究中承担的正确风险之一是它实际上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取决于什么问题有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哪个学科有必要参与。有段时间文化研究对于经济学来说不是那么感兴趣,但现在很多人说我们需要关注更多经济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一点很好,因为不关注经济方面我的研究就会招来批评。无论在《拼死寻观众》或传媒工业的研究中,都要认真将经济当一回事,因为收视率是基本的经济手段。 王毅:很有趣。上周我读了一本书,叫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21st Century)。可我跟经济学界的一些人探讨时,有的说“毫无新意”,有的说这是给一般读者看的。在我看来,它至少讨论了马克思主义、贫富差距以及未来的问题。 洪美恩:哦,是的,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tty)写的。在美国,关于此书有很多辩论。因为贫富差距拉大……因为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的书如此轰动,将问题带上了议事日程。因此,我认为这是一名学者应有的方式,对论争进行实质性的影响将是非常有趣的。 王毅:我读它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问题…… 洪美恩:太对了!我不知道这样一本书……不知道他的分析如何适用于中国,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研究这些问题了。 王毅:有关文化研究应以何种方式更多地转向经济? 洪美恩:这是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其实经济学如今如此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有经济价值的色彩。在如何与亚洲接触的讨论中,不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讨论,同时也讨论文化和艺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等。虽然它现在不能产生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实际上它发生在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流行的期间。但文化研究如此,也许它本身在并行发展中成为大系统,人们意识到实际上不得不与它接触。 王毅: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文化研究在未来20-30年会如何? 洪美恩:我不知道,那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王毅:就说在澳大利亚。 洪美恩:在澳大利亚,我想很难说。因为它取决于谁将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者。我希望未来的20-30年文化研究仍旧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关注社会的重要问题。从个人来说,我们将要看到未来的20-30年世界的许多变化,所以文化研究能够以某种方式发展和变化,提供了解这些变化的话语很重要,因为这些变化意味着很多人会感到不安。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文化研究能参与到这些问题中来。 王毅:如果我们现在能看到未来,您能否给我一个例子,一个个案研究,就是您或您的研究生研究的澳大利亚典型问题。 洪美恩:很难。好。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当前项目。例如我的项目之一是关于悉尼唐人街的研究。你听说过吗?这是一个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资助的项目。我跟同事一起探索悉尼唐人街在过去50年是如何变化的,重点是过去的10年。其实唐人街的历史很有趣,因为它说明了某种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过去唐人街是边缘化的,是受人鄙视的社区,即使从19世纪淘金热以来就存在。在白澳政策下一部分或一群华人过着相当边缘化的生活,唐人街使他们得到一种归属感。现在唐人街是一个民族的飞地,与过去所说的唐人街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多的是跨国的枢纽,人群的流动,不同的文化、成就一个跨国空间,链接到亚洲,不仅仅中国。通过研究唐人街的这些变化,表明它反映了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变化。我个人很满意这个项目。我们的方法是我们谈了很多…… 王毅:历史吗? 洪美恩:不。我的意思是历史已存在,但人们如何应对变化更有意思。很多老一辈的华人过去居住在唐人街……他们仍然在那里,现在有70岁到75岁。跟他们谈论他们眼中的变化,谈论他们的记忆,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很重要。我们也谈地产代理商、餐馆老板,以及现在很多人到中国去工作。所以研究地理是很重要的。他们在这里只是因为这是一个空间,但是空间的边界正在改变,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这个地区。现在的悉尼唐人街不像过去那么熟悉了。 王毅:真的吗? 洪美恩:在该地区有很多学生,当然悉尼科技大学离那儿不远。学生人口增加产生大量的青年文化。不过人口的流动性也很大,因为学生不会住太久。通常几年便又有一群新学生到来。这就是为什么地区可以实际上变得非常充满活力。我们发现有相当多的学生最终开餐馆,或开商店——一些从大陆来的学生,他们的父母给他们钱来开餐馆。 王毅:上个周末我去一家餐馆,就是我的学生在这里开的。父母说如果餐厅能收支平衡就很好;如果不能,不要亏太多;如果赚钱,就是好消息。 洪美恩:他们一定是非常有钱的父母。 王毅:是的。 洪美恩:我非常想做的下一个项目是……现在我很感兴趣中国对澳大利亚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包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你知道,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我认为澳大利亚太专注于经济的整体,正如你所知,关于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的话语是非常片面的,都集中在矿业。 王毅:正是。 洪美恩:(笑)但是我觉得提出一种主观的维度、文化的维度要有趣得多。 王毅:文化的维度?我几个月前去了墨尔本,发现当地居民抗议中国人把他们地区的房价抬高了。中国人不明白,有什么不对?我们让你们的房子更值钱了。但是那些抗议的人说他们是为“孩子们的未来”。这样涨下去下一代就买不起房子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像您所说的中国人来这里带来很多的钱,但有时并不会使社会更和谐。 洪美恩:我注意到这类事情的一个方面,不清楚你是怎么想的,就是华裔在这方面非常不敏感。因为华裔已经不再边缘化,他们在澳大利亚开始变成相当强大的一个群体,应该对如何居住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更好的协商。这也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尤其是对那些能讲汉语的人。 王毅:我在想因为您在做悉尼唐人街的研究,您是否也研究悉尼其他地区的人群,或者悉尼唐人街本身的发展? 洪美恩:呃,目前只是唐人街,但我认为未来会更进一步……因为实际上唐人街已不再是华人的了。现在韩国人,还有你知道这么多不同的中国侨民,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所以唐人街更多像一个泛亚洲地区,有摩擦也有充满活力的身份认同。 王毅:但唐人街就像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是吗?如果谈论地理或地区,唐人街如何理解?那里有什么文化吗?我仍然非常感兴趣您在研究中寻找的东西。 洪美恩:悉尼市非常热衷于将唐人街保持为一个单独的区域,所以有一点充满异国情调。 王毅:它的中国园林。 洪美恩:对。还有一些传统的商店、主题老旧的中国餐馆、一些传统家族的住宅。但这些只是唐人街的一小部分。其他部分更现代化,居住的人群也不同,比如说有几个非常好的餐馆! 王毅:所以唐人街只是一个名字,但它不意味着中国! 洪美恩:的确,有趣的是世界各地都有唐人街。 王毅:但是悉尼的唐人街相当知名。 洪美恩:是啊,三藩市、洛杉矶、纽约都有唐人街…… 王毅:有的是最糟糕的(笑)。 洪美恩:是有最糟糕的。但它们的确各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