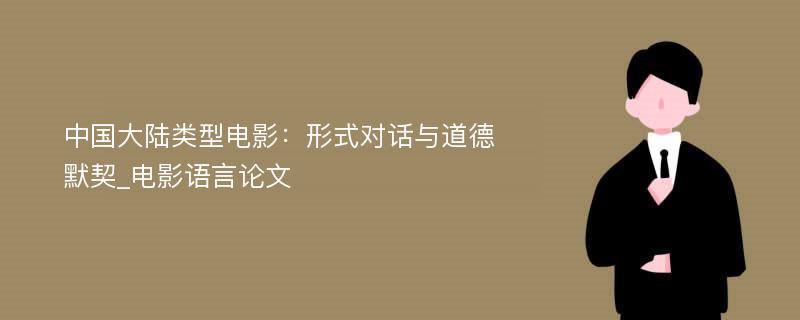
中国大陆类型片:形式对话与道德默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陆论文,默契论文,道德论文,形式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中国大陆电影仍然维持着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的三分格局,它们分别代表着三种话语:占据权威地位的主导文化、显现大众心理的大众文化、标示高雅趣味的精英文化。主旋律电影在政策资源、发行档期、院线安排、作品宣传等方面还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尽管如此,中国大陆商业电影也在艺术话语、商业票房等方面做出了持续探索,有了显然的、成绩喜人的发展。在近年来的商业电影制作中,类型化仍然是创作者和制片人最重要的艺术方法和市场策略。在取得较好市场成绩并引起文化讨论的影片中,类型电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简单列举就可以看到:喜剧《疯狂的石头》、《大笑江湖》、《三枪拍案惊奇》、《大内密探零零狗》、《决战刹马镇》,侦探悬疑剧《风声》,武打片《投名状》、《剑雨》、《武侠》,警匪片《窃听风暴》,爱情片《山楂树之恋》、《杜拉拉升职记》。我们还看到,这些中国大陆出品的类型片也时常使用融合类型的策略,例如融合了喜剧和武打元素的《大笑江湖》、《刀见笑》,爱情片和喜剧元素融合使用的《非诚勿扰》、《爱情呼叫转移》,使用惊悚片叙事模式来营造恐怖效果的《荒村客栈》、《孤岛惊魂》。2010年,十分富于个人色彩的动作、喜剧融合类型片《让子弹飞》也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并引起了对其文化意义的讨论。笔者认为,于此时对大陆类型电影创作的一些艺术方法和底层价值观做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类型作品与以往类型片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抄袭,什么是一种艺术对话?类型片作者过于强烈的创新冲动是否影响了作品与观众的互动交流?笔者还试图强调,在中国大陆类型片创作中还有一个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类型片的底层到底是否具有一个坚实的价值观?创作者对基本价值观的认识是否会对电影叙事、观众认同有所影响?
一、对话关系:类型沿革与观众熟知
类型片是艺术模式超越题材的作品,也是主题隐藏在类型之中的作品。类型片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对价值观的判断隐喻性地蕴含在故事讲述中,而不是像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那样以强化的符号来进行“宣传鼓动”的。观众在观赏类型电影时首先看到的是一种艺术趣味与深层心理情结的组合搭配。
“作者电影”是许多作者和研究者一直偏爱使用和强调的一个概念。一些论者不时表现出鄙视商业电影经济模式和语法规范围的倾向,有时更暗含着一种艺术电影等级更高的观点。就笔者的阅读经验,法国《电影手册》谈论“作者电影”、“作者导演”这一概念首先是指那些在商业电影的规范中工作,在类型电影话语系统内进行创作而又能保持某种“作者的签名”的导演。美国电影理论家达德利·安德鲁这样认识类型电影艺术电影的关系:“首先,类型电影价值的作用抵消了妄自尊大的观念电影的尊崇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类型研究和作者论批评携起手来,因为两种方法都在风格中予以真实的价值,这是电影独有的方式,它是通过影像来形成思想的。”①
类型模式其实是一种话语系统,对这种共同话语系统的广泛熟知使作者与观众有了一个共同的游戏场,有了一个对话、回馈、交流、评说的公共舞台。要拍类型片,作者就必须抛弃艺术电影的自我欣赏和主旋律电影讲究导向和宣传功能的教化美学。
在研究类型电影的美学思考中,研究者使用了语言学的一些思路和结构分析的方法。类型电影研究者托马斯·沙茨借用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对于“语法”和“话语”的辨析来研究电影类型的规则与具体电影作品对这种规则的创造性使用。②基于对当下中国大陆类型电影创作和评论、研究的文化氛围的观察,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掌握类型语言系统,在熟知的基础上形成对话,在尊重和建立商业机制的基础上营造作者风格。也是基于对当下中国商业电影创作、研究现状的思考,笔者希望在本文中提出对于“对话关系”的强调。俄罗斯美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注重研究话语与叙事的关系,文本内部的多声部话语的关系、文学的对话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巴赫金那里,“所谓对话是‘两种并列的文本、陈述发生了一种特殊的语义关系,我们称之为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就是交际中所有话语的语义关系’”。③从巴赫金的论述中,可以从中引申出对于类型研究的重要启示。对话理论引导我们研究类型电影的作者如何处理独创性与对话先前作者的关系。在巴赫金看来,“每一部作品都拥有一套任何人都能理解的符号系统,一种‘语言’(艺术语言?)。在作品中,所有一切可重复、再生、反复和复制的东西与其相符,甚至还有一些作品之外所具有的东西。但同时,每一篇文章(作为阐述)又表示某种个体的、独一无二的和不能反复的东西,这就是它的全部意思(它的目的,为什么要创作它)”。④在这里,“一套任何人都能理解的符号系统”可以看作是在以往创作、观赏中形成的那一套类型模式,而“某种个体的、独一无二的和不能反复的东西”就是具体作者在具体作品中完成的某种重复中的创新,看似再生的新颖。类型片讲究的是与以往形成的一些既定话语模式对话,这种对话建立在作者和观众熟悉这一话语系统的基础上。在徐克、李惠民的《新龙门客栈》相对于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在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相对于英国导演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一类文本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沿用和变形的对话关系。
在创作访谈和电影评论中,我们时常看到向某某导演、某某作品致敬这样的表述。所谓致敬,其实就是有意识地与以往作品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在这种沿用、再造中,作者往往会追求一种变形处理来改变原有的意义和形式趣味。由于是对已有的形式进行处理,作者会使用观众熟知的戏剧结构以及镜语、台词、人物动作,观众也会在对此中来评价这种带有陌生化的重复,会品味这种在使用陈规、沿用旧模式中的创意和机巧设计。在周星驰的《功夫》中,我们看到许多这种使用旧桥段、熟悉场景和武侠小说的情节和功夫描写,该片向多部影片致敬,但是都有所翻新。在这种看似重复、致敬的游戏中,《功夫》完成了一种对话基础上的创新,很好地完成了这部作品的核心创意:一个一直想学坏的无能小混混不断发现自我,在功夫能力和人生目标方面升华成一个惩恶扬善的非凡英雄。在吴宇森的《英雄本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对以往作品的对话性使用。吴宇森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座中曾经提到法国导演梅尔维尔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在《英雄本色》中,我们看到宋子豪在出狱后大雨滂沱的夜色中与弟弟宋子杰冲突打斗,那场戏明显可以能看到梅尔维尔黑色电影视觉风格的影响。
在类型电影的语法规范和商业规律中,对演员的使用也讲究一种类型化,讲究观众以往对这个演员的熟知和某种性格认同。在冯小刚导演拍摄《夜宴》时,负责海外发行的制片人就要求“章子怡必须有一些动作”。这就是基于海外观众对于章子怡这个演员在《卧虎藏龙》中形成的熟知,基于她已经形成的核心性格魅力。在一则美国信用卡的广告中,章子怡就是以一个成猛、刚劲的武打明星出现。于是冯小刚设计了一段吴彦祖回到宫里和章子怡饰演的青女对打练武来回忆他们两人青梅竹马时光。那套动作没有致命动作,而是一种舞蹈性的游戏,以此来点明他们两人的恋爱关系。⑤
《风声》将几个正面主人公设计成共产党人以形成主旋律呼应。本片变形化地从相反方向使用了侦探推理的叙事模式,故事主线是通过逻辑推理查出“老鬼”,只不过在本片中是追查一个好人。让观众揪心的剧作设计是,如果这个好人(老鬼)被查出而不能送出警报,就有人会丧失生命。本片的重要艺术设计是在故事情节中加进了酷刑展示。影片的血腥和酷刑场景引起了一些讨论和质疑。如果按照商业电影的规律来分析,作者这个明确而清晰的设计恰恰形成了宣传的炒作点和观赏中的重要兴趣点。类型电影不避讳对人类隐秘欲望的承认和展示,时常会对人类阴暗心理有所触摸。通过这种艺术活动中的处理和触摸,通过欲望发扬和受到训诫的二元对立,商业电影其实是在建立一种内在心理秩序。在类型电影的观赏和评说活动中,人性是被反思的对象,这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给人类提出的“认识你自己”这一理性任务的当代演示。但是《风声》对于类型模式也有一种背离,结尾周迅饰演的老鬼是自己说出来的。就叙事来说,这是违反类型法则的,违反了侦探推理类型模式的游戏规则。侦探片推理类型中,一般是有一个洞察世态人心而又通晓逻辑的高人来为剧中人(其实是给观众)用坚实的逻辑推理指出那个竭力隐蔽自己的人。
如果我们把目光扩展到华语电影更广阔的视野,有些香港的电影创作者在类型电影的创作方面明显有着更清晰的观念和更圆熟的艺术处理。就处理类型惯例与创新的关系而言,香港导演杜琪峰创造了十分成功的案例。由杜琪峰监制、游达志导演的《暗花》在叙事结构方面娴熟地使用和改写了强盗片模式,营造了形式精致、优美的黑色强盗片文本。片中梁朝伟饰演的阿深虽然身份是警察,而其价值观、行为目标和他的自我身份定位其实是一个黑道人物。而这个黑道人物的最高目的又是维护澳门的秩序,避免一场帮派之间的血拼和杀戮。就叙事模式而言,《暗花》的故事结构与美国导演大卫·芬奇的《七宗罪》有着隐隐约约、十分巧妙的对话关系:主人公用尽心机,但一切都在邪恶对手的掌控之中,他们拼命挣扎、追寻,却只是走向对手所设定的命定结局中。杜琪峰的《黑社会》、《放逐》等作品也让笔者看到他与科恩兄弟、赛尔乔·莱昂内作品的创造性对话,形成了精当的叙事肌理和熟悉而又有所翻新的镜语。
二、中国大陆类型片创作的创新情结与反语言冲动
同时,笔者也观察到不少中国大陆涉足类型电影的创作者有着过分的创新追求,显示出较强烈的反语言冲动。由于创作者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商业机制不够完美的电影行业运作,他们可以用一种反语言策略来凸显作者个性,用个人化来作为展示才华的方法。但是,纵观世界范围内的类型电影创作,作者们首先注意的是对以往类型模式的掌握,在与作品对话中寻求新意、在观众熟知的套路中营造个人风格。进行类型电影创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在成规基础上寻求创新和突破。“一部影片内在的价值在于它显现出的常规(convention)与创见(invention)之间的具体比率。在于某一类型的要求和应用这一类型的作者的独创性和世界观。既然类型的规律明确是受人公开检验的,那么这些规律便可以从任何被研究的影片中分解出来,留出作者的贡献供人研究和鉴赏。”⑥这就是说,在进行类型电影创作时,创新要求作者具备娴熟的类型掌控能力。创新不应该是另起炉灶的颠覆和革命,而是在对艺术语言规范稍做偏离的“陌生化”设计。⑦同时,一般容易忽视的是,类型欣赏也要求观众对一部影片的语言趣味、类型模式有所应和,形成对话,形成游戏。从当下中国大陆一些类型电影作品笔者看到,一些作者的反语言冲动导致一些类型片出现了明显的反常规语法,在观众表现出不理解和观赏时的疏离感时,有些作者往往自认为是一种创新和突破。
《刀见笑》以武打片作为类型定位,但是,其文本中的元素搭配和叙事方法过于远离武打片的类型传统。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过多的独特怪异的人物造型,较为随意的故事走向。这当然显示了导演的想象力和独特艺术趣味,但是观众却未能得到熟知的武打片传统中那些可以期待的动作美感和故事趣味。就视觉元素而言,本片使用了类似罗德里格斯的《罪恶之城》那种黑灰的色调,这使得影片的色彩基调很灰暗。对过于冗杂的元素和影片的视觉处理,许多观众和电影从业人士有所质疑。2011年3月17日《信息时报》报道:“把动画、新闻、游戏等各种体裁的呈现方式混在一起,用在《刀见笑》这部主旨不是恶搞的电影中有些突兀……《刀见笑》的造型‘脏’惹来了最多争议。”作者以“先锋武侠喜剧”作为广告语,看来,作者追求先锋的创新冲动压倒了他对于类型规律的探寻。
在冯小刚的《夜宴》中也有反语言的笔触,厉帝看到自己面前那一番刀光剑影的生死争斗,他忽然自己拿过半杯毒酒把它给喝下去了。这是对基本剧作模式的忽视。冯小刚在关于《夜宴》的访谈中说道,这是饰演厉帝的演员葛优临时想到的主意,可是根据一般的商业电影剧作语法,一个人物自杀这么大的动作应该服从于整体的人物定位、人物走向设计,应该放在整体剧作结构中加以考虑。在《夜宴》的结尾,还有一处这类反叙事语法的笔触: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把匕首,刺死了章子怡饰演的婉后。冯小刚后来提到,在意大利很多媒体希望导演告诉他们谁杀了章子怡,他回答说是秘密。⑧
拍摄类型电影然而却做成了一部元素混杂的非类型片的较典型案例是由中国大陆星美集团等公司出品,陈可辛导演的《武侠》。
《武侠》使用的演员、本片的片名和公映前所做的宣传都定位于武打片,这都是与观众签署的不成文合同。但是,导演显然过分得意于自己的游戏而未能遵守这一默契。作为一部武打片,竟然只设计了动作明星甄子丹三场武戏,第一场打完两个通缉犯后,在随后漫长的剧情中观众都看不到他的动作戏。导演最后安排让他连打两场结束。这种武打场面的分配比例显然违反了动作片的模式。《武侠》的最大问题是故事结构随意游走,枝杈太多,开端和发展的大部分,刘金喜没有麻烦。就故事看,他真正怕的是七十二地煞。但在影片叙事中,这个威胁没有建立起来。讲故事是一种在时间顺序中设计因果关系的艺术,要这样看,徐百九调查勾连出县衙的小官吏到刘金喜义父那里告密,这种偶然的阴错阳差就不是戏,因为这不是人物动机的冲突。结尾时让雷电把反面的一号邪恶人物劈死,与武打类型的叙事传统风马牛不相及,被许多网友戏称为“雷人”。今天的创作者应该承认,从《火烧红莲寺》开始,中国武打片已经有了近百年的拍摄历史,在这过程中观众和作者历经多方探索,经过反复的艺术对话,是形成了一套默契和章法的。在就《武侠》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陈可辛表示这是自己的创新游戏:“这部戏就是一部游戏之作,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剧作结构)可以割裂,不甘心安于传统。”⑨显然,《武侠》的作者对武侠片近百年历史中与观众形成的那点默契和游戏规则显出某种蔑视或者无知。⑩
三、类型片:底层伦理与道德默契
在中国大陆类型片创作中,反语言冲动以及对类型模式的生疏、忽视还表现在对电影内在的伦理价值观的模糊、悬置甚至错误走向上。在当下电影文本中,价值判断混乱或叙事中善恶判断的虚空是常见现象,这一倾向构成了对中国大陆类型片创作最大的损害,也是当前电影创作的最大瓶颈。分析这种文化氛围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在此只考察这种倾向在类型电影文本中的呈现。
在笔者上文所强调的“对话”关系中,基本伦理的认同和统一是实现对话的前提条件。巴赫金给对话下的定义就是:“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11)就是说,对话必须主体具有同等价值,只是认识有所不同才能实现对话。这其实也就是孔子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讲故事、听故事是一种分享,基本的伦理价值观不同,就不可能在一起享受开怀大笑或者扼腕痛惜。
电影叙事的内在观念是好莱坞电影作者十分注重的一个底层基石。在美国著名电影剧作家罗伯特·麦基看来,善与恶的对立在电影故事中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根本性意义,是一种人的本能情感归属:“随着故事的开始,观众会自觉地或本能地考察负载着价值的世界和人物的全貌,力求分清善恶、是非以及有价值的事物和无价值的事物。他们会力图寻找‘善之中心’。一旦找到了这一核心,情感便会倾向于它。(12)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强调,电影叙事文本是否感人至深,最基本的讲究并不在于叙事的技巧,而在于其中的底层伦理,在于其弘扬的价值和情感。我们读一个故事,听一个叙述,必须在伦理价值观方面与作者有一种尽在不言中的默契,德国文学教授冯·麦特(Pete von Matt)将此称为“道德合约”。“道德合约指的是一些与价值有关的默契。每个故事或者叙述都是以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为框架的。读者一定是在接受了这些价值观的前提下,才会觉得故事说得好,觉得受到感动,觉得心不由己地同情故事中的人物。”(13)“道德默契”概念的思想内涵与诸多中外学者偏爱的意识形态理论大相径庭,前者认为社会有可能建立某种共识,而后者认为现存的社会观念、伦理价值都是虚假认识,都是某个阶级炮制的精神迷药。笔者认为,如果说类型学说对于模式的认识使得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理论中强调“宣传鼓动”、“阶级功利作用”(14)的观点显示出其美学上的暴力,讲故事、听故事需要“道德合约”的论述则使意识形态理论成为一种激进的反文化理论或者犬儒主义的避风港。
王朔语言和王朔文化在电影中的影响就可以作为考察观众心理需求与故事价值观相互应和的案例。王朔喜剧语言的核心是对“文革”语言和“文革”意识形态的超越。从电影《顽主》、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我们看到一种个体价值的凸显、一种对权威话语的反驳。王朔和新时期以来兴起的喜剧语言是对僵化、反人道的“文革”意识形态的嘲弄和解构,这种文化影响一直延续在冯小刚的一部分电影中。也可以多少解释笔者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近年来类型电影片例中喜剧片居多的现象。在《一声叹息》、《非诚勿扰》、《手机》等影片中,我们都看到王朔的语言风格和王朔那种解构整体价值观,强调个人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在笔者看来,张艺谋的《红高粱》成功也在于该作品形象而有力地表现出新时期的时代思潮:呼唤个体觉醒,赞美和肯定个性的张扬和勃发。在“保利博纳”等公司出品的《窃听风云》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中隐喻性地蕴含着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个体违法获取利益将受到惩罚;家庭、爱情的重要意义,对邪恶暴力非法之人的复仇。
在当下中国电影中,表面化地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有意无意地模糊人物的定位,以至对人物失去历史判断、在叙事中无力把握价值判断成为一种常见错误。有时,为了在混乱的方向上寻求伪深刻而牺牲叙事的流畅和基本人情的逻辑甚至成为一种时髦。
《武侠》中“一人犯错,众生犯错,每个人都是同谋者”很有点深意思考。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讨论的四种罪责中,这是最远离个体责任的一种罪责,是指作为人未能阻止罪恶发生、未能完全按照人性行事的“形而上罪过”。(15)但是这个深刻台词与影片叙事相悖,唐龙是参与犯罪之人,影片没有写出唐龙对于自己的过去是个什么态度,对于自己参与的七十二地煞大屠杀是什么态度。灭门屠杀那一段本来是一个对人物给予清晰定位,甚至完成突变的重要戏剧情境。但那个场景没有表明唐龙的行动和他对那次杀戮的态度。如果人物在根本的善恶伦理定位上没有理清楚,他的深刻台词就没法在叙事中落实,这就是笔者认定伪深刻的一个案例。
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在镜语和台词等方面显示出导演掌握模式并与以往作品对话的形式才华。但是在剧作上显示出导演设计人物、安排动作走向时忽视电影叙事蕴含的基本价值观。按照导演的写法,张牧之是个正面的英雄人物,他早年追随过蔡松坡,这是写他有建立共和的好主张。导演强调此人当了土匪也不忘记讲道义,他带队伍进城喊的是劫富济贫号子。“我要做的有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面对恶霸黄四郎,他也有社会理想:“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没有你!”可我们接着看到的是,导演为了向《鬼子来了》致敬,为了故事能走到底,就让这个人物把那假黄四郎砍头,还战刀飞扬,血色飞溅!看到前面的故事,观众还以为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正义牛仔带着志同道合的勇士来到小城匡扶正义、建立法治,观众以为鹅城能够走向共和了。但是,到了这里这一笔,我们看到导演对于人物设计和故事内在价值观的认识有着巨大的空白。难道,为了复仇,为了建立美丽新世界,砍个把人头是不要紧的?死个把小人物是值得的?正面英雄人物不可以杀无辜之人,这是动作片讲故事的语法,也是我们对“不可杀人”这一人类文明基本信条的肯定。这就是讲故事必须有的那个“善之中心”,这就是我们听故事时在不自觉中也会在意的某种“道德默契”。
虽然商业片和类型电影不够繁荣的原因不完全在于作者对艺术语言的掌握,不一定是由于作者对基本价值观的无知,有时也可能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管理机制等外在原因;但是笔者还是要强调指出,对于一部具体的作品而言,只有创作者对其负责。在创作商业化的类型电影时,作者必须在熟知类型的基础上与以往作者、作品有所对话而不能罔顾电影的百年历史和既有的模式,同时作者也必须对故事中的共同伦理和道德默契有所尊重、顶礼膜拜,而不能违反人道伦理和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法则。
注释:
①[美]达德利·安德鲁《评价——对于类型和作者的评价》,彬华译,《当代电影》1988年第3期,第152页。
②参见[美]托马斯·沙茨《好莱坞类型电影》,冯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
③④转引自[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它》,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⑤参见冯小刚、郝建、贾磊磊、尹鸿《新作评议〈夜宴〉》,载《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
⑥[美]达德利·安德鲁《评价——对于类型和作者的评价》,彬华译,《当代电影》1988年第3期,第152页。
⑦“陌生化”是文学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话语策略。俄罗斯批评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指出,文学前置其媒介物的主要目的就是生疏化(estrange)或陌生化(defamiliarize)。换言之,文学靠打乱语言述说的一般表现方式,使得平常所认知的世界“变得陌生”从而更新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参见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类型电影由于其艺术特征和经济运行模式在使用“陌生化”方法时对于既定语言模式所做的偏离要小得多。
⑧同⑤,第68页、72页。
⑨参见《陈可辛:我的电影我做主》,载《新京报》2011年7月5日C02版。
⑩对于这部作品的剧作、类型观念等方面的评述也可参考郝建《〈武侠〉:随意游走、主题悬空》,载《新京报》2011年7月12日C02版。
(11)《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载《话语创作美学》,莫斯科1979年版,第309页。转引自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12)[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13)Peter Van Matt,Verkoummene Sohne,missratene Tochter:Familendendesaster in der Literatur、Munich: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7.p.36.Quoed by Stefan Maechler,The Wilkomirski Affair,p.275转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48页。
(14)爱森斯坦对于电影宣传和政治主题功能的强调可参见:[苏]爱森斯坦《电影杂耍蒙太奇》,《世界电影》1990年第2期。对于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学说的暴力性质分析可参看拙文《美学的暴力与暴力美学》,载《当代电影》2002年第5期,第90页。
(15)“二战”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思考道德罪过和公民责任时区分了四种罪过,刑法罪过、道德罪过、政治罪过和形而上罪过。具体介绍和论述可参见《道德罪过和公民责任》,载徐贲《知识分子——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