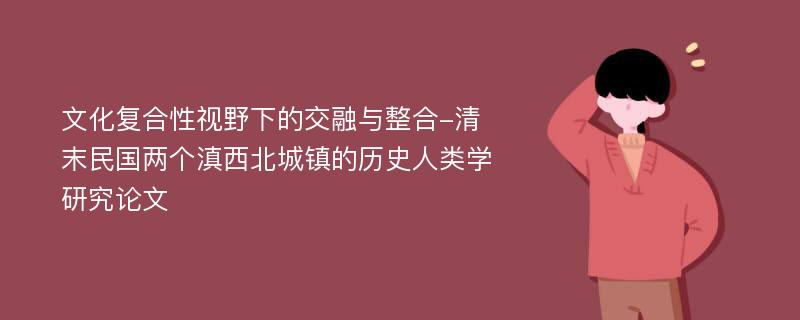
文化复合性视野下的交融与整合
——清末民国两个滇西北城镇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刘 琪
[提要] 文章是对清末民国时期两个滇西北城镇——独克宗与阿墩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基于文化复合性的视野,文章指出这两座城镇在历史上容纳了多样的人群与文化,又在多样的基础上构建起了整合性的社会秩序。多样的人群源于城镇与更大的社会体系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包括军事与贸易两个方面;而整合的力量则来自共同的社会规范、中心象征及围绕其展开的仪式体系,这套仪式体系中的交融使得人们形成了超越特定族群的共同体感受。城镇的社会秩序是当地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发构筑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键词] 文化复合性;城镇空间;交融;仪式体系;共同体
一、研究背景
对于以原始社会研究为标榜的人类学而言,城市是新的研究主题。20世纪初期的美国,移民浪潮带来了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市问题也相应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以帕克(Robert E.Park)为首的芝加哥学派为城市研究开了先驱。
以生态学的方法考察推动城市人群组合与再组合的社会力量,是帕克倡导的城市研究的要点。帕克认为,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传统上同一个社区内个体间直接的、面对面的初级(primary)关系开始为次级(secondary)关系取代,这为城市控制带来了难度,而个体情感寄托的丧失,也带来了社会问题的增加。在帕克看来,看起来井井有条的城市中其实蕴含着失序的风险,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找到飘零的个体如何结成社区的共同纽带,换言之,在于使社区重新成为共同体[1](代译序P.9)。
帕克的城市研究对城市特征进行了精准的概括,即一方面,城市有着多样的人群与文化;另一方面,城市又需要在多样的基础上构建起社会秩序。帕克指出,这种社会秩序的构建,关键在于城市居民之间的联结纽带以及形成居民对于共同体的感受。然而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城市中,帕克并没有找到这样的秩序,他看到的更多是失序的风险。
帕克观察的城市是随着现代化与移民潮成长起来的现代城市,而他所描述的多样人群与文化实则在“前现代”的城市也同样存在。帕克指出,在欧洲的古老城市中,不同的人群之间基本是相互区隔的(segregation),人们按照种族与文化的差异,形成相对独立的居住社区,社会交往也基本限于自己的族群内部。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中国,尤其是多民族交汇地区的城市,便会看到另一番景象。
在滇西北的调查中,笔者注意到了这里的两个城镇——独克宗与阿墩子。这两个城镇均有着令人惊叹的人群与文化上的多样性,然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这种多样性都从未给城镇秩序带来混乱,也从未带来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区隔。相反,在尊重差异、保护多样的基础上,当地人民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内在的社会整合秩序。这种整合性的力量从何而来?当地的人群如何既相互区分又彼此联结?笔者认为,当前对这种社会机制的探讨有着极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笔者看来,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回到历史中考察这两个城镇的建城史及历史变迁。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对晚清中华帝国的城镇研究中曾经指出,城镇的起源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帝国官僚政治设置的地方治所,二是经济贸易需要形成的集镇。施坚雅指出,大都市通常是大区域经济的顶级城市,然后依次向下,会有地区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等,最低一级则是农村的集镇。集镇通常以集市体系为特征,一般包括十五至二十个村庄,组成了构筑经济层级的基本单位。通过复杂叠盖的网络,每一层次的社会经济体系又上连于更高层次的体系,每一个区域体系均是一个有连结点的、有地区范围的、又有内部差异的人类相互作用的体制[2]。
施坚雅的考察提醒我们把城镇放在更大的区域网络中考察。城镇既是介于村寨与城市之间的对象,也是村寨与更大的社会体系之间联结的结点。城镇之所以形成人群的集结,多是出于这种联结的需求,而城镇一旦形成,便会面临如何整合内部人群、构建新的秩序等问题。
槭树科(Aceraceae)植物泛称“槭树”或“枫树”。槭树科植物树叶可呈现出绿色、紫色、红色、金黄色的亮丽色彩且季相变化明显,是世界著名的色叶观赏树种。河南槭树科植物资源丰富,且具有南北交融、东西过渡的特征[1]。笔者以郑州地区适宜生长槭树科植物为例,探讨其在植物景观中的配置模式,以充分挖掘利用河南地区槭树科植物资源,进而为槭树科植物在园林景观中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施坚雅讨论的城镇,大多位于文化相对单一、中央政府控制相对严密的核心区域,对于边疆地区的城镇,他没有给予关注。事实上,相对于核心区域而言,边疆地区的城镇有其自身的特征。一方面,这一区域在历史上有着很强的流动性,因此这一区域的城镇呈现出比核心区域更加多样的色彩;另一方面,至少在晚期帝国时代,中央政府还难以形成对这一区域有效的控制与管理,这使得城镇秩序更多地是在内在自发的基础上形成。此外,边疆地区的城市层级远没有施坚雅描述的那样复杂,村与城之间的城镇往往同时承担了地方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功能。对边疆城镇进行考察,需要运用与核心区域不同的理论工具。
综合情况分析:超剂量使用杀虫剂致鱼不摄食。此养殖户本次用药,如药物符合国标规定的话,可能当日就引发鱼类中毒死亡事故;目前仅几天不摄食,还算比较幸运。当杀虫剂超出安全剂量,低于死亡剂量时,鱼类表现为中枢神经受抑制,食欲差;严重时,体色加深,一个多星期不摄食。一般采取换水或加水的方式稀释池水药物浓度加以解救。
文化复合性的意思是,不同社会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内部结构生成于与外在社会实体的相互联系,其文化呈杂糅状态。文化复合性有的生成于某一方位内不同社会共同体的互动,有的则在民族志地点周边的诸文明体系交错影响之下产生,是文化交往互动的结果……文化复合性亦可理解为一种“复杂性”。这里的“复杂性”与过往人类学者探究过的、不同于原始“简单社会”的文明“复杂社会”有关,但也有着自身的特殊含义,意味着,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社会,文化均形成于一种结构化的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之中,使他者和外部也内在于“我者”。我们以“内外上下关系”来认识文化复合性的构成。[3](P.9)
在笔者看来,“文化复合性”的概念对于我们理解边疆地带的城镇有着极大的启发。这里的城镇以人群与文化的杂糅为基本特征,这种杂糅既来自于城镇的“内外上下关系”,又在城镇内部的社会互动中将“他者”纳入“自我”之中,从而形成富有自身特点的内部秩序。笔者将带着文化复合性的视野,对独克宗与阿墩子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考察。
笔者将首先勾勒这两座城镇的建城历程、空间格局与人群分布,之后将着重探讨这些不同的人群如何通过共同规范与象征体系形成内在自发的整合性力量。笔者认为,虽然这两座城镇都位于藏区,无法脱离藏文化的“底色”,但真正将所有族群联结起来的仪式与象征并不是从有建制的藏传佛教中来,而是来源于更为“原始”的“山水之间”。对于圣地的崇拜与促进社会再生产的节庆相结合,成为人们超越族群边界、结成共同体的关键性力量。时至今日,即使城镇的经济与政治样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套象征体系仍旧保持相对稳定并仍旧作为社会整合的力量发挥作用。最后,笔者将通过对这两个边疆城镇的案例呼应帕克提出的关于城市秩序如何构建的问题,并讨论这两个个案对于我们当前理解现代城市可能带来的启发。
在对西南地区的研究中,王铭铭提出了“文化复合性”的概念。他写道: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s)选择 F 检验,计数资料[n(%)]选择 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建城历程、城镇空间与多样人群
自丽江西行,路皆危岩峻坂,如登天梯,老桧交柯,终岁云雾封滃,行者不见马首,几疑此去必至一混蒙矣。讵三日后忽见广坝无垠,风清月朗,连天芳草,满缀黄花,牛羊成群,帷幕四撑,再行则城市俨然,炊烟如缕,恍若武陵渔父,误入桃源仙境。此何地欤?乃滇、康交界之中甸县城也。[4](P.143)
1932年,奉国民政府之意出使西藏的刘曼卿路过中甸时留下了这段文字。这段文字中提到的“中甸县城”古名建塘,其县城所在地被称为独克宗。根据史家的考证,“独克宗”意为石丘山上的白色寨堡,因吐蕃时期即在山包上设寨得名。由此可见,独克宗作为最早的“城”,其雏形源于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吐蕃时期所建的寨堡,很快便消失于历史长河。此后,木氏土司也曾在独克宗之地修筑日光、月光两城,此后又毁于战乱。雍正元年(1723年),云南提督郝玉麟在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的过程中进驻中甸,次年再度修建中甸城。《新修中甸志书稿本》记载:
(2)提出了基于实时道路交通情况与充电站分布位置的道路简化模型,充分地化简了复杂交通网络,为快速的最优路径规划提供了基础。
中甸古称“建塘”,为西藏所管,无城池。自归化后,蒙总督云贵部院中协副总兵官孙(宏本)奉命到甸,于雍正二年(1724年)间,始建立土城一座,由白鸡寺山腰斜挂于东门山脚。周围长三百六十丈,高一丈二尺。安设四门城楼,并无垛口、炮台。周围顺筑土墙,墙外亦无壕池。内建兵房数十余所,以为兵寓。[5](P.18-19)
可见此前政权所建的城池均已被毁,清政府修筑的中甸城,首先是作为“兵寓”存在,城址并不在坝子中央,而是依山而建。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山下的坝子是藏民的世居之处,清朝驻军建的这座城里面“只有汉人”。藏民有土地,靠耕种土地而来的粮食生活;汉民则没有土地,只有朝廷发下来的口粮和饷银。建城初期,汉藏之间并没有多少来往,藏民并不会主动前去汉民的城里,汉民则需要来山下坝子的水井打水并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打水的时候,汉藏之间还会偶有矛盾冲突。
油气管网管理体制的目的是管住中间,提高管输效率,降低管输费用,让终端用户获得实惠,增强天然气的竞争力。
这个时期,虽然作为兵团的汉人还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但城下的坝子随着商业的繁荣已经开始出现族群融合的趋势。历史上,中甸早已是汉藏之间贸易的孔道,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达赖喇嘛求互市于金沙江,总督范承勋以内地不便,请令在中甸立市,许之”[6](P.285)。从此以后这里便进入了新的繁荣时代。当时的贸易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运送货物路过独克宗时在此从事交易,这种交易通常以委托当地藏民的形式实现;二是直接在街子上开设商号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开设商号的人大多是来自鹤庆、丽江等地的纳西族、白族和回族商人①。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他们便向当地藏民购买土地并逐渐定居在这里,同时开始与当地人通婚。
由此可见,无论是独克宗还是阿墩子的节庆,都与山、水等圣地直接相关。相较而言,阿墩子节庆中“野性”的要素更重,这或许与它更加远离文明中心的位置有关。这种对于圣地的崇拜是所有人的交融,直接指向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无论是在抢水、转山还是圣地游玩的过程中,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身份、社会身份都会被暂时搁置,他们只会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这种对于共同体的情感会在节庆结束后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段史料中提到的“石山”,即大龟山,这是吐蕃最早修建寨堡之处,也是整座独克宗古城的中心。山前的井水是城里所有居民的生计来源。城中的住宅围绕着大龟山四散开来,这些住宅基本是土木结构,除住宅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庙宇与会馆。这些庙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藏传佛教的经堂,其中一座位于大龟山顶,另一座位于山脚下;第二类是汉人建起来的各种寺庙,如观音阁、关岳庙、灵官庙等,这几座庙宇基本处于当年的旧城内,是当时清朝驻军的后人所建;第三类是各式会馆,以丽江会馆、鹤庆会馆为代表,馆内会供奉神灵,当地老人也把这些会馆称为“庙”。有趣的是,本应作为权力机构的县政府却处在很边缘的位置。当地老人曾用“三行”来概括民国期间中甸城内的社会群体,即藏团、汉团与商会②,这三个社会群体各自有其活动领域,既有所区分又没有完全隔离。
今城在旧城之东,与旧城基为连环形——县政府即在连环套中,原为守备衙门遗址——城墙周围六百余丈,高二丈一尺,厚六尺,覆木为檐,盖以草饼,以御风雨。其形不方不圆,有五门十一碉。中有石山,形圆如龟。藏民建经堂于龟背,即环石龟而居,谓之“本寨村”。因嫌旧城狭隘,又复缺水,故始改筑新城,而围石山于其中。石山前有清泉涌出,全城饮料取给于此。城外无壕。[7](P.48-49)
在农村垃圾形势日益严峻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下,各个地区积极开展农村垃圾治理工作,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治理模式,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各个地区应该相互借鉴,共同致力于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还农村更美的景、更蓝的天。
综上可知,独克宗的建城与发展始终与其军事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相较而言,阿墩子则主要是由“市”演化而来。关于这座城的来源,《德钦县志》中记载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据说,明朝丽江木氏土司在出征藏区的路上,得到了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铜像本身重量不过百余斤。在经过阿墩子原德钦寺旧址的时候,有一土墩,台高数尺,木氏土司见这里清泉幽雅,翠竹成趣,便命手下人落马休息。哪知道第二天清晨,佛像忽然变得重达往日数倍,不能启运。于是,木氏土司便在此建寺召僧。当时,马鹿厂银矿、茂顶金矿都很兴盛,陆续商集成市,就以其土墩台地为名。自民国后,取其墩字土旁,义为边界墩和平安。[8](P.382)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阿墩子的建城与明代木氏土司的扩张有直接的关系。从地理位置看,独克宗更靠近汉地并且有一块相对较大的“坝子”,这也使其更具有军事控制与战略上的重要性;而阿墩子则得益于其在川藏贸易通道上的重要位置,由此“商集成市”。
到了清末,阿墩子虽然也有中央王朝派来的驻军,但并没有修建城池,仅在三条主要街道的入口处建有一座石拱门。民国时期,阿墩子的商业得到了极大的繁荣,这其中除了寻常推进贸易的要素以外,还得益于县城旁边的神山——卡瓦格博的存在。
希老、中、青全体人员铭记于心,不论自己或他人都应遵我佛清静为本,纤尘不染之教义,虔诚崇奉皈依三宝为首要之信条,严守“十不善”之诫训,诺遵处世三行为、言语四行为,特别要以三不行为为诚信,守意念。三行为:不嫉妒,不害人,容忍不同观点,不将己见强加于人之行为;为生生世世痛苦之源,能摒弃此三恶之念,即可达到我佛之意念,必将永远受福受益。[10](P.244)
此雪山名震康藏,为西藏八大山神之一。每到冬季,康藏善男信女来朝雪山者极多。藏俗不朝雪山者,死后无人抬埋。此时德钦商业因而繁盛。故当地人云“十冬腊三个月的生意,其利润可以维持一家一年生活”。朝山人之多,生意之繁盛可以想见。每属“羊”年,即隔十二年一次,康藏人来此朝山者尤数十百倍于平时。笔者以为,与其说“雪山太子”③为德钦名胜,毋宁说雪山为德钦人的一座“金山”较为适宜。盖无此山,德钦商业及人民生计成问题也。[8](P.379)
这座神山成为阿墩子人民生计的重要来源。刘曼卿在日记中也写道:“各商店中商品,以及沿街摊卖者,除滇产茶糖、布疋、铜铁器、杂物外,余多洋货。如洋火、纸烟、洋蜡、洋疋头、洋瓷器、洋袜、毛巾、手电、胰皂等……无一非外人生产过剩之品。且价格奇昂,劣等纸烟一小盒,售价半元,问之令人咋舌。”[4](P.149-150)在笔者调查过程中,当地老人也曾多次感叹当年街市上物品之丰富,并说当时的阿墩子有“小上海”“小香港”之称。可见这座边疆小镇曾经有过令人难以想象的繁荣。
虽然从城镇规模与人口数量来看,阿墩子无法与独克宗匹敌,但物品的流动与商业的繁盛同样也带来了多样的人群。这里同样有清朝驻军的后代,同样有前来做生意的商人及其会馆,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有一座教堂和清真寺。清真寺是雍正年间定居阿墩子的回民后代所建④,位于正街尽头与口袋街接壤之处;而在后街尽头则是鹤丽会馆与天主教堂⑤。与独克宗类似,这些人群各自有其活动空间,但在清末民国时期,随着人们的社会交往逐渐增多,他们开始相互通婚、相互融合。更重要的在于,无论是独克宗还是阿墩子,外来人群在此定居之后,都自发地在共同生活中构建起属于他们自身的社会秩序。
三、整合性的力量:规范与节庆
在某种意义上,独克宗与阿墩子就像是汉藏通道上的“容器”。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接纳了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人们,让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纵观历史,独克宗与阿墩子都曾被多个外来军政势力占领,但无论哪股势力都难以真正实施有效的管理,当地的秩序基本上是老百姓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根据史家考证,早在很久远的年代,这里便形成了一套以地域为基础的“属卡制”,此后进入这里的势力,无论是元军还是木氏土司、和硕特部落,乃至清王朝、国民政府,都是在这套制度的基础上征收税务,进行统治[9](P.111)。同一属卡的老百姓会制定自己的“村规民约”,对内部事务进行规定,属卡与属卡之间的纠纷则通过更高级别的会议来解决。
独克宗被称为“中心属卡”。笔者在史料中找到了数份关于属卡内部的“公约”,这些公约涉及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涉及具体事务,例如如何摊派赋税、如何修建房屋、如何安排轮值等;一类涉及行为规范,例如第一份“中心属卡汉藏公约”出现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里面写道:
为汉夷大小同心议例,以垂永久,以杜更张事。窃甸治属木府管辖,本寨户口尚少,该地建立围墙,安设四门,街道宽阔,房屋整齐,边留余地,约为火烛、盗贼起见。缘遭兵马,前基倾颓。嗣上下寄籍重多,房屋稠密,被火二次。又至近时,汉籍续住,效尤起铺,将寨街路面侵占,至若寨之石岗,挺立中央,境脉天然,四山环拱,众夷绕居,五方商贾,络绎聚归……近来客籍徒增登□利,倚强侵占,将寨岗土石余地凿开建修。适有段姓铺内被火,附近汉夷之家,本身几逃外地,器物无处搬移,众所昭彰。今汉、土官民公议,欲照其向时制度,约略可认火星巷道,出入便路应各留宽三尺,寨岗相连之地,应遵古制,不得占修。[10](P.213)
这份公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社会价值。正如前文所言,木氏土司时代这里定居的人口相对较少,康熙雍正年间随着商业的发展,有很多汉人迁来贸易居住。这些新来的移民为城镇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而解决这些挑战的方式则是土官与民众坐下来一起商议,制定公约。这份公约详细规定了所有房屋、道路的建筑细节,文末附有属卡内所有居民的签章。此后类似的公约不断出现在档案之中,虽然从这些公约也可以看到汉藏之间存在着一些张力⑥,但总体而言,立约的方式仍旧得到了百姓的认可。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具体事务以外,在一些公约中还有佛教文化影响下对人们行为规范的规定。例如,道光五年(1825年)的“本寨老中青公民应遵守的公判布卷”中写道:
通过加快开采技术的创新与研发,有效提高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对于现阶段应用较广的开采设备与开采技术进行创新与改进。另一方面,矿山企业要与科研教育单位进行密切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此外,还要注重先进开采设备与技术的引进,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地质环境保护质量奠定基础。
卡瓦格博为藏区八大神山之一,每年秋冬两季便有很多外地藏民前来转山,这是阿墩子最为热闹的季节。民国期间常驻阿墩子的国民政府官员黄举安写道:
这份公约虽然也有对具体事项的商讨,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指导性的社会规范。这种规范既有藏传佛教的影响,也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容忍不同观点,不将己见强加于人”,这显然与独克宗人群的杂糅特征有直接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在独克宗还是在阿墩子,笔者所访谈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提到自己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要尊重不同族群的风俗,这种世代相传的教导使得多族群之间的共处更加成为一种可能。
共同的社会规范为城镇秩序的塑造提供了保障,然而正如帕克所言,如果要使城镇真正成为“共同体”,人们还需要找到共同的情感寄托。那么,在独克宗与阿墩子,这种情感寄托又来自哪里呢?
前文提到在这两个城镇,不同的人群有着各自的宗教场所与节庆活动。例如,汉人会去关帝庙、观音阁里烧香,会在七月半的时候祭祖;商人会在各自的会馆中商讨事务,搭台唱戏;藏民会去寺庙拜佛,会去经堂请喇嘛念经;回民则会去清真寺礼拜,过伊斯兰三大节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独克宗还是在阿墩子,都有着所有族群共同享有的象征符号及围绕其展开的仪式,这些象征符号与“山”和“水”有着直接的联系。
孙中山去世后留下的政治遗产成为继承者确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资源,故而后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党统之争亦表现为对“总理遗教”解释权的争夺。在国民党高层的政治竞争中,无论是谁,都要高举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旗帜。
在独克宗百姓的口中,大龟山脚下的水井曾经是他们最重要的生计来源。正如光绪年间的史料中记载:“龟山即造城之主山——土城建于龟山之上——由东门外接脉东向,土石并结,团聚高墩,时人号曰‘土官寨’。寨下流出清泉一溪,名为‘水井’,所有兵民商贾,共汲饮于此水焉。”⑦这口水井位于全城中心,水质佳,因此城里的老百姓都喜欢去那里取水。在水井之上,即大龟山的半山腰处,建有一座龙王庙,庙里供奉着龙王,这是与水直接相关的祭祀。
除大龟山以外,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圣地”还有两处,一为五凤山,一为百鸡寺。史料记载:“五凤山,在境内之东南隅,离城五里,犄角于南关之外……山腰间土人建立山神庙一所,四时祈祷,必到庙内焚烧天香,遍插灵旗,求之则应,叩之则灵,山神亦时为显应焉”[5](P.26);“百鸡寺在西门城后之山顶上,建自明时,年月无考。惟高阁倚天,危楼拔地,上敬黄教祖师,傍列护法诸神。土人有病患灾疾,许愿祈祷,敬送家鸡一只放生寺内,习为风气,鸡声成群,因名之曰‘百鸡寺’。”[5](P.55)五凤山被认为是独克宗所有居民共有的神山,而其上的山神庙则是供奉山神的所在。百鸡寺是一座黄教寺庙,但与离城三十里远、富有盛名的松赞林寺相比,百鸡寺显然是更让老百姓感觉亲切的场所。光绪年间的《新修中甸志书》中将百鸡寺所傍的那座山头称为“龟城之发脉”[5](P.55),可见其之所以被百姓崇拜,仍旧与山的灵气有关。
在独克宗,春节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⑧。按照当地习俗,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居民们便会聚集在水井前“抢头水”,用勺子把井里的水舀出来,再倒回去。此后,还要前往五凤山山神庙烧香,再去百鸡寺,等到这一圈转下来,天也差不多亮了,再去亲戚朋友家串门祝贺。可以看到,独克宗一年的开端也是围绕着“山”与“水”进行的。通过对与生计密切相关的共同神灵的崇拜,这座城里的居民意识到,无论哪个族群,他们都需要依山傍水生存,需要联结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
类似的,在阿墩子,大年初一的绕山也是当地居民的“集体活动”,只不过这里没有专门给阿墩子山神修建的庙宇,人们的祭拜大多直接指向卡瓦格博。大年初一,阿墩子的百姓会围着县城周围的小山转一圈,但更重要的是大年十五去“曲顶贡”的活动。曲顶贡是卡瓦格博外转经的起点,汉名称为白转经台,由一座转经台和一座庙宇组成。民国期间,黄举安记载了当地青年妇女“耍白转经”的习俗。黄举安写道,阿墩镇里的青年妇女每年新年初三以后便去商号或者税关找经理或长官“敬酒贺年”,名为拜年,实则找他们索要钱财,若是不给便“按下全身检查”,将荷包里的银元全数搜光。正月十五之后她们便拿着年节期间凑拢的钱一起去“耍白转经”。所谓“耍”,即在那里铺地而食,食罢便在草地上卖弄歌喉,且歌且舞,且唱且和,直至醉眼朦胧,翩翩欲倒之势[8](P.377-378)。
时至今日,这两座城镇的样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涵盖所有族群的仪式空间仍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⑨。独克宗全城百姓曾经依赖的那口水井已经不再,但龙王庙却依旧留在龟山山腰并经历了数次重建;山神庙与百鸡寺仍旧是所有百姓都会前去朝拜的地方。更为有趣的是,为了方便不同的人群,山神庙前还分别搭起了藏式与汉式两座烧香台,两座烧香台相隔约十米远,但香都烧给汉藏共同的山神。在这两座城镇,每年春节,老百姓仍旧会绕着周围山头的“圣地”转一圈,而在阿墩子,三月十五的“狂欢”则被改至端午。在这个春夏交加、万物萌动的日子里,人们依旧会用竞赛与欢乐的方式,庆祝社会共同体的再生。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市区附近的红男绿女,不分贵族平民,各约至好,均到是地撑持帐篷,且各盛装,做些东西来吃。吃毕,凡感情较好的青年妇女,集在一场,分做男女两组,同时歌舞。且和且唱,各尽所能,各吐胸中的挚闷情怀,要求对方和答。此时此地的社交绝对公开,毫无约束。亦正是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调情之时。这一天是此地青年人的佳节,也正是万种情怀透露之期。在此节日,好玩者放枪“打靶”,好赌者作“竹城”之游,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直至日落西山,方才尽兴而归。[8](P.378)
不难看出,这两场节庆蕴含着共同的要素:第一,社会地位的倒转。在日常生活中处于高位的人在这个时候会被调戏、被捉弄,或者暂时搁置自己的身份。今天阿墩子的老人还记得三月十五聚会的场景,他们在回忆中强调,无论是土司、洋人还是设治局的官员,这一天都会来到这里“与民同乐”;第二,节日的庆祝伴随着歌舞与男女之间的结合,它既是节庆又是社交的场合。在这一天,男女之间可以肆无忌惮地表露情感,通过对歌的方式结成百年之好。
植被覆盖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面积的大小以及植被生长的茂盛程度,能代表植被的生长状态和生长趋势,是刻画植被在大气圈、水圈、岩石圈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参量。在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时,常将植被覆盖作为评价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3]。考虑到从行政区角度对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进行研究不太准确,因此根据生态区的划分原则,将黄土高原划分为九大生态区,并对这九大生态区的植被覆盖、变化趋势、植被覆盖指数(NDVI)与降水之间的相关性、NDVI与气温之间的相关性分别作GIS遥感影像分析与处理,以探讨植被覆盖对水和热的响应。
事实上,这样的场景非常类似于葛兰言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分析的上古节庆。葛兰言(Marcel Granet)提到,在上古时代,共同体的人们经常会在春季,在山川圣地举行盛大的节庆,男女之间的结合是这些节庆最重要的内容。在万物勃发的日子里,人们一方面与圣地自由接触,在圣地中随处游玩,半裸着跳入河中,以此吸收其保护力量;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同时进入公共生活与性爱生活中,用一种激烈的比赛的方式(对歌),结成社会之间的联盟。换句话说,看似混乱的节庆,实则蕴含了最根本的促进社会再生的秩序,这可以激发人们对于共同体的认同。[11]
②钱忠好:《非农就业是否必然导致农地流转——基于家庭内部分工的理论分析及其对中国农户兼业化的解释》,《中国农村经济》2008年第10期。
好景不长,清军所筑的城池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杜文秀回变中被焚毁。此后,无所依归的汉人只好“下山”来投靠藏民,汉藏之间开始融合。到了民国十年(1921年),城又一次被筑起来,而这次的城便将所有人都囊括其内。民国《中甸县纂修县志材料》中写道:
3.培养绿色意识,提供创业新起点。大学生在校期间,应当树立和培养绿色意识,形成良好的心理自制力。大学生绿色意识的培养需要外在的学校教育和内在的自我教育相结合,并且把内在的自我教育放在最关键的位置。大学生坚持自我学习新发展理念,形成良好学习习惯,将绿色发展理念植根于心中,充分发挥到未来工作当中。高校要向大学生宣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意识,让其在创业的初始阶段,就放弃破坏环境以及浪费资源的创业项目,要求大学生创业遇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时,一定要以保护环境为先。
这样“略带放荡”的歌舞,从表面上看似乎与白转经台的“圣地”身份不符,而这种类似的活动在阿墩子的年度周期中还不止一例。例如,在阿墩子百姓的心目中,离城几里远的一处海子算是另外一处“圣地”,上面挂满了经幡。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老百姓们都会聚集在这里举行一场盛会。黄举安这样写道:
四、结论与探讨
综上,笔者以滇西北的独克宗与阿墩子为例,描述了这两个边疆城镇的形成历程、空间格局与族群构成,并讨论了它们如何在多样的基础上构建起融洽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合性秩序,它源自城镇与更大的社会体系之间的联结,又在内部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结构。它并没有消除人群与文化的差异,而是在差异之上构建起了包容差异、超越差异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以共同规范为基础,以共同的象征符号与情感寄托为依归,在围绕圣地举行的仪式活动中,社会最本原的需求被重新唤起,人群与人群之间的边界被打破,形成了交融的局面。人们都意识到,他们必须突破自己特定的族群身份相互联结才能维持得来不易的和平。今天,虽然城镇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仍旧会在每年的某个时刻重温“共同体”的感受,并将这种社会记忆持续不断地传承下去。
本文虽然描述的是滇西北边疆地区的两个城镇,但这种多样性是所有城市都具有的特征,如何在多样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秩序是每一个城市都需要面临的挑战。在帕克观察到的城市中,人群之间或相互区隔或仅出于劳动分工的需要构成机械性的联结,却没有真正找到超越自身特定群体的对于整体城市的归属感。今天的城市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祛魅”的城市,个体主义的兴起、对现代文明的标榜,固然使得城市有了光鲜亮丽的外表,但也造成了城市中个体的巨大孤独以及由于各种“失序”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意识到,文明不一定能带来社会整合,任何一个文明之地都需要自然的、原始的、与人类本性契合的力量来维持基本的社会团结。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我国边疆城镇历史上的社会整合秩序,或许可以为我们反思今天的“城市病”带来些许启发。
注释:
①这里的“族”是按照今天的民族分类称呼的,事实上,当时中甸县城里的藏族人也把这些人一律视为汉人。
②关于“三行”的情况,可参见杨若愚“‘夷汉杂处’——一座边地古城的政治、族群与文化”,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③“雪山太子”(或“太子雪山”)为民国时期普遍流传的汉人对卡瓦格博的称呼。据当地人介绍,这个称呼来源于清末任阿墩子弹压委员的夏瑚,但笔者没有找到相关史料证明。
4)臂架俯仰、旋转机构:臂架俯仰机构包括液压系统和固定支架2部分。液压系统安装在臂架和行走机构之间,采用双油缸拉杆作俯仰运动。臂架相对于水平线15°~25°俯仰。臂架旋转机构包括液压油缸和回转轴承,臂架相对于中心线-30°~+30°左右旋转。
④这些回民很快就与当地的藏族融合,成为“藏回”。关于“藏回”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刘琪《民族交融视域中的“藏回”——基于云南省德钦镇升平镇的实地考察》,载于《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⑤关于阿墩子的天主教堂,也有老人说其实没有明显的标志物,只是一座普通的楼房,是当时的天主教传教士用来搞活动的地方。
⑥例如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本寨藏公堂布卷公约”中写道,新任乡约“希图名誉,不照旧规,相率行汉礼铺张办事”,造成了开支方面的困难;同治七年(1868年)的“公众立约”中也写道:“建塘独肯宗自兴汉族规矩操办婚丧嫁娶等事以来,所费过于繁重”,并通过立约的方式,试图节省开支,回归传统风俗。换句话说,这一时期汉人的风俗已经开始影响独克宗。参见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驻昆办事处编《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汇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35页。
⑦据当地人的回忆,直到通自来水之前,这口井里的井水一直是全城人的生活来源。最近十余年间,由于地下水抽取过多,井水已经干涸。参见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驻昆办事处编《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汇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⑧这里的“春节”,指的是农历春节而不是藏历年。根据当地人的回忆,至少从民国时期开始,独克宗与阿墩子的人们便开始过春节,藏历年则是在“乡下过的”。我们可以把这种习俗视为汉文化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两座城镇具有文化上的杂糅性,所以必须尽量淡化“藏”的底色,才能更好地促进各个族群之间的融合。
⑨梁永佳在对大理的研究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参见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根据钻探揭示,依据岩土体的成因、时代、埋藏分布等特征,结合室内土工试验综合分析,场地勘察深度范围内岩土层自上而下可划分3大工程地质层,现分述如下: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E.帕克.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C].杭苏红译,张国旺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3]王铭铭,舒瑜编.文化复合性:西南地区的仪式、人物与交换[C].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4]刘曼卿.国民政府女密使赴藏纪实:康藏轺征[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5]中甸县志资料汇编(二)[Z].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0.
[6](清)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Z].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7]中甸县志资料汇编(三)[Z].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1.
[8]云南省德钦县志编纂委员会.德钦县志[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9]王恒杰.迪庆藏族社会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
[10]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驻昆办事处编.中甸藏文历史档案资料汇编[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11][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赵丙祥、张宏明译,赵丙祥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7—0005—07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现代都市族群社会治理研究”(2018ECNU-QKT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琪,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民族问题、西南区域研究。上海 200241
收稿日期 2019-03-16
责任编辑 李克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