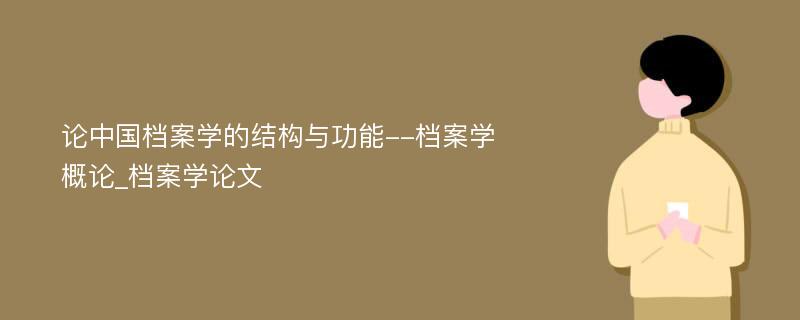
论中国档案学的结构与功能——档案学概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学论文,中国论文,概论论文,结构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学概论是我国档案学中唯一以“档案学”作为学科名目的学科,也是一门真正以档案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概论的形成时间比较晚。如果以正式出版物为标志,档案学概论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是我国档案学中的“后来者”。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档案学概论实际上是一门“档案学的反思学科”。(注:窦晓光:《刍议〈档案学概论〉的知识范围与体系》,《档案学理论新探索——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专题报告、发言集》,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页。)正是这种“后来者”的优势,档案学概论有时间和能力对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对档案学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更系统地研究和分析,也更容易成为中国档案学的“品牌”。
一、档案学概论的基本结构
在我国正式出版的《档案学概论》中,其基本结构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即都可以分为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四个部分。
(一)档案。
档案是已经出版的《档案学概论》共同具备的结构内容。这部分大体包括档案的起源、档案的定义、档案的属性、档案的价值和作用、档案的种类和形式,以及国家档案全宗等问题。在《档案学概论》的作者看来,档案是包括档案学研究在内的一切档案现象的“根源”;如果没有档案,就不会存在关于档案的活动,就不会出现活动中的问题,当然也就更不会有解决问题的所谓理论。“当档案与档案管理工作复杂到必须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方能实行有效管理,方能使档案发挥作用、实现价值的时候,档案学就应运而生了。”(注:冯惠玲、张辑哲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因此,向读者阐述有关档案的基本问题,就成为档案学概论的当然内容。
(二)档案工作。
档案工作是占60%的《档案学概论》中所设置的结构内容。这部分大体包括档案工作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档案工作系统的基本特征、档案工作与社会环境、档案工作领域中的矛盾运动、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档案工作的性质、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档案工作现代化内容等问题。在《档案学概论》的作者看来,档案工作的出现是档案的内容、形式与社会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我国早期档案学作品的直接内容都是档案工作的管理方法一样,档案学之所以不是“载体学”而被称为“管理学”,就是因为它是以研究“档案工作”这一管理现象为基本内容的学科。因此,向读者阐述有关档案工作的基本问题,就成为档案学概论的当然内容。
(三)档案事业。
档案事业是占80%的《档案学概论》中所设置的结构内容。这部分大体包括国家档案事业的概念、档案事业管理工作、部门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档案专业教育与人才管理、档案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档案宣传出版工作,以及国际间档案界的交往活动等问题。在《档案学概论》的作者看来,档案事业“是以管理和开发国家档案信息资源、服务于国家各项事业为宗旨的,包括各种档案机构活动和必要工作条件在内的一项专门事业。”(注:丁永奎:《〈档案学概论〉的知识范围和体系》,《档案学理论新探索——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专题报告、发言集》,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如果从档案学概论所赋予“档案事业”的实际结构看,它是“档案工作”的一种合理延伸,是“档案工作”的主体和活动状况;而档案工作主体的结构、规模、层次及其管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档案学所对应的管理实践的水平和层次。中国档案学正是建立在对这种“管理实践”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因此,向读者阐述有关档案事业的基本问题,就成为档案学概论的当然内容。
(四)档案学。
档案学是已经出版的《档案学概论》共同具备的结构内容。这部分大体包括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档案学的一般特征、档案学的体系结构、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档案学与相关学科、档案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在档案学概论的作者看来,档案学是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它是“研究了”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之后的必然结果。在档案学概论没有产生之前,档案学研究的上述问题只能散落在档案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之中,缺乏合理发展的空间。而作为中国档案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档案学概论,它就是为了弥补这一历史缺憾才“应运而生”的。因此,向读者阐述有关档案学“是什么”和“有什么”等基本问题,就成为档案学概论的当然内容。
二、档案学概论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已经出版的《档案学概论》中,其结构内容是大体相同的,即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和档案学。只是在档案工作与档案事业的提法和归属方面略有差别。这种从档案的论述开始,经过档案工作或者档案事业,最终归结于档案学的模式,以及对它们之间依存关系的表述,就是我国目前的档案学概论试图向读者展示的全部学科内容。这种学科结构的基本状态,与中国档案学中其他学科的建构模式非常相似。
从档案学概论确立的最初设想来看,它是作为集中解决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而产生的学科,它应当是我国档案学理论中较为成熟部分的总结。实际上,在中国档案学形成、发展的数十年的历史中,其“较为成熟”的理论就是对档案以及管理的研究。换句话说,中国档案学就是围绕着“档案以及管理活动”而建构的理论体系;作为对中国档案学进行总结和归纳的档案学概论,当然不能脱离这种理论模式。正如吴宝康先生于1984年10月31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秘书教学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所说的那样,我国的档案学“走的是首先注意积累和总结实际工作经验,分别建设各门专业课程,然后再概括上升为理论,编写档案学概论的道路。”(注:武重年:《〈档案学概论〉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构成》,《档案学理论新探索——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专题报告、发言集》,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从档案学概论的体系结构来看,它作为研究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的学科,当然无法回避“档案现象”中这种经典的问题。自中国档案学产生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档案学概论止,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现象”的最基本的认识,都是围绕“档案及其管理活动”展开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谈“档案及其管理活动”我国的档案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档案及其管理活动”是档案学概论最直接的研究对象;档案学概论必须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进行认真分析之后,才有可能发现其中规律性的东西,才有可能建构自己的学说。
从档案学概论的形成过程看,它作为新中国档案学教育较早涉及的学科,始终存在一种对档案学基本内容无法割舍的传统。在我国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档案学概论实际上就是档案学的统称,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描述和分析实际上就是档案学概论的基本内容。正是这种学科的“惯性”,决定了学科结构的基本状态。此外,专业主管部门对学科的计划要求,也对档案学概论的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作为一门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学科,档案学概论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描述和分析,与档案学的各分支学科中的“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描述和分析应当有所不同,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转移”,以及“详略”的问题。档案学概论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研究,应该是立足于发现其中的本质和规律,通过对这些规律性问题的分析和提炼,最终建构自己的学说;而其他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研究是为了发现和总结活动本身的程序和方法。比如,同样是对“档案”的认识,档案管理学是在分析其管理对象,它的一些管理程序和方法,都是由这些对象的特质决定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是在分析被传播的载体,它的一些传播程序和方法,都是由这些载体的特质决定的。而档案学概论对“档案”的认识,应当建立在解决这样一些命题的前提下,即档案这一社会现象所引发的人们的思考是什么,人们在对其管理和利用的过程说明了哪些社会发展规律性,根据这些“规律性”的认识如何去建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同直观现象及其中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因此,档案学概论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分析和认识角度绝不应与档案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相同,它的研究过程和结论要带有明确的理论色彩,是一种理性研究的使命感使然。只有这样,才能使同样的结构为不同的学科功能服务。就像对一枚螺栓的认识一样,它用于桌椅是为了连接,用于机器是为了传动,而金属学却会从中发现一部完整的科技发展史。
三、档案学概论的功能及其结构
档案学概论无论是在其最初开创时所设置的、较为宏观的“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知识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的学科宗旨,还是目前较为明确的“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功能,都是要通过档案学概论的具体的结构体现出来的。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档案学概论》的情况看,它们的结构在反映学科功能方面基本上是合理的。如果说存在什么问题或者有待完善之处的话,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其二是论述问题的角度。
首先,档案学概论应当以论述档案学本身的问题为主,不宜将大量的篇幅放在对“对象性事物”的描述和阐述上。否则,就势必挤压自身的发展空间,而出现结构上的“喧宾夺主”。如上所述,“档案及其管理活动”对于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论述,已经成为档案学其他学科实现功能而必须具备的结构。如果这些学科失去这部分结构,就会造成其学科功能的缺陷。而档案学概论的功能在于营造档案学本身的学科体系,从整体解决档案学所有的“元问题”,其学科结构的设置要服从和服务于学科建构的这一基本前提。如果涉及到其他分支学科已经涉及的问题,也应当有一定的包容性,即围绕着档案学概论的体系重新设置和安排这部分的结构。比如,可以在“研究对象”中简要地阐述“档案及其管理活动”的情况与趋势等。更为重要的是,档案学概论要围绕自身的功能进一步健全自身的学科结构。在这方面,如目前档案学界经常论及的“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档案学的体系结构”、“档案学研究的类型及特征”、“档案学研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档案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以及“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注:李财富:《档案学本体论》,《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5期。)等等,都是可以借鉴的内容。总之,档案学概论必须以自身的功能为导向,重视现有成果又不拘泥于现有体系,实现档案学概论结构的重构,才能为自身发展打造出新的空间。
其次,档案学概论应当建立起研究问题的独特视角。既然档案学概论已经明确了“以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和“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学科的基本功能,就应当确立起与学科功能相适应的论述问题的角度和结构模式。所谓论述问题的角度,就是档案学概论中对档案现象分析的立足点,即以何种目的来讨论档案现象——是研究实际问题,还是讨论管理方法,抑或发现活动规律。讨论问题的目的和立足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很大区别。毫无疑问,档案学概论是为了分析档案现象的学科,它在论及“档案及其管理活动”时,就应当与档案管理学等其他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在论述问题的角度方面有一定的区别。否则,也就只能得出与其他档案学的分支学科相同的结论。如果是这样,就会动摇档案学概论的存在基础和发展空间,使档案学概论的建构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因此,要使档案学概论得到发展,就必须在其论述问题的角度方面有所改变。与“论述问题的角度的改变”相适应,就是要进一步确立档案学概论的结构模式。档案学概论的结构模式是档案学概论的功能和已经改变了的“论述问题的角度”的物质承担者。也就是说,档案学概论的功能和新的论述结果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容器”,并通过这个“容器”将这些成果“固化”。因此,这个“容器”的大小和质地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档案学概论的发展状况。
此外,档案学概论除了在对现有结构进行调整以充实学科内容之外,还应当围绕学科的基本功能着力拓展研究空间,注意学科发展规律的探求。
档案学概论应当注重对档案学的生存环境的研究。不论档案学者如何演绎,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档案学是适应一定的主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这些独立于档案学之外的主客观因素,就是档案学的生存环境。档案学的生存环境决定着档案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和自身的发展机理。比如,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定的“档案及其管理活动”基础;这种实践基础的层次和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档案学的理论水平。档案学概论作为一门关于“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的学科,如果缺乏对这种实践基础的清晰认识,就无法解析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及其管理活动”实践之间的特有关系,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学科定位和实质性的学术突破,当然也将妨碍其学科功能的体现。再如,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理论条件。这些理论条件是独立于档案学之外的、为档案学的学科建构提供直接相关的基本原理或基本模式的学科。档案学可以在这种“理论坐标系”中确定自身的位置和发展曲线,在科学学和方法论方面得到支持和滋养,从而减少研究的盲目性,提高学科建设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档案学概论应当注重对档案学发展史的研究。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有着自身的特有轨迹,档案学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档案学从其发生、发展到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在国外据说也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漫长的时间进程的各个具体阶段,档案学的研究活动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内容和特点,各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其特有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档案学概论作为一门关于“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的学科,其真正的理论只能寓于这些特有的历史范畴之中。史学家通常所说的“论从史出”,就是指的这个道理。笔者认为,档案学概论作为一门关于中国档案学的统领学科,当然应当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档案学发展基点上。事实上,我国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状况,以及其中赋予学科本身的种种“先天因素”,给了档案学概论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和学术领域;只有牢牢把握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才能自立于世界档案学术之林。
档案学概论应当注重对档案学研究主体的研究。笔者始终认为,档案学归根结底还是由人研究和发展的。档案学概论作为中国档案学的统领学科,如果缺乏对档案学特有研究群体的认识,就无法解释档案学的理论状况和发展前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档案学者的文化素质、知识结构、人生经历和生活地域等,都会给其研究成果赋予深刻的印记;这些印记的运动轨迹就表现为档案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原理及其发展过程。比如,具有相当外语水平的档案学者常常采用“他山之石”,以求攻“玉”;具有一定哲学功底的档案学者则希望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评价档案的价值;而常年从事实际工作的档案学者多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来描述档案学。因此,档案学概论作为一门关于“档案学各门分支学科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的学科,在评价和阐述档案学的理论成果时,就必须将这些特定的成果与其研究者的状况联系起来;在探求档案学的发展趋势时,也必须把这种学者因素考虑进去。只有这样,档案学概论才能真正成为“档案学之学”。
就一门学科的建构而言,当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总要产生一些对学科的本质及其相关问题的揭示与思考。这些具有一定抽象意义论题,往往成为概论类学科的形成条件。换句话说,概论类学科的产生和完善必须以相应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对学科本质问题的揭示程度为前提。因此,概论类学科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承载与反映学科的本质问题。简言之,此类学科就是为了阐释学科的发展规律而产生的。实际上,在档案学的理论体系中也只有档案学概论能够承担这种科学和历史的双重使命。当然,要想完成这种“使命”仅仅具备科学的理念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相应的学科模式(结构)与之相适应。而这种对学科发展模式的设计,并不同于对一种管理过程的描述,它不可能按照档案学传统学科的方法来进行,它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对科学本身的营造,需要其研究者对学科发展规律的驾驭和对学科命运的思考。由此可见,这种理论需求的实现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是与档案学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能动的行为,是档案学人的一种自我超越。
四、从中国档案学的结构演化看档案学概论的学科定位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社会的需要、学者的贡献和科学逻辑的完美结合。而分析这种“完美结合”的过程,就将成为探求学科发展规律的起点。如果从学科结构的发展顺序来看,中国档案学的演化可以表述为以下过程:
首先产生以档案管理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档案管理学,其学科结构主要为“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和“管理过程”三大内容。这些内容是作为一门管理学科不能缺少的。而管理科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提高效率和维护公平。在以档案管理学为代表的中国档案学的基本学科结构形成的过程中,这种基本的价值取向是通过政治——行政的推动力和档案学者的职业经历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说,作为管理(行政)科学的组成部分,中国档案学在学科结构的建构上必然首先关注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管理过程的设计。这种基本的理念体现在档案管理学中,则突出地表现为对“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模式。不论是中国档案学的早期著作,还是中国档案学的新近作品,都用了很大篇幅分析这种“管理模式”。以至每当人们论及中国档案学时就必然涉及档案管理学,而涉及档案管理学则又必然涉及档案管理的业务环节(程序)。这就使得档案“管理模式”成为档案管理学、乃至中国档案学的“代名词”,成为中国档案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因为如此,笔者曾经多次断言中国档案学是一门真正研究管理方式、管理程序的学科,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对管理过程(程序)进行系统分析。如果离开了这种学科的基本结构,中国档案学既不可能形成,更不可能发展。
随着管理活动的运动形式、层次和程度的发展,对其进行研究的学科也会出现一些“衍生”的形式。中国档案学演化的“第二步”,就是在对“管理过程(程序)的系统分析”的基本学科结构上“衍生”出“其他学科”。比如,档案文献编纂学就是典型的“衍生学科”;它实际上是以档案的一种开发、利用形式为依托,发展成为一门横跨历史文献学、编辑学和档案学的传播学科。现代档案学研究领域中“档案××学”的衍生机理都不过如此。在这些学科的“衍生”过程中,其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非职业经历”起着关键作用:正是他们的知识结构赋予其观察问题的视角,使他们能够从广博空间中去分析档案管理活动,从浩繁的科学体系中去审视中国档案学;正是他们的“非职业经历”赋予其挑战权威的勇气,使他们能够不拘泥于档案管理活动,敢于突破中国档案学的固有体系。当他们将上述“优势”转化为实践时,就意味着中国档案学众多“衍生学科”的产生。但是,从学科结构发展和演化的角度分析,不论此类学科自身的体系和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不能超出档案学为其设定的基本框架——它们只能是一种管理活动的“衍生物”,其学科结构的设置也只能以档案学的基本学科结构为基础。否则,它们就会从“档案××学”变为“××学”,进而失去在中国档案学中的位置。实际上,当这些“档案××学”退变为“××学”时,其“学术生命”就自然终止了——就像杂交水稻退化为野草一样,等待它的将是大自然的风霜。
当中国档案学的学术群落充分发达时,在其基本学科结构中就会演化出一种以“揭示档案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形式。这就是带有“学中之学”味道的“抽象结构”——档案学概论的产生。在最初的学科设计中,许多学者都期望档案学概论能够成为中国档案学中集中解决“基础理论”问题的学科,应当成为我国档案学理论中对“较为成熟部分”的总结。综观科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学科的发展和创制过程,在形成概论性质的学科方面大体有两种路径:其一是将该学科所涉及问题与分支进行综述。如情报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等学科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性质的概论一般都形成于该学科的建构之初,因此,所谓“概论”不过是该学科基本结构和轮廓的一种勾勒。其二是将该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特别是有关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加以系统概括。如史学概论、科学学概论等学科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性质的概论一般都形成于该学科的“学术群落充分发达时期”,因此,所谓“概论”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深层次思考,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从档案学概论的形成时间来看,它不应当属于第一种情况;但是,它又与第二种情况中的“形成要件”尚存距离。客观地讲,这种距离主要是指中国档案学目前并不处于“学术群落充分发达时期”:它还缺乏时间、学者和理论的准备。换句话说,我国档案学概论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行政干预”的影子——它是根据政府主管部门规划而产生的。笔者始终认为,“行政力”作为一门管理学科的“第一推力”是完全必要和科学的,因为它基本反映了社会管理的需求;但是,如果将这种“第一推力”当作学科发展的持久动力,则是违反科学发展规律的,因为它有时会破坏学科结构的内在平衡,使该学科在不恰当的时候“长出”不恰当的成分,进而浪费“理论资源”。也就是说,科学理论作为一种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中必然包含着许多“人为”因素。但是,要使这些“人为因素”能够真正转化为科学发展的“有用功”,只有依靠从事科学理论创造的主体对科学规律的感悟和把握。
中国档案学的学科结构及其演化规律是科学理论发展规律的一种具体体现,从中国档案学的具体学科状况看,它已经处在从“基本结构”向“衍生结构”过渡和发展的时期,并且已经出现了产生“抽象结构”的“萌芽”。但是,如果从学科结构整体去考察,中国档案学尚未处于“颠峰”状态。换句话说,一门学科的结构处于何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研究者的主观愿望——无论是学科的基本结构、衍生结构,还是学科的“抽象结构”,都是社会需要与科学逻辑的有机结合。在中国档案学的科学体系中,这种学科结构的位置和次序是不能颠倒的。否则,就要受到科学发展规律的惩罚。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能期望一个初生的婴儿同八十岁的老者一样慈祥。同样,我们也不能苛求一门形成仅仅十余年的学科就发展得十分完善。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那就是档案学概论已经具备了发展的基础,取得了“蓄势待发”的优势;而其目前的研究盲点和空白,却恰恰预示着其巨大的潜力和光明的前景。我想,这也是档案学概论的“制作者”们的期盼。
(北京市,邮编:1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