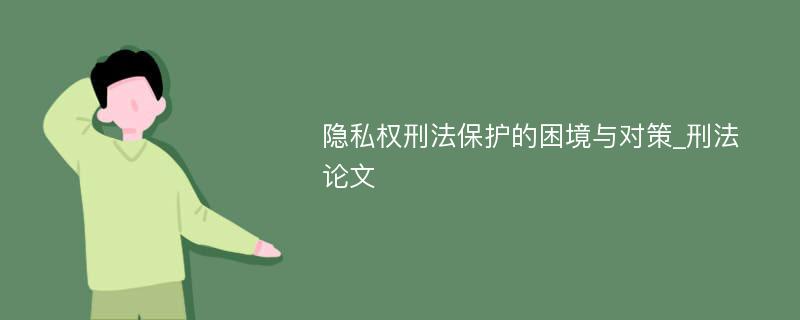
隐私权刑法保护之困境及因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应论文,刑法论文,困境论文,隐私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隐私权具有一般人格权的属性,而一般人格权是一种弹性权利,其最大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并且随着人类文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亦愈发丰富,对此几乎无法做出概括性的表述。隐私权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必然会使得隐私权刑法保护尤其是在犯罪化方面要遭遇诸多困顿。故此,隐私权刑法保护不应停留在对当下尚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定法的注释及应用上,而更应该开放视野放眼未来。隐私权刑法保护中所可能遭遇之种种窘迫与艰难等前瞻性、宏观性问题,都应纳入刑法学的研究范围之内。惟其如此,才能使隐私权刑法保护呈现出勃勃生机,并使其自身具备适应复杂多变社会现实之能力。
一、隐私权不确定性与犯罪化之困境
一般人格权是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由联邦最高法院以司法判例的形式,通过援引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2条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框架权利”,其突出特点在于“不确定性”,何种行为侵犯一般人格权、是否以及如何对之提供救济皆由法官根据个案进行判断。①因此,即使法律明确规定了“一般人格权”,也仅仅是搭起了一个“框架”,其具体内容须待生活现实填充,并由法官(不是制定法)根据具体个案情况进行自由裁量。②故此,一般人格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权利,并且随着人类文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范围及内容亦愈发丰富,对此几乎无法做出概括性表述。
隐私权属于一般人格权之范畴,一般人格权以捍卫人性尊严,呵护“人性尊严所溢流出的价值之自由为初衷,旨在概括、承接、保护尚在孕育中的自由权,防止法律保障产生漏洞。”③而隐私权自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此种使命。如在1972年的Eisenstadt v.Baild案中,法官已将私人应受宪法保障的隐私领域扩大至未婚妇女之避孕权利,接下来的案例更将隐私领域几乎涵盖到所有个人活动,如婚姻、性生活、堕胎、安乐死等方面。④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隐私权更像是新生权利萌芽成长的“孵化器”,而这也恰恰昭示着隐私权一般人格权之本性。如今,隐私权已形成一类似指导原则,而其保障范围也从一般独处权或个人信息自主权,进而发展到与人格密切相关之部分。“简而言之,隐私权最终保护之对象即为一般抽象性人格。因而,隐私权实质上与一般的人格权所扮演的角色相同。”⑤由是观之,隐私权与一般人格权具有极其紧密的内在关联,隐私权的内涵及其边界始终处于一种持续发展状态,并随时滋养出大量特殊人格权,符合一般人格权之不确定性及开放性之特征。
对于人格权的保护是刑法的必然内容,但是首先遭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犯罪化。犯罪化是刑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性问题,更确切地说,刑法学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研究何种行为应当予以犯罪化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犯罪化。“犯罪化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指如何界定刑法涉足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确定犯罪圈、刑罚圈大小的问题。”⑥一般认为,某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之犯罪化,同时会牵涉形式及实质两个侧面的理论问题。单由形式面来看,犯罪化是立法者行使立法权的权力决断,由此而言,“(立法)犯罪化指的是透过刑事立法的方式,创设一新的刑事不法构成要件,并赋予其刑罚法律效果,使其成为刑法规范中明定处罚之犯罪行为。”⑦立法者是以何标准决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我们固然可以采取极端实证主义的立场,认为当立法者认为什么是犯罪时,它就是犯罪。⑧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⑨毕竟何种行为属于犯罪并不是立法者突发奇想随心所欲之创造或一时兴起拍拍脑袋想当然的结果。因此,犯罪化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更应当考虑其实质之层面,故而“立法者必须先观察哪些已发生的生活事实可能需要动用刑法加以规范,接着针对此些生活事实进一步透过犯罪学、法社会学的研究得到一个初步的确认,经过此种初步确认的特定事实于此已经成为一具有法律与社会交互影响关系的法事实,再藉由刑事政策与刑法理论的观点加以评价筛选。”⑩与实质层面的犯罪化理论相一致,在严重侵犯隐私行为的犯罪化过程之中,一方面应当确定何种侵犯隐私的行为具有刑法意义上之严重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在对该种严重社会危害性之行为做出确认之后,仍需经由刑事政策或公共政策之价值衡量来最终断定该种行为是否有进行刑事处罚之必要性。
犯罪化是实现隐私权刑法保护的必经之路,但由于隐私权具有一般人格权之属性,不确定性是其重要特征,故此,与隐私权不确定性的狭路相逢注定会使得这种犯罪化困境重重。就严重危害隐私权行为的犯罪化而言,无论是对该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确定,还是对该种行为做进一步之筛检,以确定该行为刑事处罚之必要性而言,都会遭遇隐私权不确定性所招致的种种困境。
隐私权法益范围具有不确定性,这也是隐私权一般人格权属性的应有之义。而隐私权法益范围之不确定性,必然导致隐私犯罪的法益侵害无法准确界定。而刑法本质上是一部法益保护法,而法益先于刑事制定法而存在,具有高于实定法之属性。“不可能从现已存在的各种法定构成要件中发现法益概念,而必须从前实定的领域中寻找法益的实质定义。”(11)准确地说,法益并非立法者之发明而是其对既存利益的发现与立法确认。“法益是先于立法者制法之前而存在,法益保护是制定刑法规范的理由和追求的目标,只有行为侵害了受保护的法益,才具有非难性与应受刑罚性。”(12)而犯罪也因此应具有侵害法益的本质,刑事政策上对于运用法益概念来寻求可罚性界限的需要亦随之相对提高。“简单来说,无法益保障即无刑法规范。如有不清楚时,则无可罚性的原则也因此得以确立。”(13)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山田教授亦认为,所谓犯罪化“系指针对某一破坏法益的不法行为,经过刑事立法政策上的深思熟虑,认定非动用刑罚的法律制裁手段,无法平衡其恶害,或无法有效遏阻者,乃透过刑事立法之手段,创设刑事不法构成要件,赋予该不法行为刑罚的法律效果,使其成为刑法明文规定处罚的犯罪行为。”(14)因此,没有具体明晰之法益即无犯罪化之必要性。
而隐私权法益的范围则难以界定,隐私权所及的范围应当以是否属于私人生活领域为准,而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却不存在明显之边界,从而导致隐私权法益的边界也非常模糊且容易迁变。(15)因此,以何标准确定某一事项属于个人的隐私以及进而确定某行为是否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将异常困难。这必然会使严重侵犯隐私行为的犯罪化丧失标靶,从而无法完全罗列出现存的所有隐私犯罪。另外,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传播媒体、新兴资讯、技术、监控设备、资料库发展、经济与社会形态成长、人际关系日趋疏离与复杂,加速了隐私权侵害之变化可能性,导致了隐私权内涵常随时代变化而迁变。而社会变动牵连隐私权益范围的不断调整,会使得先前进行的犯罪化时常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并因此使该犯罪化迅速丧失意义。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隐私权公共政策也具有动态性,因此即便准确断定某一行为实质上侵犯隐私法益,也应当考虑法益均衡及处罚必要性,不能不加辨别而轻易对其进行犯罪化。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甘添贵教授所言:“刑法之任务,虽主要在保护法益安全,但社会伦理亦在同时维护之列。因此,判断行为有否处罚之必要性以及是否成立犯罪,应先视其对于法益有否造成侵害或危险,以为决定。以对于法益造成侵害或危险,作为认定犯罪之最外围或最大限。在已对于法益造成侵害或危险之前提下,再视其侵害法益之行为态样,有否违反社会伦理。倘亦违反社会伦理时,即可肯定该行为具有处罚之必要性。”(16)仅就现实生活而言,具有严重侵扰隐私而不能以专门立法予以犯罪化的行为不胜枚举。如喧嚷视听的“人肉搜索”,尽管其能够对个人隐私构成致命威胁而被称为隐私权的“骨灰级天敌”,但在网络社会中,其首先仍然是公民表达自由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对此不可过分压制;其次,“人肉搜索”以公序良俗为基点,基本上是以针砭时弊、惩恶扬善为主旨,已经具有张扬公益的“向善”倾向,并因此而获得相当强大的主流社会伦理的支持。即便通常之“人肉搜索”行为可能会危及公民隐私权,但从立法层面将其犯罪化是难以获得社会伦理以及普通民众的集体认同的。然而,在实践中亦不能排除存在某种极端性“人肉搜索”行为,其单纯为了自娱或其他利益而放弃公益之限制,并因此严重侵犯他人隐私。该种行为已然超越公共表达之界限,亦为社会伦理所不容。因此,从隐私权公共政策之角度观之,刑法难免会在“人肉搜索”行为方面左右摇摆,既不能在立法上将其犯罪化,(17)又不能全然放弃某种情况下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可能性。对此如何取舍,显然是隐私权刑法保护中值得认真思考的难题。
二、隐私权刑事保护的方法论前提——刑法开放性应对措施
隐私权具有一般人格权之属性,随时会变化模样,因而使得对严重侵犯隐私行为的犯罪化困难重重。但刑法对此并非束手无策,其完全可以针对隐私权之不确定性,设计某种具有弹性、机动性与开放性之措施,进而力图将各种严重侵犯隐私的行为一网打尽。
刑法开放性措施是本文针对隐私权刑法保护之困境而专门提出之命题,亦是对古典罪刑法定思想的反思和矫正。罪刑法定是刑法基本原则之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其经典表述。犯罪和刑罚事先都是由立法者所预先设定,是否就意味着以罪刑法定原则为依托的刑事立法也会因此而凝固成一个僵硬而封闭的系统呢?李斯特就曾为刑法科学设计了这样的封闭框架,即“在纯粹的法学性和技术性的考虑中犯罪和刑法应当作为概念性的概括来加以思考;法律的各个条文在一直向最后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升华中,应当发展为一个封闭的体系。”(18)因此在古典刑法学者眼中,受罪刑法定原则之禁锢,刑法应该是一个外延封闭和理论自洽之体系,其已经预计到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并安排好了答案,司法者仅需依照刑法按图索骥,便可实现刑法之目的。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及理性的局限性,刑法从未生产出古典刑法学家所许诺的输入问题即给出答案的“刑法万能公式表”。(19)许乃曼因此指出:“人们必须从一开始就阐明,从仅仅具有很少公理性的上位概念中引导出来的一个封闭的演绎性体系,就像现代学术理论为数学和逻辑学所塑造的样板体系一样,在法学中不仅没有被严肃地尝试过,而且本来也是不能实施的。”(20)因此,人们可以制定一个确定的、永恒的刑法规则体系,只要从这个体系出发,然后再通过纯粹的逻辑运算,“一个包罗万象甚至连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缺的法律体系可以推导出来”的愿望永远都不可能实现,“这种法理学方法已是昨日黄花了”。(21)
事实上,刑法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刑法中不仅存在着诸如“开放式构成要件”、“空白罪状”、“例示法立法模式”等实体性弹性规范,而且还存在“期待可能性”、“客观解释”、“社会相当性”等赋予刑法开放性的理论。(22)而且,即便是传统刑法所认为的绝对封闭的规范也是开放的。“甚至,封闭的构成要件一直是相对的,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及人类语言的模糊性、边缘性等角度来说,并不存在真正封闭的构成要件,所有构成要件其实都可以说是开放的。”(23)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刑法应当是开放而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而刑法的开放性也是本文为应对隐私权之不确定性而专门提出“例示法立法模式”、“模糊性规范”、“刑法客观解释”、“司法犯罪化”等刑法开放性措施的基本前提。
1.例示法立法模式。就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而言,列举式规范是最为理想的立法模式,也颇受中国刑法青睐。(24)然而,由于现实生活的多姿多彩以及人类语言概括能力的有限性,刑法对于某些犯罪即便采取再为详尽复杂之列举亦难以穷尽该类行为的全部。如就我国《刑法》第198条保险诈骗罪而言,立法者以列举式规范将其客观行为限定为“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等5种行为。在此,立法者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立法能力,因为此5种行为之外的与保险事宜有密切关系的诈骗行为还有很多,如恶意重复保险、隐瞒保险危险、被保险人自伤自残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以其性质而言,都应归属于保险诈骗罪。或许立法者可以继续以列举式规范将这些行为补充进《刑法》第198条,但这种努力不仅会使得保险诈骗罪的条文庞杂,而且会出现越是具体细致反倒越是破绽百出的现象。
与僵硬教条的列举法立法模式相比,例示法立法模式能够体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例示法是在对犯罪构成诸要件进行表述时所采取的,列举法和概括性话语相结合的一种立法模式,其首先体现在对客观行为的描述方面。“例示法,对行为的方式、方法、手段作了比较详细的列举,同时以‘其他方法’防止刑法描述的遗漏(即存在‘兜底’规定)。这种模式因为存在‘其他方法’的规定,所以,其规定或列举的行为具有举例性质。与列举法相比,例示法更能对应社会生活事实。”(25)但同时,例示法也体现在对犯罪主体或犯罪对象的列举与概括中,如我国《刑法》第261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难看出,该条即采取了典型的犯罪对象的例示法立法模式。在欧陆刑法中,例示法是一种常用的立法模式,究其存在之原因,德国学者考夫曼曾深刻地指出:“类型无法被‘定义’,只能被‘描述’。因此,对立法者而言有两种极端情况:或者整个地放弃描述类型而只给予该类型一个名称。例如我们在德国《刑法》第185条所看到的,该条仅简单规定:‘侮辱’将如此如此处罚。此方式将使法律的适用上获得较大的弹性,但相对地也换来法律的不安定性;或者试着尽可能精细地(‘列举地’)描述类型,例如德国《刑法》第250条加重强盗罪之规定。此种方式具有较大法律安定性之优点,但也造成谨慎拘泥以及与实际生活脱节的结果——耗费大而收获小(事倍功半)。前面曾提过的‘例示法’——这在新的刑法典中经常被运用,例如在加重窃盗罪(德国《刑法》第243条)——则取二者之间而走中庸之道;立法者只例示性地描述类型,因而明白地指示法官可使用类推的法律发现。”(26)概言之,“例示法是概括条款与个案列举法的一种有机结合,它既能保障刑法的安定性,也赋予法官对此类或类似的案件作出同样处理的任务,既能对应社会生活事实,也能限制法官权力。因此,现代刑事立法越来越愿意采取例示法。”(27)
例示法是一种弹性的立法模式。其首先关注“抓大”,即明确罗列出常规性、典型性的犯罪类型,并藉此解决通常情况下的一般性犯罪问题。但例示法在“抓大”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打小”,其在实现对常规性犯罪类型涵盖的同时,并不放过对异常情况下的特殊性犯罪类型的包容。故此,该种立法模式可以基本上做到刑事法网严密,法益保护周至,凡此类型之事态,无论巨细皆在刑法掌握之中。
2.模糊性规范。对于新型犯罪的犯罪化而言,立法者唯恐有所遗漏,一般都会倾向于对其犯罪构成进行具体而详尽的描述。但需要指出的是,详细性不等于明确性,“法律明确性之要求,非仅指法律文义具体详尽之体例而言,立法者于立法定制时,仍得衡酌法律所规范生活事实之复杂性及适用于个案之妥当性,从立法上适当运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而为相应之规定。”(28)过于详细而具体的条文表述,往往会适得其反,使得条文的意义与范围复杂、混乱进而丧失明确性。因此,“如果概念仅止于掌握事物闭锁且单义的特征,那么也只剩数字。因此为了能够更为周全地规整各式生活事件,法律概念的运用也不应该放弃抽象化的概念。”(29)形式化、抽象性、一般性以及概括性在法律规范中亦无可避免,适度的抽象与概括、中性的言说与表述可以使犯罪构成有一个清晰而固定的核心,同时亦可以保护弹性开放的界限。即使立法时不曾存在甚至不能预见之事实,亦可包容在抽象性模糊性条文中。同时,“从价值取向上讲,如果说刑法的精确性旨在限制刑罚权的发动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着重体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那么,刑法的模糊性则有利于推动刑罚权的发动,重在体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人权保障固然重要,社会保护同样不可轻视;特别是在社会治安比较严峻,各类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犯罪、跨国犯罪日趋严重的形势下,适度设立一些模糊性、柔软的、概括性的规定,对于强化刑法的适时性、灵活性与超前性是很有必要的。适度的模糊性也是刑法规范保持其生存所必要合理张力的必要条件。”(30)而事实上,“从各国刑法典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来看,不确定的刑法规范与模糊的构成要件用语,正是构成要件立法的现状。明确性只是相对的,不明确在所难免。”(31)在中国刑法中,模糊性规范更是随处可见,如《刑法》第20条第3款所使用的“行凶”、第227条第1款所使用的“倒卖”、第247条所使用的“暴力”、第267条第2款所使用的“凶器”,甚至第14条所使用的“故意”等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事实上,刑法中绝大多数词语并非绝对清晰,因为“词句并不构成小小的水晶石,以其坚硬的外形把词句所隐含的内容与所有别的分离开来。在边缘地带,所有的词句都是模糊难懂的。”(32)因为任何词语都具有中心清晰、边界模糊的空缺结构特征,(33)故刑法也不可能将所有具有模糊性的词语驱赶殆尽,而恰巧是这些模糊性规范,让刑法规范充满弹性,从而能够在条文字面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大大提升刑法规范的实际容量,进而使得刑法规范得以在必要时能够随时扩展条文的实际内容,用有限的条文包容更多的犯罪行为。
3.刑法客观解释。由于隐私权的不确定性,且随着社会之发展,仍会在将来出现一些当下刑法所无法预测的侵扰隐私权的具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保持刑法条文的相对稳定性,刑法可以考虑采纳客观解释论,以解决某些局部性细节问题。
刑法需要解释,“法律不是摆在这儿供历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有效。”(34)而在刑法解释上存在两种对立之观点。传统之主观说认为,法律的解释目标应在探求历史上的立法者事实上之意思;而时下更为流行的客观解释论则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即在发现法律的内在意旨,是故司法者应当客观地确定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然后在其范围内挑选出最符合刑法目的并且最合乎时代要求的解释结论。刑法客观解释论者径直将解释对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常理、人之常情。因为立法者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在立法时考虑到未来世界的模样,所有对立法者过分的顶礼膜拜与盲目追随都是愚蠢的。否定过时的“立法意愿”,而赋予其崭新内涵正是对立法的尊重。
事实上,两种解释论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其在刑法所应持有的是开放性或是封闭性之立场上的大相径庭。刑法主观解释论主张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应以探求“立法者原意”为唯一目标,因此“立法者原意”应被固定在立法之中,不可能再有拓展变动的空间,因此刑法主观解释论实质上就是一种封闭、停滞的解释论。而客观解释论者则认为,“新的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现象,强烈要求根据现有的法律规范作出法律判断……因此,我们就处在比历史的立法者自己所作的理解‘更好地去理解’制定法的境地之中。设想我们从当代,带着几十年的问题,回到与我们根本无涉的立法者的意志中,不可能是我们的使命。”(35)刑法客观解释论不拘泥于过去的立法意图,不受缚于规范的外在形式,致力于从刑法规范中探求刑法规范的目的,洞察刑法规范可能的合理内涵,变动的社会现实始终是其目光的最终投向。开放性是客观解释论的重要属性。而对于客观解释论的开放性,诸多学者曾予以盛赞。“萨维尼曾谓:解释法律,系法学的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的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如果解释仍停滞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偏重主观说解释之面向,而着重于探求立法者之意思,则法律之发展,仍将受制于已作古人的意志而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法律的释义学在今日随着民主法治国与社会国原则的开展,不得不着重于客观说之面向,阐释法律本身在这个时代所应蕴涵之意旨。法律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即谓:法律犹如船,虽由领港者引导出港,但在海上则由船长指挥,循其航线而行驶,不受领港者之支配,否则将无以应付惊涛骇浪与变异的风云。康德亦谓:解释者较诸作者本人,更能认识自己。”(36)
笔者也较为推崇客观解释论之立场,法律解释并非在找寻法律背后之个人创见,而是在探究法律本身之意义。赋予作品比创作者自身所知更深沉的意义,此乃人类创作的神秘力量,也是作品能在新时代体现出新意义的思想源泉。(37)而客观解释论所呈现出的开放性特征能够保证刑法在条文稳定的情况下与时俱进,大体上适应社会发展,因而更应该被大力提倡。在欧陆刑法中经过长期的角力,客观解释已然占据不可动摇的主流地位,并且因此使得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的发展能够和社会客观需要形成丝丝入扣的相契与衔接,尤其是在分则方面更是如此。如“按照日本刑法的规定,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是盗窃罪,而所谓财物,按照民法的规定,是指有体物,而电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物,难以符合人们心目中的有体物的观念。但是,当时电力是一种很珍贵的资源,对盗用电力的行为不处罚的话,显然不能保护电力公司的利益。于是,司法机关通过解释,认为电力是可以管理之物,应当属于盗窃罪中所谓的财物,因此,盗窃电力的行为也是犯罪,从而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38)显然,将“电力”作为“财物”,也是客观解释论贡献所在。
4.司法犯罪化。“人肉搜索”、垃圾短信、垃圾邮件等虽危害隐私利益,但基于隐私权公共政策之动态性,亦不能对其立法犯罪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上述侵扰隐私行为熟视无睹。在此,本文将引入“司法犯罪化”的概念,并借刑法解释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39)
“司法上的犯罪化,也可谓解释适用上的犯罪化,即在适用刑法时,将迄今为止没有适用刑法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新的解释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决定了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需要很长的过程;而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随时都可能发生。”(40)
在法治社会中,“立法犯罪化”自然是较为理想的犯罪化方式,也更能迎合罪刑法定原则。但“立法犯罪化”在法治国家中深受繁琐而冗长的立法程序限制,在此过程中,仅仅依靠“立法犯罪化”必然会使得大量新型犯罪行为游离于刑法之外。而相对于“立法犯罪化”对社会危害行为的反应缓钝,“司法犯罪化”本身没有过多的限制条件,能够及时方便地填补“立法犯罪化”所遗留的处罚间隙。“一般而言,对于某一种会影响或会改变人类行为的新事物或新社会现象,我们并不会立即制定一个新的法律去规范因应,因为我们尚无法判断其是否会对社会生活形态有根本的改变。我们会试着将其纳入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中,试着用解释的方法,将现行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及于该新事物或新社会现象。如有相当实际案例的累积显示这种做法并不符合社会正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即会检讨调整现行法律,并尝试修正现行法律或制定新法,以作合理的规范。”(41)“例如,我国刑法并没有像国外刑法那样规定超速行驶罪、酒后驾驶罪,直到现在,司法机关一般也没有将超速行驶、酒后驾驶以犯罪论处。但是,这并不排除刑事司法将部分严重超速行驶、醉酒驾驶等行为,依照刑法的相关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司法解释完全可能做出如下规定:对于以超过规定速度2倍以上的速度驾驶机动车辆的,或者因醉酒或吸食毒品而丧失驾驶能力后仍然驾驶机动车辆的,以《刑法》第114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在‘两高’没有做出这种司法解释时,下级司法机关也可能对上述行为以该罪论处。这种情形亦可谓‘适用上的犯罪化’。”(42)又如,尽管先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并未出现过骗购经济适用房这种崭新的犯罪现象,但这也并不妨碍司法者开动脑筋,对该种行为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以合同诈骗罪、伪造证件罪、玩忽职守罪对骗购者及其相关国家工作人员定罪处罚。
因此,立法犯罪化和司法犯罪化应是适应社会发展的两种相得益彰之方法,而“司法犯罪化”是“立法犯罪化”的有益补充。为了有效应对新型犯罪的出现,在立法对该种犯罪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司法犯罪化”能够对“立法犯罪化”的不作为提供有效救济。(43)这也为刑法保护隐私权设定了基本前提。
三、刑法开放性措施在隐私权刑法保护中的应用
维护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刑法当仁不让的职责,即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巨变时,刑法也应当始终保持规范与生活事实、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动态平衡。而刑法开放性措施是刑法规范和社会事实进行沟通交往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工具,其之所以有强大生命力,在于其始终面向实践、面向发展着的现实开放自己,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其灵活性、柔韧性、开放性有助于司法者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面前,遵循法律偏爱人情、照顾人生的基本精神,使得刑法得以对变动的社会现实做出及时、准确的调整和回应。隐私权固然具有变动不居之不确定性,但若在隐私权刑法保护中,让诸如“例示法立法模式”、“模糊性规范”、“刑法客观解释”、“司法犯罪化”等极富弹力的刑法开放性措施充分施展手脚,则必能使隐私权获得刑法细密的保护。
1。例示法立法模式在隐私权刑法保护中的应用。由于隐私权之不确定性,其权利边界始终处于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因而列举式立法模式对其难以发挥效用。如日本《刑法》第134条规定的泄露秘密罪就是隐私权刑法保护中典型的列举式立法模式。该条规定:“贩卖者、助产士、律师、辩护人、公诉人、证人或者曾经从事此类职业的人,无正当理由,泄漏由于处理业务而知悉的他人秘密的,处6个月以下惩役或者10万日元以下罚金。从事宗教、祈祷或者祭祀职业的人或者曾经从事此类职业的人,无正当理由,泄漏由于处理业务而知悉的他人秘密的,与前项同。”(44)尽管其对犯罪主体的列举繁琐冗长,但仍然遗漏了诸如网络销售、物流企业、公共服务网站、房产公司等众多有可能通过自己职务行为掌握个人信息并进行贩卖的情况。而作为一种重要的刑法开放性措施,例示法立法模式则能在隐私权刑法保护中大有作为。显然,若在此处对该罪犯罪主体采取例示法立法模式,在条文中增加“以及其他因业务原因知悉他人信息者”的规定,则能够完全涵盖行为人泄漏自己在业务活动中所知悉的雇主隐私的背信行为,从而使刑法规范体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与适应性。
事实上,我国的隐私权刑法保护也应当积极采纳例示法立法模式,对某些容易引起争议的隐私权刑法保护规范进行修正。如近年来某些行政机关和电信、金融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将其在履行公务或提供服务活动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泄露,业已严重侵扰了公民私人生活的静谧与安宁。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七)》第6条设置了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45)该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收买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本罪之犯罪主体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该条文在列举行为人所属各种单位之后用“等”字作结尾而未像例示法立法模式那样附加“以及其他单位”,因此,本罪之犯罪主体是否应当包括诸如购物网站、物流企业、猎头公司、中介组织、市场调查公司、房地产公司,尚不无疑问。
在汉语中,“等”字用于列举之后有三种解释:(1)用在人称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面,表示复数,如我等、彼等;(2)表示列举未尽,如北京、天津等地,纸张、文具等等;(3)列举后煞尾,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46)而在刑法中,如何理解具体法条中“等”的真实含义则至关重要。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法律中,有时一句话或一个字就能影响到人的生命财产、企业的活动、机关的职责,法律用语发生错误,会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性,并导致破坏法制。”(47)而在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中,对“等”字含义的理解则更是如此。尽管笔者认为,刑法中的“等”字应当理解为列举未尽,(48)而对于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中的“等”字也应做如此理解,但明确性是对刑法规范的一个基本要求,在需要明确并且能够明确的场合,刑法完全不必故弄玄虚,将一个能够明确表达的概念或能够明确界定的范围故意弄得含糊不清。因此,立法者在此处也应当采取例示法立法模式,将该罪犯罪主体表述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从而消解本罪之犯罪主体是否应当包括诸如购物网站、物流企业、猎头公司、中介组织、市场调查公司、房地产公司之争议。
2.概括性抽象性条文在隐私权刑法保护中的应用。对于严重危害隐私行为的犯罪化而言,由于隐私权之不确定性,因而隐私权刑法保护规范在设计隐私犯罪罪状,采取抽象性模糊性的表述上就显得尤为重要。“概括性抽象性条文”表述都是典型的模糊性规范,其在应用效果方面,较之明确性规范反倒更能够适应隐私权不确定性的特征。如同样是处罚基于正当原因获得并泄漏他人隐私之行为,在德国《刑法》第203条的侵害他人秘密罪的规定中,立法者为力图条文明确不厌其烦地详尽罗列了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侵扰隐私的各种行为,即便如此,竟然还遗漏了诸多有可能通过自己职务行为掌握个人信息并进行贩卖的情况。(49)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第189条将违反保密罪罪状表述为“未经同意,泄漏因自己之身份、工作、受雇、职业或技艺而知悉之他人秘密者”。其虽外表模糊但涵盖宽泛,实质效用远胜于德国刑法之侵害他人秘密罪,事实上已经能够将违背保密义务泄漏他人隐私的行为一网打尽。同时,在隐私犯罪的罪状设计中,可以采用更加具有抽象性与包容性的词语,如用“通讯”而不是“通信”、用“信件”代替“书信”、用“散布”代替“泄漏”、用“工具”代替“器材”,等等。尽管从表面上来讲,这些用语似乎较为笼统、模糊,但却更符合法益保护的要求,因此能在隐私权刑法保护的司法实践中取得“以柔克刚”之良好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而在隐私权刑法保护中大量采取模糊性规范是否和罪刑法定原则相抵牾呢?笔者认为,法律规范明确尽管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者如何在具体语境中,对规范的表述不至于使人产生歧义。(50)其实“由于语言(与认识意识相关)是思考与传达信息的工具,因此,所要求的明确性程度是随着使用目的的不同而变化的。像木匠、外科医生根据其需要分别使用各种精确的刨子、手术刀一样,我们通常应当选择最能适合达到目的程度的明确语言,不必要的高度的明确性,与不充分的明确性一样,反而妨碍目的的实现。所以,刑事立法要注重法条的表述、描述是否有利于法条目的的实现。”(51)任何概念或命题都有其独特的适用语境,即便某些隐私权保护规范在表述上抽象而模糊,但只要其借助具体语境可以达至立法意旨,都不应认为有悖罪刑法定的明确性要求。(52)
3.刑法客观解释在隐私权刑法保护中的应用。在传统社会中,隐私利益一般集中在私人住宅及个人体态,故传统隐私犯罪及刑法也都将重点倾注在侵犯住宅罪及非法搜查罪(客体为私人住宅及个人身体)。而传统的通信一般也仅限于书信往来,刑法中的侵犯通信自由就自然不包括电子邮件及包裹。但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及科技手段的应用,传统刑法已经不适应隐私保护的切实需要。对此,刑法可以在条文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对相关概念做出客观解释。如可以将“住宅”解释为“私人空间”,因此,诸如汽车、船只、航空器甚至暂时容身的酒店客房、户外帐篷都可以视为住宅的特例,对上述场所及其中存放的手机、笔记本、日记等物品的非法搜查都可以成立非法搜查罪。同理,将侵犯通信自由罪中的“开拆”解释为包括“查阅”等内容,就可以将运用科技手段、在封闭状态下查知信函内容的行为包括在内;而将“信件”解释为“书信和物件”,由此可将书信、图片、影视录像、电子邮件、QQ或MSN聊天记录等搜罗网尽。只要是未经允许探晓上述物品及其内容的,均可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定罪处罚。
不仅如此,刑法客观解释在填补隐私权刑法保护规范漏洞时还能发挥无可替代之独特功能。仅以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为例,该罪的客观行为方面存在明显的漏洞。该罪仅规定对“出售或非法提供个人信息”行为的处罚,却忽视了上述机构工作人员亲自散布自己掌握的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事实上,之所以对“出售或非法提供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处罚,就是为了防止公民个人信息因被非法散布后而广为人知,从而损害隐私权人的人格尊严。因此,从发生学角度来讲,“出售或非法提供个人信息”行为应当是“非法散布个人信息行为”的上游犯罪,其社会危害必然要通过随后的“非法散布个人信息”才能彰显。对“出售或非法提供个人信息”以及“窃取、收买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等行为的刑事处罚,应当被视为“非法散布公民隐私信息”的一种处罚早期化的条款。对于“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隐私信息”的行为固然应当予以打击,对“非法散布个人信息”的行为则更应当严厉惩罚。
尽管立法上对“非法散布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处罚付诸阙如,存在严重的漏洞,但刑法本质上届于一种实用性知识,因此,对刑法漏洞无论是冷眼旁观,还是攻伐鞭挞,都不应当是刑法学人应有之态度。刑法学研究之目的并非仅为发现漏洞,而更应当施展才智,运用技巧,消弭缝合这种漏洞。“不要以为,越是能设定刑法‘漏洞’,就越有学术成就。因为刑法学的任务不是设定漏洞,相反应当合理地填补漏洞。没有人会认为,能将谋杀解释为无罪,是学术上的辉煌成就和罪刑法定主义的伟大胜利。”(53)刑法客观解释论是填补刑法漏洞的重要理论,刑法客观解释论者径直将解释对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常理、公平正义,并根据社会客观需要,对立法进行创造性解释,追补更正立法之不足,并作出符合同时代一般社会观念和刑法精神的解释。而依照刑法客观解释论,司法者可以将上述行为以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本文将对刑法客观解释论及其在本罪中的适用予以详细论证。
填补非法散布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处罚漏洞,应当是在客观解释论的势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提供”一词之本意为“提出可供参考或利用的(意见、资料、物资、条件等)”,(54)仅从字面意思来讲,“提供”行为中,被提供者一般都是确定的单个人或少数人,如《刑法》第156条规定的“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第226条规定的“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第310条规定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这些条文中的“提供”一词均可作上述理解。而在“散布”行为中,被散布者则为不确定的多数人,如《刑法》第221条规定的“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被散布者即是不特定多数人。因此,“提供”和“散布”的含义存在明显差异而不能互相代替,仅依字面解释,非法散布个人信息似乎难以成罪。
但此时司法者完全可以对“提供”一词做出符合司法实践需要的客观解释。尽管在通常情况下,“提供”和“散布”的含义迥然相异,但“一个词的通常的意义是在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因此,当一个看来是属于某一词的意义范围内的事物出现时,它好像就被自然而然地收纳进去了。这个词语的词义会逐渐伸展、逐渐扩张,直到人们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将应归入这个词名下的各种事实、各种概念都包含了进去。”(55)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及新情况的出现,“提供”一词的含义也在发展,向特定对象“提出可供参考或利用的(意见、资料、物资、条件等)”固然是常见的提供行为,而“散布”这种向不特定对象“提出可供参考或利用的(意见、资料、物资、条件等)”也可以解释成一种偶见的提供行为,因此,“散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提供”,非法散布个人信息的行为自然也能够以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56)
4.司法犯罪化在隐私权刑法保护中的应用。现实生活中,对个人信息威胁最大的行为莫过于“人肉搜索”,在《刑法修正案(七)》制定时,也曾有专业人士疾呼对“人肉搜索”进行犯罪化。(57)但“人肉搜索”不仅是公民表达自由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而且大多数“人肉搜索”之初衷为张扬公益。对其进行立法犯罪化则有可能伤及普通民众的伦理感情。然而,在实践中亦不能排除存在某种极端性“人肉搜索”行为,其单纯为了自娱或其他利益而放弃公益之限制,并因此而严重危及个人信息安全。该种行为已然超越公共表达之界限,亦为社会伦理所不容。尽管刑法不能对“人肉搜索”进行立法犯罪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会听任恶意“人肉搜索”者为所欲为,司法犯罪化则是解决“人肉搜索”问题的最佳路径。
借助“司法犯罪化”手段,刑法完全也可以在保持立法相对稳定,不增加、不修补现有刑法条文内容的情况下,将某些不具备社会伦理性及正当性的“人肉搜索”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将“人肉搜索”适当分解为若干具体行为,并借助“司法犯罪化”理论对各具体行为具体认定,应当是刑法处置“人肉搜索”的最佳路径。如在“人肉搜索”中,对他人恶意嘲笑、辱骂,或散布他人的生活隐私、生理缺陷等,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会因此而涉嫌侮辱罪;若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也可以诽谤罪定罪处罚。而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机构以及购物网站、物流企业、猎头公司、中介组织、市场调查公司、房地产公司中负有保守个人信息义务的相关从业人员在“人肉搜索”中,故意泄漏他人个人信息的,自然会成立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因此,司法者可以采用“司法犯罪化”策略,对于符合该罪犯罪构成的部分恶意搜索行为定罪量刑,而不必坐等刑法修正案或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规定,从而遏制恶意“人肉搜索”行为的发生。
注释:
①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②参见朱庆育:《权利的非伦理化:客观权利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命运》,《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
③张万洪、徐亮:《隐私权本质的解析与界定——隐私权的法哲学反思》,《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④参见詹文凯:《隐私权之研究》,台湾大学法研所1998年度博士论文,第42~43页。
⑤蔡佳峰:《新兴科技下信息隐私权保障之研究——以无线通讯、低射频辨识系统为中心》,台湾中正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6年度硕士论文,第13页。
⑥游伟、谢锡美:《犯罪化原则与我国“严打”政策》,《法律科学》2003年第1期。
⑦林山田:《刑法的革新》,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28页。
⑧实证主义的法理论反对法学者试图超越现存的法律制度而去识别与阐述法律思想的企图,要求将价值考虑排除在法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将法学的任务限制在分析实存法律制度的范围之内。只有国家确立的法律规范,才是其研究的法。因为实证法的观点不问法律的道德问题,亦即不问法律内容的应然问题,所谓法律,乃成为“立法者所创造的法律,亦即人类的权利以意志行为创造的法律。”对此可参见颜厥安:《法与道德》,《台湾政治大学法学评论》第47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页。
⑩高金桂:《利益衡量与刑法之犯罪判断》,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1页。
(11)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12)丁后盾:《刑法法益学说论略》,《刑事法要论——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13)参见郑昆山:《台湾刑法改革之理论与实务》,载翁岳生主编:《刑事思潮之奔腾:韩忠谟教授纪念论文集》,2000年作者自刊,第389页。
(14)同前注⑦,林山田书,第154页。
(15)究竟是以主张隐私权人主观上所认定之私领域为准,还是以社会上一般人所合理期待为私领域之范围为准,在理论上也无定论。即便是相对客观的社会一般人的认识,也是随着地域的不同或社会的变动而大异其趣。如堕胎及安乐死问题,在美国属于隐私自决权范围,而在当下中国却与隐私权毫无瓜葛,但其未来之发展趋势实难预料。又如犯罪记录当属个人绝对隐私,但是否所有种类的犯罪记录都应当作为一种隐私法益而为刑法刻意照拂?何以美国在保护这种隐私的同时,又出台《梅根法》要求性犯罪者自我曝光?这些争议的存在都可归咎于隐私权的边界不明。
(16)甘添贵:《犯罪除罪化与刑事政策》,载《罪与刑——林山田教授六十岁生日祝贺论文集》,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626页。
(17)本文于此强调的立法犯罪化概念,是与下文的司法犯罪化相对应。
(18)[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19)事实上,除了1804年《法国刑法典》之外,也很少有国家做类似的立法尝试。
(20)同前注(18),克劳斯·罗克辛书。
(21)[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22)关于刑法开放性的更多知识背景介绍,可参见王立志:《开放的刑法及其路径》,载谢望原主编:《刑事政策研究报告》第2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411页以下。
(23)刘艳红:《开放的构成要件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24)我国《刑法》分则中到处可见列举式规范,如第96条强奸罪、第263条抢劫罪等都是典型事例。
(25)张明楷:《日本刑法典的发展及启示》,载《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26)[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3页。
(27)同上注,第72页。
(28)靳宗立:《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变更之适用原则》,载台湾地区刑事法学会主编:《刑法总则修正重点之理论与实务》,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02页。
(29)[德]卡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25页。
(30)杨春洗、杨书文:《试论持有行为的性质及持有型犯罪构成的立法论意义——以持有假币罪为理论起点》,《人民检察》2001年第6期。
(31)刘艳红:《刑事立法技术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实践——兼论罪刑法定原则实施中的观念误差》,《法学》2003年第8期。
(32)参见[美]安·塞德曼、罗伯特·B·塞德曼:《法律秩序与社会改革》,时宜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33)哈特认为语言在其意思的边缘区域是不确定的,语言本身存在空缺结构的特征。对此可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及以下。
(34)Gadamer,Hans-Georg,Truth and Method,New York:Cross Roads Inc.,1984,p.231.
(35)[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
(36)韩忠谟:《法学绪论》,台湾地区韩忠谟教授法学基金会1994年印行,第83~89页。
(37)这一点很类似于后现代文学中“作者退场”的现象。而事实上客观解释论的基本哲学基础就是后现代哲学,而其法学基础则为自然法精神。
(38)黎宏:《日本近现代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借鉴意义》,《法学评论》2004年第5期。
(39)“司法犯罪化”之实质为刑法解释适用上的犯罪化,其本身与刑法解释尤其是刑法客观解释密不可分,甚至就是刑法客观解释之产物。如在1997年《刑法》制定之初,现实中尚未形成对电子邮件或QQ聊天信息的大规模侵犯,故当时侵犯通信自由罪也不会包括上述犯罪对象。但通过刑法对“通信”的客观解释,完全可以将对上述两种对象实施侵犯的行为“司法犯罪化”。但“司法犯罪化”作为和“立法犯罪化”相对应之命题,其具体意义和客观解释有所分野,而其范围也要大于“客观解释”,如对于超速驾驶行为及偷阅他人电子邮件行为,也可以借司法解释的手段实现“司法犯罪化”。本文特意将二者区分论述。
(40)张明楷:《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法学家》2008年第4期。
(41)林子仪:《〈资讯、电信与法律〉序》,载王郁琦:《资讯、电信与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2)同前注(40),张明楷文。
(43)立法为了保持稳定性和连贯性,其条文字面用语应相对稳定。但相对而言,立法相对于社会发展总会有一定的迟滞性。然而立法却应当保持这样的保守性,一方面立法需要时间对危害行为的犯罪化进行观察与评判;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司法犯罪化”作为“立法犯罪化”的探路石,验证对某类危害行为犯罪化的社会效果。
(44)《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45)“两高”尚未对《刑法修正案(七)》的罪名做出解释,“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之罪名是本文为了研究方便,而自行确定之罪名。
(46)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6页。
(47)吴大英、任允正:《比较立法学》,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
(48)1997年《刑法》中共有36处地方使用了“等”字,都应理解为列举未尽。对此可参见张庆旭:《刑法中“其他”及“等”略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2期。
(49)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06页。
(50)如游客问:“故宫怎样走?”回答是:“我是外地人。”尽管故宫位置的询问和外地人身份的表白似乎难以构成标准的对答模式,但在此具体语境中,游客不会误解回答者话语的真实意思,即“我不知道故宫的位置”。
(51)[日]碧海纯一:《新版法哲学概论》,信山社2000年全订第2版补正版,第123页。转引自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52)以《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行凶”而言,不少学者攻击其边界不清而违背明确性原则。但只要考察其所在条文中“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词语,就不应将所谓的“打耳光”、“揪耳朵”、“踢屁股”等轻微暴力行为涵盖在内,进而主张对此类行为实施特殊防卫权。
(53)张明楷:《正义、规范、事实》,载《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一卷):刑法解释问题》(200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54)《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78页。
(55)[法]F·P·G·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页。
(56)本文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其可以从相关刑事立法中得以佐证,如《刑法》第161条规定,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因此,刑法尽管包含着大量的日常用语,但不能完全依从日常用语的常用本意推敲其在立法中的应有真实含义。
(57)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志刚就提出,“人肉搜索”泄露公民姓名、家庭住址、个人电话等基本信息,是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建议在刑法中对“人肉搜索”行为予以规范。
标签:刑法论文; 法律论文; 隐私权论文; 人格权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刑事犯罪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