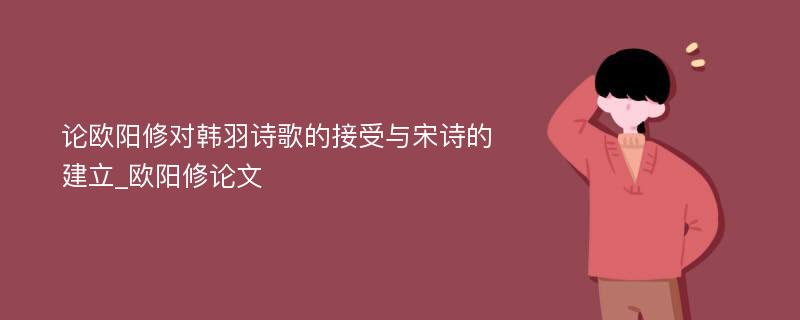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韩愈论文,欧阳修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先生论述中国古代的文化学术演进历程,以中唐为转关、赵宋一代为鼎盛,而韩愈、欧阳修则是中唐至北宋文化学术转型中承前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单就诗歌史而言,中唐至北宋一段亦为我国古典诗歌一大变局。在诗歌由唐转宋的过程中,韩愈、欧阳修仍旧是起到转捩作用的枢纽人物。韩愈堪称中唐诗歌开拓新变的杰出代表,而欧阳修则是宋诗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对于欧阳修诗歌,古今一致认为韩诗是其主要艺术渊源。本文拟从接受美学角度考察欧阳修对韩诗的接受历程,一方面,全面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通过欧阳修的尊韩、学韩,总结出欧诗从树立典范、师法典范到独创新意的诗学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以期明了欧阳修对“寂寥二百年”的韩诗有“发明之功”,并于此基础上进一步推究欧诗承韩对奠基有宋一代诗风所具有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
欧阳修在宋诗发展史上得风气之先,开一代新风,是宋诗中一大家。梁昆《宋诗派别论》曾标榜“古文诗体”[1](P39),认为其盛行于北宋仁宗天圣至神宗熙宁间约40余年,当时穆修、石延年、余靖、石介、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的诗歌皆以韩愈为宗,就中以欧阳修为领袖,号昌黎派。梁氏的昌黎派或古文诗体云云,其概念内涵并不十分明确,在文学史上恐不能成立。不过此论却也指出了韩诗与北宋诗歌、特别是欧诗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拿欧诗与韩诗比较而读,一温丽深稳,一雄健奇崛,表层风貌并不十分相类,甚至颇有差距;然而宋以来的诗论家皆以为欧阳修师法韩愈,并认为他在众多学韩之人中是升堂入室、出蓝胜蓝的。如:
王安石:“欧阳公自韩吏部以来未有也。辞如刘向,诗如韩愈而工妙过之。”[2](P166)
张戒:“欧阳公诗学退之。”[3](P452)
严羽:“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4](P26)
陈三立:“宋贤效韩,以欧阳永叔、王逢原为最善。”[5](P2)
钱锺书:“唐后首学昌黎诗,升堂窥奥者,乃欧阳永叔。”[6](P177)
考察欧阳修毕生的诗学道路,探究其诗歌创作,可知他对韩诗的标举、学习是贯穿终生的。他的师法研习不仅停留在对韩诗题材、词语的模拟和化用上,更表现在对韩诗深层特质的准确理解与把握中。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欧阳修尊韩、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
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记载了一则轶闻:
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言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昨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7](P140)
这里的“公取”、“窃取”提法很有意思,不妨把“公取”理解为对韩诗表面特征诸如题材、语词、句式、典故等的明显借鉴与模拟;而“窃取”则并非亦步亦趋式的仿效,而是在对韩诗内在特质的准确把握基础上,渗入自己的诗学思考,达到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更高艺术境地。
欧阳修现存诗800余首,如将其诗歌创作按阶段论述,似更能对他接受韩诗的历程作出较清晰的说明,而且还可从中窥见北宋中期诗歌的发展轨迹。试将欧阳修诗歌创作阶段粗略划分为三个时期:(1)自少年应举至贬官夷陵前,这是欧阳修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他苦心追摹、尝试“以文为诗”的“学韩”时期;(2)两次贬官外任时期(指被贬夷陵与滁州),这是他大力标举研习“以文为诗”、进入神形兼备的“似韩”时期;(3)从再次入朝直至去世。欧阳修“以文为诗”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是他建立平易疏畅诗风的“变韩”时期,晚年的欧阳修和韩愈一样,诗风也体现出某种回归传统的态势。应该指出,这种分期基本以欧阳修对韩诗的接受为着眼点,贯穿几个时期的中心线索是他对韩愈“以文为诗”的标举、研习与发展。
(一)学韩期
欧阳修自天圣元年(1023)17岁起三次应举,天圣八年(1030)得中进士第一,次年春赴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从此登上政坛与文坛。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是当时学风、文风发生微妙变化的转折时期。《欧阳文忠公文集》从天圣九年(1031)开始收诗,少作一概不录,可知他是“悔其少作”的。试看《居士外集》收录他未及第时及洛阳所作近体诗,风格气息甚有西昆意味。不过,当时他与同在洛阳为官的梅尧臣已不满于流行的风气而开始了新探索。宋初以来,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都曾作为一时诗坛典范而颇有影响。欧、梅等既要矫西昆之浮华,就必须选择其他的诗学范式,他们于天圣年间始为古文歌诗,而韩愈诗文就成为研习的主要范本。由此开始,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在北宋诗歌创作中得到接受与发展。
不同于当时另两个学韩小团体的粗豪狂放(注:欧阳修初登文坛的天圣、明道年间,诗坛主流自是西昆体的雕章丽语,但早于欧阳修,已有“山东”、“东京”两个文人群体开始了新探索,“山东”指石延年、石介、杜默等籍贯是山东的诗人,“东京”则指当时在东京的穆修、苏舜钦等人。总体而言,这两个文人群体学诗皆以韩愈为宗,除苏舜钦后来有较高成就外,很多人的诗狂怪奇涩、气势猛烈,并不能从根本上给宋诗带来新变化。),欧、梅的学韩表面平和沉稳而骨子里却给宋诗带来深刻变化。欧阳修学韩的主要倾向在于加强诗歌的记叙性与议论作用。陈延杰《宋诗之派别》认为:“欧阳修诗原出昌黎,痛绮靡之作,始矫昆体,以七格为主,故其诗敷腴,宋诗风气为之一变,最长七言古体,幽咽豪迈,不可一世。”[8]宋初三体:白体、西昆、晚唐皆喜作律诗,欧阳修则多作古体,这也是有深意的,符合其增强诗歌叙议作用的初衷。一般认为,欧阳修的古体比律诗成就要高。
在洛阳,欧阳修评价梅尧臣诗曰:“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书梅圣俞稿后》)这与他晚年《六一诗话》里推崇韩诗“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云云是一以贯之的,由此可见他非常重视诗歌的体物表现力。强调诗歌穷形尽相地叙写,就意味着对诗歌抒情传统的部分疏离,朱熹云:“杨大年诗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及至欧公,渐渐要说出来。”[9](P3334)杨亿与欧阳修诗风差异的深层信息是欧、梅的诗已与典型意义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统作品有所不同,“说出来”表明欧诗对记叙、议论的注重,这已逗露出几丝诗风转化的消息。
试看他的创作实践。欧阳修是由学习韩愈的儒学与古文进而及于师法韩诗的。洛阳诗作中,他有三首专写黄河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即《黄河八韵寄呈圣俞》、《巩县初见黄河》与《代书寄尹十一兄杨十六王三》。这些作品有意识地借鉴了韩诗的手法,可以看作欧阳修对“以文为诗”的初步尝试。以《巩县初见黄河》为例,这是他在目睹黄河的磅礴气势后一气写下的70单行。王士禛谓欧阳修“七言长句,高处直追昌黎”[10](P154),此诗之用赋法铺叙,注重气势,正体现了欧阳修心摹手追韩愈的雄劲笔力。作品先赋黄河汹涌澎湃、惊心动魄的雄奇景象,次叙历代治水及秦汉以来的严重水患,最后以颂扬当代治水作结,表达了讽谏朝廷为民造福的寓意。此诗500余字,仅引其中一段:
江海淮济洎汉沔,岂不浩渺汪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万古不敢肆凶厉。惟兹浊流不可律,历自秦汉尤为害。崩坚决壅势益横,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驱民就溺财随弊。盖闻河源出昆仑,其山上高大无际。自高泻下若激箭,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冲急乃迸溢,其势不得不然尔。前岁河怒惊滑民,浸漱洋洋淫不止。滑人奔走若锋骇,河伯视之以为戏。呀呀怒口缺若门,日啖薪石万万计。明堂天子圣且神,悼河不仁嗟日哨。河伯素顽不可令,至诚一感惶且畏。
全诗层次分明,多用散文句式,写黄河出以奇思妙想,发议论显得意气风发,可算欧诗发轫期对韩愈古诗章法笔力较成功的一首仿作。
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作《庭前两好树》,与韩诗《秋怀》第一首“窗前两好树”的起兴基本一样,而且走的都是六朝人的路数,融合陶、谢二家,以精语运淡思,寄兴悠远。从一开始,欧阳修就不专力于韩集里最有特色的奇崛雄健之作,却注意到了韩愈的平淡之作并刻意仿效,可见他后来的学而能化并非偶然。
这一时期,欧阳修已明确标举了学韩的大旗,欧诗重叙写,发议论,和梅尧臣初步开拓了宋诗以气格为主的新路。不过,此期他的接受韩愈基本还停留在浅表层面,多表现为对韩诗题材、章法、语词明显的模拟和直接的借用上。
(二)似韩期
景祐至庆历年间,欧阳修仕途坎坷。先是因声援范仲淹而贬官夷陵,几年宦海沉浮后,又因庆历新政的失败而被贬滁州。自贬官夷陵起,欧阳修诗歌最显著的变化是开始渗入理性思考,注重诗歌记叙议论作用的倾向更加明显。他在学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进行诗歌篇章结构的探索,借鉴散文作法而创出新意。
七古《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是此期学韩的具体而微之作。方东树评曰:“起段从源头说起,夹叙夹议,学韩而老,但少其兀傲。‘高台’二句逆入。‘同行’四句学韩之奇。此皆从《赤藤杖》来。”[11](P282)此评颇精到,试申述之。“从源头说起”,指起首历叙古瓦所出之地建成前的历史及铜雀台的始末。诗自“高台已倾渐平地,此瓦一坠埋蓬蒿”始叙古瓦,这是“逆入”。“舟行屡备水神夺,往往冥晦遭风涛,质顽物久有精怪,常恐变化成灵妖”四句“学韩之奇”。结尾“长歌送我怪且伟,欲报惭愧无琼瑶”,则是从韩愈《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妍词丽句不可继,见寄聊且慰分司”化出。可见欧之学韩已有相当深度。欧阳修作于庆历六年(1046)的《重读徂徕集》以浓烈的感情驾驭叙议,悲愤石介的被诬,颂扬其忠义刚直,诗从立意、章法到意境都有韩愈长篇五古的影子,也足以说明永叔精研韩诗,深有会心。
皇祐三年(1051)欧阳修作《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自诩为平生得意之作,《石林诗话》载欧阳修语:“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12](P424)欧阳修虽自负《庐山高》非太白不能为,但顾随先生《宋诗略说》认为“太白诗真不像欧”。[13](P211)这诗骨子里实是学韩愈的“以文为诗”,将散文的句法与气格意脉写进诗里,像“长江西来走其下,是为扬澜左里兮”、“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尝恶其学幻而言哤”、“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这样的句子很有韩诗的味道。散文化的写法使诗歌在叙事状物方面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庐山高》押险韵,一韵到底,又安排些奇字硬语,锵金铿石,因难见巧,追步韩愈。清人刘熙载亦持类似观点:“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为逼近耳。”[14](P66)作为开启有宋一代新诗风的欧阳修,当然会博采前代众家诗人之长,但韩诗无疑是他众多艺术渊源中的最重要一维。
此期欧阳修的学韩已臻形神兼备的境界,作于庆历五年(1045)的《读蟠桃诗寄子美》表露出他对韩孟诗风的倾心:“韩孟于文词,两雄力难挡。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众鸟谁敢和,鸣凤呼其皇。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继而他以梅尧臣比孟郊,暗含自比韩愈的意思。就欧阳修此期诗作来看,他学韩已超越了亦步亦趋的浅表层次,而能于模仿中别创生新,并开始有意回避韩诗的奇险硬涩。他最倾心的是韩愈之“浩穰穰”(即无施不可的雄健笔力),可谓学到了韩诗的精萃所在。
(三)变韩期
至和元年(1055),欧阳修服母丧期满入朝,为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随着名益高、位益崇,他的文坛活动取得了重大实绩。除古文运动获得突破性进展外,其诗歌创作沿着已开拓的道路顺利发展,欧阳修在当时文章道德为一世宗师,他的推崇韩愈有登高一呼而众山响应的深刻影响力。
此期,欧阳修的诗歌创作达到成熟阶段,借鉴前人而不事蹈袭,学韩并最终超越了韩诗,是思虑深沉的理性精神促成了其平易疏畅诗风的最终确立。吴之振等《宋诗钞》谓欧诗:“其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昌黎时出排奡之句,文忠一归之于敷愉,略与其文相似也。”[15](P315)“以气格为主”的评价很精辟,指出欧诗学韩并非句摹字袭,而是具有拓旧创新的通变之功。又,明人王鏊云:“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韩师孟,今读韩文,不见其为孟也;欧学韩,不觉其为韩也。”[16]“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评语道出了欧阳修成功接受韩诗的真精神。
韩诗之奇崛险怪与欧诗之晓畅明达自是各具面目,但不同表象之间却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关捩点在于“以文为诗”的构思方法和专主气格的诗学意念。一言以蔽之,韩以奇崛见气格,而欧则以疏畅见气格。欧阳修对韩愈的变化超越,不在奇崛险怪之风貌,而在气格恢振之神气;不在造语用字的刻意生新,而在章法笔力的纡徐委曲。诸如《和王介甫明妃曲》、《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等作品,以文为诗,铺张敷衍,更觉纯熟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用一种晓畅明达的散文化语言抒情状物叙事,熨贴条达,细密清峻,韵散同体,诗文合一,颇得韩诗“以文为诗”之神髓。试看《赠李士宁》:
蜀狂士宁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疑,诡谲非一行。平生不把笔,对酒时高咏,初如不着意,语出多奇劲。倾财解人难,去不道名姓。金钱买酒醉高楼,明月空床眠不醒。一身四海即为家,独行万里聊乘兴。既不采药卖都市,又不点石化黄金。进不干公卿,退不隐山林。与之游者,但爱其人,而莫见其术,安知其心?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
作品“以文为诗”的特色尤为显著,已完全突破常规,还带有韩诗特有的诙诡,类似韩诗的《嗟哉董生行》、《寄卢仝》等,散文化意脉、句法、虚词等艺术手法信手拈来,淋漓尽致,即使与韩诗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鬼车》则是仿效韩愈的《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铺陈敷衍而能另辟一奇。
就欧诗学韩而言,注重的是以散语铺排意脉,风格虽转归平易仍然不乏“气格”。李详《韩诗萃精序》云:“宋欧阳永叔稍学公诗而微嫌冗长,无遒丽奇警之语。”(注:转引自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之附录,1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李详是以欧诗学韩学得像不像着眼评价的,而欧阳修的目的不是做韩诗的忠实传人,而是借韩愈的“以文为诗”为宋诗开创新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修学韩并最终超越了韩诗,说“超越”并非指欧诗的艺术成就盖过韩诗,而是指欧诗在韩诗基础上的创新发明完全成为自我个性风格的写照,是“这一个”,而非韩诗的翻版。(注:限于文章的篇幅与结构安排,关于欧阳修诗“变韩”的更多论述放在第二部分,结合宋诗奠基来谈,此处就不展开论列了。)
二
自宋初柳开、穆修始,韩愈就在道统与文统两个方面受到高度赞誉。但彼时宋人看中的只是韩文,对于韩愈“诗格之变”的意义还鲜有明确体认。梅尧臣说韩诗“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可知韩诗自晚唐以来曲高和寡。宋代对韩诗创作在诗歌史上的意义首先进行标举的是欧阳修,其《六一诗话》有一大段阐释论析韩诗的文字,迻录如下: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故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惬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这段话之所以被研究者频频引用,就在于它精辟地揭示出韩诗艺术的深层特质,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是欧阳修阐扬了韩诗“无施不可”的雄健笔力。“无施不可”即任什么内容都能表达得好,指表现力、感染力之强。“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云云,都是推崇韩诗长于记叙、精于说理的特色。韩愈“无施不可”的笔力之所以值得标举,是因为它能“曲尽其妙”,写出穷本探妙的道理。欧阳修《紫石屏歌》自述:“大哉天地间,万怪难悉谈。嗟予不自量,每事思穷探。欲将两耳目所及,而与造化争毫纤”,其《圣俞会钦》又称赞梅尧臣“诗工镵刻露天骨”,可知欧、梅二人都在创作中不遗余力地追摹韩诗的雄健笔力。欧阳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以文为诗”,但他的诗论已接触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欧阳修对韩诗的新解读是韩诗深层特质被发现的标志,也是独具特色的宋调得以形成的认识基点。
欧阳修的最重要盟友梅尧臣亦极其推崇韩愈,他认为“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健笔走霹雳,龙蛇奋潜蟠。飏风何端倪,鼓荡钜浸谰。明珠及百怪,容畜知旷广。其后渐衰微,余袭犹未弹。我朝三四公,合力兴愤叹。幸时构明堂,愿为栌与栾”。(《依韵和王平甫见寄》)。宋初的白体、晚唐体气格不振,稍后的昆体诸家又华靡不实,欧阳修、梅尧臣等之所以推崇韩愈,正是欲借他这支“走霹雳的健笔”来革宋初浮浇的诗风。欧、梅等不仅看重韩诗“革浮浇”的精神,更学习他“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铺叙妥帖而排奡,议论劲健而沉稳,真正开创了有宋一代的新诗风。钱锺书《宋诗选注》云:“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17](P27)就欧阳修接受并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而言,实为王安石、苏轼等人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因此在韩诗接受史上尤具开创意义。
宏观地论诗史演进,中唐至北宋的诗歌历程是一段疏离传统、寻求新路径的艺术创新之路。韩诗对宋诗有筚路蓝缕的作用。韩诗的戛戛独造根源于艺术上的创辟,而“以文为诗”(注:“以文为诗”可以有多种层面的解释,如只从字面意义考察,就是“诗句似作文样做”(吴垧《五总志》引陈师道语,这是关于“以文为诗”的最早解说),现代学者往往概括为“以古文(散文)章法、句法入诗”,但是这一解说仅局限于艺术手法,似嫌狭义直观,不利于深刻理解它含义上的包容性、不确定性,亦不能充分揭示其在诗歌由唐转宋中所起的新变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将其理解为一个血肉丰满“立体”概念,韩愈与北宋诸人的“以文为诗”体现的是一种诗歌与散文的自觉整合关系,可用以概括韩诗与北宋某些诗人创作方法、语言特色和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就是韩愈变革诗歌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的提法,概括出韩诗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语言形式的主要特征。“以文为诗”的实质是一种“破体”,亦可称“出位之思”,它是诗歌借鉴散文的思维、手法,通过文体间的碰撞交融以推进自身发展的新鲜动力,其意义在于突破诗的旧界限,开创诗的新天地。中唐至北宋注重理性思辨的时代精神渐趋发展,并深刻濡染于文学创作,逐步引起了诗歌题材、语言、艺术表现及风格上的一系列新变。这种变革适应了唐宋之际诗歌发展的历史趋势。诗格之变始于杜甫、韩愈,至宋代欧阳修、王安石再到苏轼、黄庭坚,宋诗诸大家以自身为主体,在传承“以文为诗”中加以创变,而宋诗的基本面貌特质亦在此过程中凸显确立。欧阳修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既已明了欧诗学韩主要在于承袭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下文拟以“以文为诗”为关捩点,再就韩诗与欧诗的题材、以议论入诗、散文化章法等有关宋诗根本特质的重要问题,略述韩愈、欧阳修二家诗的承传嬗变及其与宋诗奠基之间的艺术关系。
从题材内容来看,“以文为诗”扩大了韩诗、欧诗的表现范围,拓展了诗歌的记叙功能,无意不可入诗,无事不可入诗,使诗歌真正变成贴近生活、触手生春的抒情工具。韩愈、欧阳修对诗世界的开拓主要表现在诗的日常生活化和以不经见之新奇题材入诗。韩、欧不但擅长用诗来议论时政、社会问题,表现重大题材;同时也喜欢写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或奇异事物,而且他们长于将士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件描述得富于情韵,充满诗意。韩愈写过南方风土的荒蛮凶险、月蚀、斗鸡、叉鱼、落齿等题材古怪的诗,欧阳修受其影响,也写过《憎蚊》、《和圣俞聚蚊》、《鬼车》、《汝瘿答仲仪》等奇异丑怪题材的诗。欧阳修还有意识地多方扩展诗的记叙范围,他的咏物诗所咏对象有些属于新奇而琐细的物品,如《初食鸡头有感》、《双井茶》、《梅圣俞寄银杏》、《日本刀》等。欧阳修对宋诗题材的更大贡献体现在他那些观画、听乐、读书等含蕴文化精神的诗作里,这些都浸染出作为学者的欧阳修的文人雅致。士人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诗意都被发掘出来,宋代士人的雅量高致、艺术旨趣在其作品里有充分展现,这对后来的苏轼有相当影响。韩诗记叙范围已相当广泛,在一般唐人之上;欧阳修只不过是顺着韩愈“以才学为诗”的道路向前继续演进,而这,后来也成了宋诗的一大特色。
韩愈是继杜甫之后第一个以大量议论入诗的,《荐士》历论诗歌之发展,旁及孟郊之才及其不遇;《调张籍》充分肯定和评价了李杜在唐诗中的杰出地位,这些在诗中发议论的成功例子体现出韩诗特有的雄肆和锋芒。欧阳修诗多发议论,亦得力于韩诗不少。韩、欧皆长于以议论入诗,两相对照,则欧诗议论又自具面目,不似韩愈的峭刻直露、滔滔汩汩,欧阳修所发乃理性思考后富含凝敛感情之议论。欧诗七古《菱溪大石》学自韩愈《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作品先以神思妙想推溯大石经历,平叙之笔时夹奇诡,“皆云”以下十四句又以议论代替叙写,运笔如风而自然流畅;不似韩诗的一味怪诞天纵、缒幽凿险,欧诗体现出一种长于理性思考的特点。欧阳修诗之议论往往把抒情与说理、写景与议论结合起来,以形象化语言置于诗之转关处,立一篇之警策。朱熹云:“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尝有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好议论。”[9](P3308)朱熹推许的议论名句出自《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诗表面歌咏崇徽公主远嫁回纥所留之手痕碑,实则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意在抨击时政,故得朱熹激赏。擅发议论而思虑深沉是宋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欧阳修等在诗歌由唐代的长于丰神情韵、兴象玲珑转为宋代的重兴寄、重思理筋骨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欧阳修师韩“以文为诗”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谋篇布局的法度精微。韩、欧都有很多整体风貌散文化的篇章,诗歌而有散文化的效果主要是借鉴散文章法结构、叙述方式写作的结果。关于韩诗章法布局的精妙,清人方东树作过不少切中肯綮的分析(注:方氏系桐城派姚鼐弟子,主张以“古文文法”通于诗,故其《昭昧詹言》多“以文为诗”技法的分析。),其《昭昧詹言》卷十二云:“至于章法之妙,非太史公与退之不能知之,故知不解古文,诗亦不妙。”[11](P296)方氏又云:“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章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11](P238)、“学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11](P275)、“欧公之妙,全在逆转顺布”[11](P276),可见欧阳修也是精于章法的斫轮老手。比如欧诗《寄圣俞》,方氏认为“真似退之”[11](P278),然则何处似韩诗?恐怕即在于诗之章法结构,作品前叙梅尧臣人才难得,次愧言己不能提携之,最后叹惜其遭遇而深有感触,抵得上一篇情意真切的书信。余如《归雁亭》、《紫石屏歌》的章法从韩《李花赠张十一署》、《赤藤杖歌》来,《赠沈博士歌》学韩《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铺叙安排,不一而足。总体而言,欧诗谋篇布局的章法化韩诗之笔势腾掷、浑噩急厉而为疏荡平易、自然精悍,较韩诗细密平和,这也算欧阳修由模仿韩诗到自创新意的一个发展。
韩愈确是开启宋诗风气的关键人物。因为韩诗与唐宋之际文学转型的时代精神暗合,在宋诗里,他不知不觉犹如被用于临池的字帖,宋诗诸大家在学习临摹基础上更施以笔墨之功,创出更为新鲜凝练的字体。对于韩诗的艺术独创性,一班谋图新变的宋诗大家很是赞赏,欧阳修尤其心仪韩愈变革诗格的雄健笔力;然而,他对韩诗过分狠重奇险的缺失亦有清醒认识,其《菱溪大石》有云:“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争奇斗异各取胜,遂至荒诞无根源。”欧阳修虽然力学韩诗,但观其“荒诞无根源”的评说即知他对韩诗之奇险直露一面始终抱有戒心。欧阳修又言:“诗人之意,言之愈切,则其言愈缓。”(《论尹师鲁墓志铭》)韩诗境界毕竟距宋人向往追求的清老平淡诗境相去有间,故而欧阳修之学韩是“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注:语出吴之振《宋诗钞》序:“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式的艺术交流,表现为一种学而能化、反思修补的思辨色彩,他继承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一方面使宋诗趋向散文化、议论化,技艺法度愈加精微,另一面,他斟酌了学韩的利弊得失,以平易疏荡扬弃了韩诗过分拗峭奇险的弊病。追求雄豪健拔而归于平淡隽永的诗学道路正是宋诗独特面目与风格得以形成的第一阶段。方东树评欧阳修七古云:“欧公情韵幽折,往反咏唱,令人低回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余味,但才力稍弱耳。”[11](P276)这话虽是专论七古,但用作总体评价欧阳修的“以文为诗”亦称惬心贵当。伴随着欧阳修领导诗坛和后来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推波助澜,“以文为诗”终于从宋初的不绝如缕发展到蔚为大观,成为北宋诗坛普遍的创作倾向。
欧阳修接受韩愈的时代背景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古思潮的勃兴与道统观念的渐趋强化,在此种大环境中,北宋诗文革新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以欧阳修为核心的众多文人的尊韩、学韩,宋代文、诗等文体开始缓缓起变化,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欧阳修接受韩诗的诗学意义可总结为韩愈诗学典范地位的确立与具有独特岁貌的“宋调”的开启。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欧阳修借鉴韩诗,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而这其中,韩愈起到了诗学典范的重要作用。欧、梅等对韩愈“以文为诗”的继承与发展,为宋诗创辟一代之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从而奠定了他们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论欧阳修对宋诗的开拓之功曰:“由修而拗怒,则为黄庭坚,为陈师道;由修而舒坦,则为苏轼,为陆游。诗之由唐而宋,惟修管其枢也。”[18](P520)这个评说是客观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