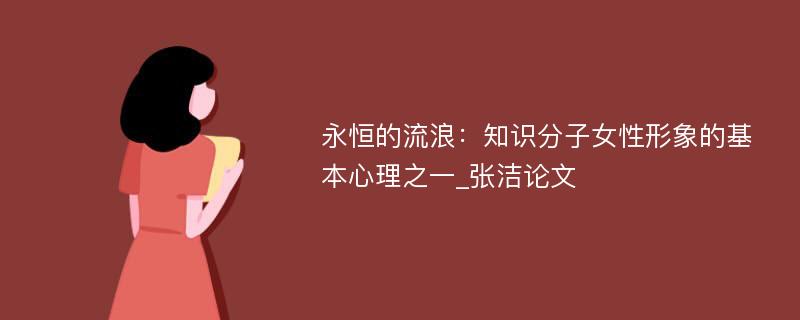
永远的流浪——知识女性形象的基本心态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形象论文,女性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流浪:一种古老而又现实的心态体验
新时期一位女性主义诗人伊蕾在她的诗歌《流浪的恒星》里面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诗:“我在被囚中到处流浪/我在流浪中到处被囚。”这几乎成为知识女性所固有的生存处境和基本心态的典型概括。所以,当张辛欣在京杭大运河的北端骑一辆赛车起步之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她的身体“在路上”的同时她的心灵已经经历过并又重新开始了“在路上”的流浪体验(《在路上》①);张曼菱在极其理性地为自己的主人公们选择着生活方式的同时仍有“为什么流浪”的困惑与自问(《为什么流浪》②);赵玫本文中所充盈的苦闷与焦虑情绪归根结底是来自那种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感。
流浪心态对于知识女性而言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之后,那种蒙昧混沌但安宁和谐的伊甸乐园生活便结束了,迎接她的是颠沛与流浪。智慧之果使夏娃心明眼亮,懂得了善恶与羞耻,同时也注定了她面对宠大而芜杂的世界时那波荡不平的心灵世界。幽默的马克·吐温在他的晚年作品《亚当夏娃日记》中借夏娃之口对那个古老的神话作了不无反讽的改写,夏娃说“开始我想不出我被创造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但现在我认为,我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探索这个世界的各种秘密……”③这与耶和华创造夏娃作伴侣以免去亚当孤独的初衷无疑相去甚远,但却明白道出了拥有知识的“夏娃”们必然的生命选择。
所以,当“五四”那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意味着既往历史的一次颠覆的伟大变革开始之后,在文学界,在高声呐喊着的男性声音中竟开始出现了女声,这声音由小到大,由寡到众,由脆弱变刚强,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女性文学团体。
无疑,这率先打破沉默的是一批知识女性,也只能是知识女性。知识有如智慧之树的果子,拨开了她们心灵上厚厚的蒙昧尘埃,使她他看到了这个社会以及自身的处境,“探求这个奇妙世界”并力图改变这世界的主体意识复苏了,“夏娃”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伊甸园。不满于现实继而不安于现实便是女性们主体意识觉醒后的最初心态——这是“流浪”的开始,也是被动而沉寂的女性生态的结束;探索与寻求一种合适而合理的生命方式是“流浪”的第一程,于是,在“五四”时期,在“女人无史”之后的“有史”的开端,知识女性结束了“被注释”、“被命名”的悲哀历史,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有了形形色色的理想抉择与追求的方式,出现了沅君式的、庐隐式的、丁玲式的“话语”。作家们借各自笔下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女性形象宣示着自己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思索,又在不得结果的苦闷中彷徨、叹息,同时否定着旧有的生活模式设计,去尝试更新的。这种在困惑中追求,在追求中迷失,再从迷失中力求奋起的心灵过程中,不知所向,无所依附的“流浪”感一直附着在女性们的情绪体验之中。
沅君式的知识女性们似乎不存在“价值追问”、“理想选择”、“意义寻找”上的彷徨流浪心态,她们拥有一个极明确、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要完成“爱的使命”,“爱情”成为这些知识女性们自身生命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殉爱的使命”在她们看来是“天下最光荣的事”。因此,她们的流浪心态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与确定上,而是发生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然产生的矛盾冲突中——母爱与情爱的冲突,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性爱行为的冲突。她们明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却又摆脱不了母爱与旧的道德观所带来的负疚感。所以,浑身洋溢着叛逆精神的“我”固然有勇气与自己的爱人一起出去旅行,却又不住地自责自己的行为给母亲、给旧家庭中的情人的妻子所带来的痛苦。她们的态度是决绝的,但她们的灵魂却在两个声音之间永远地徘徊,一个声音要求着“解除旧礼教旧习惯造成的关系”,另一个声音却谴责着“男子们为同别一个女子发生恋爱,就把他的妻子弃之如遗”的不仁行为(《旅行》)。精神的悖廖使她们在极度的痛苦中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牺牲生命来殉爱”:母亲的爱,情人的爱。
沅君为她的知识女性们安排了一条近乎悲壮的道路,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实质却是一种逃避——逃避现世,逃避压力,逃避来自于心灵的苦苦挣扎的痛苦。她们最终一无所获,既没有成为实现了爱情的幸福伴侣,又没有成为传统道德观念下的贤淑女子,沅君式的女性在结束生命的同时也结束了精神的继续探索和流浪。
庐隐式的知识女性较之沅君笔下的知识女性又前进了一步,她们已经从“爱情至上”的虚幻王国里走出来,认识到“爱情也是靠不住的”,这虽然不免带有爱情失望之后的极端情绪色彩,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促使她们从唯爱的狭窄情感世界中抬起头来,看看这个广的世界,思索一些爱情之外的个人价值。但思想的局限仍然使她们不知所向。如果说沅君式的女性在奔向目标的过程中终于淹没于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中的话,那么庐隐式的女性们则在新的目标确定上感到无可医治困惑,于是只有“一味放荡着,——好像没有目的地的船,在海洋中飘泊……”(《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们曾经试图走出“或人的悲诮2”,结束灵魂的飘泊状态,这种努力在1931年的《何处是归程》中仍隐约可见。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归宿”在庐隐的心中仍然是一片茫然。为人妻为人母的沙侣的选择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她抛弃了“理想的花园”重新堕入传统的家庭模式之中,“事业与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抱独身主义的妹妹在闻了同样独身主义的姑姑的艰难(生活上与事业上的)之后也开始动摇;国外归来的玲素权衡两者的苦闷之后同样不知所措,发出“何处是归程”的惆怅。庐隐一直试图为她笔下的知识女性们确定一个“归宿”,却一直没能如愿。这些人生路上“不知归程的旅行者”终于被无所依附的漂泊感磨蚀掉了所有的锐气,在灵魂的极度疲惫状态中消声匿迹了。
在历史的舞台上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的是丁玲式的女性们。她们的精神追求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轨迹:即不断地否定“旧我”,重塑“新我”,且这些重塑中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梦珂在宣布“无拘无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需要的生命”之后不久便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迎合那“有拘有束”的生活,但丁玲式的女性没有堕入虚无——一直自问“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的莎菲出现了。莎菲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需要什么,苇弟的懦弱是她不要的,凌吉士的卑陋灵魂是她不要的,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使她拒绝了两种爱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自我”。莎菲可以理智地处理自己的感情却又不知在爱情之外生命的出路何在,所以她的精神流浪以到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消耗生命而告终。告别“莎菲”之后,丁玲的寻找仍在继续。当“言说娜拉”已经成为一个陈旧的话题之时,美琳却做了丁玲笔下的又一位具有时代个性的“娜拉”(《一九三六年春上海(一)》),且是一位成功的出走的娜拉。“革命+恋爱”的模式化痕迹多少影响了这一形象的真实性,但丁玲为知识女性寻求出路的努力是可贵的,何况她在“革命的女性”身上的确寄寓了一种非常真诚的希望,丁玲总是有一种热情,一种“参与”的热情,不知疲倦地探索的热情,正因为此,陆萍(《在医院中》)才能在失望之中重新燃起希望。在挫折之中唤起对未来的信心。于知识女性的丁玲亦成丁玲式的知识女性而言,“寻找”的过程与其说是苦闷加困惑的悲壮过程,还不如说是一段乐观向上的历程,她似乎很有把握地料想到在精神的流浪之后必有一个理想的归宿在前面,尽管她还不清楚这“归宿”是什么,尽管这“归宿”的获得需要付出艰辛与代价。
沅君式的女性也好,庐隐式的、丁玲式的女性也好,她们既然做了“铁屋子”里面率先觉醒的女性,就必然地去寻求冲出这压抑环境的办法。但是怎样“打破铁屋子”以及冲出这“铁屋”之后又该怎么办,一直是她们心中纠缠不清的问题。探索是不可避免的,但探索过程中的困惑、迷茫和无所依附感也是不可避免的。
“五四”已经成为历史——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五四”时期的知识女性也作为这巨册史书中辉煌的一页被时间之手轻轻翻过,但知识女性的流浪心态却仍在继续,因为只要存在“肉体的囚禁”(伊蕾诗)、心灵的困顿,存在对自由的追寻,这种流浪感就不会终止。
寻找归宿与拒绝归宿:“流浪”的必然性
毕竟换了时代。尽管在80年代到来之前这个古老的国度曾一度迷失,但她终于拨开了重重雾障。知识女性的探索也在迷失与一段的停滞之后重新开始。
“五四”知识女性的身后是一段沉重的历史,一个漆黑的梦魇。她们从不回头也许是不敢回头,或者是只顾呐喊前行而无暇回头,她们的探索热情大于反省热情。新时期的知识女性则多了些冷静与审慎。历史教会她们思索也迫使她们去更深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她们仍然努力去追寻历史剥夺的本应属于她们的一切,尽管这追寻中仍有迷茫困惑,却多了些义无反顾的、决绝的精神。如果说五四知识女性一直在为流浪的灵魂寻找一个归宿又因不得归宿而到处漂泊的话,那么新时期的知识女性则从拒绝归宿(与理想相悖的归宿)开始,别无选择地踏上流浪的跨途,“对目的地不存希望,只要一个人,哪怕象瞎子一样摸索着,只管在黑暗中不慌不忙地骑,骑,不管前边有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有。”④
她们的出发点,也是第一个不愿停留的“归宿”即传统而又传统的“家”。“家”应该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意象,它给人安宁,给人慰藉,是流浪者终生向往不已的温暖乐园,正所谓“归心似箭”,人们不惜代价,不远万里,匆匆跋涉而回的,无非是一个“家”。但新时期知识女性的目光却落到了更远处,于她们而言,“家”实质是一条温柔的绳索,它在给你安宁的同时也囚禁了你的灵魂,阻止你继续前行的脚步。但要走出这“温柔之乡”又绝非易事。需要战胜的东西很多,你拒绝这归宿就意味着要同环境、同公共舆论甚至同自身的惰性进行一场搏斗,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女性战争。尽管如此,新时期的女性们仍然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孤注一掷,我对自己说/家是出发的地方”⑤,她们在这一归宿已经得到或唾手可得的时候拒绝了它。
于是芩芩极其理智地收回了迈向那安乐之所的双脚(《北极光》)。她清楚地知道未婚夫傅云祥可以提供给她全套的家具,时髦的服装,温柔的体贴与抚慰,但有却永远不可能理解她终生向往的美丽无比的“北极光”,那是她的希望,她的精神寄托,是积极向善的美好人生。傅云祥不仅不能理解这些,还会以他的硕大身躯永远地遮挡住芩芩心中的“北极光”。所以,尽管芩芩还没有找到生活的答案,“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但她宁愿放弃这一归宿,面对未婚夫的责骂、父母的痛斥,重新踏不漫漫征途。
如果说芩芩拒绝“归宿”所要抵挡的还只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的话,那么张辛欣笔下的“女导演”走出家门时所需要克服的就不仅仅是外部的压力,还有来自内心深处的依附意识(《在同一地平线上》)。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使得两性关系的固定模式(女性依附男性)已经成为一种深层的心理积淀,对这一模式的反叛无疑意味着心灵深处的一次巨大变革。走出家庭的“女导演”们固然成为“自我”的主宰,但传统依附意识却往往使她们在生存地艰难之中重新向往与迷恋那种古老的被动然而轻松的生活状态。所以张辛欣早期小说中的知识女性们常常在返归家庭与走出家庭的临界点上久久地徘徊。
但“走还是要走的!”虽然“不知此去前面有什么”,虽然“不知道怎么停下来”⑥。张辛欣的韵味就在于她常常把写实与情绪传达联合起来,让人在了解故事进程的同时又被某种情绪所感染。这篇既可以说是纪实散文又可以说是小说的文章(《在路上》)从题目到内容都是一语双关的有关知识女性的“流浪之路”——“旷野中,唯一的路”。
“有家不回”注定了流浪的必然,“无家可归”面对的同样是必然的流浪。如果说前一个“家”的“所指”对于知识女性来说倾向于传统意义上的束缚与囚禁的话,那么后一个“家”则代表了她们所向往的两性和谐组建——互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相促进、互相发展、没有矛盾的家庭。但是只要存在两性世界的隔阂与对立,只要人(男人和女人)仍然没有实现彻底的解放,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马克思语),两性的完美合作便不可能实现。张洁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的早期作品中有很多“无家可归”的知识女性,钟雨如是,荆华、柳泉、梁倩如是,曾令儿也如是。她们或是不能与所爱的人共建家庭(钟雨、曾令儿),或是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共建家庭的爱人(荆华、柳泉、梁倩),只有孤独一生,漂泊一生。但张洁似乎不甘心(或许是不忍心)让她的知识女性们在灵魂的孤独无依中流浪终生而一无所获,所以她总是无法自制地为她们(其实也是为自己)安排一个精神的归宿,这归宿就是女性自身的完善人格。《方舟》中张洁曾强调女性的解放不仅仅要靠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解决,更重要的是要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信和实现”。这一观念无疑具相当程度的真理性,但当她把女性自身的“自信”与“自尊”强调到近乎偏激的程度时,她所提供的“解放”途径便稍稍偏正轨。张洁对女性人格的韧性与完美表现出特殊的青睐。《谁生活得更美好》中的女售票员正是靠一种宁静而大度的个性无声地征服了那些青年,钟雨和曾令儿也以无法想象的博大胸怀接纳了来自爱、来自生存的种种艰难。张洁企图靠一种“无穷思爱”的人格力量去消解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去抚慰那些“无家可归”的知识女性的灵魂,同时也为自己对于女性前途的焦虑情绪寻找一点安慰。但她仍然无法心安理得,因为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完美的人格的虚幻性,于是在后来的张洁的笔下,你很难再看到任何有关人格的赞美色彩——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失望的张洁已经懒于去为女性们寻求灵魂的安歇处,她在“博大”之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尖刻,对于两性精神深处的“劣根性”,她剩下的只有嘲讽,嘲讽,无情的嘲讽。
知识女性将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一次果决的自我放逐,在“家”与“流浪”之间她们选择了后者,但“流浪”终究不是她们的最终目的,她们所希望拥有的,仍然是一个“归宿”,一个“避风港”,但这“归宿”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她们不得而知。于是“我到底要什么”的疑问在知识女性那痛苦、迷茫的灵魂深处纠缠不休。
就像陆星儿一直试图为女性们寻找一个最佳的生活方式以解决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冲突一样,嵇伟一直想为知识女性们孤独迷惘的精神寻找一个理想的休憩点。她的知识女性形象比之张洁与张辛欣的知识女性少了许多传统的负累。她们洒脱,自由,可以率性而行,有充分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但这种优游的生存状态却仍然无法使她们的灵魂停止流浪,获得永远的安歇。她们选择了一个又一个的归宿。同时又不断地拒绝着这些归宿,让灵魂继续那种寻找的流浪,《永远的女人》是典型例证。嵇伟不无沉重不无叹息地写下这一题目之后便开始与她笔下的知识女性“我”一起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生命的选择与淘汰。
应该说“我”与老孟的结合是一次理想的结合,这是在开放而现代的思想基础上追求与建立而成的家庭,两厢情愿,丈夫如父如兄,这无疑正是张洁的知识女性们苦苦寻觅而未得的理想家庭模式。“我”甚至曾经一度拥有一个孩子,完全沉浸于为人妻为人母的传统人伦关系之中去,但老孟以事业为借口拒绝了这一要求。也许正是这一拒绝使本来不安于现状的“我”发现了这场婚姻与自己精神的悖谬之处,从而在即将陷入传统的囚所的边缘及时地收住了脚步。与老孟的离异与其说是来自于老孟对爱情的玷污,不如说是蓦然惊醒的“我”对旧有的生命方式的一次积极的淘汰。
在老孟之后出现的男性是诗人林中华。“我”与林中华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互相需要的纯粹的肉体关系。林中华的虚伪、自私和放荡是“我”所鄙弃的人格,但“我”又总是在精神的极度疲惫与心灵的孤苦无援和茫然中接受林中华温柔的抚慰,让灵魂在暂时的欲望之欢中得到片刻的休憩。一个使嵇伟也使她笔下的知识女性们苦苦思索的命题便是特质与精神(亦或说是灵与肉)在无法和谐的情况下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物质(肉)的享乐吗?——但在享乐之后充斥那些知识女性们的心头的分明是无可医治的空与失落感。精神(灵)的殉道吗?——但只要是人,生活在尘世的人,欲望的宣泄与满足总是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性,更何况是被文明教化又反叛文明且心灵正处于疲惫与迷茫中的女人。
嵇伟笔下的知识女性们拥有一颗躁动的心,她们渴望理清自己的思绪,读懂自己的灵魂再去进行永无止境的追求。正如小说中的林中华所评价的,她们“有流浪者的血统”。“我”就是属于那“习惯于流浪”的一类人,在“他们的心的深处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所以他们老是想走,想寻找,想逃避。”⑦但就是这样一个艰难却决绝的“寻找”的女人面对自己近乎宗教般的爱情却无能为力。那个从法卡山上下来的“他”占据并将永远拥有“我”最圣洁、最炽烈的爱情。“我”和“他”的爱情是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在完全属于他们两人的一个夜晚,彼此克服了欲望的冲动,然后在凌晨永别。很难对“我”与“他”的行为做出道德的抑或人性的评价,就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样做究竟有何价值,有何意义。但“我”崇敬每一种宗教,“无论它是多么愚昧,它都是崇高的,诱人的。”其实此时嵇伟已经做出了她的价值判断:老孟的宽厚纵然可以给“我”安宁,林中华的抚慰纵然可以使“我”愉悦,但那使“我”的心灵疼痛不已并最终无法放弃的仍然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走”了将近十年的知识女性们可以走出家庭,走出环境压力,走出世人的冷嘲热讽,走出性爱的道德束缚,却终于没能走出张洁笔下的那份宗教情感。嵇伟的女性们不再前行——不是因为找到了归宿,而是因为无法摆脱情感的困境。
“新写实”:流浪的疲惫感
任何一个被文明教化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许多观念的束缚:历史的,道德的,传统的,女性承受的似乎更多一些。伊蕾说:“我落地生根,即被八方围困”⑧,这无疑是知识女性们真实而又深刻的生命体验的概括。因此,打破那“没有栅栏的囚所”,获得属于人的那份自由,是女性们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她们渴望甩掉肩上的传统的负累,从历史的“旧我”中脱胎换骨,重建一个“新我”,于是一场为追寻灵魂的自由而进行的跋涉开始了。迷惘过,孤独过,痛苦过,寻找并拥有过归宿,但又拒绝了那归宿,继续流浪,在流浪中探索。
不可避免是流浪的疲惫感。新写实小说不是阻止亦不是嘲讽知识女性的这种执着的“流浪”心态,他们只是极其冷静(冷静到了不无悲哀),他们清楚地看到这过程的漫长和那个理想境界的渺茫,于是无望的疲劳感不可抑制地伴随着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女性们。
在新写实小说家的笔下,过去已经不可更改,而将来又是遥远的、迷茫的将来,所以重要的是低头下视现实。无论你有多么远大的前程、高贵的理想,也无论你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历史亦或多么卑琐的过去,你仍然要为现实的你的眼前的职称问题,房子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为蔬菜的价格,为工资的高低而头痛不已。知识女性可以清高,可以执着于自己精神的追求,但这些琐碎而现实的生存问题所带来的疲惫感并不亚于灵魂找不到归宿的疲惫感。
而且,即使早撇开这些“形下”意义上的羁绊不谈,那些精神上的困扰仍然使你很难一如既往地前行。你想摆脱历史的阴影和负累吗?但历史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与你共生共息,无可摆脱;你要重构未来吗?但过去已经或正在宿命般地影响着你的未来,全新的“重建”是不可能的。冬儿(池莉《你是一条河》)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便决定从此永远不回头,她对整个家庭——在阴暗与污浊中只知道本能地求生存的家庭以及整个沔水镇都有一种近乎绝望的鄙弃心理,她更改姓名,隐埋历史又考入大学无非为了摆脱自己沉重而灰暗的过去。但是在一个深夜,在距离她所在的北京非常遥远的沔水镇上的母亲死去的一刹那,一种近乎神秘的血缘沟通使她从梦中忽然惊醒,她所企图永远抹去的历史重又衔接在她的现实生命中。
丙星子(方方《桃花灿烂》)则力图在反抗与逃避她所隐入的情感困境之后重构自己的未来。星子爱粞,爱得刻骨铭心,粞也爱星子,但粞绝对不会放弃权利同心爱的星子结婚,于他而言,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成为妻子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妻子都可以给他带来权利。粞结婚了(尽管又离了婚),但星子却怎么也难逃脱对于粞的情感迷恋。当她终于以知识女性的理智与自尊同爱她的亦文结婚之后,却忽然闻听粞患癌症的消息,理智的高墙瓦解了,她与粞在最后的情感中完成了灵与肉的结合。九个月后,她生下一个男孩,那酷似粞的一双眼睛让她心惊肉跳。星子所努力重建的未来之梦被粉碎,她仍然未能逃出粞的情感控制,那双眼睛将伴随她的一生也影响着她的一生。
池莉和方方不约而同地以一种颇有宿命意意味的结尾方式宣示了女性所难以逃脱的精神困境,冬儿和星子都将无可奈何——面对历史,面对情感。
正是这种对生命的参悟带来了新写实小说流浪的疲惫感。他们没有嘲笑崇高、正义、真理和追求精神,但他们在长途跋涉之后面对遥遥无期的终点望洋兴叹,最终在一种无法医治的劳顿心态中收回目光,一点一点去铲脚下的坎坷,抑或从此淹没于那些“坎坷”的纠缠中去了。
但“走还是要走的!”西蒙·波伏瓦说:“……我对个体生命最关注的,不在幸福而在自由。”⑨知识女性作为觉醒了的“第二性别”中的一部分,她们必将跋涉不已,去追寻作为人的自由存在境界——为自己,也为仍在蒙昧中的姐妹们。70年前的梦珂说:“无拘无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需要的生命。”70年后的张辛欣说:“假如有假如,我将在无数的前途中选择自由地流浪。”⑩她们的流浪不是被驱逐的荒野之魂的流浪,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我放逐,于她们而言,“自由地流浪”要远远胜于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囚禁。
注释:
①④⑥张辛欣:《在路上》,《收获》1986年第1期。
②张曼菱:《为什么流浪》,《当代》1987年第4期。
③马克·吐温:《亚当夏娃日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⑤翟永明:《人生在世》,《诗刊》1986年11期。
⑦嵇伟:《永远的女人》,《收获》1988年第5期。
⑧伊蕾:《流浪的恒星》,《当代》1988年第4期。
⑨西蒙·波伏瓦:《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⑩张辛欣:《年方二八》,《收获》198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