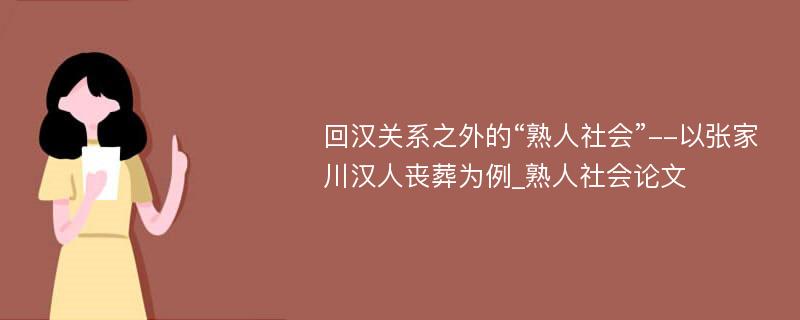
超越回汉关系的“熟人社会”——以张家川的汉族葬礼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为例论文,葬礼论文,熟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6-0042-05
仪式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和重要议题,维克多·特纳曾经说道:“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之时,一个群体会出现某些变化;而伴随着这些变化的就是仪式。”[1](P171)仪式因为其源远流长的历史,繁缛复杂的模式和迷幻离奇的象征表演备受人们关注。[2]同时,仪式与民俗也是密不可分的,生活文化林林总总,其中只有那些体现着一定模式的事像才是民俗。[3]仪式在西方学术界有比较悠久的研究历史,取得过很多的研究成果,出现了格兰姆斯、涂尔干、拉德克利夫·布朗、格尔兹、盖内普、特纳等一大批研究学者,他们对仪式的起源、本质、特征、过程、功能、类型等方方面面都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从西方仪式研究中吸取营养,在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中,把仪式研究作为重要内容,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就其主流来说,仪式研究领域目前主要局限在民俗学、人类学,对象主要集中在民间的民俗仪式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地区与民族的仪式。仪式的现代性和仪式在当今社会的意义研究较少。[4]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拟以亲身经历的一次葬礼仪式的田野调查作为仪式现代性研究的鲜活事例,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折射西北地区回汉民族关系,从一个侧面验证民族学、民俗学理论。从而呈现别样的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机理。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调研发生地张家川大阳乡的基本情况。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东北,总面积1311.8平方公里,总人口31.97万人,其中回族20.69万人,占69%。张家川地处黄土高原,是中国西北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地区,由于这里自然条件艰苦,比较封闭,因此有许多风俗习惯保留得相对完整,具有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极具鲜明的西北地方色彩。大阳乡地处张家川县西部,距县城22公里,下辖24个行政村(其中回族聚居村14个)。
本文选取的G村就是这个回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自治县里面不多的汉族村庄之一,全村40余户,基本上靠务农为生。G姓人占绝大多数,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亲戚关系,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宗族社会环境。G家的老奶奶在八十几岁时去世,G家的族人乡亲都来葬礼上帮忙,在祖屋内搭建了临时大棚,设置了灵堂。G家族人考虑到在民族地区,前来慰问看望的人有回有汉,为了方便招待来人,特地聘请了几位回族厨师来做清真饭食。G家族人把原料采购费与加工费交给他们之后,全由他们安排,回族厨师买来了大约700来斤清真牛肉,若干只鸡,又准备了胡萝卜、粉条等,做西北城乡比较常见的“大碗菜烩肉”招待来人。招待客人的支出是葬礼的最大支出,“大碗菜烩肉”里肉多菜少,由此可见G家人招待亲友来宾非常实诚。按照张家川略微低于省城兰州的牛肉价格,700多斤牛肉就得10000多元,而同庄户人家人均5元一共200多元的搭礼,明显是杯水车薪,即便如此,主人家依然没有太计较付出。因为通常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仪式能否定期举行、排场大小如何,都直接表明一个家族组织的疏密、财富的多寡,进而决定着一个家族在村落社区中相对于其他家族的威望。[5]随着不时有人进来凭吊亡人,因此主人家基本是“流水席”招待。通常每人首先是以同样的“大碗菜烩牛肉”招待,是借鉴当地回族人的饮食习惯,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平等观。之后再是上凉菜,主人向能饮酒的汉族来宾敬酒以示答谢(伊斯兰教禁止穆斯林饮酒,回族来宾多不喝酒),是对民族习惯求同存异的一种质朴表达。为期数天的葬礼仪式,主要是答谢亲友,厨师也处于不间断的忙碌当中,不停地煮肉、上菜。
“库拉圈”实践中常常是,一个人的社会等级越高,这个义务就越大,他的地位越高,就越要突显他的慷慨。[6]由于死者家里有人做过县里的干部,故在当地干部群众中有较多旧相知,有汉族亲戚朋友前来送花圈挽联的,也有回族同胞前来安慰家属的。比较“教门”的回族亲友多不在死者家吃饭,即便是回族厨师打理,在汉族村庄吃饭还是觉得不妥,但也有的是因为行程时间紧张而例外。而且这些回族厨师进入汉族村庄工作,锅碗瓢盆等所有炊具都自备而来。总而言之,在陇东民族地区乡下的汉族葬礼上,虽然两个民族始终保有风俗习惯各异的界限,但是却能感受到回汉百姓彼此之间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异”并没有构成疏远二者“和”的藩篱,有回族研究学者曾经把回族群体内部称之为“熟人社会”,而在张家川这样一个较小的空间范围与社会环境中,“熟人社会”的内涵是超越民族边界的,回汉群众在长期的互动交往中早已结下了熟悉而又友好的情谊,而这种“熟人社会”往往隐藏着透析黄土高原乡土社会和族群关系的关键信息。
剖析张家川“熟人社会”的成因与特点,离不开对整体环境的分析。首先,张家川回汉杂处的“熟人社会”是中国西北尤其是甘青宁地区的缩影,甘肃省是回族人口位居第二位的省区,而张家川就是甘肃省内除临夏之外回族人口聚居最多的自治地方。因此,张家川超民族界限的“熟人社会”的形成就是建立在此地回汉长期杂居的历史基础之上的。从地理上看,张家川位居关陇交通要道,从元明开始,已有少量回族居住。到清代中期,境内汉多回少,有“汉七回三”之说。民族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失败后,清政府把被迫投降的回民安置到甘肃清水、秦安两县境内的张家川镇、恭门镇、龙山镇、胡川、刘堡、平安、张棉驿、川王、连五、梁山、阎家等15个乡镇,被安置在张家川的降清回民共有5万人左右。至此,张家川地区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以前的汉民多回民少变为回民多汉民少的回族聚居区。
其次是张家川回汉群众之间的相互熟悉。以G家人为例,就有父系一脉是汉族,母系一脉是回族的家族成员。众所周知,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回族主要是族内婚,而汉族也多与汉族通婚,然而,据在张家川工作生活的亲友介绍,即便是在张家川这样民族宗教色彩较浓的地方,回汉通婚也逐渐增多,但是几乎都是另一方皈依伊斯兰教来解决双方习俗差异的问题。不论是回汉族内婚还是回汉相互通婚,基于生活在共同地域而衍生出来的对兄弟民族的熟悉、了解与信任都是双方关系的主轴。其族际关系形成机理可以在“工具性依赖”的“谢里夫试验”得到应验。1961年,以谢里夫(Sherif M)为首的心理学家们邀请22位彼此不认识的男孩分成两队到郊外露营,两队营地相距甚远,互不来往,各队队员自然形成一个友善、内部团结的群体(in-group)。在实验的第二阶段,故意安排两队从事相互竞争性的活动,比赛的胜利只属于一方。因此,两个群体彼此敌对。在实验的第三个阶段,谢里夫安排了一个使两组队员形成工具性依赖(instrumentally interdependent)的实验条件,即两个群体必须通过合作才能达到一系列共同满意的超级目标(super-ordinate goals),如此经过多次相互合作的经验后,戏剧性的结果出现了:两个群体间不仅逐渐消除了隔阂与敌对,而且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谢里夫的试验是解释族群关系的浅显易懂的最好样本,试验的第一阶段可以看做是各个民族形成发展初期,试验的第二阶段产生了民族之间资源的竞争和争夺,第三阶段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和依赖,民族之间开始了合作,而且在合作的过程中打破了民族的界限,进而产生了同伴的感情和集体归属感。通常接触理论认为由于群体间的接触对刻板印象有影响作用,因而对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也产生着影响,认为敌意性的刻板观念源于社会性隔离以及受个人相识、了解的不完整的影响,当接触是一种正常的接触种类时,处在一种有利的背景下,就会倾向于减少偏见和歧视。[7]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经济联系形成的“互嵌”格局,正是回汉两个民族形成工具性依赖的前提,而持续接触使得双方熟悉程度不断加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相互隔阂的滋生,因此,相对狭窄而紧凑的空间和生活圈子正是“熟人社会”产生的重要土壤。
再次是张家川回汉群众对对方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认可与尊重。一个方面是汉族人尊重回族人的习惯。在这次葬礼中,G家人考虑到可能前来体恤慰问家属的回族朋友的生活习惯禁忌,特地没有置备猪肉,而且专门聘请回族厨师准备符合清真宰杀程序的牛肉,充分尊重回族厨师的自主权,由其自带锅碗餐具,招待人的筷子、纸杯都用一次性的,不仅无碍前来凭吊亡人的汉族亲友,而且方便了回族朋友来家里茶歇慰问。这样的安排,既秉承了G家人的先长辈在张家川这样的回汉杂居地区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良好家风,也是与整个张家川地区回汉群众历史上长期传承下来的互敬互让的优良传统这样的大气候、大环境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则是回族人对汉族人习俗的尊重。无论是在大棚边准备饭菜的回族师傅,还是前来看望慰问家属的回族干部群众,都对汉族丧葬仪式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尊重。笔者看到送来的挽联中,也有回族书法家写的哀悼亡人的挽幛或文字。甚至有熟识的阿訇等回族宗教人员也前来慰问家属,虽然大多行程匆匆,稍做停留,但是都表现了来自两个民族的熟人朋友之间哀悼逝去老人的共通的情感,同时透射出彼此之间对差异的包容与豁达态度。民族生活习俗的迥异并不能构成人性哀思故去亡人的阻碍,葬礼成为民族间情感交流的桥梁。
不仅如此,在葬礼过程中还感到一些微妙的变化反映了对“他者”习俗的借鉴。例如,陇东一带包括张家川的汉族人家里人去世通常要请“阴阳”,由“阴阳”来决定何时下葬亡人,一般都安排在去世几天后才下葬。早在林耀华、许烺光、弗里德曼(Freedman)等人对中国宗族组织、祖先崇拜的研究基础上,戴维(David)和沃尔夫(Wolf)就已经明确总结出中国民众信仰的神、鬼、祖先三足鼎立的模式,[8]这种被汉族民间广泛接受的“阴阳”一定程度上就担负了沟通死者和死者亲属、阳世与阴间的象征功能,葬礼的很多安排都要听取和遵循“阴阳”的意见。但是由于仪式的繁琐,一些人的抱怨中似乎透射出反思自身和移风易俗的倾向。在为期四天守夜的过程中,一位死者家中的“大大”(西北地区通常以此称呼伯父或者叔父)就讲道:“还是人家回民葬亡人快当。”他是在平时生活中看到了回族人速葬、简葬的习俗才发此感慨的。他记得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己的外婆(回族)前一天下午去世,次日上午就安葬了,去世当天通知清真寺,寺里马上来人拉亡人,洗净遗体缠上白布,同一教坊的人一起帮着抬亡人,阿訇念一段古兰经后就把亡人安葬了。理论上讲,每一个民族在表达自己独特性的问题上都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只要不对其他民族构成伤害,表达什么、如何表达都是各民族自主决定的事情。[9]两个民族的丧葬仪式是各自文化的一部分,正如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也不能说各种丧葬礼仪孰优孰劣,但是从他的话语中,起码可以反映出对文化合理成分的比较与思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民族相互之间的熟悉、尊重与认可,否则只可能产生偏见、隔阂与狭隘。
此外,在葬礼仪式中从来客给“礼金”环节中发现,回族和汉族之间还存在着行之有效的“赠礼”机制来维系和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无论回、汉民族,尤其在举办大规模的公众化仪式活动中,都以收礼的多少作为“砝码”来衡量主人的社会威望和人缘关系。收礼越多越荣耀,尤其有“异族”来参与被认为很有脸面,也是事后主人炫耀的资本。当回族或汉族举办此类活动时,仅捎“礼”(一般为现金或物品)不去人反而会受到对方的责备,用地方性话语来说:“不管你送礼不送礼,只要你人来就给我给足了面子”。值得一提的是当“异族”给对方送礼时,礼金一般都高于同族同类型仪式下的礼金,地方性话语叫“薄礼薄自己”。如果只收礼不送礼,会被其他村民叫做“啬皮”或“没人情”,因而会失去地方性社会资源。在此葬礼仪式的案例里,也可以充分看出这一点,族性的差异非但不会成为乡土社会交往的阻碍,相反恰恰由于“赠礼”机制的存在而成为维持社会生活和地方性知识的建构性力量。
不同的民族成员对族性的感知程度不同,所以不同民族成员对民族群体的认同水平也不同。[10]斯蒂夫·芬顿认为族性是关于“血统与文化”的概念。[11](PP.3—4)在德沃斯看来,族性是由主观的和被一个群体使用的具有符号性或象征性的文化内容所组成的,[12](P86)而回族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流动中建构的生存方式,从而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构筑了回族社会的“面”。正是在这个“面”上,创造了共同文化,塑造和维系了“我群意识”和族群认同。但是在张家川回汉杂处的环境下,族性的因素更多情况下是一个影响族际交往的隐形因素,真正需要考虑的显形因素是宗教及其相应的风俗习惯。宗教在少数民族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伊斯兰教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规程是回族借以建构族群边界、保持自身特色的认同表征与民族心理素质的核心要素,西北黄土高原的汉族人,也耳濡目染了很多回族人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在张家川这样相对狭小封闭的空间里长期互动,彼此对于对方的宗教习俗和生活方式了然于胸,宗教和族性的影响基本上都稀释在邻里、朋友和乡亲的氛围当中了。对偶尔发生的纠纷也都能将其视作社会生活中普通个体之间的私人纠纷加以解决,一般不会将其轻易上升到民族层次,更不会上升为族群之间的对抗,这也从历史上得到验证,选取某一历史断面也可以说明,张家川回汉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绝非是一朝一夕的。在清同治以前,张家川回汉民族彼此互相援助,解衣送食,表现了亲如兄弟般的民族关系。同治以后,这种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如在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陕西固关回民千余人,因受清军和地方团练的胁迫,拔眷离境,越过关山来到张家川上磨村一带,上磨东山王家堡子的汉族人民,看到固关回族处于背井离乡、缺吃少住的困难境地,于是,便由汉族人王平安出面,一边慰藉固关逃出来的回族百姓,一边动员本村汉族人捐衣、捐面、捐粮油。这样所形成的回汉民族关系是和睦的、友好的,他们所形成的回汉民族关系对今天都有影响。[13]可以说,过去一百年来,西北回族社会发生的转变是巨大的,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不可否认的是,其转变还是与汉族等兄弟民族的交往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相交融、同进退的,从而才呈现出黄土高原独特的跨族界的“熟人社会”的景观。
当然,张家川回汉群众之间也有隔阂,然而他们有时会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表达和舒缓这种情绪,并不会影响总体融洽的性质,甚至更加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这次田野调查的葬礼仪式中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些关系很密切的回汉朋友私下里相互嘘寒问暖、聊天打趣时,回民称呼汉民为“呆迷”,而汉民称呼回民为“老回回”,然而这绝非恶意,并非是带有侮辱、挑衅或歧视意味的称呼,而是双方关系熟悉融洽的氛围下类似于调侃或打趣的称呼。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绰号往往反映了人际交往中的亲密程度,只有双方熟悉了解到一定程度,才常常用绰号称呼对方,从个人放大到民族方面同样如此,这从这种不雅又略带调侃的称呼甚至成为乡土语言中民族的非正式代称就可见一斑。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能够豁达地接受对方给自己起的绰号而不至于敏感动怒,也反映了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与心态的平和程度,以及双方的良好紧密关系。在一个民族壁垒森严、自身与他者区分明确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滋长出这样的现象的,而只可能是猜忌、防范与封锁。实际上,张家川回汉群众相互走动频繁,比如汉族人给回族朋友开斋,回族人给汉族人拜年等参加对方的仪式活动的例子在当地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民族间在生活习俗仪式方面的差异不仅没有成为交往的障碍,相反为双方交往和走动平添了些许由头,从而进一步增进和融洽了彼此关系。张家川回汉关系是西北地区乡土回汉关系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稳定、团结和互相尊重是张家川回汉关系的基本特征。
文化自觉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对文化自我的一种自知之明。[14]张家川大阳乡的葬礼仪式的微型个案,从另一个角度生动地展示了乡土社会中两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是如何促成了更大的文化认同的。因为,一个共同体有多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取决于它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文化。[15]共同的语言文字使得回汉民族之间的心理素质与思维方式比较接近,不论张家川的回族还是汉族,大家共同操一种近似于陕西关中口音的方言,由此具备了产生地域社会认同的前提条件。社会认同,作为一种集体观念,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它来源于可以被个人感知的集体活动。涂尔干认为正是在集体活动中,个人才能感受到一种来自集体的情感和力量,但是,集体活动并不能直接产生社会认同,它须借助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力量才能实现向社会认同的转化。[16]包括婚丧嫁娶在内的乡土社会的各项活动仪式正是培养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的土壤。同时也从侧面昭示了,文化认同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国家层次,而且涉及文化如何在地方性社区中发挥作用。对于本案这样互动极其频繁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环境和场域而言,族际藩篱基本上都稀释在邻里、朋友和乡亲的氛围当中了,共生性认同是常态。由此可以看到少数群体权利的辩论经历了从社群主义到自由主义族裔文化中立,最后到少数群体权利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回应的过程,这也似乎隐藏了从微观到宏观的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存续和发展的生命力的原始密码,而本文微型个案提供的黄土高原“熟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民俗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交叉视角审视民族关系,可以说是对中国乡土社会和族际互动的管窥与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