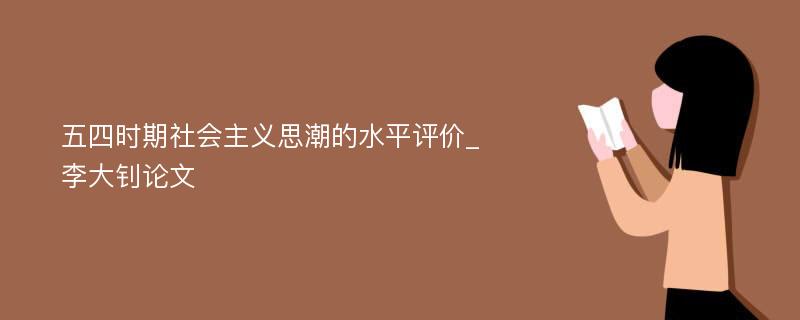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水平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水平评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有如一个人类社会主义思想的博览会,在西方世界产生、流传的许多社会主义的流派几乎都在中国得到展示。中国知识界关注社会主义的热情,大大超过了以往对资本主义思想的热情。一种社会思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恐怕是此前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
然而,影响较广且拥有较多信徒的社会主义思潮,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几种。笔者认为,上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总体水平是比较低下的,但它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又都曾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对此也必须给予恰当的评估。本文试图就此进行论析。
一
五四时期,最早对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是无政府主义。这固然因为自清末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宣传,也还在于无政府主义学说否认一切社会秩序的挑战性勇气和对无政府社会的描述,对强烈追求政治和生活自由的青年人颇具诱惑力。但是,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水平,无论是与其崇拜的西方前辈,还是同辛亥前后刘师培和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相比,都是相当低下的。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最为推崇的西方无政府主义大师是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在他们看来,“无政府的学说,从蒲鲁东先生的时候才成立;无政府的运动,却始自巴枯宁先生。……克鲁泡特金不单是能从学理上发挥无政府的精义,并且还实际的做各种的革命运动,在现在的时候,总要算他是一个‘集无政府主义之大成’的人了。在支那的无政府党,大半都是采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页。)他们所钟爱的这些西方无政府主义者, 都曾进行过大量的理论著述,并建构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或曾有过值得称道的贡献。如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曾说“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3页。), 而其名著《什么是财产》“是共产主义者用法文写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哲学意义的作品,……作者在揭露私有权以及这一制度所引起的后果——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上,表现了非凡智慧和真正科学研究精神。”(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2页。 )再如克鲁泡特金,一生著作颇丰,其《互助论》、《组织论》、《社会进化与无政府主义之位置》、《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均被译成中文,对中国知识界产生过极大影响。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就是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和崇拜者。
无政府主义思潮自清末传入中国至五四前,刘师培、刘师复当是无政府主义宣传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刘师培为主要代表的“天文派”无政府主义,提出了“人类平等说”、“人类均力说”,主张废除政府、实行共产等,构成了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个较完整的理论形态。他们强调以“劳民”即农民和工人为无政府革命的依靠,以“农民革命”为无政府革命的基础,甚至提出“没豪富之佃,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的口号,在当时的思想界也算是发人之所未发;他们主张包括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平权、教育同等、废娼等为内容的“男女革命”,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更为天下之先。再如刘师复,其影响远在刘师培之上。他自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淬厉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以死”(注:郑佩刚撰:《刘师复墓表》,转引自徐善广等著《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被其信徒誉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的“模范革命实行家。”(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50页。 )他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以及关于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整套设想,构成了“师复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大都是师复主义的信徒。其代表人物黄凌霜和区声白等人,即明确宣示师复主义“就是我们的主义”(注:凌霜:《师复主义》,《进化》第1卷第2号。)。
反观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无法与其中西前辈的水平相较。他们没有像蒲鲁东那样写出“有哲学意义的作品”,更缺少他那样的“非凡智慧和真正科学研究精神”。在无政府主义宣传上,他们除了重复克鲁泡特金主义和师复主义外,则别无新招。倒是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方面大大超过了刘师复。他们指斥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的定义”(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7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抹煞个人”的“强权”,必须反对;俄国“工农兵苏维埃”也是“独裁专制”,应早早废止(注:A·F:《为什么反对布尔雪维克》,《奋斗》第8号。 )。他们如此咒骂马克思主义,意在为无政府主义争取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信徒,结果却适得其反,倒使他们在理论上的无知和荒谬得到充分暴露。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击下,无政府主义者纷纷败下阵来。之后,无政府主义宣传就“奄奄一息,几无生气”,渐趋沉寂了(注: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2页。)。可以说,黄凌霜、 区声白等一班人只是把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推到了中国无政府主义史上的极盛期,却鲜有理论上的发展和建树。整个五四时期也没有产生过刘师培和刘师复那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颇流行。比较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水平也很低下。我们知道,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曾称颂他们“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注: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对于鼓吹泛劳动主义的托尔斯泰, 列宁也认为他的主张中“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注: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页。)。 而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激烈抨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地狱社会”,向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但这种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均缺乏深沉的理性思考。他们所提出的“菜园世界”、“工读互助团”和各种“新村”的方案,只不过是法国“鹰山共产村”和美国“蓝路共产村”的移植。他们为实行这些方案而进行的各种试验,除了使自己遭遇与其西方前辈同样的失败命运外,并未使这个理论在中国得到合理性验证和新的长进。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水平十分低下,但却拥有众多的信徒和追随者,其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一度远在科学社会主义之上,这其实并非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繁荣,恰恰相反,这是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步入穷途末路前的回光返照,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存在严重的理论“饥荒”。
二
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涌动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流派。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学习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黎明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水平也是比较低下的。
我们知道,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在欧洲大地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涌现了一批具有杰出理论才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中有理论上“有高深的造诣”的倍倍尔(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有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的拉法格等等(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8页。)。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中,普列汉诺夫也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所写的许多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其中,《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416、418页。 )。相形之下,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却没有产生如上所提到的那样的理论家。从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对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宣传来看,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陷。
第一,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决裂。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都钟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曾参加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他们肩负起介绍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后,思想上仍然残留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痕迹。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也是五四时期水平最高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发表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同时,仍然主张建立“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页。)。 他认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第222页。),而“协合、友谊、互助、 博爱的精神”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他在承认“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的同时,也强调“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4页。)。 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李大钊比较正确地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明了“道德之历史的变迁”问题,但他又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把道德的本质阐发明白了”(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0页。)。 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语义抽象的、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印痕的话语,如“自由、平等、博爱、互助”,“自由、平等、爱助”,“人道主义”、“人类都是同胞”,等等(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1页。)。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陈独秀思想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他在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此前迷恋过的资本主义文明仍然难以割舍。在《谈政治》中,陈独秀明确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按理,既然是“第一需要”,就应该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他却马上改口说:“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贫苦的劳动者”(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页。)。陈独秀代表“贫苦的劳动者”向资本家提出了“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即“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他说,中国工人“吃苦耐劳而工钱又极低贱”,如果中国资本家不满足劳动者这些可怜的要求,那么,外国资本家就会涌入中国办实业,革中国资本家的命。这就不单是“工人底不幸”,也是中国资本家的不幸了。显然,陈独秀是企求资本家向“困苦”的中国工人发“善心”,以劳资相济抵御外资。看来,他除了“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外,并没有拿出帮助“贫苦劳动者”的好办法(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页。)。后来,他又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页。)。这与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如出一辙。可见,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思想上并未完全剪断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瓜葛。
同时,各种流派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很大。李大钊似更偏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认为“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协合与友谊”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他引证了克鲁泡特金的话:“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说“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正因此, 他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常谈及“协合”、“互助”的道理(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7页。)。 陈独秀也将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我们持论底榜样”(注:长沙《大公报》1920年1月11、12 日。)。他和李大钊也是工读互助团的热心支持者。李达甚至将“正统派社会主义”(考茨基派)、“修正派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派)、“工团主义”、“组合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多数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统统纳入“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认为各派社会主义“在社会改造的根本原则上”是相同的,“都是主张将生产机关归社会公有的”。只是“因为各国国情和国民性不同”,才使“所采手段,各派各不相同”(注:《新青年》第9卷第2号。)。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一般的观点,没有从整体上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和稍后陈独秀的《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是较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文章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大都是根据日本社会主义宣传家河上肇的译文,而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他们理论的重要论著,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除《共产党宣言》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根本没有中文全译本,有的甚至没有外文本(注: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页。)。据此,我们可以认定, 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未完全阅读过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因此,使他们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造成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浅薄和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曲解。
我们仍以李大钊为例。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认为马克思“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0页。 )。他在指出唯物史观“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和“莫大的功绩”的同时,又说它有“夸张过大”、“流弊”和“应加救正的地方”(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4页。)关于剩余价值学说, 他也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劳工价值论”也存在很大“遗憾”(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5页。)。很显然,李大钊自己未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只是从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中初知了马克思主义的片断和零星的知识,依此而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批评,自然是错误的了。
第三,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时,表现了明显的幼稚和“初步”水平。五四时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初知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后,就尝试运用它来分析研究历史和社会问题,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因为其理论上的幼稚,使这种分析往往玉石不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解释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问题的重要论文。他指出:“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它“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页。)。这里, 李大钊剔除了道德起源问题上“神明的赏赐物”等错误观点,却又把人看成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人,把道德看作是动物的某些本能的延续。他正确地认为社会经济关系(即“物质”)的变化是道德变化的基础,但对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道德所具有的阶级性则忽略了,而提倡抽象的所谓“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3页。)。 显然,接受唯物史观后的李大钊,思想上还残留着达尔文主义和唯心史观的影响。这样在研究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在某些方面尽管可以给人以新鲜感,却也难以得出准确和科学的结论。
如上我们主要以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为例,指出了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水平普遍比较低下。吴玉章在回忆自己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那时候,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115页。)。他的这段话,也是五四时期共产主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水平的真实写照。
三
一种理论是否被一个民族所接受,取决于这个民族对这种理论是否需要。换言之,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具有适宜这种理论生长、发育的土壤和条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说明了这一点。
面对五四时期光怪陆离、异说纷呈的思想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饥不择食。他们宣传其先辈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企图以此作为救治中国的药方。但这些理论本身缺乏科学的基础且早已过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西方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流行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鼓吹他们所信仰的理论时,并未细心考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他们的言论,无论是对封建主义的抨击,还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都充斥着情绪化的愤激之辞,带有明显的非理性倾向。他们所提倡的貌似超凡脱俗的行为规约,也明显缺乏时代特点。他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也如镜花水月。这样,当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流传时,因其主张状貌新奇而吸引了不少人为之洗耳,但喧闹一阵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新奇的议论有如一种隔世之音,于是纷纷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厌弃心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也因此而陷入窘迫境地。自然,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无法达到其前辈的水平,或无法提供一些比其前辈新的东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境遇相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从一开始在中国传播时就显示了自己的勃勃生机。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审慎比较推求后的理性选择。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既不是个人情绪的渲泄,也不是纯粹的学理研究,而是要运用这个伟大的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指导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新道路。用李大钊的话说,是要研究怎么可以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0页。), “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页。)。可见,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显现了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良好开端。至于说,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或不能熟练地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则主要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充分展开,因为他们所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不多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始阶段,这种现象也是难免的。我们在指出他们科学社会主义水平较低的同时,也不能过于苛求。
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总体水平是相当低下的。然而,对各方面人士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却不可低估。在评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时,我们不能忘了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民族产生了伟大的理论家和伟大的理论,不一定会推动这个民族出现巨大的进步。而当一个落后民族的先进分子初知了这个理论,并运用它来指导本民族争取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斗争时,却可以使这个民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随先辈们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足迹,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在五四时期所从事的巨大的科学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实际中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伟大理论的指引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成就了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伟业,从而把落后的中国导向了社会主义的新境域。正如此,李大钊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具有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纪念的意义。
同时,对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的历史作用也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作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尽管不可能把中国导向光明的前途,但他们却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汇聚在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大合唱,社会主义也成了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这在客观上营造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文化氛围。无政府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满现实的呐喊和对其理想社会方案的宣传,确曾使许多青年人心旌摇动,自然,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也成了人们了解社会主义的窗口。许多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正是通过他们初知了社会主义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是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梯。
收稿日期:1998-09-16
标签:李大钊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陈独秀论文; 空想社会主义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