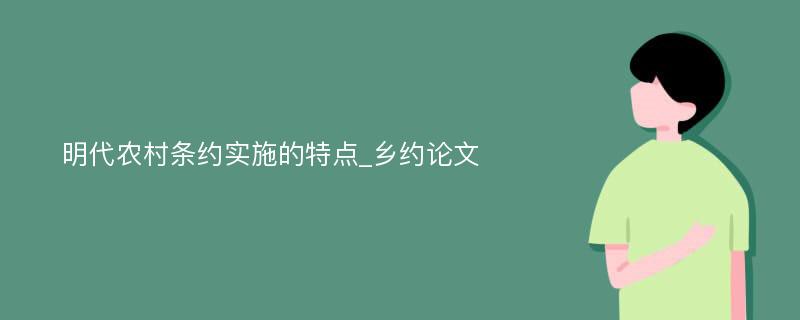
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乡约的倡行,是中国古代乡治理论与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据现有的资料考查,乡约盖渊源于周礼读法之典,州长、党正、族师咸以时属民而读邦法;其滥觞于北宋蓝田四吕兄弟,以《吕氏乡约》为后世作则;大张于里甲毁坏、社学失修、朱明统治出现全面深刻危机的明代中后期,本文拟就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谈些粗浅的认识。[1]
一、民办和官办的共存、综合性与专门性的并举
明代最早建议举行乡约的是解缙,在《大庖西室书》中,解氏“欲求古人治家之礼,睦邻之法,若古蓝田吕氏之乡约,今义门郑氏之家范,布告天下”[2],但明太祖未予采纳。后来成祖“取蓝田吕氏乡约列于性理成书,颁降天下,使诵行焉”,不过他看重的只是乡约的规条,并不欣赏其民众自治性质,因而此时的乡约只是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未能付诸实践。
明代乡约究竟始行于何时何地?学界一直说法不一,有系统研究中国乡约制度史者,称正德十三年(1518)王守仁所行南赣乡约,是明代的第一次乡约[3],有研究徽州府者,谓所见行者以嘉靖五年(1526)为最早[4],近又有以河南、山西为例,论明代中叶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者,称依《明史》所载,正统间吉水刘观(正统四年进士)致仕以后行乡约于邑中,似无人较其更早[5]。依笔者所见,刘观之前举行乡约者已不乏其人,如福建人王源行于任所潮州和桑梓龙岩,广东“平步六逸”行于乡里。王源为永乐二年进士,在知潮州府任上,“刻《蓝田吕氏乡约》,择民为约正、约副、约士,讲肄其中,而时偕寮寀董率焉”[6],正统三年,已退居林下的王源又于邑中倡行乡约,[7]其在官董官办乡约,在野率民举乡约,论明代乡约者实不可不提。由此亦可见,明代乡约推行伊始,便是民办与官办同步。在正统至弘治朝(1436—1505)的八十年间,官办乡约曾在泗州、济宁、温州等州县出现,举民办乡约的有吉安罗伦等乡绅。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乡约,无论是民办还是官办,发展都是缓慢的,尤其民众自发举行乡约,“欲乡人皆人于礼,其意甚美,但……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势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施之父兄弟宗族之间哉”[8]。进士曾昂就因举民办乡约而遇到过麻烦,据罗洪先称:“今所传乡约,公手笔也,其后谤胜于朝,谓公居乡专制生杀,台谏将纠论之”[9],乡约的发展步履维艰。
正德以后,明朝的统治出现了全面深刻的危机。一些饱读经书,以修齐治平相砥砺的儒生、官吏,纷纷倡行乡约于乡里、任所,视举乡约为济世安民之迫切良策。期间,潞州仇氏乡约和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影响尤著,前者可视为民办乡约的代表,后者则开启了明中叶以后官府倡办、督办乡约的全盛之局。
仇氏世居山西潞州南雄山乡之东火村,自明初开墓雄山,至正德六年仇楫、森、桓、栏举行乡约之时,已历五世,其百口同爨庭无间言,有三晋第一家之誉[10],仇氏兄弟所行之乡约,盖以蓝田吕氏为蓝本,又以仇氏家范配合而行,其理想则谓“居家有家范,居乡有乡约,修身齐家以化乎乡人”,自冠婚丧祭及事物细微训后齐家之则,靡有阙遗,仇楫营义房一区于家,敦请乡先生以教宗族子弟,免其束修,再起义学一所于乡里,以训乡党童稚,资其薪水,设医药以济穷乡,有疾病者置义冢[11],刊印太祖高皇帝训辞,家给一册,讽诵体行。“为当代之所崇尚,秉笔之士亦笑谈而乐道之”[12]。
南赣乡约是一种新型的乡约,“此中丞阳明公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也”[13],正德十三年十月后,在南赣颁行。王氏指出:“民俗之善恶,岂不由积习使然哉……自今凡尔同乡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伤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其规条共十六项,规定约中职员出于约众之推选,约众赴会为不可规避之义务,约长同民众得调解民事之争讼,约长于集会时询约众之公意以彰善纠过。在王守仁的多次倡督之后,其乡约法在南赣及福建龙岩、江西吉安、广东揭阳等地得到了推广,王守仁学问不让于朱子,而事功又远在一般士大夫之上,其生封伯,死赠侯,门徒遍及江右、浙中、南中、楚中、闽粤、北方,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对乡约的倡导与重视,对此后的士大夫们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嘉万(1522—1614)之世,乡约的举行,在劝善惩恶、广教化厚风俗的总体精神指导下,全国各地还产生了一些为某一具体目的而建立的专门性乡约,如护林乡约、禁宰牛乡约、御倭乡约、御虏乡约、御贼乡约等。祁门三四都侯潭、桃墅、灵山口、楚溪、柯里等村,早在弘治年间就成立过护林乡约会,嘉靖二十六年,由于近来山木“节被无籍之徒……望青砍断,斩掘笋苗,或为屋料,或为柴挑,或作冬瓜芦棚”,致山林遭到破坏。为保护生存环境造福子孙,各村人众遂合集一处,重新订立规约,将各村人户共编为十二甲,甲立一总,置立簿约十二扇,付各处约总收掌,一年四季月终相聚一会,“并将议约规条由众人联名俱状,赴县呈告”,由县衙告示印钤,四处张挂,俾人人知晓,自觉遵守[14],嘉靖十四年,被廷杖除官的前御史朱淛,以乡里莆田县“间有惯习屠牛,阴通盗贼,行凶逞暴,作过为非,凡有失盗之家,便来此寻觅,叫号喧闹,无日无之,鸡犬为之不宁,乡里被其污蔑”,遂与乡民倡行誓禁屠牛乡约,“今乡中父兄子弟同兴善心,共立约会,就于天日之下,重发誓愿,除老疾暂食以外,断绝此味……今立此簿,与各人笔,自书名姓,岁时朔望,告于里社,呈于乡众,期于共守,以还淳风”[15]。嘉靖十九年又率乡人重申前誓。嘉靖二十三年,致仕乡居的歙人郑佐以“今者天时亢旱,人心忧危。奸党乘机邪谋窃发,假称借贷敢拥人于孤城。倚恃强梁,辄紾臂于单弱。白昼公行而无忌,昏夜不言而可知”,倡导乡绅预为桑土之谋,举办带有团练性质的岩镇乡约,“一镇分为十八管,有纪有纲。每管各集数十人,一心一德……理直气壮,强暴知所警而潜消。力协心孚,良善有所恃而无恐”[16],嘉靖二十九年,蔚州人尹畊著成《乡约》一书,曰堡置、堡势、堡卫、堡器、堡蠹、保众、堡教、堡习、堡符、堡费、堡候,要在倡乡人抵御“北虏”之患[17]。嘉靖三十四年,岩镇乡民以“倭寇势甚,陆梁冷落。孤踪辄奔溃而四出偷生,余孽益草窃而蔓况入”,遂爰集里众重订新盟规约,“模仿甲辰岁御寇之条事款,益损大参双溪郑公之旧,固严闸栅,庶缓急守卫有基,推举晓勇,俾临事当关足恃用”,称“岩镇备倭乡约”[18]。崇祯十五年(1462),吉安乡仆结细户“乘机叛主,自称小约,其党羽甚者号大约,焚掠劫杀无忌弹,启衅于永福上乡、宣化、延福,及各州亦蔓延焉”[19],由此可见乡约的组织形式在明代的社会生活中,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朝野不同人物所接受。
二、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建构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体系
伴随着官办乡约局面的兴盛,嘉靖以后,明代乡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就是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关系的日益密切,四者由各自举行,互不关连,进而相辅而行,互有侧重,再为完全打成一片,形成以乡约为中心的乡治体系。
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的关系可谓源远而流长。保甲法创始于宋熙宁间之王安石变法,而溯其源又在程灏之保伍法[20],其法与吕氏乡约多有融通之处,以至有人误以保伍法为乡约之肇始者[21]。社学与乡约的关连,在朱熹的《增损吕氏乡约》中便已露端倪,只不过社学一词在元朝以后才出现,当时称乡校[22]。社仓出现的时间虽至迟不晚于隋,然则其与乡约发生关系,似乎仍是明中叶以后之事。乡约、保甲、社学、社仓是明代乡治中的四大要素,明代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关系的演变实肇于王守仁的南赣乡约。
在王守仁的乡治思想中,保甲、社学、乡约是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分三个步骤独立举行的。王守仁首先推行的是十家牌法(即保甲法),先后颁布有《十家牌法告谕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法》、《申行有司十家牌法》、《申谕十家牌法》、《申谕牌增立保长》,此法编十里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每日沿门按牌审察,遇面生可疑之人,即报官究理,若有隐慝,十家连坐[23],这是针对南赣治安状况差坏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以故明人多以为敷教同风莫善于乡约,禁奸止乱莫善于保甲。社学在明初已出现,明太祖曾诏令各地延师以教民间子弟,然而延及正德时“其法久寝,浸不举行”,诏令徒为具文。王守仁治南赣,遂严令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免,延师教子,并不时下乡巡察、纳入官吏考成,促成“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24]。
在南赣乡约初颁的条规中,乡约与保甲、社学是各自独立、各有职司的,乡约就是乡约,保甲就是保甲,不过乡约与保甲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相辅而行之事也已发韧,在《南赣乡约》颁行的次年,王守仁就将约长的资格作了修订,原定“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推服者一人为约长”,代以“各自会推家道殷实、行止端庄一人充为约长”,道德标准被弱化,经济实力更受注重,并且要求“将各人户编定排甲,自相巡警保护,各勉忠义,共图国难,敢有违抗生事,警扰地方者,就便弩解赴官,治以军法”,执行本属保甲的部分职责。
率先将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提倡而行之的是黄佐的《泰泉乡礼》,其说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于古者,再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25]。概而言之,黄氏的治乡方略有以下特点,其一,是以乡约为侧重,乡约与社学、社仓、乡社、保甲综而行之,约正参与社学、社仓、乡社、保甲的一切重大活动,教读、保长若无合适人选,由约正兼之,成为乡村教化、行政最高首脑。乡约之众即编为保甲之民,教读、约正申明乡约于乡校,违约者罚于社,入谷于仓。其二,明确规定乡约的自治性质,“约正、约副则乡人自推聪明诚信为众所服者为之,有司不与。凡行乡约,立社仓,祭乡社,编保甲,有司毋得差人点查、稽考,以致纷扰。约正、约副姓名亦勿遽闻于有司”[26]。其三,官府与乡约的关系在于官倡民办,有司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为民去其十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提解、招引告讦、重垒催科、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逢月朔,教读率约正约副之贤者,以次往见有司,有司赐见坐谈,言可用者予以褒奖。
黄佐《泰朱乡礼》之后,继续倡行将乡约与保甲、社学、社仓打成一片的,是章璜的《图书编》。不过在章氏的治乡方略中,乡约不作为中心,而是与保甲、社学、社仓完全平行的,并且乡社不另独立开来。对于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他指出“四者之法,实相须也”、“保甲即定,即此举行乡约”,而后兴社仓、社学。“约正或系乡宦、或有德年高,有事不必赴官,保正代之”。又指出“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盗贼也,而不知比闾族党之籍定,民则自不敢以为非。乡约之法,人知其足以息讼也,而不知孝顺忠敬之教行,则民自相率以为善,由是社仓兴焉,其所以厚民生者为益周,由是社学兴焉,其所以正民德者为有素”[27]。
以乡治的核心——乡约、保甲兼行而加提倡的,在嘉万以后尤为多见。其理论较备者如吕坤的《实政录》和刘宗周的《乡保事宜》。
《实政录》为吕坤门人赵文炳集其从政要端而成,所论治术颇多具体扼要,吕坤乡约方案的特点在于合保甲乡约为一条鞭,将乡甲约完全纳入官治系统。主张官倡官办,吕坤指出“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乡约保甲原非两事,本院捧读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应行事列,谓乡约所约者此民,保甲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究诘为重,议将乡约保甲总一条鞭”,约长与保长,一身而二任,十甲甲长,依然不动,只多添了一个甲正副,约史、约赞、约警、知约俱由保甲公职者充任,期以“良民分理天下,有司总理于上”乡约与保甲合二为一,“提绵挈领,政教易行”[28]。
刘宗周也是主张乡约与保甲合一的,只是在以何者为中心的问题上,前后又有一个变化。崇祯二年,清军骚扰京畿,时宗周为应天府尹,为保境安民,遂发表《保民训要》,这是一个将乡约与保甲相结合的方案,以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禁、保甲之备相倡。其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内容近似于乡约,保甲之养则涉及社仓,整个乡治方案的中心是保甲,次以乡约社仓相辅,是寓乡约、社仓于保甲之中。崇祯十五年,刘宗周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职司风宪纲纪,又作《乡保事宜》,寓保甲于乡约之中,以乡约为中心,推行教化施治。是书分约典、约戒、约礼、约制、约法、约备六部分,其约典、约戒分别开列圣训六言和吕氏四条;约礼仿于洪武间乡饮之制;约制举彰善、纠恶条例;约备指出约众要有器械和粮贮,要守望、巡逻,此亦保甲和社仓份内之事,而对于社学虽未完全不提,但已列于从属地位。
真正从体制上理顺了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关系的,是陆世仪的《治乡三约》。陆世仪生当明清易代之变,在朱明崩溃的前夜,他对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指出“乡约为纲而虚,社仓保甲社学为目而实”,乡约“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因而他的乡治三约,也就是一纲(乡约)三目(社学、保甲、社仓)的乡治体系,“乡正之职,掌治乡之三约,一曰教约,以训乡民;一曰恤约,以惠乡民;一曰保约,以卫乡民”,“凡乡之教事责教长,恤事责恤长,保事责保长”,若“长非其人,责约正”[29]。其乡约之法,纲举目张,职责分明,尽得乡治阃奥。唯以朝代更替,陆氏终未能将其法付诸实践,但束之高阁,而无以求得实践之检验。
综上所述,自王守仁、黄佐、章璜至吕坤、刘宗周、陆世仪,乡约与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由自成体系,不相为谋;而四者并重,打成一片;而以乡约、保甲为中心,以社仓、社学相辅;而以乡约为纲,以社仓、保甲、社学为目,纲举目张。尽管这种关系大多存于官倡、官督的乡约之中,有些还只是停留在文字上,尽管各地官办乡约的形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它反映了明代乡治理论的日趋完善和乡约体制的日臻成熟,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乡约在乡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组织管理也日益完备。
三、推动宗约、士约、乡兵约、会约的兴盛与发展
伴随着乡约活动的兴盛,宗约、士约、会约、乡兵约等依一定的身份和目的而结成的民众自治组织也趋于活跃,它不同程度地受着乡约发展的影响,有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乡约的发展,使明代中后期的乡村、城坊、仕林中出现了社、会、约兴盛的格局。
(一)宗约 乡约与宗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范畴和组织。作为一定的民众共同恪守的规条,宗约是与宗族祠堂管理相配套,规定和说明族人与宗族、家庭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宗族的职责和对族人的权力,处理与族人事物的原则等等,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与乡约的条规不尽相似。而作为一定的民众自治组织,乡约约于一乡之众,宗约只约于一族之人。乡约与血缘虽不无关连,民众们多是聚族而居,但强调的地缘,是一族以上的几个族人的结合体。宗约注重的则是血缘,讲究血缘亲情。乡约与宗约在一定的时候又可以互相转化,或由宗约的示范推而广之为一乡之约,或由乡约受阻退而行于一宗之内,再或是乡约与宗约并倡,举乡约不忘宗约,举宗约时恪于乡约。有些乡约本身也就是宗约。
乡约自问世伊始,就与宗约有着不解之缘,明中叶以后,随着乡约的兴盛和民修祠堂的驰禁,宗约也随之兴盛。清人陈弘谋在为明《王孟箕讲宗约会规》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按一乡之内,异姓错处,尚且有约,交相规劝,况于同宗,以其尊长,约束子弟,临以宗族,训诫后裔,较之异性,事情更亲,观感尤易,则合爱同敬,谨身寡过,均不外于宗祠焉得之”[30]。万历初年,丹阳知县甘士价倡乡约,乡绅姜宝即请“兼行保甲法及予宗自为约,不令他姓人得参与,有所妨”,甘士价特许举行,据姜宝自称,举行不久便见成效,及甘士价丁忧去职,其邻里他约皆停寝,姜氏又请于府台,提出改乡约为宗约,以宗约行,同时指出,“由予一家遍推于家家,由一时行之于时时将见,化行俗美,盗息民安,于讼不严而渐少,逋免不严而易完,无论民间受益,即官长不烦心力,可卧而待治矣”[31]。此宗约所行,俱乡约之职,宗约者,一姓之乡约也。
不过,一般的宗约大都是在组织形式上仿于乡约,在具体条规中又体现出宗族性的色彩。笔者所见《王孟箕讲宗约会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讲宗约会规,乃王孟箕居乡时所定,共七款,包括期会款式、讲约规条、周咨族众、讥察正供、平情息讼、矜恤孤苦、禁戢闲谈。约定每月两会,或朔望,或初二、十六,会所摆列书案、坐席,东西相向,族人照班辈、序次分坐,案上各置所讲之书,另设讲读之席于前,择声音响亮或新进秀才二人为约讲、约读,又设约警一人,手持云板,维持秩序。有些宗族还将遵行乡约列入宗规之中,如笔者另见《王士晋宗规》凡十六条,第一条便是乡约当遵,称圣训六言包尽了做人的道理,无论圣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今于宗祠内,仿乡约仪节,每朔日,族长督率子弟,齐赴听讲,各宜恭敬体忍,共成美俗”[32]。
一些在官倡行、督行乡约者,致仕还乡退居林下之后,也多有倡行宗约之举,万历二十五年,吕坤致仕还乡,亲作宗约以备其法,使宗人修祀事、讲宗法、睦族情,又作宗约歌八十五首,用“极浅、极明、极俚、极俗”之文字,“但令人耳悦心,欢然警悟”,宗约内仿乡约也设有彰善纠恶之册,只是名称做了些改动,纪善的叫做鹄史,纪恶的称做颚史。崇祯七年,刘宗周在家乡居,作《乡约小相篇》,请行于邑中,既不获知县采用,便作《刘氏宗约》行于族内。约设宗长一人,总一宗之教,约九族之人,又设宗翼两人辅弼宗长,宗干一人司钱谷出纳,宗纠一人,纠绳纲纪。约内还置有彰善纠恶簿,月朔行告庙之会,演讲圣训、祖训。据称,“服习既久,风尚一变,二十余年,通族莫有讼公庭者”,其殁后,族人“犹遵行教不衰”[33]。
(二)士约 乡约者,约于民众,而士约只约于诸生。虽乡约之民众也包括有诸生,诸生则为民众中一特殊群体。明代的士约,多起于讲学会和文人结社,而组织管理形式又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乡约的影响。
士,作为生员衣冠之族,其言行关乎世风尤重,“士肯好修,同学见其人而爱慕,居乡熏其德而善良。官于内则为朝著仪形,官于外则为缙绅师表”[34],故此无论是民办,还是官督民办、官倡官办之乡约,士都是核心力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世风日下,作为缙绅之表、乡里风范的士,其道德沧丧、不学无术、不问世事之举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一些以振刷世风、挽明于即倾的士大夫们便又倡行起士约来,“顾人心之良不触则不发,良心之发,不聚则不凝,一番拈动,一番觉悟,一番聚会,一番警惕”,故“爰为会规数条,与诸友共守之”[35]。
据王徵《士约》称,“兹欲以三物之教望今日,诚恐骇人心目。吾姑为其卑近者。所愿该学于诸生相近所在,不拘多寡,各立会约”[36]。每约给以进德、修业印信两簿,选年长公直者为约正以主察举,选通敏博洽者为约率负责倡导。进德之先要纠十二过,士有免此十二过者,即纪之进德簿中。修业则先讲十二政,若能讲明此十二政,则录之修进簿中。
在江西吉安,仅乡人邹元标为之作序颂扬的就有“青原盟”,“龙泉文明会”,“仁里斯文会”等士约,据邹元标称“一日,九邑有青原盟,诸长曰;龙泉学者,少宜以人代,诸友闻而奋曰;此吾乡辈继往开来,衣钵非人有任,吾觉自任之,于是醵金为费……诸君归而举文明会章,章有纪,邹子为之约”[37]。这些士约不但有组织、规章、簿籍,而且不定期聚会,互通生息,相互砥砺,与乡约并行不悖。
当然,明代的乡约与士约间虽有不少相近、或融通之处,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在于士约强调身份,非诸生不得与,非从科第明经及奉褒崇者不得与,“类聚严而祀典明备”。而且乡约影响和作用主要是在地方,士约在聚文讲习、格物明德之余,则不少都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因而明中叶以后,朝廷对士大夫倡行乡约是支持的,而对他们聚会讲学、结社会文则是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
(三)乡兵约 乡兵约,是乡约的一种,前文所述的专门抵御倭寇、鞑靼、“盗贼”的乡约,性质即多类此,它源于历史上的结寨自保武装,也是近代团练的雏形。不过,明确提出乡兵约这个概念的,似是明末泾阳人王徵。崇祯二年正月,王徵著成《乡兵约》,号召“凡我同乡地方居民人等,听我誓约,目下岁饥盗起,人心易至忙乱,却不商量一个拿盗贼保护身家性命的好方法,只要听信小人故意摇惑宣传的虚声,先自家慌作一团,把些妇女、衣物、粮食、头畜乱行迁移躲避……今誓约陈说款项,大家照款同心协力,鼓起锐气,实实的整顿备办操练一番。一遇贼来,大家都要仍前齐心奋勇杀贼,以为诸乡之助”[38]。按照王徵的设想,乡兵约分为约束、训练、劝富、谕贫四个部分,凡乡村约在五七里之内,可以联络为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约束,每村各自择立一总,其兵至五百,立大总保一人,战阵勇敢者予以重赏,无功或脱逃者记册受辱。故此可知,乡兵约与历史上的一般的结寨自保组织形式又不尽相同。
(四)会约 明代的会约,形式、种类很多,不仅前文所述由讲学会、文人结社而建立的士约,属于会约的范畴,而且一些其他的民间结会、善会、游戏怡老之会等,不仅多有自己的会约,而且不同程度地受乡约影响的也不为少见。
尽管明代的会约是五花八门,各有旨趣,其要却都在约束内部成员,使组织更具凝聚力,并且,追随乡约遗规,强调内部团结,互相规劝,互相帮助,去做记恶赏罚工作的屡屡可见。例如,桃堌居民为里社之会,以做老实人相砥砺,称老实会约,其宗旨在于“夫存心老实则心有余闲,持身老实则身有余乐,治家老实则家有余财,处人老实则人有余爱,于事老实则事有余稔,是故五谷必老实而后可食,材才必老实而后可用。是会也崇真尚朴,务质守廉,以此而居乡则情厚,以此奉祀则鬼神享”[39]。是知其意也在化导乡俗,讲究礼俗相交,德业相劝。又如倪元璐创设“一命浮图会”,正值明末米价昂贵、天灾未已之时,乡村农民嗷嗷待哺,饿孚于道,鼓励人们布施赈济,每人“认救一命”,以“为此功德,胜于浮图”相诱[40],这又是借释教佛图之说,行儒家赈济、互助之实,弥补社仓之不足,患难相恤也。再如市井负贩之人孙节等结成的“孝和会”,其目的也是为了发扬一种互助精神,解决“老亲之后事”,此后“惟老亲之后事忧,相与会钱以待其费,计一岁所积若何。亲先终者,先给,不足,则尽数给,彼此无论也。且一家丧,一会为衰奔走,当孝子半”[41],又在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之间。
四、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忧
对于明代乡约的推行,时人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褒之者,称“此二帝三王之遗制,虽圣人复起,执众齐物,舍是无术矣”,“乡甲之行,有十利而无一害”,可谓推崇备至。贬之者又“以为愚阔,腐儒行之,多增烦扰”。
其实,事物的发展总是相对的,一法立,则一弊生,一物生则一弊存,问题的关键,在于此法此物是否顺应了历史的发展,符合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是一个不断地兴利除弊的过程。明代乡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固然有不少流弊,但其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事实。客观地评价应该是一分为二。综合明代各地所举行的各类乡约,大体上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过一些积极作用。
首先就是美俗息讼、安民弭盗,这是乡约的宗旨,也是明代乡约能兴盛一时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仇氏兄弟举乡于雄山,约众“户崇礼让,人识廉耻,风俗为之大变”,“讼因以息,渐且乡无盗贼僧道之迹,户绝奸慝淫乐之事”。吕坤倡乡约于解州,“天下望而效之,盖有身不恨逮者”,几及二年,解州“讼争既鲜,盗亦颇戢,耆寿修行,小子有造”。在河东运城,举约之前“民故健讼”,而“今日相观而善,耻讼改行”,程文德举乡约于安福,“礼耆彦而任之,盗息讼简,我安福怀之不能谖”。其次是弥补官治之不足。乡约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即使是官办乡约,也是民众自我管理,乡规民约,人人签字画押,同声起誓,不仅从感情上、心理上易于为民众所接受,而且使乡里纠纷、公益事业能够较为及时、公正地得以处理,运用乡党的舆论,使乡评重于斧铖,达到教化施治的目的,不失为一种具有一定成效的乡治方法。在“大小有司,束手无策,皆谓张望不可理”的南赣,自王守仁“立明约,遂为治境……江右之民为立生祠,岁时祝祭,民心不忘也可见矣”。此外,对于组织民众抗击外来暴力相侵保卫家园,弘扬和造就保耕护林、邻里相助等良好的社会风尚,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同样,明代乡约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乡约提倡的民众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有人称之为民治的胚胎,但是真正的或完整意义上自治,在君主专制社会里是不被允许,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明代乡约所倡行的自治实际上又是一种被扭曲的自治,或可称之为有限自治。随着官府对乡约介入的愈来愈深,乡约的民众自治色彩也日益淡化。作为乡甲约的积极倡导者,吕坤就曾明确指出,“得千良民,不如得一贤守牧”,“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选四乡公正“各给帖文印子,以便行事,先给与耆老衣冠,如果正直无私,督约有功者三年给予冠带”,因而这种以“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的乡甲约,不惟已成为官治的工具,并趋向成为官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明代各地的乡约中,民众自倡自办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官倡民办、官督民办乃至官倡官办,而后者举行与否,便完全听命州县之长,凭其好恶,于是“有司往往以为应上之具,或行之而法不备,或备矣而时不久”,甚至“卒格不行”。一些乡约为恶棍或豪强所控制,藉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在吕坤倡导乡甲约之时,他面对的是山西一些乡约的正副讲史“俱是光棍,地方任其举报,善良而谨畏者,避迹沙潜藏,浮夸而纵恣者,投足争进”。此等乡约焉能不病民扰民?还有一些乡约徒具形式,敷衍塞责,而实效靡征,“所谓百家情愿保结,不过手本开名,该房造册而已”,其武断乡曲,势横州里之人,乡约不敢不保者,“间一有之”,或乡中有善便肯纪录,至于行凶赌博,惯刁巨滑,一乡畏惧者,无人敢举,“使大恶纵横,而纪小恶以塞责,何贵于行乡约哉”,交河县“第乡约虽行,不闻有惩一人旌一人者”,泗州“所谓约长者,因缘为奸,浸失初意,即有按行故事者,亦不过徒咨口耳,以饰观听”,如是而欲化民成俗难矣!至于视乡约为“用贱以治贱耳”,使执“勾稽之役”,而使约众沦为力役也在在有之。陆世仪就有这样的遭遇,他是乡约的积极倡导者,本希望约正的选用,定要“誓于神,诏于众,隆其礼貌,优其廪给,委之心膂而用之”,然而他家乡实际推行的做法,则使他有切肤的畏惧,想方设法地要逃避充任约正之职,如此乡约,又能对其作何指望呢?此外,乡约聚会时的繁文缛节、陈规套式,易于使约众生厌;与会之资对贫寒之家不失为一种新的负担而难以承受。
总而言之,明代乡约的推行,可谓利弊共存,就乡约本身所具有的潜质而言,积极向上的一面应是主流,其主张修身齐家,和睦邻里,共赴公益,共御外侮,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时人吕坤尝云,乡约之法“但实行则事理民安,虚行则事繁民扰,不行则事废民恣”,又云“有司视为常套,谈者反唇。闾巷苦其骚烦,闻之疾首,非法之不良,民之难令,则行法者为法之疾也”[42],此言不无一定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不惟清代乡约依然盛行,进入近代以后,倡行乡约的仍不乏其人,梁漱溟先生理想中的乡村社会组织,乡村下级机构,便是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乡约之法还传入了朝鲜,可见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当然,在明朝这样一个君主专制、吏治腐败、村社动荡的社会里,将乡约的成败,完全寄于对贤守善令的期盼,或早或迟都势必是要落空的,官办乡约如此,受制于官的民办乡约同样也是如此,故此明代乡约实际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种种流弊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百姓之不幸,也是乡约之不幸。
乡约的倡行,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滥觞于程朱理学倡明的宋代,大张于阳明心学昌盛的明中后期,与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乡约的发展是朱明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用地方乡坤与宗族的势力,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巩固政权基础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以从自治标榜的明代乡约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注释:
[1]参阅拙文《明代乡约发展的阶段性考查》(原刊于《江西社会科学》93年8期、人大《明清史》93年11期复印),《王守仁的心学思想与南赣乡约的推行》(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94年6期、人大《中国哲学史》95年2期复印)
[2]《明史》卷147,《解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
[3]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页161,山东乡村服务训练处1937年。
[4]铃木博之《明代徽州府の乡约について》《山根教授退休纪念明史论丛》。
[5]朱鸿林《明代中期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韩国《中国学报》1992年。
[6]《明史》卷281,《循吏传》。
[7]王兰荫《明代乡约与民众教育》,《师大月刊》1935年。
[8]章懋《枫山集》卷2,《答罗一峰书》,四库本。
[9]罗洪先《念庵文集》卷6,《纪事》,四库本。
[10]何瑭《柏斋集》卷5,《三晋第一家序》,四库本。
[11]《柏斋集》卷10,《宿州吏目仇公墓志铭》。
[12]何瑭《柏斋集》卷5,《三晋第一家序》,四库本。
[13]邹守益《东廓邹先生遗稿》卷9,《乡约跋》,光绪三十年版。
[14]嘉靖《祁门三四都护林乡约会议约合同》,原件藏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15]朱淛《天马山房遗稿》卷6,《誓禁屠牛乡约》,四库本。
[16]余华瑞《岩镇志草》贞集,《岩镇乡约叙》,清抄本。
[17]《丛书集成初编》第3227册。
[18]余华瑞《岩镇志草》贞集,《岩镇乡约叙》,清抄本。
[19]刘峙《吉安县志》卷1,《大事志》,民国间修。
[20]《古今图书集成·交谊典》卷27、26,中华书局影印本。
[21]焦竑《献征录》卷89,《辰州守程廷策传》,上海书店影印本。
[22]《古今图书集成·交谊典》卷27、26,中华书局影印本。
[23]曹溶《学海类编》第168册。
[24]杨希闵《明王文成守仁公年谱》卷1,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25]黄佐《泰泉乡礼》卷2,《乡约》,四库本。
[26]黄佐《泰泉乡礼》卷2,《乡约》,四库本。
[27]《古今图书集成·交谊典》卷27、26,中华书局影印本。
[28]吕坤《实政录》卷5,《乡甲约》,同治十一年刊本。
[29]陆世仪《辨录前集》,转引自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30]陈宏谋《五种遗规》卷1,同治七年版。
[31]焦竑《献征录》卷89,《辰州守程廷策传》,上海书店影印本。
[32]陈宏谋《五种遗规》卷1,同治七年版。
[33]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页234,山东乡村服务训练处1937年。
[34]王徵《王徵遗著》,页175、70、181,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5]萧良余《稽山会约》,《泾川丛书》第12册。
[36]王徵《王徵遗著》,页175、70、181,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7]邹元标《愿学集》卷4,《龙泉文明会约序》,四库本。
[39]吕坤《去伪斋文集》卷5《老实会约序》;卷3《孝和会序》,清同治光绪间补印本。
[40]倪元璐《鸿宝应本》卷16,《一命浮停兰会疏》,崇祯十五年刊。
[41]吕坤《去伪斋文集》卷5《老实会约序》;卷3《孝和会序》,清同治光绪间补印本。
[42]吕坤《实政录》卷5,《乡甲约》,同治十一年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