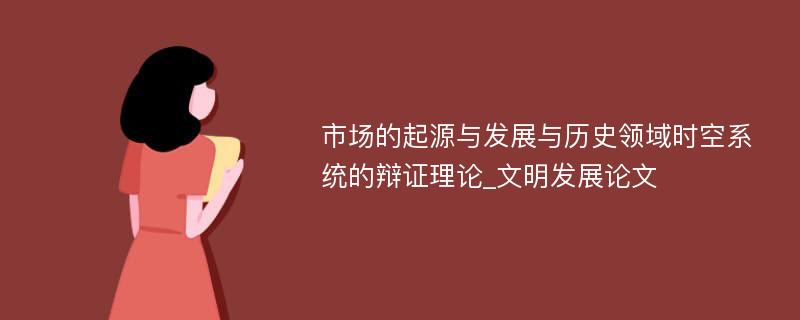
市场的起源、发展与历史场的时空系统辩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时空论文,历史论文,系统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场比之于市场而言更为复杂。历史场是人类历史活动中具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内容丰富的立体空间、多维结构的嵌套时空;市场则是特指具有经济属性的子系统,它嵌套、包容在历史场嵌套结构时空之内。时空嵌套结构的历史场,有如下两种主要的情况:相同的时期具有相同的历史场,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场,这种同步性的时空嵌套是主导性的方面;而非主导性的另一面,即相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场,不相同的时期具有相同的历史场,这是非同步的时空嵌套;这两方面交叉嵌套,形成了复杂的历史场时空嵌套结构(注:引自于拙著《东亚文明系统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8-59页。)。历史场的上述情况已有专著论述过,这里只是有必要提及一下,而本文主要讨论历史场的时空系统辩证论和市场的起源、发展与历史场的关联。
一、历史场扩展的时空系统辩证论
世界历史经济场由分散到整体,既呈现出场所扩大的空间效应,又呈现出越来越加速度的时间效应(注:引自于拙著《东亚文明系统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4-59页。)。所以在论述市场的起源、发展之前,得首先论述历史场扩展的时空系统辩证论,因为经济系统初始敏感值随机放大效应的总趋势,是伴随着具有社会环境属性的历史场的时空效应而体现的。历史场,它不同于只是三维空间的静态场,而是一种既有空间又有时间共四维的动态场,这种历史场态是一种强调发展过程的动态网络。所以“历史场经济学”立论的哲学依据首先是关于历史场的时空系统辩证论。
“系统都有自己一定的规模,都有一定的位置关系、排列方式和空间样态。系统和系统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结构秩序,不论大系统、小系统,其存在形式只有相对性的差别,而没有空间本质的不同。……系统总是运动的,表现为过程,因此也离不开时间形式。”(注:乌杰著《系统辩证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嵌套于历史场的经济系统学就不是一种瞬时横截面式的存在,亦非那种不把场态放在重要地位上而只偏重于所谓经济“内容”的论说。其实,在“历史场经济学”看来,系统经济论说的时空既是其存在的形式,又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内容”,深深地体现着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历史场经济学论说的历史场态、经济机制的开放系统,是一种物流、能流、信息流、特别是其最主要的载体和主体——人流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输出、输入耗散结构的理论。“宇宙中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各种系统结构,无一不是与周围环境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开放系统”;“封闭系统与外界不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不能形成活的有序结构。……实际上,这种系统只是相对存在,绝对的封闭系统是不存在的。”(注:乌杰著《系统辩证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06页。)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社会性最强的动物,而人作为经济系统的主体,乃至经济系统内的原料、工具、产品、市场,等等,都具有自然物质属性和社会化属性的二重性。所以经济系统必然同自然环境场态和社会环境场态进行输出、输入耗散结构式的联动。而经济系统的历史场,就是这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其系统自身共同构变而成的。无论是自然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从古到今丰富多姿的历史场上“演化”的活的有序结构(无序是非主导性的方面,而有序则是其主导性的方面)。因为系统在条件允许时,本身都有一种有序化的自组织机制和趋势,而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有机环境场与系统的输出、输入和框架制约。系统是有机联系的活的整体,它在整体内外的种种流动、活动中保持生命力,并追求自身生命的延续,就是说生存发展力是系统有机整体的目标和动力。小到细胞核、细胞膜,中到器官、腔壁,大到人类及其历史场,皆具有这种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自在和自为的“繁殖”目标,否则该系统就会被它系统取而代之或排挤、异化,甚至解体。
上述系统这样的生命力、扩张力,具体讲就体现为对空间的占有和扩大以及对时间的延续。因为系统对时空上述两个方面的依从,所以人们通常在论述事件时要注重背景和时代;在自然科学方面最伟大的现代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注重的是在低速和光速世界的时空曲率,将时空和速度的关联科学地表现出来。“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是古代道教式的时空和速度关联的想象。然而现代科学实验已证明,极科学的钟在极大的速度(例如光速)下变慢,即一瞬间相当于地球上常速下的更长时间,就是说系统要想在一瞬间占有更长的时间只有加快自身的运动速度,此即可谓之加速度效应。可见时间的长短是相对的,是随速度快慢不同而变化的。系统对空间的占有亦然,常速下很远的地方,而在高速下很快地占有之,即空间感亦是相对的。何谓空间?空间是系统运动的制约框架,而这种制约在系统速度不同的情况下是相对的。低速运动的系统在“同种”空间中受限小,形象地说可谓之“自由驰骋”;而该系统加速后却受原空间限制大而要突破此种空间的界面。可见同种空间的框架作用在系统的不同速度下具有相对性。空间的意义,更重要的在于系统的结构区位作用,如对于相同元素的不同结构而言,空间的区位效应不同:最简单的例子如体积相同时圆球和长方体所占的空间区位不同,空间的占有、利用率不同。金钢石和石墨的硬度等物理性质差异极大,虽然其元素相同,但结构区位不同而导致了空间效应的不同,这是典型的证据。可见空间的相对性是客观的存在,无论是空间感、空间的框架制约、空间的利用率、区位、结构,都是随其变化而致空间效应变化的。其实用性意义在于,改变系统的速度和结构以利用时空的相对性。
综上所述即为:与系统追求时空的占有和扩大相制约的是,具体的系统在一瞬时内,对空间的扩展是有限度的;而在有限的空间内其时间的延续也是有限度的。这样,系统对时空的占有和延展,就表现为追求一定限度内提高对时空的利用效率。即:一定的时间内系统以有效的结构利用空间;而在有限的空间内,争取自身的加速发展。这就是说具体的系统可以充分地利用有限的时空。而无限的时空内则充斥了无限繁多、结构复杂、多样性、生存力转化不停等嵌套、重叠的系统群体。所以在宇宙有限和无限的辩证论中,拙论认为宇宙是由有限的种种宇宙嵌套出无限的宇宙,无限的宇宙并非是一个匀质态或混乱态,而是一种复杂有序的嵌套结构、重叠层次的无穷多系统的整体。
二、世界历史上的市场随历史场的扩展而扩展
“洞穴文明——分散的洞穴及其周围地带→大河文明——如两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多瑙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大域文明——东亚~中亚~欧亚;南亚;地中海周围;加勒比海周围→大洋文明——整个地球→星际文明——地球及其它星球和“太空”……→(新的文明周期)(新的有限宇宙嵌套)。‘历史场’是互相嵌套的:例如,东亚大河文明阶段,东亚是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但同时存在某些未开化的少数民族之洞穴文明场;东亚大域文明阶段,以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为代表,但从隋唐到清代皆属于大域文明阶段,而嵌套着宋朝和明朝等大河文明农业民族为主导的逆向干扰系统的随机‘事件’,其地域就主要是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主了;即使唐、元、清大域文明顺向系统,历史场极宏大,但也还有日本农业文明的小场域嵌套其间(由于日本古代历史发展落后于东亚大陆,日本几乎没有经过大域文明,而直接卷入了大洋文明阶段)。大洋文明阶段日本被卷入大洋文明时,东亚偏远地区还固守某些小范围的后进的文明场带。这是东亚系统历史场的内部嵌套。还存在全球各场域文明阶段不同步的嵌套:如当两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黄河文明等先行演进到大河文明时,世界其它场域还是洞穴文明的历史场,造成大河流域历史场与极分散的洞穴文明历史场的嵌套;同样,当东亚大域文明进入隋唐、蒙元大帝国时,西欧等地还处在众多的小领地、庄园主割据的大河文明阶段;再如,当1492年后欧美较早地进入大洋文明时,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中日还固守着华夏体系的场态……。‘历史场’的嵌套效应,就形成了历史的丰富性、差异性,民族性格开放程度的相异性,意识形态成熟程度的差异性,等等。”(注:引自于拙著《东亚文明系统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8-59页。)这里所引的几百字大体上列出了人类历史场的纵横嵌套结构,而这部几十万字的专著的任务是以此为主线,以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群为启迪,以史实为依据,而论述东亚为典型的世界历史阶段论和东亚为典型的世界未来出路;下面专门论证上述人类历史场的扩大同市场逐步扩展乃至世界经济整体化的关联。
人类历史各个时代转换的加速度效应,是伴随历史场扩大效应的;商品交换的发展程度则是随着市场、商道扩大而扩大的。
任何商品交换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场”,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场”则发展得更为完整和巨大。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组成要素就是市场;要有交换的场所。而“市”的本义就是一种场所属性的词。人们谈市场,往往只偏爱产品,而在理论上将场所的内容空洞化。其实,市场差价是经济活动中人们最重要的追求之一;商品差价中地区差价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即使坐商,也是从他人——例如生产者的场所直接或间接地流动来商品的。如果产品不动场所,只在原场地待着,是实现不了价值而只有使用价值、得不到交换价值。市场的场所效应非常明确而具体、形象地体现出产品场所变换的流动效益;商品流动是经济活动中极重要的效应,否则呆滞积压库中是最不合算的,如积压资金,增加存放和管理费用,等等;即使囤积居奇也是为将要出现的流动效应创造非正常——非常的场所效益。
那么,世界历史上,最能发挥市场、商品交换效应的便是那种巨大的历史场带。本文所说的市场是同历史场相伴随的。历史地域越分散,越阻隔(包括自然阻隔和人为的阻隔,如关卡林立等),越不利于交易商品,越不利于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300万年的人类洞穴文明时期,场所是极其分散的,动物本能式的吃光、扔掉的方式,极低下的生存能力、获取食物的能力,没有剩余品可供交换,不但没有交换价值的意念,亦无交换物品使用价值的意念,所以也无所谓商品和交换场。洞穴文明时期,人类分散在一个一个洞穴及周围百里左右地带(注:参见前揭《东亚文明系统论》,“第二章东亚洞穴文明系统论”,第61-65页。),这种“历史场”,并没有市场相伴随。到了洞穴文明晚期和大河文明早期二者共同构成的交叉过渡期,至今1万年到几千年前,人类社会生产第一次大分工,出现了农牧业的分工;后来出现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也从农牧业中分工出来。有了分工才有了交换,产品的交换场所即成为商品市场。在东亚,大河文明5000年左右的期间(注:参见前揭《东亚文明系统论》,“第二章东亚洞穴文明系统论”,第54-55页。),农业文明系统和游牧文明系统,及其各自内部专门的手工业生产者,即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者之间、管理者之间,除了供系统内部的直接消耗的产品外,其余的部分产品就可进行交换。“西周的商贾和当时的百工一样,是隶属于奴隶主贵族的,所以说‘工商食官’。他们主要是替贵族经营……。由于商品交换日繁,在都市中出现了市场。奴隶主国家设立了专门的职官来管理市场的交易……,‘质人’就是管理市场的经济人,由他制发买卖的契券。”(注: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6-257页。)人类进入大河文明时期后,商品交换的市场伴随着历史场的扩大而扩大,是洞穴文明晚期分散的历史场无法比拟的。例如,古希腊地中海上的贸易,黄河、长江文明历史场通向其它文明系统的历史场之间的“丝绸之路”,商品交换从规模到活动频率都是相当大的。东亚大河文明期间,以农业系统为主导,游牧系统竞争、协同,二者边境贸易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例如长城左右的“互市”贸易,就具有了农牧两个文明系统之间的生存、扩展、争战、和亲、南下中原、北上经略等错纵复杂的局面,历史场的争夺、协从“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画面:例如为了历史场的存在和扩展的需要,导致了汉匈之间长期的竞争和协从,甚至出现了匈奴西迁驱动西罗马帝国境内外“蛮* 入侵”,伴随奴隶起义,而终于使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所谓的“中世纪”“黑暗时代”来临。这种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之源就在东亚的长城上下、蒙古高原的阴山南北。而世界史上著明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就出于汉族等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即农业文明主导系统和游牧主导系统之间的掠夺和交换人、财、物的需要,较大的交换场带和较大的历史场相伴随,导致了内政、外交、经济和军事活动的活跃。更古老的大河文明如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同多瑙河、地中海文明之间,或先或后演化出更为错纵复杂的“历史场”竞争、协从画面,除了直接的政治、军事需要外,根本的原因是生存发展的需要,有些则是直接地争夺商业利益之需要,争夺市场和扩大历史场的需要溶合为一。例如:“吴尔第三王朝的国王们利用全部统一起来的美索布达米亚底大量经济资源进行坚决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全部西亚细亚树立强大的苏美尔-阿卡德王国的领导权。在国王淑利吉(公元前2100-2042年)当政的时期这一政策被发挥到最高限度,他曾九次出征……。”(注:〔苏〕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83页。)这是人类最早进入大河文明时期的两河流域,大规模地扩展历史场的其中一例。后来,游牧部落集团“希克索斯人”从亚细亚侵入埃及中王国,在埃及统治了100多年(公元前18世纪末到公元前1580年),这是游牧文明主导系统与尼罗河农业文明主导系统的一次历史场争夺战,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低得多的游牧集团掠夺埃及的人、财、物。在埃及新王国时期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对于原料、奴隶的经常需求,以及进一步发展广泛的对内贸易的必要,“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对内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埃及商人通过叙利亚运回从更遥远的国家(喜特国、爱琴海诸岛和美索不达米亚)转运来的大量商品。”(注:〔苏〕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266页。)埃及的商队在陆上、海上“远征”。“拉姆捷斯二世(公元前1317-1251年)的战争 谢提一世的继承者拉姆捷斯二世以更广泛得多的规模来推行侵略政策。……为了使埃及重新取得在巴勒斯坦、腓尼基和叙利亚的统治地位,拉姆捷斯二世就必须摧毁喜特人在这些地方的主要军事力量。”(注:〔苏〕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291页。)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王国
的形成,同商业有密切的关系:“商队商道从巴勒斯坦向南,通过培特拉而到西乃半岛、阿拉伯和红海沿岸。向北的商道通往叙利亚内地商业大城市,特别是大马色;以色人在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商业街。”(注:〔苏〕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444页。)以色列王国著名的国王大卫当政时期的“著名的事件是占领古迦南城市耶路撒冷”(注:〔苏〕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447页。),并将其变为国家的首都和宗教中心。现今分散世界各地以经商著称的犹太人,同古代的历史场——两河流域文明的商业场道密切相关。“经营海上贸易是迦太基人致富之源。……前3世纪开始与罗马(已统一意大利)争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权,从而导致布匿战争(前264—前146)”(注:靳文翰等主编《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页。),这个非洲北部古国为争夺“市场”通道在历史场上存在过400多年。
古代世界争夺历史场可与匈奴西迁比的大事件,要数马其顿亚历山大之出征印度了(公元前327—前323年)。此前,印度各区成了波斯的“大流士一世想发展对外贸易……波斯王的广泛的侵略政策……印度各区成了波斯最富饶的各郡。印度行省向波斯王纳特别大的贡献(360塔兰特金砂)”(注:〔苏〕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669页。)。亚历山大帝抱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公元前334年始,在对波斯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以后,于公元前327年开始率军征服印度。他“在东起印度河、中亚细亚至巴尔干半岛,南自尼罗河第一瀑布,北大多瑙河下游南岸的广袤领域内,建立‘亚历山大帝国’。”(注:靳文翰等主编《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但是由于这时期世界史的总态势,是大河文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历史场为主导系统整体态势,亚历山大帝国这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如此长宽的历史场只是一种个别的随机事件,正像横跨东亚直到欧洲的匈奴西迁没有建立超越大河文明历史场一样,短命的亚历山大帝国随着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的病殁而迅即瓦解。但它既然作为大地域历史场的个别随机事件存在过,就对历史场效应中的“市场”等打上了随机烙印,例如它使最西边的多瑙河文明与东边印度河文明的文化和商道拉近了一下——“在发掘坦叉始罗城的时候,曾发现一种特殊的希腊印度风格的雕刻和钱币”(注:〔苏〕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672页。)。
虽然大河文明主导系统的内地之间有更多而丰富的内容,但农业系统和游牧系统之间长期的相互竞争、协同,更具有历史的趋向确定性,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以后,人类历史实现了更大的地域文明。《东亚文明系统论》论述道:“在游牧文明系统主导的北方‘组织严密’等,与南方‘腐败’(指南宋朝廷——本文作者)的农业文明主导系统之间,涨落‘差值’放大的效应下,如蒙古帝国游牧系统这个吸引子,‘吸水泵’就‘吸引’了整个东亚文明系统为一个内部稳定的系统,并利用中亚和东欧的‘差值’,将东亚文明系统效应放大到整个中西‘通道’疆域,相当广大的地域。因为相对于蒙古族主导的东亚系统之‘涨势’,中亚、东欧这时正好是‘落势’,或者如花剌子模王朝等统治者软弱无能,等等。这样东西方之间的涨落差迅速地大规模地放大,各自系统自身的涨落效应在宏观上放大。如蒙古族主导的严密组织系统及其古代快速部队骑兵的威势,还有农牧互补的优势(这时是游牧系统主导的时代——大域文明时代,排斥了农业文明系统的独立、分离、偏安及苟延残喘倾向),东亚文明的优势大长,而中亚、东欧的上述劣势导致其大‘消’,于是这种差值效应放大到宏观上典型的蒙元帝国,这一大域文明的代表类型出现”(注:前揭《东亚文明系统论》,第41页。)。此前和此后的唐帝国和清帝国,也在种种涨落效应差值随机放大中,实现了大域文明历史场的效应,支配了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整个东亚地域。在大河文明阶段以后的特定时空中,大域文明在历史随机事件增多的基础上显示了世界历史的新的确定性。所以与隋唐、蒙元、清朝支配的东亚历史场,或前或后、或同时地嵌套的大地域文明,有如地中海地域文明(如西、东罗马帝国、起始于红海地域的波斯帝国等)、加勒比海地域文明(如印加帝国等)、红海地域文明(如起始于此的公元7-13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印度印洋文明,等等。这些大地域文明,比起大河文明阶段的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黄河长江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多瑙河文明、密西西比河文明、亚马孙河文明来,历史场效应更大,其中的“市场”交换通道更为长远宽广。如蒙元帝国时,以蒙古高原和林为中心的亚欧大陆商路和以东南沿海为终点的海上贸易颇为发达,皆超过了大河文明阶段开劈的河西走廊至中亚以西的“丝绸之路”之商道长远和范围广大。所以,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即使大规模地屠城(敌方拒不投降时的少数事件)时,也特别注意保存
工匠、商人;所以对色目人的地位划为第二等(蒙、色、汉、南蛮,人分四等),除了比南蛮来说色目人归顺早些,但不见得比北方的汉人归顺都早,的确因为色目商人对缺乏商品的游牧民族来说非常吸引人,当然商队的有意无意的情报亦直接地有用。一个如此巨大的地域在共同的最高统治者支配之下,无疑便于商品流动,更有利于秩序的保障、驿站的建立。中古大域文明阶段的市场,虽然不及后来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外市场的统一性和紧密程度,但比之于大域文明之前的大河文明时期的市场来发展得多了。再如,东罗马帝国是存在了将近11个世纪的中古帝国,是地中海大域文明稳定的历史场,公元5-6世纪时囊括了欧、亚、非相当大的版图。所以地中海文明此阶段的商业更为发达:“它的很多部门都是皇帝专利,政府大量任人承包这些专利。私营商业也很发达。……在东方与印度、中国、塔普罗巴那(锡兰)岛;在西方与意大利、西班牙、高卢。叙利亚商人从东方运来香料、香水、宝石、生丝、皮革以及奴隶。……此外埃及商人还与非洲若干地区……进行广泛的贸易。”(注: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83页。)东罗马帝国的大地域历史场,造成了巨大的境内外市场,特别是造成了许多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如君士坦丁堡不但是帝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工商业中心,是“全世界船只云集”的市场。其它的境内城市如安提阿、亚力山大、以弗所、士麦那、巴特惹、底比斯、哥林基、帖撤罗尼迦,等等。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比西罗马帝国时期更密切,大庄园没有变为孤独自在的经济机体,大地主和奴隶主被卷入帝国的商业流通。(注: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第84页。)《中世纪史》的这些资料极为重要,因为它提醒人们,不要对中古时代的庄园过于抱有偏见,似乎庄园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完全的自然经济;这种轻视市场交换的中古史学观、经济学观是与史实有出入的。中古史上著明的十字军远征,从1096年到1270年,欧洲人对东方进行9次殖民、侵略的军事活动,涉及的地域广泛(从西欧、中欧各国直到地中海周围的许多地区),参与者也极其广泛,从教皇、国王、骑士,到自发进来的大批穷人,甚至约有3万童子军被欺骗、胁迫进来,尽管各自的直接动机不同,但财富却是一种最诱人的要素,特别是威尼斯“变十字军的愚蠢行为为商业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5卷,第194页。转引自* 寰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页(没注出处)和前揭《中世纪史》第1卷第327页。)。十字军远征导致了广泛的严重后果,领土目的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后来对欧洲文艺复兴发生过重要作用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地中海商业统治者的影响得以继续和发展。可见争夺历史场的过程与争夺商业通道、市场对人类社会进程的相关度之大。
蒙古帝国再强大,也受到了大洋的阻隔,忽必烈两征日本被海风吹翻大船,后以失败而还,第3次征日本未出征即罢。中国人、欧洲人,即使早已个别地域群体地到了美洲,但大洋阻隔,在大河文明、大域文明阶段,美洲同欧亚大陆连片的人类主要活动场所比起来,密西西比河文明也罢,加勒比海地域文明也罢,毕竟是孤立的文明。所以人类发展到15世纪时,出现了征服大洋的壮举,郑和七次下西洋,虽然因其早了一些,以及因明朝和北元的竞争,此种壮举而以随机事件作罢,但毕竟随之而来的是哥伦布、麦哲伦的征服大洋;然后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美等西洋列强打开印、中、日门户,于是地球文明最终地连成一片。当今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洋黄种人更具有大洋文明的典型性,经济发展更快,如日本岛国大油轮为代表具有便宜的油价、运输费和巨大的吞吐量;到21世纪,中日联合起来的黄种人东亚文明,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信息广域网为条件的大中华文明圈,对世界的作用更大,黄种人在地球连成一片的大洋文明阶段,将是人数最多的地球主体;然而主体不是主宰,西方在大洋文明前期的霸道主义,早被孙中山批驳,是大洋文明的初级形态;而以王道文化为精神的东亚文明早被孙中山论证了优越性,反对侵略,特别反对武力、征服、战争,符合当今和平与发展为主的世界大趋势,因为它更适合大洋文明时代精神:大洋交通方便之利将地球连成一片,方便的市场,交换在更大范围和规模进行;东亚王道文化适应大洋文明时代,更重视仁爱、文明交易,更反对不等价交换;更反对超经济掠夺。所以以东亚系统黄种人为主体在下个世纪,即21世纪这大洋文明顶峰——大洋文明晚期,是地球文明成熟到异化阶段进入星际文明的最适合的载体。
可见,五大文明的前四个阶段,发展到当今时代,世界历史越整体化,市场越来越大。从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至今,大洋文明的绝大部分时代内容就是打开各国门户,打破闭关政策,倾销商品;今天世界各国“入关”还是以市场为主要的经济视角,所以随人类历史场效应越扩大而市场经济越发展。
从经济的产业内容也可看出,五大文明对市场要求越来越强烈:洞穴文明采集狩猎,交换极不发达,分散群体自采自食,无多余品可交换;大河文明时,比以前市场发达,中国古代出现了“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肆即市场(店铺式的市场),可见之经常(久入)入肆交易,习惯其市场风味。然而大河文明规模之大主要是农牧产品交易,手工业比起下阶段来规模不大,大河农业文明时期,自然经济还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耗为主(广义的自己,如同一个庄园内的自我消费包括庄园主的管理和庄丁护卫、庄户人家的生产活动);到人类大域文明这第三阶段,农牧业在竞争中更频繁地实现着流动,包括民族流动,物质流动,精神文化流动;这时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方,造纸便于经济文化情报印刷流传等,火药传出变成了快枪快炮,指南针便于轮船航海,于是人类在15世纪开始了大规模征服大洋的活动。在大洋文明阶段,开始是商业为主,而后工业为主业,现在是高科技产品为主,物质生产越发达越需大市场。
1492年到21世纪是大洋文明时代,地球文明连成一片;商品经济的场所遍及整个地球,终归要发展成为全世界整体化的市场经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受市场经济的机制制约。大洋文明阶段,地球上对统一的世界历史场和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确立,最大的阻隔大洋不但被彻底扫清了,而且变为全球整个历史场和世界上统一市场最为有利的要素,海洋的运输量之大和之廉价是最为显著的。至于1492年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的航海冒险、殖民活动、贩卖黑奴,对世界市场的追求及其影响,这里无需旁征博引,因为对这些众所周知的史实及其意义,马克思等世界级的大理论家、经济学家、史学家、政治家,等等,都作了大量的论证,都对地球这个圆通的历史场之打开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之关系作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各个学派和政治派别得出的结论不同,对大洋文明历史场的含义、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态度完全相反。有人把世界近现代、当代史的欧美文明称为蓝色(海洋色、蓝眼)文明,是赞颂欧化美化的文明观。而拙著《东亚系统文明论》则论证了大洋文明,是前半期以大西洋两岸的欧美为主导,从当代直到21世纪的大洋文明后半期则是以中日等黄种人为主导的仁爱文明观:在“地球村”内加强国际通婚相亲相爱(人流);全球范围内加强“儒商”式的市场经济(物流);加强旅游、访问、留学等各种人的活动(人流与信息流);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环境保护);今后更要反对侵略、战争,像孙中山所说的东亚“王道”那样,不同于西方的“霸道”。(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7页。)主导不等于主宰,中日等黄种人新的仁爱观,是因黄种人为全球文明人数众多的载体,它的人力、加上财力、资源、科技、经济增长活力,谋求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等黄种人作为人类众多的文明载体,因地缘近而勾通起来今后相对容易些(起码是运输航程短,节省时间和价钱),但不排它,不封闭;建立全世界的开放市场,打破了人为的贸易壁垒(因其不符合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在当代及其后的总趋向)。这就涉及到理论上如何看待当前世界上到处出现的地域性经济组织,及其同世界经济整体化的关系。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阐明。不过可以概括地指出,历史场、市场的总体进程是: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化,世界市场从分散化到整体化* 二者是总体上同步,其进程是曲折地、随机地确定的。现代世界上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分别结成了大的集团,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重新瓜分殖民地造成的。当代世界的地域性经济集团,如果出现某种随机诱因,有可能变成集团式的斗争,甚至战争;但是正像两次大战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后,人类社会历史场在整体化的进程中迈出了更好的步伐,世界市场关联度更大了,总进程的整体化趋向是确定的。上述地域性经济组织,如果处理得当(例如加强对话等),随机诱因如果有利于总趋向,则不但可以避免战争,而且所有的地域性经济组织可以作为世界市场整体的结构层次和要素,加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的经济组织的改进和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再加上联合国的巨大组织和作用的进一步完善、增强,大洋文明后半期的人类历史场的整体优化会更明显地体现出来。上述地域性经济组织和世界经济组织,进一步在场所和功能上结构复杂有序化,从而自组织和他组织成为整体化的全球市场经济。局部战争虽然不少,但世界大战的机率不如和平与发展的机率高。这种机率的高低确认,不仅因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而且还因为当今和下个世纪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机遇:比如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资源减少;新的疾病更加厉害;新的毒品和精神污染更加可怕和广泛(世界性的电脑网络也可“钻入”大罪犯);官场腐败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穷国和富国、民主和专制国家,经济犯罪、权钱交易数额皆有“天文数字”出现,等等。需要全人类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决果断合理的具体举措,才能克服共同面临的种种危机。而高科技手段和产品的合理、有效的运用,已出现了新的征兆:人类在大洋文明阶段以后,地球文明将以整体的态势出现在星际文明,人类的经济活动将随科学的更加发达、有序(如解决太空污染等),共同开发星际,球外活动及其场态与地球历史场态共同组成星际文明更大的历史场态。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差异和冲突的世界上,但我们又的确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虽然说民族国家及其自利性将长期存在,但世界各国都正面对着一个独自难以解决的共同难题,都面临着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发展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需要一种秩序,使各国能安全生存并发展。各种文明的冲突时时存在,但不会象亨廷顿所断言的那样,会最终危及整个人类文明。不然,世界经济新秩序又从何谈起呢?”(注:乌杰主编《系统科学理论与应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系统科学理论与应用》,这部102万字的巨著,用现代系统科学群的新理论探讨了包括世界经济新秩序在内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甚至宇观问题;本文则以历史场发展为主线的世界文明系统论,试着探讨世界市场的产生、发展的时空系统辩证进程。本文加入这一思潮涌动的学术争鸣,对十多年来经常神交和面对面的多次探讨而启迪过我的众多学者谨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