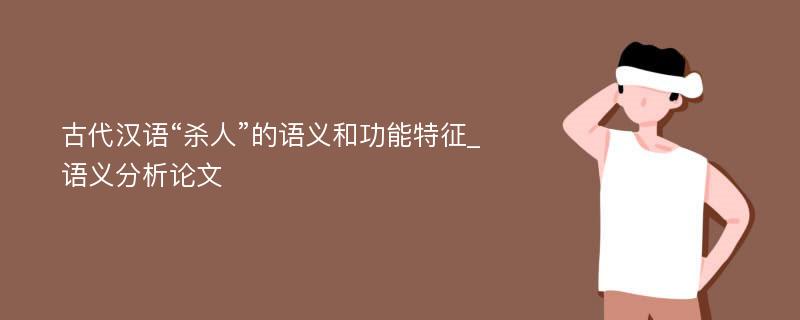
古汉语中“杀”的语义特征和功能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语义论文,功能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杀”的语义特征
1.0
郭锡良等《古代汉语(上)》文选《孙膑》“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一句下注:“刭,用刀割脖子。《史记·魏世家》说庞涓是被杀的。”(204页)查《史记》,《魏世家》有“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军遂大破。”(1864)(注:文中引《史记》据中华书局(1959)标点本,只标页码。)《田敬仲完世家》有“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1894)《孙子吴起列传》中有上例。《商君列传》有“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2232)《孟尝君列传》有“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2351)为什么多处说庞涓是被杀的,而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庞涓“乃自刭”呢?这涉及到对“杀”的释义问题。
1.1 “杀”这个词甲骨文中是否使用, 古文字学界尚有争论(见《甲骨文字释林》“崇”字条),但从先秦两汉汉语看,“杀”的基本义是“致死”,其语义特征可描写为“+采用某种工具或手段;+致死;+有生命物”,也可以描写为“+工具/手段;+动作;+结果;+受事对象”。“杀”作为一个词在使用中其语义特征的典型表现是:工具/手段——兵器;动作——刺、击等;结果——生命结束;受事对象——人/动物。但是我们知道,词的意义是抽象的,概括的,“杀”在使用中其抽象、概括义就是“导致对象生命结束”,并不只是其语义特征的典型表现,《史记》中的“杀”尤能说明这一点。
庞涓“自刭”与(齐或田忌、孙膑)杀庞涓,二者并不矛盾。庞涓之所以“自刭”,是因为他的军队被齐或田忌、孙膑打败,自知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自刭也好,被杀也好,都是庞涓的“生命结束”,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是齐或田忌、孙膑的行为。
1.2 古籍中同时记载一个人自杀和别人杀之的情况很多, 仅《史记》中就有十数例。如:
1 项燕遂自杀。(234)
秦将王翦破我军於蕲,而杀将军项燕。(1737)(王翦)杀项燕。(2565)王翦杀其将军项燕。(2341)
2 (纣)自燔於火而死。(124)
元王曰:“……纣不胜,败而还走,围之象郎,自杀宣室,身死不葬……”(3234)
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1515)殷纣之国,……武王杀之。(2167)
3 二世自杀。(274)
赵高杀二世,立子婴。(221 )子婴与其二子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275)
及赵高已杀二世。(361)居无何,二世杀死。(3203)
4 项王乃自刎而死。(336)
汉五年,既杀项羽,……(2015)
5 (吴王夫差)遂自刭死。(1475)
(吴王)遂自杀。(1745)
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2181)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2200)
6 崔杼妇自杀,崔杼毋归,亦自杀。(1502)
初,庆封已杀崔杼。(1503)
7 申生自杀於新城。(1646)
申生乃雉经於新城之庙。(《国语·晋语二》)是岁,晋杀太子申生。(1489)
是岁,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1578)
人或告骊姬曰:“二公子怨骊姬谮杀太子。”(1646)
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1656)
骊姬既杀太子申生。(《国语·晋语二》)是以晋骊姬杀太子申生。(《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8 (楚)子玉自杀。(1668)
成王归杀子玉。(1677)
9 (吴王)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1743)
(子胥)乃自刭死。(2180)
句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1743)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2181)
(李斯)仰天而叹曰:“……吴王夫差杀伍子胥……”(2560)
10 (文)种遂自杀。(1747)
大夫文种,……句践终负而杀之。(2423)
11 (武安君白起)遂自杀。(2337)
(应侯范雎)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杀之。(2417)
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2569)
12 (扶苏)自杀。(2551)
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1950)
我们不能根据上面这些材料怀疑司马迁掌握的史实不清楚而前后矛盾,或两说并存。实际上,上举自杀者都是别人的行为促使其自杀的,自杀者的生命结束是别人造成的,虽然不是别人亲手将其杀死。史书中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只要导致甲的死亡有乙起决定作用,并且是乙的主观意图,就可以说“乙杀甲”。如例1 是王翦击败项燕导致项燕自杀;例2、4、5、6与此相类。例3二世自杀是赵高逼迫的, 《李斯列传》中就说“高即因劫令(二世)自杀”(2562)。例8 子玉是楚王令其自杀,例9伍子胥是吴王令其自杀,例10文种是句践令其自杀,例12 扶苏是二世令其自杀。例7申生是骊姬设计陷害他,向晋献公进谗言, 晋献公令其自杀;例11白起是范雎向昭襄王进谗言,昭襄王令其自杀。《韩非子》中有一例在同一段话中说楚成王被杀和自杀,也足以说明古人用“杀”,重点是强调“导致死亡”的结果,而并不强调动作的实施。
13 (楚)商臣作乱,遂攻杀成王。……(成王)遂自杀。(《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1.3 史书中还有甲被杀,既说“乙杀甲”,又说“丙杀甲”, 因为甲被杀既有乙起作用,也有丙起作用。上述庞涓、申生、白起是其例。再如《淮阴侯列传》载韩信与张耳一起攻赵,“斩成安君泜水上”(2616)成安君并不一定是韩信和张耳亲手杀死的,但是韩、张率兵杀死的。同篇记蒯通游说韩信,说常山王(张耳)与成安君(陈馀)初为刎颈之交,后张耳投奔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2624)又说“足下(韩信)……诛成安君”(2625)。义帝怀王,《史记》中多处说项羽杀义帝,《黥布列传》又说“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2599)实际上项羽、黥布都没亲手杀义帝,而是项羽命令黥布等人,黥布又命令手下杀死义帝的。又如《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於桃园”,而“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大史说得不对,大史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公羊传·宣公六年》记此事说:“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实际上是晋灵公欲杀赵盾,赵盾手下经过一番搏杀,赵盾得以逃跑,之后赵盾之昆弟赵穿杀了灵公(又见《史记·晋世家》)。《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其母(晋叔向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成公二年》:“是(指子灵之妻,即夏姬)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即夏征舒),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据载,夏姬是春秋时有名的淫女,但她并不曾杀人,所谓杀三夫,是说子蛮、御叔、巫臣三人皆因娶此淫女而死(注:《史记·陈杞世家》正义引《列女传》云:“陈女夏姬者,陈大夫夏征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所谓杀一君,是指陈灵侯与孔宁、仪行父三人共通於夏姬,夏姬之子夏征舒忍受不了,杀了陈灵侯(《左传·宣公十年》:“公出,(夏征舒)自其厩射而杀之”);所谓杀一子,是指夏征舒杀了陈灵侯一年后,楚庄王以此为名伐陈,“遂入陈,杀夏征舒”(《左传·宣公十一年》)。因为陈灵公、夏征舒被杀都与夏姬有关,所以也可以说是夏姬杀一君一子。又《战国策·魏策四》载“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史记·魏公子列传》既说“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2381),又说“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2382)。
1.4 从以上分析可见,古书中的“杀”, 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某人亲自使用某种工具将别人(或动物)杀死,只要是某人使用某种手段导致别人(或动物)死亡,就可以说某人杀某某。绝大多数常用辞书对“杀”的释义基本上都把握了其语义特征,尤以张永言等《简明古汉语字典》的释义(“使失去生命,弄死”)最为准确。但《汉语大词典》分列“杀戮”和“死,致死”两个义项,似不妥当。
二 “杀”的功能特征
2.1 “杀”的语义特征包括受事对象, 这一点表现在句法功能上就是具有及物性,在句法结构中一般都要带受事宾语。“杀”的及物性表现在句法功能上,就是在句法结构中一般都要带受事宾语。如《史记》中“杀”共使用约1080例,形式上带受事宾语的就有约850例, 只有以下几种情况形式上不带受事宾语:1)在上下文中宾语承前省略;2)“自杀”、“相杀”这种语义上动作受事自足形式;3 )“杀”不是出现在述语位置上。以上三种情况约200例。4)“杀”用於受事主语句,如“周幽王为犬戎所杀”(1566)(比较:“犬戎杀幽王”〔1637〕)“专诸曰:‘王僚可杀也。’”(1464,2517)“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1884)“杀”用於受事主语句约30例,但“简公立四年而杀”这种“反宾为主”句仅4例。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杀”的及物性,是因为我们见到《史记》中出现大量的“N1V杀N2”结构,不少学者认为这种“杀”是V的结果补语,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注:太田辰夫(1958)、梅祖麟(1991)、蒋绍愚(1999)等人已论证两汉以前的“V杀N”中的“杀”不是结果补语。),因为“N1V杀N2”结构中,N2不仅是V的受事宾语,同时也是“杀”的受事宾语。如:
1 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158)
2 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2449)
3 项王烧杀纪信。(326)
4 晋人执杀苌弘。(1364)
5 (李良)遣人追杀王姊道中。(2578)
《史记》还有很多“N1V而杀N2”结构,在这种结构中, 更能看出N2同时兼任V和“杀”的受事宾语。如:
6 使囚病而遗守囚者酒,醉而杀守者。(1508)
7 (大夫文种)功已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2423)
8 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2885)
9 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2193)
我们知道,结果补语在形式和语义上都是不能带受事宾语的,所以太田辰夫(1958)、梅祖麟(1991)都强调判断结果补语必须依据“V1+V2”中的V2是不是自动词。查汉以前古籍,“V杀”和“V而杀”之后都有受事宾语(注:梅祖麟(1991)说在先秦两汉“V 杀”居句末只看到一例:“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汉书·晁错传》)又说“上面整段都是四字句,‘身自射杀’是否属於(丁)型(即“受事者+V杀”型)不容易判断。 ”汉以后也很难见到“V杀”后不带受事宾语的用例。 《世说新语》中有“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假谲》4 )但此例“杀”后显系省略宾语“之”。《贤愚经》中有“宁受绞死,不乐烧杀。”(北魏·慧觉等译,《大正藏》,4,0373a),但此例中“烧”和“杀”都是用於被动意义。),而且受事宾语都是V和“杀”共有的。《史记》之外的例子如:
10 宋万弑闵公於蒙泽,遇仇牧於门,批而杀之。(《左传·庄公十二年》)
11 桓公召而缢杀之。(《公羊传·僖公元年》)
12 公怒,以斗击而杀之。(同,《宣公六年》)
13 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刺而杀之。(《战国策·齐策六》)
14 商臣作乱,遂攻杀成王。(《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15 饮食人以不洁净,天怒,击而杀之。(《论衡·雷虚》)
16 李斯、赵高谗杀太子扶苏。(同,《变动》)
即使“杀”跟在一个VO(动词带受事宾语)后,“杀”也要带上受事宾语,虽然这个宾语与前面动词的宾语是同一的。如:
17 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左传·桓公七年》)
18 丁巳,其夫攻子明,杀之。(同,《襄公二十二年》)
19 楚人执陈行人干征师而杀之。(《春秋经·昭公八年》)
20 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谷梁传·昭公十一年》)
21 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1639)
22 六年春,三郤谗伯宗,杀之。(1680)
23 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1880)
24 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2298)
25 (李)广曰:“吾为陇西太守,羌常反,吾诱而降之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论衡·祸虚》)
26 狄人攻哀公而杀之。(同,《儒增》)
以上各例“杀”的宾语“之”都是复指前面动词所带的受事宾语。“杀”后必须带受事宾语,正是其语义特征包含“受事对象”在句法功能上的表现。如果“杀”后不出现受事宾语,那么一定是用於被动意义,即用於所谓“反宾为主”句。所以像“简公立四年而杀”,在《史记》中不会像现代汉语中“鸡吃了”那样产生歧义(参见詹人凤,1992)。包含“受事对象”是“杀”的语义特征,带受事宾语是“杀”的功能特征。可见一个词的功能特征是与其语义特征分不开的;反过来,词的语义特征也往往会在其功能特征中得到反映。
2.2
“杀”和别的他动词共现於谓语位置并共同带一个受事宾语时,“杀”位於别的他动词之前的用例(N1杀VN2或N1杀而VN2)很少,位於别的他动词之后的(N1V杀N2或N1杀而VN2)却很多,在《史记》中,前者只有10余例,如:
27 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1913,裴駰集解引韦昭曰:“防风氏违命后至,故禹杀之。陈尸为戮。”)
28 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3228)
29 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3228)
30 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2906)
后者多达近200例,如前举例1—5。再如:
31 项王迁杀义帝。(2695)
32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315)
33 (高祖)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379)
34 征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1579)
35 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1624)
36 (梁王)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2085)
通过分析“杀VO”与“V杀O”,我们发现,这种结构严格地遵循“时间顺序”原则(参见戴浩一,1988)。“杀VO”中,上举例27—29分别为先杀后戮,先杀后取,先杀后用;例30“杀略”是并列的,“杀略千余人”是说杀死和虏略共千余人,“杀”和“略”没有时间先后顺序。《史记》中还有数例“所杀伤”、“所杀虏”(没有“杀伤O”、 “杀虏O”),这种“杀”和V也是并列关系,也不涉及时间顺序的问题。“V杀O”中,从时间顺序来讲,一定是先V后杀。 过去许多学者在谈到这类结构时,往往说两个动词是并列的(见王力,1958;梅祖麟,1991;蒋绍愚,1999)或称之为“等立的复合动词”(太田辰夫,1958:196),我们认为这些说法还不太确切。准确地说, 应是两个动词的连用,这种连用遵循时间顺序原则,从语义结构关系看应属连贯关系,我们称之为“动词连用”(注:先秦两汉,特别是两汉语料中,除“V 杀O”外,还有大量的“动词连用”式“V1V2O”,它们同样遵循时间顺序原则,笔者另有《论先秦两汉的“连动共宾”结构》一文专门讨论。)。如上举例31—36,分别为先迁后杀,先诛(责问,问罪)后杀,先追后杀,先射后杀,先击后杀,先刺后杀。这些用例可以作如下变换:
迁杀义帝→迁义帝而杀之→迁而杀之/义帝
诛杀曹无伤→诛曹无伤而杀之→诛而杀之/曹无伤
追杀项羽→追项羽而杀之→追而杀之/项羽
射杀灵公→射灵公而杀之→射而杀之/灵公
击杀南宫牛→击南宫牛而杀之→击而杀之/南宫牛
刺杀袁盎……→刺袁盎……而杀之→刺而杀之/袁盎
为什么与别的他动词连用时,“杀”多位于别的他动词之后?上面我们用时间顺序原则作了回答。但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根据时间顺序原则,“杀”大量用於别的他动词之后而很少用於别的他动词之前呢?原来这与“杀”的“终结”语义特征有关。
所谓“终结”语义特征,在这里是指一些及物动词的语义得到实现时表现出的如下特点:在施事实施动词表示的动作之后,受事就会处於一种既成状态,这种状态伴随动作的终结而产生。比照郭锐(1993)对现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的分析,这类动词的“续段”很弱,“终点”很强,所以其所表示的动作很难持续(注:如“伤、断、破、绝、灭”等。)。同时,动词所表示的动作实施后,施事对受事的“处置”往往就告结束,不能或很难或无须施以有关的后续动作行为。
行为动词都包含一个过程(参见郭锐,1993),谓语位置上的两个行为动词连贯出现,就构成两个过程相加的“连续过程”。汉以前语料中的“V杀O”都无例外地是表示“连续过程”,前一个动词表示“连续过程”的开始,并具有持续性,“杀”表示连续过程的延续和终结。
有些学者把“V杀O”中的“杀”看成结果补语,可能是因为“杀”具有“终结”语义特征和“杀”在“V杀O”中表示连续过程的终结。但是第一,如前所述,O不仅是V的受事宾语,同时也是“杀”的受事宾语;第二,“V杀O”可以变换为“VO而杀之”和“V而杀O(之)”,这说明“杀”与前面的V并没有紧密结合, 而是与其后的受事宾语不可分开;第三,虽然在“V杀O”中“杀”都是表示连续过程的终结,但“杀”与V的关系从语义上分析有两种情况:1)“杀”只是紧接着V 后发生的事件,并不是V导致的结果,如上举例31—33,“杀”并不是“迁”、 “诛”、“追”的结果;2)“杀”是紧接着V后发生的事件,是整个连续过程的终结,同时“杀”也是V导致的结果, 并且也是施动者的最终目的。但即使是后一种情况,也不能把“杀”看作V的结果补语, 因为V导致的结果不是“杀”,而是“杀O”,O仍然是“杀”的受事宾语。 蒋绍愚(1999)曾论证《史记》中出现在“V1V2O”的V2位置的16 个动词(包括“杀”和用作使动的形容词)都不是结果补语,是非常正确的。
《史记》中不仅有“V杀O”,还有“V1V2杀O”、“V1V2V3杀O”如:
37 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济。(2590)
38 田荣怒,追击杀齐王市於即墨。(2645)
39 还,梁刺客后曹辈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2745)
40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1482)
41 汉击破,杀辟光。(2010)
42 宛贵人……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3174)
43 定国使谒者以他法劾捕格杀郢人以灭口。(1997)
三个动词、四个动词连用,就构成一个更大的连续过程,“杀”处於连用中的最后位置,表示整个连续过程的终结。如上举例37是“先击后破,破而后杀”的连续过程,至“杀”而整个过程终结,例43是“先劾后捕,捕而后格,格而后杀”,至“杀”而整个过程终结。余例类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在“V杀O”或“V1V2杀O”、 “V1V2V3杀O”中,“杀”和前面的动词共现是严格地遵循时间顺序原则的,“杀”和前面动词之间的次序不能变更,这说明“杀”和前面的动词是连贯关系,不是并列关系。(2)“杀”进入“动词连用”有“杀VO”和“V杀O”两种,“杀VO”极少,而“V杀O”非常多;在三个、四个动词连用时,“杀”只出现在第三或第四的位置,这是因为“杀”具有“终结”语义特征(注:先秦两汉有一批他动词(单语素)具有“终结”语义特征,如“破、败、灭、伤”等。这些他动词也可以位於别的他动词之后表示“连续过程”的终结,如“李牧击破秦军”(2451),“楚伐败齐师”(2351)“(晋)袭灭虞”(1647)“越王句践射伤吴王”(1717)等。这些词都和“杀”一样,不能看成结果补语。他动词的终结语义特征具有相对性,如《史记》中既有“伐败”、“击破”,又有“败杀”、“破杀”,在“伐败”、“击破”这样的“连续过程”中,“败”、“破”是连续过程的终结,但在“败杀”、“破杀”这样的连续过程中,“败”、“破”是连续过程的开始和延续,“杀”才是连续过程的终结。这说明,相对於“败”、“破”来说,“杀”的“终结”语义特征更为突出、显著。这类动词在古汉语中究竟有哪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一语义特征在连续过程中往往就表示整个过程的终结,所以“杀”一般都出现在“动词连用”中的最后位置。
三 结语
3.1 古汉语中“杀”的意义既包含动作又包含结果, 有些辞书简单地释为“杀戮”,严格地说是不够准确的。《简明古汉语字典》用动结式“弄死”和致使结构“使……”来释“杀”,就充分突出了“杀”的语义特征。
3.2 词的语义特征与词的功能特征是有密切联系的, 要准确认识一个词的意义,不能脱离对该词的语法功能的分析;要准确认识一个词的功能特征,同样不能脱离对该词的语义特征的分析。
3.3 “杀”除四种情况外,在句子中一定要带受事宾语, 即使是与别的动词连用,也一定要带受事宾语,这一功能特征与“杀”的语义特征包含“受事对象”有关。“杀”和别的动词连用时,一般只能出现在后面的位置,“杀”表示连续过程的终结,这一点与“杀”的“终结”语义特征有关。
3.4 揭示“杀”的“终结”语义特征是很有意义的。 以往学者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一些“V1杀NP”中的“杀”或认为绝对不能看成结果补语(王力,1958;太田辰夫,1958;梅祖麟,1991;蒋绍愚,1999等),或认为肯定是结果补语(注:何乐士(1984)说《左传》中“余掖杀国子”是《左传》中已有结果补语的“铁证”。),原因就出在后者只看重“杀”的“终结”语义特征,忽视了“杀”的动作性和及物性特征。如前所述,先秦两汉的“杀”后面是必须带宾语的,而汉语中,动宾结构绝对不能充当结果补语。先秦两汉的“V杀NP ”中“杀”貌似结果补语,那只是其“终结”语义特征显示的表象,从句法关系和“杀”与V、NP的语义关系看,“V杀”绝对不能分析为述补结构,“V”和“杀”甚至不是直接成分关系。
太田辰夫和梅祖麟都曾试图通过论证“杀”由他动向自动转化来确定动结式的产生时代。为什么“杀”会由他动向自动转化?梅文分析了四种因素。我们认为,这种转化还与动词的“终结”语义特征有很大的关系,不仅是“杀”,“伤、败、破、灭、断、绝”等都在六朝以后陆续发生了他动向自动的转化,这些动词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终结”语义特征。至於如何从形式上准确证明动词的“终结”语义特征,古汉语中这类动词有哪些,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