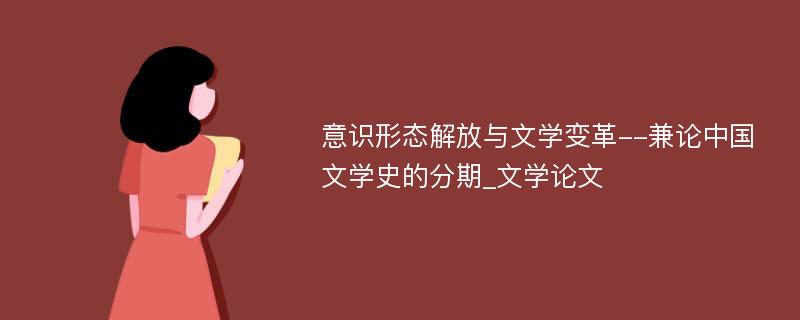
思想解放与文学变迁——兼论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个意义重大的思想解放时期,分别发生在汉魏交替、宋元之际和本世纪初,虽然起因及表现形态各异,但客观上皆造成了对正统儒家文化独尊地位的强力冲击。这种冲击的思想史意义已为世人所公认,但对于中国文学整体发展之决定性影响,除了第三次冲击导致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因而形成共识外,前二次则似乎至今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究。本文拟结合目前有关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之讨论,对此作几点思考。
一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礼崩乐坏社会大裂变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严格说来,彼时正是中国古代哲理思想产生和形成时期,之前尚未出现足以束缚整个社会的成熟的思想体系。至于西周礼乐,则似集中体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虽不能说与思想无关,但终究是两码事。况且由于时代等方面原因,先秦诸子及其著作除了客观上构成先秦散文之一部分外,于文学史整体发展并无直接关系。故而倘若考察思想文化与文学变迁,进而为把握文学史分期提供参照,自然宜从发生在大一统社会崩溃、经学衰微后的东汉末乃至魏晋南北朝入手。
魏晋时期,无论对于中国思想史还是文学史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代。
汉王朝是继秦帝国之后我国第二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继秦始皇接受李斯主张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之后又一次建立文化大一统的尝试。由于接受了前代的教训,找准了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思想结合点,这一次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尽管汲取了道家、阴阳家乃至法家的思想源泉,董仲舒鼓吹的神化儒学已与先秦孔孟儒学拉开了距离,但无论如何,随着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汉书·董仲舒传》)禁令的实施,以儒学为主体的经学正式成了社会的统治思想。
非但如此,经学还兼并了文学。换言之,文学本身即构成了经学。先秦文学之主体——诗歌(“诗”)和散文(“书”、“礼”、“易”、“春秋”)上升为经书即为明证。即使体现非中原文化精神之南方文学代表《楚辞》,汉以后亦因其充满忠君思想而被纳入经学研究的范畴。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有助于人们思想的同一和大一统社会秩序的稳固,但另一方面也压制了人们自由创造的精神,导致社会发展应有活力的窒息。尤为重要的是,它模糊了文学的本来面目,阻碍了文学按自身规律独立运作的历史进程。
当然,此类问题并非直到汉代方始出现,先秦文学即呈诗乐舞结合、文史哲不分之混沌状态,孔子论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集中体现了当时人心目中非独立、非自觉的文学意识。这种状况进入汉代后由于文学升格为经学而变得愈加严重。乐府刻意追摹诗经,继承了祭祀、朝会和采风观俗等方面的职能,在诗乐舞结合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汉代散文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到贾谊、晁错、王符、仲长统之政论,在性质和类型上皆未逸出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范畴。至于由战国时荀子所开创,并受楚辞作家宋玉等人深刻影响的汉赋,也由于经学笼罩的缘故,硬给自己规定了难以胜任的“讽谏”任务,从而陷入了“讽一而劝百”的尴尬,以致身为汉赋代表作家的扬雄,晚年也认为辞赋乃“童子雕虫篆刻”,无补于规谏,“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如此皆可显示时代思想束缚对于文学发展之消极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状况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大一统社会崩溃,经学对人们思想控制的松弛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宣告了文学自觉和趋于独立的时代的到来。
汉末黄巾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结束了延续四百余载的汉朝大一统社会政治局面,与此同时,武帝以来定为一尊的儒家经学思想控制也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糅合儒道的玄学以及外来的佛教取代了它的独尊地位。曹操公开宣布“唯才是举”,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本领的人,都一律加以选用,使得习惯了察举孝廉、征辟贤良的文人瞠目结舌。如果说桓、灵时党锢之祸已使他们感到“学而优则仕”传统道路前途黯淡的话,此际更是心灰意冷,从而不得不调整自己心目中的是非标准,在选择人生道路时自觉不自觉地和传统经学伦理拉开了距离。
“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这并非曹氏父子力能回天,而是大一统社会崩溃和经学自身式微的必然结果。稍后嵇康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更集中体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摆脱经学精神束缚的思想解放特征。
思想之解放体现在文学领域首先是对文学本体之正确认识。魏文帝曹丕明言“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不仅第一次明确地将纯文学的“诗赋”和肩负国家大事之应用文体“奏议”、“书论”以及“铭诔”划清了界限,而且直接了当地指出“欲丽”的美学特征。相比较而言,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尽管已将“诗赋略”与“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辑(总集)”并列,显示了朦胧的文体意识,但随即表白“登高作赋,可以为大夫”,“古者诸侯卿相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依然是经学之声口!联系前述扬雄所称“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正可谓如出一辙。与曹丕观点相较,距离当不以道里计。至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分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对文章诸体的理解基本上与曹丕相近,区别仅在于从观念的更新演变到制度之确立而已。到了这一步,文学之自觉和独立进程应当说是最终完成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文学创作本身。魏武笔下虽仍保留有四言篇什,但皆已纳入了“借乐府古题写时事”的轨道,事实上开了后世文人拟乐府的先河,其五言古诗更属新时期诗歌形式之开拓。至于曹丕,则除了以帝王之尊公开宣布其思路清晰之文论外,创作亦多有建树。五言诗成就已为时人所称道,又以一曲《燕歌行》较早为七言诗导夫先路。曹氏父子并非专业作家,但惟其具有统治者之身份,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思想变为统治社会的思想。政治上,他们“好法术”、“慕通达”,使天下“贵刑名”、“贱守节”,导致了正统思想束缚的松弛。文学上,他们对传统的继承和变革同样可以影响和作用于一个时代,范围大至整个社会。在他们周围形成以“建安七子”、曹植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集团,其成就无疑显示了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最新风貌。此后的“正始文学”乃至两晋南北朝文学总体上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们从五七言古诗、拟乐府、骈体文以及《桃花源记》等文艺性散文中容易看出自觉进行文学创作和审美追求的努力,至“永明体”诗歌更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格律的基础。
我们尽可以对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原因作出各自不同的具体解释,但整个魏晋乃至南北朝唐宋的文学自觉和独立发展,却不能不追溯到汉末大一统政制分裂、经学衰微所带来的思想解放。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文学才得以摆脱了传统精神束缚。如果说在先秦两汉,文学处于早期混沌状态,或甘为经学附庸而不自知,还停留在“自在”阶段的话,则魏晋以后无疑进入自觉、独立的“自为”阶段。本世纪20年代,鲁迅即曾明确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他同时稍前,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也说:“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中国诗论史》)他们所指虽仅在于曹魏这个时代,但文学的自觉和独立是一个历史进程,曹魏的文学变革,正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开始。整个魏晋南北朝完成的文学自觉和独立,则为唐宋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公元13世纪元帝国的建立是古代史上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掌握了全国政权。在此之前,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古代中国虽然一直存在着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甚至还出现了五胡十六国、西夏、辽、金等与汉族中央政府相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但那大都是短暂的或局部性的。这一切随着元王朝的建立而彻底改变了,这当然不可能不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思想领域。确切地说,元王朝的建立客观上是对中国古代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一度动摇了它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如前所言,儒学体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即成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汉末大一统社会随着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崩溃之后,经学式微,儒学的统治地位第一次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由此导致了曹魏时社会性思想解放和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然而这种冲击和挑战来自内部,是汉民族文化在面临时代变革时所作的内部调适。魏晋南北朝虽然处于大一统政制崩溃之后,但社会的宗法性并未改变,世家大族掌握着政权,极重门第血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将宗法制移植于自身。这样,集中反映宗法制的儒家纲常名教,仍然是维系国家、社会的基本原则。正因为如此,当时尽管儒学的独尊地位已经失去,统治者采取兼容佛道的思想政策,但并不意味着儒学失掉了它的正宗地位。经学虽然风光不再,但构成“五经”的诗歌和散文形式仍为此时期自觉、独立的文学所继承。至唐宋时,统治者将诗文作为国家选拔治国人才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形式,以诗歌散文为主流的中国古典文学终于发展到了繁荣阶段,这里面当然有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在起作用,但显然也与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的鼓励和指导有关。宋代以后,理学大兴,儒家理论更加严密、充实,诗歌散文为主体的古典文学自然构成儒家正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亦变得更加精致、高雅。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儒家思想社会功能的强化,魏晋以后儒学文学之间日趋分离的关系至此际又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结合,而元帝国的建立则再一次拆散了这种结合并连文学自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蒙古贵族进入中原之初,的确是不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道理的,他们中甚至有人认为“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元朝名臣事略》),只是由于耶律楚材等人的反对,这个荒唐建议才未被采纳。但是蒙古军事贵族在灭亡金和西夏等华北、西北地方割据势力的时候,已经严重破坏了广大汉族人民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大批儒家文化典籍和文物遭到洗劫和破坏,许多堪称儒学楷模而又具有民族气节的汉族官员如文天祥、陆秀夫等相继被俘或自杀,而一些卖身投靠、为虎作伥的汉人军阀如张柔、史天泽等却封王封侯,成了新王朝的功臣。此外,大批原来信奉“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高”观念的儒生被断送了上进之路,更多地被战胜者当作俘虏逼迫为奴。这些无疑都使得构建在汉族士大夫心目中的传统思想堤坝开始坍塌,旧的伦理标准和是非观念似乎都已根基倒置。当时人刘因总结道:“昔金源氏之南迁也,河溯土崩,天理荡然,人纪为之大扰,谁复维持之者?”(《翟节妇诗序》)这样,我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思想解放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和前一次不同,发生在蒙古军事贵族南下过程中的这种思想解放已不仅局限于体系内部调适,而是伴随着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调整的深层变革。如果说魏晋时玄学仍未放弃儒学招牌,而南北朝时佛、道二教也未否定儒学正宗地位的话,此际情况便已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当时人王恽在《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中写道:“举世皆曰儒者执一而不通,迂阔而寡要,于是士风大沮。”这在此前是从未有过的。时人记述当时的社会等级,从“一官二吏、三僧四道”直到“七猎八猖、九儒十丐”。连身为色目大臣,后为有元第一忠良的余阙也说当时“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贡泰父文集序》),是为元代儒学儒生社会地位之实录,同样为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曾有。地位如此,其对社会思想控制能力可知。正以此,元代文人思想解放程度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以致周文王、姜子牙、诸葛亮这些历史上的圣君贤臣、道德和事业楷模亦成了人们笔下嘲笑的“五眼鸡”、“两头蛇”、“三脚猫”。传统文化之权威陵替,于此可见一班。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权威衰落导致了社会思想控制的松弛,也造成了时代文学观念革新和文学进程之改变。
我们知道,从先秦到唐宋,以儒学为主体的我国传统文化造就了文学以个人抒情贯穿的短篇创作。儒家诗教强调诗歌和文章“言志抒情”特性,历代统治者出于思想控制需要人为地抬高这种文学的地位,以至隋唐后将其作为科举取士的主要标准,这些都使得传统诗文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国古典文学长期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则导致我国古代戏剧、小说等叙事文体发展长时期受压抑,人们的思维习惯于抒情而短于讲故事,综合想象和虚构能力先天性不足。这样,再加上以宗法专制为特征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束缚,更加强了人们思想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具体表现为对戏曲小说等叙事文体的极端鄙视,鄙视的结果自然而然导致了文学形式之间的不平衡,而且假如没有外来因素作用的话,这种不平衡还将继续下去。
同样值得庆幸的是,元王朝的建立,对于汉民族传统文化而言,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强力冲击,它在短短的时间内摧垮了汉族文人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原来处于独尊地位的正统道德观念一下子被翻了个儿,而与之相联系的儒家诗教也随之失掉了它的制约力量,再加上此前由于外来佛教影响而得到大大刺激的民族综合和想像力的适宜土壤,可想而知,我国古代长篇叙事文学和综合艺术的产生和繁荣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强力冲击,元代汉族文人的地位也在短短的时间内一落千丈,只比乞丐稍强一点,甚至不如娼妓。不仅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元王朝废弃了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元世祖忽必烈且云:“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元史·赵良弼传》)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文学形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手段效益的怀疑。如此一来,原来由于社会性思想解放已缓解了对戏曲小说鄙视心理的文人,又被堵塞了他们赖以进入仕途的科举道路,也就只好与娼妓乞丐真正打成一片,从事起传统不屑的“贱业”而其乐融融了。如果说此前处于支流地位的叙事文体(宋金杂剧院本及诸宫调、讲史平话等)未能也无法吸引大批专业作家投入中去,因而未能蔚为大国的话,这一步则由于元代建立过程中的主客观条件的促使而达到了。于是原先一直萎缩难振的通俗叙事文学(以元杂剧和讲史平话为代表)一下子如火如荼地繁盛起来,此后的明清传奇和章回小说、拟话本一直兴盛不绝。而相反,原先占据正统的诗歌散文却失掉创新精神,从此走了下坡路。站在文学自身发展角度考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传统诗文已经走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后来的努力也是超越不过前人的余响和尾声而已。戏曲小说等通俗叙事文学之所以能够自元代开始压倒正宗的诗文而成为文学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正是作家摆脱了传统的思想束缚而走上了创造新兴艺术样式的道路。
三
至此,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社会性思想解放与时代文学变革有关,研究文学史分期除了关注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外,还应充分考虑社会思潮等方面因素。如果说汉魏交替经学式微促成文学自觉时代来临的话,则过了一千年,至公元13世纪的宋元之际,漠北草原文化对中原儒家正统文化之强力冲击导致了中国文学进程发生了质的转变,性质和类型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先秦两汉、魏晋到唐宋、元明清和近代即自然而然呈现着中国古代文学三种不同的历史面貌,借用历史学的术语,亦可称此三个历史时期分别为中国的上古文学、中古文学和近古文学。
上古,史学界一般是指有文字留存的商周秦汉这段时期,和我们这里文学分期可谓不谋而合。但在文学史界却存在不同认识,突出如目前通行之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章“上古文学”即明确仅指诗经、楚辞诞生前的传说时代,显然时间概念狭窄得多,况其后又不曾出现“中古文学”、“近古文学”的划分,无疑不是对这种分期概念的成熟和系统应用,可作特例看待。真正对这种分期方式进行认真思考的袁行霈在《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5 期发表长文《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其中第三部分“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即明确论述了“三古”即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概念,而“上古期”恰恰包括先秦两汉。然而,袁先生的结论,是建立在文学的各种体裁、思想基础、文学思潮以及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的基本格局皆孕育或形成于这个时期基础之上的,与本文强调的思想解放与文学变迁的互动,恰恰显示着不同的思考角度,可说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中古期划分的情况稍涉复杂。史学界一般定在魏晋至隋唐这一时期,文学史界则自本世纪初刘师培先生《中国中古文学史》起始,“中古”专指汉末到陈亡,实即魏晋南北朝文学。80年代初问世的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以年为纲,上起公元53年扬雄生,下迄公元340 年卢湛死,即跨越西汉至东晋。至于这样的范围依据,却皆未提供详细论证。前数年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其内容仍未逸出魏晋南北朝的范围,可以说仍继承着刘师培的传统。相比较而言,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思考并系统论证过的前辈学者应为郑振铎,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将中国文学分为三期,名目稍有不同,为古代文学、中世文学和近代文学,其中中世文学“开始于晋的南渡,而终止于明正德的时代”。此外,袁行霈在前引文章中亦认为中国文学的“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不难看出,此二人所使用称谓及具体划分虽略异,但内在精神一致,同较史学界“中古期”划分向后推延了数百年。
凭心而论,郑、袁二位的观点,着眼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揭示出一些实质性问题,特别是袁氏将魏晋作为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看做上古文学和中古文学分界的标志,言之成理,令人信服。然而,正如任何宏观通论总难免存在照应不周之处一样,他们的观点也不无值得商榷之处。比如郑氏认为“古代文学”(上古)和“中世文学”(中古)的区别在于“本土文学”和“受了印度文学影响”文学之间的差异,袁氏强调文学语言、传媒以及作者读者的社会层面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等等,皆难说即为定论。最突出的还在于他们都没有将文学性质和类型之时代变迁放到应有的位置去考虑,没有重视文学主流之前后嬗变。虽然他们也提到了戏曲小说,袁氏且认识到自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文坛主导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将文体本质有异之诗词和曲混同起来,且未指出元以前处于非主流地位之传奇话本和明以后跻身文学主流之章回小说、拟话本之间的差别。正因此,郑、袁二位皆将元代直至明中叶之文学一并归入中古(世)期,从而使得本文结论与之明显有异。
近古,史学界一般是指宋代至清鸦片战争以前,系基于社会性质分析而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之所谓“近代”排除在外的。文学史界则很少使用“近古文学”这个概念。本世纪30年代日本知名学者青木正儿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乃认为戏曲在唐以前殆无足论,宋代稍见发达,是戏曲史之古代期,元代为中世期,明清为近世期。故他笔下之“近世”与我们这里谈论的所谓“近古”显然不是一回事。前述郑振铎、袁行霈二氏对“近古文学”亦有看法,认为系指自明中叶至“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实际上包括了史家所称“中古”后半段和整个近代,显示了社会和文学发展不同步之特点。
应当说,郑、袁二人的观点,将历史上的“近代”归入文学的“近古”是有道理的。因为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列强入侵的是西方思想文化的进入,这同样反映在文学的创作之中,如所谓“新派诗”、“新文体”等等。但严格说来这些“文体革命”还都只是“旧瓶装新酒”,用当时新派作家自己的话说是“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以,此时期的诗文和戏曲小说在形态上与鸦片战争之前实质上并无不同,作为古典文学工具的文言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状况直到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后才得以根本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四”以前的文学都应归入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近古文学”的下限应划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至于郑振铎、袁行霈二氏所称“近古(世)文学”上限应在明中叶,是因为他们过分重视“印度文学的影响”,过分重视市民文艺、主体意识以及通俗文体社会化等非文学本体因素所致。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后出现了根本性转折,是由于文学整体性质、类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前后迥异的文艺主潮。明代中叶文人注重个性、反抗传统以及市民文艺之抬头,正是强化而不是扭转了这股文艺思潮的方向。倘若以此作为近古文学的开端,而将元杂剧及《三国》、《水浒》等长篇小说排除在近古文学之外,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
自然,文学史“三古”分期尚可进一步细致。如将上古文学分为先秦和两汉两个阶段。其理由,除了借助于历史上两个相对独立的时代使得上古文学变得更容易把握外,还在于先秦较明显地呈现文史哲不分、诗乐舞混合之特色,而两汉则除了残存上述特色外,还出现了脱离历史、哲学的纯文学汉赋。其“不歌而诵”的特点也使得它最终同音乐舞蹈拉开了距离,虽然夹着一条“讽谏”尾巴表明它和时代文学一道受到经学的牢笼,自觉皈依儒家诗教的范畴,但毕竟显示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将其与先秦文学分开是有根据的。
以此类推,中古文学可分为魏晋南北朝和唐宋两个阶段。它们的共同特点即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前半部主体——诗歌和散文的成熟与繁荣。不同在于前者以古体诗、骈体文作为自己创造精神的代表,后者则拥有近体诗、词和古文创作的辉煌,而这辉煌又是建立在前者已创造成就(如永明体等)基础之上的,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双各具特色,自然而然成为一个时期两个阶段划分的合理依据。
至于近古文学,同样可以进一步划分,不过其划分阶段的界限却颇费斟酌。前面说过,明代中叶并没有扭转文学史进程的因素,鸦片战争决定的是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不是文学史新的历史转折,此二者皆不可能作为近古文学划分阶段的依据。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文学的本体研究上来。
公元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在近古文学史上应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其理由在于,首先,传统公认的近代文学第一位大家龚自珍即诞生在此年。上述鸦片战争不能作为近代文学上限,原因还在于龚自珍于战后次年即去世,如此分期造成的尴尬在文学史界已为人所共知,因而必须将界限向前推移,龚之生年不可忽视。其次,在此之前,作为古典戏曲最后两位代表作家蒋士铨、杨潮观已分别于1785年和1791年逝世,而以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为标志,戏曲从此进入了以京剧表演艺术为中心的发展时期。第三,代表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艺术高峰的《红楼梦》,其一百二十回全本(程本)正于这一年全部面世。此后的小说,或表现对海外文明的向往(《镜花缘》等),或表现对现实政治的皈依(《荡寇志》等),在前进和倒退间撕扯和冲撞。和龚自珍诗文一样,都打上了近代文学的印记,传统辉煌已是昨日黄花了。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以这一年为界限,将近古文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样,再加上前述上、中古分期及阶段,我们完成了本文“三古六阶段”分期结论的寻绎。
毫无疑问,构成我们结论的来源是历史文化和文学自身的结合分析,这符合文学史既属于历史科学之一部分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客观实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史演变往往伴随着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而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往往又是以朝代更替为契机,所以完全突破朝代构架的文学史发展是不可能的。另外,还应看到,文学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又不总是协调同步的。前者使得本文论述三古六阶段时基本将人们习见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带有明显朝代印记的分期概念保留下来,后者又使得近古文学下限不是以公元1911年清王朝覆灭为标志,而是向后移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且近古第二阶段上限不始于鸦片战争而是始于龚自珍的生年。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历史和文学的切入点,如何把握影响文学史进程的社会思想文化巨变。明乎此,文学史规律也就不难寻绎了。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经学论文; 古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