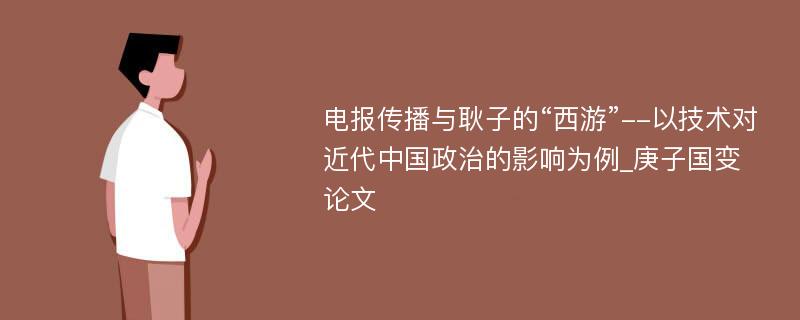
论电报通讯与庚子“西巡”——近代中国技术影响政治一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报论文,一例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通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庚子国变对于晚清政府产生了巨大打击,并客观加剧了中国封建体制的消亡。在这场波及全国的事件中,清廷中央政权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各省的督抚大员在事件中有着各自的政治筹谋,保皇会、革命党等政治势力借机发动武装斗争,加之义和团运动、联军入侵等事件所带来的不稳定的政治因素,都对清廷的中央政权和行政效力造成了重大挑战。
清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庚子国变其间其后仍然保持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地位,除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之外,作为通讯手段的电报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正是电报技术所建立起来的全国通信网络,才使清政府在偏安一隅时能够与各省官员保持必要的联系,基本实现了政令畅达,客观保证了国家机器的勉强维系,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因信息中断而面临的政治统治危机。
在庚子国变的过程中,清廷的行为可以按照时间和事件的顺序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清廷的政治统治都与电报技术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西巡和驻陕的阶段,清廷对于电报技术达到了空前依赖的程度,将电信联络视为关系政治存亡的重要措施。从史料反映的历史信息来看,越是清廷信息不畅、电报中断的时候,越是其政权遭遇危机的时刻。因此,电报通讯成为了考查庚子西巡期间国家政治状态的一条新线索。
一、清廷“西巡”前的电信情况
义和团对电报设施的破坏是造成清廷电报通信危机的主要原因。在庚子国变过程中,基于长期积累的华洋矛盾,义和团在全面抵制西方文化的同时,亦对西方设施与器物进行了自发性的打击与捣毁。在义和团捣毁的各种“洋物”中,电线、电杆、电报局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5月,随着华洋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加之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直隶、山东等地全面爆发。直隶地区作为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区域,在整个庚子国变期间遭遇了义和团、清军和联军的多重打击,因此也是电报设施损毁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北京失陷之前,清政府的对外电信联络已经陷入全面中断的局面当中。按照庚子以前的电报通信线路,北京对外联系的电报线共有三条,一条由北京经通州接往天津,再经津沪线接通上海,被称为“东线”;一条由北京经卢沟桥通往保定,再经太原接至西安,被称为“西线”;一条由北京经张家口通往库伦,再接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被称为“京恰线”。在三条线路中,西线最早受到破坏,特别是北京至保定一段,随着卢保“铁路被拳匪拆毁,电杆亦被砍断”[1]卷21,16;东线地处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带,在庚子国变之初便已受到大规模的破坏,“拳匪倡乱,京津电线首先被毁;”①京恰线亦“被匪割断”[2]70,外来电报只能交“张家口专马递京电局”[2]74。对于庚子国变期间京畿电报线路的残破情况,《东华续录》曾有过记载:“光绪二十六年,拳匪倡乱,畿辅电线首先被毁。南至津沽,北至张家口,西至保定,东至山海关,千余里间同时拆毁。”[3]353
电信断阻对清廷与外界的联系造成了较大影响,尽管临时采取加急驿递的方式传递信息,但其实际效率和便捷性却与电报技术相去甚远。从晚清的电旨、电奏制度来看,随着电报技术二十余年的应用,清廷在政治统治和军事调度等方面已经对于电报通讯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依赖,当这种通讯手段因为突发事件而临时失去时,电报技术长期应用所形成的历史惯性会使清廷的政治统治陷入困境。因此,直到北京失陷前夕,清廷仍然致力于恢复电报通信的尝试,足见其对于电报技术的依赖之深:
“现当用兵之际,军情瞬息千变,全赖电线无阻,消息灵通,方可通筹因应,迅赴事机。著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文武营汛,务将电线一体认真稽查,实力保护。倘有匪徒纠众掘断毁坏情事,即行勒拏严办,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严惩处。至直隶、保定、及山西、陕西一带电线被毁尤多,著裕禄等饬属查明地段,即行设法修复,不得稍有迟误。将此由六百里谕令各将军、督抚知之。”[4]109-110
二、清廷“西巡”中的对外通讯
1900年8月15日,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清廷部分官员仓皇出逃。在此次“西巡”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清廷的对外电报联络完全隔绝。由于直隶地区“溃勇、匪徒甚乱”[2]200,“专马难入京”[2]196,因此驿递也无法取得联系,清廷与外界陷入了“文、报均阻”[2]200的艰难处境当中。对外联系的中断使中国的国家政治陷入一种权力真空的状态当中,在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的特殊时期,这种权力的真空对于社会思潮和政治局势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由于整个国家的中央政权一时失去联系,中国出现了“南北梗阻,人心皇皇”[5]659的社会局面,这种局面早在两个月前北京失去对外电报联络时便已显现端倪,其时“京城半月无信,各省人心摇惑”[2]84。
直到8月22日,东南各省督抚所收到的消息仍然是8月13日北京寄往山东的信件,称“两宫仍在京”,其余则“杳无消息”[2]199,至于“洋兵是否攻入”、“庆邸留京议款之说确否”、“随扈大臣何人”[1]卷39,19等督抚们关心的问题,“京城、行在皆无消息”[2]195。8月22日当天,盛宣怀等人才接到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的电报,称“两宫廿一西幸”[2]201,方知西巡之事。清廷与外界联络中断所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在国外亦产生了一定影响,据驻德公使吕海寰所述,德国国内对中国形势的评估因电报阻断而谣言丛生,“北事因电阻生谣,致肇衅端,近沪亦有蜚语,诚恐煽惑起波。”[6]21驻美公使伍廷芳亦称,“北线断,谣言多。”[7]335
由于直隶、山西两省的义和团运动规模浩大,电报杆线破坏严重,因此清廷在进入陕西之前,其对外联络大多以人工驿递为主。尽管清廷令各处官员选派“精壮驿夫飞马驰递”,[8]57但是马拨传信耗时甚长,效率低下,对于早已习惯于高效快捷的电报传信方式的清廷和地方行政系统而言,驿递很难满足庚子国变时期政情传递的需要。
庚子国变以来,清廷饱尝缺少电信之苦,特别是经历了西巡初期文报不通的困境,已经对电报通讯的重要性形成了深刻的认识。因此,在8月23日暂驻宣化之时,清廷便传谕山西巡抚毓贤保证晋省的电信联络,“现在南北文报梗阻,晋省电线半遭拳匪毁坏,着赶紧派员修理,以通消息”[9]4009,将“晋省文报能否畅行”作为拟定西巡计划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与此同时,各省督抚迫切需要通过山西电线来获取朝廷的最新动向,以便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鉴于山西电线对陕西、直隶、湖北、四川等省电报通讯的重要性,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位大员分别对于山西电线的修复寄予了期望:
“与各国商议事件,全赖电线灵通。臣鸿章行抵上海,即查明直隶、山西两省电线全行被匪拆毁,只得暂驻上海,尚可与外洋往来通电……速将晋线次第修复,中外枢纽方免阻滞。”(李鸿章)[9]4026
“晋省电线未修复,殊为焦急。祈速设法赶办,以通诏奏。”(刘坤一)[1]卷39,19
“太原距京较近,但晋粮极贵,拳匪极多,运道艰,电报梗,种种不便。地主又别有见解,奏报供亿俱不如陕,故留晋幸陕俱不敢请,只可敬听圣裁。总以奉旨捷速为第一义。”(张之洞)[1]卷40,15
尽管清廷屡次严谕山西官员修复电报线路,但是该省电报杆线受创严重,大量电报线路数月前即为拳民砍断,加之“地方官不肯保护,不能修复”[2]118,清廷到达山西时,“晋线拆毁几完”。[2]250线路漫长、材料不足,使得短期内修复电线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因此,直至9月10日,两宫“前抵太原,电线无杆修通”[1]卷40,13。
由于太原电报通讯的断绝,清廷抵达太原之后与外界进行电旨、电奏联络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上谕只能继续通过“六百里谕令”的方式进行传达。随着与各国议和行动的开启,清廷需要同北京的庆亲王奕劻和由沪抵津的李鸿章等人随时商讨议和事宜,电报通讯在这一时期对于政治统治的意义更加突出,“电报不通,于该亲王等商议各件,转辗恐多延误。”[10]325因此,在清廷决定继续西巡赴陕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电报通讯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正如清廷在上谕中提到的:
“驻跸太原,将近两旬……省城电报不通,京外往来要件,转辗每多延误。不得已谨择于闰八月初八日启銮西幸长安。”[10]326
清廷放弃长期驻跸太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灾荒、民生等社会原因,亦有联军西侵等军事原因。然而,从对外通信的角度来看,电报不仅是清廷实现对外通信的技术保证,更是维持其统治的政治保证。鉴于电报断阻所造成的“朝廷之指挥,封疆之机要,两不相及,贻误实多”的局面,②清廷为了延续其政治统治,必须保证自上而下政令畅达的行政效力,因此,电报技术成为了清廷在政治危机时期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这也是清廷选择电报线路受损程度相对较少、对外电信联络基本畅通的西安作为目的地的原因之一。
三、电报通讯与清廷的议和与回銮
西巡抵达西安之后,由于电报通讯基本畅通,清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各省的政治、社会情况,各省官员也可以较为迅速地了解清廷的现状与意向,双方因电信数月断绝所产生的疑虑和猜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由于双方信息交流的加速,清廷可以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各省督抚亦可以根据清廷的具体信息采取相应的策略。尽管清廷与地方督抚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并未因此消失,但是电报通讯降低了中央与地方产生进一步误解与疑忌的可能,使得国内政治关系略趋明朗。
电报通讯的另外一层意义在于促进中外和谈的进行。西安的清廷,直隶的李鸿章、奕劻,东南各省的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都是中外和谈的重要参与者。由于大家分处不同地区,电报通讯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了凸显,特别对于清廷而言,“行在诸人,皆恃庆王、李相为泰山,望电报如饥渴。太后曰:‘我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11]328由此可见,此时的国家行政系统已经与电报技术密不可分地交织到一起,形成了一套以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政治运行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电报通讯起到了重要的串联作用,它不仅是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载体,更是各种政治关系的有效串联者。
从电报通讯的具体运行层面来看,西安电报局作为临时性的中央通讯机关,在清廷西巡期间发挥了电信枢纽的作用。由于外省往来电信频繁,电报线路需要随时巡修以保持畅通,电文收发亦需做到保密、快速,加之清廷对外电报通讯需要按照电旨、电奏等奏报制度进行处理,原本作为省级电报机关的西安电报局在西巡期间承担了大量的清廷政治事务。正因如此,西安电报局的地位受到了各方力量的充分重视,被赋予与京城电报局同等重要的地位,“西安电局目前办事重大,一如京城”,其工作性质亦给予了明确的界定,“一曰勿阻线,二曰勿洩漏,三曰勿延搁,四曰勿多事。”③
清廷对于电报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西巡的危乱局势当中,还体现在庚子国变之后局势渐趋平缓的时期,这一情况在清廷回銮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1901年10月6日,清廷自西安起銮返京,由于“回銮过豫、直各境无线,谕旨、章奏阻搁堪虞”,清廷在回銮之前谕令各省“筹款展造潼关至河南、直隶电线,以备跸路传递要报”,其中重点修设的线路工程包括“由潼关开工至孟县”,“由孟县开工至正定”,“由保定至京,京至天津,天津至德州各处线路”,此外还包括收回法军所占之正定至保定电线。通过电报线路的修建,“总期于谕旨、章奏朝发夕至。”④除了加强线路修设之外,电报总局督办盛宣怀还在起銮之前特别电令西安、临潼、潼关、陕州、洛阳、开封、郑州、怀庆、卫辉、彰德、正定、定州、保定等电报局“廿四起銮赴豫,北路各局添守夜班”,⑤以保证电报随到随发,免于耽搁。基于长期使用电报通讯所形成的技术依赖性,加上庚子西巡中因电报通讯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清廷将电讯畅通作为顺利回銮的重要保证,从而再次将电报技术与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四、结语
从技术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来看,电报技术与庚子国变期间诸多政治事件所发生的联系反映了技术对于晚清政治的介入与影响。在参与庚子国变的主要政治势力中,清廷重视电报通讯,是基于维系统治、巩固政权的政治考虑;督抚重视电报联系,是基于稳定政局、保存实力的政治预期。在电报技术与晚清政治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既有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联系,又有地方督抚之间的横向联系。电报不仅是各种政治关系的串联者,同时还是各方政治意向的反映者。
电报技术在晚清朝廷中的应用可以分为常态时期和非常时期。在常态时期,由于电报线路基本畅通,电旨、电奏可以按照既定的电信制度正常进行,各省信息亦可以较快地传至清廷,对于各地影响政治统治的不稳定因素,清廷可以迅速获得消息,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然而,与常态时期相比,当一些极端的政治、军事、社会事件发生时,电报技术对于统治者而言通常会体现出一种非常时期的状态。就晚清政府而言,在庚子国变发生的过程中,清廷经历了西巡之前和西巡途中三个多月的电讯阻隔时期,在此期间清廷对于电报通讯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常态时期,仅靠驿递传送的有限信息无法满足清廷在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时期急需了解各方讯息的愿望,亦无法解决地方大员掌握朝廷动向的信息需求。因此,电报通讯成为了庚子国变时期中国各方政治力量共同期待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了清廷维持中央政权合法效力的重要工具。
在庚子国变期间,谣言是各种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公使被戕的谣言推动了各国向中国派遣联军的行为;清廷存亡的谣言使各省督抚人心惶惶,几欲自立。谣言丛生是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的直接表现,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电报信息联系的中断。由于难以进行有效的电报联系,各国政府无法快速掌握驻京公使的情况,南方督抚也无法掌握清廷的最新动向,电报通讯的中断增大了信息交流双方的猜疑与焦虑,进而加剧了庚子时期的政治危机。
清廷对于电报技术之重要性的认识是一个逐渐加深的历史进程。在晚清电报事业发展的三十余年里,尽管电报技术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官方的强调,然而,正是庚子国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沉重打击才促使清廷重新评估电报事业的政治影响。从电报事业的运行角度来看,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兴起的官督商办经营体制与官办体制被共同应用于电报事业当中,纵横全国的电报线路被划分为“商线”、“官线”和“省线”,经营方式和线路产权的多样性使得电报事业缺乏统一的监控与管理。多元化的管理方式在国家稳定的时期基本可以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但是在社会动荡、战争爆发的特殊时期便无法保证全国的电报事业得到统一的管理,亦无法使电报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
庚子国变加速了电报事业的国有化进程,其中重要的政治考量就是将电报事业与政治统治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庚子国变时期因电报阻隔所加剧的政治危机使清廷认识到了对电报事业进行国家统一管理的必要性,从而逐步将商办电报和各省电报收归国有,并建立专门的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管理。在电报事业的国有化过程中,无论是电政大臣,还是邮传部电政司的官员,都将“电政”作为一项专门的国家事务加以管理,“电”与“政”的结合不仅证明了电报事业已经由经济事务发展成为政治事务,亦凸显了电报事业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共属性。
电报通讯问题不仅反映了庚子国变时期“中央-地方”的政治关系,而且对上述关系施加了实质的影响:在庚子国变过程中,清廷电报通讯长期阻隔,而南方各省督抚的电报联络却基本畅通,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原有的政治关系出现了失衡。各省与清廷的联系受阻,使得短期之内出现了一种近乎于“无中央政府”的政治状态,由于南方各省之间可以进行自由快速的电报信息沟通,这就使各省督抚在实施“东南互保”的同时,彼此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政治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加剧了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对立,亦对此后清末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国内政治关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影响。
注释:
①《电报事宜清折》,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案号:061938。
②《愚斋奏稿》,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案号:027189。
③《盛宣怀致孙宝琦函》,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案号:015030。
④《愚斋奏稿》,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案号:027189。
⑤《盛宣怀致各电报局电》,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档案号:014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