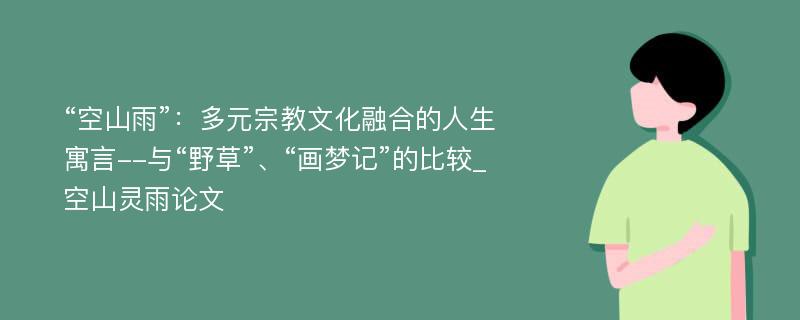
《空山灵雨》:融合多重宗教文化的人生寓言——兼与《野草》、《画梦录》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野草论文,寓言论文,宗教论文,人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3)05-0050-07
一
学术界及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都一致公认,鲁迅的《野草》是中国现代散 文诗开先河的作品。《野草》1927年7月由北平北新书局出版,收入散文诗23篇。但从 时间上来看,《野草》显然不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版的散文诗集。1925年6月,上海商务 印书馆出版了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收入散文诗44篇,它比《野草》的出版整整早了 两年多,这也是一本典型的散文诗集,而且它的影响也不小。文学史家没有把《空山灵 雨》作为现代散文诗的开风气之作(至少是开山之作之一),应该说是不客观、不准确的 。其后出版的另一本典型的散文诗集是何其芳的《画梦录》,1936年7月由上海文化生 活出版社出版,收入散文诗16篇。尽管这个小册子仅4万余字,但它出版后对散文诗理 论与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它于1937年与曹禺的剧作《日出》、师陀的短篇 小说集《谷》同时获得天津《大公报》文艺奖。“五四”以来及至40年代,虽然也连续 出现过一些现代散文诗作品,但从典型性和实际影响来看,都不如上述三部作品。
我之所以选择《野草》、《空山灵雨》和《画梦录》这三部作品作为现代散文诗创作 的代表进行对比,主要还考虑到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和三种不同的审美 表现方式。
《野草》属第一种类型,它是一种由外部聚集种种痛苦的感受,不断向内心深处集中 压缩,最终以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方式(自我磨难、自我剖析 + 世相透视、社会批判)来 抒发情感。我理解,《野草》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乎要怎样地启发别人,也不一定非要 别人理解作者自己不可,它主要是一种作者的自我折磨,自我剖析,一种对痛苦的自我 承受,自我消化。因此,作者的性情和人格魅力实际上是这部作品的根本底蕴。但这种 自我折磨的外在因素,即时代社会的意义,确是十分明显的。这也就是高长虹所说的“ 入于心”而“面于外”。长期以来,人们喜欢用“难以直说”来概括《野草》的思想和 艺术特征,其实,并非爱情风波、思想苦闷等“落实”之事难以直说,而是很多情绪感 受本身就难以直说、无法落实。人们认为《野草》在本质上是诗的,更多的就是看重鲁 迅在这部作品中所表露的情绪和感受是异常浓郁、丰富和复杂的。
《空山灵雨》属第二种,与《野草》相反,它是一种由内向外扩散型的人生思考方式 ,主要是以作家个人的内心感受为基点,以作家明确追求的人生价值观念与文学表述方 式为核心(比如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共同主张和许地山个人善于超越人生的思考模 式),向外寻求一种表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力图以作家个人所感受到和领 悟到的生活真谛,来感染和启发别人,教化和改造社会。《空山灵雨》整部作品的设喻 式的结构方式,贯穿始终的以苦为本、以苦为乐的强烈意识,都是与作家的人格类型和 审美追求密切相关的。
《画梦录》属第三种,与上述两种类型相比,它更为独特。它是以作家自己内心深处 的感受为出发点,再回到作家自己内心深处这样一种自我倾诉、自我言说的方式。这也 就是何其芳独创的所谓“心灵的独语”,它自始至终以作家的自言自语构成了一种“独 语体”的表述方式。《画梦录》强调自我心灵封闭的意义和价值,向散文的“纯粹性” 方面更接近了一步,但在本质上,《画梦录》还是期盼得到世人的理解和同情的,并没 有真正封闭或潇洒到完全不需要别人理解的超然境地。这也正是作家深感苦闷的地方, 也是读者难于理解作品的困惑之处。
三种类型,鲁迅的《野草》更具有思想家的精神特质,更具有灵魂拷问的深刻和苛求 ;许地山的《空山灵雨》更带有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即问题文学的探求特点 ,寻找和拯救是作家的价值取向;何其芳的《画梦录》则更接近本原意义上的诗人,更 重视情感本身的诉说,更注重理想化的情态,更富有敏感的神经,更有一种自我陶醉的 气氛。相比之下,鲁迅的《野草》更注重的是情感本身,因此从中很难看到这种自我陶 醉的情绪。
二
三部散文诗集当中,《空山灵雨》最为清淡、平实,但又最有玄思妙想;三位作家当 中,许地山看似最不以才华见长,但他对信念的追求最为执著,最为独特。
《空山灵雨》是许地山惟一的散文集,显而易见,“空”“灵”二字似乎已经定下了 这部作品的思想基调和艺术旨趣。所以,有论者指出:“‘空’‘灵’实乃佛家惯用之 词。他以此为集子命名,最能说明他的艺术趣味。”[1]更有论者直接指认《空山灵雨 》是“佛教散文”,认为“佛教思想,就是他散文的最独特处;而贯穿《空山灵雨》的 基调,还是佛教思想”;虽然寓言体式“是所有宗教文学作品最常用的形式”,但《空 山灵雨》“在艺术形式上,主要还是受了印度宗教文学的影响”,与佛教有一种特别的 “渊源”关系。[2]
其实早在30年代,沈从文在他的那篇《论落华生》中就强调过许地山散文与佛教思想 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意义:“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 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 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但是沈从文紧接着强调“这调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 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糅合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作者 的风格是由此显示特异而存在的”。在同一篇文章中,沈从文甚至又重复强调了“佛的 聪明,基督的普遍的爱,透达人情、而于世情不作顽固之拥护与排斥,以佛经阐明爱欲 所引起人类心上的一切纠纷”,这一切的融合才是许地山散文的本质所在,才是确立许 地山“在中国,不能不说这是唯一的散文作家”之地位的根本原因。[3]遗憾的是,有 些研究“许地山的佛教文学”的论者在引用上述沈从文话语时,只保留了沈从文文中强 调佛教文化与许地山散文关系的地方,偏偏去掉了沈从文同时强调基督教文化及“近代 文明与古旧情绪”等多种文化与许地山散文同样相关的地方,这就不仅不能“相当公允 ”地理解沈从文对许地山散文的论述,而且也难以真正公允地讨论许地山散文的本质内 涵了。
我认为,《空山灵雨》无论在思想倾向或是艺术表现手法上面,都鲜明地体现出某种 程度的佛教文化的色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空山灵雨》并不仅仅是作为“佛 教散文”而体现出其根本价值的,它同时还包容了多种宗教文化的因素。当年阿英在评 论许地山《空山灵雨》的时候就曾指出:“他的小品文的境界,不是一般的,不是完全 和现代思想契合的,基于他的思想与生活,反映在他的小品文中的,是一个很混乱的集 合体。”[4]至于《空山灵雨》的思想内涵如何“混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多种文化 思想的“集合体”是符合《空山灵雨》的思想特质的。在《空山灵雨》中不仅体现了许 地山对佛教文化的体悟和阐释,同时也“集合”了他对基督教文化、道教文化乃至现实 主义人文文化的多重思考和体认。而这种多种文化思想的“集合”性,才是更接近《空 山灵雨》的思想本质和思考特征的。
《空山灵雨》中的相当篇什确实是以“生本不乐”的佛教思想为基本色调的。在其“ 开卷底歌声”中就唱道:“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积怨成泪,泪又成川!”其第一篇散 文中那只可怜的蝉,永不停歇地一次次往松根上爬,又一次次被雨珠毫不留情地打摔到 地下,而且还要遭受蚂蚁、野鸟之类的嘲笑。这无疑是一则人生是苦、苦海无边的寓言 。又比如《海》这篇散文,它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我”和“朋友”于茫 茫大海之中“坐在一只不如意的救生船里,眼看着载我们到半海就毁坏底大船渐渐沉下 去”,于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对话开始了。“朋友”说:“人底自由和希望,一到海面就 完全失掉了!”因为“在这无涯浪中无从显出我们有限的能力和意志”。而“我”回答 :尽管我们的能力有限,尽管谁也说不准我们将会被海浪抛向何方,但“我们只能把性 命先保持住,随着波涛颠来播去便了”。看着那大船被茫茫空海吞没,“朋友”焦急而 空泛地议论着,“我”则劝他弃绝“纵谈”,“帮着划桨”。“朋友”问道:“划桨么 ?这是容易的事。但要划到哪里去呢?”“我”说:“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 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海上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罢。”《海》是《空 山灵雨》中最富有象征意味的篇章之一,“海”的象征意味是十分明显的:茫茫空海犹 如人生苦海漫无天际,人在这苦海之中真是太微不足道,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海所吞没 。佛教文化对人生苦难的认同在这里得到了高度象征性的表现。然而文章并没有停止在 面对无边苦海的困顿上,而是又突出地强化了“划船”意识:不管遇到何种灾难,力求 先保持住性命,无论会漂向何方,都要“尽管划罢”。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其小说 《缀网劳蛛》的主题意蕴:“世间没有一个不破的网”,“所有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 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但网破了就得补缀,“你爱怎样,就结成怎样”。显 然,这个主题与《海》的主题是相通的,它们都体现了浸透在许地山人生思考之中的道 家哲学:在迷茫中把握自己,在困境中顺其自然,在“无为自然”的境地里达到现实与 精神的双重超脱。许地山在《海》、包括在《缀网劳蛛》等许多作品里都苦苦思索着如 何摆脱苦海从而达到理想美满境界这一人生的终极问题,他也往往以佛教文化的“苦海 ”意识为其思考的基点,但他终究没有停留在佛教文化认同苦难以及把理想境界的建立 寄托在空幻玄虚的彼岸世界的层面上,而是积极演进佛教文化的“生本不乐”,使之走 向“以苦为乐”,并进而与道教文化“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观念糅为一体,最终在“ 自然无为”的状态下把握今生现实。《海》中对话的双方“朋友”与“我”,显然强调 的是“我”,而“我”强调的正是这种以“划船”意识来超越“苦海”意识的思考。
《债》是《空山灵雨》中又一篇重要作品。它诉说的是一个身处优裕环境却精神极度 苦恼的人,他突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还债”意念,只觉得自己“欠底债太多”。欠债 的缘由如他所说:“我看见许多贫乏人、愁苦人,就如该了他们无量数的债一般。我有 好的衣食,总想先偿还他们。世间若有一个人吃不饱足,穿不暖和,住不舒服,我也不 敢公然独享这具足的生活。”这实在是佛教文化超凡脱俗大慈大悲的一副热肠,就连其 岳母听起来也觉得“太玄了!”岳母毕竟是非常现实的,所以在肯定了他的“先天下之 忧而忧”的精神之后,竟认真地问他,所欠之债“你要什么时候才还得清呢?你有还清 底计划没有?”他没有想当然也不能答。于是,岳母讲出另一番人生的道理:“这样的 债,自来就没有人能还得清,你何必自寻苦恼?……说到具足生活,也是没有涯岸的: 我们今日所谓具足,焉知不是明日底缺陷?……生命即是缺乏底苗圃,是烦恼底身田; 若要补修缺陷,拔除烦恼,除弃绝生命外,没有别条道路。……还是顺着境遇做人去罢 。”可岳母这一问一劝,使“他底耳鼓就如受了极猛烈的椎击”,“越发觉得我所负底 债更重”,终于义无反顾、一去不返地还他的人生之债去了。细读起来,这篇小品有三 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 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 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债必须还,而且“舍我其谁?!”尽管 这篇小品带有明显的说教色彩,它却浓缩了许地山围绕现实人生的价值所展开的多重宗 教文化的思考。虽然这种思考的深度也很有限,但它毕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探讨了人生 价值的多重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作品里许地山并没有对顺其自然的道家人生哲学 表示赞同,这与他在许多作品中所表达的看法似乎有所矛盾(或借用阿英的话讲是一种 “混乱”),但无论如何,它表现了许地山对人生宗教意义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是“集 合”性的,而把它仅仅归结于佛教文化的范畴显然是不全面的。
在《空山灵雨》中,有些篇章明显偏于强调回归自然、追求本真,进而达到超脱凡尘 俗世的境地。《香》是这样阐释佛法的:“佛法么?——色,——声,——香,——味 ,——触,——造作,——思维,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底爱不是佛法。”“因为你一 爱,便成为你底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许地山在这里明白无误 地把“本然”作为佛法的最高境界,连“爱”都弃却了。《美底牢狱》同样追求一种“ 听其自然”的美:“所有美丽的东西,只能让他们散布在各处,我们只能在他们底出处 爱它们;若是把他们聚拢起来,搁在一处,或在身上,那就不美了。”但是在《愿》里 则又表明不仅愿做“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做“如意净明珠,能普 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做“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做“多宝盂兰 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有“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 间等等美善事”,而且更“愿做调味底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底形骸融散,且 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这里虽然仍有追求自然 本源的意味,但更多地又融进了佛教“普度众生”和基督教舍己献身的博爱精神。《三 迁》先是说花嫂子为躲避世俗恶习,带着孩子一迁再迁,从城里到乡下,最后到了深山 洞里,终于是彻底避开了世俗,然而花嫂子却疯了。这篇小品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是一 个追寻自然本真反而被其淹没的悲剧。《鬼赞》里的幽魂一面高唱“那弃绝一切感官底 有福了!我们底骷髅有福了!”尽情赞美了佛教“灭欲”的超脱:“哭底时候,再不流眼 泪”,“发怒底时候,再不发出紧急的气息”,“悲哀底时候再不皱眉”,“微笑底时 候,再没有嘴唇遮住你底牙齿”,“听见赞美底时候再没有血液在你底脉里颤动”,而 且永远也不再受“时间底播弄”,真可谓彻底超越了世俗与时空。然而另一方面幽魂又 同声齐唱:“人哪,你在当生、来生底时候,有泪就得尽量流;有声就得尽量唱;有苦 就得尽量尝;有情就得尽量施;有欲就得尽量取;有事就得尽量成就。”这又转入了对 道家执着于现世今生哲学的礼赞,呼唤人们尽情合理地享受人生应有的那“一部分美满 ”。佛教彻底的“灭欲”与道教有节制的“无欲”又一次“集合”在一起,成为许地山 思考人生的两个侧面。
《空山灵雨》的寓言体式无疑地增强了作品的宗教文化色彩和思想启发力。一部分作 品类似佛经文学“设喻式”加“对话体”的形式,比较玄妙空朦,往往暗含哲理,启人 顿悟,如《暗途》,在简洁的对话中制造了一个喻体:黑暗中行路,与其提着灯把自己 亮在明处,不如不要灯,把自己隐在暗处。作品以此巧妙地传达出一种以暗为明、以退 为进、以守为攻的人生哲理和姿态,既浅切明了又令人深思。另一部分作品又颇似耶稣 基督的那些传教格言,在轻盈飘逸的叙述中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如《落花生》,在平 静朴实的叙述中发出意味深长的忠告,在亲切关爱的氛围里使人深受感动和启迪。多种 宗教文学体式的运用,是《空山灵雨》多重宗教文化的必然体现。因此说,无论从思想 性还是艺术性上看,《空山灵雨》实为一部融合多重宗教玄想的人生寓言。
三
由《空山灵雨》我们看到中国现代作家在融合宗教文化与现实人生的思考中有一个比 较集中、比较突出的命题:即认同苦难而又寻求对苦难的解脱与超越。这在那些受宗教 文化思想影响较明显、较深刻的作家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冰心、许地山、丰子恺等作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显示了宗教文化色彩浓郁的创作特色,而且这种特色于宗教 文化的理性思考也具有某种代表性和象征性。冰心虽然以基督教爱的哲学作为最崇高的 人生宗旨,但她实际上明白:人类社会本身恰恰是缺乏爱的。冰心并非无视现实社会与 人生中的苦难,而是力图用爱来解脱和超越这些苦难。她把爱奉献给孤寂冷漠的“超人 ”,奉献给无私的母亲和天真的儿童,奉献给纯净的大自然,同时又用爱来鞭挞无情冷 酷的社会,鞭挞卑琐自利的小人。其实,爱究竟能否实现,能实现多少,在冰心那里并 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坚定地传达出了一个强烈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有了爱就 有了一切,就能化解一切!因此,爱对于冰心来说并不是治愈某种苦痛的具体药方,而 是一种超越现实苦难的精神寄托。她的那个关于母亲与母亲,孩子与孩子,即人与人从 前生到今生到来世都紧紧相连,都应该心心相爱的著名公式,听起来确实有点玄乎,甚 至有人会觉得幼稚可笑,但这其中蕴含着的绝不只是冰心的一片纯真和热诚,更是凝结 着她的冷静思考:没有爱就没有了一切,不懂得爱就无所谓苦难,不理解爱的人,也不 会真正体会到苦难的味道,爱与苦难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恰恰是一体的。
与冰心的这种基督教文化思想的表现形态有所不同,更多受到佛教文化思想影响的许 地山等人则首先认同苦难,强调苦难于人生的意义。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认同苦难的 意识最强烈的应该说就是许地山,在其思想理论及文学创作中甚至体现出一种难以割舍 的“恋苦情结”。“生本不乐”可以说是许地山理论及创作的原点,正是从这里形成了 他反映社会和人生的独特视角。看起来,在许地山那里似乎确有一种过于悲观的情思, 他在《空山灵雨》的《弁言》里就开宗明义地说:“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 在床上那几小时”,可“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这实际上 是说,做人就不要希冀,也不可能有安适享乐的生活,以苦为本,以苦为乐,才是人生 真谛。这种意识确实深深地浸透在许地山的创作中——尤其要强调的是,这种思想绝不 只是出现在其前期作品中,其后期作品诸如《春桃》、《铁鱼底鳃》等,也同样强烈地 表达出人生多难,命运莫测的思想。世界的残缺、人生的残缺,在许地山看来,就是生 活的本色和人生的本源,“不完全的世界怎能有完全的人?”[5]因此,在许地山那里没 有高昂激奋的人生目标,而多是低沉的人生叹息,以及深深的负债甚至负罪感:“我不 信凡事都可以用争斗或反抗来解决。我不信人类在自然界里会有得到最后胜利底那一天 。地会老,天会荒,人类也会碎成星云尘,随着太空里某个中心吸力无意识地绕转。所 以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 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6]
人们有理由认为许地山在认同现实苦难、体认人生本质方面带有相当程度的悲观情调 ,同时应予正视的是许地山的这种悲观情调的确来源于佛教文化思想的深厚影响,这也 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佛教文化中悲观意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有一种比较普遍的 看法,认为“佛教只看到趋向死亡的一面,而不承认新生的一面,只看到个体的毁灭, 而没有看到族类的发展,这当然容易得出人命短促,人生是‘苦’,人就是一大‘苦聚 ’的悲观主义结论”[7]。“佛教的中心思想是否定人生,第一大命题就是‘一切皆苦 ’。”[8]“在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上,佛教以有生为苦恼,认为人生如苦海。自有始以 来,人便沉溺在这可怕的苦海中,生死轮转,一生一灭,永远不得超度。”“佛教对‘ 人’这一命题进行探讨时,是以否定现实生活为前提的。尽管现实生活是那样活生生地 摆在眼前,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的客观实体,但在佛教那里,却认为这一切都是 虚幻。它们颠倒本末,把客观存在看作虚无,反过来,却把它们想入非非的虚幻世界视 为实有。……本来,它们也是以索回人的价值为起点的,但在它们手里,结果却是,人 的最后一点人性也丧失了,而代之以完全脱离人类实体的神性。”[9]这些论点不仅指 出了佛教文化的上述根本缺陷,而且指认许地山等人正是因为与这些缺陷有了明确的区 别或自觉的超越,所以才形成了各自的价值。对此,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觉得上述佛 教文化的种种缺陷虽然是明显存在的,但却并非孤立存在的,而往往是与它的积极因素 并存共生的。佛教文化的确竭力强调人生的苦难和虚无,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其实恰 恰包含着启发人们更为轻松、更为洒脱地面向生活的积极意念,而并非绝对消极地指向 死灭。认同苦难不等于被苦难吞没。在认同苦难的过程中享受人生,这正是佛教文化的 妙处。而许地山等人的妙处则在于他们领悟了这一点。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哲学具有 浓郁的思辨色彩,苦与乐、生与死、虚与实,往往是糅于一体而并非割裂、更非对立的 。对佛教文化的完整体悟是许地山等现代作家在思考、吸取宗教文化方面的真正价值。 而对宗教文化整体理解的损伤则会损害这种思考的价值。我认为,过于强调许地山后期 创作克服了前期的消沉低落等等,不仅是不确切的,而且无助于阐明他在吸收宗教文化 方面的真正价值,以及他创作本身的真正价值。事实上,并非许地山等人对佛教文化的 某些消极因素有了多大的改造,而是佛教文化本身的积极因素在引发他们的正确思考。 因此,许地山等人在认同苦难、表现苦难的同时,也积极探求摆脱苦难、超越苦难的人 生之道。许地山不仅把“生本不乐”作为一种坚韧、柔忍的人格修炼,而且在他笔下那 些最终能把握命运、战胜命运的人物形象恰恰是那些看起来性情柔弱、顺从命运的人, 这其中不能不使人感到对“生本不乐”思想的积极理解的作用。“生本不乐”不只是对 苦难命运消极的顺从,它还包含着对苦难命运的积极的怀疑和否定,正如茅盾曾说过的 :“他的‘彻底’就是他的怀疑的根。”[10]许地山不仅描画出了不可捉摸的命运之网 ,同时也构造了无可回避的补网哲学。他在《缀网劳蛛》中说,尽管谁也“不晓得那网 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但“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 自然罢了”。对苦难的认同和超越在这里完满地融成了一体。所以那种指认佛教的多苦 观“使许地山对人生苦难看得过于严重,以至认为人生除了在梦中的那‘几小时’之外 ,几无乐趣可言”,而“这种过于悲观消极的思想,使他看不到摆脱苦难的希望,更看 不到人生还有光明积极的一面”的看法[9],不仅过于强调了许地山认同苦难的一面, 对其超越苦难的探求认识不足,更重要的是对佛教多苦观本身的积极意义也缺乏应有的 认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省和沉思的问题的根本。
收稿日期:2003-04-08
标签:空山灵雨论文; 许地山论文; 散文论文; 野草论文; 画梦录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佛教文化论文; 缀网劳蛛论文;
